从接受到求真
——关于《德国精神的向度变型》中的主体性
□叶 瑶
【导 读】叶隽在《德国精神的向度变型》中考察了以歌德、席勒、尼采为代表的德国文学,如何通过身处侨易时空中的近代留洋学人在国内获得接受与传播,以及其在此过程中呈现的向度变型,后者又关乎文化交流中的主体原则与求真原则。本人在肯定接受者作为主体的基础上,拟对叶著提出的“求真”问题做一些辨析。
“西学之名,不始于晚清,晚明已有此词”[1]。但西学之大传播,肇兴在晚清,贯穿民国,起伏兴衰,延绵至今。惯常上,学界把这次大传播过程统称为“西学东渐”,并认为其经历了先器物、后制度、再学术的顺序。“西学东渐”一词虽客观描绘了近代以降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的主要形态,但一方面并未反映全部历史事实,另一方面还暗示着“西”为主体、强势输入,“东”为客体、被动接受的不平等结构,以致在接受者一方激起“文化融合之名掩盖文化殖民之实”的反应,因此被有些学者认为有失偏颇,应正名为“西学中取”[2],重新认识“中”方引进西学的主动姿态,以体现“主位在我”,凸显“我”的主体地位与意向性目光。从晚清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始,如此之“我”便日益壮大,其中最能代表“中取”姿态的非留学生群体莫属。叶隽先生在其著作《德国精神的向度变型——以尼采、歌德、席勒的现代中国接受为中心》中(以下称“叶著”)考察不同时空、迥异境遇中的近代留洋学人如何接受以歌德、席勒、尼采为代表的德国文学,推动其传播,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国人本身,可谓呼应了“东渐”向“中取”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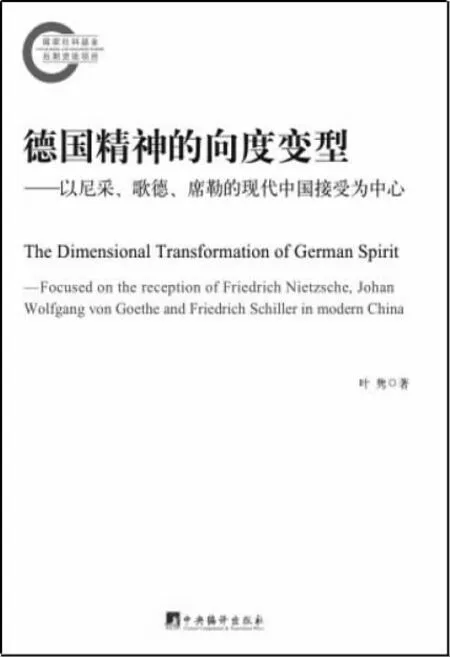
叶著就研究范畴而言,属于比较文学领域的影响研究。影响研究旨在实证性地探明不同民族或国家的文学之间或单向,或交互,或复杂的影响关系,它要呈现的不是文学本身的比较,而是文学史层面上的相互勾连,即在世界各种文学系统之间发现彼此交流的事实,进而建立起网络结构的文学关系史。“西学东渐”无疑正是中西文化之间不断深化交往交流关系的历史,而叶著从中所择取的“德诗东渐”关注的正是德国文学的在华传播及其对近现代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不过,叶著虽将自身归入影响研究的范围,但其设定的目标在于“深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人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收到(德诗)影响,并将其运化到自身的创作实践中”[3]7。这意味着叶著并不限于在“创作实践”中确定“德诗”之影响的事实性存在,更要根据影响程度的深浅,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人物”之间做出区分,另一方面还要基于这种区分,探究影响的具体发生方式与实际经过。如此设定,使得叶著首先要面对“是谁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促成了影响”这一问题,也就是“谁为主体”的问题。
根据影响的传递路径,影响研究可细分为基于接受者的渊源学、基于传递者的媒介学和基于放送者的流传学。[4]叶著大致上将接受者与传递者合并论述,认为他们是受到影响的一方,称为“受者”;把放送者则区分为“诗人巨像”与“文学镜像”,也就是作家与作品,认为它们是有着规定性力量的原型,即“授者”。对于严格的影响研究而言,谁为主体并非其关注的重点,因为任何主体最终都只是文学关系网络上的一处节点,比如,接受者无非是影响传递链上的一端,是影响之事实最终汇集并显现出来的地方。叶著有所不同,它期待通过代表性的个案,还原影响之发生现场,展示经由不同类型的受者而达致的影响的诸般可能性,继而主张“向度变型”作为可能性之一的优越性。“向度变型”是指“由授者、受者的共谋而达致的一种创造性转化”[3]9,但其中关键在于“受者主体有意识地本土化、消化和创化”[3]8,叶著明显传达出为受者确立主体地位的冲动,试图表明所谓影响乃是经过受者过滤甚至加工的影响。具体到“德诗东渐”而言,叶著意在为其描绘出一幅错落有别的“中取”光谱图。当然,鉴于历史的不可重现,这幅图不可能真实如初、面面俱到,只能展现经过归纳处理的类型化受者,但他们不再是影响关系网络上的节点而已,而是积极主动的主体,乃至于代表着“民族文化主体”[3]7。这番强调,展露了叶著与接受美学理论的亲缘,这一点亦见证于它最后的定位:“一种有选择的德国诗人的中国接受史。”[3]159
接受美学的核心特征在于把读者置于文学文本之理解与阐释的中心地位,它拒绝传统文论所主张的文本具有确定的、由作者给定的真义,转而提出“任何文学(文本)都具有未定性,都不是决定性的或自足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多层面的未完成的图式结构。……意义的实现则要靠读者通过阅读对之具体化”[5]4。换言之,作家虽是文学作品的创造者,但并不因此而拥有阐释其意义的真理性地位;文学作品带来怎样的意义,是由读者在“期待视野”中具体决定的。接受美学建立了“文本—读者”二元结构,读者虽为接受者,却拥有强势的主体地位,这显然为叶著彰显“受者”之主体性提供了理论支撑。此外,叶著言其关注重点是引进异质文化资源时“接受维度的变形问题”[3]164——前述“影响的诸般可能性”,也可借由接受美学的“期待视野”得到更好理解。后者一般被看作“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5]6,具体而言,是指“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6]。正是由于先在期待结构的存在,读者才能在面对文本时“翻身做主”,他的主体性才不至于空洞,而是充满内容。异质文化在被接受的过程中出现变形,便是因为别国的“受者”作为主体有着不一样的期待结构或期待系统,这一点很明显地反映在叶著归纳的“致用”意识中。
叶著在论述清末到民国的尼采之在华接受时,区分了留日学人与留德学人对尼采思想的不同关注点,但也指出他们同样的让异国文化资源“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国人初识尼采,始于留日学人。1902年最早在《新民丛刊》上介绍尼采的梁启超,当时正流亡日本,《新民丛刊》也是在横滨创办、在日本发行的刊物;最早从学理上对尼采展开论述的王国维“很有可能从指导他哲学研究的老师藤田丰八那里,受到日本学术界对尼采理解方式的影响”[7],认为尼采的学说是“绝对之个人主义”,“欲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8]还有翻译过《苏鲁支语录》序言的鲁迅,“可能是1902年至1903年,他在东京弘文学院时开始对尼采发生兴趣的”[8]。彼时,日本国内因脱亚入欧正遭受文化上的混乱与危机,而尼采成为部分思想界人士开展文化批判的工具。这种接受方式无疑影响了留日学人,但促使后者响应如此“接受”的,更因其契合了当时中国试图从“打倒孔家店”、清除礼教羁绊的角度来解决民族发展危机的“期待”,因此,当第一波尼采热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对他的推崇亦集中在他对奴隶道德的批判、对正统伦理的反对、对一切价值的重估上。比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借尼采对于主奴道德的区分要求“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并指明儒家的“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胡适说尼采“对于传统的道德宗教,下了很无忌惮的批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确有很大的破坏功劳”[9]158;鲁迅也说尼采“张大个人之人格”,“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以抨击扫荡焉”。[10]
留德学人同样有强烈的致用期待。留德潮出现较晚,要待20世纪30年代才迎来一波高峰。30年代恰是日本逐步扩大侵华范围、中国到了民族存亡系于一线之际,此时的留德学人较之留日学人,在接受尼采时的最大不同是更加注重“权力意志”与“超人”学说。关注点的
改变虽与德国本土对尼采哲学的接受变化脱不了关系——彼时正值现代法西斯主义兴起,尼采哲学被德国纳粹党改造为他们的思想先声与官方代言,但更重要的是如叶著指出,这种“改造”之所以在中国获得留德学人陈铨及其战国策派的积极回响,皆因后者想“借用德国的思想文化先哲之精神来激发民族意志”[3]69。所谓民族意志,在现实层面上自然是指全民族一致抗战到底的意志。战国策派认为30年代整个世界局势就是“中国战国时代的重演:一方面是强国对强国的决斗,另一方面是强国对弱国的吞并”[11]23-29。逢如此时代,“要存在下去,只有靠力,必须学习‘力’最强的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11]。在陈铨等人的眼中,这里的“性格和思想”无疑是尼采。他们期待把尼采作为“立人”与“立国”的“第一锻造者”,认为尼采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把国家看得非常重要,到紧要的关头,都主张牺牲个人,来维持国家的生存”[12]27-33,尽管尼采曾激烈批判俾斯麦治下的德意志帝国;认为尼采是元首至上主义者,“最反对民治主义,他理想的社会,是天才的社会,是超人的社会”[12],尽管尼采的“超人”并非强人,而是强调人必须不断地“超越”自己,不断地“创造”;认为遭受侵略的中国理应“接受尼采的‘主人道德’,来作为我们民族人格锻炼的目标”[9]483,甚至于认为尼采主张通过战争来实现向超人的进化,尽管尼采的“主人—奴隶道德”其实应当置于基督教伦理批判的框架内去理解,所谓的“战争”亦应发生在该框架之内。在战国策派的期待中,尼采似乎坐实了法西斯主义哲学家的头衔。

致用式的期待与接受,对于授者而言,极容易致其失真,叶著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尼采这个例子上,它援引其他论者指出:“尼采作为一个现代性思想家的形象未被中国知识界认真而充分地刻画出来。”“作为其深层支持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理论未及从学理上建树性地开拓过。”[13]尼采并非孤例,相同的失真亦出现在歌德与席勒身上。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冯至对于歌德之《浮士德》的接受,他在牵头编写《德国文学简史》时宣告“《浮士德》是西欧三百年历史的总结,是资产阶级中进步思想的顶峰……反映了明朗的、进步的、科学的势力和阴暗的、反动的、神秘的力量的斗争”[14]359,歌德要“通过浮士德这个人物的发展体现出人是怎样摆脱开中世纪的蒙昧状况,探寻新的道路,跟一切的困难和障碍搏斗,克服了内在的和外在的矛盾,最后走向胜利”[14]352,用魔鬼这个形象来“对于当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也通过魔鬼揭开资本主义的罪恶”[14]358。叶著指出冯至的这番论述与其在新中国成立前对《浮士德》的观点可谓大相径庭,首要原因或在于时代语境的转变。当知识精英集体左转,思想意识“马列化”,冯至亦难避免,何况他本就属于“自觉向左转的学者”[3]97,自表“在人民的面前要洗刷掉一切知识分子狭窄的习性”[15]342,要“自觉地在自己的研究中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歌德”[15]。如此做法,也可看作由致用意识主导的期待引发的一种接受。
如前述,叶著的目标是考察“德诗”对“我”的影响程度,其落实方法则是比较不同受者之间的接受维度,或曰授者的不同变形程度,归结而言都与期待视野有关。致用式的接受让授者的变形达到了失真的程度,其中虽充分体现着受者的主体原则,实现了受者的期待,但并未得到叶著的赞同,因其没有走向“向度变型”。那么,“受者”与“授者”该如何“共谋”以达到“向度变型”式的接受或变形呢?叶著为此引入“原相变形”作为比较,即“一种相对自然的……由原来的授者群体的本来状态而产生的变形情况”[3]8,也可理解为受者对授者的模仿,对之全盘接收。叶著认为“原相变形”在逻辑上要先于“向度变型”,是后者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必经阶段。至此,可看到叶著中出现了三种接受维度,或曰三种变形情况:致用式的、原相变形与向度变型。三者的关系在书中缺少明确的说明,但可以推断得知:致用式的接受中,授者变形最多,受者之主体性最强,对自身的期待视野最是坚持;原相变形中,受者是模仿者,若仍然视其为主体,那么它的主体性显然最弱,授者之变形可以忽略期待视野的干扰;向度变型则处于上述两者的平衡点,它一方面要肯定“授者原相的规定性因素”[3],注重“其提供资源的力度、角度、多元与否”[3]98,另一方面强调受者的主体原则“不是毫无疑义的‘以我为主’,而是应当‘求真、求善、求美’……以求真为最基础之原则…… 行之久远的‘元原则’”[3]174。因此,在向度变型中,受者在发挥主体作用时是有所限制的,既要保持原相的不失真,又要顾及自身的期待,既要提防被致用式的期待所误导,又要有所创新地达到授者的变形。
为阐明向度变型,可用叶著对冯至的论述为例。叶著评价冯至大体上走的是“一条孤独的、属于自己存在之思的道路”[3]69。因此,冯至虽与陈铨一同留德,专业相同,经历相近,交往亦频,但他关于尼采的看法与之悬殊甚巨。冯至说尼采“绝不是偏狭的国家主义者,更不是侵略的倡导者,所谓‘超人’,不过是他对于人类的憧憬,他曾经颂扬战争,是觉得人生必须奋斗”[16]。他还明确指出纳粹党对于尼采乃是利用关系,遮蔽了尼采思想的原本面目。叶著认为联系到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以及全国一致的“救亡”热潮,冯至对尼采的理解可谓相当客观和理性,是“在非常专业的层面去审视尼采的”[3]34。
冯至在新中国成立前对于《浮士德》的接受也是一例。冯至自述留德期间曾有过“数月以来专心歌德”[17]的阅读经历,但他投身歌德研究则始于1940年前后任教西南联合大学期间,且上手便是《浮士德》。他自述当时读《浮士德》,是“把它看作是一部肯定精神与否定精神斗争的历史”[18]378。魔鬼梅菲斯特“是个虚无主义者,一种揄扬否定力量的精神,瓦解或摧毁所有肯定的东西”[19],而浮士德作为梅菲斯特的反题,具有“肯定能力”,一方面受魔鬼的诱惑,另一方面又与之缠斗,“在百岁高龄虽不免于死亡,最后还是宣告了虚无主义者魔鬼的失败”[18]378,同时实现了自身的蜕变。比起新中国成立后冯至论《浮士德》,此时的冯至显然更有“自己之思”。叶著分析,冯至之所以能从一种精神斗争的角度解读浮士德,首先可能与他的“夫子自喻”有关,彼时正值抗日战争艰难之际,对时局有感者,内心难免冲突与煎熬,冯至需“在艰难的环境中求生存,而又不溟灭对正义的向往和追求”[3]74,而浮士德给予了他突破精神困境的榜样。其次与冯至对歌德的喜爱相关,他“对歌德的重视不全是出于学术眼光,更是由于心灵契合的‘喜爱之情’”[20],并由这种个人之爱生出“只求没有曲解和误解”[18]376的存志,从而消解了“功利致用”的期待,而是展露自己真实的解读。再者是冯至对歌德的蜕变论思想深感认同,能从蜕变的角度去看浮士德。最后是冯至“更着力于从文本的细读入手……着手的往往是比较小的口子……而且参阅了相关资料乃至研究专著”[3]74。他关于《浮士德》的立论是细致且有所凭据的,“以透析文本内涵为主旨的研究策略,引经据典、细密深入的论证方式,显然得益于其留德期间系统的德国语文学训练”[20]。简言之,他的接受半露出德国面相。[19]266-289新中国成立后的冯至否定自己,自认新中国成立前“是用歌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看待歌德这个人和他的创作的”[21],是不正确的,但叶著恰恰又以向度变型否定了冯至对自己的否定。
基于对冯至的分析,叶著进一步提出了文化交流中的接受者一方应具备的四大因素:“一是受者本身的学术积淀与研究深度;二是受者本土关怀的通融维度及对当下问题发掘的敏锐度;三是与时代语境及其知识精英认知层次的互动维度;四是学者独立品格的自觉意识与坚持。”[3]95这些因素其实也是对向度变型中受者之主体性的细化说明,是为期待视野筑一圈边墙。除此以外,叶著虽未明言,却主张这些因素更应始终受到“求真原则”的统领。唯此,致用式的接受与向度变型之间才能有所区分,因为以上诸因素,其实同样可以出现在致用式的接受中,比如,叶著中出现的李石岑。后者在民国初期连出多篇文章推介尼采,更在刊物上组织过“尼采专号”,他对尼采思想的研究“不但具有一般知识精英的接受热情,而且也有哲学家的纯思探究”[3]27。叶著评其已做到“尽可能客观地还原尼采在历史语境中的位置及其思想本色,通过学理的探究而寻求其本义”[3]。饶是如此,李石岑却把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看作了彻底的实用主义学说,试图借之批判国人“既乏进取之勇气,复少创造之能力,乃徒以卑屈之懦性,进而为习惯上之顺氓”[9]83的脾性。从“求其本义”到“尼采则实用主义之骁将也”[9]62,李石岑的例子提示了致用式接受与向度变型之间并非决然的泾渭分明。
行文至此,可看到叶著其实为“向度变型”规定了两个原则:主体原则与求真原则,且前者应当以后者为先。当然,求真也是受者作为主体而展开的求真,是对受者可能滥用主体原则的防范,不是取消或贬低受者的主体性。用求真原则来约束与调和主体原则,其实也说明叶著意识到了接受美学理论的一大弱点,试图加以修补。接受美学以“期待视野”为核心方法论,主张读者总是以其在阅读前便已形成的“先在结构”去把握任何文本,这“使文本在理论上成为可有可无、随意阐释的东西,这势必使意义走向‘相对主义’和‘无政府状态’”[22]82-93,最终阻碍公共层面上的对话。对于叶著考察的跨文化交流而言,这种负面效应尤甚。来自异文化的读者,往往带着差异甚大的期待视野,如其任凭自己的期待主导对文本的阅读与阐释,最终造就的只能是“自说自话”,丢失了文化交流的对话意义。
期待视野内含的这种隐忧,较早便引起了关注与批判,接受理论本身也对之有所警觉,并试图加以调整,其方式是强调读者阅读过程中期待视野的可变性特征,即“期待便在阅读过程中……被完整地保持下去,或被改变、重新定向,或讽刺性地获得实现”[5]29。换言之,读者的主体性不仅仅基于先在的期待结构,还包含在阅读过程中对这种结构的偏离与改变。有论者称之为“体验建构”,它是使先在结构“现实化、清晰化,以及动态变化和开放吸纳”的过程,与先在结构“共同构成了期待视野的现实生成方式”[22]。这种对于阅读过程的强调,似乎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但其实未能回答:既然阅读意味着先在期待结构的现实化,那么与之不一样的体验建构因何而起?体验建构是否一定造成先在结构的变化?体验建构着眼于读者作为个体的差异,这同样会导致意义的分散化,那它何以避免“自说自话”?
叶著提出的求真原则,类似于体验建构强调阅读过程中读者的更多可能性,也是把目光转向了受者在期待视野之外还具有的内在能动性。但有所不同的是,体验建构仍着眼于从接受美学的理论内部对期待视野进行调整,而求真原则其实意味着要在接受美学理论之外来为上述隐忧寻找解决之策,因为求真必然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何为真?
如前述,向度变型以求真原则限制了受者的主体性,但仍充分肯定其主体地位,这未超出接受美学关于接受的理解。然而紧要的是,向度变型是将求真与授者原型的规制作用关联起来的,换言之,“真”并不源于受者,而是来自授者。从叶著用原型、原相、本义等词语来形容授者便可看出,它不认为“真”是可以脱离授者的参与而谈论的,它要恢复作家与作品在“意义之实现”上的主动权,要把“真义”还给文本。这固然有助于文本意义的稳定,为公共对话提供保障,但如此一来,叶著与接受美学关于“真”的看法已大大相悖。接受理论是一种后现代主义文论,其“期待视野方法论的提出,本身就是要动摇文本中心主义的文本坚固性”[22],破除西方传统文论中的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接受美学不会认同唯一之真或所谓本义的存在,它若承认“真”的存在,那也必然是多元化的“真”,且必然来自身怀期待视野的读者一方。当叶著把“真”送归授者,其实就在接受美学之外为期待视野重新配了对手,而且对于读者而言,它们都是先在的。
对于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而言,“何为真”又更为复杂一些,因其多了一层跨文化的维度。如果认可“真”来自授者,认可它是作者本身给作品注入的意义,那么对于异文化的受者而言,作品之本国读者以其期待视野给出的阐释要做何处理?是将其归入授者的原相之中,还是视其为与自己一样的接受者?这样的疑问似乎已无法从接受美学那里寻求解答,叶著由此引入侨易学理论。后者其实放弃了“文本—读者”的二元划分,也不纠结于期待视野的归属问题,转而以文化为分界,并提出一种二元三维结构。就“德诗东渐”而言,中德文化无疑构成二元对立,而留学精英作为受者,乃是两者之间的“‘流力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如此就构成了三维结构,是个稳定性结构”[23]。这个“三维”并非与“二元”平起平坐的第三“元”,而是两者凭借“流力因素”打开的“交域”,也就是受者与授者共谋而达致的向度变型。“真”既不为这“一元”独占,也不是那“一元”私有,而在“交域”之中。由此,侨易学又部分取消了授者对于“真”的主权,它虽认定向度变型是走向“真”的路径,但“变型”至何种程度可谓之“真”,似乎仍旧面目不清。
注释
[1]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
[2]张志扬.“唯一的”、“最好的”,还是“独立互补的”?——“西学东渐”再检讨[J].现代哲学,2007(2):39-45.
[3]叶隽.德国精神的向度变型——以尼采、歌德、席勒的现代中国接受为中心[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4]曹顺庆.比较文学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第二章.
[5][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6]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61.
[7][韩]李珠鲁.鲁迅与近代思想——围绕尼采思想的接受[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1):167-183.
[8]王国维.叔本华与尼采[A].静庵文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9]成芳.我看尼采——中国学者论尼采(1949年前)[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0]鲁迅.文化偏至论[A].鲁迅全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9.
[11]王元明.20世纪尼采哲学在中国的盛衰[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
[12]陈铨.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J].战国策,1940(6).
[13]金慧敏,薛晓源.尼采与中国现代性[A].金慧敏,薛晓源.评说“超人”:尼采在中国的百年解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9.
[14]冯至.德国文学简史[A].冯至全集(第七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15]冯至.写于文代会开会前[A].冯至全集(第五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342.
[16]冯至.德国民族性的分裂及其可能的演变[A].冯至全集(第五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281.
[17]冯至.书信、自传、年谱[A].冯至全集(第十二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37.
[18]冯至.“论歌德”的回顾、说明和补充[A].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C].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
[19][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冯至与歌德的《浮士德》——从靡非斯托非勒斯到海伦[J].杨治宜译.国际汉学,2005(1).
[20]胡蔚.新中国六十年歌德戏剧研究[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4(6).
[21]严宝瑜.冯至的歌德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0(4):65-72.
[22]陈长利.期待视野——接受美学方法论的反思与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4).
[23]叶隽.侨易学的观念[J].教育学报,2011,7(2):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