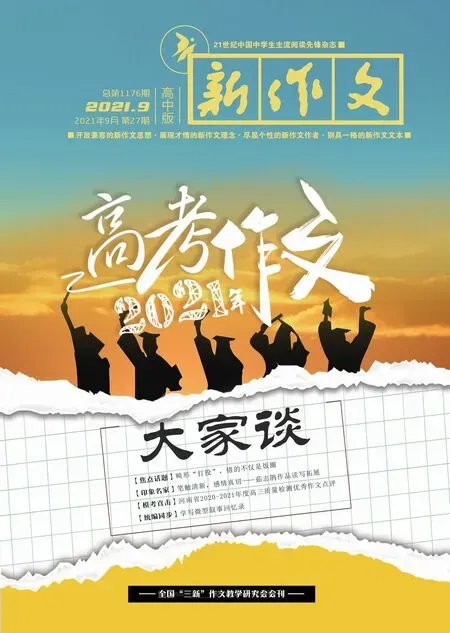笔触清新感情真切
——茹志鹃作品读写拓展
茹志鹃(1925—1998),当代著名女作家,代表作《百合花》,曾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茹志鹃长于写抒情心理小说。表现战争题材,以空灵精致的笔触展示军民间的深情和厚谊;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生活,那柔美纤细的笔触常游弋在劳动女性的心灵世界,显示人物内心的热切和性格的贤淑。

原文摘录一
静静的产院
◎茹志鹃
谭婶婶跨出房门,心里就是个老大的不快,原来荷妹已把两个产妇掇弄起来,站在房里做操呢!三个人嘻嘻哈哈,又弯腰又踢腿。荷妹喊着“二二三四”,两个产妇一边做操一边笑,三个人不断地嘻嘻哈哈。
本来安安静静的产院,现在好像有一股什么风闯了进来,把一切都搅乱了。
……
谭婶婶回到产院,就愣住了。细心收拾过的办公室,粉刷得雪白的产房,现在却是满地的木屑竹片。还有,还有那雪白的墙上,已打了水桶大的一个洞,荷妹在洞边接竹管,那两个产妇也在递这拿那地帮忙。她们一见谭婶婶回来,立即欢呼起来:“谭婶婶快来看自来水!”
“自来水?”谭婶婶扶起一张凳子坐下,她觉得向她涌来的东西太多,她累极了。
“婶婶,水自己流进来不好么?”
“……好!”水自己流进来怎么不好!当然好。不过谭婶婶不能理解,荷妹为什么要这样着急地去弄它,好像是没自来水就不能生活似的,便开口说道:
“二丫头,乡里当然不像城里那么方便,我们什么都学城里,肩膀也怕碰扁担了,这可不好。”
“对!”荷妹收敛起笑容,认真地说道,“不过婶婶,乡下不是永远都是乡下,我们现在可以做到有自来水不去做,还是肩膀碰扁担,这可不是光荣,这是落后……”
阿玲心直口快地说道:“能做的不做,这不是落后?这样一来,不是又省事,又卫生,又科学?回去我也推广去。”
“是啊!”谭婶婶答应着,心里猛地动了一下,这些话好熟悉啊!自己曾经说过的,三年前头,推广新法接生的时候,自己对许多人说过“又卫生,又科学”,其中对潘奶奶说得最多。
荷妹说:“婶婶你知道我们现在往前面奔,我们现在奔的是共产主义啊!你看,我们现在有电了,我们还要想办法来利用电,电疗,电打针,早产儿用电暖箱……”
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风暴席卷而来,仿佛滔天的巨浪向前扑来,它们气势磅礴,排山倒海地向前推,向前涌。谭婶婶忽然非常清楚地理解了三年前潘奶奶的心情,那时候为什么潘奶奶对她跳脚,又对她诉苦,为什么有时候又苦了脸,谭婶婶现在知道,那是她恐慌,却又不肯承认自己落在时代的后面。
(选自《人民文学》一九六零年六月,有删改)
写作得法之人物素描:
小说取材以小见大,借发生在农村产院中一个时间段里的生活小事,展现了主人公谭婶婶内心新旧思想的矛盾斗争。谭婶婶三年前推广新法接生,有强烈的自豪感。但如今她满足现状、不愿改变、不求进步,看不惯荷妹等人的求新举动,产生了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同时,小说鼓励安于现状的人们追求新生活,显示出社会的变革与时代的进步。
原文摘录二
路标
◎茹志鹃
没有,没有,没有石子,没有草棍,没有树枝,更没有白粉,没有任何一点路标的痕迹。
没有人,没有一个人。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地,在这灰蒙蒙的天地当中,只有自己,站在一条灰蒙蒙的路上。
伍原感觉在这灰蒙蒙的后面,有什么东西活动了起来,无数隐蔽的眼睛,冰冷的枪口,潜伏的危机。但是,往哪里走呢?
伍原狠狠地跺了一脚,听天由命地坐到地上,泪水便像决了的堤。
这是什么?好像冥冥中有神,不,鬼!鬼火?
远远的,贴在地上,就那么一小点,一小点黄黄的光,不飘忽,不闪烁。伍原不敢眨眼,屏息静气,站起身,啊!一站起,它便像钻入了地下。伍原
赶紧趴下。在呢!荧荧的,黄黄的,小小的一点。这如豆的一小点光。
世界再不是死的,自己再不是孤独的,部队就在前面。
有人了!找到人了!我到底找到老乡啦!“老乡!”伍原迫不及待地叫了一声。这一声叫,却不防把自己的眼泪叫得掉了下来。可是窝棚里静静的,没有任何反应。里面确确实实有一个人,一个老乡。
“老乡!”伍原稍稍放大了声音。那人依然低了头朝一个口袋里搓着玉米穗。看来,是一个聋子。伍原爬进棚去,正伸手想拉他一把,突然之间这聋子像背后长着触角,敏捷地跳起,转身想跑。伍原两臂一伸,把聋子的腿抱住了。那个人也不做声和伍原扭打起来。伍原不肯还手,一边抵挡着,一边死死抱住不放。哑巴“唔唔”地叫着,挣出手来进行袭击。
伍原绝望了,这个人不但是聋子,还是个哑巴。伍原捉住哑巴的一只手,把它贴到自己帽子上,想让他明白,这不是国民党的大盖帽,这是八路军的帽子。可是哑巴并不理解,利用这个机会,迅速灵活地向伍原脸上猛击几下。
急、痛、头昏,眼前金星直冒,浑身大汗淋漓,伍原不知如何才能摆脱这一窘境。
忽然,伍原觉得有只手,轻轻地摸索着自己的头,自己的帽子,自己的脸颊。哑巴“哇哇”地大叫起来,挣脱了出来,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伍原。猛然,他似乎省悟了什么,双手直向棚外挥动,又急急地拿起灯,拉着伍原爬出窝棚。他一手擎着灯,一手直指东北方向,然后做了个正步走的姿势,一双眼睛急切地盯着伍原。伍原点头,然后敬礼,然后回身走去。
伍原走上大路,回头望望,那一星豆子似的灯光,不飘忽,不移动,像是镶嵌在夜空当中。
(选自《茹志鹃小说选》,江苏文艺出版社,有删改)
写作得法之精雕细磨:
选段讲述了一名迷失方向的战士在老乡的指引下追赶部队的故事。在写作上,本文有以下特点值得借鉴:
1.精雕多处景物,为故事开展提供了背景,突出人物无助的心理状态。一小点光烘托了人物从迷茫到有希望的具体变化,展现出看到灯光和夜空后的坚定信念。
2.细磨外在细节,刻画人物内在特征。如写老乡,“一手擎着灯,一手直指东北方向”。
原文摘录三
故乡情
◎茹志鹃
小路引我走过一个小村尾,一团绿雾似的小竹园,掩映着一排白灰墙乌板门。一个五六岁的女孩,不知哪里受了委屈来,抹着眼睛。裤脚吊到小腿上,散了半边的辫子,遮着她有一点点脏的半边红脸蛋,独自寂寞地走在竹后面。我猜,在那紧闭着的黑板门中,总有一扇是她家的。
啊!家,是了,是家。哦,故乡。没有我的家的故乡!从前,当我也像这女孩这么大的时候,你不曾好待我过。记得么,你让我走在那矻噔噔的石板路的深巷里,两边偌高的风火墙把我隔在外面,连想象的翅膀都无法飞越。那幼稚的想象,无非只是想到里面有一张眠床,有一碗热饭,有一点点不那么冷的暖意。
没有我的“窝”的故乡啊!你未曾好好待我过,然而却在梦中无数次地使我萦回。我梦见故乡的天,故乡的地,故乡的山,故乡的水。因为,你给我的就是这些;因为,我把这些就当作我的家。我的家啊,总是席卷了所有的荒漠、贫瘠,顶着一片黄苍苍的穹苍,四周围垂着灰蒙蒙的暮霭,当中缀着一弯淡淡的孤月,反复地出现在我的梦里。多么冷啊!你冰醒了我少年时代的梦。
我也做过好的梦。那是在后来,在那冷的北方,我梦见了温暖的故乡,梦见一个青山郁郁、绿水悠悠的故乡。那里有白米饭乌干菜,有自家的冬笋,有野生的蘑菇,有鲜红的杨梅,有金黄的蜜橘,有青布蓝衫的姑娘,有母亲般的温柔关注。多么好的故乡,多么美的梦啊!
绕过了小村尾,石板路接着石拱桥。傍河的小镇,沿河伸开了一条街道。豆腐担连着鲜鱼摊,担儿前的人多,摊儿前的人少。点心店里热气腾腾,倒并不客满,布店柜台边却站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富裕的人置冬装,更富裕的人在买花的确良。立冬刚过,有人已在筹备添夏天的衣裳。
哦!于是在那好的梦的前面,我又看见那些盖着花手帕的小竹篮,那些穿着布鞋儿的匆匆脚步……
石拱桥连着石板路,石板路带我回到老友家的村头,看见路上相遇过的那些姑娘,已换下干净的新布鞋,脱下了山青水绿的新衣裳,正蹲在河埠头洗菜,正“啰啰”地唤着小鸡小鸭……我赶紧回到了不是我家的“家”里,把鱼放进淡水缸里,干搁了两个钟头的鲫鱼,居然又悠悠地游了起来。
故乡,这就是我实实在在的故乡。
(选自《惜花人已去》,上海文艺出版社,有删改)
写作得法之情感动人:
文字扑面而来的,是淡雅的画,是浓烈的情。作者用女性的细腻笔触,以“我”的所见所闻为线索,用“梦”这个介乎于幻觉与现实之间的状态来联系这一幅幅画面与一重重情怀,描绘着故乡多彩多姿的风貌,表达“我”对心灵深处的精神家园的依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