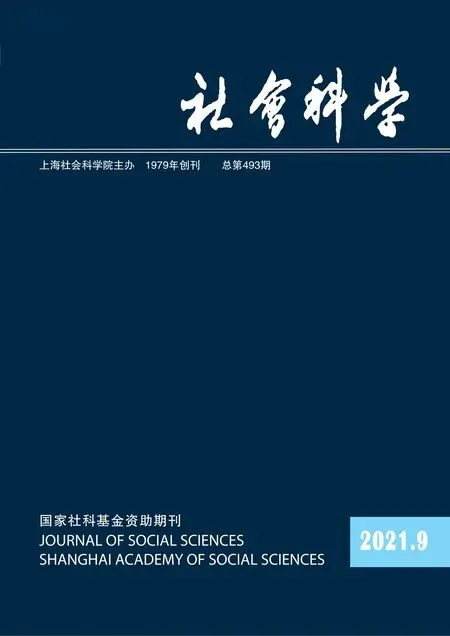数字货币:从国家监管到全球治理*
陈伟光 明元鹏
引 言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全球正在呈现出数字化内嵌式的变革,传统经济社会向数字经济社会演变,数字货币在数字化浪潮推动下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数字货币就发行主体不同,分为私人数字货币和主权数字货币。私人数字货币是货币市场自发演化的产物,由货币当局以外的市场主体发行,不具备法偿性。根据赋值方式不同,私人数字货币分为两类:一类是依赖区块链系统并在该系统内产生和使用,又称加密货币,如比特币、以太坊等;另一类是在区块链上发行、运营并受链外资产支持,又称稳定币,如Libra、USDT等。主权数字货币是以国家信用为背书的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具有法偿性,全球80%的央行正在推行试点,(1)“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Towards a Global Approach”, https://www.finextra.com/blogposting/18450/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ies-towards-a-global-approach.如中国央行推行试点的DC/EP、新加坡央行主导的Ubin项目等。据cryptocurrencies网站显示,截至2021年6月26日,全球交易的私人数字货币种类共计5460种,在全球20445个交易平台上24小时不间断交易,交易总额达1.29万亿美元,每天交易额超过935亿美元,其中,比特币交易份额占整个数字货币市场的76%以上(2)CoinMarketCap, “Global Cryptocurrency Market Charts”, https://coinmarketcap.com/charts/.,头部效应显著。(3)“头部效应”指在一个领域或行业中,第一名拥有更多的资源,获得更多的关注,收益越高,发展越快。
与传统货币体系相比,数字货币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重新定义支付、经济活动和用户数据的互动方式,用户不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即可直接进行点对点交易,从而减少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移动商业模式和互联网模式与数字货币的结合,有效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增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以及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4)焦瑾璞、孙天琦、黄亭亭、汪天都:《数字货币与普惠金融发展——理论框架、国际实践与监管体系》,《金融监管研究》2015年第7期。数字货币基于互联网和算法,以超低成本完成货币创造、流通、交易,并且跨国界流动,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经济和信息互联的方式,进而改变货币和支付系统,建立“数字货币区”,使货币与特定数字网络的用户关联起来,而不是将货币与国家关联起来。(5)VOX, “Digital Currency Areas”, CEPR Policy Portal, https://voxeu.org/article/digital-currency-areas.尽管大部分国家对私人数字货币的法律地位未予以明确定位,但其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很多国家根据本国国情和金融环境,出台了相关监管政策。同时,G20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世界经济论坛(WEF)等国际组织,也关注数字货币对全球金融市场和资产流动产生的重大冲击和影响,数字货币全球治理逐步提上议程,预示着数字货币从国家独立监管走向全球治理的合作。
私人数字货币的飞速发展呈现出向法定数字货币拓展的态势。平台机构在技术创新和网络效应的推动下,拥有了非国家货币的发行权,这种私权利对国家发行货币的公权构成了挑战。私人数字货币的兴起更像一个叫醒电话,唤醒中央银行重视法币的稳定价值,中央银行不能忽视数字加密货币这一难以回避的技术浪潮,应重视央行货币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创新。(6)[德] 诺伯特·海林:《新货币战争——数字货币与电子支付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寇瑛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7页。当前,各国央行加快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实验,反映出公权力对私人主体觊觎货币发行权的警惕,(7)许多奇:《从监管走向治理——数字货币规制的全球格局与实践共识》,《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以及对私人数字货币规制和治理的重要性。针对上述议题,本文主要聚焦私人数字货币的治理问题研究,总结国内外数字监管的经验教训,探讨数字货币从国家监管走向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行路径。
一、数字货币风险分析
数字货币的点对点支付可以提升支付效率,网络间交易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匿名性特征可以强化隐私安全,跨国间流动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但其建立在“共识机制”、“去中心化”、分布式账本技术之上,只是由特定密码学与共识算法验证的一连串数字,(8)范一飞:《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依据和架构选择》,《中国金融》2016年第17期。没有内在价值,也无法创造价值。私人部门设计和发行数字货币缺乏国家信用背书,发行目的不是为了便利商品流通,而是为了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数字货币发行后可借助未受限的网络空间跨境自由流动,高风险性凸显。
一是交易风险。交易风险指投资者在数字货币交易中的权利和义务缺乏法律的具体规范,权益得不到保障。其一,数字货币价格泡沫严重。比特币、莱特币、以太坊等数字货币受到全球投资者的追捧,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大的资产泡沫之一。(9)邹传伟:《泡沫与机遇——数字加密货币和区块链金融的九个经济学问题》,《金融会计》2018年第3期。以比特币为例,2017年初,最低价为789美元,2017年底飙升到18674美元,2021年4月16日达到历史最高价59893.45美元,同年6月26日跌至32028.26美元,价格暴涨暴跌,极其不稳定。其二,数字货币在互联网上匿名交易,参与者几乎不受监管,用户资金缺乏安全保障,用户隐私和重要信息容易泄露。其三,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处于自由发展状态,存在虚假宣传、蓄意操纵价格、内部交易、不合规经营等情况,甚至发生平台关闭或经营者携款潜逃,投资者面临巨额损失且维权无门。
二是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指数字货币在发展过程中因内部或外部的不利因素经过长时间积累而未被重视,在某段时间共振,对金融系统造成重大影响。早期数字货币市场价值和规模较小,参与的金融机构极少,对金融系统影响有限。但在金融科技的推动下,数字货币种类不断衍生、交易平台越来越多、交易数额越来越大,甚至更多的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开始持有数字货币。(10)根据世链财经(shilian.com),已有11家纽交所上市公司官宣持有比特币,总量为59.28万个,约占流通比特币的3.2%,参见https://blog.csdn.net/u013239752/article/details/108995486。这使得国家新发行的货币大量进入数字货币领域,带来信贷兴衰和资产价格周期,提升了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是引发系统性危机的因素之一,数字货币为资本跨境流动提供了新渠道。数字货币脱离传统金融系统管辖,降低了国际资本市场中的金融摩擦和交易成本,便于跨境资本流动,使外国资本更容易进入本国市场,而这些跨境资本不经过银行清算和结算,由此导致系统性风险上升。从全球层面来看,数字货币可有效执行跨境转账,绕过传统支付系统管辖,一定程度上会促进资本的流动,使货币政策执行和汇率管理变得复杂,可能会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新来源。(11)“Digital Money Across Borders: Macro-Financial Implications”,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Issues/2020/10/17/Digital-Money-Across-Borders-Macro-Financial-Implications-49823.
三是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指数字货币因供给量限制和交易量变动引发价格剧烈波动,使得市场未能有效运行。一方面,数字货币体系不具备法定货币机制特征,比特币等数字货币总量近乎刚性供给,易造成流动性紧缩。数字货币价格暴涨暴跌背后蕴藏着流动性紧缩的巨大风险。很多稳定币为缓解流动性不足,开启“印钞模式”,据DAppTotal显示,USDT在疫情防控期间增发8次,累计净增发金额达到7.92亿美元。(12)区块链网:《数字货币市场也正面临着严重的流动性紧缺问题》,https://www.qklw.com/blockchain/20200615/92040.html。另一方面,数字货币虽然采用“T+0”交易模式,但换手率低于同期股票市场,与股票市场相比,数字货币流动性严重不足。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不能直接通过法币购买数字货币,要将法币换为泰达币、比特币等一些平台币,通过平台币代购其他数字货币,这导致数字货币流动性管理难度加大,要是兑换商的流动性管理出现问题,持有者无法将数字货币兑换为法币。(13)王信、任哲:《虚拟货币及其监管应对》,《中国金融》2016年第17期。数字货币体系没有承担最后贷款人的公共机构,一旦出现风险事件,兑换商容易遭到挤兑,(14)郭晓敏、陈建奇:《数字货币如何影响国家安全:逻辑、机制及应对》,《财经问题研究》2020年第8期。消费者或投资者面临直接的经济损失。
四是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指某些组织或个人利用数字货币规避现有法规,或通过不合规的行为获取一定的利益。第一,洗钱犯罪。IMF报告曾指出,数字货币体系作为逃避资本管控的渠道,非法资金通过数字货币实现跨国流动,这给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带来挑战。(15)谢平、石午光:《数字货币的风险、监管与政策建议》,《新金融评论》2018年第1期。数字货币革新了洗钱犯罪的行为模式,快速化的支付结算提高了洗钱犯罪的概率,多样化的支付方式为洗钱提供了无形且便利的渠道。(16)巫文勇:《货币数字化场景下洗钱犯罪形态和刑法重构》,《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年第3期。第二,非法融资。首次代币发行(ICO)作为数字发行的主要融资手段,融资过程周期短、成本低。ICO项目发起人和参与者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双方的激励与责任不完全一致,参与者限于技术的专业性,难以对项目具体进展及未来方向有完整、透明的评估和判断,很多ICO最终成为“庞氏骗局”。(17)姚前:《数字货币初探》,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版,第229页。ICO存在骗取财物、组织传销和非法集资的刑事法律风险。(18)王冠:《基于区块链技术ICO行为之刑法规制》,《东方法学》2019年第3期。第三,数据泄露。随着智能设备的普及,个人成为数据信息的载体,数字货币供应商因特定的商业目的,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或交易数据,过度集中的数据面临入侵和泄露的风险,然而,诸多国家的法律和监管机制在这方面尚不明确。(19)欧阳本祺、童云峰:《区块链时代数字货币法律治理的逻辑与限度》,《学术论坛》2021年第1期。
五是技术风险。技术风险指受现有技术水平的限制,数字货币存在无法预见、无法解决的困难。数字货币的技术风险源于区块链系统和货币交易平台两个方面。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密切相关,而区块链本身存在两种技术风险:一是区块链自身技术缺陷的内部风险,如一些未知漏洞、系统不能集中关闭升级、安全漏洞修复困难,一旦51%的算力被掌握即可改写区块链数据等;二是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带来区块链应用的外部风险,如共识机制崩溃、激励机制失灵等。(20)戚学祥:《超越风险: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风险及其治理》,《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数字货币平台风险首先是平台开发中编程结构不完善、编程语言使用不当等原因产生的代码层漏洞,一旦平台被黑客攻击,用户损失无法幸免,个人钱包里的数字资产也会丢失,最后自行承担亏损。据Chainanalysis分析报告,2019年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多的交易所被黑客攻击事件。其次是智能合约的使用导致平台监管功能弱化,智能合约在触发条件下自动执行,但存在程序过程、存储结构和交易顺序等问题。(21)戚学祥:《超越风险: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风险及其治理》,《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一旦合约被执行则无法撤回,或发生安全漏洞时合约自动终止执行,这弱化了平台的监管功能,增加了管理的技术难度。这些技术风险需要长时间、大规模、全方位的实践应用才能确保技术的安全性。
六是挑战主权货币风险。主权货币代表着现代国家的独立和权威,货币垄断支撑政府权力,而数字货币的大规模发行和流通会将这种权力从政府手中拿走,形成一种与国家公权力相对的私权利。政府拥有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并利用此权力发行货币,政府也有权力规定通过哪种物品清偿塌缩发行国币标价的债务。(22)[英]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姚中秋译,海南出版社2020年版,第23页。但在国家监管缺失的情形下,私人数字货币在金融领域夺得一席之地,与主权货币形成竞争,并在数据共享、社会组织管理等方面占据一定的话语权和控制权,届时,社会分层和政治组织形式将会发生改变,传统国家的治理模式将被颠覆。比特币已成为继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卢比之后的第六大“货币”,(23)《比特币成为世界第六大货币》,参见https://www.wwsww.cn/btbwhy/6437.html。随着全球影响力的提升,比特币可能会逐步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使得一些主权货币边缘化,丧失国际地位。数字货币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货币传输的“去中心化”,不可避免地出现金融生态“去政府化”。以Libra为代表的稳定币尝试凭借“共识”创造全球性货币,保留传输记账过程中的“去中心化”“去权威”优势,同时承接传统银行的财政信用,功能更为全面,具备在全世界普遍使用的潜力和公信力。(24)何为、罗勇:《数字货币来了》,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版,第98页。数字货币背后的寡头科技公司一旦具有了公信力,就有了与政府同台竞争的机会和能力,社会公众可能不需要将信用托付国家,依托一个私营组织完全可以通过“共识性机制”满足全球金融支付方面的需求,主权货币所面临的潜在威胁就更大。
综上所述,数字货币存在的诸多风险不可回避。随着时间的推移、场景的变换和技术的更新,数字货币的风险可能会进一步扩散,危害金融安全。面对数字货币演进中不断显现的风险,其已被纳入世界主要国家金融监管议程。
二、数字货币监管的各国实践
数字货币作为技术创新催生的新业态,或将成为新一代金融基础设施,(25)杨东、马扬:《天秤币(Libra)对我国数字货币监管的挑战及其应对》,《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1期。它的出现是对传统金融制度和金融安全的挑战。对所有国家而言,数字货币是新生事物,如何对其实施有效监管、如何平衡数字安全与隐私保护、如何在金融创新和风险防范之间寻求平衡,都是各国政府在制定监管政策时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一)主要国家的监管实践
数字货币监管已成为全球性难题,根据代币网统计,全球257个国家或地区中,132个国家对数字货币发行、交易、流通没有限制,(26)Coin Dance, “Global Bitcoin Political Support & Public Opinion”, https://coin.dance/poli.其余国家将数字货币纳入本国监管体系,制定相应监管政策。各国根据国情和金融市场发展情况,对数字货币监管态度不尽相同,但监管内容和监管框架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主要包括数字货币的定位、发行、交易、税收等方面(见表1)。其中,美国、英国、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监管政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1 全球主要国家数字货币监管政策比较
第一,美国。美国对数字货币的监管实行联邦和州合作的监管模式,采取鼓励发展与监管并举的策略。在联邦层面,监管机构从金融创新角度规制数字货币及其衍生品,例如,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将比特币定义为“可转化的虚拟货币”,规定比特币的“传递业务”要接受《银行安全法》监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称私人数字货币是一种证券产品,比特币的“挖矿”合同属于“投资合同”等。在州层面,各州制定自己的数字货币监管规则,政策独立、多样,尚未形成统一。比如,纽约州率先推出牌照制度,对数字货币从业者实行监管,怀俄明州免除加密数字货币的财产税,亚利桑那州和佐治亚州允许居民使用加密数字货币支付税费等。(27)参见https//news.bitcoin.com/majority-of-us-states-with-stance-on-bitcoin-and-blockchain/?utm_source=OneSignal%20Push&utm_medium=notification&utm_campaign=Push。随着数字货币市场广度和深度的开拓,美国构建灵活的监管体系,SEC在数字货币监管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SEC要求ICO公司必须在证券交易所注册,(28)参见https://www.klgates.com/。发布了“数字资产”投资者合同框架,把数字货币定性为证券。(29)参见https://www.sec.gov/divisions/corpfin/cflegalregpolicy.htm。2019年2月,美国参众两院提交了“区块链促进”法案,明确区块链的产业政策,提出对数字货币加强监管。(30)赵炳昊:《加密数字货币监管的美国经验与中国路径的审视》,《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Libra白皮书发布后,参众两院举办两轮听证会,从Libra的运作机制、治理结构、属性等方面,对其带来的监管问题进行严厉“问询”。2019年底,美国国会一共提出21个与区块链和加密数字货币有关的法案,其中,参议院提出的《加密币2020法案》将加密币分为三大类——加密商品、加密货币、加密证券,并由期货交易委员会、金融执法网络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分别予以监管。(31)参见https://finance.yahoo.com/com/news/expect-cryptocurrency-legislation-2020-1800028179.html。2020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多国央行及私人数字货币竞相布局的背景下,美国收紧对数字货币的监管,美联储、美国货币监理署(OCC)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考虑成立“跨部门冲刺小组”,创建统一的数字货币监管框架。(32)参见https://www.jdfi.com/kx202077.html。
第二,英国。英国对数字货币持开放态度,实施“监管沙盒”。英国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行为管理局(FCA)成立数字货币工作组,管控数字货币风险。(33)朱嘉明、李晓等主编:《数字货币蓝皮书2020》,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页。2015年,英国财政部发布《数字货币政府号召信息反馈》报告,指出英国政府采取“反洗钱法”监管数字货币,同时联合数字货币标准协会及数字货币行业共同制定一个监管框架。(34)付蓉:《数字货币监管的国际经验借鉴和启示》,《金融科技时代》2017年第2期。同年,FCA提出“监管沙盒”模式,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可申请进入“监管沙盒”,申请通过后的数字货币交易所在英国合法存在。英国对ICO活动的监管态度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敏感,未出台具体的监管方案,只发布ICO风险提示,提醒投资者注意ICO活动风险,ICO也不在FCA监管之列。2018年,英国央行表示对数字货币交易所采取与证券交易所相当的管理标准,严厉打击数字货币的金融犯罪。正如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在达沃斯论坛演讲中指出,数字货币的监管关键在于打击金融犯罪。(35)《贝利2021年1月25日达沃斯论坛演讲》,http://www.21jingji.com/2021/1-27/zNMDEzNzlfMTYyMjYzNQ.html。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HMRC)将数字货币视为一种资产,数字货币交易需缴纳资本利得税,从事“挖矿”工作也需要按英国相关法规纳税。(36)中币区块链:《中币调研报告4月(上)——2021年全球各国对加密行业监管态度与新规》,https://news.huoxing24.com/20210409100011756384.html。2019年,FCA发布《加密货币资产指引》文件,拟定数字货币市场的监管框架,并指出交易性代币暂时不受监管。由于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的波动性过高,2021年,FCA禁止向零售型消费者出售加密数字货币资产的衍生品,以保护消费者利益。
第三,中国。中国对数字货币实施严厉的监管政策。2013年,比特币价格飙升,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定位比特币为不具法偿性的虚拟商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37)《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http://www.gov.cn/gzdt/2013-12/05/content_2542751.htm。2017年,比特币价格再次暴涨,ICO活动风靡全球,央行联合其他部门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38)中国政府网:《工商总局等七部门〈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http://www.gov.cn/xinwen/2017-09/05/content_5222745.htm。明确指出代币发行是非法融资行为,禁止ICO,由ICO延伸出来的STO、IFO、IEO、IMO等均被认定为非法金融活动,并对数字货币交易平台进行集中整治,关闭国内所有数字货币交易平台。(39)比特币家园:《中国互金协会:〈关于防范比特币等所谓“虚拟货币”风险的提示〉》,https://www.btc126.com/view/1763.html。2018年,银监会发布《关于防范以“虚拟货币”“区块链”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警惕虚拟货币的炒作,明文禁止金融机构不得开展数字货币相关业务。2021年6月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全面关停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挖矿”,并要求银行与支付机构全面排查识别虚拟货币交易所及场外交易商的资金账户,及时切断交易资金支付链路,数字货币在中国的合法空间十分有限。相对而言,中国香港地区对数字货币监管较为审慎,数字货币的法律地位较为明确,监管框架相对完善。中国香港证监会先后发布《有关首次代币发行的声明》《有关针对虚拟资产组合的投资管理公司及交易平台运营者的监管框架的声明》等文件,明确监管内容和监管范围。
第四,日本。日本积极支持数字货币发展。日本拥有全球第二大数字资产交易市场,是全球第一个将数字货币交易合法化并推出交易牌照的国家。日本内阁在2016年签署《资金结算法》修正案,将数字货币纳入法律体系,规定比特币等数字货币可以用于支付。日本金融服务局(FSA)全方位监管数字货币交易所,制定了数字货币交易商监管条例,明确数字货币交易商的运营规则。FSA为全球各大数字货币交易商、区块链技术商办理营运牌照。FSA不断完善数字货币监管机制和法律体系,2019年颁布《新币发售规则及其指导意见》,加强数字货币的规范监管,使数字货币业务透明化和合规化。鉴于数字货币的跨境交易支付特征,日本监管机构通过经验分享、举办加密资产圆桌论坛等方式,加强与海外监管机构的合作,实施协同监管,在数字货币国际监管和协作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日本国税厅(FAQ)正在讨论数字货币的税收问题,拟颁布《虚拟货币的收益及其他所得》,实施对数字货币的税收监管。
第五,新加坡。新加坡对数字货币较为包容。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SA)实施“沙盒监管”,旨在为金融科技企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2017年,MSA发布《数字货币通证指南》,将数字货币划分为证券类、应用类和支付类。MSA在推进“沙盒监管”的过程中不排斥ICO项目,新加坡成为全球尤其是亚洲各国区块链企业规避本国政策、赴海外代币发行的聚集地,成为全球第三大ICO融资市场。(40)《新加坡成为全球第三大ICO枢纽》,https://www.wwsww.cn/ico/2065.html。MSA从风控和合规两方面,对数字货币交易所和场外交易等平台进行监管,主要包括洗钱及恐怖融资、平台合规运营、网络和技术风险等内容,并按照《支付服务法案》实行“牌照制度”。(41)“‘Payment Services Bill’-Second Reading Speech”, http://www.mas.gov.sg/News-and-Publications/Speeches-and-Monetary-Policy-Statements/Speeches/2019/Payment-Services-Bill.aspx.新加坡当局也很注重数字货币的税收监管,新加坡税务局(IRAS)发布的《数字货币所得税课税指南》规定,使用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买卖商品或服务的企业,缴纳7%的商品增值税,数字货币交易所获得利润需缴纳17%的所得税。(42)朱嘉明、李晓等主编:《数字货币蓝皮书2020》,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版,第134页。
(二)数字货币监管改进
通过对上述主要国家数字货币监管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各国在数字货币的法律地位、行政管理、市场准入和税收征管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各国监管立场和法律政策的差异性,显示出对数字货币这种新生货币形态认知的难度。(43)惠志斌:《数字加密货币的形成机制与风险监管研究》,《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随着数字货币发展的日新月异,各国的监管政策也要与时俱进。
第一,转变监管理念。数字货币是新兴科技与传统金融深度结合的产物,是金融领域的重大创新,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金融监管理论和现有的经济理论框架。监管过程中套用或照搬传统的监管方式和理念,不仅会因监管的滞后性和高成本性而抑制新兴技术的创新应用,还会造成监管混乱或失灵。在金融科技带来的数据化、技术化或智能化浪潮中,传统的被动式监管或响应式监管需要向主动性、包容性、适应性监管方向转变。(44)巴曙松、王珂、朱元倩:《Libra的监管挑战——基于金融创新视角的研究》,《金融论坛》2020年第5期。现行的监管受传统监管理念影响,过度依赖法律法规,忽视技术本身的功效,而数字货币融合了区块链技术、加密技术、可信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智能合约等新兴技术,利用这些新兴技术实现智能化监管是促进数字货币发展的有利选择。我们需要转变监管理念,实现“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技术”和弦共振,鼓励新技术的创新应用,发挥政策引导的调节效应。监管机构可以通过嵌入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平台,对数字货币进行实时监控,实现高质量和常态化监管。
第二,统一监管标准。目前各国将数字货币界定为商品、证券、支付工具及数字资产等,分别从资产交易、支付、税收、ICO、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消费者保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对其进行监管。(45)姚前、陈华:《数字货币经济分析》,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版,第125页。各国监管标准不同,监管侧重点迥异,这种各自为政的监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数字货币的全球性风险。当前数字货币的交易监管、税收监管、ICO监管及支付监管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由于跨国流动性,数字货币“趋利避害”现象层出不穷,避开对其不利的监管政策,趋向对其有利的国家。重复征税和国际避税问题是数字货币国际监管权力协调的重要内容之一,(46)李智、黄琳芳:《数字货币监管的国际合作》,《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0年第1期。也是监管标准差异的症结所在。为避免监管重复、监管空白、监管冲突,降低监管成本,提升监管的透明度和效率,通过国家间合作与对话,统一数字货币监管标准,建立适用不同主体的“共识性”制度,以便在国际监管标准建立和实施的同时,各国之间进行同等性监管。统一监管标准既能为数字货币创造监管抓手,又能实现监管的互联互通。
第三,完善监管法规。数字货币的急速发展给全球带来的影响远超立法者和监管者的设想。未来或许会形成数字货币区或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网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监管支付网络、控制私人财产跨境流动的有效性会削弱,法律制度不完备成为新常态。(47)许多奇:《Libra:超级平台私权力的本质与监管》,《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1期。国家的法律和监管政策往往固化或滞后新兴技术的发展,而数字货币的跨境交易和支付使其法律风险向境外溢出成为可能。例如,数字货币的境外商业行为违背中国的行政规章,但在海外某国或地区属于合法行为,那么,这种商业行为可通过互联网平台向中国提供服务,中国在境内具有管辖权,但存在境外执法障碍。(48)邓建鹏、孙朋磊:《区块链国际监管与合规应对》,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第56-57页。因此,各国监管部门需完善监管法规,实现对数字货币的跨境管辖,就像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可以管辖全球数字经济企业一样。(49)邓建鹏、孙朋磊:《区块链国际监管与合规应对》,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第56-57页。跨境监管涉及行政法、金融法和国际法等多个法律学科,立法和执法层面有待进一步研究。非主权数字货币可能会成为主流,国家法规需寻求更长远的应对之策,(50)杨东、陈哲立:《法定数字货币的定位与性质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形成全球性的数字货币监管规则。
第四,优化监管方式。传统的货币监管以央行为核心,建立了复杂的制度体系来维护国家权威,严禁私人货币信用的运行。传统的监管制度建立在中心化、中介化基础之上,而数字货币以去中心化为核心要义。数字货币借助区块链技术,改变了中心化的信用创造方式,通过技术背书,建立“信任网络”进行信用创造。传统的审慎监管、功能监管、行为监管、流动性监管等监管方式,已不适应数字货币的长远发展,面对数字货币带来的隐患,也是防范乏力。根据数字货币的发展态势,把握金融监管、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优化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技术,选择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以适应数字货币领域的变革,及时回应金融市场的新变化。国家在平衡鼓励创新和控制风险的基础上,推动监管方式的优化与变革,解决技术发展与监管滞后的矛盾,使数字货币的监管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
第五,加强监管协作。由于地域限制,各国对数字货币的监管存在天然的监管空隙。现有的资本管制和监管制度都是以主权国家为界,单纯依靠一个国家对数字货币的监管非常困难。数字货币的跨国流动并不受制于单个国家的监管政策,对单个国家而言,监管俘获、监管空隙、监管套利、监管竞次等一系列监管失灵现象将长期存在。(51)Hossein Nabilou, “Regulatory Arbitrage and Hedge Fund Regulation: A Need for a Transnational Response”, Fordham Journal of Corporate & Financial Law, Vol.22, No.4, 2017.此外,全球范围内流动的数字货币面对不同法域的政府监管,有的国家承认数字货币的合法地位,有的国家对数字货币加以限制并审慎对待,这种不同政府的监管差异易产生监管方式的多样性、监管内容的复杂性,甚至出现监管冲突,监管的有效性得不到保障,监管的合理性得不到认同。基于平等、公平、互惠、合作、共享、开放等理念,形成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建立数字货币监管部门的合作关系和合作机制,明确数字货币跨境交易的监管范围,共同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监管机构在监管理念、监管机制、监管模式、监管经验、监管合规水平、风险治理机制等方面互通有无,达成共识。国家之间在协作过程中建立协调机制,实现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形成若干各国必须共同遵守的决议和指导各国行为的法规,以此作为数字货币全球治理的基础。
综上所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或监管部门开展了一系列的数字货币监管工作,各国基于不同的制度环境,强调数字货币满足本国监管部门的要求。综合国内外监管机构对数字货币的监管政策,在监管理念、监管标准、监管法规、监管方式、监管协作等方面亟须改进和完善。然而,由于国家间政策差异、市场差异、技术条件限制,各国对数字货币的看法和态度难以达成共识,监管效果甚微,监管难题层出不穷。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下,数字货币在结构和功能上呈现出鲜明的类别特征,国家独立的监管已无法适应数字货币在全球范围内的井喷式发展,必须从国家监管上升到全球治理,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治理体系,制定全球性规则,将数字货币纳入公平合法、安全可控的发展轨道。
三、数字货币全球治理机制的形成
各国对数字货币的态度各异,导致数字货币市场乱象丛生,监管参差不齐。数字货币无国界性使其在跨国流动中带来全球性问题和整体性风险,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管控。面对全球性监管难题,数字货币从国家监管转向全球治理是大势所趋。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最早关注数字货币全球治理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政府间国际组织、非官方国际组织等各种组织,也充分认识到数字货币全球治理的迫切性和复杂性,提出相应的治理方案。数字货币全球治理提上日程,治理机制正在形成之中。
一是G20峰会机制。2018年3月,布宜诺斯艾利斯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首次关注数字货币全球治理问题。会议公报指出,加密数字资产可能会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影响,呼吁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SSBs)继续监控数字资产及其风险,必要时需评估多边应对措施。(52)新华网:《G20财长会强调坚持贸易对话》,http://www.xinhuanet.com/money/2018-03/22/c_1122573400.htm。彼时数字货币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不同国家对数字货币态度各异,G20并未形成数字货币治理的一致行动,但考虑到数字货币发展速度和数据缺口等内容,G20提倡预警性监控。之后的历届G20峰会越来越关注数字货币治理问题,设置专门议题讨论(见表2)。
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作为G20峰会主导下的核心机构,被誉为“全球央行”,负责监管全球金融体系,数字货币兴起后,FSB极为关注其发展动态。2019年,FSB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合作开发了一个监管框架并确定了衡量指标,分析数字货币可能影响全球金融稳定的风险点及其传播渠道。(53)FSB, “Crypto-Asset: Work Underway, Regulatory Approaches and Potential Maps”, May 31, 2019, p.5, https://www.fsb.org/2019/05/crypto-assets-work-underway-regulatory-approaches-and-potential-gaps/.FSB主席Randal Quarles曾表示,全球金融监管机构有可能因数字货币行业的快速创新而落伍,他呼吁全球金融监管机构紧跟数字货币发展的步伐,尽快制定数字货币全球监管规则。(54)《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需要加快制定数字货币监管规则》,https://www.bitcoin86.com/news/52175.html。Libra白皮书发布后,FSB聚焦以Libra为代表的全球稳定币(GSC)对全球金融稳定的影响。FSB于2020年7月向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提交了一份咨询报告,指出全球稳定币可能会给监管带来一系列挑战,主要是金融稳定、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数据隐私和保护、财务诚信、减少逃税、公平竞争和反垄断政策、市场诚信、网络和运营风险等方面,(55)《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致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的公开信》,https://www.163.com/dy/article/ERJOMES205198086.html。同时提出应对全球稳定币挑战的十项监管原则。(56)FSB在《解决“全球稳定币”所引起的监管与挑战》报告中,提出十项原则,包括:(一)当局应拥有并利用必要的权力和工具以及充足的资源,全面地监管、监督GSC项目及其多功能活动,并有效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二)当局应在职能上将监管要求应用于GSC项目,并与其风险相称;(三)当局应确保对跨境和跨部门的GSC项目进行全面的监管与监督,国内与国际相互合作与协调;(四)主管部门应确保GSC项目建立了全面的治理框架,并为GSC项目内的职能和活动明确责任分配;(五)当局应确保GSC项目具备有效的风险管理框架;(六)当局应确保GSC项目建立了健全的系统保护、收集、管理和存储数据;(七)当局应确保GSC项目具有适当的恢复和解决方案;(八)主管部门应确保GSC项目向用户和相关利益者提供全面和透明的信息;(九)主管部门应确保GSC项目为用户提供任何赎回权的性质和可执行性以及赎回程序的法律清晰性;(十)当局应确保GSC项目在特定司法管辖区开始任何运营之前,符合特定司法管辖区的所有适用监管和监督要求,并构建必要的适应新监管要求的系统和产品。FSB还从国家和国际层面促进对全球稳定币的治理:在国家层面,强调各国政府需要在“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的原则下应用监管工具,建立符合FSB指导的监管框架;在国际层面,正在制定全球稳定币的国际标准,预计今年底完成相关标准制定。(57)“Addressing the Regulatory, Supervisory and Oversight Challenges Raised by ‘Global Stablecoin’ Arrangements: Consultative Document”, April 14, 2020, https://www.fsb.org/2020/04/addressing-the-regulatory-supervisory-and-oversight-challenges-raised-by-global-stablecoin-arrangements-consultative-document/.

表2 G20峰会对数字货币的关注情况
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MF将数字货币治理列入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2019年9月发布专题报告——《数字货币的崛起》,对新兴数字货币进行详尽讨论,呼吁国际合作和信息共享,加强对数字货币的集体监管;(58)IMF Blog, “Digital Currencies: The Rise of Stablecoins”, https://blogs.imf.org/2019/09/19/digital-currencies-the-rise-of-stablecoins/.2020年10月发布报告——《跨境支付数字货币:对宏观金融的影响》,讨论了数字货币的四种可能应用场景及其对宏观经济和监管政策的影响,报告还认为促进大型科技平台之间的竞争,有助于减轻稳定币等私人数字货币缺乏竞争和治理不确定带来的风险。(59)“Digital Money Across Borders: Macro-Financial Implication”,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Issues/2020/10/17/Digital-Money-Across-Borders-Macro-Financial-Implications-49823.数字货币等创新产品对老牌金融企业已产生明显影响,正“撼动”银行体系,甚至动摇整个金融体系,金融行业的这种变化使得IMF对数字货币的态度由“均衡监管”走向“强化监管”。(60)Wei-Tek Tsai, Dong Yang, Kangmin Wang, Weijing Xiang and Enyan Deng, “Srisa: A New Architecture to Enforce Travel Rule”, FICC, 2020.数字货币已形成大规模且成熟的地下市场,而各国现有的监管政策注重合规市场,对此,IMF呼吁各国政府通过监管科技布局地下市场和合规市场,强化链上、链下和交易所的监管,同时妥善处理数字代币、稳定币和法币的竞争关系。IMF指出,在数字时代,私人数字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可以相辅相成、互利共生,通过扩展这种双重的货币体系逻辑,对私人数字货币加以规范的引导和治理,促进货币形式的多样性和创新性。(61)IMF Blog, “Public and Private Money Can Coexist in the Digital Age”, https://blogs.imf.org/2021/02/18/public-and-private-money-can-coexist-in-the-digital-age/.
三是政府间国际组织。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巴塞尔银行委员会(BCBS)、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从不同视角关注全球数字货币治理问题。FATF早在2015年就制定了数字货币指导方针,呼吁所有国家采取协调行动,防止虚拟货币被用于洗钱和恐怖融资。《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建议40条》(简称《建议》)是FATF为全球反洗钱工作设定的基本工作框架,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2018年,FATF对《建议》作出更改,其中,第16项专门针对数字货币,规定了数字货币的使用范围,包括法定和虚拟数字资产交换、虚拟资产之间的交换与转让、发行或承销虚拟资产有关的活动等,修改后的《建议》肯定了数字货币作为货币、商品和资产的合法地位。(62)参见http://www.fatf-gafi.org/media/fatf/ddocument/recomendations/RBA-VA-VASPs.pdf。随着数字货币市场热度不断攀升,FATF发布了《基于风险的角度:监管数字资产和数字资产服务商的章程指南》,明确要求数字货币交易所涉及资金转移时,“交易双方”的相关信息与执法部门共享,且只有在执法部门要求的情况下,才允许披露用户隐私的相关信息。(63)FATF, “Guidance for a Risk-Based Approach to Virtual Assets and Virtual Asset Service Providers”, 2019, http://www.fatf-gafi.org/publications/?hf=10&b=0&q=Guidance+for+a+Risk-Based+Approach+to+Virtual+Assets+and+Virtual+Asset+Service+Providers&s=desc(fatf_releasedate).为降低数字货币成为金融犯罪工具的风险,FATF发布了针对数字货币的“旅行规则”(Travel Rule),要求所有数字货币交易所都要履行“KFC”(了解你的客户)义务,虚拟资产提供服务商必须共享发起方和接受方超过特定阈值的数字货币交易信息等,这些举措为反洗钱和打击金融犯罪(AML/CFT)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框架。“旅行规则”在美国、欧洲、亚洲部分地区已经得到了转化性使用,但各国对“旅行规则”的接受程度不同,执行存在分歧。
巴塞尔银行委员会(BCBS)通过对从事加密资产活动的银行制定高水平的监管标准、跟踪加密资产的动态、合理量化银行对加密资产的直接和间接风险、对银行加密资产进行审慎处理等一系列政策,(64)“Designing a Prudential Treatment for Crypto-assets”, https://www.bis.org/bcbs/publ/d490.htm.规制银行机构参与数字货币交易的行为,增强全球银行业稳定性。BCBS设计了一个虚拟资产审慎监管框架,并提出该框架需遵循一致性原则、技术中立原则、简单性原则和最低标准原则,各国可以在此基础上制定对数字货币的监管标准。(65)参见https://www.bis.org/fsi/publ/insights23.pdf。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围绕分布式账本技术在支付、清结算领域的应用情况,搭建了一个治理框架,促进各国支付、清算、结算体系的安全高效运行。CPMI与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设立联合工作组,密切监测数字货币在清算和结算方面的创新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影响。IOSCO将稳定币监管作为重点,发布了《全球稳定币协议报告》,评估全球稳定币可能引起的监管问题以及现有准则是否使得当前行业获得发展,开始研究如何制定适用于全球稳定币的监管标准和规则。(66)国际证监会组织:《全球稳定币或将受到证券法规监管》,https://www.weiyangx.com/354368.html。
四是非官方国际组织。世界经济论坛(WEF)、世界数字货币论坛(WDCF)、博鳌亚洲论坛(BFA)等非官方国际组织,致力于全球数字货币治理。世界经济论坛的职责是探索和解决世界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而数字货币正在颠覆金融服务领域,给全球经济带来新的问题。针对当前数字货币监管的分散状态,世界经济论坛创建了首个全球性组织——数字货币治理联盟,旨在规范数字货币的发展空间,并打造有信誉且可信赖的数字货币。该组织计划设计一个全球数字货币治理框架,并制定可操作、透明和包容的政策,促进各国协同建立一个包容性、集成性的全球数字货币系统。(67)World Economic Forum, “Digital Currency Governance Consortium”,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digital-currency-governance-consortium.世界数字货币论坛是全球第一个以专题领域命名的国际组织,聚焦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治理,对数字货币引发的全球经济、政治、金融、文化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2019年12月,世界数字货币论坛启动全球发布会暨亚元ACU白皮书发布会,世界50多个国家政要及区块链专家就数字货币引发的问题进行商酌,并倡导加快数字货币全球治理的步伐。为应对“数字货币战争”给国家和地区带来的挑战和威胁,世界数字货币论坛提出了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倡议和宣言,引导数字货币全球治理,促进世界各国政府在数字领域的合作。(68)参见http://news.iresearch.cn/yx/2019/12/311409.shtml。博鳌亚洲论坛作为一个增进亚洲各国及亚洲与全球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为解决亚洲或全球经济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博鳌亚洲论坛关注数字货币如何改变未来的支付体系、给金融体系带来何种影响以及如何治理数字货币等问题。2021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专门设置“数字货币与跨境支付”分论坛,各国政要就跨境使用数字货币可能带来货币替代的压力、加剧货币错配的脆弱性、削弱政府管理货币政策的能力及影响跨境支付等问题,进行全方位的交流并研讨治理方案。(69)中新网:《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举行“数字支付与数字货币”分论坛》,http://www.chinanews.com/tp/hd2011/2021/04-19/980436.shtml。
综上所述,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组织,已着手数字货币全球治理。虽然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机制,但相应的治理原则、规则和规范正在酝酿之中。数字货币全球治理将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竞争与合作的重要议题,能否实现“高效、统一、包容、透明、可信任”的治理目标,(70)世界经济论坛成立的“全球数字货币治理联盟”提出的目标。合理有效的治理路径至关重要。
四、数字货币全球治理路径
数字货币全球治理还处于探索阶段,如何在缺少科层制组织结构和中心权威协调的条件下,维系技术演化和组织结构的共识,成为数字货币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71)贾开:《双重视角下的数字货币全球治理:货币革命与开源创新》,《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我们以加强全球合作模式、构建全球区块链、建立风险评价体系三个维度为载体,从市场协调、科技治理、风险监管三个方面切入,探索数字货币全球治理路径。
(一)加强全球合作模式
一是以数据驱动为核心。数字货币不仅依赖区块链和互联网技术,更依赖高质量的数据和强大的计算能力。数字货币治理需要以数据为本,丰富数据监管多样化手段,构建实时、动态的治理体系,其真正的内涵在于以数据为核心,采取有效的数据收集、报告、分析和管理流程,推动治理模式由“了解客户”向“了解数据”转变。(72)“FinTech and RegTech in a Nutshell, and the Future in a Sandbox”,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2240254_FinTech_and_RegTech_in_a_Nutshell_and_the_Future_in_a_Sandbox.具体而言:其一,数字货币交易、流通等相关数据的获取以及辨识这些数据的真伪。从市场角度看,若监管者能及时掌握数字货币的流动特征,实时观测金融机构的运营状况,可以提升市场的稳定性和竞争水平。(73)D. Arner, J. Barberis and R. Buckley,The Evolution of Fintech: A New Post-Crisis Paradigm,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pp.1271-1319.监管者通过大数据技术,全方位获取数字货币的数据,采取相应的措施辨识真伪,通过分析数据,察知数字货币的动态走向以识别风险。其二,数据分享。各国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国际组织之间共享数据是数字货币全球治理的基础。数据保护或本地化规则会导致数字货币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低效,产生“孤岛”。打通国家间数字货币的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提升国际社会协同治理的能力。其三,构建数据分析和风险预警机制。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量子技术等前沿技术,实现对数字货币流向的追踪,提前预防其在市场运行中的风险,为事中事后监管提供强有力的证据。(74)杨东、潘曌东:《区块链带来金融与法律优化》,《中国金融》2016年第8期。其四,监管机构将收集的数字货币数据信息建立数据库,以此为基础进行风险识别和风险警戒线设置,一旦有迹象表明数字货币市场可能会面临风险,监管部门可以提前介入,采取管制措施。(75)杨东:《监管科技: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与维度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二是以二级市场治理为重点。数字货币市场同证券市场一样分为两级:一级市场指借助新兴技术创造数字货币,二级市场指数字货币的交易市场。一级市场来源于技术创新,有助于促进国家的技术进步,提升国家的竞争力,一级市场的治理应该由各国自行裁量。数字货币全球治理应侧重于二级市场的治理,以交易平台为治理纽带。交易平台记录着数字货币的发行和交易信息,国家监管机构、国际组织借助交易平台监测资金动向。监管部门对交易平台建立规范制度,确立运营准则、明确技术安全,以便合理掌控平台的权利尺度,约束平台。
三是发挥非政府间合作论坛的作用,推动行业自治。数字货币的设计融合了密码学、计算机技术、数学、博弈论等多个学科,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特点。组建非政府间合作论坛,各领域专家交流解决数字货币领域共同面临的问题。譬如,2017年11月,俄罗斯区块链与加密数字协会召集了三十多个国家的行业代表,讨论设立全球统一的ICO评级标准,以应对评级方法不透明及评级市场的操纵问题。(76)[美] 亚当·格林菲尔德:《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货币:黑科技让生活更美好》,张文平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178页。2018年1月,瑞士加密币协会提出起草ICO行为准则的建议,为行业自律奠定基础。互联网治理主要是把分散的多方利益关联起来,数字货币治理也可以效仿互联网治理模式,将发行主体、交易平台、技术极客等多方利益主体关联起来,形成治理网络,推动行业自治。(77)Garry Jacobs, “Cryptocurrencies &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Governance”, Cadmus, Vol.3, No.4, 2018.成熟的市场自治对该领域的发展产生良性效应,数字货币全球治理过程中应发挥非政府间合作论坛的作用,积极引导行业自治体系的形成。
(二)构建全球区块链
一是核心国家共同构建一个智能合约编程框架。数字货币全球治理建立在各国共同参与的基础之上,Libra稳定币已经对此作出了尝试,虽然遭到了各方监管的掣肘,但其设计和发行机制给全球数字货币治理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从技术层面而言,核心国家可以共同构建一个底层的、关于智能合约的编程语言框架,在这一框架基础上,根据相应规则发行数字货币,并建立一个“全球中央银行”管理数字货币发行。(78)高奇琦:《主权区块链与全球区块链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0期。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货币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实现对数字货币的治理。通过共同的智能合约编程框架,“全球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获得类似铸币税的收益,并将这部分资产聚集到国际组织手中,为国际组织增加资金来源,提升治理效率。同时,各国将一定的资产映射到数字货币体系中,一旦某国违反国际组织的相关规定,智能合约自动生效,各国的数字资产在相应的区块链系统中实现增减,对其他国家产生威慑效应。(79)高奇琦:《主权区块链与全球区块链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0期。这种由核心国家构建的智能合约编程框架可以缓解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也可以减少公权与公权的冲突,既有利于全网风险追踪和风险联控联防,也有利于监管部门的有效沟通。(80)姚前、陈华:《数字货币的经济效应分析》,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版,第144-145页。
二是以开源治理协调各国集体行动。开源治理来源于开源软件社区治理,即在一个松散的社区网络结构下激励参与者的积极性进而就程序代码的开发实现共识。(81)贾开:《区块链的三重变革研究:技术、组织与制度》,《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1期。开源软件与传统软件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向全球提供巨大的代码数据库,有利于后来者的渐进式创新。开源治理参与者的激励动机不同于产权回报基础上的传统生产模式,不同主体的多元化动机都可能激励其参与到开源技术的完善进程中来。(82)[法] 普里马韦拉·德·菲利皮、亚伦·赖特等:《监管区块链——代码之治理》,卫东亮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84-185页。开源治理试图解决的问题与区块链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开源治理的经验可以为破解区块链的发展瓶颈提供参考,也自然成为数字货币在技术演化的组织过程维度需要着重考量的范本。(83)贾开:《双重视角下的数字货币全球治理:货币革命与开源创新》,《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区块链治理的底层激励机制上采取一些经济刺激手段,引导区块链自治系统的活动,以分布式共识运作,支持网络各方有权通过协调活动,(84)[法] 普里马韦拉·德·菲利皮、亚伦·赖特等:《监管区块链——代码之治理》,卫东亮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230-231页。从技术层面的区块链治理实现数字货币的开源治理。
三是建立合规数字货币中心平台。普林斯顿大学数字货币区理论认为,未来金融市场不再以银行为中心,而是以平台为中心。(85)VOX, “Digital Currency Areas”, CEPR Policy Portal, https://voxeu.org/article/digital-currency-areas.IMF在“数字货币兴起”报告中指出,商业银行有可能在未来被数字货币平台“取代”,且“取代”后对金融体系影响很小。(86)“The Rise of Digital Money”,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Issues/2021/07/28/The-Rise-of-Digital-Money-462914.未来金融市场可能以数字货币平台为中心,而合规的平台具备安全性和合法性。数字货币中心平台有四个方面的功能优势:其一,在没有央行支持、没有银行担保情形下,有了平台就可以进行交易;其二,数字货币在平台上交易,流动性会得到保障;其三,没有平台,数字货币就没有价值;其四,在分布式金融(DeFi)时代,参与者使用平台上的智能合约从事金融活动。(87)蔡维德:《互联网——未来世界的连接方式》,东方出版社2021年版,第367-368页。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通过链上、链下、交易所、市场等方面的共同治理,建立合规的数字货币平台,依靠机器共识、价值共识、治理共识形成一种自组织。在中心平台的基础上构建治理网络,从单链转向多链,形成跨国或跨区域的链网,加强各国监管者之间的协调以及金融企业的合作与数据共享,实现数字货币全球治理。(88)[美] 阿尔文德·拿拉亚南、约什·贝努等:《区块链——技术驱动金融》,林华等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27-229页。
(三)建立数字货币风险评价体系
数字货币带来的风险已受到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注,但国际社会没有对风险展开系统性评估,也没有进行前瞻性预测。风险具有潜在性、传染性和溢出性,一旦数字货币领域的风险治理不善而扩散到其他领域,有可能危及整个经济系统。因此,有必要建立数字货币风险评价体系。综合数字货币的技术特征,通过完善的数据收集系统,借助有效的数据分析和决策,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针对数字货币的实际风险作出预估,并借助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评价体系应主要包括交易风险评价体系、系统性风险评价体系、流动性风险评价体系、法律风险评价体系、技术风险评价体系和信用风险评价体系。监管部门通过完整的风险评价体系,对数字货币产生的风险作出事前防范、事中协调和事后妥善处理。加快数字货币风险评价体系构建,设立数字货币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提升风险研判评估技术,推进数字货币全球治理并构建全球一体化的数字货币联防联控体系。
结 语
随着技术的创新,数字货币的种类持续不断地衍生,新货币、新平台、新组织及其内含的新风险向社会跨区域、跨国界和跨时间渗透扩散,导致20世纪以来相对稳定的货币和交易体系逐渐被数字货币所蚕食。(89)袁曾:《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地位、作用与监管》,《东方法学》2020年第3期。数字货币需要纳入主要国家监管体系。
各国对数字货币的监管规则是建立在传统金融监管规则基础之上。然而,近十年来,数字货币的发展是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与渗透,审慎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等监管方式面对数字货币引发的风险显得力不从心。数字货币因本身技术特性和持有者的逐利心态,往往游离于国家监管体系之外,或变相逃避监管,从而实现监管套利。数字货币没有具体形态,其通过网络实现跨国流通交易,而各自为政的国家监管受制于信息不对称、监管技术手段匮乏、监管法律滞后和监管理念过时等因素,往往会出现监管空白或监管乏力。因此,数字货币从国家监管转向全球治理是必然选择,通过全球治理构建新的监管模式,克服目前存在的过度监管、监管缺失等问题,从而将其纳入公平合法、安全可控的发展轨道。
国际组织正致力于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实践,引导各国加强合作治理,数字货币全球治理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由于数字货币全球治理面临治理主体不明确、治理内容不清晰等困境,构建“市场协调、科技治理、风险监管”相结合的数字货币全球治理路径不失为一种可行性选择。数字时代已经来临,随着法定数字货币的深入实践,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的互动关系,实现数字货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