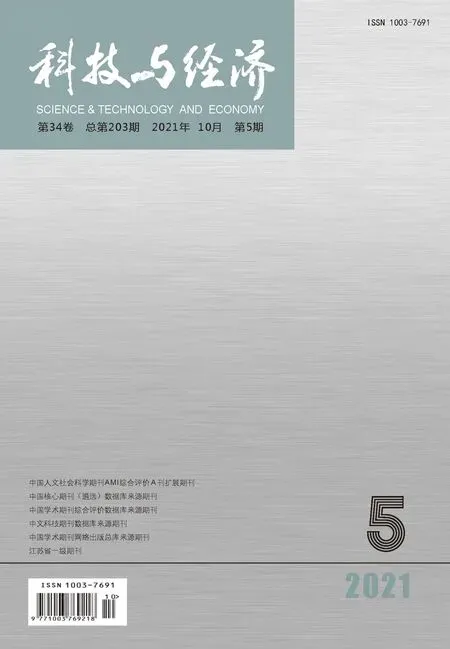国际人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及述评
——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李春浩 牛雄鹰
(1 绍兴文理学院商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武汉430073;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北京 100029)
0 引 言
移民浪潮的产生促进了人才跨国流动,经济全球化以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快了人才的跨国流动,由此扩大了国际人才的规模。国际人才是指学历高、专业知识丰富、创新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强、通晓国际通行规则和现代管理理念的个人。国际化人才涵盖经济、军事、政治等领域,具有国际化意识、国际化能力和国际化工作经验等特征,包括境外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海归、外派专业技术人员等[1]。基于此,本文通过知识图谱对国际人才研究热点进行探析,并加以文献述评。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外文数据来自Web of Science中的SSCI数据库,类型为Article,时间范围为2004—2018年,检索主题词为“international talent”或“returnee”或“brain gain”或“brain circulation”或“brain drain”,排除人类学等文献,共获712篇文献。中文数据来自中国知网,检索标准参照外文数据,共获152篇文献。
本文采用Citespace V软件对国际人才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共词分析、共引分析、聚类分析等,以把握国际人才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
2 国际人才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表明,国外研究主要关注国际移民、人才流失、人力资本形成、技术创新以及中国和美国的情况等内容;国内研究主要关注海归、海归创业、海归人才、人才流失、技术创新、海归回流、二元网络等内容(见图1)。关键词聚类分析显示,国外研究有8个聚类,分别为外派人员、人才流失、领导力、临时移民、技术创新、移民回流、海归、招聘;国内研究有5个聚类,分别为海归企业、智力回流、海归、技术创新、人力资本(见表1)。对比发现,国外研究对移民、中国和美国人才比较重视,而国内研究比较重视海归、智力回流情况,且国内外研究均重视国际人才领域中的技术创新问题。
图1中,英文文献有230个节点,560个线条;中文文献有55个节点,56个线条。英文文献的圆圈更大,节点和线条更多、更为紧密。这表明,国外研究更为深入和广泛。由表1可知,国内外研究各聚类紧密程度大多大于0.6,则反映了网络的同质性比较高。但国内研究年份大多在2012年以后,起点较晚。

图1 中英文文献国际人才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表1 聚类结果
在知识图谱中,中心度大于或等于0.1的关键词是网络中比较关键的节点,可能是研究热点从一时间段到另一时间段过渡的关键点,反映了研究热点的变化。表2中,将中心度设置为≥0.1,得到被引频次较高的关键词。中国问题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且更关注研究视角、劳动力、移民、贸易、绩效等问题;国内学者主要关注海归创业、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知识溢出等问题。同时,国内外学者都比较重视社会网络、海归、海归企业等问题的研究。但相比较而言,国内研究更为重视国际人才技术创新问题,中心度是国外的2倍。

表2 国际人才高频关键词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3.1 国际人才流动的动因
国际人才外流的原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个体原因,主要体现在收益与成本的对比,这种收益是多方面的,如技能提升、收入提高、教育机会等。Grogger和Hanson(2011)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移民,尤其是向技能回报率高(如收入、技能提升)的国家迁移[2]。Harvey(2011)研究发现,英国科学家迁移到美国主要受到专业技术的驱动,而印度科学家主要受到教育水平的驱动,但两者做出最后迁移决定都受到社交关系的影响[3]。McKenzie和Rapoport(2010)认为弱移民网络有利于移民的自我选择,而强移民网络对自我选择具有负向影响[4]。二是社会原因,移民率与人力资本水平、政治稳定性、地理邻近程度、种族/宗教分化、目的国类型、难民庇护政策、移民政策等密切相关[5]。
国际人才回流方面,Hussain(2015)认为对国内环境以及发展前景看好的情况下,当移民具有较高的技能水平,回国有利于获得收益最大化,对自己和母国更有利,移民更可能回流[6]。尤其是母国引才政策和科技创新环境都比较好、经济发展水平高、教育投资水平高,对国际人才更具有吸引力。Zweig等(2006)指出由于国际人才拥有母国缺少的专项技术、研究方法等,回到母国更有利于个人技能和能力的发挥[7]。此外,Pan(2010)发现国际人才回流还会受到国外心理文化认知、母国和东道国的关系、母国高等教育政策与国际背景下社会变化的影响[8]。同时,制度成为阻碍海归回流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法律、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对中国海归回流产生负向影响[9]。
3.2 国际人才流动的效应
3.2.1 人才外流效应
人才外流效应存在三种观点:
一是抑制作用。移民虽然有利于流出国获得汇款和个人技能的提升以及商业网络的创建,但仍无法弥补本国未迁移人福利的下降,而且大规模的人才流失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造成巨大损失[10]。
二是促进作用。一方面,由于国外较高的教育回报率会导致潜在移民加强教育方面的投资,以便未来迁移,但人力资本门槛的存在使得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无法外迁,而有利于移出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移民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且移民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推动流出国融入全球经济[11]。
三是双刃剑作用。原因如下:一是移民类型,过渡性移民利大于弊,而永久性移民弊大于利。二是国家类型和移民率等,技术移民对于人力资本的形成有利,属于“有益的人才外流”,例如中国、巴西、印度等。但是对大部分国家如人口较少的国家,人才外流不利。同时,技术移民有利于低收入国家人力资本的积累,但要求技术移民的比例不超过20%~30%[12]。高技术移民可以产生积极的网络外部性,如汇款、国外直接投资等,且移民规模越大,其网络外部性越强。人才外流有利与否与不同国家的治理水平、人口规模、人力资本形成激励、技术距离等有关[13]。同时,Barnard和Pendock(2013)认为移民经历有利于增强侨民对祖国知识分享的意愿,但失落感和内疚感会对此产生负向影响[14]。
3.2.2 人才回流效应
人才回流具有积极作用,Saxenian和Hsu(2001)发现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台湾地区工程师不仅向台湾地区转移资金、技能和专业技术知识,还促进了两个地区公司之间的合作,从而促进了产业升级、技术转移[15]。Dustmann等(2011)认为由于不同国家技能熟练程度不同,移民在发达国家通过“干中学”,获得技术积累,回流可以有效增强本国技术水平[16]。同时,Filatotchev等(2009)指出创始人的国际背景和全球社会网络对出口导向和出口绩效具有决定性作用[17]。海归跨国流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知识转移、知识溢出的新渠道,Liu等(2010)研究表明,海归对技术创新具有积极影响,而且跨国公司内部员工流动的知识溢出效应比较显著,两者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相互促进的[18]。海归还具有外部效应,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水平,还可以促进邻近企业的创新,尤其是促进具有海归领导的企业获得更多专利。但Kenney和Dan(2013)认为,国际人才虽然具有技术、管理、创业等方面的能力,但回流对母国经济的发展并非起关键作用,需要政策制定者为该行业奠定基础后,才会在第二阶段发挥积极作用。
国内学者认为国际人才流入的影响包括,一是对进出口贸易和实际利用外资的影响。魏浩和袁然(2017)认为人才跨国流动有助于克服国际贸易中非正式壁垒,降低交易成本;获取交易信息;增强信任,促进契约履行[19]。许家云(2018)证实国际人才对企业出口拉动具有持续性和逐年递增性,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出口概率、强度和产品范围及质量,且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20]。同时,朱敏和许家云(2013)指出国际人才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显著影响,且存在区域差异性。二是对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技术扩散、知识溢出的影响。孙文松等(2012)证实海归人才流动和跨国企业人才流动均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而且两者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相互促进的[21]。蒋艳辉等(2018)研究表明高管型海归和非高管型海归对技术创新均具有正向作用,其中高管型海归对创新产出更具有原创性,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效率;非高管型海归对渐进性创新的作用比突破性创新更强[22]。陈怡安(2018)认为海归回流存在知识溢出效应、技术扩散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且在我国东中部地区存在差异性,但受限于地区经济水平、对外开放程度、非制度因素等的影响[23]。
3.2.3 人才环流效应
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循环流动成为一种重要的现象,构成人才跨国流动的一种。Xiang和Shen(2009)认为人才环流强调人才频繁的跨国界流动,一般是在本国与其他国之间的双向流动,而不是永久性地迁移到另一个国家,使智力资源可以跨国界共享[24]。人才环流具有知识溢出效应、传播效应等,从而使人才流出国和流入国均能受益。Saxenian(2005)研究发现,中国和印度出生的高技术工人在硅谷工作,并与国内建立了商业联系,能够灵活地转移技术和制度知识,从而使技术和资本由单向流动的旧模式转为双向流动的新模式,即人才环流促进了技术、资本的双向流动,使流出国、流入国、人才均能受益[25]。通过人才环流,Tian(2016)认为可以实现远距离的信息交换和协作,有利于网络构建和资源的重新组合,减少国内外产出的差异,从而促进流出国和流入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26]。
3.3 国际人才创业研究
创业问题是国际人才领域的热点之一,Dheer(2018)构建了国际人才创业研究框架,涉及前因变量包括微观层面(心理特征、资源基础等)、中观层面(区域特点、网络属性)和宏观层面(监管影响等),创业过程中涉及制度和政策支持等因素,最终影响经济发展、贸易顺差、组织绩效、创业退出等[27]。Wright等(2008)发现拥有国外专利的海归公司在非大学科技园区表现更好,拥有跨国商业经验的海归公司在大学科技园区表现更好[28]。Bai和Johanson等(2017)认为海归企业家可以利用其国际商业经验、无形资产获得商业机会和企业发展,因此海归创业公司比当地同行更具有创新性,而且对当地同行具有间接溢出效应,创业效果更好。但Pruthi(2014)等认为由于缺乏国内关系网络和当地知识,以及对母国文化和制度环境的掌握不足,导致海归劣势上升,充分适应当地文化方有助于企业提高创业绩效[29]。Qin等(2017)发现,由于新入者劣势和外来者劣势,海归企业家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而且进入高技术创业领域更慢[30]。同时,Lin等(2015)指出海归企业家早期虽然会强调正规性,本土企业家强调非正规性,但海归企业家与本土企业家最终会达到正规-非正规平衡趋同,并与中国制度变迁相一致[31]。
国内学者主要关注海归社会网络的作用,如侯佳薇等(2018)指出海归越倾向于采用技术导向越有利于嵌入海外网络,采用市场导向对嵌入国内外网络均有正向影响,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识资源和资产资源[32]。彭伟等(2017)则证实资源获取与整合、创业学习和技术能力在海归双重网络及技术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内部吸收能力和政策环境在其中起调节作用[33]。赵文和王娜(2017)则认为国外社会网络对海归企业各阶段发展的影响及获得高绩效非常重要,但国内网络如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积极影响会降低,甚至产生不利影响。陈健等(2017)也认为海归创业存在外来者劣势,需要适应本土环境和文化,方可有利于企业绩效[34]。
4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国际人才流动的动因、国际人才流动的后果、国际人才创业等方面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还可能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国际人才流动的动因方面涉及个人、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但大多基于个人利益考虑,而对非制度因素涉及较少,例如跨文化适应、文化距离等方面。二是国际人才流动的效应逐渐完善,从人才外流、人才回流以及人才环流等角度分析较为全面深入,逐渐认可国际人才流动的价值,但需要研究国际人才流动效应所受到流出国和流入国相关因素的制约和促进,除了制度性因素,还需考虑非制度因素,如社会网络、文化差异等;还需要研究国际人才对管理创新、产业升级等影响的内容。同时,人才环流方面的研究还不太丰富,可以进一步探讨人才环流的内在机制、影响因素、效果等。三是国际人才创业问题研究方面已经考虑创业效果与创业环境的互动,探讨文化适应、地方关系、社会网络等多方面的问题,但还缺乏从宏观层面考虑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研究,如中国大陆因历史传承、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原因内部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对国际创业影响可能存在差异,需要深入考虑。总而言之,有关国际人才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从非制度性因素探讨,尤其是对中国等存在文化多样性的国家;另一方面可以深化国际人才效应的研究,比如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