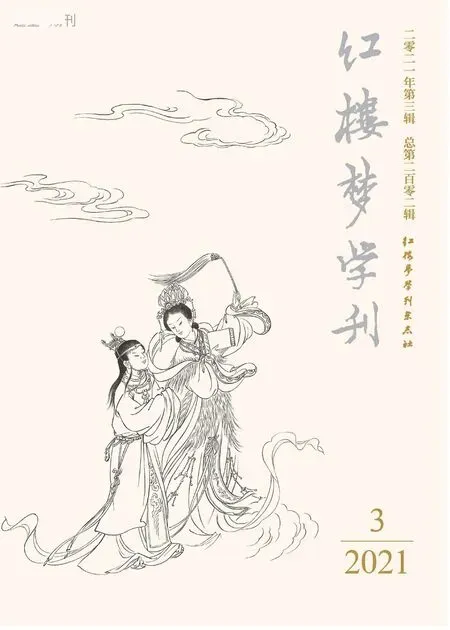民国红楼戏之新剧先声
——从《申报》所刊戏剧广告试论民国早期上海红楼戏的出现
吴雨彤
内容提要:民国时期的红楼戏改编由上海的新剧拉开序幕,虽然剧本绝大多数都未能传世,所幸有《申报》所刊戏剧广告可以一窥其上演情况。 本文将第一部新剧红楼戏出现到春柳、新民、民鸣三大主力剧团的红楼戏演出告一段落、即1913 年到1915 年6 月作为其萌芽期,梳理早期红楼戏的上演脉络。 这一时期的红楼戏几乎全为新剧作品,呈现出避开长篇小说《红楼梦》主轴、偏好撷取戏剧冲突强烈且相对较为独立的支线情节的改编倾向。 参与编演的剧人多为知识分子,显露了剧作家的初步自觉及舞台意识,在创造新剧红楼戏的同时,也推动了之后京剧红楼戏的诞生。
根据《红楼梦》创作的戏曲作品自小说百二十回本问世便层出不穷。 民国时期,戏剧生态丰富、求新求变的商业化、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成为红楼戏重镇。 作为话剧雏形的“新剧”萌芽成长,以新民社、春柳剧场·新剧同志会为代表的新剧团体纷纷从小说《红楼梦》中找寻题材。 京剧方面,更有以梅兰芳、欧阳予倩、荀慧生为代表的三大名角为民国时期的红楼戏贡献了诸多杰作。 当前学界从民国时期红楼戏的改编情况总览,到日渐丰富的稀见资料补遗,再到针对早期话剧和其演剧团体的研究以及京剧红楼戏名家作品、流派艺术分析,均已有大量论著。 只是不畏繁杂的资料整理常常停留在剧目书录列表层面,具体分析研究则局限在几位京剧名家的名作,而且早期话剧研究很少把其中的红楼戏分离出来作为一个专项看待。 在前人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前提下,还有很多关于民国时期红楼戏的真相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 民国时期红楼戏的上演状况究竟如何,这一时期繁荣的红楼戏体系是如何构建的,又有怎样的内部联系,仍旧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因此,本文暂将研究范围锁定在红楼戏重镇上海,以《申报》所刊登的戏剧广告为线索,结合同时期其他杂志、剧评、以及戏剧界人士的文章,试对民国早期红楼戏的实际演出情况进行进一步考察。
一、民国早期红楼戏的范围界定
本文中所谓“民国早期”者并非近现代史上对于民国史的阶段划分,而是着眼于红楼戏的发展阶段所做出的分期。 上海是民国时期最早出现红楼戏的城市,其上演无论从持续时间还是剧目数目或者演出频次,都堪称无可出其右者。 本文将1913 年至1915 年6 月划分为民国时期上海红楼戏崭露头角的第一阶段。 《申报》上首次出现的新剧红楼戏广告为1913 年新民新剧社所刊,而后民鸣新剧社、春柳·新剧同志会也纷纷推出红楼戏,民国时期的红楼戏篇章由此翻开。 将第一阶段的结尾划定在1915 年6 月,是因为这一时期演出红楼戏的主力三大剧团各自生变:1915 年1 月,新民与民鸣合并;春柳在《申报》上的最后一则演出广告是1915 年7 月19 日,实际解散是在1915 年秋季,然而1915 年6 月13 日的《黛玉葬花》已是新剧同志会在春柳剧场最后一次演出红楼戏,1915 年6 月25 日的《鸳鸯剑连演宁国府》是民鸣“两大剧团合演特请春柳诸巨子”的演出,春柳的红楼戏演出到此为止,且春柳分崩离析之势业已出现。 1915 年7 月,欧阳予倩、吴我尊等曾经春柳的主要成员以签约演员的身份加入民鸣社,名义上已经与春柳无关,而后欧阳予倩开始了京剧红楼戏的编演,上海红楼戏演出自此也进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 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将范围锁定在民国红楼戏的第一阶段,探讨上海红楼戏的出现,其他阶段将另行撰文论述。
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随着戏剧的发展,“新剧”“文明戏”等新的名词也应运而生,一个词汇指代的概念可能根据时间以及不同的语境发生变化,几个词汇的所指更有相互交叉重叠的部分。 当前学界常用“文明戏”指代早期话剧,但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特别是《申报》所刊广告及文章的实际用法来看,称早期话剧为“新剧”乃是当时主流,从事新剧活动的人则称为“新剧家”,“文明戏”的用法尚不多见。 故为方便行文,除引用的广告原文之外,本文中涉及到的红楼戏皆以是否采用传统戏曲演唱为主要表现方式为判断标准,将其二分为新剧与传统戏曲以示分别。
二、民国早期红楼戏的编演情况及主要团体
1. 新民社
1913 年10 月25 日,郑正秋组织下的新民新剧社刊出了一则预告,表示新民社已在筹备红楼戏,“刻意排练一俟纯熟即定期登台以飨座客”。 11 月26 至28 日连续三日刊登广告预热后,新民社的红楼戏终于在1913 年11 月28日正式上演。 提前几天刊登的广告中宣传剧名为《红楼梦》,至正式上演的28 日广告中始将剧名标为“红楼梦之一鸳鸯剑”,可知并非对小说《红楼梦》全本或主要情节的呈现,而是节取尤三姐自刎鸳鸯剑故事的片断进行编演。12 月3 日的广告中注明“此剧为马二先生所编”,马二先生即著名剧评家冯叔鸾,这一时期在新民社担任编剧,偶尔也上场客串角色。
《鸳鸯剑》首演之后,新民社趁热打铁,于12 月3 日重演一次。 12 月5 日推出其第二部红楼戏《风月宝鉴》,即贾瑞王熙凤事,亦为马二先生作。 广告中写道:“本社前排演红楼梦之鸳鸯剑一剧颇蒙海上各大评剧家及座客之称誉兹又重排风月宝鉴一戏情节较前尤佳。”不到一周时间,新民社又于12 月11 日推出其由马二先生编排的第三部红楼戏《夏金桂》。 广告中仅有剧目名称,难以判断是由小说哪一部分裁剪而成,但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中提到,其《宝蟾送酒》乃从冯作全本《夏金桂》中脱胎而生,或许可知此《夏金桂》主要敷演的是小说第一百回中夏金桂、宝蟾与薛蝌一段情节。
《鸳鸯剑》给新民社红楼戏带来了成功的开始,1913 年12 月14 日起,新民社在《鸳鸯剑》的基础上继续编演在小说《红楼梦》中与其情节相连续且人物相关性强的尤二姐故事,14 日广告中所言“红楼梦连台新剧鸳鸯剑带演九龙珮”,后半部即15 日演出的《大闹宁国府》,据冯叔鸾《啸虹轩剧谈》可知此《大闹宁国府》为翁振青编剧。 情节连贯的《鸳鸯剑》与《大闹宁国府》“双出好戏”于1914 年4 月4日再度一晚之内连演。 至此,新民社的四大红楼戏全部问世。
然而好景不长,新民社于1913 年9 月5 日起开始在上海演出新剧,却不过只持续了一年余,后被商人经营三创建的民鸣社不断挖角乃至吞并。 新民社在上海最先掀起新剧红楼戏的浪潮,而1914 年4 月14 日演出的《夏金桂》竟成为其在上海舞台演出红楼戏的“绝响”矣。
2. 民鸣社
1913 年11 月28 日开幕起,民鸣社便积极扩张势力,从新民社等竞争对手处挖角,也抓住观众喜新厌旧的心态不停推出新作。 可以看到,在新民社推出红楼戏之后,民鸣社不甘落后,在1914 年2 月14 日打出了“许啸天先生编红楼梦”的广告。 广告中提到:“啸天先生于去春在浙东编演大受社会欢迎”,可知是已经在上海以外演过的作品在民鸣社再度搬上舞台,其实际在浙东的上演情况尚有待考察。 小说家许啸天于上海曾在新新舞台短暂任编剧,后来又历任民鸣新剧社及开明新剧社的编剧,目前上海相关资料中可见的许啸天红楼戏作品只有民鸣演出的这一部,题为《红楼梦》但实际上是由三个相对独立的章节构成,“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琏偷娶尤二姐”“纵淫心金桂自戕生”三段于2 月15、16、17 日分别上演。
这一次“现成”的《红楼梦》实为新民并入之前,即早期与新民为竞争对手时期的民鸣唯一一次演出红楼戏。 其后的红楼戏演出要待1915 年吞并新民之后,故本文暂且不表,留待日后论述。
3. 春柳剧场·新剧同志会
1907 年,一批清朝留学生于东京组建春柳社从事演剧活动,并得到了日本新剧界的大力支持和好评。 其大部分成员在1911 年辛亥革命之后陆续回到中国,1912 年于上海组织了新剧同志会,几经辗转后,终于1914 年再度回到上海,为纪念春柳社而自名为春柳剧场,以新剧同志会的名义继续创作演出。
春柳·新剧同志会于1914 年4 月15 日在上海谋得利正式开演,4 月18 日即演出了其第一部红楼戏《鸳鸯剑》,5月1 日重演。 据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鸳鸯剑》是1913 年在湖南“文社”时期自编自演,是欧阳予倩的第一部红楼戏。 《鸳鸯剑》获得好评之后,春柳同新民社一样,选择了在小说中情节相连贯的《王熙凤大闹宁国府》作为其续篇并于5 月9 日上演,广告中注明“由马君绛士编成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六幕用续鸳鸯剑为尤二姐之结局”。 《新剧考证百出》中将《鸳鸯剑》作者标注为马绛士,而将《王熙凤大闹宁国府》作者标为欧阳予倩,或许因为此时的红楼新剧发展起步,在演出时内容不断调整,多人参与创作导致同一部剧作会有不止一个作者名,这一点在王凤霞《文明戏考论》中亦有提及。
5 月15 日,春柳推出马绛士编《林黛玉焚稿》。 5 月23日,又推出马二先生新编《夏金桂自焚记》,共七幕,“而包罗原书前后十余回之情节纤悉靡遗”,或较之前新民社演过的《夏金桂》有所扩充,即欧阳予倩所云“全本夏金桂”。10 月10 日又出新作《风月宝鉴》,12 月19 日推出《刘老老进大观园》(《新剧考证百出》中注“编者松风”)。 1915 年1 月,为纪念新剧同志会成立三周年,于17 日推出新作《晴雯》(《新剧考证百出》中注为“冥飞绛士合编”)。
这一阶段,春柳演出的新剧红楼戏无论是数量还是上演次数都名列前茅,1915 年6 月13 日甚至还推出了一部“古装歌剧”《黛玉葬花》,欧阳予倩与杨尘因、张冥飞合编,这就是欧阳予倩所说“在春柳剧场当余兴演的,可算是在上海第一次的古装京戏”。 遗憾的是,这是春柳第一次演出红楼京剧,也是新剧同志会在春柳剧场最后一次上演红楼戏。 1915 年秋,陆镜若英年早逝,春柳剧场最终走向解散的结局。
4. 三大新剧团以外的红楼戏
民国早期,除以上三大新剧团体之外,还有其他组织排演《红楼梦》的记录散落在《申报》广告中。如1913 年11月29 日,醒舞台打出“初排文明全部新戏红楼梦”的广告,并预告“现定初三夜(笔者注:11 月30 日为旧历十一月初三)先行演唱头二本请各顾曲诸君早临鉴赏无任欢迎”。参考王凤霞《文明戏考论》中对“文明戏”一词出现及发展的阶段论证,且广告中提到“演唱”及“顾曲”,故此处的“文明全部新戏”一词所指代的概念应为“全本改良戏曲新作”。 随后,醒舞台12 月11 日又演出一次,并标明演员为“宋志普张云青林颦卿小孟七曹玉堂李锦荣于振廷”,大约这是醒舞台独有的新编京剧红楼戏,但不知编者为谁,内容如何。 看首演日的广告内容,可知其最初是有着排出《红楼梦》全本的野心的,可惜演出记录惟有以上两次,再也无处追寻。
此外,还有法界歌舞台于1914 年4 月17 日预告要演出“潘大隐先生新编全部红楼梦”,广告全文如下:“红楼梦一书以儿女艳情写康乾故事为我国数千年来说部第一奇书近来新旧剧团多有节取该书中一二事以为剧本者阅者恒以不得窥见全豹为恨本社特请潘大隐先生将该书全部编出以江郎妙笔摹绘金玉姻缘加以本社艺员脚色之多尽力描摹当可惟妙惟肖一俟排练纯熟布景齐全即行定期开演 特此预告。”从广告内容可以推测此为新作,并非醒舞台已经排演过的《红楼梦》,但这部筹划中的《红楼梦》也只停留在这一篇预告而已,并没找到实际上演的记录,或许是排演全本红楼戏的难度实在太大,最终也没能实现。
早在1913 年1 月5 日,王钝根就曾于《申报》“自由谈”的“剧谈”一栏中透露“又闻大舞台将排演红楼梦杂剧,余尝为之悬拟诸名角之支配,惟贾璧云或可饰宝玉”,可惜这一计划似乎也没能结果。 《小说新报》1915 年第一期“剧话”栏目《伶话星星》中也提到此事,作者署名为云云:“昨晤朱素云,谈及大舞台前排红楼梦,编而未演,爰述及种种困难,第一人才难得,第二事实难纪,……大舞台欲演而不演者,亦鉴于余言,不敢贸然从事也。 素云持论甚是,予故乐为纪之。”想要排演红楼戏的剧团或许不在少数,但望而却步者有之,付诸行动却未能如愿者有之,得以成功演出却毁誉参半甚至饱受非议者也有之,可见《红楼梦》戏剧化之难。
三、民国早期红楼戏的特点
民国初期最早出现的几部红楼戏除具体情况不明的醒舞台《红楼梦》及欧阳予倩于春柳仅演出过一次的京剧《黛玉葬花》外,均出现在新剧界,且都避开了宝黛爱情的主轴。 从1913 年11 月28 日至1915 年6 月25 日,《申报》广告中可见的上海红楼戏演出共计57 次,主要演出的是《鸳鸯剑》《(王熙凤)大闹宁国府》《风月宝鉴》《夏金桂自焚记》等作品,而与小说女主角林黛玉相关的作品仅有1914年5 月15 日及8 月15 日再演的春柳剧场新剧《林黛玉焚稿》及1915 年6 月13 日春柳的京剧《黛玉葬花》两部。
“黛玉葬花”是小说《红楼梦》中极富代表性的一幕,其诗意之美历来为人所称颂,阿英《红楼梦戏曲集》中收录的清代文人创作的杂剧及传奇作品也都对其情有独钟,十部作品中除《三钗梦北曲》外,几乎部部都有葬花一节,现存不多的清代红楼戏演出记录也大都以“葬花”为主。 为何在此时的红楼戏编演中,依然繁荣的京剧市场悄无声息,让新剧专美于前,且新剧在选材上出现了回避林黛玉及宝黛爱情的一致倾向,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为市场需求。 清代红楼戏演出的史料在徐扶明《红楼梦与红楼戏》一文中有着较为详尽的整理,然而这些剧目都未能传世,甚至光绪年间票房排演《葬花》《摔玉》时饰林黛玉的陈子芳一登场,便因为扮相不符合人们心中的林黛玉形象而被台下哄笑。或许这些以往的经验教训使传统戏曲界已经深知改编红楼戏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进入黄金期的京剧市场既然已经有足够逐渐定型的经典剧目可保证盈利,民初上海大行其道的新编戏又多以“时事”“时装”甚至过激的舞台表演来做噱头,有过于文雅之嫌的《红楼梦》显然不符合一般想象中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自然无需非要来碰这块硬骨头;而新剧勃兴后,观众对新剧的好奇以及激烈的竞争促使新剧团体必须不断推出新作,尤其新剧既无可供反复琢磨的唱腔身段,观众通常在看过剧情之后不愿再看重复的剧目,欧阳予倩也提到过因为一时难以凭空创作出大量新作,从笔记小说甚至弹词中取材成了能够一解燃眉之急的方法,甚至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如此看来,红楼戏改编的一个小高潮出现在民国时代的新剧界,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为创作群体及创作动机。 《红楼梦戏曲集》所收清代红楼戏无论传奇或杂剧,均为比较传统的文人创作,虽有小部分在脚色平衡等方面显示出对舞台搬演的考虑,但究其根本,大部分作者还是以小说《红楼梦》读者的身份在戏曲创作中抒发读后感,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黛玉葬花一节无疑十分符合传统的文人审美,自然在戏曲创作中也不能缺席。 文人们案头创作的红楼戏实际能否在舞台上成功上演甚至传世,对其或许并不会有实质影响。 这些作品中曾实际上演过的不过一小部分,大部分作者连是否会在舞台搬演都不考虑在内,遑论观众接受。 民国时期的新剧团体则不同,剧作家的创作就是为了上演,卖座与否与剧团的生死存亡直接相关。 小说《红楼梦》改编着实不易,角色分配已是一大难题:宝玉黛玉难觅其选,人物众多且旦角过多,传统戏曲已经尝到这一点的苦头,可说是前车之鉴,所以在红楼戏改编上,新剧家们另辟蹊径,避开庞大的小说整体及难以呈现的宝玉黛玉人物形象,选择情节自成首尾、相对独立的支线故事。 尤其一些新剧家受到西方戏剧及日本新派剧的观念影响,对剧本创作及戏剧理论有了一定自觉,且相较于观众早已当做天经地义的中国传统戏曲,以说白为主要表现方式、没有唱腔可供观众欣赏琢磨的新剧还未能得到完全接受。 如果把《红楼梦》中的家庭生活照搬平铺,观众难免昏昏欲睡,自然需要比较热闹的剧情来带动气氛。 这样的创作动机直接导致民国时期的新剧家们对《红楼梦》选材取舍偏向风月宝鉴、尤三姐自刎鸳鸯剑、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等相对独立并具有较强的戏剧冲突的情节,故而使黛玉葬花等向来为人称颂的段落在这一时期的戏剧改编中遭到冷遇。
四、从广告与剧评看民国早期红楼戏的主张与接受
清末民初的上海出版文化空前繁荣,戏剧既为市民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申报》这部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所刊的戏剧广告也不再局限为简单的剧场及剧目名称,与晚清时的广告相比,版面更大,内容也更丰富,宣传语更是尽煽动之能事,更有大批剧评家汇集在“自由谈”版块各抒己见。 此外,还有其他小报及杂志大量涌现,亦有文人就演剧小说著书立说。 从这些宝贵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剧作者的创作主张及“苦心谈”,也可以看到一部剧作从创作、上演到获得观众、剧评家批评反馈的这一完整的接受过程。
1. 《红楼梦》改编之难:诉苦与自矜
长篇小说《红楼梦》的戏剧改编之难已是不争的事实,本文中所提到的新剧团体在为其苦恼的同时,也毫不保留地显露出编演红楼戏的自豪。 编演红楼戏,旦角过多且难以符合观众对人物形象的心理预期是其中一难,故新民社1913 年10 月25 日的广告中强调“本社本以社会教育为宗旨旦角人才之多又实在海上各舞台之上”,春柳也要强调“人才齐集支配得宜”,且“予倩君之王熙凤丰神绰约一颦一笑几疑熙凤复生”(1915 年6 月4 日)。
要改编《红楼梦》,改编者首先要具备相当程度的知识水平,所以在广告中屡屡出现对编剧或演员文学造诣的赞美,如1914 年4 月2 日新民广告中写:“马二先生之文名风采久为社会赞赏客岁串于谋得利备蒙识者欢迎良以先生熟读红楼故所演无不出神入化逈非他人所及”;春柳成员“非日本留学生即一时之名士”(1915 年1 月22 日新民舞台特请春柳),这一点更时常在广告中得到凸显,强调其社员的卓尔不群。
这些广告语当然不排除为了宣传而夸大的成分,当然越是强调角色难得,“编出戏来颇难演好”(1915 年5 月21日春柳),越能彰显自己的人才齐备,艺术高超。 红楼戏编演如此不易,各社却能纷纷拿出得意之作,在大部分演出团体文化及艺术水平都不高的衬托下,无疑显露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民与春柳技高于人的骄矜。
2. 《申报》剧评:溢美与批判
1913 年11 月28 日新民社《鸳鸯剑》甫一上演,11 月30 日《申报》“自由谈”中的“剧谈”一栏即出现了评论性文章,为丁悚所著,“昨晚(二十八号)新民社初演红楼梦。 从贾琏服中取妾起。 至柳湘莲随道出家止。 故命名鸳鸯剑”,评价其“情节甚佳”,并对何人饰何角色、演出效果如何进行了一一点评,而这种方式也成为了随后一段时期内《申报》剧评文章的主流。 如1913 年12 月17 日铁汉的“剧谈”、 1914 年4 月6 日瘦鹃《志新民社之风月宝鉴》,都采用了这样的评点方式。 其中,铁汉的“剧谈”也是论新民社之《鸳鸯剑》,作者铁汉点评演员及剧情,而后编辑王钝根在篇尾对铁汉不明之处进行解答,也附上了自己对《鸳鸯剑》演出的意见。
或许因为很多剧评的作者与编演红楼戏的新剧家们多为相识,大部分的剧评对这一时期的新剧红楼戏都给出了较高的评价,在肯定演员演技的同时也会适当指出扮演或服装道具上的不足,给出相对温和的建议。 但也有批判的声音,如1914 年1 月1 日“游戏文章”一栏东埜《蒲留仙曹雪芹敬告新剧界诸同志书》中假借蒲松龄与曹雪芹口吻对新剧界改编《聊斋志异》及《红楼梦》的现状表示了不满,认为“惟沪上淫风素炽,剧界为卖座计,恒揣摩社会心理描摹奸淫狗盗形迹,惟恐不尽”,提到《马介甫》《鸳鸯剑》《红玉》《风月宝鉴》等“致观者见其正面而不察其反影,玩其事实而不明其寓意,未能收陶情适性之功,反足为风俗人心之害”,点名批评了聊斋戏《马介甫》《红玉》及红楼戏《鸳鸯剑》《风月宝鉴》,斥其编剧选材偏离原作本意,专挑些低级趣味的风流内容入戏。 王凤霞《文明戏考论》中也注意到了这一篇文章,并提到“可能因为春柳剧场名声不错,作者在文中故意没有点春柳之名”。 实际上这篇文章发布之时春柳剧场尚未成立,还没有开始其红楼戏编演,当时上海编演红楼戏的只有新民、民鸣二社,而其中点明《鸳鸯剑》《风月宝鉴》剧名,几乎可以确定批判的就是新民社,并非作者有意为春柳讳。
冯叔鸾(马二先生)《啸虹轩剧谈》中的《钏影楼剧话之商榷》《驳黄远生之新剧谈》《风月宝鉴剧谈》三篇,针对评剧人的意见,特别对于很多辛辣的批评,冯都给出响应甚至激烈反驳,其中的《驳黄远生之新剧谈》,反驳的就是远生于1913 年12 月30 日《申报》剧谈栏目中刊登的《上海之新艺术》一文中对新民社《大闹宁国府》的批评。 “今来上海,友人相语以上海新剧之多及进步,强往观之,某日观某社之红楼梦,其演贾母,不啻一老鸨,凤姐尤二姐不啻一花烟间,贾琏直似耍猴子精卖眼药者。”面对远生的讽刺,冯叔鸾开门见山直承“某社”即新民社,其红楼梦剧为《大闹宁国府》,平心静气解释演出的前因后果,而后反唇相讥:“且徐而思之,尤二姐凤姐之人格,若在今日之上海社会,纵不至如花烟间,亦未必不似卖淫妇,即加刻划,又岂得谓之唐突。 至于谓药风之贾琏似耍猴子精卖眼药者,则余更有所未解,以余实未尝能如远生君之博闻,生平究不知耍猴子精卖眼药者之果作何状也。”
结语
早期话剧即新剧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清末上海及天津的学生演剧,但终究范围过狭,未能深入民众。 而日后王钟声、任天知等对于新剧的尝试虽被诟病为“化装演讲”,在艺术上尚有种种局限,但实质上扮演了十分有力的中国话剧先行者角色。 至民国成立,气象一新,新剧开始从萌芽逐渐成长,且终于有闲暇从救亡图存的主题中暂时探出头来喘一口气,新民社等排演《恶家庭》《尖嘴姑娘》等“家庭戏”的成功对描述贵族家庭生活的小说《红楼梦》戏剧化也起到了较大的催生作用。 民国时期红学兴起,具备一定文学素养的剧人对小说《红楼梦》的兴趣和研究也促进了新编红楼戏的诞生。 冯叔鸾在《啸虹轩剧话》中论述自己在新民社编演红楼戏的创作思想,《黛玉葬花》的作者之一张冥飞在《古今小说评林》中对《红楼梦》进行评点,而欧阳予倩甚至提到《黛玉葬花》是和张冥飞、杨尘因三人在马桶上信口编出来的,如非熟读《红楼梦》断不能至此。 归根结底,红楼戏在这一时期出现且逐渐走向繁荣,还是离不开众多知识分子对编剧甚至演剧的直接参与。 这一时期红楼戏的创作主力为冯叔鸾、马绛士、欧阳予倩等人,虽然这些红楼戏几乎都未有剧本传世,且有些红楼戏在作者归属问题上尚有暧昧之处,但无疑可以明显看出一个崭新的剧作家群体正在逐渐形成,且广告中出现明确的编剧署名已经表示其具有了一定的作为剧作家的自觉性,从这一点上看无疑是当时的“新剧”在尝试向现代戏剧转型中的重要一步。
民国早期的红楼戏出现了新剧一家独大的局面,以新民社及春柳·新剧同志会为代表,红楼戏的作品数量以及演出次数都堪称繁盛,然而或许是因为这些新剧的剧本鲜有传世,故相较于后期的京剧红楼戏来说,学界研究的关注还远远不够。 虽在本文中未能涉及,但如继续往下追究民国红楼戏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这些新剧红楼戏不只是发端,更是桥梁。 因为后期的京剧红楼戏作品有很多是从这一阶段的新剧作品中脱胎甚至直接改编而成,且早期从事红楼戏编演的新剧家之后长期活跃在戏剧界的不在少数,剧团的重组和人员的流动也促进了交流,无论对红楼戏的发展还是在中国戏剧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总而言之,上海是民国红楼戏演出的重要舞台,红楼戏的编演在上海呈现出得天独厚的活力景象。 虽然远隔近一个世纪,但幸而有《申报》等重要数据得以留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民国上海红楼戏演出的整体情况以及内部联系。 关于民国红楼戏,还有更多的具体面貌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和探索。
注释
① 本文中的《申报》广告内容皆引自《申报》影印本(
上海书店1982 年版)
,以下省略。②⑦[12] 《自我演戏以来》,《欧阳予倩全集》第六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年版,第55、55、49—50 页。
③ 冯叔鸾《啸虹轩剧谈》,中华图书馆1914 年版。
④ 详见王凤霞《文明戏考论》(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
第九章第二节“新民社始末”。⑤ 郑正秋《新剧考证百出》,中华图书集成公司1919 年版。
⑥[13] 王凤霞《文明戏考论》,第320—321、321—322 页。
⑧ 《申报》1914 年8 月14 日刊有杭州第一舞台《风月宝鉴红楼梦》的演出广告,或许是受到新民社等影响,但因本文将研究范围锁定在上海,且篇幅有限,故本篇中选择暂时不将杭州第一舞台演出的这部红楼戏列入研究范围。
⑨ 阿英《红楼梦戏曲集》,中华书局1978 年版。
⑩ 徐扶明《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45—247 页。
[11] 梅兰芳述、许姬传记《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平明出版社1954 年版,第91—92 页。
[14] 冥飞、箸超等《古今小说评林》,民权出版部1919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