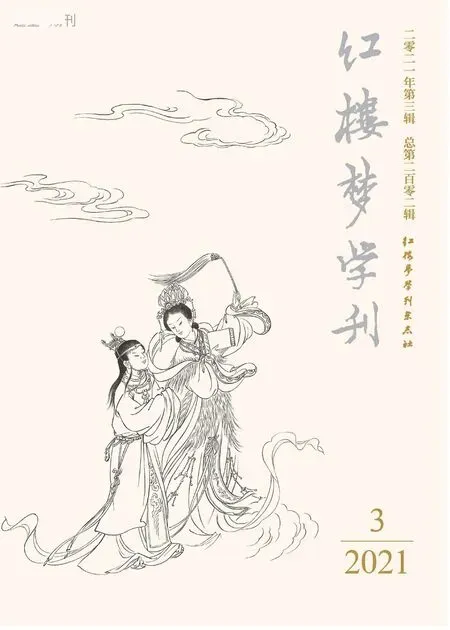论《红楼梦》在当代日本社会的传播价值*
——以王敏的翻案改编为中心
吴 昊
内容提要:进入新世纪的日本社会表现出更多的后现代性症候,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伴随着流行文化浸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青年群体中尤为如此。 辩证地看,这种现象并非完全得益于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深入人心,更现实的原因是诸如企业、家庭等公与私的场域内普遍存在阻碍个性发挥与个人独立的传统封建因袭。 在此社会大语境里,华裔学者王敏以翻案小说的形式改编了《红楼梦》,故事以平等为终极理念、以“个性伸张”和“女性独立”为主人公的奋斗目标,适应又针对了当代日本社会的现实弊病,使中国古典在异域延续了“后世生命”,是寻求《红楼梦》当代价值在日本的有益尝试。
华裔学者兼作家王敏在新世纪伊始的2001 年出版了翻案小说《红楼梦物语版太虚幻境卷》,这是日本《红楼梦》接受史上首次由华裔女性作家操刀改编的《红楼梦》衍生作品。促使翻案诞生的是上世纪末的日本社会现状,后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日趋明显,特别是来自青少年的、女性的、社会公平福祉等现代社会难题亟待解决而又一时难以解决。 针对这些现实问题,作家创作了这部翻案作品。 通过巧妙地设置,作家使中国清代的古典故事在现代的、异域的维度与角度下再次展开,回应了当代日本社会的困局,具有“二次启蒙”的社会影响。
一、寓于现代寓言中的“个性”与“平等”
《红楼梦》原著的结构是头尾两端的神话设置,开篇是基于女娲补天的“亚神话”交代“石头”的来路,结尾以魂归大荒明确了一干情痴孽鬼的归途。 无论曹雪芹还是续作者都以“亚神话”为载体彰显小说的主旨思想。 可见“亚神话”作为小说创作的一种手法,具有提示主旨的作用。 王敏也采用了相同的手法,巧妙地展示了翻案作品的小说主旨。 翻案开篇是如此重组“女娲补天”神话的:女娲决定补天后建立一个新国家,遂委托天帝全权负责,天帝之下又有“荒唐”与“无稽”两神仆负责试炼众多补天石。 由此引出了补天石受训一段:
这些补天石有严格的规格限制,需要统一接受训练。 首先是强度和耐久性测试。 即测验补天石们对水或土石的压力、冲击的耐受度。 最低标准是在百万年的时间内承受百万吨的压力。 其次是同一性和协调性。 补天如若有一处细小裂缝就会造成全面崩塌。 因此所有补天石的形状、质地必须整齐划一。 如果发觉自己与周围的补天石质地不同,那只有努力与之相同。这个同一性和协调性是补天工程独有的要求,除此之外还有“敏捷性”、“独创性”、“反应性”等从未听过的训练涵盖其中。 训练有一千天之久,还没有假期。 这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补天石,全部按时完成了训练任务。
天帝,作为石头的对立面出现,他的人才锻造标准是高度整齐划一的,他代表着现代社会权威、运行规则与统治制度,正是这些标准化的“人力资源生产”引发一系列“现代性问题”。 尽管如此,这种生产仍是强制推行的,它暗示权力抑制、限制了个人主体性。 那么,面对这种制约压力,石头在补天面试时给出了反击:面试官无稽首先开口说道,“你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 你成绩是非常优秀的,可好像听说你对协调性和独创性的训练有点微词”。 石头决意说出自己的想法:“是的。 所谓协调,我认为是所有人、或者说大多数人集思广益、共同做事。 决不是单纯地压抑个性、要求千人一面。 如果非要如此才能出人头地,那我只有放弃了。 尊重个人的独创性、建设平等的新国家,才是真正应该做的。”
石头的故事,与其说是亚神话,更像是一则充满暗喻与讽刺的现代寓言。 石头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要求当权者保护个性、提倡个性,在此基础上达到人皆平等的社会愿景。 翻案将个体差异与平等联系起来,拒绝权威主义制定的“大写的标准”,拒绝以统治阶层的利益为基础给个体做价值高低排序,倡导社会边缘与中心都享有同样的平等地位。 这个主旨设定非常契合后现代思潮,或曰该版翻案小说本就是在日本后现代社会的进程里、在面对日本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下形成改编思路的。 “天帝”可视为日本现代社会运行的资本制度,“石头”则如同字面意思暗喻处于现实社会中的千万普通劳动者。 石头的困惑与坚持折射出日本后现代社会中复杂而深刻的痼疾。 具体表现为战后经济腾飞阶段的工薪族过劳死、武士道转化成现代日企里的“忠诚度”要求、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度的“大锅饭”、鼓励以公司为家、贡献到死的“现代企业文化”。 众多工薪族就是同质同构的螺丝钉,以统一标准被制造出厂,组装进入每个资本运作的机器工厂中去,如若发生磨损就被废弃,后续自有源源不断的螺丝钉补充上来。 特别是上世纪90 年代日本经济出现颓势后,原本“公司即是家”的田园牧歌式的和谐告一段落,企业自上而下推行绩效分级、末位淘汰制,每个工薪族都被推入“成功组”与“失败组”的比武擂台,进而加速了社会的阶级分化与个体的“异化”。 这样,冷酷又高高在上的现代主义秩序必然招致千千万万如同“石头”的个体的反感与愤懑,“消解权威”、“个体发声”,这些西方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的文化政治诉求,也在现当代日本找到了合适的对接口。
作者没有就此打住,她安排石头要求个性尊重之上终极要求社会公平。 换言之,这则现代寓言真正的目的并非解决个体的问题,而是超越了个体、意在实现“人皆平等”的社会理想。 这在石头对天帝直陈其理想“尊重个人的独创性、建设平等的新国家,才是真正应该做的”时初露端倪,继而这种理念频繁地出现在全书中,与开篇的现代寓言形成了复调式的言说结构。 代表性的改编情节有贾家私塾的描写:“私塾长贾代儒是学术界的实力派人物,在官僚体系中也广有人脉。 ……子弟入私塾时,赠予贾代儒大量现金和礼物,因此风传他利用入学大肆敛财。 而私塾的现状是聚集了年龄和家庭环境差异很大的青春期男孩,秩序混乱。”除了道貌岸然的贾代儒外,翻案还择取了贾雨村、薛蟠的故事,正是这些身边的丑恶现象刺激了宝玉,促使他直面社会秩序与权利结构中的自我:“宝玉从这些事情见识到了社会人狡猾的生存方式和普通人对权力的弱势地位,不禁悲从中来。”作为贵族大家庭嫡子继承人的宝玉,也积极而深刻地自我反思:“总是侍女环绕、华服裹身、珍馐尽品的自己。 虽然生活舒适,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欢乐。 毋宁说是无聊吧! 男人们总是酒啊、花啊、赌博啊,一味沉溺在快乐中,悠哉悠哉地活着,不用辛苦工作。 宝玉对想学习却交不起私塾学费的秦钟顿生同情,心情沉重。 高贵是什么呢? 高贵不就是罪恶吗? 高贵是不可饶恕的。”这是难能可贵的。 抛却贵族身份的舒适,不认同贵族阶级的生活态度,对出身贫寒的玩伴秦钟换位思考,翻案宝玉在反思中触及到了平等理念。 为了突出宝玉的思想特质,作者继而发挥了原著闹学堂一段,设置了一个小吏儿子对宝玉揶揄讽刺:“地方上的小官吏都有护官符并任任相传。 宝玉,你犯了错也没事! 因为有护官符保护你呢!”宝玉愤怒了,“你别说这混账话! 人不都是一样的吗!”“人都是一样的”这句台词多次出现、贯穿始终。 可见,平等是整个翻案的思想核心。
平等之所以成为该版翻案小说的核心精神,须追及到文本(text)产生的社会大语境(context)中。 翻案出版时间是新世纪伊始的2001 年,其原因可在当时日本社会的变革中寻到答案。 如前所述,90 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福祉神话逐步瓦解,竞争带来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这些严酷的社会现实推动日本社会阶层差距扩大化、显性化。 一时间学术界冠以“差别社会”的书籍成堆出版,社会上检讨之声不绝于耳,却苦无良策。这些都使普通民众意识到了社会生活中处处存在的“不平等”。 然而,对于这些大多出生于战后的普通民众来说,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主轴的战后民主主义编织出的“人权”与“民主自由”的宣传早已深入人心,说它是现代日本人的集体无意识也不为过。 这就形成了民众认同的“人皆平等”的基本理念与越发“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 因此翻案宝玉挂在嘴边上的台词“人不都是一样的吗?”这句追问与呼吁便是本世纪初日本社会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政治话语。 它一方面说明了纵使高度发达的日本现代社会也存在着诸如特权垄断、贪污腐败等反现代性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社会需要文学作品不断启蒙、不断涤清。 这就是该版翻案故事落实到现代日本社会的意义活性所在。
二、“平等”之大观园中的“女性独立”
“平等”是贯穿全书的纲要,它不只体现在宝玉身上,也体现在黛玉等女性故事中。 女性故事与女性群像本就是原著的一大特色,红楼女性角色之多、篇幅之重、意义之深,蔚为大观。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 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干裙钗实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如果说作为男性的曹雪芹对女性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与关怀,那么作为女性的王敏则直接以女性立场重写红楼女性故事。 整体结构是,以警幻仙子训诫宝玉开启女性故事,以此提纲挈领分别重塑了黛玉、熙凤这两个重要人物形象,字里行间流露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试看作为女性故事引子的“宝玉梦游警幻仙境”一段的改写:
警幻道:
“这个世道,令人悲哀的还是男性中心。不管多么出色的女人,都不可能与男人有同样的工作。所谓出人头地,最多就是嫁个好人家啊,或者给富人做妾。 也就是说,女人是男人的玩偶,工具而已。 我这薄命司里收录的都是男性社会里被蹂躏的女性的悲哀记录。”……
“纨绔子弟们定会如此解释‘
淫’:
我们虽好色,但绝不会沉溺其中。 我们发生关系,可彼此有情,因此不是‘
淫’
。 大家都不知道真正的‘
淫’
是什么。我看他们就是纯粹的性游戏,什么情啊、不沉溺啊都是自我粉饰的话罢了。”……
最后警幻以开玩笑的口吻说:
“但是啊,你才是真正理解‘
淫’
的人啊。 你天分里生出对女性的痴情,你把女性看做是美、是崇高。 不是肉体的,你是与她们心心相通。 是精神的恋爱!
那就是‘
意淫’
,真正的‘
淫’
。”原著警幻仙子对宝玉论“淫”,是不占男女一方地抽象讨论“情”为何物;相比之下,作者以警幻之口旗帜鲜明地指摘男性中心社会里女性的从属地位;“玩偶”“工具”毫不客气地撕破了纨绔子弟以“爱”为名的面纱,最后重新定义了“意淫”,可谓坐实了翻案的女性立场。 首先,“意淫”的精神基调与原著是基本吻合的。 其次,翻案把原著对意淫的定义“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能语达”转化成形而上的“美与崇高”。 原著“意淫”近乎于现代意义上的“爱情”,是不排除性爱的男女情感关系。 而翻案的“意淫”则“洁化”了,过滤了性爱的生活性,将小说的女性观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 这是日译本历史中不曾有过的阐释。 由此也能看出女性作家特有的创作特征。 以此提纲挈领,宝黛故事也即将上演。 与原著相似的是,宝黛是亲密的玩伴,两人共享相同的价值观;与原著不同的是,宝黛之间不是苦于恋爱受阻,而是黛玉渴望独立、宝玉从旁支持:“女孩子们,现在已经开始自己走自己的路了。 不被传统因袭所束缚,自己开拓未来。”这是宝玉的心灵独白,也是作者为宝黛之恋赋予的新的心灵契合点。 同时也应看到,宝黛恋情已然被稀释了,小说表达的重点由“爱而不得”移置到黛玉的人生规划的雄心壮志上。 试看作者杜撰的宝黛共话女性生存之路片段:
黛玉(
对宝钗想进宫的想法)
听了道:
“确实做女官生活有保障。 但宝姐姐这样的能人还有别的可做。正因年轻才应做些有益之事。 只是这世道是女人凭借男人的地位生存,如果宝姐姐想靠女人的武器出人头地的话,那我也无话可说了。”最后这话有点过头,黛玉不觉想到了去世的父母的教诲:
“往后就是你们的时代了。 无论事业还是婚姻都能按自己的意思行事,你们创造这样的时代吧。 但是也别忘了身为女人的自豪和责任。”黛玉明白,社会虽说是有能者上、公平公开,但是究竟还是依仗着家世背景的官僚组织结构网。就像从前的先生贾雨村,他一直教导黛玉做人要一身正气,但当官后就惧怕权者、转而追求私利。 黛玉对贾雨村自食其言很失望,但她仍期待着有朝一日离开外祖母的庇护,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有块立足之地。 她暗下决心,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磨炼自己。黛玉已经不再囿于填词作赋聊以自慰,而是越界出贾府放眼社会。 她冷静地接受了社会的腐败污浊,但仍旧心怀理想,试图凭借个人努力支撑起自己的人生。 这个角色巨大的变化不仅在日本改编史上独树一帜,也对日评《红楼梦》一贯“扬钗贬黛”的传统话语模式形成了冲击。
同时,对于另一位重要的红楼女性熙凤,翻案也设置了很大的表现空间。 作者在熙凤亮相之际,就用旁白形式提前交代了贾琏的风流糜烂,使读者快速地明确熙凤光彩照人背后尴尬艰难的处境。 作者为熙凤单设一章篇幅特写,篇章名为《细腕繁盛记》,记叙熙凤协理宁国府、弄权铁槛寺一段。行文多用心理独白方式揭示熙凤内心活动,突出其精明强干、谋略算计的女能人形象。 如面对贾珍恳求出山时暗自想到:“大家都说我好强能干,而且心直口快又周到。 老祖宗也信得过我。 我苦心算计,说话也中听,也有人来问我生意经。 做生意,这些对我来说还是事儿么? ……打今天往后月余时日,便可掌握贾家实权。 就等着听他们说‘真不愧是凤姐啊的话’吧!”原著采用旁白道:“那凤姐素日最喜揽事,好卖弄才干,今见贾珍如此央他,心中早已允了。”明显地,作为男性作家的曹雪芹采取了全知视角,叙事显得冰冷,而翻案以话剧台词式的现代方式补白了“心中早已允了”的权利女性的私密心态,加强了熙凤与读者的互动。 最能说明作者对熙凤态度的是“弄权铁槛寺”片段:“熙凤操持了秦可卿丧事,目睹了贾府金钱交易的肮脏,也了解了东府乱套的实情。 她预感到可卿托梦中预言的大厦将倾的恐怖。 但她心想到‘我没事的。今晚静虚就带来钱了。 我已经有能力不靠贾家,自己走自己的路了。’”这段可视为作者为熙凤的辩护。 尽管熙凤受贿扰乱司法,但她本身也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熙凤一直用错误的方式实现合理的梦想,展示了人物的悲剧命运。
原著的熙凤形象本就是复杂的,但遗憾的是日评《红楼梦》史上对熙凤是“批判一边倒”,长久以来没有全面辩证的看法。 代表性的名家论述是战前的狩野直喜认为“王熙凤性格阴险多智,不修品行,盛气凌人,能得贾母与王夫人欢心,以其有总理家务之才,乃手握荣国府财政大权,擅威福,而彼之品行颇恶,又深嫉妒,常因其夫贾琏偷腥,大起风波。 贾琏初时欲夺回夫权,然终为王熙凤所压,无出头之日。 中国妇人如吕后或武则天等男子所不及者常有之,王熙凤亦属此类。 其权谋之深,行为之恶,虽男子亦震畏也”。 相比之下,站在新世纪的王敏以女性作家的理解发掘出熙凤凌厉贪婪的内在一面,使日本的王熙凤形象接受更加立体与辨证。
黛玉与熙凤的新形象并非作者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能够勾连出现代日本社会女性的真实生活情况。 虽然战后日本社会自六七十年代经济腾飞、物质生活变得殷实起来,创造了“一亿总中流”的中产神话,但这并不代表男女平等水到渠成。 反之,即便是战后日本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女性就业率仍旧不高,甚至出现了全职家庭主妇热潮。 正如上野千鹤子犀利指出的“什么是近代? 什么是反近代,脱离近代? 传统文化项目顺应它所处的语境,发挥着或正或负的作用”。 可见“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因袭、稳固的性别秩序与女性的惰性仍然交错地存在于表象日新月异的现代日本社会。 再将视野聚焦于翻案小说发表的新世纪伊始的2001 年,彼时的日本已经经济疲软,景气不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格局与社会对女性“贤妻良母”的价值期待,已然在下岗失业率走高等现实的打击下备受冲击,社会上出现了家庭主妇兼职潮、甚至部分家庭是丈夫留守妻子打工支撑生计。 同时,日本政府提出“男女共建社会”规划,官方上为妇女走出家庭背书。 这些都可视为翻案黛玉性格的社会语境因素。 黛玉就成为这股社会潜流的代言人,她懂得利用社会性话语解决自身问题,代表着新生代日本女性的普遍想法。
以女性立场叙说女性故事是该版翻案小说的一大亮点。 除了最能体现女性独立意识的黛玉,还有以离开贾府独立门户为人生目标的王熙凤,并不承认自己是红颜祸水的尤三姐,默默支持黛玉的李纨,并不独断裁定子孙婚姻的贾母。 这些女性形象脱胎于清代旧式贵族女性,但却都染上了现代社会的光彩,折射出现代社会不同性格类型的女性群像,共同作为平等主题下的一个故事分支,演绎着处于当下日本社会各种困局与迷惑中女性的挣扎与思索、突围与救赎。
三、改编在日本当代红学研究中的地位与意义
王敏的翻案小说是立足日本后现代社会现实的基础上的,她借男女主人公之口提出了一种面对封闭社会环境的青年突围之策。 即突破自我定式,积极联通社会。 这可视为作家给日本社会现实开出的一剂药方,是翻案的最大特征。 然而,放眼望向日本当代红学领域,却呈现出一种迥然不同的氛围。
首先,与该版翻案同时期面世的是作家小林恭二在2006 到2010 年连载在知名杂志《世界》上的《水彩红楼梦》。 他将宝玉塑造成只知美女享乐、胸中无物的混世魔王;将黛玉变形成嫉妒成性、病态刻薄的麻烦制造者。 全篇以欲望叙事为主脑,奉行的是快乐主义哲学。 如果说王敏翻案是形而上的理想主义情结,那么小林恭二便可概括为形而下的群丑狂欢。 这种类型的改编作品在日本改编史上并非首创。 战败初期1953-1954 年间华裔文人陈德胜自费出版了《新说红楼梦》,以荒诞淫乐为卖点,将《红楼梦》改编成日式的官能小说,导致名著面目全非。 新世纪以来陆续出现的同人小说、电子游戏等也采取了类似情色化做法,以中国古典的异域风情招徕消费者。 从他们的改编效果来看,形而下地解构《红楼梦》只能走情色化路线,加重原有的男女情节使之成为卖点。 这样原本属于精英阶层、强调精神境界的名著就摇身蜕化成了供大众性猎奇、情绪发泄的消费品。 这类改编中的主人公普遍都是性爱符号,特别是宝玉,没有被赋值以思想,仅是游走于章节之间用以引出性爱描写的工具。 这种名著在大众文化中的“重生”现象,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分析的那样:“当经典文化重生的时候,其本来的含义早就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具有反抗现存权力机制的功效;原本那些使人们疏离现实、保持冷静思考的意蕴也已不复存在。”虽然这类改编数量不多,也未形成时代潮流,但七十多年来从未间断。 这说明始终有作家谋求在大众阅读市场赚取噱头,不惜牺牲《红楼梦》的文学性。 换言之,以性爱为卖点的“红楼梦”已经是商品化了的、丧失文学本真性的消费文字,由此反衬出王敏版翻案的可贵之处。
其次,日本《红楼梦》改编史上迄今为止共有两部翻案小说。 另一部是战后初期由翻译家饭塚朗(日本第三套全译本的翻译者)执笔改编,连载于《大阪每日新闻》上的《私版红楼梦》。 与王敏版本不同的是,饭塚朗采用个人内省式的视角,借主人公宝玉将自身对人的存在感、人的社会身份建构、人与他人的依存关系表现出来。 可以说,饭塚朗指向主人公本体存在的哲学思考,是一种内在的心灵絮语。他的思想内核是“自我”,而且是带有日本文学传统私小说性质的,隔绝社会关联的“自我”。 与之不同的是,王敏在半个世纪之后再出翻案,走的是与之相反的联通社会、解决社会问题之路。 其中很大原因在于作者自身的写作特点,用作家本人的话来说,“读者应该觉察到《红楼梦》是酷似现代社会的书。 现代日本青年中屡屡爆出的未婚妈妈、COSPLAY 现象,都是每年举办成人式时候骚动的话题。 不仅如此,青年与父母断绝关系的新闻也层出不穷。 ……世纪末的日本诸相突显出来。 《红楼梦》与经济高度增长期的日本有着重叠之处。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此前隐藏的各种问题一齐喷涌出来。 日本没有解决的方案而困顿不堪。 这种状态不就是‘红楼梦’吗? 因此,我觉得此书是能预见21 世纪的珍贵之作。”由此看出,王敏创作的眼光总是瞄准于现实社会有感而发的。 另一方面,处于新世纪的日本青少年群体的一大问题就是过于泛滥的“自我”。 如前所述,战后民主主义是现代日本社会的思想主轴,“个性自由”是战后民主优势的极大体现,在普通日本民众的认知中多以“自我”来表述。 “自我”这个概念在战后语境中引领舆论导向,负载了多方意义。 除了正向表达之外,“自我”也成为了利己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的遮羞布;或者是回避现实、蜷缩不前的挡箭牌。 这种现象在青少年中尤为常见,那些经济弱势、地域偏僻、学力不足的青少年,借助“自我”表面上维护了他们脆弱的神经,实则是阻止他们走上社会接受锤炼的麻醉剂。 过于泛滥的“自我”也是导致当代日本社会被称之为“无缘社会”的原因之一。 诸如年轻人的丧文化、中老年的孤绝心态、全职主妇精神世界苍白等后现代问题。 高自杀率的“无缘社会”早已铺开,个体犹如孤岛,一人一星球,彼此之间缺乏积极有效的沟通,甚至连与他人沟通的意愿都很难产生。 换言之,日本现代社会常见的“自我”多数是只留意于个人情绪的“消极自我”,是种单向性的、固步自封的个体话语。 这种“自我”需要超越,成为外向性的、开放式的、与社会交流的双向性的自我,用来疗愈当代日本的社会痼疾。 而该版翻案便借助《红楼梦》既有的结构向日本社会提供了这样的“积极自我”的方法。 某种程度来说,这可视为战后思想家竹内好、沟口雄三式的“作为方法的亚洲与中国”的后现代延伸。
最后,该版翻案在日本的《红楼梦》改编史上可谓是个孤例,或曰一个统合系统内的“熵”,不同于日本的接受小传统,不能简单地化约到某种改编思想流派中去。 正是这个“熵”能够给系统提供新一轮更新的启发。 回首日本的红楼改编史,情色改编不值一驳,“消极自我”昙花一现,在新世纪的时代风土中如何续写红楼故事? 这版产生于社会、联通社会进而改造社会的、具有现实价值指向的作品,不啻为《红楼梦》改编的新思路。 一般地,名著改编是从高雅文化到大众文化,作品在跨越两个对垒的文化场域的过程中,大多数是从对抗性的、异质性的、超验的文本变成同质的、可预见性的、去政治化的文本了。 但是,此版作品并没有走日本改编的老路,究其思想根源,具象地看是王敏本身基于女性的生命感悟、生活体验与华裔学者身份,创作出不同于既往的日本本土的、男性作家的改编作品。 更深远地看,翻案的思想内核不正是积极入世的中国文学精神?原著对封建礼教的质疑与反思,对婚恋自由的憧憬与争取,与现代日本社会普通人对资本运行制度的抵抗、对传统性别秩序的突围,发生了重叠,或者说从文本抽象出的两个图式具有某种互文性。 因而以中国古典之矛,攻彼后现代社会之盾,可开辟出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 进入后现代社会的日本面临的诸多人的困局,现代性的难题,在日本的人文学界谋求解决之际,中国古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化能够透过翻译改编的形式为其提出一个思路、一种做法、一些启示;同时也使得中国故事浸润到现代日本人的心灵深处。 这对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都是双赢而有益的。
注释
① 王敏(
1954-)
,日本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作家。 御茶水女子大学博士。 主要以宫泽贤治研究为中心展开丰富多彩的研究。 作为第一位给天皇讲授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她长年致力于中国文学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现在活跃于中日文化交流事业。 翻案小说,是改编原著的时间、背景、人物等的二次改写,是日本接受外国小说的传统形式。 日本对《红楼梦》的翻案有二,一是战后初期饭塚朗的《私版红楼梦》,一是王敏在2001 年出版的《红楼梦物语版太虚幻境卷》。 王敏除了本书之外,还于2008 年在讲谈社出版过《红楼梦》的缩略译本。 该缩略译本是原著故事梗概的精要拔萃,与本文研究的翻案改编作品体裁不同。 本文是以王敏对《红楼梦》的翻案改编为主的研究。 文中的翻译是笔者所加。② 亚神话,是神话的一种亚型,或者是一种模仿。 它只有神话的形式,但没有神话的思维方式、阐释意义、宗教功能,取而代之的是具有艺术表现方式、审美价值、社会意义等。
③[
日]
王敏《红楼梦物语版太虚幻境卷》,ソレイユ
出版社2001 年版,第10—11 页。 文中有关引文皆出于此,恕不另注。④ 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线装书局2014 年版第1页。 文中有关引文皆出于此,恕不另注。
⑤ 日本评论界对黛玉形象的总体评论是认为黛玉是病弱的才女,性情孤僻,不善人际关系。 战前代表性的发言是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狩野直喜,他认为黛玉不具备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特征。 战后左翼文学观兴起之际,评论界普遍认为黛玉反映了不受封建礼教压抑的进步意识。 但是,同时也有松枝茂夫提出的“情人太太论”,奥野信太郎提出的“绢丝毛丝论”,都是扬钗抑黛的立场。 进入新世纪后,有如井波律子等女性评论者的登场承认了黛玉性格中也有坚强的一面,但整体来看日本大部分评论仍是相对消极的。
⑥ “细腕”,根据《大辞林》,基本义项是“细的、瘦的手腕”,引申义为“气力弱。 生活力弱”。 王敏以“细腕”指代王熙凤的女性属性和社会地位;然而,又用“繁盛”与“细腕”形成相悖之感。 修辞上的矛盾可见熙凤形象的复杂性。
⑦[
日]
狩野直喜著、张真译《中国小说戏曲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114 页。⑧[
日]
上野千鹤子著、吴咏梅译《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第134 页。⑨[
英]
约翰·
斯道雷著、常江译《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81 页。⑩[
日]
王敏《要译红楼梦》,讲谈社2008 年版,第10 页。[11] 无缘社会,指的是现代日本社会中,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人际关系淡漠等触因,人与人的血缘、地缘、社缘的关系弱化现象。
[12] 战后日本思想界的中国研究中,占有独特位置的是竹内好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亚洲”、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 两者思路共性在于试图从中国的思想、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寻找战后日本社会发展的多种借鉴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