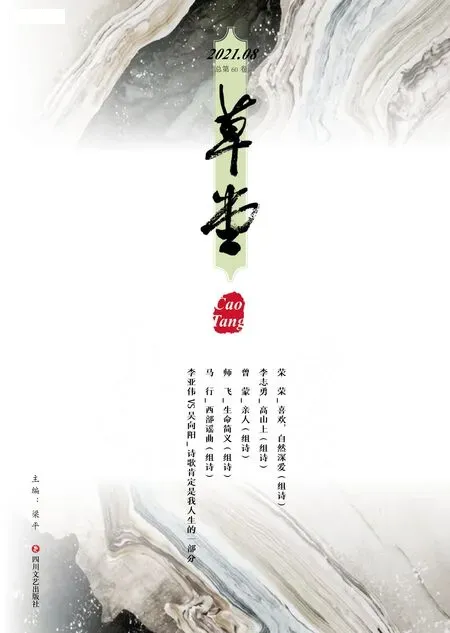“灯光照着不可描述的人间纯洁”
——读荣荣组诗《喜欢,自然深爱》
◎王彦明
一
所有人的写作,几乎都有一条隐秘的暗线,串联着时间、技艺与精神向度。就荣荣的写作而言,这条线可以观照到辛弃疾、聂鲁达及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群体;而在题材层面,她的写作是驳杂而充满生机的,固然爱情的言说一直贯穿其间,但是由此生发出的对个人精神的审视、对时代症候的省察、对传统精神的复归,都是值得我们反复体认的。 沈苇认为,荣荣的写作过程是一个从“尖锐”到“和解”,从“挣扎”到“省悟”,免于陷入虚无的泥淖,不断走向成熟和开阔的过程。当是确论。
写作进入到一种“大自在”境界而返璞归真,除却年龄与阅历的影响,个人所求同样不容忽视。在一次访谈中,荣荣说:“有时候也会开玩笑或者赌气地说,我将辽阔让给你们,我独守我的一分真二分温柔三分小。”退身向后,并非示弱,而是以退为进,回到自我的一隅;“辽阔”有时候反而是一种逼仄。这种抉择基于个人经验,展示了荣荣非凡的洞察力,她明白写作的空间只要与生活对接,就会变得开阔。此时一隅就会“别有天地”。
荣荣所谓的“真”,就是要将写作退回到生活层面,从生活之中汲取力量,谱写个人的生活史,进而构建个人的价值谱系;而她所谓的“温柔”,是要回归女性身份,探寻有别于男性的书写空间,尽管荣荣的作品曾被陈仲义视为“真挚粗放,有男性化特点”,但是纵观荣荣的写作历程,她从未放弃女性身份独有的力量,2014年出版的诗集《时间之伤》就取材于更年期女性的身心精神,这是敏感的女性诗人独特的“创造”;而这里的“小”,就是放弃大而空洞的抒情,与“真”对接,在具体琐碎的事物中,寻找美好与诗意。“我的现实是另外一种,它是大众的、普遍的、卑微的、无常的,有些戏剧性甚至还有些荒诞。我相信,我所说的现实,这是由恒河沙数之多的小人物的命运组成的。”
相对于其他女性诗人,荣荣的“温柔”是独特的,是恣肆的,是随性而洒脱的,摆脱了小家碧玉式的精致,拥有江湖儿女那种洒脱和自得。这种语言的敞亮既是个人阅历的影响,更是性情的外显。仅此,荣荣就足以成为新世纪女性诗人中的独特存在,她细腻不失爽利,温婉不失通透,阅尽人间百态,始终未曾丧失那份天真。
荣荣试图以诗“抵御掉日常的平庸与琐碎”,同时又深深明白诗“生发于日常的平庸与琐碎”,在这个吞吐消化的过程中,超拔乃至峭拔的意义得以显现,情感正是在变化中上升,语言在转换中刷新,诗意因超越而独步。在情感的迂回、校正和探寻中,她的诗将生活之中幽暗的部分照耀得明澈、清晰,增加了完整性、光芒和人性的温暖。她的目光探向那些普通的、底层的、不幸的人身上,写到了邻居、祖母、妹妹、钟点工、疯女人、出租车司机……而切入的却是现代人身心困境。她饱含深情地凝视万物,为世界保留了一份美好与珍贵的希望。
其广受好评的《一个疯女人突然爱上一个死者》,就是以“疯女人”的非理性视角、独白式的戏剧化语言表现了女人对爱情的理解和寄托,与之形成呼应的是她的《过错》,表达的是“一个缘于完美的毁灭者的内心呼号”,那种飞蛾扑火的赤诚就是一种爱的复归与召唤。这两首有着明显的差异,却都让我们在这个消解深情的时代里,感受到了传统爱情的炽热。即使是《钟点工张喜瓶的又一个春天》这样承载痛感的作品,我们也可以在细节中,感受到那种对底层人民关爱的目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荣荣的诗有母性的光芒,照耀着这个有些裂痕的世界。
二
仅从题目来看,“喜欢,自然深爱”呈现了一种简单的爱情伦理,当然视为一种精神趋向也未为不可。这里的逻辑是非常微妙的,“自然”来得过于急促,甚至省去了一个深入的过程,直接抵达了情感的巅峰。我们可以在这种逻辑里得到一种直接的欢愉,这种撇去暧昧关系的纯粹,忽视了物质、经验和秩序,而直接表达为一种朴素的情感。
不可否认的是,情感的复杂性,人心的复杂性,不是一个词汇就可以恰如其分地盖棺定论。“暗中那瘆人的撕裂声无人听见,/她仍爱着,爱所有的悔不当初!”(《她爱他所有的当初》)如果《过错》是那种情感的喷射,有赴死的决绝,这里的情绪就是暗流涌动,在词语的内部衔接着心绪的转移。这是时间在诗意上的刻舟求剑, 由此产生的焦虑、怨怼、不满、悔恨和无奈,依然化解不了深情,“爱所有的悔不当初”是在摧毁的前提下叠加,是负负得正,是要毁灭逻辑和秩序——显然,爱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当我们再回到这首诗的题目《她爱他所有的当初》,就已经可以感受到背后的包容与珍视,而这种情感的时间性,总是充满落差感,当时的温情脉脉,当时的深情、快乐、甜蜜,在现在只能是“一圈圈慢慢褪去的身影”。这种黯然是火焰的消失,是黑暗的降临。
荣荣有很强的时间感,除了表现为物象的转换,情感的迁移也是一种呈现方式。我们习惯在今昔、虚实里进行对接,荣荣的“昨日”“当初”“过往”有深深的当下焦虑与期许。这种复杂的情绪,是“时间之伤”,也是热爱的余烬。“一个且行且远的原点,注定跑偏的剧设,/像身体磨损,容颜更替。”(《她爱他所有的当初》)也许想象的修复术可以还原面孔,甚至记忆可以剔除许多糟糕的记忆,但当下的纠结却越发深重。像《残菊》这样的作品,就是在物象与心境的对接中,形成了对时间的触摸。“残”和“菊”都有很深的时间性,“菊”带有的引申属性,“残”带有的时间割裂感,把记忆打碎、混淆,乃至丢失。“细碎的波纹在心里漾开时,/我看见了一朵残菊。”这里向前推进的“细碎的波纹”,是捡拾、模拟、拼贴和还原的过程,不可避免的还有篡改和遗弃。
消解和凝结,在荣荣的作品里,表现为一种反向互助的作用,遗忘意味着深刻,深爱传达为怨怼,卑微转述着深挚,错乱体现着清晰……爱情的逻辑就是如此繁复。“此刻,广场上所有无深意的零碎,/都如台阶错落,小径浅白。”(《会展广场的午休时分》)“无”和“零碎”肢解了深情,诗句却在轻巧的节奏转换里,透露了内心的欢喜。“她的多情不被允许。/她等待的祝福,也永不会来到。/只有被篡改的记忆, 一本写坏的书。” (《全程》)词语进行着碰撞、抵牾,情感一再降低诉求,这种示弱何尝不是一种深情。 就像“她的任性只在想象里”这样的诗句,在限制之中,压制了深情,却释放了万千委屈。
荣荣从来都是一个在场者,她讨厌那种遮着面具的不爽利,她的声音回荡在内心的剧场。她的独白、低语和对话,都是在具体的情景中,炽烈地、真挚地、痛苦地展开。偶尔那些对白也会忽然跳脱一下,形成新的局面。“我无法给你我的最初,/至少让你为我画个句号。”(《遗存》)这一处直接引用,却写出多少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在这一组诗中,荣荣转换了视角,从最初的直接抒情者转换为了对他者的观察,即便如此,她的抒情依旧有一种不容置喙的执念。“她有重复的煎熬,疼痛,/她有重复的绝望。”(《全程》)她的反复就是强调,就是确指。偶尔她的抒情还交叉在情境的叙述之中,“为什么还能飞,不停地起落,/锢于一个狭隘又顽固的/早被预设的内心边界。”(《任性》)那种架空的“任性”总是来自期待着的幻想和预设之中,在彼此的钳制和撕扯间,若隐若现。
可以说,爱情诗在荣荣的创作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几乎她所有的诗集中都有,尽显一位女性诗人的敏感与炽烈,那种哀伤而甜蜜的情感,复杂而真醇。她不断转换着视角、表达方式,对过往、当下的心绪进行摹写和传递,她建构了一种爱情美学范式,而此种建筑烘托起来的却是一种人生经验之上的人生态度。“还有半明半昧的灯光,/曾照着他们勉强保留的外在清白和/不可描述的人间纯洁。”(《一场告别》)明与昧、内与外的渲染和氤氲之间,写作者的真诚和精神秩序都显现了出来。
三
如果说,“勉强保留的外在清白”暗含了一种情境的还原,“不可描述的人间纯洁”则体现了荣荣情感的价值建构,我认为“半明半昧的灯光”可以视为氛围的营建,体现了外物与内心的呼应关系。我愿意放大一点,将这“灯光”扩展为荣荣写作的技艺,而照耀的则是她所有的深情。 就像前面我谈及的,荣荣的写作已经抵达返璞归真的“大自在”境界。她的写作呼应了她的视野、情绪、呼吸和想象。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她的技艺,因为炉火纯青,所以拥有很深的自然感。如果不借用显影的方式,很难发现。
“想象力、表达力和入世之心”,是荣荣抛却女性身份,确认的诗歌应该具备的要素。这种“入世之心”是她始终如一的坚持;而她的表达力主要体现在她对词语的把控、对结构的整合和对固有秩序的“冒犯”上。荣荣擅长在结构之中,形成一种韵致。“那里清风是你,明月是你,/缺失的风景也是你。”(《任性》)这种重复形成的淡淡爱情与忧伤一起袭来。“那里,她可以娇小如甜点,/或是白月光,睡前故事或热奶。/她可以要求这样要求那样,/她可以停留,昨日重回,/看时间一圈圈慢慢褪去他的身影。”(《她爱他所有的当初》)种种假想都是以词语的重复来递增情感的热度,但是在迂回中,又回到了最冷寂的部分。
就像“这样”“那样”这一类词语,当然可以增加想象的疆域,同样在表达上也温婉如耳语,有淡淡的亲昵感与亲近感。荣荣就是这样把一些俗词、不起眼的常用词增加了美感、节奏和韵致。词语意义的扩散与压缩,在于作者的调动。在《过》这首诗中,荣荣运用了29个“过”字,甚至还拆解了这个字,体现那种切肤之痛:“‘我爱过你。’现在,中间的过,/横,竖钩,点,点,横折折撇,捺,/是过失,是过错,是过分。”这种拆解汉字的步骤和情感历程的转换存在一种暗合,同时也在时间上形成一种延宕,及至最后一句,就更是一个词一个词地切换与深入,从可原谅到不可原谅,背后隐含的是爱情世界里的步步退让与对方的变本加厉。作为一个时态助词,“过”意味着完成;作为名词,则意味着错误;作为动词呢,是过失的过程进行。荣荣几乎调动了这个词语的每一种词性,在时间和精神的双重层面,传递悲伤之情。有语言洁癖的写作者,往往拒绝重复,但是荣荣却选择了另辟蹊径。
荣荣曾写过关于“看”的几首诗,几乎都关涉视角的转换问题,其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向内的探视,譬如:“我看见自己在打一场比赛”(《看见》),“这个曾经的仰视者是否在高处/俯瞰着天空并有了造物主的忧患?”(《看》)对自我的理解与分析,是她关注生活中的看天者、打篮球者而引发的沉思。荣荣有这样一种能力,不仅可以增加词语的光华,还可以赋予万物以深情、深意。“我写万物”与“万物写我”的辩证关系里,体现的是写作者的表现能力。在荣荣的早期代表作《白洋淀》里,她就将“看”与“思”,或者说物象与精神,进行了高度融合。《在恩钿月季公园》这首诗,显然深得李清照“人比黄花瘦”“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这类作品的神韵;《毛乌素沙漠》同样如此,毛乌素沙漠尽化为情感的附属,支撑着情感的脉络。这类作品是在托物言志,更是个人深情外显于世界。
荣荣的诗有一种保鲜功能,发展得很缓慢,自然做旧也慢,阅读便会生发新的慨叹。她拒绝了周遭消费世界的影响,甚至有时候还从传统中寻求帮助,来构建壁垒,抵御“风”和“乱花”的影响,坚持在日常生活里探寻“内心渴望的精神高度”。随着阅历和见识的提升,那些来自生活中的热爱与忧伤、温暖与绝望……都逐渐变化为理解、宽容和顿悟的原材料。她守住了自我,续接了传统,试图以自己的微光,照亮那些冷了的心、孤寂的梦,以及那份“不可描述的人间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