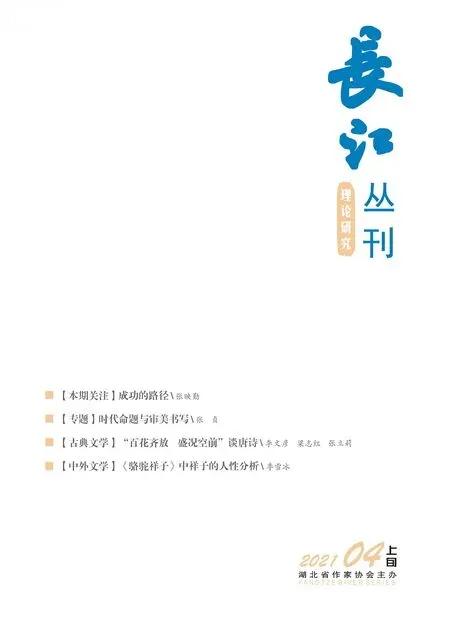生命的富余
——雷默《大樟树下烹鲤鱼》
■项 静
看雷默的小说,不由自主地跟南方联系在一起,不唯地域,我们并没有什么严格意义上可以分享与理清的南方写作特质,只是约略地谈论一种写作的面貌。它可能是简约的因而是留白的,可能是尺度狭窄的也由此而带来情感的密度,它们瞩目于花草虫鱼带来的生活趣味,却并不吝啬于以柔克刚的可能,也未必会忘却借由想象与虚构抵达的大道。比如死亡,詹姆·斯伍德把它看作核心真理,在文学和生活中,我们经常记得真实人物去世的细节,还有小说人物去世的细节,这自然毫不奇怪。他反问到,难道不是因为在这些时刻里,作家从包围着、威胁着让细节灭绝的危险中抢夺来生活的细节,以及细节的生命力吗?这是生命的富余,把生命推至死亡以外,超越死亡。
小说集《大樟树下烹鲤鱼》中好几篇小说写到过逝者,他们在幸存者们的脑海中不断闪回,以儿童的天真未凿之气,把人从世俗烟火和现世情节中短暂拉开,回到童真视域中真假难辨,此世与彼世的交接模糊地带。逝者们(死亡)不是突兀地穿越现实世界,而是借助小说中孩子们的眼睛,或者天真而感伤的情绪。他们还借助时间和技术复生,在真实的世界中影影绰绰,继续着庸常岁月与往事流年的交集。
《祖先与小丑》像是一首关于父亲的散文诗,零零散散的生活细节在父亲去世这个事件增加了一份沉重,法师为不存在的孩子取一个名字,五味杂陈,荒谬与仪式隆重、人心的哀痛,微妙的情绪一波一波地震动在心间。而在父亲去世的头七,“我”突然发现自己想不起他的模样,越用力想,他的身影越往后退。父亲去世时并不存在的孩子出生后,填补了父亲的空白,奇怪地链接起阴阳两个世界,扫墓的时候,“我”感动于孩子的童言童语,紧紧抱着他,仿佛与过去、父亲融为一体,“失去的都已经回来了”。《你好,妈妈》妈妈去世后,爸爸带着两个调皮捣蛋的男孩子,他们在各自的内心世界中保存着妈妈的样子,哥哥金甲记忆中的母亲是大波浪披肩发,父亲的衣柜中锁着旧时照片,从未见过妈妈的“我”只能想象着她的样子,父亲带两兄弟离开旧居换一种运气和生活,直到有一天两兄弟重回旧居,仿佛与记忆撞个满怀。《盲人图书馆》盲人在爸爸妈妈离异后,珍藏了一张照片,一直在想象和询问别人妈妈到底是什么样子。这几篇小说都创造了一种回到过去的装置,怀恋旧时光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补足了现实缺憾的瞬间圆满感。《祖母复活》是一个跨越五十年重新复活的荒诞故事,与祖父阴差阳错彼此错过,是生活中命运中二次错失的爱情故事,雷默的小说仿佛一直陷在一种生活的错失感中,历经生死劫难,是生活的大恸,他把这些处理成淡淡的忧伤与命运的低语,是认清了生活和生命的本质之后,做出叙事选择和姿态,如《你好,妈妈》中金甲金乙两兄弟搬家后,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是问自己,我在哪里,他们心心念念的是“那时候,我们完好无损。我们也很快乐”。
雷默还喜欢创造一种陌生者之间互动的情感空间,小说中人物的故事与叙事者之间有微妙的互动。比如《盲人图书馆》盲人持续的来访给图书馆这个既定的平静生活圈带来骚动,素昧平生的图书馆管理员惦记着来阅读的盲人,他的生活、突然的一点改变、身世和未来,搅动了另一个小世界,甚至打破了“我”与其他人之间的隔阂。《大樟树下烹鲤鱼》是同名小说集中比较复杂的一篇小说,小说承载了更多人世的风尚。这篇小说首先是异人异事,大隐隐于市的小人物传奇,老板老庄颇具名士风范和古风,在大樟树下摆两张小桌,不放凳子,客人们都站着吃,全中国都找不出第二家这样的饭馆。他一般只招待熟人,陌生人去,得看他心情,心情不好,给再多钱都没用。老庄一道红烧鲤鱼远近驰名,还有生活的哲学在里面,吃鱼和做鱼都要节制,每次杀鱼都留下一个眼珠,杀到一定的数量,老板毅然结束了烹鲤鱼生涯,留下无数玄想却绝不食言。小说的最后是老庄在当地一个重要人物的丧礼上放生鲤鱼,并亲手雕了一只可以以假乱真的豆腐鲤鱼,以假代真,震动了叙事者和围观人群的内心世界。这篇小说容易让人联想起汪曾祺的《异秉》、阿城的《棋王》,仿佛一个遥远时空的故事,跟你我没有多大关系,但又像多了一双眼睛,逼视着我们现世的生活。
雷默的小说与这些性格秉性独特的人物一样,有一种恰切的自适和精神的富余。它可能来自于小城生活的质感,物质世界的规则尚不足以形成牢笼,于是在实名制的风土与虚构故事之间调配出合适的距离感和亲切感,仿佛这些人物与故事散落在我们周围,自由恰切地各自生长存活,不会过多打扰或者刻意去寻求呼应,但你知道他们一直存在,并且安心于他们各自的故事和灵魂波动的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