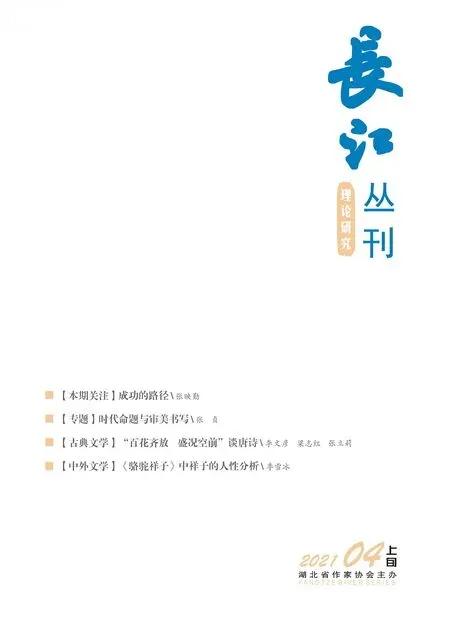密码的“隔”与“不隔”
——读雷默的《密码》
■陈怡彤
没有刺激感官,没有一味求新,雷默用一贯冷峻的语言完成了《密码》的叙事。小说讲述了大学毕业之际,女友苏梅跟“我”回厦门见家人的故事,故事的推进,正是密码逐一解开的过程。
密码是雷默设置的隐喻,它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虽无形,却经由我们的想象和感受真切地存在着,将世界分割成密码锁内和锁外。密码的真实可感,是因为我们总能找到前因后果:山东厨师把精致的粤菜烧成了东北菜的豪爽模样,空间的阻隔、气候的差异是南北之间密码、隔阂形成的原因;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在“我”眼里越来越像个怪物,真相的延迟使“我”对母亲产生了间隙;“我”和父亲在苏梅面前谈论母亲的病症时经常使用闽南话,听不懂闽南话的苏梅被我们隔绝在外,主动使用闽南语这一行为其实暗含了现实的艰涩——“我”和苏梅不上不下的关系,家丑不可外扬、亲疏有别的观念,“我”和父亲的尴尬……
人们总是偏好稳定的事物,对稳定的追求会让人拒斥“外来因素”。正如小说中来自不同地域的个体,他们凭借着地域相似性寻找到自己的同伴,形成群体,这些群体经过一次次的设密,组建出了无形的秩序以维持着内部世界的稳定。苏梅是哈尔滨人,当她听见刚上车的福建人嘲笑大厨将粤菜烧成东北菜的模样时,“翻了翻白眼”,嘀咕他们有地域优越感,瞧不起东北菜。个体在所属群体中不同程度地建立起了认同感,通过贬低其他群体,进一步探求自我与群体之间的关联。
密码是一种“隔”,也是一个“勾子”,引得锁外的人总想突破隔膜,走进那个未知的锁内世界。在小说中,“我”和父亲用闽南语谈论母亲的病情时,苏梅总让“我”用普通话向她解释;母亲患病后沉默寡言、一动不动,“我”一直渴望了解她;父亲和苏梅之间有“沟通障碍”,苏梅经常让母亲作“中介人”……密码的“勾子”功能暗示着破坏与汰旧,而与之相伴的往往是弥合与新生。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最后苏梅加入了“我”和父亲的对话,父亲和苏梅因为都不喜欢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变得“志同道合”,“我”得知了母亲背后的故事,苏梅的父亲得知了女儿的近况。小说的主人公们勇敢地拥抱亲密关系、血缘关系等情感联系,让我们看见了密码由“隔”转为“不隔”的可能性。就这样,苏梅和“我”这两个“外来因素”顺着情感的纽带融进了锁内世界,锁内世界的一切和“外来因素”重新编排,开启了一轮新的循环。
读《密码》这篇小说很像在冬日经过一条河流,河流不经意地缓缓流淌,但当你即将离开它时,暖阳照在河面上散射出的光亮又会引你逗留。在后半部分,小说开始解密,最终以母亲想起“我”是谁后戛然而止。这令人诧异的结尾同时伴随着一团悲哀,连解开密码后的喜悦也化解不开。些许是密码解开后又揭示出了一片更大的混沌吧,那里夹杂着人生的无常。毕竟密码不是故意设置的,背后总是有一系列因果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但“我”和苏梅明明相爱却最后分离的情节又让人想到密码有时候又不完全受制于因果,人生的无常就在此处用孑然一身的预言恫吓我们。比起用“赤条条无牵挂”进行自我欺骗,我更愿意用《死亡诗社》的台词“因为你的存在,因为伟大的戏剧正在继续,你可以奉献一首诗”,拥抱无常,因为它让我们即使悲伤仍能拾起继续走下去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