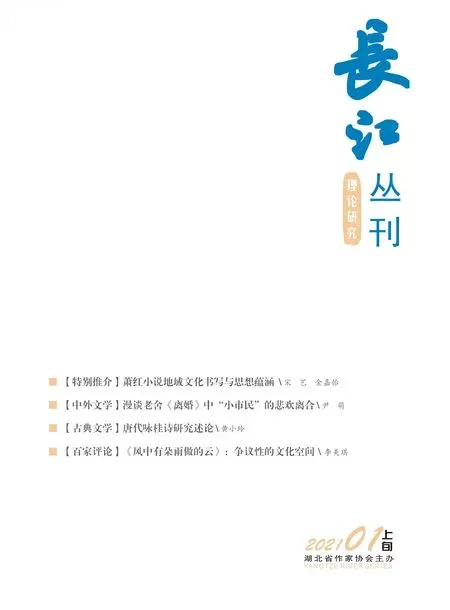楚山孤
■林东林
1
一位穿戴还算干净的老人仰坐在大成路菜市场门前的空地上,一只手撑着地面,另一只手举着拐杖,朝周围的人不停地指指点点,试图阻止某个正从他身边走过的陌生人。路人纷纷侧目,但并没谁停下脚步——他们或许觉得他精神有问题,或许觉得他在碰瓷,等他们中的一位把他扶起来后,就会被他或某个及时赶到的人讹上一笔。就像奔流向前的河水碰到石头一样,人群在快要经过他时自动向两边分开,等绕过他后又再次汇聚起来,继续向前。
这是几年前的一天早上我见到的一幕。当时我也是看了好一阵才明白,原来他是想找个人把他扶起来。是的,我帮了他这个忙。他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土,忙不迭地对我说谢谢。我问他家住哪里,要不要我把他送回去。他说不用不用,我可以走。然后他就走了,没有不能走或随时会摔倒的意思。我放下心来,目送他走进人群,直至消失在两条路的叉口。
这本来是一件我遇到的你也会遇到的任何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小事,但是一周之后我又碰见了他。这一次是在我租住的小区。当时他正坐在一条长凳上,在我看见他之前,他就先看见了我并认出了我。哎,小伙子!他站起来,用那根拐杖指着我问,你也住这里啊?我迟疑了一会儿,继而认出来是他,便说,哦,您也住这个小区?他点了点头,示意我坐下来。
坐下来,看着他,我在脑海里一遍遍快速搜索着我在小区里见过的那些老头儿,想把他们中间的某一位和眼前的他对应起来。我们小区住着不少他这个年龄的老人,我经常见到他们遛弯儿,在那排健身器材上荡来荡去的,或者目光呆滞地盘踞在那几条长凳上……按理说,在我租住到这里之后我应该见过他才对,但我对他一点儿印象也没有,换句话说,我完全不能把他从我见到的那些老头中区分出来。——这也不能怪我,事实上他们身上似乎已不再有什么个人特征,老,因为老而带来的行动迟缓和样貌变化,就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特征。
至于那天早上坐下来之后,他说了些什么,我又说了些什么,时至今日我差不多已经完全忘了。只记得他问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多久了,是买的房子还是租的房子,面积有多大,租金是多少,之类的。租的,五十多平,每月三千,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他操着湖南一带的口音说,那也还是挺贵的嘛!说完之后,他就陷入到自己盘算着的什么事情里去了。
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我这个,而我的回答又会对他有什么用。与此同时,我也不知道他的身份、年龄,等等,但是他看上去很有可能比真实年龄还要老——而后来果然也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当时我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主要是因为他满脸的老年斑、手臂上松松垮垮的皮肉和几乎掉光了头发的红褐色头皮。尽管坐在长凳的另一侧,和他相隔着两个身位,不过我还是能感受到一股衰老的气息不断从他那边传过来,被我看到、闻到、听到。
吊诡的是,这次之后我时不时就会再碰见他。在小区门前的那条小街上,在楼下绕花坛和树林一周的矩形步道上,或者健身器材旁边的那几条长凳附近,还有一次也是在菜市场——我进去时他正拎着一条五花肉出来,那块猪皮上盖着一小块深蓝色的椭圆形印戳。最开始我还会跟他打个招呼,闲扯几句。后来再看见他而他没看见我时,我就会提前躲开。尤其是散步时,如果看见他又坐在那条长凳上,我就会在到达他不能发现我的某个位置时绕回来,反着走;等走到另一侧又快接近那个位置时再绕回来,如是反复。是的,我在躲他——怕没什么好说的觉得尴尬?不愿意接近他那种衰老的气息?又或者怕他拉着我问这个那个?
2
我住在建于上世纪90 年代末的一个小区,住户大多在周围上班或上学。像很多小区一样,每天等他们去上班或上学之后,小区里就安静了下来。除了骑着电动车一趟趟进出的快递员,带小孩玩滑梯的一两个女的,在健身区锻炼的老头儿老太,几乎见不到什么人。我经常会在这个时候下楼吃早点,去一趟菜市场,或者散步,然后再上楼去看看书,写写东西。
小区不大,只有五栋楼,四栋小高层罗列在周围,中间是一栋低层楼房。低层楼房及其前后的花坛和树林——健身区就在树林之中——周围,就是我经常散步的那条步道。步道一侧花木茂盛,春天有美人蕉、玫瑰、石榴花和各种盆栽,夏天有苍翠的竹林、团团如盖的棕榈和散缀着果实的桑葚,秋冬还有漫天红叶的枫树,以及那些一年四季常绿的低矮灌木丛。
小区西侧,与花坛相隔着一条步道的是几排老房子。红瓦灰墙,中西合璧,据说是新四军留下来的古迹。那些房子已经多年没住人了,墙体剥落,山梁垮塌,院子里的荒草有半人多高,其间散落着垃圾。这就便宜了那些成群结队的流浪猫了,它们把那儿当成了自己的家,在房间里睡觉,在草丛中嬉戏,在屋顶上跑跳,或者摊开了晒太阳,也经常到小区这边来晃荡。饿了,就在小区变电房楼下的墙角里吃喝一番——那儿放着几只豁了角的破碗,经常有老人把剩饭剩菜倒给它们吃,很多次路过时我都看见那几只碗总是被舔得干干净净的。
在我几乎快忘了那个老头的一天中午,我又碰见了他。当时我走侧门花坛穿过来,就在我将要穿过花坛一半时,他喊了我一声。我吓了一跳。这儿呢!他站起来,摇晃着那只拐杖说。我说,是您啊,您躲在这儿干嘛呢?!他戴了一顶帽子,穿着一件老式对襟唐装,比之前精神了不少。我注意到他旁边铺了张卫生纸,上面有几块饼干和两根已经剥开的香肠。
他往旁边指了指。我先是看见一排冬青树,然后又看见了卧在那儿的一只橘黄色的老猫。接下来,他把饼干掰成小块,把香肠也都掰成一小截一小截的,一块块投过去,先投到那只猫的身子底下——它衔起来吃了,又投到它前面一点,然后一次次地缩短投递的距离!
后来我又在小区里碰见过他几次——背着手遛弯儿,在那条长凳子上长时间枯坐着,再不然就是喂那只橘猫,好像他一天到晚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从没见什么人和他一起出现过,一个年貌跟相仿的老太太,一个他子女那么大年龄的中年人,一个他孙子孙女模样的小孩子,没有,一个都没有。我想他可能是一条老光棍,一个丧偶的老鳏夫,大概是这样。
再后来,就像为了解答我的疑问似的,我见到了他儿子一家。那是前年中秋节,那天早上,我正出去时,他刚好从外面进来,旁边跟着一对中年男女和一个小学生模样的小女孩。那个男的提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子,那个女的拎着一盒月饼,那个小女孩则抱着一床毛巾被。他不无骄傲地跟我介绍说,——我儿子,——儿媳妇,——小孙女儿。他又把我介绍给他们,把几年前我扶他起来的事也说给他们听了。他儿子忙摸出烟来给我让了一根,又点上,连声说谢谢、谢谢。这让我觉得他还是很幸福的,至少比我之前想象的幸福多了。
3
我们小区本来就有一个停车场,后来又新辟了一个,但这些车位仍然满足不了年年增加的私家车的停放需要。后来,小区里的步道两边也都停满了车。这些乱停乱放的车辆以及它们堆积出来的空间,就成了那些流浪猫撒欢的乐园。它们在车前车后追逐嬉戏,从这个车顶跳到那个车顶,或者钻到车底下睡大觉。早晚散步时,我经常被从车顶上跳下来或从车底下窜出来的它们吓一跳。我曾不止一次地担心过它们中的一只说不定哪天会被突然发动的车辆轧死。果然,这样的念头冒出来还没多久,有天早上我真的就看见了一只被轧死的猫。
轧死它的那辆车已经开走了,只剩下它躺在那儿——不是躺,准确地说是被粘在了水泥路面上,身子下面是一小滩暗红色的血迹。能看出来,临死前它经历过一番痛苦的挣扎,现在它仍然保持着那个挣扎的姿势——四扬着爪子,像要抱住点儿什么。一个女的和一个小男孩走在我前面,前者边走边数落后者,快踩到那只死猫时她才发现它。接下来,就像被某种力量弹射出来一样,她一下子撤出去老远,然后就捂着鼻子,领着那个小男孩绕了过去。
被轧死的是一只黑色的小奶猫,并不是那个老头经常喂的那只。也不知道为什么,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松了一口气。而接下来,我又看见了那群凄凄惶惶的流浪猫——大大小小竟然十几只之多,它们时不时往那只死猫的方向望一眼,发出来一两声尖厉伤感的低沉之音。
是的,我还没热心到要打扫那只死猫的地步。我继续一圈圈散步,只是在路过它时就像那个女的一样远远绕过去。转到第三圈时,我就看见他——那个老头——从门洞走出来,提着一只搓斗和一把扫帚。他扬了扬手里的家伙冲我说,有只猫被轧死了,我把它丢了去!
我还以为他把那只死猫扔到垃圾桶或者隔壁的院子里就完事了,没想到他还那么郑重其事——不知道他从哪找来一块木板,在那棵开满了火红石榴花的石榴树底下又刨又挖的,弄出来一个小坑。他又把死猫丢进去,填上土,又踩几脚,把上面那层松软的泥土都踩结实了。是的,尽管做不到,但我可以理解这一点,尤其是对他和他这个年龄的老人来说,如果子女不在身边,如果子女的子女也不在身边,他们就会把泛滥的爱心释放给那些小动物们。
等我再次转过来时,他已经从花坛里出来了,坐在他经常坐在的那条长凳的一侧——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知道他是在等我。怕他一时伤感,我走过去,在长凳的另一侧坐下来。
我们的正前方是一片火红的石榴花和几株开得烂漫的美人蕉,不远处是微风轻轻摇动的竹林。花木茂盛,风和日丽,眼前的一切似乎很快就把那只死猫从我们脑海里驱除干净了——至少从我脑海里驱除干净了。我们坐在一棵樟树的树荫里,一缕缕阳光透过细密的枝叶撒下来,撒到我们身上和我们身后那堵斑驳灰白的水泥墙面上,日斑散缀,交织堆叠出来一圈圈明暗相间的光晕。而那只橘黄色的老猫,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跑了过来,横卧在距离我们几步远的一小片阳光里,半眯着眼睛望着我们,继而睡着了,身子一吸一鼓的,间或发出一阵阵悠长安然的呼噜声——眼前的一切似乎也很快把它死去的同伴从它脑海里驱除干净了。
他说,小伙子,我经常见你在小区里转啊转的,不用上班吗你?我说,上啊,只不过不坐班。他说,你做什么工作?我说,编辑!他说,报社的还是?我说,杂志。他又问,什么杂志?我本来不想说的,但还是说了,诗歌杂志。他眼睛里闪了一下说,诗歌杂志好啊!我以为他只不过随口那么一说,就没再去接他的话。是的,我当然没有告诉他我还是一个诗人,一个作家,也没那个必要。接下来,他又问我做忙不忙,收入怎么样,老家是哪里的,有没有结婚,为什么还不结婚,有没有女朋友,之类的只有我七大姑八大姨才会问的问题。
我耐着性子回答了他,同时觉得人到了这个年纪真是麻烦——被人嫌弃,还不知道为什么被人嫌弃。他又说,小伙子,现在没什么事吧你?我说,没什么事,怎么?他站起来,拿上搓斗和扫帚说,走,到我那里坐会儿!听他这么一说,我顿时为自己的诚实和没有及时离开感到一阵后悔。去坐会儿嘛,坐会儿,喝杯茶的功夫,耽误不了多长时间!他说道。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到他那里又有什么好坐的,但是又不太忍心拒绝,于是就跟着他去了。
4
他住在小区最里面那栋,底层。一进门,一股老年人住久了的气息就扑面而来,同样的气息,二十几年前我在祖母独自住了很多年的那个小房间经常可以感受到。现在,重新置身于这样的气息中,我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二十几年前,在某个瞬间我甚至产生了一种这样的幻景,觉得祖母好像随时会从里间颤颤巍巍地走出来——虽然她已经去世整整二十年了。
进来后,他就开始忙前忙后地烧水、刷杯子、沏茶。我说我不渴,不用泡茶了——同时我也不好意思直说怕他刷不干净杯子,或者茶叶可能已经发了霉。他没听,继续忙活着。
他和我租住的那套房子的结构几乎一模一样,一室一厅一卫,带一个小阳台,这种房子估计是开发商统一装修的单身公寓。不过,相比于我那边,他这儿采光差多了,客厅的三面墙壁上都没窗户,唯一采光的地方是通往阳台的那两扇玻璃推拉门——而他还在上面挂了一道布帘。我过去把那道布帘卷起来系住,阳光通过地面折射过来,房间里这才亮堂多了。
重新坐下来,我才注意到挂在对面墙壁上的那两副字,一副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另一副是“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我不由笑了笑,我知道同时也不止一次地见识过,很多刚入门的书法爱好者和县市一级书协的老家伙们都喜欢写写这种内容。虽然不写字,也不懂字,不过我能明显感觉到眼前这两幅字写得很一般,横撇竖捺,中规中矩,完全谈不上什么个人风格。这两副字都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因为落款是同一个印章,篆文阴刻,张龙标。
沏好两杯茶,他给我端过来一杯——杯子里外都刷得很干净,茶叶也是清亮碧绿的。
我指着那两副字说,这个张龙标的字写得不怎么样嘛!他一脸诚恳地说,是不怎么样,还要多练习,怎么,你也练书法?我说,我不练,不过好坏能看出来一些,这个张龙标的字明显不行!他笑笑说,这个张龙标就是我!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竟然一直不知道他名字——也从没想过要问他姓甚名谁。我尴尬地笑了笑说,其实我也不怎么懂字,乱说的!乱说的!然后我就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了,一直埋头吹杯子里的那几片茶叶,小口小口地喝水。
他又说,我这房子也是租的,儿子给我租的,一个月三千一,比你租的还贵一百!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想起之前他问我是租的还是买的房子,租金多少。我说,您儿子也在武汉吧,怎么没跟他们一起住啊?他说,他那哪有地方给我住,有,儿媳妇也不情愿让我住啊,这儿挺好,一个人住清净,也习惯了,我是12 年来武汉的,老伴一死我就从老家过来了!
我说,您老家哪里?他说,湖南黔阳,唐朝时我们那儿叫龙标,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来的。我说,好名字,有历史!他又指指阳台上说,武汉有黄鹤楼,我们那儿有芙蓉楼,是大诗人王昌龄贬到我们那儿时修建的。经他一指我才发现,从我们坐着的位置就能看见黄鹤楼,它就矗立在被阳台切割出来的那片天空中——而在我租住的房子里,也能望见黄鹤楼。
一杯茶喝完,我说得走了。他才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说,哦哦哦,我差点忘了!说着他就去了里间。再出来时,他手上多了两个笔记本,他递给我说,这是我写的诗,你拿回去看看能不能在你们杂志上发几首。我还以为他找我来只是聊天,没想到他在这儿猫着我呢!
他的那些诗——如果还能称之为诗的话——四言、五言、七言之类的古体诗,我在回来的路上只翻了几页就看不下去了。是的,想都不用想,肯定发表不了,至少在我们这个新诗刊物上是发表不了的。且不说古诗还是新诗,也且不说平仄和韵律,单单就最基本的文学水准来说,他这些名为《天下为公万古青》《当代老年之歌》《白头老翁享华年》之类的“诗”,在我看来也不具备任何发表价值。所以,上楼后我就把他那两个笔记本丢在了一边。
后来,在接下来的那些天,怕哪天不小心再碰见他、他再问起我他的那些“诗”,我也就不怎么在小区里散步了;很想出去散步时,我就把地点换成了附近的紫阳公园或者是蛇山。
此后的一两个月,我确实没再见过他——虽然偶尔还是会想到他,去楼下扔垃圾时或者在街上遇到一个跟他差不多的老头时。我不知道这段时间他是怎么过来的,是不是还经常在那条长凳上一坐半天?去花坛里喂喂那只老猫?或者写写那些算不上书法的书法,写写那些根本不会有人看的“诗”——同时也等待着我的消息?哦,说到他那些“诗”,我不知道他还在写那些破玩意儿有什么意义,虽然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写的那些东西又有什么意义。
5
你知道的,这年头做编辑挣不了什么钱,何况还是在一本诗歌刊物,何况还是一个兼职编辑。所以我不得不在外面零敲碎打地接一些小项目,去年一年我几乎有一大半时间都在忙活这些。而可能正因为这样,在后来的那段时间里我也就把他和他的那些“诗”彻底忘了。
去年年底,我因为一个项目在广西待了近一个月。回来的那天中午,我看见不少人在小区里进进出出,又是敲锣打鼓又是唱歌的,很热闹,一开始我还以为在搞什么促销活动。后来下楼散步时,我才发现是什么人家里办丧事,在花坛旁边的空地上搭了一顶灵棚。因为小区里之前也时不时地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也就没怎么注意。直到要上楼时,我才猛然看见挂在灵棚最上面的那条白纸,上面写着一行苍劲有力的毛笔字——“沉痛悼念张龙标先生”。
进了电梯,才突然想起来张龙标原来就是那个老头,又想起来他交给我的那两册笔记本和里面的那些“诗”。上来,翻箱倒柜地找了一圈,最后我才在一箱子书的底下找到那两个笔记本——这一箱子书我是准备当废品卖掉的。没错,确实是张龙标,其中一册笔记本的扉页上竖着写了五个字“芙蓉楼诗抄”,右下角是他的名字和年月日——张龙标,2008 年3 月。
翻看着他的这些“诗”,我有点儿难过——不是因为他死了而他的“诗”没发表出来而难过,而是这些压根儿就不是诗,这一点毋庸置疑。是的,我当然更不会因为他的死而把这些东西就说成是诗,然后以安慰一个在天之灵的老人的名义,在我们或者别的杂志发表出来。
打开另一册笔记本时,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宣纸掉了出来。四开大小,折了四折,上面是他抄的一首诗,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没有上款,只有这首诗和旁边的一行小字——丙申仲春于江城武汉张龙标敬书。不知道这是他的练笔,还是准备装裱了送给谁的,也没说送给谁——不过肯定不是送给我的,丙申仲春,也就是2016 年的三四月间了,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
我把字叠好夹到笔记本里,想着下楼交给他儿子或亲戚,但出门前又把字拿了出来。
花坛旁边那个的灵棚,外面摆满了花圈,不断地有人进去,也不断地有人出来。我进去时,里面正热闹着,一些腰间和脑袋上都缠着白布的男男女女正在抽烟、嗑瓜子、聊天。他的黑白照片——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他——摆在一张桌子的正中央,被旁边两个巨大的花圈簇拥着,一边的挽联上写着“父亲大人千古”,另一边写着他儿子、儿媳和孙女的名字,以及他女儿、女婿和外孙的名字——原来他还有一个女儿。而他,现在已经孤孤单单地成了一个古人——化身为了一缕扶摇直上的青烟,或者正安安静静地躺在某座殡仪馆的太平间里。
我先是给他——他的黑白照片——鞠了个躬,然后又找到他儿子,跟他说了说大概的情况,把两册笔记本都交给他——而他到现在才知道自己的父亲竟然还写诗。从他儿子那里,我了解到他是因为心肌梗塞去世的,走得很突然,因为突然,所以也并没有受什么罪。
现在看起来,他走得真是非常及时而幸运。事实上,他刚去世不久,先是武汉,再是全国,继而是全世界,就爆发了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没完全结束的新冠肺炎疫情。而因为疫情突降,我也在武汉封城之前一天回到了河南老家并一直待在那里,直到半年后才回到武汉。
重新归来,继续接轨以前的生活,我又恢复了散步的习惯。他,张龙标,当然已经不在了,但是他经常喂的那只老猫还在——它竟然躲过了这场很多人都没躲过的疫情。我看见它的那天傍晚,它正蹲在小区变电房楼下的墙角边,等着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把剩粥倒进它面前的那只破碗里。是的,它还活着,没死掉,也没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而是接受了另一个老人的喂养。是的,我很理解,它只是一只猫,一只饿了就会到处找吃食的流浪猫而已。
第二天早上我买了一筒饼干打算也去喂喂它。找了半天,才在树林里找到它。像张龙标之前那样,我也把饼干掰成小块,一块块投过去——不过它一口也不吃。我走过去,把饼干往它身边踢了踢,它一下子跳开了,发出一阵呜呜之声,也不知道它怎么回事。我在长凳上坐下来远远看着它,但它并没有像我看着它一样看着我,而是移到一棵树下继续打盹儿。
接着,我就看见昨天傍晚喂猫的那个老太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一前一后地拍着巴掌——手起手落之间,传来一阵阵清脆的掌声。老太从我面前走过去,拐到健身区,登上了一台漫步机,走动起来。过了一会儿,那只老猫也从树林里走了出来,一直走到老太正前方的空地上,蹲下来,巴巴地望着她。我看见老太走下漫步机,从兜里摸出一个塑料袋,又从里面拿出半只馒头,掰成小块儿小块儿的扔到它跟前,那只猫就开始吃起来。看到这一幕我才突然明白,或许它不是不吃食物,而是只愿意吃张龙标的或者一个像他那种年纪的老人的食物——他们喂着它,它同时也在喂着他们;而我,距离他们那个年纪还有一段漫长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