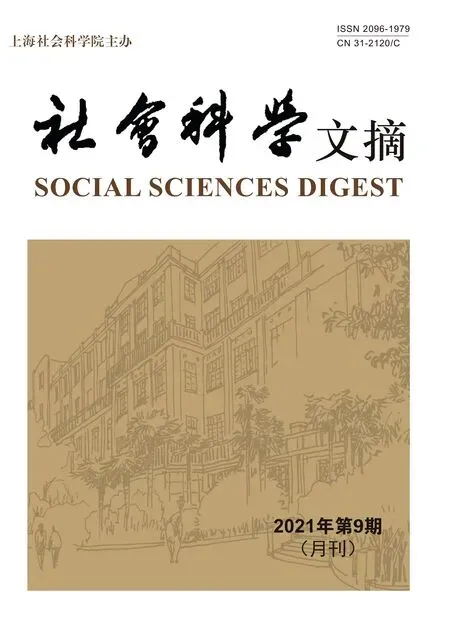清朝“内亚性”的再商榷
——以多民族语文合璧书写为视点
文/强光美
多民族语言文字的共存、并用与合璧书写是清朝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所谓“合璧”,满语称“kamcime”,是指在同一场合或书写载体中同时出现两种及以上文字,且内容相互对照或配合。这一现象引起美国“新清史”学者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卫周安(JoannaWaley-Cohen)、罗友枝(Evelyn S.Rawski)等人的关注,他们将其视为清朝区别于传统中原王朝的“内亚性”(Inner-Asianess)的重要表征。柯娇燕认为,多民族文字的合璧昭示着清朝的所谓“合璧式”,或者称“共时性”(simultaneous)君权,代表清帝同时具备汉人的天子、满洲的汗王、蒙古的可汗、藏传佛教界的文殊菩萨化身等多重身份。卫周安指出,18世纪的清朝用以纪念帝国征战胜利的碑铭,几乎都以满、汉两种文字刻写,有时添加蒙古文,或者藏文、察合台文,多语并用宣扬了清朝的“普世精神”(universal spiritual)和“陆地霸主地位”(terrestrial overlordship),其中注入了一种“清朝特色”(a distinctively Qing colouration)。上述观点强调蒙古、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性,无疑是对以“汉化”和朝贡体系为中心的传统清史研究的修正与突破。但在“新清史”的话语体系中,清朝被设定为统治着汉、满、蒙古、回、藏等诸多族群的帝国,中国则等同于汉人的国家,只是帝国的一部分而已,从而否定了清朝与中国的合一性。事实上,以多民族语文合璧为代表的所谓“内亚性”是否真的构成了清朝与传统中原王朝的根本区别,大有可商榷之处。本文将从清代合璧书写的历史延续性、合璧书写推行的理念和动机、合璧书写与清朝统治者的国家认同三个层面着手,就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
“新清史”学者强调,清朝通过多民族语文合璧书写强化了对内亚边疆地区的经营,这是其区别于传统中原王朝的重要表现,而与辽、金、元等所谓“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一脉相承。与此同时,他们又夸大明清差异,将明朝当成纯粹汉人政权,而有意无意地掩盖其统治中的内亚因素。这种割裂历史连续性的处理方式,容易使人忽视合璧书写在元朝以后的发展演变,从而对清朝推行合璧书写的历史传承性,形成某种片面理解,进而也就放大了清朝的内亚属性。
一方面,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起的王朝,清的统治风格的确有效仿辽、金、元的一面,体现出明显的“内亚”影响。就多语文合璧书写的源流而言,它并非清朝创举,而是“内陆亚洲”(Inner Asia)地区的人们在长期的经贸往来和文明碰撞之中,为方便交流而自发形成的,起初并不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最先将合璧书写运用到国家政治生活中,使之上升为朝廷正式书写模式的统一政权,是契丹入主中原后建立的辽朝。随后,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女真人建立的金、蒙古人建立的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都曾自上而下推行这一书写模式。早期满洲人在政权发展和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常借鉴、效仿契丹、女真、蒙古人的做法。合璧书写作为辽、金、元朝大力推行的重要书写模式,被满洲统治者效仿和使用,自在常理之中。
另一方面,我们更不应忽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一向被“新清史”学者视为典型汉人政权的明王朝也曾大量使用合璧书写,并对继起的清朝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明朝立国以后,由于统治地域的扩大与民族成分的增加,在边疆治理中,不得不效仿蒙古人的诸多统治策略,合璧书写因能消弭文字隔阂从而便利沟通的特殊功能得以沿用和发展,成为明朝官方与新疆、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交流交往的主要书写模式。明朝合璧书写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体现,即中央创设了专门负责翻译边疆少数民族及邻国语言文字的机构——四夷馆,编纂女真、高昌、鞑靼、回回、西蕃等各馆译语,制成汉字与相应地区民族文字对照的《华夷译语》,彻底改变了历代中原王朝忽视非汉文字的局面。
此一时期,“合璧”之功能与内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如果说辽、西夏、金、元时期的合璧书写,主要为推广王朝新创制的文字、宣扬政权的民族属性,是一种重要的民族认同符号,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作用,那么,明朝的合璧书写,显然已经从民族建构和认同的范畴,蜕变为完全的政治手段,是中央政府为有效处理边疆民族地区事务,而采取的一种带有折中主义意味的灵活方式,其结果是合璧的实用性功能更加凸显。但无论如何,合璧书写由于兼具实用性与象征性的双重功能,逐渐发展为历代王朝可资利用的统治手段,已是不争的事实,少数民族政权可以用,中原王朝亦可使用。也就是说,多语文合璧并非内亚特有现象,自然也不能作为判定政权是否为内亚属性的依据。
正如汉人为统治者的明朝可以继承蒙古人为统治者的元朝政治遗产一样,满洲入主中原后,保留和继承了明朝诸多政治制度,其中自应包括以合璧书写为代表的边疆事务处理机制。甚至可以说,清代的合璧书写更多时候是对明朝政策的直接沿袭。例如,清朝入关后即接收了四夷馆,改为“四译馆”,后又继续整理编辑《华夷译语》。在西藏,清朝因袭明制行使主权,颁赐给西藏首领的敕谕文书也保留了合璧书写形式,只是根据时局对文种略作调整,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自然延续,而与其是否为内亚政权,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由上述分析可知,“新清史”学者将一个王朝有没有使用多语文合璧作为判定其政权属性的依据之一,并不符合历史的逻辑。清朝的多语合璧及其边疆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中原明王朝边疆治理经验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二
“新清史”另一位代表学者罗友枝以“清朝在许多方面与10至14世纪的征服王朝相似”,“都追求双语或多语政治”,为其“内亚性”追求的集中表现。但此推论并不能成立。清与辽、西夏、金、元虽然同样使用多语文合璧书写,然其内在逻辑与追求却并非一致。更进一步说,这些所谓的多语政权只是表面上的书写制度类似,背后的政治理念却相距甚远,“内亚性”的判定也便存在疑问。
辽、金、元提倡合璧书写,固然是对统辖区域内多族群文化并存的因应,但究其主要目的,仍在于推广新创制的“国书”,以此维系本族群的文化和身份认同。这方面又以元朝统治者蒙古人最具代表性。有元一代,皇帝和蒙古大臣不仅不愿学习汉字汉文,而且以合璧书写为手段,强行在汉人和境内各族群中推行新创制的“国书”——八思巴蒙古字,不仅要求“南北之民”均学习使用,且从一开始即试图以八思巴字译写包括汉字在内的“一切文字”,使其成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而以此为基础构建新的国家认同。
在这一点上,满洲人与蒙古人有着天壤之别。清朝统治者认为,“盖天下之人,有不必强同者,五方风气不齐,习尚因之有异……至若言语嗜好之间,服食起居之末,从俗从宜,各得其适”。他们提倡合璧书写,虽然也有推广满语满文、保持自身传统的初衷,但并未试图构建其他族群的满洲认同,也很少鼓励甚至是反对他们学习满语满文。合璧书写的目的之一即是因俗而治,各自使用和认识本族文字即可。
由于理念不同,清朝合璧书写的发展趋向也与元朝有异。与元朝合璧书写相伴随的是八思巴字的强行推广,而清朝的合璧书写既有在原文字基础上增添满文、体现“国语”地位的一面,也有根据实际需要,在满文基础上添加汉字等其他民族文字的另一面。清朝统治者对合璧书写的推广,主要出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统治的现实需要,这一点倒是与明朝统治者的出发点更为接近,即更加重视合璧书写的实用性功能。
为了达到更好的治理效果,清朝统治者甚至不惜以合璧书写淡化他们原有的“满洲特色”。如清初八旗、宗人府、内务府等衙门发给外省的文书均以满文书写,为提高行政效率,乾隆四十八年(1783)《吏部则例》规定,八旗等衙门转行外省满文文书,在发出前必须先行翻译为汉文,满汉文兼书。清代官方翻译、出版大量满汉合璧儒家经典,目的即是以中原传统文化加强对满洲人的教化,这一过程恰恰“解构”了其自身的文化认同。
实际上,清朝和元朝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元朝奠定了“大统一”的基础,但蒙古统治者的民族特性也深刻影响到其政治风格。如果说元朝合璧书写是蒙古人维系自我认同的主要体现,具有较强的“内亚性”,那么清朝合璧书写的“内亚性”色彩显然没有那么强烈。元史专家张帆评价道:“元朝是统治民族自身特色比较明显的一个朝代”,“如果用‘新清史’的视角来看元朝,说不定还更合适一些”。“新清史”学者通过清朝统治者推行合璧书写的现象,即得出其与辽、金、元等王朝统治者理念相似之结论,进而以此论证其保持“满洲特性”“内陆亚洲特性”的动机,可谓徒见其形式而不观其内里,得出的结论也就与事实不符。
三
“新清史”学者强调清朝“内亚性”的另一个代表性见解是,清朝政治文化深受蒙古影响,并试图从多方面构建清朝与以蒙古为代表的内亚边疆地区在政治风格和文化传统上的渊源关系。他们甚至认为,清政权代表了蒙古传统的精华,包括使用多种语言的记录方法。这一观点显然意在强调蒙古即内亚因素对清朝政治文化影响的同时,弱化中原文明或者可以称之为“中原因素”的影响,从而印证清朝与以中原文明为核心的传统“中国”之差别。然而,从多语文合璧书写在清代的发展轨迹来看,清朝统治者在文化倾向和政治认同上恰恰经历了一个“去蒙古化”而逐步融入中原文明的过程,突出表现为入关前后合璧体系中蒙古字和汉字的地位消长。
清入关前主要奉行满蒙汉三体并书原则,且蒙古文一度超越汉文,成为合璧体系中仅次于满文的主体文字之一。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登基,“满洲、蒙古、汉官捧三体表文立于坛东,以上称尊号,建国改元事,宣示于众”,从而以国家大典形式正式确立了“三体并书”原则。自此,举凡重大仪式的敕书表文、政书典志的编纂、宫廷建筑的题字、各种纪念碑铭等,均用三体合璧。在各种仪式和表文上,一般遵照首满文、次蒙古文、再汉文的秩序安排,凸显了蒙古的重要地位和满蒙的亲密关系。
但入关后,随着清朝统治者重心的转移和政治文化认同的演变,上述三体并书格局被打破,满汉合璧书写迅速普及。早在顺治元年(1644),清廷鼓铸“顺治通宝”钱,就要求“一面铸‘宝泉’二字用清文,一面铸年号用汉文,颁行天下”。其他如印信、牌符、凭文亦如此改制。清廷还陆续颁布一系列谕旨,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衙门中推广满汉合璧书写。与此同时,蒙古文及其代表的内亚因素在清朝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下降。顺治十三年(1656),清廷谕令太庙牌匾“停书蒙古字,止书满汉字”。此后各坛庙、皇家宫殿园林匾额纷纷“从太庙例,去蒙古字”,这标志着清入关后在礼制化过程中蒙古因素的渐次退场。而以满汉合璧形式书写新的牌匾,则是清朝统治者以一种公开的姿态宣示“满汉一体”,以便获得法理上的认同,进而构建王朝统绪的合法性。这一点与“新清史”强调的清朝统治者一直恪守“满洲之道”和蒙古传统截然相反。
罗友枝还认为,以乾隆帝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的天下观,与历朝儒家君王试图教化所有民众,从而形成文化共同体的儒家思想有着根本不同,因为乾隆帝扶持和发展满、蒙、藏、维、汉五种官方语言。然而事实是,清朝统治者不仅以中原正统自居,而且创造性地利用多语文合璧书写重建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同文秩序。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同文”的内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此时“同文”的精髓不在于文字本身,而在于文字所蕴之“理”。《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等人认为,“文字之声音,越数郡而或不同;文字之义理,则纵而引之,千古上下无所异;横而推之,四海内外无所异”。这里所谓的“理”,显系以中原儒学为核心的道德教化。由此,清廷以合璧书写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同文”意义的活动。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谕令,永陵、福陵、昭陵所有下马木牌,俱改用石牌,“镌刻清、汉、蒙古、西番、回子五体字,以昭我国家一统同文之盛”。清廷还通过开展大型合璧图书的编纂工程,宣扬多元文明的共同发展。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当属乾隆二十七年(1762)武英殿刊刻六体合璧《钦定西域同文志》。该书不仅涵括了当时受清廷认可的满、汉、蒙古、西番(指藏文)、托忒、回字(指维文)六种文字,而且在提要中钦定了各文种间秩序,“首列国书以为枢纽,次以汉书详注其名义……次列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排比连缀”,象征清朝建立起对多元族群井然有序的统治。
在清朝的同文秩序中,汉字一直处于中心地位。清朝统治者甚至将有没有使用汉字作为判定是否符合同文要求的基本依据。例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平定廓尔喀后,清廷决定在西藏统一发行制钱,但乾隆帝对福康安等人所进钱模正、反面均用唐古忒字(指藏文)不以为然,指出钱模“并无汉字,与同文规制,尚未为协”,要求正面用汉字铸“乾隆宝藏”四字,背面用唐古忒字亦铸“乾隆宝藏”四字。清廷在西藏制钱上添加的是汉文而非满文,显然,使用汉字才符合“同文规制”。次年,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请求派人赴西藏学习汉文,乾隆帝甚为欣慰,将廓尔喀人主动要求学习汉字的举动,视为其在文化心理上归顺中国的重要表现。
结语
以上本文主要从历史的延续性、推行的理念和动机以及清朝统治者的国家认同三个层面对清代多民族语文合璧书写进行了考察,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历史的延续性来看,清朝的合璧书写不仅仅效仿自辽、金、元,而且直接受到明朝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中原明王朝政治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这是由于合璧书写兼具实用性与象征性的双重功能,已然成为历代王朝可资利用的统治手段,而非内亚特有现象。
第二,从推行的理念和动机来看,清朝统治者之所以大力提倡合璧书写,主要出于维系多民族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而非保持所谓的“内亚性”。突出表现在,在清朝的国家治理中,合璧书写的实用性功能得到极大程度的发挥。
第三,从统治者的国家认同来看,自入关始,清朝统治者即自觉以中原正统自居,从未自外于中国,并尝试利用多民族语文的合璧书写重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同文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下,“合璧”象征着各族群文化传统在清朝的延续,但其前提是对大一统中国的认同。此外尚需注意的是,在清朝的“合璧”体系中,不同文种之间并非无差别的平等,汉文及其代表的儒家教化长期居于核心地位。
由以上论述亦可知,“新清史”一味强调多语文合璧彰显的“内亚性”,却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其不过是清朝统治者维系王朝正统性和巩固大一统政治的一个技术手段而已。清朝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也完成了从满洲政权向“大一统”王朝的蜕变,成为“历史中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