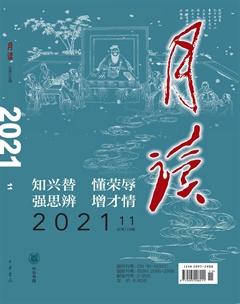元代求唯美的尚态书风
葛承雍

假如说晋人是仿自然的尚韵,唐人是重技法的尚法,宋人是主抒情的尚意,那么元人则是求唯美的尚态。这种传统划分当然是太简略了,而且有些偏颇,但是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各时代的书法主流。再进一步从章法变化上说,晋人将法自然化,唐人将法规范化,宋人将法散漫化,元人则反宋人之道,倡导法的精微化。但无论是赵孟頫还是鲜于枢,那种“浪子回头”式的复古主义势力,既失去了那种“不践古人”的勇气,又得不到悄然远去的“古法”的真谛,犹如作茧自缚的春蚕编织了一个自我封闭的空间,其外壳越深厚成熟,活动的余地就越小。后世评论家把这个阶段的书风概括为“尚态”,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从韵势到态势,意味着笔法的活力更趋衰竭,更依赖于章法、墨法的翻新,人们只能关注个人情趣和风格的差别,而领悟不到风格背后的支撑物和内动力,即精神观念变革的重要性。特别是宋元以来,理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突破,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三纲五常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秩序。这在书法创造思维上,形成了一套不可逾越古人成就的正统思想,整个书苑趋于衰微也就毫不奇怪了。
诚然,对元代书苑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是欠公道的,但整个书苑表现出来的基本风貌就是没有大的建树,虽然大家都在标榜宗法晋人,但实质上并没有学到晋人的神韵和精髓。原因很简单,魏晋书法的内在神韵是由魏晋文人士大夫的心理素质及审美追求决定的,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抒情达意,超逸优游。而元代书法家根本不具备这种潇洒不羁的精神气质和“怡然自足”的自信心,甚至连宋人那种细腻、敏感的心理也不具备。尤其是唐代楷书的极度成熟,更使后世与魏晋之间开掘了一条法度的鸿沟,后人要想越过这道鸿沟而直追晋人是非常困难的。元代的绝大多数书法家,都陷入这道法度的鸿沟而无法自拔,就像舟船拥挤在壅塞日甚的河流里,要想另辟一条通道以获取超越自我的机会是非常小的,反而有可能在一股汹涌不安的潜流中翻船。
此外,元朝统治期间,社会始终没有达到较长期的稳定,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活待遇也不理想,他们低徊抑郁,愁苦凄凉,这恐怕也是影响元代书苑艺术发展的原因之一。
除了赵孟頫、鲜于枢,元代还有一批书法家,如擅长章草的邓文原,擅长行书的冯子振、虞集、吴炳,专学赵书的俞和,以及“行草师二王,婉约丰妍”的周驰,以小篆独步当时的吾丘衍,“正行书师晋人,苍古有力”的揭傒斯,“仿率更父子,力求劲拔”的鉴书博士柯九思,善篆隶的泰不华,“草书亦飘逸”的饶介,“字画清逸”而有唐人风格的張雨等。他们或受赵孟頫艺术复古主张的影响,或直接仿效他的书法,继承多于创新。在赵孟頫的影响下,元代书法家虽然努力复活了各种古书体,如钟鼎文、石鼓文、诅楚文、汉隶、章草等,但终究新意不多,没有产生超越前代的优秀成果,也没有造就出群星灿烂的书法家。像康里子山,“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他的正书师虞世南,行草师钟繇、王羲之,圆劲流便,笔画遒媚,自称一日能写三万字,未尝以力倦而辍笔,墨迹有《颜鲁公传张旭十二法》《谪龙说》《李白古风》《秋夜感怀诗》等。但他的书法“结法少疏”“沉着不足”,没有跳出妍媚温润的意态。其实,康里子山能“名重一时”,倒不是因为他的书法真能光彩飞动、长虹驾海,而是因为他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的政治地位和蒙古贵族的高级身份。
又像耶律楚材,他的书法源于颜真卿、黄庭坚,追求气魄宏大,笔法苍老,尤其是他晚年的字体,率直自然而又奇崛挺拔,泼辣豪放而又点画不谬,似乎给人以刚毅劲健之感。但在线的飞沉涩放、墨的枯湿浓淡、点的稠稀纵横上,仍失之单薄,有呆板的缺陷。其实,耶律楚材的书法也并不是因“落拓不俗”而得到“高标自许”的操行评定,而是因他担任过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的重臣,官至中书令,加之他出生于一个汉化很深的契丹贵族家庭,辅助蒙古统治者治理天下。这说明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占有重要地位,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不多,为艺术而艺术的书法家也少,许多知识分子在直接参政并取得高官显位后,又用自己的书法作为抬高声誉的一种途径。一些人的书法被当时或后世所推崇,首先是因他的政治角色,其次才是艺术建树。
在元代书苑众多书家水平相当、风格也十分接近的情况下,相比较而言,较有个性和新意的书家,应推杨维桢和著名画家倪瓒、吴镇等人。
生于浙江诸暨的杨维桢,字廉夫,泰定年间中进士,后官至建德路总管府推官。由于他为人倔强,所以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官僚网中得不到重视。因而他筑楼于铁崖山,植梅万株,聚书数万卷,自号铁崖,表示自己独倚寒窗,自甘淡泊。晚年居于松江,喜游山水,张士诚、朱元璋都征召过他,但他均加以拒绝,整日追求清新脱俗的新异歌词,并写了许多反映盐民生活和揭露盐商奢侈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

耶律楚材书《送刘满诗》(局部)
杨维桢的书法风格一如其文,奇诡生拙,正是通过这种“独怪”的风格,而超越时俗,独标气骨。他把隶书及章草的特点融入行草中,有意打破隋唐以来整饬严密的楷书规范,用笔草率不工,字形欹侧错落;风格质朴,新奇自然,个性强烈;书风偏于壮美,追求堂皇气象,因而在元代书法家中格外引人注目,被称为“矫杰横发”。他的作品传世的有《梦游海棠城记》《真镜庵募缘疏卷》《壶月轩记》等。刘璋称“(廉夫)行草书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喜”。吴宽则说:“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斨,例载而归,此(廉夫)书或似之。”都说明杨维桢怪诞诡异风格的书法,不入当时偶像如赵孟頫、鲜于枢之列,不合元人所崇尚的欣赏习惯。其实,这种所谓“颠、狂、怪、奇”的书法作品,从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角度来看,往往是书法艺术创新的先锋。我倒认为,杨维桢倔强无润的“狂怪”风格,正是发泄了他满腔的郁愤,以痛快淋漓的“乱世风气”和拔山挽涛的诡形怪状,来打破当时庄肃森严的模式,与其说这是唯我独有的艺术形式,毋宁说是身处元代末期的知识分子表达思想感情的特有方式。
倪瓒和吴镇大概是以士人做画家的缘故,其书法既不像一般书家那样重法度,也从未花费心思去模仿古人,他们采取隐居山林不问政治的态度,用书画来发泄在野士大夫对现实的不满,这就摆脱了复古主义的习气,逐渐形成挥洒自如、孤傲清高的特征,因此比当时其他书家的字都富有自然和清新的机趣,真正是个人性情的流露。

杨维桢书《张氏通波阡表》(局部)。此系应张麒之求,为其建于松江县(今上海松江区)北通波塘之先祖墓地所作的碑文。阡表即建于墓道之碑。
倪瓒的字以行楷书为主,在疏朗的结体里流露出一种幽雅萧肃之感,在细劲的线条中渗透一些隶书的简淡意味,同他“天真幽淡”的山水画一样,其书法也十分空灵,并带有一些禅意。这或许与倪瓒性好洁净迂僻有关,或许与他五十岁后参禅学、卖田产而寄居佛寺有关,总之是要写出胸中的逸气。
吴镇擅长草书,取法于五代的杨凝式,用笔迅疾,奔腾而下,一变“淡墨轻岚”的风格,显得笔力劲爽,墨气淋漓。他曾在村学教书,终身不仕,性情孤介,自号梅花道人,比喻高尚的气节和不争艳的风度,因此其书不以消遣闲情为目的,而以抒发个人性情在元末书苑中独树一帜。
特别是这些人把书法与绘画紧密结合起来,从元画开始,强调笔墨,重视书法趣味,成为一大特色。这是唐宋时期所没有的,画面上有意识地大块留白,以便用书法落款题识,不仅使书、画两者以同样的线条美来彼此呼应,更重要的是通过书法杰作来加重诗情画意,传导文人士大夫的喜怒哀乐和心绪观念。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元代书苑在复古尚态的影响下,书学文集虽有盛熙明的《法书考》,陶宗仪的《书史会要》等著作,但在书法理论上并无多大贡献。他们处在复古主义的旗帜下,以先哲之言为至论、以先贤文体为至善的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了书法理论的突破和发展,甚至影响到明代,因此明朝的论书之作也无足大观。这表明如果一味抱住老祖宗的傳统章程去汲取营养,而不知变革、发展和创建具有时代风貌的理论体系,那么传统的理论财富也会成为阻碍后人前进的、沉重的“金包袱”。
当然,也有极个别的元代书法家提过一些有见地的看法,例如郝经说书法是“寓性情、襟度、风格其中,而见其为人”;虞集强调了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和书法的关系;韩性论述过“理”与“工书”的联系;袁裒概括了“意达”乃能“巧臻”的变化;董内直解释过“无往不收”“无垂不缩”“如折钗股”“如屋漏痕”等特殊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