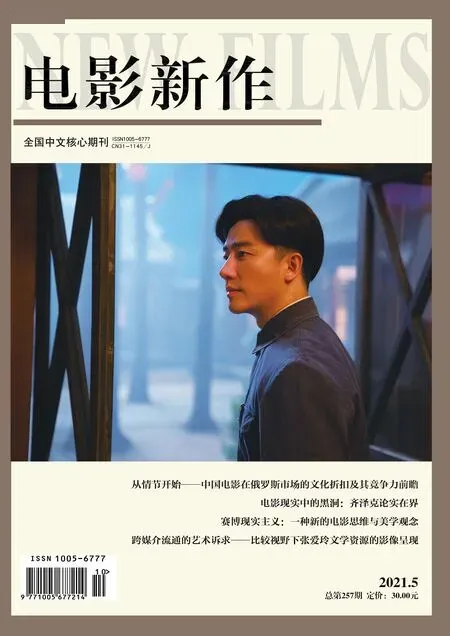开放而流动的同主题影像叙事
——从《我和我的父辈》思考短片集锦的形式美感、延续性和文化全球化
杨俊蕾
三年前的国庆档,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以新颖的短片集锦样式亮相在全国观众面前。大银幕上飘起红色旗帜的画面,以及观众耳边奏响的同名爱国歌曲的旋律,高频闪现的次数远远超过常规剧情片的影像叙事规律。然而,观众们不仅没有因为视听重复而出现审美疲倦,反而被围绕相近主题进行的多角度叙事与多风格影像唤起了注意力和探索心,在距离很近的期待视野中一次次刷新感知。翌年国庆档迎来《我和我的家乡》,整部包含的短片数量较前一次有所减少,并汇入观感更趋轻松的喜剧成分。由于受到2020年“后疫情状况”的连带影响,电影业尚未全面复苏,观影人数和票房表现没有如预期那样,出现后来者居上的乐观场面。由此也给今年第三次拍摄同主题系列的新片《我和我的父辈》以更高的期望、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市场不确定性。正是有鉴于该系列献礼片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二周年国庆档中的具体表现,以该片作为主要对象和入思途径,思考短片电影集或者拼盘式、集锦型影片的形式美感与同主题影像叙事在时间线索上的延续性,以及在文化全球化运行中的对话关系等,就成为需要深入辨析的真实问题。
一、集锦式美感来源于短片间的主题关联,以及整体复合后的全片完成度
《我和我的父辈》在形式结构上由四部短片构成,按照映出的顺序是《乘风》《诗》《鸭先知》和《少年行》。表面上的出场先后顺序,实际上也对应着四部短片在时代取材上的自然排序。第一部《乘风》取材于20世纪40年代的冀中骑兵团,抗日战争的尾声阶段;第二部《诗》在场景铺设中将时间、地点明确标为“1969,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第三部《鸭先知》是在1979年新春伊始的上海;居于结尾位置的第四部《少年行》则横跨了当下与未来两个时间点,先让人工智能机器人逆时空穿越回2021年的深圳南山区,又脱出正常时间运转,再一次将机器人复原后的时间设定在2050年的未来维度。由此排列出“父辈”主题中的时间运行和时代指向,增加短片叙事单元之间的内在指涉。
除了上述时代线索上的着意编织之外,“父辈”主题在导演人选上也包含了寓意明显的一致性追求。吴京、章子怡、徐峥和沈腾都是演而优则导的生动实例,并且都在自己导演的短片中出任了主演。导筒的艺术和表演的魅力彼此辉映,构成四位一体般的话题加强效果。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文本内情节发生时间的有意设定与排列,还是文本外导演阵容的精心物色与安排,都不能越俎代庖,无法取代电影作为第七艺术所特有的视听语言系统化、整体化的规定。
以此次广受观众好评的《诗》来说,画面上暖黄怀旧的色调和精致布光的视觉达到了银幕叙事的基础美感。小男孩相继两次失去亲父和养父的悲惨遭遇一步步构筑起情节运行的落差悬念,营造出人物命运的时代跌宕感。再加上选择适宜的无名诗作在画外音中诵读得当,仿照诗歌中顶真修辞的回旋反复结构,渐次感染着观众们的同理心和共情感。最终导向家国一体的同构叙事,以女儿成为航天员的梦想成真画面,在时空的双向维度上进行家与国的意义联结和结构修复。女航天员的太空视野浮动在火箭成功发射的基础上,是“火箭为了梦想,抛弃了自己”的旨归目的。章子怡扮演的母亲是切割发动机燃料的火药雕刻师,代表着军工技术解密后被誉为大国工匠的一批特级岗位技师;黄轩扮演的父亲则是为了要肉眼观察到发动机的穿火位置而在爆炸中殉职的内燃工程攻坚人员。海清扮演了他们成年后的女儿,乘坐航天飞机进入太空,而这个航空航天器正是由父母倾注生命和心血参与研发的长征火箭推进器所发射升空的。
从火箭基地家属院中懵懂玩耍的小儿女,到21世纪中国正式加入太空俱乐部后的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宇航员,《诗》把国旗出现的位置做了新的改动和延伸,具体而微地聚焦在飞行员制服的胸章上,体现了同主题献礼短片的镜头语言创新。但是,作为完结此段故事并带出下一段改革开放叙事的集锦段落,它难以合适解决的人物与行为难题是陈道明所扮演的哥哥形象。此前,程度最为剧烈的矛盾连续发生在儿时的哥哥身上。他与生父疏离,对养父倔强,和养母一再爆发冲突,对妹妹也只是曾经同放孔明灯的工具化陪衬使用。由此导致的后果是,片中前半段作为主观行动力最强的中心人物在故事尾声突然转变,降格为纯粹旁观的被动听众。甚至是他和成年后的宇航员妹妹之间的关联互动,也只能通过没有影片内在逻辑指涉的简单设计匆匆一笔带过。以上显露出的问题正是献礼短片集需要格外注意解决的困难之处。
在电影中,画面与画面间的诗意感固然可以片刻地脱离叙事内在的时空逻辑与因果关系,却需要此前潜在的完成丰沛而坚实的情感奠基。短片《诗》在大跨度的时空象征方面进展地迅速而顺利:将火箭的燃烧与建设者的奉献进行了可信的比拟,通过新一代航天员升空成功来印证父一辈牺牲自我的意义。在中国漠北的科研基地与浩瀚宇宙之间构建出起点与目的地的有效联结,片头部分的漫天黄沙,在结尾处被抒情地、诗意地升华美化为太空中的绚丽虹霓。然而,诗意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不能以略去中心人物的核心行为和真实成长为代价。片中的工程师说:“大不了下次拿眼睛看。”火药技师说:“我能把火药精度提高到0.2毫米。”这些真正包含技术关键点的专业行为是科研人才独有的价值闪光,值得选用更有视听含量的画面来表示,而不是在一次次的配角人物台词中单方面地宣布技术攻关开始了、进行着、成功了。
在以《诗》为例探讨了如何加大短片内部的主题与影像之间的叙事密度后,接下来的问题继续指向短片与短片之间的联结关系如何呼应并增强。在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中,短片《相遇》和《夺冠》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出场,前者的故事时间是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者则是1984年中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取三连冠。为了加强上下文间的逻辑语境联系,《相遇》在结束前甩出一个长长的时间拖尾。张译扮演的无名英雄与任素汐扮演的相亲女子在街道上的庆祝游行中再次相遇,却又马上被人流冲散,情节上已经接近闭环。没想到银幕在淡出、黑场之后,又突然在声音层面上插入1981年中国女排在世界杯比赛上第一次夺冠的电视实况转播声,将画面重新推回筒子楼,以观看女排比赛的集体画面和庆祝胜利的集体游行场景,为下一单元提供了影像上的准备和过渡。可惜,这样的手法和努力在翌年的《我和我的家乡》中就完全隐而不彰,失去了可供观众索引理解的线索,成为完全独立、散装的五部短片。
二、更开放、更流动,拓宽新主流电影格局并增加新生文化活力
“我和我的”系列是中国当代新主流电影中的重要IP,从祖国到家乡,再到父辈,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提升了中国电影工业的运行效率,更卓有成效地集合了当前观众们的观看兴趣。网络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自发讨论在预测,接下来的主题命制可能是怎样的题目?它所要召集的编导、主创与演职人员又会呈现哪些风格或者新的特点?与此相仿的讨论乐趣就像历史上的人们对于宋朝画院选摘诗句用于画题那样津津乐道并一再阐释,也好比于具有高忠诚度的影迷群体对漫威、复联、速激、007和碟中谍等超级大IP的用户黏性,在每一次续集正式推出之前就预先构筑起非常具有活力的真实意向空间,促进电影产业链进入更为良性、向好的运转。
在今年的“父辈”电影宣发中,导演徐峥的“三朝元老”身份不断被作为热点话题谈及。确实,为数众多的导演中只有他是连续三年参与“祖国”“家乡”和“父辈”的,而且他所组织的沪上演员班底和上海弄堂置景也几乎是年年有份出演。这种情况和去年的“家乡”短片集有相似之处。以“北京”为名的《北京好人》明确接续了“祖国”系列中的《北京你好》。葛优扮演的非典型中年男子张北京的角色,连续两年在献礼片中带来平民世界的真情实感和发自内心的会心一笑。从2008年中国第一次成功举办奥运会,到2020年后疫情时代里带着乡下表叔参加新农合全民医保,“祖国”与“家乡”的关键命题之间建立起了真正有亲情、有互动的影像叙事,让具有原创性的中国故事具有继续成长、发展新生的生命活力,表现出乡土中国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有处境。
相较来看,这也是为什么“我和我的”电影系列在结构布局上不断进行着既精简做减法,又扩容做加法的全方位调整。
一方面,构成全片的短片单元数量在删繁就简。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包含七位导演的七部短片,《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和《护航》,在共和国的当代史上标出一连串牵动人心的重大时间节点:1949年天安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84年中国女排三连冠、1997年香港回归、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2016年神舟十一号返回舱安全登陆和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史中有事,事中有人,人心中有对祖国母亲的热爱。到了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短片数量减少为五个,影片的主题线索也从主要依靠历时性的线性时间顺序,调整为着重展现国家地理的空间新格局。《天上掉下个UFO》取景西南贵州地区,《北京好人》涵盖华北平原,《最后一课》联结起江浙沪东南沿海与海外的境内外空间,以及代表西北地区的《回乡之路》和代表东北地域的《神笔马亮》,集锦式地拼搭出东西南北中的风物全景。
受到减法修整的部分不单是表面上可以看到的导演数量和短片数量,还有相对抽象的类型风格、主题情节等层面。和上一部“祖国”的悲欢交织不同,“家乡”的五部短片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喜剧为主的情节模式。每一段故事的核心转折都基于喜剧效果的隐瞒、掉包,或者善意的谎言。沈腾扮演的画家马亮为了照顾待产的妻子而假扮身在国外,范伟扮演的归国老师因为病入沉疴而获得以往学生们的联合照顾与集体换装表演,如是等等。相对集中而喜剧化的短片风格可能会给观众带来较为一致的轻松流畅观感,但在影响长远的观影价值上,它折损了“我和我的”系列影片所应有的开放格局和流动性。
此处进行一个细节上的前后类比会有助于深入理解上述问题。2019年“祖国”中的《白昼流星》表现了内蒙古四王子旗的实景,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在短片中真人出镜,本色出演了返回舱安全着陆后的敬礼场面。两位航天员台词不多,却非常能够说明新主流献礼片的开放性格局。他们说:“感谢祖国和全国各族人民,向祖国和全国各族人民敬礼。”
在这个面向摄影机完成的敬礼动作中,画面的性质和价值远远溢出单个镜头的范围,达成了新主流献礼片的主题高度。从国家重点发展的航空事业带着真实身份入画的航天员将真实感注入场面中,而他们致以崇高敬礼的对象是作为抽象概念的集体共名,并不能在下一条镜头中直接进入画面、参与叙事。于是就形成一个象征性的摄影机休止符,即同时包括了完全的真实性与完整的象征性的节奏空场。这个节奏空场构成了献礼片所特有的共情时刻,在音画渲染中拉动观众们的情绪感受,促发出相伴审美而生的文化认同感。观众们感受到强烈的情感起伏,不由自主地加入同一主题的心理感召,将祖国与中国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再次形象地纳入眼前这些正在具体进行中的台词和场景。
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电影中的少数民族形象问题,在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中出现于《天上掉下个UFO》。该段落的空间重点是位于贵州苗族聚居区的天眼小镇——平塘县克度镇,叙事目标是通过重建西南大山隔断的爱情故事,表明新基建过程对于民生幸福的切实帮扶。作为全片主题中重要而稀缺的少数民族故事,其实地取景既有西江千户苗寨的民居胜景,也有代表中国科技硬实力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但是上述元素不仅未能在仿制“唐探”风格的喜闹剧中发挥出本身所包孕的重要内容和重大意义,反而在导演陈思成偏于浮滑轻飘的拍摄惯性下流露出错误的倾向。如果只是在物象层面上将射电望远镜的球面外形恶搞为“天眼酸汤鱼火锅”,至多不过是低劣趣味使然。可是片中让饭店打工做服务员的青年伢崽穿上模仿ET外星人的连体衣来抬火锅上菜、制造营销噱头就是需要马上改正的文化挪用问题了。因为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单一民族国家不同,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成,各民族间的团结与祥和是国庆档献礼片中的重中之重,需要正确而准确的艺术展现。

图1.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剧照
发展到第三个年头的《我和我的父辈》又一次做起了减法,导演数量和短片数量继续减少为四个,短片的叙事主题也重新回到时代发展的主线。不过,“父辈”系列所操作的减法不单是表面文章,而是更为成熟的、有明确指向的多义性增减。减中有增,减后保持全片的总时长不变,与前两部“祖国”和“家乡”一样,总量维持在150分钟左右。这样一来就显得《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更加集中,在家国同构的双层主线上叙述建国前的战争历史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科技建设,继而从国家开始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期进入科教兴国的未来方向把握,在结构布局上呈现出线索明晰、分段明确、风格明快的集锦式叙事。电影的艺术特质与其他很多类型不同,过于明了的判断可能会冲淡美感的体验,尤其是对于“父辈”这样具有全球化文化共性的时代影像主题而言,增加主题内的反思力度与拓宽影像表现的格局空间一样值得更多探索。
三、对照国际视域中的“父辈”命题潮流,感受愈加复杂而深刻的国族文化遗产
在全球文化逐渐趋向一体化的互动影响下,关于“父辈”的思考意味着更为复杂而深刻地感知自身所处的国族文化境况。其中,围绕“父辈”在上一次战争语境中的真实遭遇和行为深层反思,捕捉极端情境下的人性闪光点,成就了尤为重要的影像魅力。
2006年,克里特·伊斯特伍德与斯皮尔伯格合作完成了战争片《父辈的旗帜》(Flags of Our Fathers
),开始了以父之名,重识世界当代史的主题影像探索。子一代的叙事动机受到双重身份认同的合力推动。既在一个家庭内刚刚接替衰老的父亲,成为所有家庭成员的依靠,又在社会的迭代发展中意识到成熟的自己正在被召唤,需要接过一些历史上的观念、事实和信念遗产,并在某个必要的誓言场景中诚实地亮出自己经过反思并最终确认的新生立场。这个问题直接联系着国族文化的传承与续接,逐渐在不同国家的相同主题影像叙事中获得关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英国电影人连续拍摄短片《我们的父辈》(Our Father
,2015)和《父辈的足迹》(Footprints of Our Fathers
,2016),将单数的“父亲”(Father
)和复数的“父亲们”(Fathers)集合为“父辈”的主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的1915年威格顿征兵演讲(Wigton),到1944年诺曼底登陆前一队英国巡逻兵的意外遭遇(Normandy),这些旨在重走父辈足迹与心灵旅程的作品一改战争片中常见的胜利叙事法则,将影像重点安置在战事中的官兵真实心理感受上,继而将思考向人性深处的幽暗处探寻。通过驾轻就熟的战争场面重现,创新性地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代入到父辈们真正身处其中的生死一线,将代表宏观话语的国旗前战斗动员与擦着耳际掠过的炮火声编织在同一个文本中,用子一代的主动求知和探寻来后置式地介入历史书写,使电影的媒介属性延展为记录集体记忆的影像装置。“你想成为怎样的人,又被怎样地记住?”(How you want to be and how you want to be remembered?)历史上某一时刻的誓词或者话语被重置于带有危险的叙事张力下,经过重复修辞的音画综合强调,以刻入记忆、形成新的父子认同与国族历史共识的完整过程来成功做到观念上的拼图或镶嵌,并在重新勾划的未来社会组织运行中隐在地继续生效。比如在短片中出现递进的设问句式后,紧跟着会有代表国族身份集体认同的语句加以应答,“我不是懦夫,我为保护我的同胞、保护了我的国家而自豪。”(I am not a coward,and I protect my fellow country men. I was proud to protect my country.)
图2.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海报
2013年,德国和俄罗斯同时拍摄了重现父辈英雄艰难作战的作品。电视电影《我们的父辈》(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
)在德国电视二台ZDF(Zweites Deutsches Fernsehen)播出后,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整个西欧世界的震动和讨论。就连同步制作的纪录片《我们的父辈幕后纪实》(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Die Dokumentation
)也接连制作出三部,分别对应着剧集中的“一段不一样的时代/Eine Andere Zeit”“一场不一样的战争/Ein Andere Krieg”和“一个不一样的国家/Ein Anderes Land”,将作为影片人物原型的东线士兵、战地护士、占领区游击队员、受遣返的犹太人,以及唱歌劳军的女歌手和逃兵等一一集结在聚光灯下,让他们在采访的话筒前平等说出关于战争的真实反思,批评简单思维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对历史上的纳粹主义,尤其是战后年代仍然残存在德国社会体制中的极端主义者们提出思想上的预警。片中战地护士夏莉的原型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坚强了,能够在截肢手术中帮助医生处理濒于破碎的人体,但在目睹一位父亲在烛光中陪伴阵亡儿子时还是觉得“太令人心碎了”,她在完全破防后不知不觉地说出代表少数人想法的话,“死亡是悲哀的,就算是为了自己的祖国”。这一幕就像曾经在东线战场的堑壕里听到《莉莉·玛莲》歌声的思乡士兵所感受的那样,“他们还没有经历过什么,只经历过这一场战争”。值得多说一句的是,尽管中文引进版本将该作品统一译为《我们的父辈》并授予第20届白玉兰最佳电视电影编剧奖,但是原版德文片名也包括母亲且位置还在父亲之前,直译应该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围绕战争的全景别表现和关于战前战后的全性别叙事一样值得重视。这个自觉追求复杂性和深刻性的想法与同年另一部俄罗斯电影的历史立意殊途同归。
2013年,费奥多尔·邦达尔丘克导演完成了俄罗斯第一部IMAX-3D巨幕影片《斯大林格勒战役》(Stalingrad
),也是该国电影史中以“斯大林格勒”作为片名的第六部剧情长片。导演小邦达尔丘克对于父亲拍摄的卫国战争影片《他们为祖国而战》熟悉而认同,不止一次地在创作阐述中将新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描述为“献给父辈的诗篇”。诗篇包括两个重点维度,分别指向未来与生命。在炮火倾泻的特效场面基础上,该影片旨在推出关乎未来叙述的篇章,特别是战后的俄罗斯精神如何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发挥领导力。接下来,在父辈、战争等关键词缠绕生出的生命意象里,影片给出了一个孩童叙事的视角,并进一步模糊、甚至擦除孩童身上外在的单一国别属性。用来反衬和突出什么呢?当然是能够作为生命依傍的宽厚母性与父爱。片中被保护的少女卡嘉与另外五名驻守孤楼的红军战士一起,面对作为敌手,但也可能是另一群父辈的德军兵团。确定的母亲形象与不确定的生命DNA来源一起构成未来国族文化的叙事基础。人们或许会发现,今年在《我和我的父辈》的集锦开端与收尾,各有一个关于父子生命接续的主题叙事。向抗战历史再次回望并致敬的《乘风》,以及眺望未来并礼赞牺牲精神的《少年行》。两个短片分别以失去亲生儿子/补上非亲生的同名儿子、失去亲身父亲/补上非人类的AI机器人父亲的情节构思完成父与子之间的象征性团圆。相较来看,《乘风》的艺术手法过于显豁、直白,较为轻易地让观众们猜出“乘风”一词在阵亡士兵和逃难途中分娩的孩童之间的同名关联。这说明编剧已经意识到了父子主题需要实现跨血缘连接的国族历史叙事,却没有找到更好的艺术手法来具体地加以实现。同样,由开心麻花团队主控出演的《少年行》,本质上还是重复了前一年献礼片《我和我的家乡》“欢闹国庆”的思路,在进一步巩固自己“中国喜剧梦之队”的前提意图下,将故事情境命名为“开心麻花实验小学”,缩小了而不是开阔了关于科技进入校园青少年教育的主题格局。
联系近年来全球各国出现的父辈主题影像叙事,可以看到不仅是英、美、法、德、俄等欧美地区主要国家在进行严肃认真且具有刷新历史认知的拍片探索,还包括一些地处欧亚交接,以及亚洲、非洲的国家,也在集中思考父辈历史影响下的国族文化精神遗产问题。由日本五大电影公司之一,角川映画株式会社完成的太平洋战争影片《日轮之遗产》(The Legacy of the Sun
)在2011年上映。曾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天坛奖(最佳男配)的《父辈足迹》(If Only Everyone
,2012),是亚美尼亚电影人对于二十年前爆发的纳卡战争的精神凭吊。就在电影上映后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同样还在纳卡地区,又是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开始了局部战争。影片中着意刻画的父亲墓地在新一轮战争中再次遭受到难以想象的暴行摧残,在国际社会的一片谴责声中,也为亚美尼亚电影中的“父辈”主题平添了预言不幸实现的苍凉悲怆感。另外,南非 《我父亲的战争》(My Father's War
,2016),以及同年传出筹拍消息的韩国同名电影《我父亲的战争》(My Father's War
),分别以涉及本国的战争战役作为影像对象进行思考与再现。结语
综合上述多个方面来思考《我和我的父辈》,会发现该系列的同主题叙事在结构布局的形式美感追求方面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自觉,对于观众笑点的预期布置也格外重视。但是经验中曾经较为合理地建构起来的文本间互相指涉和关键人物形象上的延续性等,反而没有得到足够的跟进,造成了风格独立各异、松散有余,却不够开放广阔的影像布局。事实上,“我和我的”系列在进行到第三个年头时,正是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开放和流动是其中的关键词。开放观念,开放更大的主题空间并激发出中国电影产业现代化的制作能效,是增加“我和我的”IP内容活力的双赢步骤。而流动,意味着文化上的活力新生,让它在未来的筹备和制作中吸引更多元的新人员组成,容纳更多探索,合力汇聚成中国讲述、传播全球的优质影像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