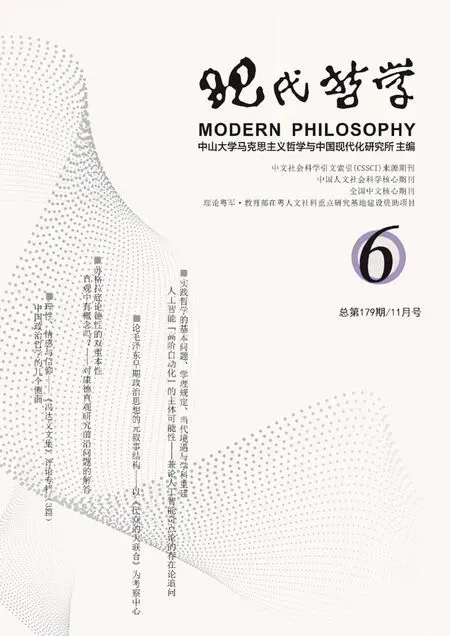从“断裂说”与“游魂说”看观念儒学的存续
曾海龙
如果以皇权制度为儒学存在的必要条件,那么皇权制度解体之后,儒学便已“走入历史”,似乎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结论。而从观念论的角度而言,儒学的存续是一个既成的课题。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的“断裂说”与余英时的“游魂说”,就呈现出这种悖论。他们对儒学现代命运的判定,既表明制度儒学已经“走入历史”,也印证了儒学在现代以观念化的方式重新获得了自身的存续。
一
列文森曾指出,历史上儒学与君主制度相伴而生,结为一体而又相互利用,到20世纪又互相牵连,双双衰落。即便是廖平、康有为,也已经与传统儒家产生了决裂,失去了儒家的特征。进而,列文森将廖、康等人视为反传统主义者,认为廖平与康有为把经书当作预言时,就终结了他们自己对经书的理解之路。“廖平是想从经书中寻找开启终极智慧之门的钥匙;康有为也想寻求智慧,后来是寻找‘国粹’,他们虽生犹死。”(1)[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列文森试图证明:在廖平、康有为之后,中国的历史之河正在枯竭。在他看来,廖平、康有为等人不仅舍弃了儒家的历史,也背叛了儒家的理念,以至于像“井田制”这样的话题也彻底地改变了它的历史意义,并为社会主义与共产道路之兴铺了路。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已经与传统尤其是儒家没什么必然联系,作为“历史”的儒教只能被送进博物馆。
不难看出,列文森对于现代中国的解读有个先入为主的框架,即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的冲击,中国不能独立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传统中很难孕育出现代性。换言之,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不仅制度是断裂的,观念也是断裂的。“20世纪的第一次革命浪潮真正打倒了孔子,珍贵的历史延续性、历史认同感似乎也随之而被割断和湮灭。”(2)同上,第324页。儒学退出历史即意味着走入历史,放弃未来。对于踏上现代征程的中国来说,“历史之河正在枯竭”(3)[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294页。。廖、康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接受并喜欢共产主义,是因为后者提供了一种普遍性的历史观念。这与廖平相信千年至福的太平盛世及康有为追寻大同世界出于同一逻辑。与廖、康一样,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进步史观也是与传统的决裂,但又提供了解释这种决裂的方法。与此同时,列文森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意识到传统的局限,但很难接受有着几千年传统的中国要遵循西方的现代化路径。于是,他们需要寻找一种能与西方现代化竞争的发展模式。如果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产生于传统,也不愿遵循西方业已成功的现代化路径,那么社会主义与共产道路或某种“井田制”似乎就成了某种必然的选择。
中国共产主义者既反封建又反帝国主义,他们在被抛弃的儒教中国和遭到抵制的现代西方之间确定自己的折衷地位。从历史上看,1919年反传统的五四运动保持了伟大的传统。但五四运动本身就要求人们必须把革命思想与胡适和蔡元培式的反革命思想区别开来。因为这些人是自由知识分子,他们的自由主义文化倾向依赖于欧美,在中国缺乏根基。而共产主义却恰好处于垂死的儒学和首次挫败了儒家的西方资本主义之间。(4)同上,第299—300页。
列文森解释了中国在近现代何以必然走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道路。在面临西方文明压力时出现的民族主义者,在运用传统抵御西方文明时屡遭挫败,不得不视传统为包袱。而要甩掉这个包袱以应对现代西方文明造成的巨大生存压力,选择一种既反对传统又反对已有的现代西方文明的第三条道路,就变得理所当然。而共产主义在苏俄的成功,恰好给予中国知识分子及时的召唤。然而,即便是立场最为激进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完全不承认中国传统,在心理上也是难以接受的。虽然他们在最初激烈地反对传统,但之后却一直在重新建立与传统的联系。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者一方面拒斥传统,一方面又在继承传统。“人民的传统是能被重新解释的中国的过去,而以前一直作为中国过去的儒家传统或自主传统则被完全地否定掉了。”(5)同上,第118页。在列文森看来,“井田制”作为一种隐喻或一种社会理想在20世纪复活,开启了共产主义在中国落地的先声,恰恰表明其已经不再具备儒教本有的内涵。“井田制”和今文经学依据《公羊传》所构想的“太平世”,都是对传统的反叛。因而,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对传统的阐释理路,本身不是对所谓真儒学的信奉,而是与之决裂。“井田制”作为一种隐喻和社会理想的复活,是中国在面临西方压力时选择的一种与“西方化”不同的现代化模式。
列文森对现代中国与中国传统的关系所作出论断,可用“断裂说”来概括。其主要内涵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是一种断裂而非连续的关系,现代中国是对传统中国的否定。列文森从传统中国的稳定图景被打破的过程中,看到了“现代化”对于传统的破坏。这一点无疑是基于他本人深刻的历史感受。然而,因为他对于“模式”的过度执著与其所秉持的“欧洲中心观”视角,使他的中国研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即便是持最激进立场的现代中国的研究者,恐怕也难以完全同意这一观点。
二
在列文森之后,余英时曾用“游魂”来形容儒家与儒学,尖锐地凸显了儒学在现代遭遇的困境。他的问题意识最终归纳为:“如果儒学不甘仅为‘游魂’而仍想‘借尸还魂’,那么何处去找这个‘尸’?”(6)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58页。在他看来,儒学赖以存在的“尸身”正是以儒家观念为基础的一系列传统政教制度,其中尤其以科举制最为重要。进入20世纪后,随着皇权制度的解体,儒学和制度的联系已经中断,以制度为基础的儒学之“尸身”就已经死亡。因此,“让我们用一个不太恭维但毫无恶意的比喻,儒学死亡之后已成为一个游魂了”(7)同上,第56页。。
余英时这个判断可以表述为:制度化的儒学已死,作为道德教化与学术研究的儒学未亡。制度儒学的死亡或解体,已经是众所承认的事实。而作为道德教化与学术研究的儒学,虽然失去所赖以依附的“尸体”,然而其还未完全消失也是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在余英时看来,传统儒学的特色在于它全面安排了人间秩序,因此只有通过制度化才能落实自身,而没有政教制度依托的儒学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余英时比较了儒家和基督教的现代命运,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他认为传统儒学与基督教的差别有二:其一,基督教作为一般意义的典型宗教,是有教会组织的宗教,虽然曾经与许多世俗制度融为一体,但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后,最后以政教分离的方式栖身在宗教制度之内;而儒学并无独立的制度或组织,而是以一切社会制度为依托,其所赖以生存的制度解体,便再无容身之处。其二,中世纪基督教在思想上居于最高地位,哲学与科学都是其婢女。自从科学革命后,基督教在学术、政治等领域到处退却。与基督教不同的是,儒学是全面性的,它无所不在,因此不能在任何一条战线上撤退,连宗教的领域也必须奋战到底。因此,一旦离开政制论述的场域,儒学就走向了末路。
虽然余英时与列文森同样认为政教制度对儒学而言是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但与列文森的“冲击-回应”模式不同的是,在余英时看来,从晚清到“五四”,儒学的批判其实是从内部开始的。余英时认为,明清儒家的政治社会思想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倾向,这一倾向可能恰好与外来的西方观念相呼应,对晚清儒家接受西方观念发挥了暗示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明清儒家思想中出现了西方式的现代观念,因为他们对儒学的批判主要还是基于传统资源。无论是今文学家还是古文学家,虽然都受到西方观念的冲击,但并未意识到自己是站在西方的思想的立场上进行反儒学活动的,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只是借助外来观念发挥儒学的精义而已。
余英时阐明了儒学基于自我批判以应对现代变局的“内在理路”:“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反儒学的运动最初源于儒学的‘内在批判’,那么儒学吸收西方思想这一事实也许可以看做是出于它本身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并不是‘用夷变夏’这个简单的公式所能解释得清楚的。”(8)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第133页。他进而认为,中国现代性意识源于明清之际思想界的某些新倾向,这又恰好构成现代儒学接受西方观念的诱因。“1894-1895年以后,一部分的儒者才发现西方思想与制度是中国富强所必须借鉴的。这一新发现引出了明清思想界的一个新发展,即通过西方的观念和价值重新发现儒家经典的现代意识。”(9)同上,第169页。按照这种理解,廖平、康有为等人不仅没有背叛儒家,反而坚守了儒家的立场。
按照余英时的理解,这种对传统的“内在”批判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在20世纪上半叶,无论是反对儒家还是同情儒家的知识分子,都曾是儒家文化的参与者,他们的生活经验中都渗透了不同程度的儒家价值。他注意到,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学术各方面都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西方的新观念和新价值,但在立身处世方面却仍然保守儒家的旧义。然而,到20世纪下半叶,儒家的中心价值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已经不能公开露面。知识分子在生活经验中已经很少能接触到儒家的价值。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海外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来说,也终不免书本上的儒学远超过生活中的儒家价值。余英时对20世纪上下两个半叶儒学遭遇不同命运的解释如下:“前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向慕西方主流文化,所以‘民主’与‘科学’成为‘五四’新思潮的两大纲领;后半个世纪则是反西方的西化在中国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在这两个时期,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所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10)同上,第264页。因此,儒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在20世纪下半叶已然中断。对这种判断的评判牵涉到如何评价中国革命的问题,也涉及到如何看待儒学在20世纪下半叶的生存境遇。所谓的“游魂说”,是就后一阶段的儒学命运而言。
余英时所谓儒学的当代生存困境,主要是指儒学生存的“体”无法落实。无“体”之儒学只能成为“游魂”。这种判断当然有其理据。儒学在传统中国体现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这一套生活方式依附在整套的社会结构上。20世纪以来,传统的社会结构解体了,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于是不可避免地带来两个趋势,一是儒学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论说(discourse),二是儒家价值和现代的“人伦日用”越来越远了。儒家价值和现代社会结构之间重新建立联系的希望十分渺茫,甚至连儒学教育都无处容身。因此,儒学只能作为一种“论说”而存在,成为“游魂”是其不可避免的命运。
同“断裂说”一样,“游魂说”也是基于对儒学原本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基础已然不复存在之后对儒学命运的判定。问题在于:儒学赖以存在的政教制度究竟为何?如果是单指以皇权体制为中心的传统政制,那么在皇权体制已经瓦解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学术方面接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同时,何以在立身处世方面毫不违和地保守儒家旧义?如果20世纪上半叶的政教制度依然能够与儒家传统“人伦日用”相容,那么前者是否依然可以称为后者的“体”呢?如此,则“游魂说”的内涵就颇有商榷的余地。
三
作为“挑战-回应”模式的质疑者,柯文(Paul A. Cohen)将解读中国现代进程的模式分为四种:挑战-回应型、传统-现代型、帝国主义-殖民型与柯文自己试图建构的“中国中心观”(11)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前言。。前三种模式都有先入为主的历史观和预设立场,是“西方中心观”的产物,都不足以描摹真实的现代中国路径,无法完全准确地描述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路径。唯有柯文自己采取的没有先设的历史模式以中国认识中国的进路,才能准确呈现中国历史画卷。而余英时对儒学在20世纪上半叶命运及其之前的历史论述,也是一种“中国中心观”模式(12)就对20世纪下半叶及其之后的中国研究而言,余英时抱持着一种远观立场与稍显悲观的态度。无论是对中国的政治、学术乃至在港台的现代新儒家们,他总是有些敬而远之而又表现出些许“不经意”的关心。。
严格来说,无先入为主的立场来进行历史叙述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不可能不通过既有的语言和概念来表达思想与描述场景一样。柯文这种看似没有立场的阐释,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支离破碎的荒芜泥潭。类似列文森所持的“西方中心观”虽然有其缺陷,然而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图景如果缺少了西方的对照,显然也是残缺不全的。
当然,“中国中心观”依然有其重要意义。它为我们检视“断裂说”与“游魂说”及二者的差异提供了一条路径。如果说余英时以“游魂”来形容儒学的现代困境,毕竟还有些眷恋的乡愁意味,那么列文森对这种怀旧似的乡愁表现出了明显不满。柯文指出:“就列文森本人而言,他当然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深刻的敬慕。引起他不满的并不是这一文化本身,而是近代保守派拒不承认这个文化已经死亡。”(13)[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74页。在这个意义上,余英时就可能成为列文森批判的对象。余英时虽然认为儒学已经沦为“游魂”,但要说儒学完全死亡则从情感上还难以接受。杜维明更敏锐地看到了列文森与余英时的不同:“列文森为儒教中国悲叹,他看到这些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窘境:他们在情感上执著于自家的历史,在理智上却献身于外来价值。”(14)[美]杜维明:《探究真实的存在——略论熊十力》,《熊十力全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37页。显然,“他们”也包括余英时在内。
列文森与其师费正清以“冲击-回应”模式来阐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们断言儒家在此过程中已经退出历史并“走入历史”,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存在“断裂”,前者对后者并无继承性可言。这种判断乃基于他旁观1950-1960年代的中国文化政策。20世纪80年代后,列文森的主张频繁受到挑战。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并没有遵循西方世界尤其是欧美已然完成的现代化模式;更进一步的逻辑在于,虽然传统已经面目全非甚至难为人所辨识,但孔子和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民族传统与心理结构,始终作用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因此,传统尤其是儒家对现代中国的行为和心理影响是现实存在的,列文森以之为研究对象的1950-1960年代也莫之能外。
儒学是否能够与现代性相容抑或可以自身资源阐发出现代性论述,依然还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儒学是否一定要与皇权政制同谋才能保有自身的生存土壤,当下也倾向于否定。传统儒家更多地致力于与皇权达成某种平衡,士人阶层一方面为君权提供了合法性论述及权力运作层面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从权力运行结构中约束与限制君权使其无法过度扩张。就此而言,儒学既可以为皇权政制提供支持并致力于达成道统与权力的平衡,也可能为现代政制提供支持并对其权力所有者产生制约。
而列文森认为儒家已经“走入历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坚持现代性观念只能来自西方,并与儒学完全不能相容。这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在于,儒学只能依托于皇权政制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列文森秉持此种观念,显然与其对儒学内部张力缺乏必要的了解有关,以至于其未能准确把握儒学的现代命运。换句话说,列文森坚持以制度儒学为儒学存在的标志,以至于他坚持认为,皇权制度解体之后,儒学便已经“走入历史”,再也没有活的生命。
与列文森对儒学抱持理性与决绝的态度不同,余英时在理性与情感或信仰之间颇为挣扎。余英时也看到了制度解体对儒学的致命打击,但他不能完全同意儒学已经“走入历史”。这不仅关乎理性,更关乎情感与信仰。即便如此,余英时对儒学的发展前景依然是悲观的。他认为儒学因为其自身的特征,在现代社会的各个场景中都不可能获得其本身所期望的作用,甚至连将儒学作为一门专业性的学问都颇为困难。因此,在理性层面而言,余英时的“游魂说”除了承载飘零的悲情与乡愁外,与列文森的“断裂说”也无根本差别。他们在理智上都认为,作为制度性的儒学解体之后,儒学已经不能再获得其存在的空间,只是余英时在情感上很难接受这个结论。
特别要指出的是,虽然就结论而言,“断裂说”与“游魂说”颇为一致,但二者的论述逻辑却有着很大不同。前者的逻辑是:中国文化传统已经死亡,无论是就其作为体的政教制度,还是就其观念和价值而言,都已经“走入历史”,无复继续存在可能,中国不能从其传统中产生出现代性。后者的逻辑是:虽然作为承载价值体系的政教制度已经死亡,儒学不能够再次全面安排世间秩序,但作为一种情感或信仰的儒学与作为一门学问的儒学却获得新生,对儒学的现代批判也是从其内部开始的;无论是以康有为、谭词同为代表的今文经学,还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经学,虽然都要借重西方的观念来阐明儒学的意义或批判儒学,本身都是儒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不是“用夷变夏”。
检视“游魂说”的内在逻辑,可以提供一个与制度儒学不同的儒学观念。“游魂说”本身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概念。游魂者,本指无所依托之魂。然而既是魂,就是一种精神存在或观念存在。精神或观念附之于或存在于生活世界才成其为存在。“游魂”存在乃因为其在人们的精神或观念中,而且“游魂”之“游”有活着的意味,活而未见其体其形,故为“游魂”。在余英时看来,儒学之魂所依附之体之形,是儒学对应的社会结构与政制。儒学所托之社会结构与制度解体,儒学遂成为“游魂”。然而,制度儒学解体之后,儒学依然有其“魂”,有“魂”便有依附者。无“魂”才是列文森所谓的“走入历史”。“游魂说”是在学术上论证儒学已经“走入历史”,却在情感上依旧眷念着儒学。实则,眷念着的便依旧活着,活着的便没有“走入历史”。这其中内涵的矛盾,恰恰表明了儒学在当下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制度儒学的存在方式存在着。因此,儒学是否走入历史,不能仅从制度层面去判断,也需要从情感、信仰与生活经验领域进行观察。作为制度建构基础的儒学或许已经“走入历史”,然而作为观念——情感、信仰、生活经验,儒学显然还活生生地存在着。这不仅为列文森本人所承认——虽然他不以为然,也为余英时的“游魂说”所证实。
四
“断裂说”与“游魂说”都视政教制度为儒学的生存根基,即都是将制度儒学视为儒学的核心或全部。制度解体,儒学死亡。历史产生断裂,儒学死亡或沦为“游魂”。这种论述的基本前提是:制度是儒学生存在根基。问题是:究竟是儒家思想与价值体系催生并支撑了传统政教制度,还是因政教制度维系了儒家的生存土壤?从历史脉络而言,答案显而易见。儒家的诞生乃至儒家价值体系的形成当然早于其政教体系。而儒家思想乃至儒家价值获得全面的效用,则在其与政教体系结合之后。
而列文森与余英时似乎都抱持制度儒学观,即儒学的生存系于中国传统的皇权政制,离开皇权政制的土壤,儒学必然“走入历史”。这种特定的制度儒学否定儒学与其它制度结合的可能性,当然不会认为离开皇权政制儒学还有其生存的土壤,更不会承认制度化之外儒学还有生存的空间。然而,原始儒学并不依靠皇权制度产生。脱离政制之后,儒学也依然是观念存在或生活经验。换言之,在制度儒学解体之后,儒学获得它原有存在方式,犹如儒学在最初产生时候,就是以一种非主导的观念和价值形态来影响人们。以这种方式存在的儒学,我们将其称之为观念儒学。
观念儒学伴随着儒学自产生至今的全过程,一度与制度儒学一内一外共同构成皇权体制下儒学的存在图景。从结构上而言,制度儒学的设计以观念儒学为基础,并与观念儒学构成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传统儒家在观念儒学与制度儒学的张力中挖掘出巨大的阐释空间。以两宋为例。自周濂溪、张载、二程到胡五峰,无疑是以观念儒学为主的,他们所关注的重点并不在制度层面,而是在思想价值观念层面。而两宋的政制及政治实践是王安石等儒生和士人所重点关注的方面,因而他们可被视之为制度儒学的代表。
近年来,制度儒学解体带来的社会思潮与观念的冲击亦开始为今人所关注研究(15)参见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任剑涛:《当经成为经典——现代儒学的型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陈壁生:《经学的瓦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现代儒学的存在方式显然不同于制度儒学。现代新儒家们大都放弃了以儒学资源建构制度论述,而采取一种观念化的叙事来重新展现儒学的义理。这得益于佛学、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的理论支持。当然,儒学不仅存在于这些儒学研究者的观念中,也依然存在于当下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传统在当下的复兴,并不仅因为几个学者的学术研究,更因为其深根于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中。这些生活经验并不会因为政制的转变与经济模式的变化而消失殆尽。
就儒学作为中国人的生活经验、情感需求与信仰对象而言,它既不会“断裂”,也不会成为“游魂”。虽然儒学曾经与皇权相结合产生了特有的皇权体制,但脱离皇权,儒学依然有自身可以存在的空间,并有可能与某种政制达成平衡。如果以外在的视角拘泥于特定的理论模式或某些具体的史实,当然不能对作为思想价值观念的儒学存续作出肯定的解读。儒学在现代如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教制度相互制衡并获得效用,那么现代儒学就展现出一种与传统儒学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进而彰显儒学价值的普遍性。
列文森以“冲击-回应”模式来理解中国的现代性路径,看重的是两种异质文明产生冲突时,弱势的一方将采取何种态度。他意识到,在面对强势的外来冲击时,某一民族或社会的存续需要一种不同于其传统的新的异质“真理”,此种真理将否定他们自己传统,为此他们会经历一种巨大的精神迷失。然而就现代中国而言,虽然曾经历了巨大的迷失,但这种否定传统的模式不仅已为现代新儒家们所拒绝——现代新儒家既是传统的复兴者,又是现代价值的支持者或现代政制的设计者,也已经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所否定——四十多年来传统的复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观念儒学可以阐明如下课题:制度儒学解体之后,儒学如何可能得以继续存在,并将继续对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体,现代与传统的分离倾向主要体现在政制与社会结构层面,而现代化又是一个不断返归、借鉴、融合传统观念的过程。现代新儒学基于沟通中西在观念上的建构,虽未能取得令人十分满意的成果,却宣示着作为思想观念的儒学恐怕要比作为制度基础的儒学更有生命力。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共识。现代性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原则,在不同民族国家的具体制度中呈现出何种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民族的传统。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儒学或儒教,脱离了与其相互支撑传统政教制度,显然不可能再产生如此那般具有垄断性的影响。但儒学脱离了制度的羁绊,也意味着获得新生。儒学作为一种活着的观念,其存续是一个动态过程。儒家的价值既然可以主导某种政教体制,也可以脱离某种特定的体制获得其存续。正如余英时所言,“在20世纪上半叶,无论是反对或同情儒家的知识分子都曾是儒家文化的参与者,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中都渗透了不同程度的儒家价值”(16)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第265页。。此种描述依然适用于当下。儒学作为中国人的生活经验,无论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都受其浸润。
——儒学创新发展的趋势与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