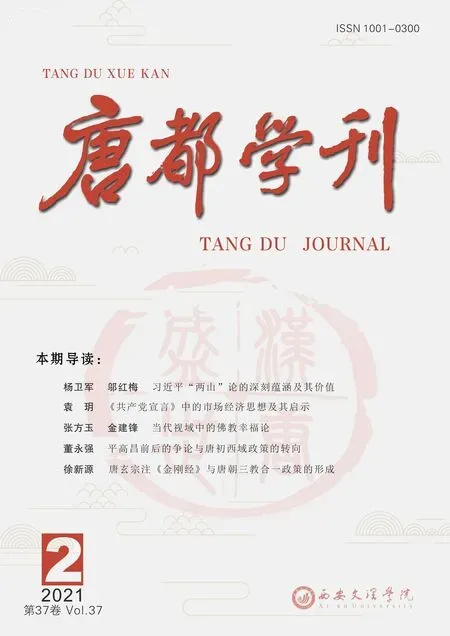从“创造性诠释”到“还原性解读”
——关于宋明理学张载《西铭》诠释模式的反思
李 睿
(西安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100)
学术界以往关于张载之《西铭》的解读与诠释比较多样,代表性的创造性诠释有两种:一种是程朱理学以“理一分殊”说来诠释《西铭》之旨;一种是明代以来以“万物一体”说来诠释《西铭》之旨。尽管这两种诠释都有其意义,但是否符合张载的原意是有待考察的。这些问题的根源还是需要放置于张载《西铭》本身思想形成进路中考察,以张解张,才能更加靠近张载的本意。当然我们不仅要看到张载《西铭》思想的具体构建,更要看到《西铭》思想中一贯的“天道性命相贯通”的理论主旨和价值关怀。
《西铭》(原名《订顽》)言简意赅,内容充盈、发人深省,历来被学者称赞,并以之教化启蒙学子。为更好地辨析学者们对《西铭》的解读与诠释,特征引《西铭》全文如下: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1]62-63
关于《西铭》内容的解读与诠释是有多样性的。通过以往学者对张载《西铭》的解读和诠释,可以促进我们侧面了解《西铭》[2]。发掘以往各种对《西铭》的创造性诠释中存在的问题,是我们还原性解读《西铭》的基础。
一、以“理一分殊”说解读和诠释《西铭》
以“理一分殊”说来诠释《西铭》之旨主要有两个阶段:开始是源于杨时向程颐请教关于《西铭》的相关疑问时,程颐为其解说时提出了“理一分殊”之说;后来朱熹对以“理一分殊”说诠释《西铭》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发。
程颐的弟子杨时认为《西铭》虽然接续了前圣之学旨,但是“言体而不及用”,这样容易与墨家的“兼爱”混淆。程颐《答杨时论西铭书》予以警醒:
横渠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至于《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子比而同之,过矣。且谓言体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为用也;反谓不及,不亦异乎?[3]
杨时首先肯定了《西铭》所阐明的义理是符合儒家圣人之道的,接着又批评《西铭》中横渠的阐发是“言体而不及用”的,又认为《西铭》中所提倡的“民胞物与”思想有流于墨家“兼爱”的危险。所以他怕后世解读《西铭》时牵强附会,以墨家兼爱解读张载的思想,因此他希望程颐能够“推明其用”以弥补《西铭》“言体而不及用”的弊端。虽然杨时看上去好心一片,但其实未曾真正理解《西铭》体用相即之旨。所以程颐马上回信纠正学生理解之偏。程颐先高调表扬了张载《西铭》所论是有“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的,这是肯定了张载的“造道”之功。随后程颐进一步区分了墨子和张载的立论:墨子所言之“兼爱”是天人“二本”的,而且墨家所言无差别的爱,是绝对的“无分”,可以说是无我,消解了人之为人最主要的立脚点:主体性;然后程颐以“理一分殊”来诠释《西铭》:虽然儒家所言的“分殊”,是可能存在“私胜而失仁”的弊端,但是当能够以“理”统摄“分殊”,则能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程颐由此以“理一分殊”之说来解读和诠释《西铭》之旨。到南宋时,朱熹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特意作《朱熹西铭论》:
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不有圣贤者出,孰能合其异而反其同哉!《西铭》之作,意盖如此,程子以为“明理一而分殊”,可谓一言以蔽之矣。
盖以乾称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弊;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牿于为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旨也。
观其推亲亲之厚以大无我之公,用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盖无适而非所谓分殊而推理一也,夫岂专以民吾同胞,长长幼幼为理一,而必默识于言意之表,然后知其分之殊哉![1]410-411
朱熹之所以更进一步地解读《西铭》,一方面是出于其理本构建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再次深度回应杨时的疑问。除此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回应陆九渊兄弟对《西铭》的误解。陆九韶曾经认为《西铭》以“乾为父,坤为母”是多此一举:“横渠之言不当谓乾坤实为父母”,人是由父母而生,察其本心即可,“人物实无所资于天地”[4]562。其实陆九韶与其说是批评《西铭》,其实是批评程朱理学以“理一分殊”解《西铭》,主要还是在表明人只需要澄澈“仁心”之本体即可,无需外求一个天道本体。
朱熹正是面对陆氏兄弟的发难,再次详尽地阐发如何以“理一分殊”来解读《西铭》。他回应陆九韶的人乃父母所生,何以再外求乾坤做父母的质疑:“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为父母者,即是乾坤”[4]561。在朱熹看来,《西铭》通篇都可诠释为在贯通“理一分殊”之旨。从形上本体而言,万物皆有此“理”一以贯之,“无物不然”;从形下实践而言,则必然产生大小、亲疏之别,而不得不表现为“分殊”之象。可以说,程朱理学在为《西铭》形上形下之一贯义的辨析上是功不可没的。程朱理学以“理一分殊”来诠释和解读《西铭》,的确有助于明确《西铭》体用一贯之旨,有效回应了“言体而不及用”和“横渠之言不当谓乾坤实为父母”的疑问。但是张载《西铭》之主旨是否就是为了贯彻“理一分殊”之旨是存疑的,以“理一分殊”诠释和解读《西铭》其实是存在过度诠释之嫌的[5],我们还是需要以张解张,将考察放之于《西铭》本身,并结合张载其他著作思想共同诠释,才可能最为靠近张载之本意。
二、以“万物一体”说解读和诠释《西铭》
明代到现代,众多学者将“万物一体”看作是《西铭》的核心主旨。明代薛瑄(1389—1464)曾直言:“读《西铭》,知天地万物为一体。”薛瑄的思想是以“理-气”的宇宙架构来完成的,自然也是以此来理解《西铭》的。他主张:“万物皆气之凝聚,而理亦赋焉”,理气共同作用下生成天地万物,理在气中,气之凝聚以生万物。薛瑄以“理在气中”、理气不离不杂的观点发展和革新了程朱“理一分殊”的观点,其“万物一体”最终也是落之于“气”。王夫之(1619—1692)也是以“人之与天,理气一也”“理在气之中,而气为父母之所自分,则即父母而溯之,其德通于天地也,无有间矣”来解《西铭》:
……然濂溪周子首为《太极图说》,以究天人合一之原,所以明夫人之生也,皆天命流行之实,而以其神化之粹精为性,乃以为日用事物当然之理,无非阴阳变化自然之秩序而不可违。然所疑者,自太极分为两仪,运为五行,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皆乾、坤之大德,资生资始;则人皆天地之生,而父母特其所禅之几;则人可以不父其父而父天,不母其母而母地,与“六经”、《语》、《孟》之言相为蹠盭,而与释氏真如缘起之说虽异而同。则濂溪之旨,必有为推本天亲合一者,而后可以合乎人心、顺乎天理而无敝;故张子此篇不容不作,而程子一本之说,诚得其立言之奥而释学者之疑。窃尝沉潜体玩而见其立义之精。其曰“乾称父,坤称母”,初不曰“天吾父,地吾母”也。从其大者而言之,则乾坤为父母,人物之胥生,生于天地之德也固然矣;从其切者而言之,则别无所谓乾,父即生我之乾,别无所谓坤,母即成我之坤;惟生我者其德统天以流形,故称之曰父,惟成我者其德顺天而厚载,故称之曰母。……人之与天,理气一也;而继之以善,成之以性者,父母之生我,使我有形色以具天性者也。理在气之中,而气为父母之所自分,则即父母而溯之,其德通于天地也,无有间矣。若舍父母而亲天地,虽极其心以扩大而企及之,而非有恻怛不容已之心动于所不可昧。是故于父而知乾元之大也,于母而知坤元之至也,此其诚之必几,禽兽且有觉焉,而况于人乎![6]
王夫之认为,周敦颐的思想仍然存在与释氏相同的天人二本、体用殊绝的弊端,张载的《西铭》正是可以纠偏此处,诚如程颐的“理一分殊”说揭示了《西铭》的“一本之说”。王夫之接着以“理气一也”来进一步发展“理一分殊”说,将道德属性赋予“理”和“气”,并随着“气”之生化流行贯彻于万事万物的生长变化之中,所以说“其德通于天地也,无有间矣”。王夫之对《西铭》之诠释也落在万物一体于“气”之生化流行中。
薛瑄和王夫之等明代学者,以“理在气中”“理气一也”为本来诠释《西铭》之旨,试图发展程朱的“理一分殊”说并弥补其强调所本然而无法圆融所应然的弊端。除此以外,明清时期以“气”为本的学者还有黄宗羲、顾炎武、戴震等人,他们各自的“气”本思想展现出不同的面向[7]。整体说来,将张载思想中原本存在的“万物一体”和气化流行的面向发扬扩大,虽然有合理的一面,但毕竟无法全然掩盖体系庞杂的张载思想的全部蕴含。如果说程朱理学以“理一分殊”诠释张载《西铭》主旨存在过度诠释,那么明清的以“气”为本的“万物一体”说来诠释《西铭》则存在以偏概全的缺憾。而且明清这种以“气”为本诠释《西铭》主旨的做法,对现代张载思想研究影响很大,现代站在道家、道教角度研究张载思想与道家思想关系的学者也大都以此“万物一体”说为理论基础。
孙以楷主编的《道家与中国哲学》宋代卷中,张载与道家、道教思想关系部分应该是李仁群先生所撰,因为该部分与其博士论文内容基本一致,其中论及《西铭》中的道家思想部分时,主张“万物一体”的宇宙意识是《西铭》的基本出发点,在引用余敦康先生以本于道家自然主义来解《西铭》首句来佐证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
其实,道家不仅是将宇宙的伟大和人的渺小进行对比,这种对比的基础首先在于老庄从道为万物之本原出发,肯定人和万物构成为一个整体的宇宙世界,天地万物便有了平等的地位。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说:道“无所不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些都是一种以道为本原的整体论的宇宙观。《西铭》所谓“乾称父,坤称母”,“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固然在强调人的重要地位方面有突破道家思想之处,但肯定气生万物和人从而赋予人以天地之性,并由此断定“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仍然未超出老庄的论断。[8](1)同样文本另见于李仁群博士论文《两宋理学与道家思想》,复旦大学2005年学位论文,第48页。应该是李仁群后来负责撰写了《道家与中国哲学》(宋代卷)中的一部分内容。
其实可以看出,这里对《西铭》的论说仍然是在明清以来的“万物一体”说基础上进行的阐发,并由“气”生万物的宇宙观来讲张载《西铭》的思想,将其归于道家自然主义。而且以此为基础,来诠释“民胞物与”理想所主张的平等观念,并认为《西铭》“存,吾顺事;没,吾宁也”的生死观是受庄子“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和道教“天地之性,独贵自然,各顺其事,毋敢逆焉”之义的影响。看起来证据充分,言之凿凿,却未必可以立得住脚。顺着以“气”为本的思路,以“万物一体”说为基础,以道家自然主义对张载的《西铭》主旨和“民胞物与”理想以及存顺没宁的生死观作解读和诠释是大成问题的[9]。
三、以“张”解“张”,还原《西铭》之主旨
尽管以“理一分殊”和“万物一体”这两种观点诠释《西铭》之旨都有其意义,但也都有其弊端。其对《西铭》主旨的揭示是否符合张载的原意是有待考察的。从张载《西铭》本身思想形成进路来考察,以张解张,才能更加靠近张载的本意。当然我们不仅要看到张载《西铭》思想的具体构建,更要看到《西铭》思想中“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义理指向和“民胞物与”的理想境界与价值关怀。
那么,张载《西铭》的主旨究竟是什么?不管是杨时“言体而不及用”的观点、程朱的“理一分殊”说、陆九渊兄弟的“人物实无所资于天地”的观点还是明清的“万物一体”说,对张载《西铭》理解的不同与偏差主要基于对《西铭》前几句“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理解的不同。
张载《西铭》首句“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当作何解?此源出于《易传·说卦》:“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张载此处有新的诠释,将“乾坤”称“父母”,却不言“天地”。这不是简单的缩写或概括,而是张载有意为之,张载曾明确提出:“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言天地则有体,言乾坤则有无形,故性也者,虽乾坤亦在其中。”[1]69在张载看来,“天地”是具象的形下之体,而“乾坤”则是“无形”的创生宇宙万物的“性”之根源,“父”“母”并非指谓实然的“父母”,而是以此来阐发“乾坤”顺应天道本体的生成性。“乾坤”乃“天”“地”“人”三才一以贯之之道,张载言:
易一物而三才备:阴阳气也,而谓之天;刚柔质也,而谓之地;仁义德也,而谓之人。
一物而两体者,其太极之谓欤!阴阳天道,象之成也;刚柔地道,法之效也;仁义人道,性之立也;三才两之,莫不有乾坤之道也。易一物而合三才,天地人一,阴阳其气,刚柔其形,仁义其性。[1]235
可见,“乾坤之道”贯通天、地、人,成为“阴阳”“刚柔”“仁义”之本,“阴阳”之“气”、“刚柔”之“形”“仁义”之“性”皆符合“乾坤之道”,故而曰“天地人一”。从《西铭》首句看,确实是展现出“万物一体”之旨。不过这一“万物一体”之旨尽管有对道家和《周易》中宇宙生成论思想的汲取,但经过了改铸,将平面化的宇宙生成秩序变成了“乾坤之道”对“天、地、人”的立体贯通。
再看“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一句。此源出于孟子“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和“志、气之帅,气、体之充”,张载对孟子思想创造性的继承,也是在发挥孟子“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思想。朱熹解此处甚佳:
乾阳坤阴,此天地之气,塞乎两间,而人物之所以资以为体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体。”乾健坤顺,此天地之志,为气之帅,而人物之所得以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帅,吾其性。”深察乎此,则父乾母坤,混然中处之实可见矣。[10]
朱熹以《西铭》首句的“乾坤之道”为解此句之一贯之旨,看到乾坤、阴阳之感和生“天地之气”,以“天地之塞”(气)为“吾其体”(形体);乾坤、健顺之德为“天地之志”,以“天地之帅”(志)为“吾其性”。“天地之志,为气之帅”,“志”乃“气”之“帅”,“性”乃“体”之“帅”,“乾坤之道”“混然中处”,阐发了“天道性命相贯通”之旨。朱熹此解是比较符合张载思想的,张载对“志”“气”关系的论说可以与之相证:
气与志,天与人,有交胜之理。圣人在上而下民咨,气壹之动志也;凤凰仪,志壹之动气也。[1]8
此也是对孟子“至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思想的继承。“气与志”“天与人”皆是可以交相胜的,“圣人”之所以要“以意逆志”,就在于要改变“下民”的气质之性以上达天地之性,此所谓“气壹之动志”;而当“凤凰仪”此天瑞太和之象出时,此“志”已然是天地之志,只需顺应天地之志之“帅”下的“气”的顺化流行即可,故而谓“志壹之动气”。那么这个能够代表“天地之帅,吾其性”之“志”,也是“圣人”所追求的代表天地之志的“志”,所“志”的本质内容是什么?张载提出:
可欲之谓善,志仁则无恶也。诚善于心之谓信,充内形外之谓美,塞乎天地之谓大,大能成性之谓圣,天地同流、阴阳不测之谓神。[1]27
“可欲之谓善”源出于《孟子·尽心下》:“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张载自己有特意揭示过“可欲之谓善”的含义:“‘可欲之谓善’,凡世俗之所谓善事可欲者,未尽可欲之理,圣贤之所愿乃为可欲也,若夷惠尚不愿,言‘君子不由也’。”[1]324可见,张载引用“可欲之谓善”,在这里已然不是“世俗之所谓善事”,而是“圣贤之所愿”的“至善”。与之相应,“志仁则无恶”,所“志”之“仁”是仁本,也即超越性的道德本体。如此至善的道德本体,才是“信”“美”“大”“圣”“神”得以一以贯之“道”。可见“志”的本质内容即仁本(至善的道德本体)。此仁本正是太虚本体,张载多次阐发此义:
虚者,仁之原,忠恕者与仁俱生,礼义者仁之用。
敦厚虚静,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虚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又曰“思诚”。
虚心然后能尽心。[1]325
这也是圣人之道上合天道、复归于天的根源所在。
在这种超越性的仁本的支撑下,自然生发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理想境界。张载《西铭》接下来对“仁”“孝”的具体实践的论说,也都是基于此理想之下的。但有的学者将张载“民胞物与”的理想与道家“无我”的自然主义对等,是不符合张载思想的。张载《西铭》开篇一直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展开,都是为了突出儒家超越性的道德本体,将“仁”的道德根源性归还于人,突出人的主体性,由此接续并超拔了先秦儒家“为仁由己”之旨。张载心怀这种积极的人生实践,突出“为仁由己”之旨的“民胞物与”理想,构建了万物一体之仁的世界,为当时振奋儒家学者的信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关怀。这与理一分殊的主体进路不同,与万物一体之气的世界所本之本体不同,与道家自然主义指导下的世界则是有着价值归属的本质区别。
由此出发,张载之“民胞物与”“天人合一”既然合一于性、合一于天德,那么,作为人性、天德之形上根据何在?这就再次提出了张载哲学究竟是不是气本论的问题。如果张载是气本论,那么其“民胞物与”自然是无价值取向的天人一气,但这种天人一气是否符合张载的“造道”追求以及理学家“为天地立心”的价值理想呢?显然,20世纪形成的张载哲学之气本论的定性是需要再斟酌的。因为张载的“天道性命相贯通”必须是道德与价值理想基础上之一贯,而不确立张载哲学的太虚本体论及其价值理想(天德),所谓天人是“贯”不起来的。
无论是程朱理学“理一分殊”说的诠释还是明清学者“万物一体”说的诠释,处在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潮流中,都有其逻辑上的必然性。在分析这些不同诠释的基础上,以对《西铭》的还原性解读为根基,进行再诠释,更能体现《西铭》思想中“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义理指向和“民胞物与”的理想境界与价值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