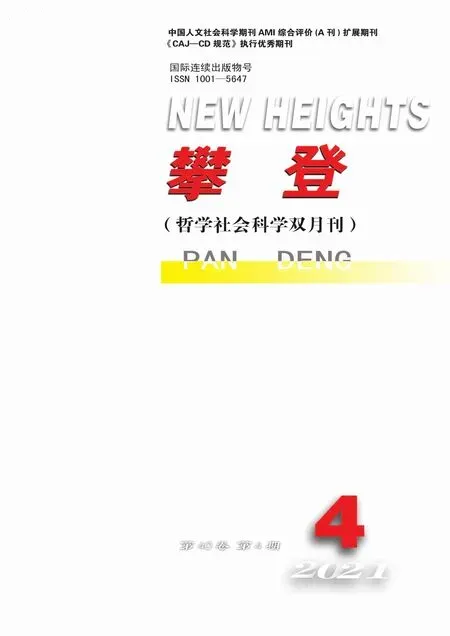生产性保护视域下的热贡堆绣文化产业化发展研究
拉么加 王建深
(1.政协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员会,青海 同仁 811399;2.中共黄南州委党校,青海 同仁 811399)
随着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民间工艺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融入社会已经成为必然之势。在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不断成熟的背景下,家庭作坊式生产方式和家族式、师徒式传承等传统的工艺传承模式受到新的审美价值、体验层次以及创作方式的激烈冲击。因此,契合当下新的传承方式,探索新的发展途径是更好地传承和保护堆绣文化的迫切需求。
一、传承溯源:热贡堆绣文化久远而灿烂
热贡堆绣是一种独具一格的造像艺术,它采用传统的“剪堆”技法,实现了刺绣与浮雕技艺的完美融合。堆绣题材以佛经故事里的人物形象为主,通过不同色彩、图案和绸缎的搭配,塑造和体现人物形态,对比感强烈,展示出一种独特的浮雕效果和立体效果,并体现出高超的工艺美术价值,堪称我国民间艺术宝藏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热贡堆绣是热贡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热贡堆绣的传播时间,首先要弄清楚热贡艺术的历史渊源。热贡艺术最早发源于西藏,但究竟何时传入热贡地区,学术界尚无定论。据《热贡唐卡》记载,公元13世纪前后,西藏归顺于元朝,总揽全国宗教事务的萨迦法王八思巴,从萨迦王廷派出瑜伽法师拉杰直纳瓦为首领,安排三百余名佛学弟子和佛像匠人等组成随从人员来到热贡地区传佛弘法。其中,部分泥塑及彩绘手艺人成为当时热贡地区藏传佛教绘画艺术的启蒙者和传播者[1]。公元15世纪之后,藏传佛教在西藏达到了鼎盛时期,教派林立的历史现状促成了齐岗、曼塘、钦泽等画派的相继诞生,这一时期宗喀巴大师创立格鲁派。明宣德年间,格鲁派日益兴盛,隆务寺由萨迦派改宗格鲁派寺院,由一世夏日仓活佛在改、扩建母寺隆务寺的同时,在热贡地区大兴土木修建附属子寺,给地方画师队伍的成长和特色画风的形成提供了广阔舞台。到18世纪,热贡艺人陆续外出,到信奉藏传佛教的地方参与壁画、塑造佛像等活动,吸收不同地区的画派风格,形成了现在的热贡画派,成为藏传佛教画坛上的一个重要流派。
根据田野调查和研究相关文献显示,堆绣传入青海涉藏地区约有250年的历史。热贡堆绣工艺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广为流传,历代名人高手辈出。相传,尕沙日村有位很有名气的老画匠制作的堆绣特别精彩,在热贡麻巴部落②的乙格寺里所陈列的一幅长40米、宽30米的巨幅堆绣就是其杰作,此堆绣被公认为是当时热贡地区最大和最精彩的堆绣。此类巨幅堆绣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对绘画和雕塑的要求都极高。20世纪七八十年代,能制作此类巨幅堆绣的,同仁地区只有两人,一位是已故的久美大师,是年都乎村人,不仅绘画技艺超绝,且对雕塑、堆绣、缝纫、石刻等都非常精通,他的弟子造巴、录赛日等也为四川阿坝的一座寺院制作了一幅长24米的堆绣,为近年来之最大;另一位是老艺人尖措,吴屯下庄人,他的绘画和雕塑都非常出色,手艺高超、作品精湛,他不仅在同仁,还为甘南、四川阿坝等地寺院制作过巨幅堆绣,被誉为“堆绣神匠”,是当今堆绣艺术品制作的代表。
热贡堆绣随着隆务寺的兴盛而发展,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和发展,使热贡堆绣独具地域特色,经过尕沙日村老画匠,年都乎村久美大师及其弟子造巴、录赛日,及其吴屯下庄老艺人尖措等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和不懈努力,使热贡堆绣艺术名扬四方。这群老手艺人代表了一种工匠精神的延续,他们用双手在热贡艺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得这门手艺绵延不绝、代代相传。
二、困境透析:文化传承萎靡与产业发展薄弱并存
(一)发展现状
热贡堆绣按品种分类,主要有巨幅堆绣和立体堆绣两种,前者在藏传佛教寺院每年正月间举行祈愿大法会时展出,供信教群众朝拜。大面积的堆绣佛实乃人间罕见的堆绣艺术之奇,是热贡艺术的一大奇观。主要分布在年都乎村、郭麻日村、尕沙日村等,精品代表作有黄南隆务寺、甘肃拉卜楞寺、果洛拉加寺等寺院的释迦牟尼大晒佛,在甘、青、川等涉藏地区有一定影响。后者面呈长方形,长约70厘米,宽约50厘米,镶锦缎边,有卷轴,与卷轴画极相似。堆绣正中为主佛像,主佛像周围是护法等众神像。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堆绣开始走出寺院,走向社会,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当地的民间艺人利用堆绣开发了内容丰富、制作精良的新产品,很多艺术精品纷纷进入市场,融入社会使古老的传统技艺大放异彩。经过多年努力和政府部门积极申报,热贡艺术先后于2006年和2009年分别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代表作名录。2018年5月,热贡艺术入选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2008年8月,热贡成为由国家文化部正式批准设立的我国第三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也是藏族聚居区第一个正式批准设立的国家级生态保护试验区。近几年来,黄南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黄南州”)立足丰厚的文化底蕴,积极发挥热贡唐卡、堆绣等为代表的文化艺术领域的优势资源,通过政府引领、项目扶持、平台打造、技艺培训等方式,有力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技艺创新、增收致富。目前,黄南州现有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8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5名,省级民间工艺师72人(其中工艺大师13名),州级工艺美术大师90名,州级民间工艺大师111名,州级工艺美术师58名。黄南州经营热贡堆绣的公司和个体户达150余家,家庭作坊350余家,现有国家级传承人1名,省州级大师共有15名,堆绣艺人从业人员达2500余人,年收入达1.3亿。
热贡地区是青海省人文旅游资源相对富集区。近年来,政府部门虽然在非遗保护与传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与国家对地方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求及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相比,热贡堆绣工艺传承与保护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情况,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的关系尚未厘清,活态传承与静态保护未做到并行并重。
(二)面临的困境
1.乡土文化逐渐消失。传统村落是热贡堆绣文化存续的空间根基,热贡地区仍有大量的传统村落,这些村落蕴藏着丰富的乡村文化与自然生态景观资源。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村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特别是农村、牧区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很多传统村落、老宅变成了没有原住民居住的“空心”遗址,很多宝贵的乡土文化资源正在加速流失。因此,留住原住民,保护传统村落迫在眉睫。
2.转型升级缓慢。堆绣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产品的更新换代能力来看,由于堆绣的主题仅限于宗教内容,使堆绣文化日益趋同化,缺乏应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加上很多手工艺人因循守旧,不敢越“雷池”一步,堆绣产品种类单一,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文创产品研发力量相对薄弱,营销推广方面缺乏有效策略,观众虽多,但实际购买力远远不够。
3.传承体系断裂。传承体系不完善、教学方式落后、传承后继乏人、技艺断层是热贡地区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面临的一道难题,热贡堆绣传统手艺也同样面临失传的境地,且从业人员呈逐年递减态势。从品质要求来看,“只有画师具备深厚的功底,才能完成大幅堆绣作品的创作,但现在有些年轻艺人为了“赶稿”,普遍采用白乳胶粘贴的方法,而通过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堆绣会因为潮湿、闷热等气候原因容易出现脱落和开胶的现象,难以保证其质量”。③从专业教育来看,由于缺乏大专、本科教育培养模式,现有的手艺人队伍大多数为非专业人员,从业人员缺乏系统的理论培训,整体文化素质不高。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堆绣艺术品制作主要集中在同仁市年都乎乡年都乎村中,周边村庄普及力度不大。根据意愿调查不难发现,在非遗传承人中,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学习手工艺,他们普遍认为学习非遗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加上学习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很难实现传承目的。从年龄和性别结构来看,存在青少年群体较少、中老年人居多的尴尬局面,传承人群在各年龄段不均衡,培养的堆绣代表性传承人数量较少,很难发挥示范带头效应,尤其是女性艺人的数量远远不够,这也是热贡堆绣发展面临的一道难题。
4.产业链条不健全。从市场信誉度来看,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近几年在工艺品市场上虚假产品不断涌现,严重影响到热贡堆绣的信誉和口碑。从客户群体和市场竞争力方面来看,热贡堆绣艺术品主要以藏传佛教内容为主,目标消费群主要集中在各地藏传佛教寺院,放大到全国市场来看,因为局限于宗教内容,缺乏现代创意产品,堆绣产品营销渠道狭窄,难以形成统一的品牌效应,一直处于规模小、产业链条短、发展模式分散、销量持续下滑、客源不足的局面。
三、路径依托:以生产性保护赋能热贡堆绣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
生产性保护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通过生产过程实现“非遗”保护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使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可持续传承的动力,其核心技艺在生产实践中得到传承,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达到活态保护和持续发展的目的。[2]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进程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热贡传统堆绣工艺的形态,使其呈现出新的特征。只有把握新的社会需求趋势,以保护其原生文化土壤为基点,以生产性保护作为切入点,进一步拓展堆绣产品的应用领域和使用价值,不断提升其审美情趣,正确处理好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才能实现活态传承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保护原生文化土壤,筑牢生态文化圈
热贡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其肥沃的原生态文化土壤(热贡文化)孕育了绚丽多彩的堆绣形态,这些长期积淀的文化土壤是稳固和肥沃的,为堆绣的保护、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在浓厚的藏文化滋养下,不断丰富和世代相沿。以热贡堆绣技艺早期发祥地之一的曲麻村为例,该村除了拥有热贡地区最早的寺院根基当格乙麻寺[3]等朝圣之地外,曲麻尚木德村遗址、曲麻勒加村遗址(省级)等卡约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人骨、木头、红泥制成的粗陶片、彩陶,是热贡文化遗址相对富集的地区[4]。其独特性、创造性既是藏族人民灵性的张扬,又是情感的宣泄,代表着广大藏族同胞们的探索、实践、思考和精神力量。从生态文化圈的概念来看,由于族群文化心理、语言环境和风俗习惯的差异,不同区域和族群文化的独特性往往呈现在各自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思维惯性等方面[5],热贡堆绣即是具有区域特征和原生特质的文化样态,原生土壤是热贡堆绣文化生存、发展的根基,而原住民是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核心动力。基于生产性保护的视角对堆绣文化生态保护放在突出的位置,在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及开展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中,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不能忽视其得以孕育、滋养的人文环境,让“鱼”和“水”相互成就,也就是“见人见物见生活”。留住村民,让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得以延续,让他们记得住乡愁,避免传统村落变成只有外在建筑,没有原住民的空壳,避免非遗失去传承基因和土壤环境[6]。因此,要构建科学合理协调发展的城乡空间布局,按照在热贡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沿隆务河谷形成的“一带三区、一核多点”④的空间格局,曲麻村作为热贡彩绘艺术的早期发祥地之一,将曲麻村纳入年都乎组团区——热贡民间艺术保护区(包括年都乎村、吾屯村、郭麻日村、尕沙日村、隆务镇)。在保护与开发中要充分尊重地域文化的原真性,完整地保护文化的原生态环境和本真性,同时,要充分发挥群众积极参与的内生动力,以确保当地群众在非遗保护中的主体地位。将原生土壤的静态保护与原住民的活态传承有机统一起来,共同构筑成为热贡文化链上最重要的原生态文化圈。
(二)加大政策扶持,培育文化创意产业
在宣传推介方面,争取省级扶持资金,由省、州、市宣传文化部门牵头,邀请国内有影响力的纪录片导演和民俗学专家,组织拍摄一部有温度、接地气的热贡堆绣工艺纪录片,在省内外大型城市开展热贡堆绣专题宣传推介活动(纪录片),并争取在央视纪实频道等主流媒体进行宣传报道,营造良好的宣传环境和舆论氛围,进一步提升热贡堆绣艺术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政策引导、项目支撑、资金扶持、人才培养等方式,把热贡堆绣产业发展列入全省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的大盘子中,设立省级的热贡堆绣产业基地、热贡堆绣保护传承基地和省级妇女创业基地,并争取省妇联、文旅、扶贫、就业等部门的扶持,积极搭建平台,开展团队合作,共同设计研发一批有市场需求的热贡堆绣文创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提高热贡堆绣产品在全国市场中的销售量,实现打造热贡堆绣产业、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增加群众经济收入的目标。在提高信誉度方面,建立热贡艺术协会“会标”以鉴定艺术品。召集专家、文化部门、第三方检验检测,对热贡艺术品进行鉴定,建立艺术品质量溯源体系,通过有效沟通手段,将“会标”根植于艺人和消费群体心中,加大热贡堆绣工艺品专利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三)加强队伍建设,建立人才智库
非遗保护的关键是传承,传承的核心是人才。堆绣作为一项非遗保护重点内容,在人才培养方面,应将堆绣人才培养纳入领军人才、创新人才、高端人才培养计划。省级层面出台相应的扶持办法,扶持建立一批热贡堆绣艺术品制作基地、堆绣企业,命名一批领军人才和示范户等。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应以其绝对的文化品格而得以自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除了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还需要围绕其渊源自有的文化品格而延展,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远传承和持续发展更离不开社区和民众的文化自觉[7]。因此,要强化本土人才培养力度,进一步拓宽传承渠道,大力支持和激励妇女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扬,逐步打破热贡艺术传承“传内不传外、传僧不传俗、传男不传女”的传统思维,从家族封闭式传承转向开放式传承,培养一批妇女堆绣艺人队伍,基本形成家庭、村落、传习中心、寺院、学校等多领域和全覆盖的艺术人才培养及传承体系,为堆绣工艺传承发展做好人才储备。在理论研究方面,加大热贡艺术研究院机构职能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和文化艺术智库建设,联合省内外大中专院校设立热贡堆绣本科专业课程,走学院式的教学之路,建立集科研、教育、创作为一体的艺术科研中心和艺术教育中心,为党政部门决策提供文化艺术方面的真知灼见,担当起文化领域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将深入的调查与理性的分析相结合,整理出版热贡堆绣精品教材,扶持出版热贡堆绣成果系列丛书。建议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等衔接省内外有关部门,形成高校与地方联动、合作促进非遗理论研究的工作机制,邀请高校民俗学、文化遗产学等学科领域知名专家教授前来热贡进行有深度的田野调查,对在职文化从业人员进行系统的理论培训,建立相关档案,将调查数据转化为调研成果,实现资源共享。在对口援建方面,积极争取天津援青项目,在黄南州设立大学生实践基地,解决食宿及基本的生活保障,鼓励支持省内外高校中与非遗有关联的民俗学、文化社会学、考古学等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在黄南州开展为期1~3年的志愿者服务活动,充实到文化基层一线,提供智力支持,提升文化队伍整体素质水平。
(四)突出文化特质,开发文化创意产品
随着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不断追求与向往,城市居民对田园生活与乡村文化的需求不断增加,乡村旅游产业成为乡村经济的新生长点。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文化创意产品已经超越了本身的内涵,具有实用性、文化性、区域性、纪念性等特点[8]。实用性是产品设计的基本前提,热贡堆绣也不例外,但其使用的途径较为狭窄,多数是用于唐卡制作,仅限于宗教内涵,在生产性保护的进程中,堆绣功能的拓展是必要环节,将堆绣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开发出特色鲜明的文化创意产品(服装服饰、背篼、挎包等日常用品),才能扩大并升华其与社会大众生活的广泛深刻联系,推动其在当代社会的持续发展。随着农村牧区旅游经济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乡村旅游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艺人们首先应该对艺术持有严谨的态度,更好地去传承父辈们那种用手工缝制堆绣的难能可贵的工匠精神,因为艺术创作只有尊重和挖掘本土文化价值,达到本土价值与创意思维的深度融合,才能不断保持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创造活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提升其品牌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在这方面,有很多基础性和应用性的工作急需要做,比如挖掘堆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价值,深入挖掘与堆绣工艺背后的乡村历史文化、民间文化、自然文化的旅游价值,大力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产业;挖掘当地独特的乡土文化品牌价值,开发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
(五)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建立堆绣文化产业链
堆绣产业链的形成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过程。在堆绣工艺向产业化转型发展中,其内在价值决定了堆绣产品的性质,并形成了相应的价值关联关系,即价值链。“价值链是文化产品内在价值的延伸,是文化产品的内在属性,而产业链是价值链的外在表现形态,是指由一个产业衍生出与其他相关联的其他产业”[9]。从堆绣文化产业的价值链来说,藏族人民的造物理想、审美取向、宗教意识和伦理观念等文化要素在绣品上集中体现,展现了对自然的体验、对社会的认知、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人生的感悟,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并在产业链中形成了核心的竞争力,奠定了供需链构成的基础,即大众消费的文化要素。热贡堆绣的空间分布情况由年都乎乡和隆务镇构成,集中分布在同仁市年都乎、郭麻日、尕沙日、曲麻等村庄。这些村落作为示范可以进一步推广到其他更多的乡镇和村落。其次,绣品主要作展示和生活所用,暂未进行产业化开发,因而并未成为热贡堆绣产业链的补充。因此,应以建构热贡堆绣文化创意产业园为基础,有效整合堆绣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区域和人力优势,建立一个集制作、生产、销售、反馈为一体的产业链。通过热贡六月会、“雅顿”文化艺术节等文化旅游节和“於菟”等民俗文化活动为代表的地域性重大节庆活动的举办为契机,重点挖掘特色产业、民俗、工艺、建筑等区域文化资源,在建立热贡堆绣艺术村、热贡堆绣特色小镇和堆绣古村落等一批特色文化旅游小镇的基础上,激发地摊经济的活力,打造热贡堆绣创业一条街,形成产业、城镇、旅游、生态、街巷“五位一体”的新型文化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热贡艺术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瑰宝,在佛教艺术各门类中独树一帜,也是藏族群众生产生活的不同地区之间、藏汉等民族文化之间交相辉映的产物。这些年,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乡村治理和长远发展。正如鞠熙教授所言,“传统文化能为乡村的生态宜居提供地方经验、为产业兴旺提供智识资源、为有效治理提供贴近民心的策略”[10]。因此,在保护文化生态的基础上处理好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因地制宜建构堆绣生态文化圈和文化创业园区,既是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大势所趋,又是热贡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热贡区域文化、经济发展的内在呼唤,更是堆绣从业者的人心所向。
注释:
①2018年黄南州提出“三区建设”战略,奋力建设全省生态有机畜牧业示范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和藏区社会治理示范区。
②麻巴部落,属热贡十二大部落之一。
③根据热贡堆绣艺人桓贡(男,土族,青海热贡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口述转译。
④注释:一带:隆务河谷热贡文化生态走廊。沿隆务河谷带状分布;三区:保安组团区——热贡军屯文化保护展示区、年都乎组团区——热贡民间艺术保护区、曲库乎保护组团区和热贡生态文化保护区;一核:隆务古街,包括铁吾古城堡在内。多点——民间活态文化保护点:包括吾屯村、年都乎村、郭麻日古堡、尕沙日村、江龙村、江什加村、木合沙村、麻什当村、牙什当村等众多古村落古城堡,对其实施整体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