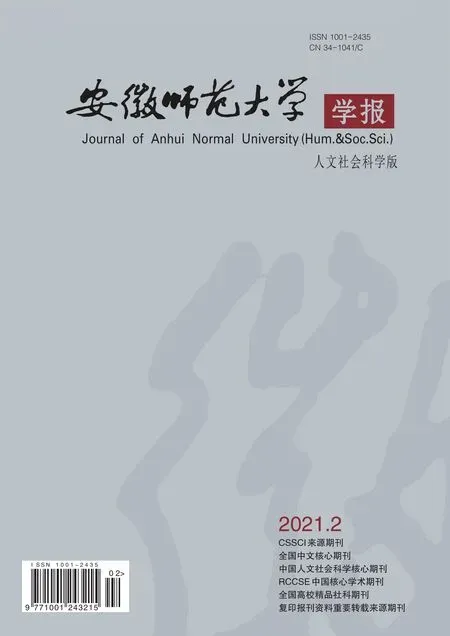自然美的转向:从“祛魅”到“复魅”*
——以大自然文学创作为例
张 娴
(1.安徽大学文学院,合肥230001;2.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合肥231131)
自然美问题一直都是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始终围绕“人与自然关系”这一核心要素展开。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语境的变化,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以及人类对自然的审美态度也发生着不断的转变,从起初把自然作为客体性对象进行神化膜拜,到后来“人类中心主义”提出对自然的“祛魅”①“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最早出现在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观点“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里,其本意是指西方国家在从宗教社会向世俗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对世界宗教性统治的解体,后多为美学界引用。、将人的主体性及创造性凌驾于自然之上,再到“生态中心”论“自然全美”等观点的提出,美学界以呼吁对“世界的复魅”[1]3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审美模式的彻底反拨,有关自然美的生成范式及审美转向在美学及文学创作领域也有了划时代的体现。在20世纪全球性生态危机背景下崛起的、具有中国本土生态文学特色的大自然文学,就是以自然美及人与自然关系为主要书写内容,并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意家园为最高审美理想,具有鲜明的现代生态伦理意识的一种文学现象。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生态存在论等角度探讨在当今绿色发展语境下自然美的转向及其新的审美核心,通过阐述工业时代以来“祛魅”所导致的人类生存困境及在现代文学创作领域中体现出的反思,提出以“人在自然中存在”来体认生命之“魅”的观点,为自然的“复魅”之路构建新的哲学美学维度,最终指向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类“诗意地栖居”①出自海德格尔在其论著《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所引荷尔德林的诗歌名句“Full of merit,yet poetically,man dwells on this earth”(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地球大地上),后被译介为“诗意地栖居”。。
一、“祛魅”导致的困境
工业时代以来,现代科学以种种量化的指标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进行抽象化比较与剥离,使得人与物、人类与世界之间最本真的价值联系丧失。马克斯·韦伯的“世界的祛魅”[2]168之说,认为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人们不再相信世界上存在着“任何神秘、不可测知的力量”[2]168,一切事物都是可以通过技术性的方法计算并掌控的,世界在人们眼中不再具有神秘魅力。人类过分迷信并自信于科技知识对自然的驾驭、对世界的改造,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力量与神圣性被彻底祛除,更多的是作为人类科技进步作用下物质资源的占有与利用而存在。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认识论美学应运而生,它以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作为审美的哲学基础及逻辑起点,把人与自然进行形而上的分离,将人的认知凌驾于自然之上,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忽略并抹煞自然的本体意义。认识论美学把审美过程直接等同于人的某种政治的、经济的、功利的认知手段,自然美则等同于主体对客体征服过程中的价值确认,是价值选择后的结果。人对自然的态度从精神化膜拜转变为“理性化”主宰,并以征服和改造自然作为自身价值的体现,而仅仅被视作审美客体的自然世界,只有在符合了人类的美感形式体验时,才具有美的意义与价值。
这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思想核心的世界观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的“可知意识”过分膨胀,无限放大了人的主观力量,并以此曲解了人对自然世界的贪欲就等同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祛魅”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在对世界认知过程中所持有的一种具有主观盲目性的“超验崇拜”,但同时也将人与自然世界完全剥离,摒弃了自然的本原力量及与人类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在这种世界观的主导下,“祛魅”所导致的人类生存困境日益凸显,这一困境在社会发展中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生态危机爆发,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物种灭绝等问题频频发生,人与自然对立的状态日益严重。同时,就人类自身发展而言,如果仅仅凭借工具理性在各种科技、知识领域以符号式、量化式的形态来实现自我的价值认同,否定自然的力量及自然的规律,那么人的本真价值也必将因过分迷信知识科技的“无所不能”而沦为工具的“奴隶”,人类也就失去了自身本源力量不断上升的空间,走向一种价值归属与自身发展相悖的境地。
二、文学创作中的反思
在文学创作领域,西方作家最早开始以环境污染问题及生态危机作为文学创作新的题材,审视人类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文化启蒙主义姿态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对“世界的祛魅”的功利化态度,在反思人与自然的冲突及自然书写的核心价值中形成独特的美学追求,提出了“重返自然”理念及生态主义思想,并由此引发了环境文学、自然文学、荒野文学、生态文学等一系列有关生态书写的文学创作风潮。通过对自然神圣的复归及对自然书写的独特美学追求,来唤醒当代人类日渐消退的自然意识和融入自然的文化传统。
在中国,以刘先平、苇岸、胡冬林、刘亮程、宋晓杰等为代表的大自然文学作家,将文学创作的人本主义立场转向生态整体主义,以探索的姿态将人置身于自然整体之中。他们对自然的书写强调人的在场感、亲历性、纪实性,自觉地把过去传统文学作品里仅仅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延伸到对自然及自然界其它生命物种生存境遇的关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蔑视与戕害,拷问如果失去对大自然、对地球生命物种应有的尊重与保护,人类将何去何从,并以此吹响呼吁人类回归自然、敬畏自然的号角。“它们在人类猎杀、压迫下的苦苦挣扎……它们生存的空间,正被人类蚕食、掠夺……自然养育了人类,可我们缺失了感恩,缺失了对其它生命的尊重”。[3]在刘先平《黑麋的爱情故事》中,黑麋所赖以生存的密林被人类滥伐、生存家园遭到破坏,致使黑麋无奈之中闯入居民区以寻求人类的保护,其通过对自然界生命物种生存境况的思考,反思人类自身生存境况的窘迫;在《魔鹿》中,一连串的感叹:“是的,魔一般的鹿树,魔一般的美!美是有距离的!我愿意保持这种距离,为了欣赏美。”[4]11则是完全站在审美论的角度,由人的本位延伸到自然的本位,自然不再是被剥夺了主体性价值的美感客体,而是一种主体性的独立的美的价值与存在。
三、审美的转向
当代生态美学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应是“我与你”式的对等的主体间性关系,把人与自然作为两个主体进行平等对话,并把这种“审美主体之间的对话放到生存本体论的意义上来考察”。[5]50这种基于主体间性哲学审美世界观的转变,“把人的感性和理性统一于人的生存”[5]50,重新肯定了自然的本体意义,打破了“人类中心论”的价值体系,以对自然“复魅”的审美转向来实现对过去“祛魅”时代所导致的人类困境的突破与超越。
如果说“复魅”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对过去传统的以认识论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一种消解,那么消解之后势必也需要再次对自然美问题进行新的学理重构与认识升华。我们应该认识到,从“祛魅”到“复魅”审美转向的发生,既不是单纯地对过去人类企图主宰自然的全面否定,也不是提倡重新恢复对自然的盲目崇拜,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复魅”不是形而上的愚昧神化,也不仅仅是精神敬畏,更多的应是一种对自然的价值认同,并以此为前提重新确认人在生存发展进程中的自我价值与身份认同。
那么,在当代有关自然书写的文学作品里,自然之于人类的本质意义何在?书写自然的“魅丽”,是否就等同于恢复地球原始生命状态、等同于人的“在场性”的缺失?首先,当代自然文学作品里有关自然的审美书写,自然不再只是作为一种具有参照性的“景物”,而是直接作为艺术主体及审美本体、作为一种具备本源性美感呈现的审美存在,自然之“魅”从未消失,也不会因人的审美方式、价值标准的变化而转移。其次,回到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关系这一美学命题上看,自然美为我们展现出无穷无尽的张力与审美体验,自然美与艺术美并非对立而是统一、融合。我们的文学作品虽将自然直接作为艺术创作主体和审美本体,但并未回避“人”,作家对自然的书写也未抹去人的情感体验与人文关怀。在生态环境支离破碎、生命物种不断濒危的当下,把人置身于自然之中,直面人,直面人对自然该有的责任意识与道德关怀,既是一种对过去审美活动中非此即彼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否定,也是对当今西方“荒野文化”忽略人的“在场性”的一种纠偏,更是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与彻底的人道主义相统一的体现。
《云海探奇》里领略到大自然的瑰丽多姿及猿猴世界的精彩纷呈的主人公黑河与望春;《呦呦鹿鸣》里从打猎队的枪口下救出梅花鹿的主人公蓝泉和小叮当;《大熊猫传奇》里为了寻找一对饥饿的大熊猫母子,在川西高原充满野性的原始自然生态环境中走进自然、亲近野生动物的兄妹俩果彬和晓青。他们勇敢地走向大自然,把自我置身于自然之中,与自然融为一体,在探索自然的神圣与瑰丽的同时也在确认自我存在的价值与生存意义。
四、“复魅”:新的美学核心
马克思曾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人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6]96存在论哲学则直接指出“人不是存在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者”。[7]385自然孕育了人类,而人类本身就栖居在自然之中,也是自然存在的一部分,宇宙自然则是容万物于其中的存在场域。从这一哲学起点出发,我们可以说大自然之于人类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自然之物,它应是存在之物在不断生长涌动着的同时又向自身返场的一种“存在的晕圈”[8],并在其生生不息自融自洽的动态平衡中,源源不断地召回“人”这一存在之物,向内在的“晕圈”里去探求与发现未知世界。
“我对自然的观察,就具有了另一种视角和另一种含义——实际上是和大自然相处,融入自然……通往沙漠深处的红柳、滂沱大雨中扑入胸膛的小鸟、青藏高原的花甸、天鹅湖畔的麝鼠城堡、南海红树中的蛇鳗、从雨林中伸出的野象长鼻、进入箱式峡谷寻找黑叶猴王国……往往比结果更有意义。发现过程的艰辛,自有一种蕴藏在平常中的特殊的魅力。”[9]295-297这段文字充分体现了大自然文学创作者的自然哲学观,自然之美是建立在“关系之美”的基础上的,即人与自然在审美境域里是“此在与世界的关系”[10]43,是人在本己存在中对存在本源的融入与参悟。从这个角度去构建新的自然美,我们可以发现,对自然审美的转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人自身“此在”存在的一种本源上的确认和旨归,自然的魅力来自生命的魅力,而生命这一主题本身也意味着人与自然世界的同一性。
如果说“人在自然中存在”是自然“复魅”之路新的哲学起点,那么对自然万物生命的体认则可以作为自然审美新的美学核心。从生命万物交互通感的角度,将人的全部感官与感觉渗入自然之中,形成种种交合感应,把自然与人的感官体验、精神意志相契合,突破形而上的审美形式,以自然的存在指向生命的本质,以生命的本质展开自然的存在。这也与伯林特提出的“参与美学”相契合,他提出重建美学理论的核心就是,应颠覆过去那种把自然作为一件事物或场景在远处去“静观”,而应以人的各种感官作为审美感知和判断的基础,人应全部“参与”到自然世界中去,从而在“参与”活动中获得感性体验与哲理性思考相结合的审美愉悦。
《东海有飞蟹》里小兄弟俩对大海之生命力量持有一种本能的感知与应和;《美丽的西沙群岛》里海疆的自然之美与守卫边疆战士的心灵之美交融一体;《大熊猫传奇》里女骑士驾着黑骏马驰骋川西山野的脸庞与心灵深处的喜悦完完全全融入山原之中;在《魔鹿》中,作家在感叹带给人们魔一般美丽享受的鹿树却因物种生存竞争,被所谓丑陋的高山榕树的根包裹绞缠以致枯死腐朽的同时,为同样是自然生命物种的高山榕树的生存权利发问:人类不应赋予地球生命物种“美”与“丑”或“贵”与“贱”的定义,生命的权力都是一样的,都应得到尊重。作家把自然与人的生命意志同一呈现,把对生命本身的美感体认作为审美对象,并以人的所有感官介入来实现这一审美过程,实现人与自然自在自由的审美对话。这就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静观之美”“形式之美”,而是一种“结合之美”“通感之美”。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认识到“自然文学作家的作品实际上是人类心灵与自然之魂的沟通与对话”[11]5。
海德格尔提出了“天、地、神、人”四方一体的观点,我国古代哲人提出“道法自然”,将道、天、地、人有机相连,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天人相和”“天人合一”思想。《周易》中论述的“中和之美”“生生之美”“复归之美”,都是一种天地人道各在本位又浑然一体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体现,这种本然状态也是一种万物复归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才会构建出天人万物生命同一的美的“家园”。在此,我们提出以“人在自然中存在”来体认生命之“魅”作为新的自然美的审美核心,既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下的“人化”之美,也有别于生态中心论中完全抛弃人的立场的“自然全美”,它是一种从生态整体主义出发的“结合美”与“融入美”,是人回归自然本真的、与其他审美形态同格的“栖居家园”之美。
五、终极追求
从“祛魅”到“复魅”,以“人在自然中存在”、体认生命之“魅”来重构自然美的核心,还是要回到人类如何生存这一终极命题上来,这也是与完全抛弃人的立场及生存发展的生态中心论的核心区别所在。海德格尔指出“此在总是从它的生存来领会自身,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12]186;当代生态美学也认为,“恰恰是人与自然共生中的‘美好生存’将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统一了起来,‘生存’成为理解生态美学视野中自然之美的关键”。[10]“生存”首先意味着栖居,“祛魅”将栖居工具化、人本化,丢弃了“家园意识”,更丧失了地球生态系统中自然与生存的本质内涵。从“祛魅”到“复魅”,更多的应体现由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整体主义而非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并以此明确人与自然、此在与世界的存在关系。不回避人,不排斥人的立场,而是以“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方式将人置身于世界本源之中。
对自然的“复魅”,重在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把自然界视为生生不息孕育生命万物的有机整体,只有在这一有机整体之内,人的创造性才能协调于自然的源生力量,并融入这一力量不断蓬勃向上生生涌动的过程之中。实现了自然之神圣性与人的创造性的双重肯定,才能真正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类文明才真正得以可持续发展,人类社会才能够在磅礴浩瀚的宇宙家园中“诗意地”生存并前行。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对自然的“复魅”、确定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共同体价值,终极追求应是此在与世界生存关系中实现人类诗意精神的“返乡”与“回家”。自然的魅力是无穷尽的,这正如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也应是无止境的。对自然的“复魅”,不是退回前现代的神化膜拜,更不是抹去人的存在价值与创生力量,而是以“复魅”确认人的价值归属与生存内涵,以“复魅”带领人走向地球“家园”,在“回家”的路上“诗意地栖居”。
绿色发展理念“着眼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与生态协调共赢,为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可行途径”。[13]当代大自然文学创作的兴起及这一文学现象的繁荣,正是文艺创作领域对地球家园意识与绿色发展意识的呼唤。从红树林、杜鹃花、野百合、奇山云海,到叶猴王国、梅花鹿、金丝燕、大熊猫、相思鸟、藏羚羊、麋鹿、雪豹……世界自然万物,无不彰显着生命的广延与魅力、浸透着自然的通灵,而人在置身大自然探寻自然的魅力与价值的同时,也在体认自身存在于自然万物之内的自我价值与身份归属。这是由“此在”走向“外在”进而又回归“此在”的一种升华,是对过去工具理性下机械自然观的一种指正,是正视人在自然世界中存在、直面人对地球自然不可缺失的责任的一种人文关怀。我们认为,这种人文关怀是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形势下重构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突破,也体现了以实现人的“诗意地栖居”、实现生态平衡为核心指向的“复魅”精神的终极追求。
“我在大自然中跋涉了三十多年,写了几十部作品,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呼唤生态道德——在面临生态危机的世界,展现大自然和生命的壮美。”[9]297这是大自然文学创作群体在人类不断面临地球生态危机时的一种人文自觉,作家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为我们呈现大自然广阔的“美”与“魅”,并在这一审美呈现的张力下呼吁对地球生命万物的肯定与尊重,实现人类精神生态的返乡与回归。我们也只有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恢复对自然必要的敬畏与尊重,关注自然本身的诗意价值与审美意义,才能真正把握新时期人与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蕴涵,实现地球自然万物在整体合一的动态平衡中共生共荣、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