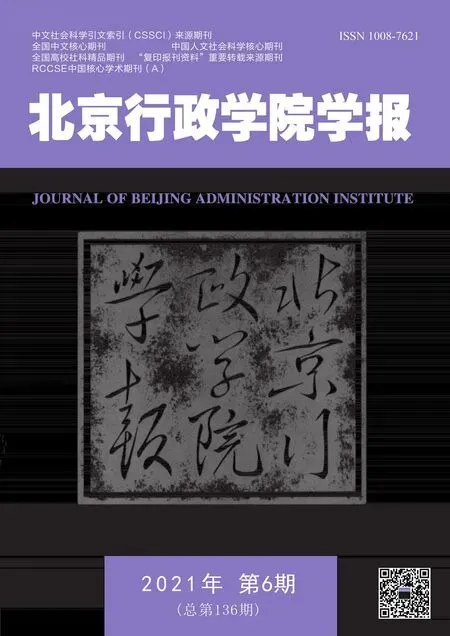《灵魂道体说》与中西哲学之辩
——论第一篇中西哲学的比较论文
□张允熠 张 弛
(1.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200233;2.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北京100891)
谈到中西哲学或中西两大文化圈之思想文化比较,利玛窦和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是实际的开创者。利玛窦的《天主实义》虽然有一些中西哲学比较的内容,但该书重点是欲从“以耶释儒”“以耶合儒”与“以耶超儒”的反向格义上达到在华布道的目的。龙华民则有所不同,他的《灵魂道体说》就中西哲学的两大核心范畴“灵魂”与“道体”进行比较研究,凸显中西哲学理念的根本差异。这不仅是一篇跨文化的哲学比较论文,而且是历史上第一篇中西哲学的比较论文。龙华民此后又写了第二篇论文《孔子及其教理》①该文于1623年前后用拉丁文写成,1676年首次以西班牙文发表,1702年在巴黎以法文再版。1732年伦敦出版了英文版:Nicholas Longobardo,A Short Answer conce ring the Contr oversies about Xang Ti,Tien Xin,and Ling Hoen and other Chine se Names and Te rms,in Dominick Fernandez Navarete,An Acco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Historical,Political Moral and Religious,Written in Spanish.London:H.Lintot,J.Osborn,1732。加拿大华裔学者杨紫烟据法文版翻译了前言部分发表,参见杨紫烟:《论中国人宗教的几个问题》,《国际汉学》2015年第1期。。相比前一篇论文来看,后者是对前者所论核心观点的深化和展开,两篇论文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重点剖析他的第一篇论文《灵魂道体说》。
一、“灵魂”与“道体”各有其源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们争相翻译、介绍亚里士多德哲学,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说及其《论灵魂》(同《灵魂论》)一书于此时开始进入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视域。按现代的学科分类,“灵魂论”属于心理学范畴,但初刻于1630年之后由龙华民撰写,并与汤若望、傅汎际、罗雅各共同订正的《灵魂道体说》不应只被视为心理学著述,更不能被看成单纯的宗教学论著,更重要的,它是关于中西思想和核心哲学理念的首篇比较研究论文。
随着西学的传播,中国知识界习惯于用儒家哲学传统的“道体”观来理解希腊哲学的“灵魂”说,这种在两种异质文化系统之间“以中释西”的格义引发了来华西士们的反向格义,《灵魂道体说》正是这种反向格义的代表作。实际上,《灵魂道体说》仅有两千多字,除龙华民的自序之外,分为“灵魂解”“道体解”“论二者所同”“论二者所异”“论灵魂之象肖天主”五部分。从文题上就可以看出龙华民力图进行中西比较的初衷。在他之前,无论是利玛窦的《天主实义》,还是毕方济的《灵言蠡勺》,对Anima一词一直采取音译,即“亚尼玛”,而到了龙华民这里,他第一次采用了意译——“灵魂”,而且拿来与中国哲学的“道体”并论,由此足见该文的意义非同一般。不过,龙华民强调“灵魂”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与神学的“天主”(Deus)同格,则主要是面对晚明中国学术思想界的现状,力图从哲学理念上纠正中国士人“以中释西”对其所传教义的解读。
龙华民在自序中开宗明义地说:人外有肉体,内有灵魂,两者相合而始成人。而人之所以与物相异,并不在于人有肉体,而在于人有灵魂,灵魂之贵为贵中之贵。灵魂“上肖造物大主”,然而,中国士人把西方的“灵魂”当成中国的“道体”,实为错谬。他写道:
“顾乃今之称灵魂者,往往以道体当之,则何欤?岂水火黑白之可互名欤!予谓名实之不称,无过是者。故草次兹篇,欲与向道君子,共识灵魂于道体之外,而孳孳汲汲,以求副其所以象肖天主者,庶不致屈人伦于物类,而上负宠畀之恩云尔。”[1]438-439
“道体”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具有本体论的意义;“灵魂”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术语,后被经院哲学利用,遂成为其核心范畴。龙华民认为,把灵魂当成道体,乃是中西不分、黑白不分,名实淆乱,没有比这更过分的了。他要跟“向道君子”即奉“道体”为本体的中国士大夫们一同来讨论什么叫灵魂、什么叫道体,以便使那些愿意信奉天主的人,不再“屈人伦于物类”,即把人类归属于物类。这简短的几行序言,提纲挈领,言简意赅,把他撰写该文的用心表达得清清楚楚——“灵魂于道体之外……以求副其所以象肖天主者”,在西方哲学语境中,它与神学相通;中国“道体”之说,反视人伦同物理,乃是先天的唯物主义。龙华民写道:
“灵魂(西原称亚尼玛),神明之体,有始无终者。天主(西称陡斯,乃剙造宰制天地万物之主)造之,赋于人身,为之体模,为之主宰,在世行善,受主圣宠,因而上天享福者也。道体,有体无为,造先莫先,一物不物,本无心意,本无色相,而万形万相,资之以为体质者也。然而二者,实非一物,即有所同,莫掩其异,且灵魂乃天主之象肖,称为道体,信为诬矣。”[1]439
希腊哲学中的灵魂概念,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已经讲得明白,它是“原理意义上的实体”,是“生命存在的原理”,“是潜在具有生命的自然躯体的第一现实性”。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不仅被基督教经院神学所接受,而且渗入到中亚的伊斯兰哲学领域,如对中世纪西方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伊本·西那(Avicenna,即阿维森纳)也著有《论灵魂》一书,其中就完全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我们的论述就讨论这个作为根源和本质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灵魂。”[2]这种“根源和本质的东西”就是龙华民所说的“神明之体”“体模”“主宰”,等等。灵魂不是质料,而是最高的善,所以说它“象肖天主”。
龙华民讲的“道体”又是指什么呢?“道体”是中国儒、释、道共同认可的一种本体,研究“道体”的学问称为“道学”。溯源而知,“道学”在隋唐时,特指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见《隋书·经籍志》),或“老庄道家之学”。但仅从“道学”两字的表面意义而论,“道学”可统指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儒、释、道中的任何一家,换言之,中国哲学史上的“道学”实为各家共同的学问。道家奉“道”为最高宗旨,儒家尊“道”为人生圭臬,其视“道”之重丝毫不逊于道家,如孔子就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道”在儒家那里就是核心价值。佛家讲“八正道”,还讲“六道轮回”,“天道”“人道”“兽道”,等等,“人道”只是六道之一。然而,《宋史》增列《道学传》,“道学”两字却另有所指。《道学传》的“道学”专指两宋时代的新儒家学派,计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及其弟子共二十四人。宋代“道学”之义也有转意,如张载说“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答范巽之书》),这里的“道学”泛指当时以儒家为主流的正统意识形态,跟《宋史》中的“道学”意义颇不相同。仅用“道学”两字特指二程兄弟所创之学,始于南宋时期的朱熹。朱熹说:“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程氏遗书后序》)!这句话中透露了“道学”二字的由来原为“传承孔孟道统之学”。可见,“道体”确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的“灵魂”,它源于中国的“道统”,而经院哲学的“灵魂”却是从希腊哲学那里移植过来的先天概念。
但“道”在朱熹那里等同于“理”,从而加重了其形而上学的色彩。朱熹说:“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则谓之道,以其各有条理而言则谓之理。”[3]“道”在朱熹那里又与“太极”等同,如他说:“太极,形而上之道也”(《太极图说解》)。“道体”两字的含义即“道”之“体”,即“太极”。唐代王通著《道体论》,实为道家著作,宋代新儒家从道家借取这一概念以诠解儒家哲学。如朱熹《论语集注》说:“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程子曰:‘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4]再如《朱子语类》载,或问:“泛观天地间,‘日往月来,寒往暑来’,‘四时行,百物生’,这是道之用流行发见处。即此而总言之,其往来生化,无一息间断处,便是道体否?”[5]这些都是把“道体”视作自然界运行规律的本然状态,此种状态谓之“体”,其生发流行即为“用”,所谓中国哲学的“体用之辩”实为“道体”与“道用”之辩。显然,“道体”作为最高哲学范畴被纳入了朱熹哲学的思辨体系。
利玛窦来华后遵行“合儒拒佛”“合儒拒道”的策略。在“合儒”上,他又提出了“合先儒而拒后儒”,此为传教策略。“先儒”指孔孟之道,“后儒”指程朱陆王等宋明儒家学说。龙华民所说的“道体”实为先儒后儒和佛道都强调的核心价值,尽管各家略有不同,但毕竟是共同承认的哲学本体。晚明是王阳明心学流行的时代,王阳明本人原是出入于佛老而后自成一家的大师。王阳明毫不讳言地说:“吾亦自幼笃志二氏(释、老),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6]他认为佛道两家之说“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也就是说,儒释道三家在哲学义理上并无太大差异。降至明末,王阳明后学蜕变为禅,空讲心性,蠹蚀世风,朝官清谈误国,士人蹈玄向虚。于是,有识之士呼吁要“实学救世”,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兴起。西方耶稣会士适时来华,利玛窦等人屡次用经院哲学概念附会儒家哲学思想,同时,接近耶稣会士的中国儒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也仅能从儒家经典角度来格义西学概念,于是,便出现了用“道体”比附“灵魂”的现象。就两者同为中西方最核心的哲学理念以及两个概念之间不同的思想基础和语义渊源来说,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利玛窦起初对此心知肚明,但出于拉拢中国士人阶层的目的,他并没有将这一问题挑破,只是在《天主实义》中反复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和形式逻辑强调“自立体”并非中国人所理解的实体。然而,潜心钻研儒学的龙华民却公开申明“道体”与“灵魂”既不同义,也非同源,唯有辨明两者之异,才能纠正中国儒士对外来基本教义的误读,也唯有从哲理上判断儒家的“道体”并非经院哲学中的“灵魂”,才能使中国知识阶层放弃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信念,从而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神学信仰,以达到他们来华布道的目的。在一部中国思想和哲学史上,这是一件重大而不可不察的事件。
二、“灵魂”与“道体”之小同大异
利玛窦在“儒服传教”中,为打通中西、融会耶儒,常用孔孟之“道”比附西方教义,如说,“道辽且广,不博问不可约守,详问即诚意之效也”,“如以无意无恶为道,是金石草木之,而后成其道耳”。[7]由于利玛窦首开其端,遂有人就把“灵魂”论纳入了“道体”之说。龙华民见此情状迫不得已,起而欲澄清之。他呼吁对“灵魂”与“道体”要“莫掩其异”,并分别对二者各“是什么”给予解答。值得注意的是,龙华民在解释什么是“灵魂”时,一方面运用了希腊思辨哲学(推理)方法,另一方面宣扬其基本教义,总体上没有脱离利玛窦《天主实义》经院哲学或神学的窠臼。他说,“灵魂非关气聚,非涉形化,非由天降,非自地出,并非从四方来投者,乃独受造于天主也。又以明灵魂第受主造,而实与主异体,一为匠成,一为受成,大有分别也。”[1]439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灵魂绝非物性,而“独受造于天主”;二是灵魂虽为“主”造,但与“主”异体,“主”是创造者,“灵魂”是受造者。显然,利玛窦这里说的“灵魂”似乎不能与“天主”(神)等同。那么,“灵魂”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龙华民搬出了“四因说”,袭用的不外乎是托马斯·阿奎那经院哲学用过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推理论证方法,原文如下:
“所谓为人身体模者何?模为形物,四所以然之一,所以置是物于本伦,别是物于他类者。当人受胎之始,精血已耳,犹未成人。乃蒙天主造赋灵魂,以为其身之体模,于是乃成人类,而异于飞潜动植一切蠢冥之物焉。譬如水与火,因其体模不同即冷热异性;又如依模之成器,模范既异,而品类之别也。”[1]440
“模”就是形式,为“四因说”之一因。这里着重强调灵魂是形式,而不是质料。但灵魂又是“天主造赋”,这与利玛窦所说同。“灵魂”与“天主”(神)究竟是什么关系?龙华民多次指出:灵魂“象肖天主”,灵魂是天主的复制即拷贝——我们只能理解为它与天主同格。人与神则不同,人的躯体的质料原是“精血”所成,唯有形式(模:灵魂)才能赋人以生命。不同的形式赋予不同质料以不同的生命,人与“飞潜动植”这些“蠢冥”之物区别,就在于形式不同,而不在于质料不同。应当说,龙华民的这种解释基本上符合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的原意。但他却强调灵魂不灭,“人死后天主之赏罚随之”,“故曰圣宠者,灵魂之生命,上天之梯航也”[1]440,这就把亚里士多德当成论证神主天国的工具了。基于这种立场,他把西方哲学的“灵魂”与中国传统哲学的“道体”比较之后,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二者小同。龙华民总结出“灵魂”与“道体”有四点相同之处:其一,二者都为“天主”所造,皆由“无”而为“有”;其二,二者永恒不灭,道体是宇宙间一切有形之物的内核,如果“道体”不存,则万物俱灭;其三,二者都是实体或本体,因二者皆为“天主”所造,皆属一定的实体,这种实体并没有消长损益的变化;其四,二者都能付实体于物,“道体”本来就是有形物体的质料,一旦为各种形式相配适,即能成全各种有形物体,“灵魂”本来就是人躯体的形式,一旦与躯体质料相配适,即能成全有生命的人身。概括起来,“道体”与“灵魂”最大的相同之处是中西哲学的各自本体,至于说是“天主”所造,只是经院哲学的悬拟,因为在基督教那里,除造物主之外,一切精神现象和物理现象都由“天主”所出。第四点与其是说二者的相同,倒不如是说二者的大不同,因为这里强调“道体”是质料,“灵魂”是形式,是两者的根本差异。把最本质的差异放在“同”中来说,只是求小同。
第二,二者大异。按龙华民所论,“道体”与“灵魂”相同之处委实不多,细数不过区区一二而已。但相异之处足有十处之多。撮其要,实际上也就是一点,即他反复强调的“道体”等同“质料”、“灵魂”等同“形式”;或“道体”等同“物”、“灵魂”等同“神”。抓住这一点,龙华民从不同角度反复论说,故使该观点成为《灵魂道体说》的立论轴心。他写道:
“道体寄于物,不能离物而独立。盖道与物原相为有无。无道,物不成;无物,道亦无着矣……灵魂不然,与身俱生,不与身俱灭,在身离身,皆超然独存独立者也。”[1]442
“道体本为质体之类(质体者,本无一定之形象,能受万形万象……)灵魂本为神体之类(神体者,既无形象亦无质体,而实禀灵明通达之性,类于天上天神,西谓谙若者也)”,自存自立,不系方所,不着色相者也。”[1]442
“道体既属质体,则所受依赖亦质,如精粗冷热大小等是也。灵魂既属神体,则所受依赖亦神,如学问道德善恶等是也。”[1]442
……
以上诸条,皆围绕着一个宗旨——“道体即质体”,或“道体”即物体。中国古代哲学无论儒道还是中国化的佛教,从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共生共处的理念出发,无不强调“天地万物总为一道体”,儒家经典《周易》与道家经典《老子》在这方面思想完全一致。如《易传·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老子的《道德经》认为“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物包括人类都来源于道,也都合体于道,所以称为“天地万物一体”。而龙华民从经院哲学的“灵魂”论出发,极力否定“天地万物总为一道体”说法。他主张灵魂为人所独有,每一个人都有灵魂,每一个人都有一完整的灵魂,彼此又各有个性,不能以一共性而束之(“人各有一,各具全体,彼此各异,不共者也”[1]442)。但灵魂又都“本为神体之类”,即虽无形象和体质,却“实禀灵明通达之性”,所以灵魂“类于天上天神”,西人称其为“谙若者”①基督教的“天神”,今译“天使”;“谙若”,即“天使”(Angel)的音译,今译“安琪尔”。,即无所不知、无所不通的神明。因此,灵魂是自由自在的实体,既无形象也无色彩。
出于这种本质性的大异,龙华民指责中国哲学:“无道,物不成;无物,道亦无着矣!”而“灵魂”则不然,它“与身俱生,不与身俱灭”。意思是“道体”既然为一物体,那它与万物就相互依赖,相互生灭;而灵魂可以使躯体赋有生命,却不因躯体消灭而消灭,灵魂是不灭的。因此,“道体”说只能使人着眼于质料本身,注重物体的精粗、冷热、大小这些外在的属性,导致物化价值观的形成,而忽略心灵中最高尚的东西,例如知性上的学问和德性的善恶。换为当下语言,即“道体”论把人引向实用主义,而灵魂说把人引向理想主义——从龙华民的逻辑出发,中西哲学的本质差异必然导致不同的价值目标。
三、形而上学的误读
龙华民对中西哲学差异性的基本认识,有着严重的认知误区。
首先,他偏离了亚里士多德基于形而上学的灵魂论,或者说它是经院哲学改造过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耶稣会士们的“灵魂”论详见毕方济及徐光启合译的《灵言蠡勺》,但该译本并没有全部传递出亚里士多德《灵魂论》的真实信息。其直接的底本是葡萄牙科因布拉学院(Coimbraii Collegii)编写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教材,而这个学院编写的亚氏著述几乎都是经过托马斯主义过滤的,宣传的是经院神学的观点,是被按神学目的改造过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或者是托马斯—亚里士多德主义。有学者甚至认为,其中有些部分直接来源于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在灵魂问题上,它继续并展开了《天主实义》未竟的工作”,它“通常采用哲学的方式进行辩论,而不是借助圣经”[8]。《灵言蠡勺》从“灵魂”概念出发,却把基督教的“灵魂不灭”论楔入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体系中,致使我国有研究者也认为:“西方哲学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皆讲‘灵魂不灭’,基督教哲学更强调‘灵魂不灭’的意义在于‘上帝’将根据人在世时的善恶而对其进行赏罚。”[9]实际上,亚里士多德不仅没讲过“灵魂不灭”,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反对“灵魂不灭”论的。
亚里士多德明确表态:“说灵魂具有广延性是不正确的;因为他所说的‘万物之灵魂’很显然是指某种类似所谓心灵的东西;它既不同于感觉能力,也不同于欲望能力;因为它的运动并不是循环的。但是心灵是单一的连续的,如同思维一样;思维包含了多个思想,但思想的结合则是连续的,正如数目的结合一样。相反,广延的联结并不是连续的。”[10]16如果灵魂具有广延性,它就可能独立存在,然而,灵魂是不能离开肉体而存在的。他指出:
“在多数情况下,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属性似乎都不能脱离躯体而存在,例如忿怒、勇敢、欲望以及一般的感觉。思维有可能例外,但如若它也是一种想象,或者至少它依赖于想象,那么它也不能脱离躯体而存在。如果灵魂的功能或属性中有某种独特的东西,它就能与躯体分离而存在,但如若对灵魂来说并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那它就不能脱离躯体而存在。”[10]5
“相反,似乎更应当是灵魂和肉体结合在一起的,无论如何,只要灵魂一旦完结,肉体就会在空气中消散并腐败。”[10]28
“躯体是潜在的存在。但是,正如眼睛既包括瞳孔也包括视力一样,生物既包括灵魂也包括躯体。由此可见,灵魂和躯体是不能分离的,如果灵魂具有部分,那么灵魂的部分也是不能和躯体分离的。”[10]32
“都不能脱离躯体而存在”“灵魂和躯体是不能分离的”……无论是动物的灵魂、植物的灵魂,还是理性的灵魂,都不能离开躯体而存在。看到上述亚里士多德反复强调的观点,我们便知道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是如何粗暴地阉割了被他们尊为“圣人”的人的原话原意。甚至包括“隐得来稀”(entelecheia)被解释为神秘的上帝推动力,实际上都是被歪曲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如《灵言蠡勺》中明确指出生魂、觉魂与灵魂区隔,这也明显跟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不符。《灵言蠡勺》是《论灵魂》在中国最早的译本之一,但须知它绝非亚里士多德哲学忠实的传播者。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与中国哲学的“道体”说在本质上更具相似之处。如朱熹认为“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佛家认为“草木瓦石皆有佛性”,而亚里士多德除认为非生物实体如“瓦石”不具有灵魂之外,人与一切植物、动物都有灵魂,这就否定了经院哲学所说的灵魂独属于人的观点。一切生觉都有灵魂,这是“泛灵魂论”或“泛神论”,众所周知,在近代欧洲哲学中,“泛神论”恰恰是“无神论”的代名词,如斯宾诺莎的实体论。
虽然亚里士多德也强调人的灵魂与植物、动物的“灵魂”不完全一样,“理性”才是人所独有的,但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中国先秦时期哲学家荀子也说过:“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这里不仅强调人体具有一切有机和无机的构成质料,而且具有任何有机物体包括动植物所不具有的知识理性(知)和实践理性(义),这种认识跟亚里士多德大体一致,甚至更为深刻。如荀子强调人的社会性是人所特有而动物所不具备的,他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这跟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与动植物种属关系不能逆向包含的论述也有相似之处。如从先秦荀子的唯物论与亚里士多德的唯物论相比较,我们不禁赞同:东海西海,其理一也。
其次,龙华民把“道体”完全物化而且等同于物质,把“道”说成“器”,从而模糊了“道器之辩”。“道器之辩”是中国哲学最核心的命题和最重要的传统——否定了“道”与“器”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也就在哲理层面上彻底否定了中国哲学固有的本体论。虽然中国哲学强调“道器合一”“道器一体”,然而《周易》明确指出“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器”,朱熹在《太极图说解》中也说:“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这里,无形的道和有形的器是有本质区别的。至于龙华民说“道体”随着物质器体的消灭而消灭,也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哲学的观点,《道德经》中就指出道是“先天地生”,即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朱熹同样强调道是第一性的,器是第二性的,如说:“凡有形象,皆器也,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答陆子静》)。甚至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又说:“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朱子语类》卷一)平实而论,在“道器”“理事”关系上,有时朱熹所论之“理”(道)无异于基督教的“上帝”(Deus),龙华民对此完全无视。
当然,朱熹的哲学是有二重性的,如晚年说:“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朱子语类》卷一)。“理先气后”仅是逻辑推理出来的,实际上本无先后可言。他的“即物穷理”的思想,既含有“物先理后”的意思,也有“道即是器”的含义。朱熹哲学的这种二重性,实际上体现着“道器合一”“理气合一”的思想,这与西方哲学传统包括经院哲学传统强调二元化世界的总体思维方式是不相容的。在龙华民看来,人类世界与物质世界尤其与动物世界是截然二分、不可混同的。他说:“道体冥冥,块然物耳,无有明悟,不能通达。灵魂则有明悟,而能通达天下之理,追究吾人自何处来、向何处去,并能识我性命根本之根本,以殚力昭事之,必敬必爱,罔或厌斁,此人所由大异禽兽者也。”[1]442他指责中国儒释道哲学的“道体论”把人与物视为一“块”,从而消灭了人的理性,把人与物混同,降为禽兽。所谓“天下之理”,即指“性命根本之根本”,即人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终极关怀问题。这一问题只能从“灵魂”论中而不能从“道体”说中去求解,因为灵魂说把人与禽兽从根本上相别,对至善神性“必敬必爱”;“道体”则无理性,无法推通(“无有明悟,不能通达”)。这里,他忽略了朱熹的“太极”就是天下之“至理”,“理”在朱熹那里具有“理一分殊”“综理成端”的法则意义,不失摆脱神性羁绊的纯理性的价值。
最后,中国哲学主张“道体”与自然界万物合一,并非把“道”混同为物。龙华民这种对中国哲学的误读,在中学西传后于18世纪的欧洲思想界同样出现过。如笛卡尔学派代表马勒伯朗士应在中国传教二十多年的梁宠仁邀请创作了《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论上帝的存在和本性》,其以“中国哲学家”比拟朱熹,文中写道:
“因为按照我说过的儒家们的话,人的精神不过是净化了的、或者适合于被理(道)所示知的、从而使之明智起来的或能思考的物质。显然,就是为了这一点他们认为理(道)是照耀一切人的光,是在理(道)中我们看到万物。”[11]
马勒伯朗士认为儒家的这种观点是不可接受的。黑格尔也写道:
“中国所特有的‘实体的精神’(道),仅仅发展到世俗的国家生活的一种统一,这既然使个人降于一种永久依赖地位,同时宗教也始终在一种依赖的状态下存在。它缺少自由的因素;因为它的对象是一般的‘自然原则’—‘天’—‘万物’。”[12]
无论18世纪的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 Nicolas),还是19世纪的黑格尔,他们的这种看法代表着西方思想界对中国哲学的一种普遍共识,其思想来源,无疑是利玛窦、龙华民等人传递到欧洲的有关中国哲学的初始信息。中国哲学之所以在西方被公认为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哲学,既由于中国哲学本身特点所致,也与这种信息的传递和解读相关,难以与“物性”脱离关系。这是中国“道体”说在“两极相逢”即中西相遇的初始期就保留了一种不无刻板的特征和印象。
四、锋芒直指宋明新儒学
龙华民居华58年(1597—1654),其间从未返回过欧洲。初入华时,他按照利玛窦的要求攻读“孔子的四部书”(《四书》),从中探寻原始儒家的思想义蕴,但所谓“四部书”却是朱熹编辑和注释的,这使他同时获得了新儒学宗旨。他不赞同朱熹对孔孟著述的解释,这是他与中国士人和其他耶稣会传教士之间在思想上的最大分歧。除《四书》之外,龙华民曾提到他阅读过的“中国古籍原本”,其中有《大全》一书,即《五经四书大全》。该书是胡广等42位翰林院学者奉敕编撰,汇集了宋代新儒学者共120家的论述,包括周敦颐、张载、邵雍、朱熹、蔡元定等有重要影响的言论。龙华民指出,这是“自秦始皇焚毁所有中国典籍以来1600年间最有名望的评注家所写的有关评注”[13]。龙华民还提到了《性理》一书,实指《性理大全》,该书与《五经大全》《四书大全》一起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被颁行全国,成为龙华民研究宋代理学的最基本的读本。龙华民在《孔子及其教理》中也多次提及《易经》《诗经》《书经》(《尚书》)和老子的《道德经》等,这为龙华民比较中西哲学和批评宋儒之说提供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和靶向底本。
另外,龙华民在华近60年间,士林中流行阳明心学。从中国思想史视域来看,王阳明于明朝中叶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主张,反映了儒学内部一种叛逆精神,其以“致良知”“心即理”“知行合一”为立言宗旨的心学,表现出具有新兴市民阶层要求个性自由的早期启蒙主义倾向。因此,在其死后不久,大学士桂萼上奏,“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明世宗怒斥道:“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作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说,皆其倡导。”[14]嘉靖八年(1529)阳明新建伯爵位被革,王学遭禁。但38年之后,至明隆庆元年(1567)王学解禁,穆宗皇帝朱载坖诏赠为“新建侯”,谥“文成”,并颁铁券表彰。穆宗在券文中写道:“两间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赏,朕甚悯焉!因念勋贤,重申盟誓。”[15]这使王阳明由“坏人心术”的“诈情”之徒一变而为“拨乱反正”的“一代伟人”。万历十二年(1584),王阳明从祀于孔庙,阳明心学进入复盛期。龙华民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来华时,是正当阳明学解禁后如日中天之际。跟耶稣会士交往的中国儒士不乏王门弟子,如作为利玛窦在中国传教事业支柱的徐光启以及与耶稣会士过从甚密的焦竑、李贽等人,都有王学背景。利玛窦一方面在人事上要利用这些人,故提出“合儒”策略,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却主张“合先儒而拒后儒”——明儒即为最后之儒。特别是龙华民其人,对宋儒之论和时儒主张皆持非常异议之论,这在他的《灵魂道体说》的一些批判命题中,可明显地看出来。
作为“外来的和尚”,龙华民对于朱熹、张载、王阳明这些从祀孔庙中的中国圣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万万不敢点名批评的,但其笔锋所向,明眼人一看便知。龙华民对“道体”的批评,首当其冲的代表性人物无疑是朱熹,如说:
“骨子”一词正是朱熹用语。朱熹原意是说“道体”是成物的核心要素。如说“道”为形而上者,本无形体,所谓“道体”之“体”,“是体质之‘体’,犹言骨子也。”[16]。《朱子语类》又载,公晦问:“‘子在川上’注,‘体’字是‘体用’之‘体’否?”[17]1354朱子曰:“只是这个‘体道’之‘体’,只是道之骨子。”[17]1354“此体、用说的是……只就那骨处便是体。”[5]239朱熹把“道体”喻为人体之“骨子”,说“骨处便是体”,明明把“道体”说成是“体质之体”,这就无怪乎龙华民认定“道体”是质料而非形式,自然不可与同格于神的灵魂相提并论。朱熹的这种“骨子”说,是与他的“理一分殊”的理论相一致的,所谓“理一分殊”,即:“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只是个理。此理处处皆浑沦。如一粒粟,生为苗,苗便生花,花便结实,又成粟,还复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各各完全。又将这百粒去种,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间只是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总只有一个理。”[18]物物相异,再异还是物,但物物皆有一理。把“理”(道)比成粟粒跟把“理”比成“骨子”,都是以物分理,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令人惊叹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用了跟朱熹同样的麦株与麦穗、麦穗与麦粒的喻例来阐明“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原理[19]。可见,朱熹的这种“理一分殊”的思想充满着辩证法。然而,龙华民从独断的基督教一神论出发,自然缺少这种辩证思维方式,即使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仅有的一点辩证法思想,在经院哲学中也被完全阉割掉了。
龙华民在批判朱熹时,也牵涉到宋儒的早期代表之一张载。当他提到“道体充满于有形有气者”——虽然如朱熹等宋儒都讲“气”,但“气”是张载的哲学核心范畴。张载是纯粹的气一元论者,主张“虚空即气”,他用“气”来否认先验的精神实体的存在,如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正蒙·太和》)。朱熹在《近思录》中对张载的这一观点评论说:“横渠曰……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近思录集注》卷一)。张载把阴阳二气相互交感产生万物的运动变化过程称为“道”,“道”作为气的一种特性,有“气”才有“道”,无气便无“道”,从而赋予“道”依“气”而存的基本属性。《周易》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张载称之为“一物两体”——“一物”分阴阳“两体”,“两体”交感化生的法则就是“道”,这里同样充满着辩证观念。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张载提出了“亲亲仁民,仁民爱物”即“民胞物与”的命题(《西铭》)。龙华民的“灵魂”说在张载的“气”之一元唯物论中是完全没有存在余地的,因此,张载的“道体”说与龙华民的“灵魂”说形成了全方位的对立。从这种意义上说,龙华民所批判的“道体”说实际是张载“气”一元论的“道体”说,而不全是朱熹的“骨子”论。
龙华民重点批判的对象是王阳明,因为正是王阳明极力主张“天地万物一体”论。如王阳明说:
“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
“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20]
此处“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正是龙华民所指责的“天地万物总为一道体”的底本。“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这里的“灵明”“良知”颇似龙华民所说的“灵魂”,但把人的灵魂也看成“万物”“草木瓦石”的“灵魂”,在龙华民看来,这当是最大的异端。王阳明还说: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21]500
“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其明德也。”[21]501
“天体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实为王阳明的理想社会,是他对儒家“大同”思想的发挥,揭示了一种人类普世主义和共同体思想,也是其哲学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然而,这种要合天地人与万物为一体的哲学主张触动了基督教哲学灵魂信仰说的敏感神经。龙华民在《灵魂道体论》中着力痛砭这一说法。如:
“道体分之则为天地,散之则为万物。而天地万物总一道体所成,无有殊异,故曰万物一体。灵魂不然,人各有一,各具全体,彼此各异,不共者也。”[1]442
这段文字虽然不多,但却揭示出中西思想文化深刻的内在差异:中国的“万物一体”彰显了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共同体志向,而西方的“灵魂”恰恰主张“人各有一”“彼此各异”的“不共者”的个体意志。龙华民从基督教经院哲学出发强调灵魂为人所独有,每一个人都有灵魂,每人都有一完整的灵魂,彼此又各有个性,不能以一共性而束之。灵魂“本为神体之类”,即虽无形象和体质,却“实禀灵明通达之性”,所以灵魂“类于天上天神(谙若者)”,灵魂只能属于人所拥有,从中可以引申出个人的自主独立性和自由性。
虽然王阳明处在龙华民的靶心位置,但“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并不为王阳明所独有,中国的儒道释三家多少都有这方面的议论,都不接受“天主”造物的信念。对此,龙华民说:
“且人既不识灵魂,而以道体当之,遂併不识造物天主,亦以道体当之。如世论,徒以太极大道虚空等,为生造天地万物之本是也。”[1]444
“儒云,物物各具一太极;道云,物物俱是大道;释云,物物俱有佛性,皆是也。所谓太极、大道、佛性皆指道体言也。且前人又谓之太乙、太素、太朴、太质、太初、太极、无极、无声无臭、虚空大道、不生不灭,种种名色,莫非形容道妙耳。”[1]441
这里说的太极(儒)、大道(道)、虚空(佛)三家,统为一“道体”,都体现了中国哲学遵循共性的原则。这难怪龙华民集中火力对着三家同时开火,后儒说“物物各具一太极”;道家说“物物具有大道”;佛家说“物物具有佛性”。“太极”“大道”“佛性”——统是一个原理,无不是指“道体”而言。所谓“太乙”“太素”“太 朴”“太 质”“太初”“太极”“无极”“无声无臭”“虚空大道”“不生不灭”等形形色色的称谓,无非都是形容“道体”的美妙而已。龙华民断言,中国儒释道三家所讲的这些东西,无非“道体”的物化,没有本质区别。有学者认为,“道”作为中国哲学“本体论”,实际上“具有多义性和歧义性”,“中国人所追求的对于‘道’的认识,同样具有‘爱智’的意义”[9],这是对的。但龙华民不承认这种“多义性和歧义性”,他认为儒释道三家之“道”没有差别,殊不知历代儒家都自觉地把孔孟之道与老释两家严加区别,如韩愈就强调,“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道也”(《原道》)。析而言之,儒家重“人道”,老子重“天道”(且有玄冥之色),佛家之“道”追求的是死后寂灭世界。龙华民不加区分地把三家之“道”统而论之,大加贬斥,未免有些武断。
需要指出的是,龙华民在批判后儒(包括佛、老)的“道体”时,对先儒如孔子则表现出肯定和尊敬的态度,他说:
“道体无意无为,听其使然而然,又不得不然,是谓有受造之能,而无创造之能。灵魂者,自有主张,行止由己,不受以强制于物。《论语》云:匹夫不可夺志也,是一验也。”[1]442-443
在龙华民眼中,《道德经》说“道体”是“无为”和被动的,那么,它就是“听其使用”,没有创造力,只是“受造”而非“创造”①其实,这是对老子哲学的最大歪曲,老子哲学的“道”是“无为而无不为”“无治而不治”。。而“灵魂”则是个性自由的体现,它有独立性,绝不受制于物,只有“创造”而绝无“受造”,孔子说“匹夫不可夺志也”,便验证了“灵魂”的这一特点。显然,作为利玛窦继承者的龙华民,在把中国哲学“道体”说与西方哲学“灵魂”论做比较时,不忘“合先儒而拒后儒”的传教方略。平心而论,一位传教士不可能不坚持其神学立场,如就纯哲学的角度立论,龙华民对中国哲学也有肯定性的公允评价,如他在《孔子及其教理》一文中,就认为中国哲学虽然与经院哲学有冲突,但却跟希腊哲学更为接近,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此处就不赘述了。
结语
从中国的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来看,《灵魂道体说》不仅开启了中西哲学比较的先河,且对中西哲学的性质和特征进行了初步揭示。就中西哲学的性质而言,龙华民指出中国哲学的核心理念“道体”不是纯粹的精神实体,没有摆脱物性的羁绊。相较之下,西方哲学的“灵魂”是纯粹的精神实体,是“象肖”基督教“神”的符号。龙华民认为,如果把中国的“道体”理解为西方的“灵魂”,它就应该是不兼不杂的纯粹“超物理”“超形性”的精神实体,不应为万行万相的合体;“道体”用四大(土、水、火、风)、阴阳、理气等概念彰显其为“兼体”(对立体的合体),这只能表明它实际上是“杂体”(若干体的混体);“兼”则不单,“杂”则不纯;“灵魂”不兼不杂,绝对纯体,因而属于“神体”,故超越于“道体”之上。但龙华民出于西方哲学之绝对神人二分的固定思维模式,不能理解中国哲学“道体”说中深藏着的辩证法思想,显示了中西哲学的差异与隔膜。
就中西哲学的特征而言,“道体”说反映出中国哲学强调“天地万物一体”的致思趋向,内含一种群体与共同体意识,体现了中国哲学重共性的特点;而“灵魂”论揭示出西方哲学重“自有主张,行止由己,不受以强制于物”的独立精神和个体意志,体现了西方哲学重个性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经院哲学虽然吸收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元素,但在龙华民所强调的“天地之大,惟一天主创造,亦惟一天主统御之”[1]443核心教义的支配下,希腊哲学的自由精神终究没有得到充分发扬,反而被一神论的基督教专制主义所窒息。
由此可见,《灵魂道体说》虽然是一篇比较哲学论文,但由于作者的基督教立场而非纯哲学立场,最后毕竟没有跳出“哲学服从神学”的经院主义窠臼。《灵魂道体说》一文扬西抑中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冯友兰曾说过,中国没有西方的宗教传统,但中国有延绵悠久的哲学传统,“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22]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实际上都是哲学流派,即使佛教哲学,不仅富含辩证法,而且宣扬一种唯心的无神论。龙华民的扬西抑中,实际上是在扬宗教而抑哲学。不过,龙华民对中国哲学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在《孔子及其教理》一文中对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的比较也是颇有见地的。
总之,龙华民对中西哲学的比较和认识,对其身后欧洲人中国哲学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年被神学思想笼罩的西方思想界把中国哲学定性为无神论和唯物论,这种影响之巨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17世纪德国思想界出现的“无机论”哲学,还是18世纪的欧洲启蒙时期,思想家由此举起反宗教的旗帜,都跟中西哲学交往的这段史实相关。如果说,中国文化中这种异质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在17、18世纪的欧洲推动了反神学的启蒙运动,而到了19世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把“物质”作为本体,把相当于中国哲学的“道”看成客观规律,那么,中国哲学在欧洲的文化土壤中终于找到了真正的知音——这是又一需要专门讨论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