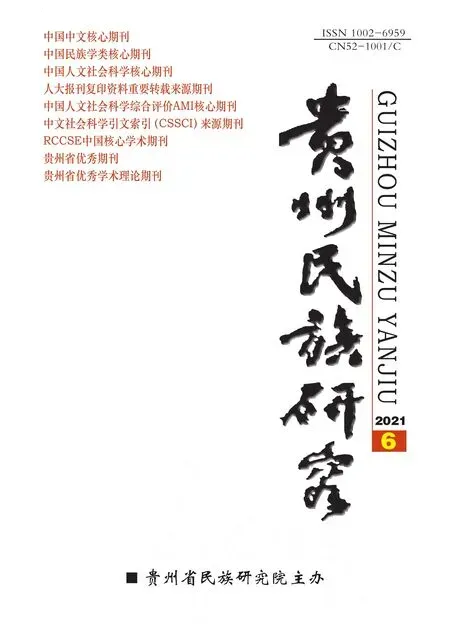贵州省民族研究所(院) 创建60周年民族文学研究成果综述
潘光繁
(西北大学 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陕西·西安 710127;贵州省民族研究院,贵州·贵阳 550004)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院) 成立于1960年,60年来,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科研人员从不同的视野和维度对不同领域的文学作品进行深入探索,发表了数量众多的论文,对贵州各民族的文学作品、文学价值及文学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文学研究聚焦民族民间文学
贵州省民族研究院民间文学研究领域涉及面广,涵盖了民间文学中的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叙事、民间戏剧等。
(一) 史诗
作为一种叙事长诗,史诗往往叙述的是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史诗涉及历史久远、空间广阔。对不同民族史诗开展研究,丰富和发展了文学学科的研究领域。
张民《从<祭祖歌>探讨侗族的迁徙》一文以《祭祖歌》为研究对象,对侗族的地名音译及迁徙路线、迁徙途中的地理环境、梧州居民与古州侗族、侗族与茶山瑶、迁徙原因及年代、迁徙时的社会状况、侗族地区的古代居民、其他诸说进行了深入探索,认为以叙述侗族祖先居住过的地方,迁徙的原因、路线,以及途中所见到的自然景象和定居的地名,作为祭祖颂歌内容保留于婚姻习俗之中,《祭祖歌》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在缺乏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可做考证的情况下,以它作为探讨侗族的迁徙线索,有现实意义[1]。
杨世章《苗族婚姻史诗<开亲歌>浅谈》一文以流传于黔东南和黔西南苗族地区的开亲歌为研究对象,这是苗族十二路酒歌中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流传最广的一路的《开亲歌》。从《开亲歌》的内容和《开亲歌》的价值进行探索,得出《开亲歌》对人类学、社会学、史学、民族学、民俗学,以及语言学的研究,都有研究价值,而对于研究古代苗族的婚姻制度和苗族的婚姻习俗,其意义尤为重大。可以说,《开亲歌》不只是苗族婚姻制的发展史、编年史,更是一部具有浓厚原始性的婚姻史诗[2]。
罗世荣《浅谈彝族史诗<勒俄特衣>中的支格阿龙》一文,以《勒俄特衣》这部用古彝文记录下来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中的支格阿龙为研究对象,史诗通过神话描述了古代人类创造世界的艰苦生活,支格阿龙是史诗《勒俄特衣》中的主人公。从支格阿龙是一个为民除害的彝族英雄、是彝族人民集体智慧的体现者等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展现了人类祖先与大自然斗争的壮丽图景,歌颂了彝族先民不屈不挠向大自然开战的进取精神。得出一个民族的神话史诗,往往是这个民族劳动人民最早集体创作的长篇作品。它不但留下了这个民族在社会发展最初阶段的生活斗争图景,记录了这个民族在其童年时代对宇宙万物、人类社会的种种解释和看法,美妙的神话、丰富的想象、富有特色而引人入胜的传说故事和生动朴素的诗歌语言,显示着这个民族在艺术创作上的聪明智慧和富于艺术才能的结论[3]。
余宏模《中国彝族铜鼓礼俗与<铜鼓王>》一文从铜鼓文化在滇桂交界彝区现实民俗事象中,仍然闪耀着夺目的光辉说起,并将诸如岁首族祭,卜选“麻公”和铜鼓;补度新春,祭祖祭鼓共欢乐;跳弓节祭,缅怀祖先响铜鼓;忌欢节期,安定万物埋铜鼓;同欢同乐,重敲铜鼓庆丰收等为例,说明彝族有铜鼓的传说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4]。
李永皇《从<开亲歌>看苗族古代婚姻的变革》一文从婚姻的角度对《开亲歌》进行分析,认为《开亲歌》并非是一部如何开亲的歌,而是一部苗族古代婚姻史,但它不是以学者的论述方式表述,而是以形象、艺术的方式来表述,而所表述的婚姻史与人类共同的婚姻史相一致,而且在一些表现上存在自己的特点[5](P322-328)。
总体来看,贵州省民族研究院建院60年来,科研人员对于民族史诗文本的研究相当丰富,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均有突破。
(二) 民间传说
作为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学的民间传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通过对民间传说进行深入研究,对继承和发展优秀民间文化有着重要的价值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今旦《台江苗族的盘瓠传说》一文把台江苗族的盘瓠传说与《搜神记》所载的盘瓠神话进行比较,得出两者的异同点[6]。余宏模《夜郎竹王传说与彝族竹灵崇拜》一文认为,夜郎竹王传说有诸多版本,虽各说不一,但始终离不开“水、夜郎”两者的关系[7]。
卢丽娟《布依族的民间传说与农耕文化》一文认为布依族先民从渔猎时代进入农耕社会,其间经历了艰苦曲折的劳动尝试,同神秘莫测的大自然进行了漫长的顽强斗争。植物种类繁多,人们在原始采集植物过程中,随着劳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发现不同植物的实用价值不同,于是选用价值较大作用的植物进行栽培。因此,产生了关于谷种起源的种种神话传说,其中以《茫耶寻谷种》最具代表性。《茫耶寻谷种》的意义在于它反映了布依族先民在农耕生活萌芽时期,战胜各种自然灾害,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8]。
上述三篇论文运用各种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理论层面,并在跨学科视野下解读中国少数民族民间传说的理论框架和内在意蕴。
(三) 民间故事
作为民间文学重要题材之一的民间故事,它是劳动人民创作并传播的口头文学作品,民间故事不仅题材广泛,其内容往往又充满幻想。
覃敏笑《汉、壮、侗民族孟姜女故事比较分析》一文认为孟姜女故事以其人物形象的生动鲜明,故事情节具有曲折感人和深刻浓郁的悲剧色彩,深受我国劳动人民所喜爱,不仅在汉族广大地区流传,同时也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引起共鸣而得到传承。作为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各民族之间文化上的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和相互交流,这本身就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向,更是构成各民族文化始终朝着共同繁荣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对汉、壮、侗民族中流传演变的孟姜女故事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同时对于发掘和发展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会有所裨益[9]。
辛丽平《试论苗族民间文学的民族特点及审美价值》 一文认为苗族民间文学形式多种多样,有诗歌、故事、童话、寓言等,作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苗族人民在漫长的劳动生活过程中,创造了色彩绚丽、内容丰富的民间文学。文章从苗族民间文学的作品内容、表现手法、语言风格上进行研究分析,认为苗族民间文学,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无论是赞扬美的事物,还是揭露丑的东西,都通过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来展示丰富的社会生活具象,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使读者感受到美的愉悦[10]。
(四) 民间歌谣
民间歌谣具有极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并往往与当地的民俗习惯交融汇合。
杨世章《苗族诗歌简谈》一文认为诗歌是苗族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最多,反映面最广,从早期的神话歌谣起,到现代的新民歌止,每个时期的作品都是难以估计的。文章对苗族古歌、理歌、苦歌、起义斗争歌、情歌和新民歌等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印证了苗族民间口头诗歌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想象丰富,气势宏伟,无论叙事诗或抒情诗都千姿百态,浩如烟海,诗歌既是苗族的文学,又是保存苗族历史、道德、哲学、宗教、风俗习惯等民族文化的宝库,对苗族历史文化研究有着重大的价值[11]。
李平凡等人的《彝文文献长诗中的“韵律”》一文着重探讨基本模式在彝文文献长诗音律中的运用,得出这种押音节的基本模式体现于传统的彝文文献中,在一个文本中,交替地押不同的音节,使长诗表现出起伏多变、生动活泼的音乐美之结论[12]。
(五) 民间叙事
民间叙事由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与地方风物有关的民间故事组成,其题材丰富多样,内容极为广泛,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杨世章《读布依族民间叙事诗<王仙姑><王刚>》一文认为《王仙姑》和《王刚》,是布依族人民以本民族农民起义的历史事件作依据,经过艺术加工而成的民间叙事诗。《王仙姑》叙述仙姑的初始和成长;《王刚》写王刚年少的智勇超凡,以及他顽强的毅力和英雄的情怀。文章对《王仙姑》和《王刚》进行深入的解读和评述,最后认为叙事长诗《王仙姑》 《王刚》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布依族人民的起义斗争,成功地描绘、塑造了布依族的英雄形象,这在布依族的民间文学中,是不可多得的诗篇,具有研究价值[13]。
李平凡《人神通婚:以彝族叙事诗<嫩妮和阿珠>和<竹仙>为个案》一文认为,在彝族婚恋类长诗中,人神通婚的题材是相对集中的一个类型。文章对彝族叙事诗中的人神通婚现象做了深入探索,认为在《嫩妮和阿珠》中,山神之女和平民之子联姻的问题不符合彝族古代等级婚姻制度的史实,但它却是对天上人和地上人婚姻关系历史的一种回忆和留恋;《竹仙》是彝族民间的一部爱情叙事诗,文章通过对神助婚姻个案的分析,得出《竹仙》这部长诗透露出彝族古代社会中等级分化的历史事实[5](P315-321)。
杨世章和李平凡从不同的视觉,分别对布依族和彝族民间叙事进行探讨,厘清布依族、彝族民间故事产生的文化根源,指出民间故事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
(六) 民间戏剧
戏剧是文学的四大体裁之一,中国戏剧历史悠久,民间戏剧丰富多彩。
陆刚《彝族古戏剧“撮泰吉”来源新说》一文在总结彝族古戏剧“撮泰吉”演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着重对“撮泰吉”演出内容与彝族其他民俗活动的异同进行观察、对比、分析,认为“撮泰吉”并不是一种单独形成的民俗活动,而是对彝族民间各种民俗活动、宗教礼仪的提取、组装和加工而成的一种新的民俗事象,在对各种民俗活动吸收、借鉴的过程中将其进一步发展成一种具备了戏剧基本要素的艺术形式。不管是祭祖习俗、开财门习俗、扫寨习俗,还是求子仪式、“吉禄谷”仪式的终极目标都是希望祖先和神灵保佑人们能够得到理想的生活[14]。张民《侗戏漫谈》一文对侗戏的产生、发展和文化价值,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评述。
二、文学研究结合经典文学篇章
经典文学对陶冶人的理想,净化人的心灵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教育作用,千百年来,对经典文学篇章的解读和研究从未间断, 《山海经》《楚辞》 《越人歌》就是其中的范例。
(一) 结合《山海经》 《楚辞》的研究
翁家烈的《从<山海经>窥索苗族族源》,以《山海经》中有关“蚩尤”“驩头”“三苗”等记述为线索,对苗族族源问题进行深入探索,认为《山海经》以神话形式从不同角度集录了我国上古时期的历史状况,其中有关苗族先民的人物、事件、时间、空间的片断记述,与众多史籍相吻不悖[15]。
杨世章的《<楚辞·九歌>与苗族巫歌比较探讨》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探索:其一,将《九歌》与苗族巫歌进行对比之后,发现两者在内容、形式都有很多相同或相近之处,认为两者间必有其渊源关系;其二,两者内容、形式相近、相同,但这并不足以说明其关系密切,必须进一步探讨《九歌》取材地点与苗族当时的分布区域情况是否一致才能说明问题。通过史书记载进行考证两者的地区是吻合的,从而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三,既然《九歌》与苗族巫歌内容、形式相同相近,《九歌》取材地区又与苗族分布区域一致,那么楚国与苗族、楚人与苗人的关系不言而喻[16]。作者据此认为,楚人与苗族关系密切,虽不能完全画等号,但楚人中大多数是苗族,是不应置疑的。
(二) 结合《越人歌》的研究
张民《试探<越人歌>与侗族——兼证侗族族源》一文从从原歌音译、楚译、原歌古音与侗音、侗译、格律和韵律几个方面对《越人歌》进行对比分析,认定这首《越人歌》乃是古之侗歌,侗族是古越人的一支[17]。
张民的《试探<越人歌>的诞生地——兼证榜枻人与侗族的关系》一文对《越人歌》的诞生之地和榜枻人与侗族的关系进行考证,从究其文、考其地、证其语、较其歌四个方面进行探索,得出《越人歌》的“诞生”之地,似在鄂、赣交界,今之湖北省的武昌和江西省的九江相连之处。榜枻人操的语言,似为吴越(或侗族)的语言。歌的格律,同吴越之歌(或侗歌)的格律。作者认为,越人的族系,似属“百粤”中的“吴越”之人,并由此推之,侗族的族源,似当“吴越”或被其所灭的“干越”,其后因种种原因,迁居岭南,濡染骆越的文化,最后定居今之地区[18]。
覃平《也谈<越人歌>》 从历史的角度,对《越人歌》进行深入探索,认为仅以某种语言的词汇来作单一比较,就得出结论说这是某个民族的语言,未必符合其历史的真实;因此,在没有更多的资料作证之前,与其说《越人歌》是侗语、壮语或其他某一壮侗语族的语言,勿宁说是古代越语——即壮侗语族的基础语更能令人信服[19]。
三、对作家作品的研究
就面世时间而言,作家文学出现的时间要比民间文学要晚得多。作家文学主要表现为作家个人对现实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描述和独到理解。
(一) 诗歌研究
贺国鉴《有关苗族史料的几篇古诗》一文以明人孙应鳌的《荒城谣十二首》和谢三秀的《蛮娃曲》 《村行即事二首》为研究对象,《荒城谣十二首》是万历四年(1576) 初,孙应鳌因病休官之后,目睹故乡清平县(后改炉山县,今凯里市清平镇) 残破衰落的景象,这一组民歌体的诗篇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处境,租赋徭役纷至沓来,苗族人民已到“泪眼已枯骨髓尽”“已无毛血待诛求”的地步;谢三秀的《蛮娃曲》描绘了苗族姑娘的勤劳倩影和苦难心情,对她们的艰辛生活过程诗人加以描述,层次清晰,凄婉动人;他的《村行即事二首》写于明代水西土司安邦彦伙同川南土司奢崇明叛变事件,为我们提供明末一段极其生动的史料;上述诗篇为探索明代苗族人民的真实生活情境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学意义和史料价值[20]。
余宏模《彝族诗人余达父及其<㥞 雅堂诗集>》对彝族诗人余达父的生平作了详细地介绍,对其著作《㥞 雅堂诗集》十四卷进行了中肯的评述。余宏模介绍诗人、诗作的目的是冀求引起民族文学史和地方文学史研究者的关注。同时,类似余达父这样的少数民族诗人、文人,历史上决非凤毛麟角,存者尚多,他们留下的著作,也应引起重视,通过抢救整理研究,才能让沉睡的文学篇章垂名后世[21]。余宏模的《<时园诗话>前言》 《<四余诗草>前言》 《<大山诗草>前言》 《<慎轩诗文集>前言》 《<芒部府陇氏诗文集>序二》 《<景云诗文集>序》等,对相关诗文著作,均作了深入的评述。
(二) 小说研究
余宏模等人的《冯梦龙写了一本鲜为人知的通俗文学著作》一文对冯梦龙的《王阳明出身靖乱录》一书进行评述。《王阳明出身靖乱录》全书用浅近的文言文叙述,个别处杂有口语。这本书是一本通俗读物,他不按小说的惯例用章回标题,而是分卷,而且给它一个庄庄正正的书名,叫做“出身靖乱录”,也足以说明作者注意到写这本书的严肃性一面,但毕竟是在写小说,写通俗读物,要引起读者的兴趣,扩大读者面,以达到宣传普及王阳明生平事迹的目的,就必须加以演义和艺增,增加了他所搜集到的许多奇奇怪怪动人听闻的传说,编造出许多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情节,使一些枯燥乏味的事件的叙述生动活泼起来,大大增强了可读性。《年谱》中只用两三句话就可说明事实,却编造成上千字故事。作者虽是写小说,但总不离王阳明的基本事迹,遇有与别的书记载不同,他还加以考订[22]。
(三) 女性文学研究
李平凡《彝族女性文学试探》一文从著名的女诗人、诗歌理论家阿麦妮说起,对彝族女性文学的源头进行了探索,着重分析彝族曲谷(曲谷常译为情歌),重点探讨了作为女性文学色彩最浓的出嫁歌、以及情歌与出嫁歌合流,最后对汉文创作的彝族女性文学进行了评述和分析。文章指出,从女性的角度看文学,或从文学的角度看女性,彝族女性在文学上的造诣及影响丝毫不逊色于在政治上的贡献。然而,以往彝学研究的注意力有明显地偏重于女政治家而忽视女文学家的倾向,事实上,历代彝族的女文学家曾为他们所热爱的民族献出过很多的爱,在彝族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位置,我们不应以冷漠的态度对待她们和她们的传世佳作[23]。
四、文学研究融入文学人类学领域
文学以其思想精神的丰富性来感染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从文学出发,实施跨学科研究,步入文学人类学领域,对于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 从文学作品探讨科技文化
覃东平《试述苗族古代的冶金技术——以<苗族史诗>为线索》一文认为流传于黔东南苗族民间的十二路大歌之一的《苗族古歌》(或译《苗族史诗》),“堪称是古代苗族的百科全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古代苗族人民生活的瑰丽画卷”,它上含天文,下罗地理,包含了古代苗族先民关于宇宙的产生、人的起源、社会生产、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苗族古歌》提到的金属有金、银、铜、铁、锡、铅及一些合金,多为常见或常用金属。文章以《苗族史诗》为线索,结合考古发现、汉文献和现代化学物理知识,分析了苗族古代的探矿、采矿及对金属性能、用途的认识,认为它源于实践,是劳动的结晶[24]。
(二) 从文学作品探讨生态文化
覃东平《从苗族古歌看苗族传统林业知识》一文以被称为“苗族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苗族古歌》为研究文本,以古歌原文为依据,论述了它所反映的制种、整地、播种、移栽、砍伐、使用等全过程,着重对《苗族古歌》中关于林木种类、选种、育苗、种植、林木使用等方面进行探索,认为了苗族人民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营林技术,如果我们对这些林业技术进一步加强研究,本着古为今用的指导思想,因势利导,一定能够在当地的林业生态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25]。
(三) 从文学作品探讨旅游文化
李平凡等人的《论彝文文献长诗休闲文化价值的开发利用》一文从建设休闲文化必要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彝文文献长诗是文化休闲旅游的重要开发对象,文章从长诗《阿诗玛》 和影视艺术《阿诗玛》的启示等几个方面出发,提出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各种文化思想激荡,在保持文化的多元和生态平衡的今天,民族文化值得进一步发扬。作者认为,如果将彝文文献精品之作都改编为影视艺术加以传播,对于讲究文化旅游和旅游文化的当今社会,对于发展彝区休闲旅游,促进彝区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是极为有益的[26]。
上述论文,从文学的角度,分析、梳理了文学与科技、生态、旅游的关系,为实现跨学科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提出了创新意义和理论研究方案。
60 年来,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科研人员在发表了数量众多的文学论文之外,还出版了相关的文学评论著作。在文学批评论著方面,有李平凡等人合著的《彝族传统诗歌研究》等;在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有颜勇搜集整理的《荔波县佳荣、岜鲜、水维三乡水族传说及习俗调查》、覃华儒收集整理的《壮族民间文学概述》 《民间传说故事拾零》 《莫家<祖公歌>》、雷广正搜集整理的《潘氏宗谱》和水族古歌、余宏模搜集整理的《辛亥革命时期彝族诗人余达父生平调查》,以及游涛搜集整理的《对思南傩堂戏的调查》等等。
五、结语
2020 年是贵州省民族研究院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作为贵州省内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科研机构,贵州省民族研究院为推动和发展我国民族科研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60年来,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科研人员发表了数量众多、题材广泛的科研论文,出版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学科论著,整理了弥足珍贵的社会历史文化资料,在我国民族学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结合时代与文学的关系,回顾与展望贵州省民族研究院建院60年来的文学研究状况,可以说,在探索中稳步前行,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研究特色,为丰富和发展我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理论体系,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