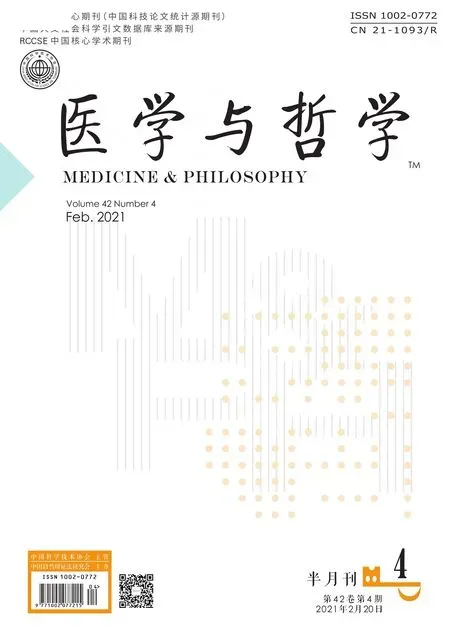中古《诸病源候论》疫疠观及后世内涵变迁*
付 鹏 王育林 周立群
在人类疾病史中,瘟疫一直是影响人类健康与社会进程的重要外感急性传染病。其中“疫疠”一词尤指瘟疫中病情暴烈的疾病。在汉末至隋初近四百年时局动荡的历史时期疫病多发。频繁的疫病逼仄下,成书于隋大业六年(601年),太医博士巢元方奉诏敕撰的《诸病源候论》(以下简称《病源》),首次较为全面地总结了瘟疫的病因、病理和症候。该书多卷涉及了瘟疫病候,如伤寒病、时气病、热病、温病、疫疠病、疟病、黄病等。在《病源》中,“疫疠”与伤寒病、热病和温病等互相并列且专门论述。如果说伤寒、热病、温病等其中也有瘟疫的病候,那么这里的“疫疠”,在《病源》的医学语词意涵下,将不能等同“瘟疫”。因而《病源》“疫疠”一词,在中古时期瘟疫范畴下,还应有更为专门的概念和认识。
1 《病源》疫疠病候疏义
1.1 病名释义
《病源》卷十,为“疫疠病诸候”,共三论,分别是“疫疠病候”“疫疠疱疮候”和“瘴气候”。“疫疠病候”论中定义了什么是疫疠:“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1]222
由此可知,巢元方认为疫疠病候:其一,疫疠是和时气病、温病、热病相互区别、相互并列、症状相似的外感病;其二,疫疠与时气病等外感病相似之处,在于主要致病因素方面都存在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暴风疾雨、雾露不散的异常气候条件;其三,疫疠以发病相似,不分老幼,病情暴烈而捉摸不定,“如有鬼厉之气”的特点作为和其他相似病症的鉴别诊断。
1.2 病候分类
《病源》所列疫疠病候种类为疫疠疱疮候和瘴气候。疫疠疱疮候表现为“周布遍身,状如火疮,色赤头白者毒轻,色黑紫瘀者毒重”[1]223。瘴气候又分为青草瘴和黄芒瘴:“岭南从仲春讫仲夏,行青草瘴;季夏讫孟冬,行黄芒瘴”,其症状“犹如岭北伤寒也”[1]223。
1.3 鉴别诊断
疫疠病候可与伤寒病、时气病、温病、热病、疟病、黄病、痢病、霍乱病等病候类型相鉴别。由于疟病、黄病、痢病各具明显特征,在此不多赘述。这里仅挑选《病源》中关于伤寒病、时气病、温病和热病的特征论述与疫疠简要鉴别。
1.3.1 伤寒
“冬时严寒,触冒之者,乃为伤寒;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必有温病者,皆由其冬时触冒之所致,非时行之气也。”[1]146这与《黄帝内经》所言“冬伤于寒,春必温病”认识一致。
1.3.2 时气病
“春时应暖而反寒,夏时应热而反冷,秋时应凉而反热,冬时应寒而反温,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病无少长,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1]146,187-188具体而言,“从立春节后,其中无。暴大寒,不冰雪,而人有壮热为病者,此则属春时阳气,发于冬时,伏寒变为温病也。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一名时行伤寒,此是节后有寒伤于人,非触冒之过也”;“七月、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小微也,其病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1]188
1.3.3 温病
“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为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而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为杀厉之气焉。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为寒毒藏于肌骨中,至春变为温病。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必有温病者,皆由冬时触冒之所致也。”[1]212-213
1.3.4 热病
“热病者,伤寒之类也。冬伤于寒,至春变为温病。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重于温也。”[1]202
从上述《病源》的病候定义看,这些症状相似的外感病可因气候大体分为两类,分别是气候顺时类(伤寒、温病、热病)和气候反常类(时气病、疫疠病)。气候顺时类都有共同的寒邪病因溯源:伤寒为当时即发;温病乃伏寒藏于肌骨,至春夏而发;热病则伏寒夏变为暑病,热重于温。气候反常的时气病和疫疠病,它们在一年之中皆可发病。其中二者区别在于疫疠病不分长幼,率皆相似,而且发病迅疾,传变迅速,故“如有鬼厉之气”的说法,这是中古时期疫疠病与伤寒、时气病、温病和热病的医学鉴别认知。
1.4 证治思路
《病源》疫疠病证治思路集中体现在瘴气候中的医理论述[1]223-224。
第一,总括治疗原则。虽然瘴气多表现为热病,但是仍需辨明阴阳和表里,不可妄用攻下。
第二,详细辨证。若素体本有热,遇瘴毒。虽然瘴毒得热更盛,然而在表者,不可妄投寒凉攻下,应当温而汗之,即辛温发散的方法。入内者,则须平而下之,即平调与通腑的方法。若素体本有寒,得温瘴。虽然壮热烦满,也当考虑到本体有寒,以温药使其发汗而解。若汗法不得解,则再用寒药通腑等下法。
第三,论述误下和变证。凡是用来攻下治疗重病的药物,药性凶猛,不可一直服用,病去即止。是否攻下,应当以疾病是否入内、是否入里做为判断准则。若数日后瘴病并未入里,也不可预先服用下利之药。否则出现脾胃虚弱,疾病会趁虚而入,增加治疗难度。若出现脾胃虚弱而治疗不佳,可能还会变生黄疸病。一旦黄疸不愈,则会形成尸疸。尸疸症候,岭北客人犹可斟酌救之,而因连续感受岭南瘴气的本土人恐无药可医。
第四,论述瘴气病的时间演变规律。其一日、二日,瘴气在皮肤中,病者表现为头痛恶寒、腰背强重,提示寒湿在表,用汗法,即发汗剂和针灸的方法,必愈。三日以上,瘴气填塞心胸,出现头痛胸满而闷,宜吐法,即吐之必愈。五日以上,瘴气深结脏腑,出现腹胀身重,骨节烦疼,宜下法,此时不再是发表解肌之汗法所能胜任的了。
故而最后提醒后学,医者应当详细询问病者得病过程,了解病患所处状态,再来参照上述治则次第,有序地开展医学救治。
总体来看,当时医学在长期反复进行症候观察和辨症治疗的过程中,总结出一些普遍适用和具有官方临床指南性质的疫病(特别是疫疠)治疗原则,如辨阴阳表里,不可妄攻;在表温而汗之,入内平而下之;汗法不解,次之吐法、下法。一再谆谆教诲,要慎用攻下,不可误治。如果误治,出现何种病证,应该如何应对等。还综合考虑到了个人体质、所处地域、发病时令等多个因素。最后强调治疗必先审症,了解次第。《病源》所载瘴气候的症候辨症层次和治疗大法,不仅集中反映了当时疫病的诊疗理论学术水平,而且对于指导其他疫病和现代临床都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2 唐以后疫疠内涵变迁
除了《病源》,《肘后方》是现见中古时期明确记录疫疠病名的主要医药文献。其卷二目录为“治卒霍乱诸急方、治伤寒时气温病方、治时气病起诸劳复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2]可见,《肘后方》是从方剂分类的角度将疫疠与伤寒、时气、温毒等病名互相区分与并称。
2.1 宋金元时期:疫疠从属伤寒病或时气病
至宋金元间,疫疠逐渐划入伤寒病或时气病中的一种病候。北宋敕修的《圣济总录》(1117年)最具代表性。其卷二十二伤寒门中,列“伤寒疫疠”。认为“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皆为疫疠之气,感而为病,故名疫疠。其状无问长少,率皆相似。俗又名天行,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治各随其证,以方制之。”[3]354文中还有“时行疫疠”“天行时疫”的称谓。并且时气病也划入伤寒病的范畴,称“伤寒时气”。认为“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是为四时正气。非其时,有其气,人或感之,病无少长,率相似者,谓之时气。如春时应温而或寒,夏时应热而或冷,以至当秋而热,当冬而温,皆是也。其候与伤寒、温病相类,但可汗可下之证,比伤寒、温病疗之宜轻尔。”[3]352文中还有“时行”的称谓。
这两处《圣济总录》对疫疠和时气病的总论,在继承《病源》的病候认识基础上,又有所变化,具体表现为三点:其一,在疾病目录上,“疫疠”病候不再成为与“伤寒”的并列项,而是成为“伤寒门”之子目,与“时气”并称。其二,“伤寒时气”中的“时行”与“伤寒疫疠”中的“时行疫疠”联系,也可认为“疫疠”有时指称“时气”之重候,如常伴有“壮热”。由此,“疫疠”又可成为“时气”之子目。其三,从《病源》强调“治有殊耳”到《圣济总录》的“各随其证,以方制之”,所选方剂多自《伤寒杂病论》,表示定性为“疫疠”的病候,证治却纳入伤寒病以“随证制方”。
同时期,《太平圣惠方》(992年)“每部以隋太医令巢元方《病源候论》冠其首而方药次之,成一百卷”[4],足见《病源》在宋代官方编撰医书中仍然占据重要参照地位。但是总的目录分类也只有“伤寒”和“热病”而无“疫疠”或“疫病”[5]。《太平惠民和剂局方》(1078年~1085年)总目录分类为“治伤寒附中暑”[6],亦似《太平圣惠方》。
金代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卷二《伤寒例第三》[7]中认为,“时行之气”是“四时气候不正之气”,其中“暴厉之气”为“时行疫气”,时气病(“时气所行为病”)较时行疫病轻浅(“非暴厉之气”)。
可见,宋以后“疫疠”开始不再与“伤寒”并称。“伤寒”意涵扩增,寒温统摄的同时,“疫疠”逐渐成为或可“伤寒”或可“时气”中以老幼皆感、症状相似为特征的一种外感重症,因而在治疗上“随证制方”,失去了“有是病用是方”的特征性。
2.2 明清时期:疫疠之中区分寒温
明末清初吴又可《温疫论》的问世,并没有撼动“疫疠”作为或伤寒、或温病的子目从属地位。虽然清代温病学逐渐兴盛,但温疫也并非全能代表疫疠。温病学中寒温之争的学术争论,影响到“疫疠”之中区分寒疫与温疫。如晚清陆懋修认为“疫有两种,曰温,曰寒;以其病为大小相同、长幼相似、如役使、如徭役,故古人谓之役,后人称为疫……不言疫中之寒者,且只言疫中之温者,不言不疫之温者,以其所遇崇祯辛巳之疫固是温疫,不是寒疫。”[8]此外,清人端午习俗中饮雄黄酒,亲友互赠佩戴白芷、丁香、佩兰、苍术、艾叶成分的香囊[9],也是辛温辟秽之法。
2.3 唐以后域外汉字文化圈的接受
宋元明清对疫疠病候病证分类的变化还影响至海外,被域外汉字文化圈所接受。
日本镰仓时代(1192年~1333年)的《覆载万安方》[10],卷六伤寒上有“伤寒时行疫疠论”,卷八伤寒下有“伤寒疫疠”。
朝鲜许浚的《东医宝鉴》(1613年)杂病篇卷之七“瘟疫”的“瘟疫之因”[11]中引《医方类聚》谈到“时气者,天地不正之气也。非其时而有其气,一家无少长率病者,时气也。又谓鬼厉之气,夫鬼无所归,乃为厉尔。若天地有不正之气,鬼厉依而为崇”,虽然指出“一家无少长率病”的不正之气为时气病,但其后又称“鬼厉依而为崇”,实为表达了疫疠病可以是时气病中“依而为崇”的鬼厉之气。
越南黎有卓《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1770年)中的《医中关键》“疫病”[12]条谈到“瘟疫乃天行时疫也”,治疗上“古方偏用苍术为辟邪之要”。不过该病“亦可依外感通治法”,“遇非时之戾气与饿荒之后,忧攘之时,岂不可变通而可得乎”。可知,同是将疫疠归入时气病范畴,治疗可依从外感病证治方法。
2.4 民国时期:西学影响下对古代疫疠的误读
民国时期,余云岫的《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以下简称《疏义》)是在西学东渐背景下疏义古代疾病名的经典著作,影响较大。当时,随着西医学传染病相关概念的传入与接受,“疫疠”逐渐成为一个历史术语,并且学界开始以“传染病”的思路和语汇分析历史上的疫病[13],以至于容易发生混淆与误读。
余云岫[14]159-160释“疫”:“疫,民皆病也。司马光《类篇》七上《疒部》‘疫’下注引《字林》云:‘病流行也’……《一切经音义》二十一《大乘十轮经》第一卷‘疫疠’下注云:‘人病相注曰疫疠’。《论衡》卷第二《命义篇》:‘温气疫疠,千户灭门。’皆与《说文》‘民皆病’之训合。严按:疫,今传染病也,微生物为之病原,古者多以为鬼神之崇。”
随后余云岫[14]160举本文前述成无己“时行疫气”的文献,认为“疫又谓之时气病,亦谓之天行病,而归罪于非其时而有之气”,并且援引《礼记·月令》“孟春之月,行秋令,则民大疫”等例文辅以证明。可是,是否气候反常并非“疫疠”的金标准,所以在理解中古《病源》“疫疠”病名时,不能认为其等同“时气病”。余云岫在这里的误读有二:一是对成无己的“时行疫气”的误读,将成氏病因学范畴的“疫气”等同“疫病”;二是对中古《病源》“时气病”与“疫疠”的误读,认为“非其时而有其气”的时气病就是“疫病”或“疫疠”,从而完成两者之间概念相同的逻辑论证。
余云岫将东汉、唐代和宋以后不同历史时期训诂材料进行书证的做法是予以赞赏的,但他却忽视了疫疠疾病名内涵的历史变迁,混用了不同语境和范畴中的同一语词。所以他在近代西学传入的客观大趋势和沟通中西古今疾病术语的主观愿望下,以当时传染病的疫疠病名含义去静态地观察和解读历史上出现的一切义项。
2.5 现当代时期:近代知识层累下的概念构建
现当代中医学专业辞书《中医大辞典》(1987年)“疫疠”[15]释义如下:(1)指具有强烈传染性,可造成一时一地流行的疾病。见《诸病源候论》卷十。又名瘟疫,时气。《医学入门》(1575年)卷四:“疫疾如有鬼疠相似,故曰疫疠,又曰时气。”参瘟疫、时气等条。(2)指湿温有强烈传染者。《六气感证要义·湿温》(1898年):“湿温一证,即藏疫疠在内,一人受之则为湿温,一方受之则为疫疠。”(3)指大头痛,溃裂脓出而又染他人者。《此事知难》(1308年)卷下:“大头痛者,虽为在身在上,热邪伏于己,又感天地四时非节,瘟疫之气所着,所以成此疾。至于溃烈脓出,而又染他人,所以谓之疫疠也。”参大头痛条。《中医大辞典》存在的问题有:释义(1)将“疫疠”与“瘟疫”“时气”简单划等号,其实不然:首先,据《病源》卷十的论述,“疫疠”是“疫”中之厉,不能划等号;其次,《医学入门》的成书时代,“疫疠”一词语义早已不同《病源》的时代。释义(2)(3)列举两项疫疠的后世流变,书证单一,所举并非主流,似有挂一漏万之嫌。
稍晚于《中医大辞典》的综合性辞书《汉语大词典》,将“疫疠”释义为“瘟疫”[16]287,“瘟疫”释义为“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总称”[16]337,与《中医大辞典》有渊源关系。然而用此义来释读不同历史时期的疾病名,难免偏颇。这两种代表性辞书的释义来源,抑或是对民国时期余云岫《疏义》中“疫”字释义的继承。
余云岫的疫疠病候疏义乃至现代权威辞书的跟风与混称,反映出近现代“疫疠”一词,早已失去了《病源》时代的病候类型划分,不再专病专治、专病专方,而是归入或伤寒、或温病之中,甚至成为瘟疫或传染病之同义词。
3 结语
甲骨卜辞中有关疫疠之疾,总以“疫”字统之[17],并未与瘟疫在医学专业术语层面上有严格区分。直至秦汉时期亦较为笼统,如《礼记·月令》云“(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18]等文献,在《病源》的视野下,可以认为“大疫”是“时气病”,说明秦汉时期疫病和时气病存在混称的现象。东汉末年以后,疫病频发,人民迫切需要救治的历史背景下,《病源》厘清汉以前瘟疫、疫疠、时气病等互相混称的局面,定义“疫疠”为疫病中之厉者,疾病分类上与伤寒、时气病、热病和温病等相并列,并指出了症候种类、鉴别诊断和证治思路。由于《病源》“业医者可以参考”[19],“被命与诸医共论众病所起之源”[20],影响广泛。故而《病源》的这一论述,是理解和还原中古时期其他历史文献资料和医学材料中“疫疠”一词最重要的参照系。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医学学术的变化,到了宋金元时期,疫疠逐渐划入伤寒病或时气病中的一种病候,在疾病分类上成为其子目,在治疗上“随证制方”,不再“有是病用是方”。这一学术变化同时影响至东亚、东南亚等域外汉字文化圈。明清时期温病学术的寒温之争,促成“疫疠”之中区分寒疫与温疫,但仍然作为或伤寒、或温病的子目,并一直影响至今。导致近现代不少学者和专业辞书在知识层累中形成了早已偏离《病源》“疫疠”含义的当下固有认知。并以当下认知作为参照系,静止地回溯、解析和评判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因而出现了矛盾与误读的问题。这一学术研究状况值得我们今人反思。
“以今论古”来理解疾病语词的历史含义而造成误读的现象,其原因在于研究者忽视了疾病学术与书籍目录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随着疾病临床诊疗实践的学术流变,疾病名的内涵发生变迁;疾病的医学认知变化,最终体现在专业文献中疾病分类的不同布局。另一方面,医学文献中疾病名不同时代的分类变化,又影响着相关学科学术走向。所以提示今人在释读古代医籍疾病语词时,应当注意与之相关的学术流变,观照疾病语词内涵的历史流动性,以期最大限度减少误读,更加准确地界定和使用古代医学文献中的疾病术语,从而更为客观地还原时情时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