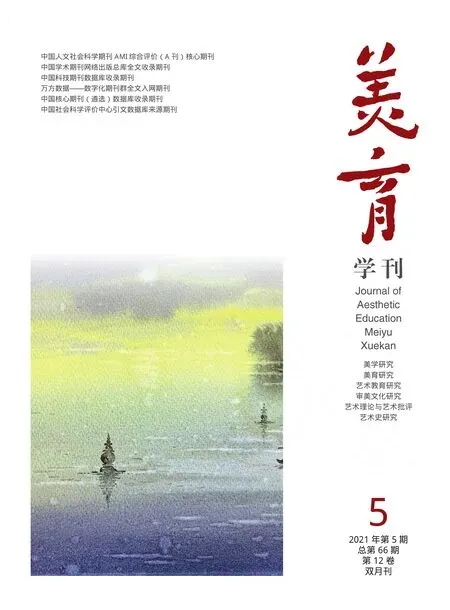“哑行者”的声音:蒋彝与中国艺术在英国
冯 晗
(陕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蒋彝(Chiang Yee,1903—1977),中国作家兼画家,江西九江人,字仲雅,笔名“哑行者”(Silent Traveller)。1933年,在经历了官场“现形记”后,而立之年的蒋彝辞去官职,跨洋西行,从上海乘船经马赛,抵达伦敦,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了22年。
20世纪初的中国因各方势力角逐的政治斗争而四分五裂,动荡不安。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有志人士忧时济世,积极外求于西方经验,探索强国自救之路。在他们的观念里,西方意味着现代化,那是一个与古老而落后的中国完全不同的世界。1915年,接受过西方教育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掀起了思想领域的新文化运动。他们抨击封建礼教,呼吁社会变革,积极传播西方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从而引发了一场确立中国现代身份的强大运动。在他们的启发下,更多的中国人争取到赴欧洲、美国和日本学习的机会,希望“输世界文明于国内”,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其中一些人选择从西方视角学习政治、法律和科学,并将新思想带回中国,如蔡和森、徐特立、周恩来等;另一些人则志于学习西方艺术的精髓,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寻求路径,如徐悲鸿、林风眠、吴大羽等。
在“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下,蒋彝大学期间报考了国立东南大学的化学专业,毕业后历尽波折,成为一名政府官员。但是污浊的政治生态使蒋彝失去了信心,于是他决定到英国研修政治经济制度,梦想着归国后能致力于中国社会及经济的改革。初到伦敦,蒋彝便入学伦敦大学东方学院(1)即现在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跟随溥仪的外籍教师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学习。然而,得益于与英国文化精英的频繁接触以及自己深厚的传统文人积淀,蒋彝积极地参与到了中国民族艺术在英国的推介与传播之中,并在英国的文化艺术界大放异彩。从他在英国的活动轨迹中,我们大致可以窥探到20世纪上半叶英国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所发生的态度转变以及与中国在外交关系方面所发生的更为深刻的变化。
一、历史际遇
在马可·波罗于1271年到达中国之前,欧洲人对古老的中国就已经有了模糊的认识——“他们生产的丝绸品质最佳,他们用稻谷酿出美酒,他们用漆刷书写文字,把一个词的所有字母化为一个字”。[1]威尼斯人在忽必烈身边侍奉了17年之久,归国后,他将一个全面辉煌的神州(Cathay)(2)神州(Cathay),是中世纪时期对中国的称谓,因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使用而流行开来。进行了完整的记录,并让此后的欧洲人读了上百年——那是一个“安定、仁爱的民族”,一个花开遍野之地。
自17世纪以来,随着东印度公司贸易的拓展,来自中国的青花姜罐、搪瓷托盘以及真漆嵌板等器物成为英国人物质生活中熟悉的存在。到了18世纪,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品味令人日久生厌,英国人转向中国智慧寻求灵感。伦敦制作的中式图案的银器、齐彭代尔的中式家具以及类似布莱顿行宫中的中式房间,在欧洲大陆无人能与之媲美。此时在欧洲最为盛行的“如画园林”,可谓是英国对当时在欧洲流行的中国风(Chinoiserie)最为突出的贡献。小山、山石、瀑布、溪流、树林和建筑采用了一种无序的设计,曲径通幽、宛然曲折,使之可以从不同角度呈现赏心悦目的美景。伦敦的邱园宝塔、埃尔顿花园的喷泉宝塔以及阿尔斯福德的中式钓鱼台这些点缀其中的建筑要素,更是对古老中国遥想的实践转化。
1857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掠夺了大量文物,形成了今天英国大英博物馆中国收藏的基础。然而,直到19世纪后期,随着在中国开始的铁路建设让英国人挖掘出了以前并不被他们所知的陶器——随葬品,英国学者才开始把中国文物视为艺术品。而且在许多年里,它们一直局限于大英博物馆的民族志材料展览,或者作为英国豪宅的优雅家具和室内装饰的一部分[2],更不用说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国绘画,英国人对其完全处于陌生的状态。
无论是对于中国艺术的收藏还是中英关系而言,20世纪都是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本世纪,西方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了解以及对他们的哲学和艺术的理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取得了更大的进步。”[3]28此时英国学界开始了对中国艺术以瓷器为中心的学术讨论。但即使如此,中国艺术仍然只能引起英国人微弱的关注。的确,在英国人传统的集体意识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是一个建立于几个世纪之前的古老而浪漫的帝国。在20世纪早期,这种认识持续左右着人们对中国和中国艺术的普遍态度。尽管中国艺术的题材、形式和材料因其异国情调而受到赞赏,但英国人却很少能将其置于适当的文化背景下进行阐释。在20世纪,这些愿景也象征着中国的停滞、落后以及“差异性”,尤其是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英国对中国艺术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许多收藏家和研究人员被中国艺术的悠久传统和文化内涵所吸引,其中少数人精通中文,能够翻译有关中国艺术及有关其收藏史的原文,这就促成了对中国艺术品更为均衡的解读。1925年,《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Magazine)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艺术》(ChineseArt)的开创性专著,首次对中国艺术进行学术层面的考察,内容与当时英国对中国艺术的界定一致。[4]引言部分由英国艺术理论家和美学家罗杰·弗莱(Roger Fry)撰写,他描述了西方文化在试图理解和诠释中国艺术和文化时所面临的挑战。他在《中国艺术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Art”)一文的开篇写道:“我相信很多人可能熟悉欧洲艺术的某些方面,但他们仍然对中国艺术感到陌生。对他们来说,遇到这样一本书,就等于进入了一个他们没有钥匙的世界。”[3]1参与本书写作有博物馆的专业人士,比如曾是大英博物馆东方印刷和绘画部的负责人的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及其助手亚瑟·韦利(Arthur Waley),还有一些私人收藏家,如珀西瓦尔·大卫爵士(Sir Percival David)和乔治·尤摩福普洛斯(George Eumorfopoulos)。他们的研究专长包括中国画、雕塑、陶瓷和装饰艺术等。
在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艺术界,有关中国艺术最瞩目的事件当属1935年11月28日在伯灵顿宫(Burlington House)开幕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展览共展出3000余件书画、瓷器、玉器、雕刻以及青铜器,其中800多件是由中国政府借出的。正如驻英国大使郭泰祺在闭幕晚会上发表的演讲所称,“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公民的慷慨捐款和艰苦合作,使有关中国艺术成就的展览成为西方世界所见过的最明确、最全面的一个”。[5]时任英国皇家美术学院院长的威廉·卢埃林爵士(Sir William Llewellyn)也说,“不用说,这将是一场无比美丽和庄严的展览,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3)The China Press,May 5,1935.据展览总监珀西瓦尔·大卫爵士说,此次展览致力于:
展示世界上幸存的最古老的文明。文化本身在其悠久的传统中是如此的复杂、深奥和传奇,因此很难立刻获取一个简单的意义。然而其意味深长。它是我们周围的未知世界之灵,渗透于我们的物质世界。它微妙地隐藏在中国人祖先崇拜传统中,在他们平和的哲学中,在对自然和其作品的象征阐释中。
展览的范围比以往任何辉煌的展览更为广泛和雄心勃勃。我们努力把中国历史从其诞生至19世纪最优秀、最具代表性的工艺美术作品汇集在一起。[6]
此次展览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形态向西方大规模展示中国艺术品,而且是一次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悠久文化和艺术传统的机会。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伦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观看人数近50万人,销售10万余册的展览图录,有关展会的消息很快在国内外传播开来,一些西方学者在看完展之后甚至认为“中国的艺术比欧洲艺术更具内涵”。[7]能获得如此评价意味着英国公众认知和欣赏中国艺术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的到来,这也成为蒋彝在英国推介和传播中国艺术坚实的群众基石。
二、蒋彝在英的文化活动
在客居伦敦的这段时间,蒋彝通过因改译《王宝钏》而在英国获得成功的熊式一(4)熊式一(1902—1991),江西南昌人,笔名熊适逸,以创作和翻译戏剧闻名。结交了许多在伦敦文化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与文化精英,其中包括沃克·温克沃斯、劳伦斯·比尼恩、赫伯特·里德、罗杰·弗莱和乔治·尤摩福普洛斯等人。蒋彝经常与他们一起参观展览、举办演讲并且就中国艺术的某些问题进行切磋与探讨。无疑,这些人对中国艺术及文化的态度与看法也影响着蒋彝在英国的生活轨迹。
(一)书写中国艺术
1935年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不但给英国大众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艺术的舞台,各大出版商也纷纷借此机会出版了有关中国艺术的著作。在伯灵顿宫的展览之前,几乎所有关于中国艺术的英文著作都出自西方作家之手,而中国本土专家少有参与。因此,当英国麦勋书局(Methuen)的经理艾伦·华特期望出版一本由中国作家书写的介绍中国艺术的新书时,熊式一毫不犹豫地举荐了自己的好友蒋彝。
1935年11月21日,一本题为《中国之眼:一种对中国艺术的阐释》(TheChineseEye:AnInterpretationofChineseArt)的书正式出版了,熊式一在序言中写道:
现有的关于中国艺术的书籍,全都是西方评论家所写,他们的概念,尽管有价值,但其所作的解释必然与中国艺术家完全不同。我想你们一定会同意,这些中国艺术家,真可惜,应当有他们的发言权。此书作者对绘画的历史、原则、哲学的处理,深入浅出,读者既获益无穷,又其乐融融。[8]ix
《中国之眼》是蒋彝撰写的第一本书。全文共分8章,共计230页,配以24幅中国绘画名作的黑白图片。全书开篇是对中国画进行的简要历史勾勒,之后的章节分别阐述了绘画与哲学、诗歌的关系,中国画的题跋、题材、核心、工具以及种类。其中在有关绘画与哲学、绘画与诗歌的章节中作者着墨最多,由此也可见此部分的重要性。《中国之眼》在为对其完全不了解的西方观众揭开中国艺术作为实践和研究对象的神秘面纱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英国公众而言中国画“是由一个离欧洲如此遥远的民族创作的,同时很容易欣赏到其表面所具有的装饰性,如果不了解中国的绘画观念,不了解中国画家对题材的处理方法,不了解其艺术背后的精神背景,我们就无法理解它”[9]。所以对中国绘画作出正确理解是基于对其深根于内的文化脉络的把握。蒋彝的这本书不仅为读者介绍了中国画的基本原理,并为如何欣赏中国画提供了明确的文化背景。然而它并不是对中国绘画的学术研究,而是基于一位中国艺术家的个人经验和视角,提供了一种如何更容易理解中国画的方法。
《中国之眼》一经出版便受到了公众和学术界的一致好评。英国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Hebert Read)认为蒋彝“清晰地剖析中国的艺术观,使我们能真正了解这门艺术,进而欣赏其本质”[10]xvii。劳伦斯·比尼恩也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道:“这本书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讲了很多内容,于所有对中国画感兴趣,想了解其本质的人而言,它将是一本入门读物。”[11]《泰晤士文学副刊》(TimesLiteratureSupplement)也发表评论说:“作为一位撰写中国艺术著作的作者,蒋彝的优势是他能够从画家的角度来理解西方的艺术,这使他能够选用恰当的例子来突出中西方绘画的差异……蒋彝历史性的概述富有价值,因为它从文化内部告诉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受到哲学、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的影响,而绘画也不例外。”(5)Times Literature Supplement,November 23,1935.
《中国之眼》之所以畅销英国市场得益于蒋彝本人作为中国艺术家所带来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并且更懂得西方读者的特点和需求。他在“讨论中国艺术和解释中国绘画的哲学、文学、美学的内质时,没有太多的学术术语,通俗易懂,引人入胜”。[12]97比如,蒋彝会用咖啡和茶的差异类比西方艺术与中国艺术,生动活泼,晓畅达意。《中国之眼》是第一本由中国作家用英文写的关于中国画的重要出版物,这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能够不经西方作家的调解,直接向西方读者传输关于中国文化的信息和思想的时代的滥觞。
1938年3月,蒋彝写了另一本关于中国艺术的著作《中国书法——美学与技艺方面的介绍》(ChineseCalligraphy—AnIntroductiontoAestheticandTechnique)。在第三版的序言中作者自述道:“在我的第一本著作《中国之眼:一种对中国艺术的阐释》取得巨大成功后,我认为我应该著述介绍中国书法的美学原则的技巧,中国绘画的主干也是由同样的美学原则和技巧构成的。”[13]19书法是中国最为普及的传统艺术,也被视为东方艺术的核心。但是在西方,大多数人对这个题目产生了畏惧。这是由于中国书法起源于古文字,他们认为只有懂得中国的语言文字,才能窥其堂奥。因此,有关中国书法的英文著作寥若晨星。(6)Lucy Driscoll和Kenji Toda曾在193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书法》(Chinese Calligraphy)的著作。林语堂在《天下月刊》中说:“作者基于对4世纪至15世纪中国古代艺术批评典籍的收集,以极其小心和审慎的态度,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心理和美学正确地理解。”参见王京芳:《中国美术研究英文论著的出版(1935—1937):以〈天下〉书评栏目为例》,载《国际汉学》,2013年第1期。而蒋彝的《中国书法》便成为了英语世界专门介绍中国书法艺术和技法的开山之作,本书的写作目的之一便是“希望帮助这些人不需学习中文就能欣赏书法”。[13]2
《中国书法》由11个章节构成。叙述伊始,蒋彝将汉语、汉字与英语做了简单比较,希望首先打破西方人对汉语及汉字学习的心理障碍。随后是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构成以及各种书法风格的论述,之后作者用4个章节的内容阐述了书法的实用技术和写作艺术。最后3章分别讨论了书法的美学原则及其与绘画、文学等艺术形式的关系。为了生动形象,书中配有22幅插图及157幅说明附图,都是蒋彝自己以及中国传统书法名家如王羲之、苏东坡、董其昌等人的作品。在论述的过程中,蒋彝并没有选择使用晦涩难懂的书法专业术语,而是选择较为浅显的白话将中国书法的基本问题向西方读者进行了解释。如此处理允许那些不懂中文的人了解和欣赏中国书法的雅致之美以及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这本书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几次再版,一些书评人在读过之后论道:“这本书既有教育意义,又令人愉悦,无论怎样的赞扬都不为过。这本书特别推荐给所有热爱中国艺术的人。”[14]
因为撰写了《中国之眼》《中国书法》以及一系列介绍中国文化与艺术的著作,蒋彝被西方学界公认为中国文化的权威。他带给英国人的“不仅是有关中国艺术和文化的知识,甚至是有关于整个艺术和文化的知识。他是属于为数不多的帮助西方人了解自己的外国人中的一个”。[13]13这些著作帮助公众拓展了视野,使对中国绘画、书法的欣赏和理解跨越国界,超越了原有的艺术界限,为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开辟了全新的途径。
(二)展示中国艺术
除了撰写有关中国艺术的专业著作,蒋彝也是英国各种艺术展览的积极参与者。初到伦敦之时,一个名为“人树总会”(Men of the Trees)的协会要举办一场画树的展览,受中国大使馆的委托,蒋彝提交了《黄州翠竹》《西湖堤柳》和《庐山古松》三幅作品,并成为参展的唯一一位中国画家。
在当时的欧洲,展览不仅是各国向西方观众展示本国艺术与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各国进行文化较量的博弈场。当刘海粟与徐悲鸿结束了欧洲留学归国之后就一直致力于向西方推广中国现代艺术家的作品。刘海粟在1929年以公派的身份赴欧考察时,便致函时任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提议在巴黎举办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以宣传中国文化。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当时的欧洲,日本积极通过展览宣传以浮世绘为代表的本国艺术,因此欧洲艺术公众对于现代东方艺术的认知,“只知有日本,而不知有中国”。[15]这一现象也使刘海粟深感在巴黎展览中国现代绘画的急迫性。徐悲鸿也曾说,“穷思吾国在国家间声誉日落,苟无文化宣传,外人观念,日以谬讹,而文化宣传之吸引力,以美术为最宏,与人印象亦较深切”[16]。
1933年5月由徐悲鸿担任策展人的中国美术展览会在巴黎国立外国当代美术博物院举办,展出了包括唐一禾、秦宣夫、吕斯百等人在内的中国绘画作品,并在巴黎引起了强烈反响,“凡开四十五天,入门统计凡二万余人”[16]。这次展览不仅是对中国画家在法国学习成果的检验,同时也是向西方展示中国艺术新面貌与新精神的机会。随后在1934年1月,刘海粟牵头的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Exhibition of Modern Chinese Painting)在德国柏林普鲁士美术院举行,蔡元培、叶恭绰、陈树人、朱家骅和驻德公使等人出席了开幕式。这次展览参观人数达14万,共售出作品53幅。随后又在汉堡、杜塞尔多夫、阿姆斯特丹等地各处巡展。这些展览不仅对确认中国艺术的连续性及其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表明了中国是一个拥有繁荣文化的现代国家。
1935年2月,刘海粟带着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来到了伦敦的伯灵顿宫。21日,展览正式开幕,出席的嘉宾有英国教育部长、伦敦市长、东方学院院长、熊式一、蒋彝等,展出作品230余幅。英国教育部长赫利法克勋爵在开幕词中说:“中国的古美术早已蜚声欧洲,一般恒以中国古代灿烂美妙之艺术,至今已成绝响,岂知看了此次刘海粟教授之作品及其所搜集之现代名作,其气派之雄厚,神味之深长,确是最高雅的艺术。”受刘海粟的邀请,蒋彝也提交了10幅小尺寸的作品,其作品在风格和题材上都源自中国传统,使用中国材料和技法来完成,这也是蒋彝的作品与其他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一起正式展出的为数不多的场合之一。此次展览期间还在伦敦中华协会举办了3次演讲,分别是劳伦斯·比尼恩的《中国近代画》、刘海粟的《中国画与六法》以及蒋彝的《中国文学与绘画》。此次活动让蒋彝意识到,凭借自己的书画功底和中国文化的背景,他有能力向西方介绍真实的中国。
1936年1月20日至2月5日,蒋彝在伦敦骑士桥的贝蒂·乔尔夫人画廊(Mrs Betty Joel Gallery)举办了个人首次海外展“现代中国绘画扇面展览”。英国艺术理论家休·戈登·波蒂厄斯(Hugh Gordon Porteus)观看完展览后在《新英格兰周报》(TheNewEnglandWeekly)上发表长篇评论,称蒋彝为“最杰出的当代中国画家之一”。(7)The New England Weekly,January 30,1936.W.W.温特沃斯在一篇介绍中写道:
在蒋先生的其他作品中,既没有亦步亦趋、拘泥于古风,也没有把欧洲传统运用到中国技法中的痕迹。在自己所有的作品中,蒋先生保持了传统中国画家的本色;在自己所有的作品中,他也保留了自己的特色。(8)W.W.Winkworth, “A Note on Mr.Chiang’s Work,” in James Cahill Papers, Freer Gallery of Art archives.
1939年,兹维默艺术馆(Zwemmer Gallery)举办了蒋彝的画展,作品大多是他的几部旅行游记的插图原作,有评论者说蒋彝的作品中“有一种人性的内质,一种真实的友谊似的生命,贯穿于无生命以及有生命的自然之中。中国画的这个最伟大的特点被运用到外国的背景,使我们原以为死亡枯萎的内容获得了生命,原以为苟延残喘的内容变得生机勃勃”。[12]157英国的玛丽王后(9)玛丽王后:英国王后,乔治五世(在位1901—1936)之妻。于5月2日光临兹维默艺术馆,蒋彝陪同参观了20分钟,并与其讨论了中国和西方绘画艺术的风格特点。王后的参观,无疑成为媒体头条,报纸纷纷刊文报道,一时风光无两。
随着国内抗日战争形式逐渐严峻,蒋彝和一些在外的华人心系祖国,希望通过展览募捐一些物资和资金以支援中国。中国青铜器、瓷器以及当代艺术家的画作出现在了爱丁堡、伯明翰等地。展览的策划者期望通过一件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将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展现给西方人。正如中国外交官顾维钧在出席格拉斯哥的中国艺术展览开幕式时所说,此次艺术展旨在提高对中国艺术的欣赏,更重要的是,以此进一步增进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理解。这场在特殊情况下举办的展览显得别有深意。
在蒋彝到达英国之际,英国公众对中国传统绘画还相对生疏。正如苏利文所言:“对于中国艺术所知甚少的西方人,欣赏中国绘画最初往往只能直观地对它所具有的美产生反应,距离真正把握中国艺术的真谛尚有很远,相当一部分西方人永远不能达到理解中国艺术的程度。”[17]2通过自己的画笔,蒋彝及中国的现代画家们将中国艺术最为精髓的部分展现给了西方观众,使原本对中国绘画处于完全陌生,乃至持排斥态度的英国公众逐渐接受、熟悉并且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东方的“他者”。从此,英国公众摆脱了以往认为只有瓷器可以作为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代表的惯性认识,对中国艺术开始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三)转译中国艺术
蒋彝的父亲是位肖像画家。12岁起,蒋彝正式跟随父亲学习中国画的基本笔墨技法。在他短暂的从政生涯里,蒋彝建立了一种以传统文人官员为基调的个人形象和生活方式。虽然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政府事务上,但是在闲暇之余也致力于绘画、诗歌和书法等艺术的创作与研究。1937至1940年间,蒋彝以“哑行者”(Silent Traveller)为名发表了一系列游记。
蒋彝原字“仲雅”,1935年起开始使用“重哑”。“他经常在信件、绘画、写作中使用,有时还索性略去‘重’字,仅仅前一个‘哑’字”。[17]104蒋彝原本就“喜欢保持缄默,当不得不开口说话时,舌头就会打结发痛”[10]xxii,到了英国之后又由于不懂英语,所以完全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重哑”也是蒋彝在英生活状态的一种描述。
1937年秋,《哑行者:中国画家在湖区》(TheSilentTraveller:AChineseArtistInLakeland,以下简称《湖区画记》)由乡村生活出版社正式刊发。这本游记总共5章,记录了蒋彝1936年在湖区为期两周的旅行,这也是画家“英格兰时光中最欢怡的片刻”。[10]27风光秀美、景色旖旎的湖区地处英国西北部的坎布里亚郡,地形以湖泊与群山为主。在蒋彝之前,“康斯坦布尔、透纳、克罗姆、格廷、科特曼与其他许多该流派的艺术家,已刻画出该地山水、原野及村庄的神髓”。同时,英国的浪漫派诗人“莎士比亚、汤姆逊、格雷、科林斯、华兹华斯、济慈与丁尼生等,开创了独特的山水诗,所有微妙的感觉与形式,都难逃他们与生俱来的洞察力,那是如此真切,直指内心”。[10]xvii蒋彝从这些英国文化精英身上看到了和中国传统文人之间的相似之处——对自然美景的热爱,一种超越了文化界限的共通感。
这部游记的中国韵味体现在蒋彝对英国风景的描绘是用中国传统材料——墨汁、毛笔和颜料以及中国画的创作原则完成的。每一章都是对湖区不同湖泊的记录。画家通过描述性的叙述和13幅单色插图相结合的方式,运用笔墨的轻重、缓急、枯湿,表现出明暗、质地、距离,传达了他所到之处独特的风土人情。他并没有“打算把英国场景变成中国场景”,而是“用我的中国毛笔、墨水和颜色”,以及“中国的方式”来诠释湖区的景致。[18]赫伯特·里德称蒋彝是“山水画艺术大师”,他的艺术作品是“……传统国画的现代诠释”。[10]xvii蒋彝证实了中国艺术“不受地理空间所束缚,那是全人类共同的,可表现中国山水,也可全是你们英国的景致”。[10]xvii这源于画家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重现事物的外观,而是抓住其基本形式和内在精神,给予自由表现,不受任何抽象理念的干扰。他认为:“画家的目的是要传达一种气氛,一种诗意的真实……无论我们是画一朵兰花、一只山雀还是长江三峡的崎岖峭壁,我们总要有一些诗意的信息要传达。只要我们能把这梦中的景观转移到旁观者的心里,我们就不在乎逼真了……”[8]104
随着《湖区画记》取得的商业成功,蒋彝又在乡村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哑行者在伦敦》(TheSilentTravellerinLondon,简称《伦敦画记》)。伦敦是蒋彝认识的第一个英国城市,他曾在此生活七年之久。这本画记可谓是蒋彝在英国生活的最亲密的写照之一。它不仅提供了对这个城市的详细描述,而且还展现了作者在那里丰富多彩社交生活。这本书从内容上分为两部分:作者首先带领读者在伦敦漫步,探索四季中伦敦的独特景色,着重景色的捕捉;第二部分考察伦敦的社会生活,如博物馆、画廊、聚会等,致力于文化层面叙述,行文自由洒脱、无拘无束。不同于《湖区画记》采取了旅行日记的形式,有明确的时间和旅行的感觉,蒋彝对“伦敦生活”这个主题的阐释采取了一种更为独特的方式。它的特点是对各种各样看似琐碎的话题进行思考,比如天气、茶点、儿童、书籍和戏剧。蒋彝都很乐意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生活的细节上,将个体的生存经验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他写道:“我不敢盯着大东西看,我通常会向下看小的。有许多微小的事情,它给了我很大的乐趣去看,去观察,去思考。”[19]x-xi。《伦敦画记》获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与艺术有关,其中共有18幅插画,2幅为彩色,其余均为单色,并以正、行、隶、篆不同字体将每首诗抄录在每章的末尾。
伴随着《湖区画记》《伦敦画记》引起的强烈反响,蒋彝又先后出版了《战时小记》《北英画记》《爱丁堡画记》《牛津画记》等作品。在“哑行者”系列游记中作者想要表达的并不是中国艺术与英国艺术的差距,而是二者之间的“共通性”。于蒋彝而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英国“所有真实的感觉与思维都是相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两种永恒的关系,天地恒在人恒在。会变的是人类表述与感知这层关系本质的能力”。[10]xviii这一系列游记的吸引力之一在于其不常见的富有“异国情调”的审美气质,一种新奇的“东方化”的英国景观,蒋彝以一种轻松迷人的笔触,尝试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捕捉了自己沉醉于一种对新文化的体验之中。其次,我们不应该忘记“哑行者”游记出自“一个思乡的东方人”[10]27。它们表面上是英国自然风情的描绘,但在叙述中却交织着对中国的指涉。画记中对中国文化、历史和传统的反思,为作者提供了一个与过去的中国重新建立联系的机会,也抒发了蒋彝的思乡之意。
三、文化态度的转向
作为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代表,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从文化霸权出发,揭示了“看似超然、与政治无关的文化原则实际上依赖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殖民主义运动这一卑劣历史”[20]41,并且“以一种复杂的形式成为帝国主义事业的一部分”[20]186。在20世纪初的英国,随着政治、经济、外交地位上的领先,英国人对中国的理解总带有文化上的偏见。比如为迎合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许多去中国仅仅几个月的旅行者回来后会写关于中国的书,包括从文学、哲学到家庭、社会生活和经济状况”[19]x。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图书馆所藏书籍中充斥着外交官或传教士对中国的负面描写,他们将中国人塑造成乞丐、苦力、鸦片鬼等形象,这些负面的刻板印象在傅满洲(Fu Manchu)(10)傅满洲(Fu Manchu),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中的反派人物,西方人眼中“黄祸”(Yellow Peril)的拟人化。身上得到了想象的投射。此种民族心理上和文化理念上的扞格给蒋彝的内心留下了深深的刺痛。更不必说与欧洲绘画分属不同体系的中国绘画,长久以来都被带有偏见的眼光进行审视。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在其《艺术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ofArt)中宣称:“只有欧洲有纯粹而又珍贵的古代艺术,亚洲和非洲都没有”[21];塞尚在评价高更的画作时也说“高更不是画家,他只搞了些中国玩艺儿。只用一根黑线来包括轮廓,并认为“这是应该用一切力量来避免的缺点”。[22]
在给自己的好友英尼斯(Innes Jackson)的信札中蒋彝提到自己“一辈子坚持不懈写作绘画的决心”,志于成为“真正把祖国的艺术美展现给世界的独一无二的中国人”。[23]在自己社会性文化实践活动中,蒋彝采取了一种反传统的手法,他“旨在刻画人与人之间的相似之处,而不是彼此之间的差异,或搜奇抉怪”。正如在谈到中国绘画中的线条时,他说西方人“对于波蒂切利的绘画名作《春》想必不会感到陌生,画中描摹人物华美服饰所采用的精致、流畅的线条与中国画家典型的线条处理手法颇为相似”[8]179。蒋彝的这种行文策略在《中国之眼》的引言中也已阐明:“关于美和艺术价值,任何世界上两个民族或地区都不会有差别,显然的区别在于技巧和手法。艺术对心灵说话,呼唤人类的灵魂,中国的绘画名著受到西方人的赞赏就如同西方的名画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一样。期望将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把中国客观地介绍给西方,以此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8]3
帝国主义时期,西方中心论的思想主宰着西方文化界。许多人深感于西方文化是最优越的,包含最合理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最应普及于全世界。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建制,其实质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压制,一种文化霸权行为。法国比较文学家洛里哀(Frederic Loliee)曾公开作出结论说,“西方之智识上、道德上及实业上的势力已遍及全世界。东部亚细亚除少数山僻的区域外,业已无不开放。即使那极端守旧的地方也已渐渐容纳欧洲的风气……从此民族间的差别将渐被铲除,文化将继续它的进程,而地方特色将归消灭”。[24]“但是,若要使西方各国与中国的交流产生良好的结果”,西方人“就不应该自命为高等文化的使者;更不应该视中国人为劣等民族,而自以为有剥削、压迫和欺骗他们的权利”。[25]2美国哲学家菲尔莫·诺斯洛普(F.S.C.Northrop)在1946年出版的《东西方的相遇:关于世界理解的探讨》(MeetingofEastandWest:AnInquiryConcerningWorldUnderstanding)一书中认为当前世界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冲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东西方的相遇”。但问题解决的办法在于对不同意识形态的了解、调整与妥协。东西方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非此即彼的,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原因在于它们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个主题的观照:“一方……需要另一方。”[26]也就是说,对于东方文化实践和思想的审视应该借用东方的角度,而不能囿于西方的理论框架和文化观念中。
因此,当19世纪建立的帝国主义框架在20世纪开始逐渐被更严谨的学术研究和对中国及其文化的介绍所瓦解时,英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蒋彝以及一些中英知识分子通力合作,以展览、演讲、学术著作等方式身体力行地向英国人介绍中国艺术,英国人逐渐地开始怀着欣赏的态度审视中国艺术,合理对待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正是文化差异的存在才允许文化之间进行交流与互鉴,才能诱发人们的灵感和创造性而导致个性。英国哲学家罗素(William Russell)曾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25]146于是异质、异源的东西艺术也开始进行互识、互证和互补。而作为文化表征的绘画又是涉及人类的感情和心灵,较少功利打算,而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较多的共同层面,最容易相互沟通和理解。
正是在艺术这一拥有更多文化共同性的场域中,蒋彝通过自己一系列的社会性实践活动实现了中西艺术之间跨国家、跨文化、跨民族的平等对话。无论是他撰写的有关中国艺术和文化的书籍、所发表的演讲,还是自己的旅行日记,都对这个西方当时几乎无人了解的主题提供了非常必要的解读与阐释。这也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发轫——中国人第一次能够直接向西方观众展示自己的文化,从此评说中国文化,不再是西方作者独享的权利,中国人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