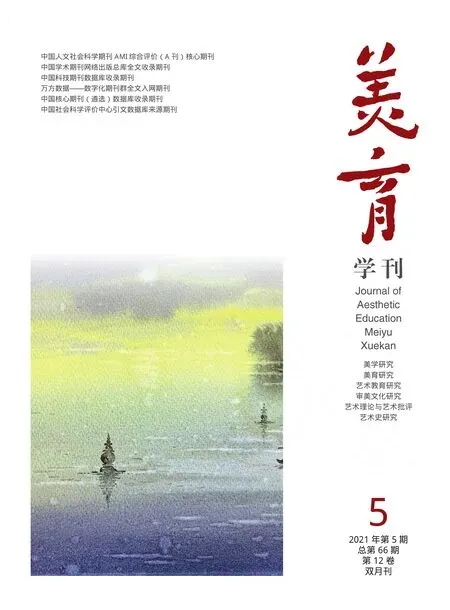“生生的节奏”:中国现代艺术形上学的典范形态
冯学勤
(杭州师范大学 艺术教育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21)
20世纪20年代末,宗白华对中西形上学的比较式研究,奠定了中国艺术形上学的哲学基点。这个基点,即“神化的宇宙”及其所象征着的大全图景:“道与人生不离,以全整之人生及人格情趣体‘道’。《易》云:‘圣人以神道设教’,其‘神道’即‘形上学’上之最高原理,并非人格化、偶像化、迷信化之神。其神非如希腊哲学所欲克服、超脱之出发点,而为观天象、察地理时发现‘好万物而为言’之‘生生宇宙’之原理(结论!)中国哲学终结于‘神化的宇宙’,非如西洋之终结于‘理化的宇宙’,以及对‘纯理’之‘批判’为哲学之最高峰。”[1]此“神化的宇宙”,乃中国生命哲学的超越性之维,即指向一种艺术和审美意义上的形上学境界,而非宗教形上学的境界。因为这个境界只有以“乐”表之(1)“西洋科学的真理以数表之。(《乐记》云:‘百度得数而有常。’)中国生命哲学之真理惟以乐示之”,见宗白华:《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宗白华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89页。,亦即形式和生命相和谐的境界,表征着艺术形上学与生命形上学的一体性。“神化的宇宙”即“生生宇宙”,此“生生”二字最终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形上学的本体论之核;而“生生的节奏”,则构成中国现代艺术形而上学最为成熟、最具典范性的范畴。这一范畴,主要出现于宗白华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所作的文章当中,如《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1932)、《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1934)、《中西画法表现的空间意识》(1936)、《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1943)等,尤以《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最为重要。
一、中国画的“最深心灵”
宗白华对中国形上学的探索,为其深入到中国古典艺术形式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视点,构成了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他的关注重心,逐渐从20年代对西方哲学和艺术学的引介和感悟,转向了三四十年代主要对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发掘和探索上来。1932年发表的《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正是这样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这篇文献当中,宗白华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中国画的最深心灵”。文章开篇宗白华即指出,尽管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宇宙美”“人生美”和“艺术美”,但美学研究的总倾向以艺术美为出发点,甚至以艺术为唯一的对象。何以如此?“因为艺术的创造是人类有意识地实现他的美的理想。”[2]43宗白华称西方美学理论与其艺术“互为表里”,西方美学中的模仿论、形式论、和谐论等与西方艺术的起源——古希腊艺术紧密相连,而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艺术则给西方美学提供了诸如“生命表现”“情感流露”等命题;进而,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的特殊性问题,也被宗白华提了出来:
中国艺术的中心——绘画——则给与中国画学以“气韵生动”、“笔墨”、“虚实”、“阴阳明暗”等问题。将来的世界美学自当不拘于一时一地的艺术表现,而综合全世界古今的艺术理想,融合贯通,求美学上最普遍的原理而不轻忽各个性的特殊风格。因为美与美术的源泉是人类最深心灵与他的环境世界接触相感时的波动。各个美术有它特殊的宇宙观与人生情绪为最深基础。中国的艺术与美学理论也自有它伟大独立的精神意义。所以中国的画学对将来的世界美学自有它特殊重要的贡献。[2]43
宗白华提出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命题,他称中国艺术的中心是绘画,而由画论所产生的“气韵生动”“虚实”“阴阳明暗”等,同样为中国美学提供了重要的范畴。他进而指出中国画学和中国美学的更大意义,是为未来的世界美学提供特殊性样本。而各个民族和文化所产生的美学和美术,又与不同民族和文化独特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紧密相连。于是此前对中国形上学的揭示,在宗白华的思想发展中,就自然为其本土美术探索提供了超越性价值的支撑。宗白华进而设问:“中国画中表现的中国心灵究竟怎样?”他通过与“西洋精神”的差别来说明。在他笔下,古希腊的宇宙观是“圆满”“和谐”与“秩序井然”的宇宙,以“和谐”为美与艺术的标准;而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洋宇宙观则视宇宙为无限的空间与无限的运动,人生也是因这无限而产生无限的追求,哥特式建筑、伦勃朗的画和歌德的《浮士德》成为近代以来西洋艺术的典范,宗白华最后将之概括为“向着无尽的宇宙做无止境的奋勉”。在以此归纳西洋现代精神之后,宗白华提出此文的中心问题:“中国绘画里所表现的最深心灵究竟是什么?”[2]44
需要指出的是,宗白华这一问题本身,标志着一种本土现代艺术形上学构建产生了自我意识。何以如此?尽管中国绘画的“最深心灵”针对的是中国古典绘画和中国古典画论而发,然而宗白华将这个问题放在西洋“无限”与“无尽”的这一概括之后提出,显然将这种精神视作一种未能满足本土现代性需要的他者,从而这一问题本身的出发点正是本土现代性,而非与西洋同一的现代性。本土立足点本身就决定了这点。宗白华进而直接道出了问题的答案:
它既不是以世界为有限的圆满的现实而崇拜模仿,也不是向一无尽的世界作无尽的追求,烦闷苦恼,彷徨不安。它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它所启示的境界是静的,因为顺着自然弦则运行的宇宙是虽动而静的,与自然精神合一的人生也是虽动而静的。[2]44
宗白华的前两个否定中,第一个否定是古希腊的宇宙和艺术观,第二个否定是西方现代性那无所慰藉的观念,两个否定的结果是本土的天人合一观念,亦即现代以来被中国哲学、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学共同构建的形而上学顶峰。
需要注意的是宗氏对“静”之属性的界定,显然针对的是西方现代性那种无限追寻的永动色彩;然而其论证“静”之属性,又是与本土形上学的朴素辩证性紧密相关:“它所描写的对象,山川、人物、花鸟、虫鱼,都充满着生命的动——气韵生动。但因为自然是顺法则的(老、庄所谓‘道’),画家是默契自然的,所以画幅中潜存着一层深深的静寂。就是尺幅里的花鸟、虫鱼,也都像是沉落遗忘于宇宙悠渺的太空中,意境旷邈幽深。”[2]44尽管中国画所描绘的对象皆“气韵生动”,然而自然之道——所谓“法则”之存在却是一种永恒的静穆;而这种“动”与“静”的关系,又被立即转换为“虚无”“道”“自然”“天”这些表征永恒秩序的范畴与“动”的关系,“中国人感到这宇宙的深处是无形无色的虚空,而这虚空却是万物的源泉,万动的根本,生生不已的创造力。老、庄名之为‘道’、为‘自然’、为‘虚无’,儒家名之为‘天’。万象皆从空虚中来,向空虚中去。所以纸上的空白是中国画真正的画底”[2]45。于是,静与动的关系,就自然转换成有与无的关系,无被视为有的源泉与根本;进而,无与有的关系,又立即转换为留白之虚与对象之实的关系:“这无画处的空白正是老、庄宇宙观中的‘虚无’。它是万象的源泉、万动的根本。”[2]45
此处,我们看到作为超越性价值论的中国艺术形上学,构成了中国艺术最为核心的创造性原则,与中国画留白的形式特征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进而,宗白华又据此与西洋画法进行了比较:“西洋油画先用颜色全部涂采画底,然后在上面依据远近法或名透视法(perspective)幻现出目睹手可捉摸的真景。它的境界是世界中有限的具体的一域。中国画则在一片空白上随意布放几个人物,不知是人物在空间,还是空间因人物而显。人与空间,溶成一片,俱是无尽的气韵生动。我们觉得在这无边的世界里,只有这几个人,并不嫌其少。而这几个人在这空白的环境里,并不觉得没有世界。因为中国画底的空白在画的整个的意境上并不是真空,乃正是宇宙灵气往来,生命流动之处。”[2]45正因为“意境”不是“真空”,是对“宇宙灵气”和“生命流动”的表征,因此宗白华认为中国画的表现是最为“客观”和真正“写实”的。这种客观与写实并非如同西洋画那样从某一个体化的视角出发,对景物形成单一视角的透视,而是在天人合一之境中消泯主观视点,表现“客观的自然生命”,呈现“具体的全景”。据此,在宗白华看来,宋元山水画和花鸟画都是“最写实的作品,而同时是最空灵的精神表现,心灵与自然完全合一”[2]46。自然,“中国艺术”的“最深心灵”,也是中国人的“最深心灵”:
中国人不是像浮士德“追求”着“无限”,乃是在一丘一壑、一花一鸟中发现了无限,表现了无限,所以他的态度是悠然意远而又怡然自足的。他是超脱的,但又不是出世的。他的画是讲求空灵的,但又是极写实的。他以气韵生动为理想,但又要充满着静气。一言蔽之,他是最超越自然而又最切近自然,是世界最心灵化的艺术,而同时是自然的本身。[2]46
追求“无限”的浮士德表征着西方现代性精神,然而此种精神在宗白华看来并不能给必死的、有限的生命提供终极的慰藉——在西方宗教传统所提供的幻象被撕裂的情况下,这种“无限”的追求中隐藏着的是一种致力于摆脱虚无主义的强烈焦虑感,这种无法取消的焦虑感构成了西方现代艺术的根本动力。相反,所谓丘壑花鸟中发现和表现“无限”的中国人,及其所获得的“悠然意远而又怡然自足”的情感经验,皆来自自然,也即与道的“体合为一”;在宗白华看来,也正因这种“体合为一”,方能为必死之人提供来自本土传统智慧的终极慰藉。
二、澄观一心与腾绰万象:意境创造的形上学始基
“以气韵生动为理想”“又要充满着静气”“最超越自然而又最切近自然”,这种张力性的表述实际上指向了意境的动态生成。换言之,张力本身是对发生过程的描述,构成意境生成的动力,而非停留于静止的对立性结构。于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西形上学以及中国画艺术的阐释基础上,宗白华于20世纪40年代推出了其关于中国艺术形上学的经典之作——《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
该文首先引述龚自珍、方士庶、恽南田等人之言,直言意境为画家诗人“游心之所在”,即“独辟的灵境”“创造的意象”,构成“艺术创作的中心之中心”。进而他称:“什么是意境?唐代大画家张琳论画有两句话:‘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化和心源的凝合,成了一个有生命的结晶体,鸢飞鱼跃,剔透玲珑,这就是‘意境’,一切艺术的中心之中心。”[3]326意境作为造化和心源的“凝合”,也即二者的“合一”,“就是客观的自然景象和主观的生命情调的交融渗化”。[3]327需要指出的是,宗白华对意境那二元统一的结构性描述,令人想起梁启超对“趣味”发生机制的表述,即“趣味是由内受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的”[4]。而朱光潜对“美感经验”的界定亦相类似,即“所谓美感经验,其实不过是在聚精会神之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5]。此处,宗白华的“客观的自然景象”、梁启超的“外受的环境”以及朱光潜的“物的情趣”,构成外在自然的一元,而“主观的生命情调”“内受的情感”与“我的情趣”则构成审美主体的一元。这种二元论结构在中国现代美学中极为普遍,为“意境”“趣味”或“情趣”等美感—艺术经验范畴所统一。而这种统一的过程,即宗白华所说的,“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因而展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境象,为人类增加了丰富,替世界开辟了新景。恽南田所谓‘皆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这是我的所谓‘意境’”[3]327。换言之,在宗白华那里,意境为情景交融的产物。然而,正如朱光潜所谓“物的情趣”来自我的“移情”一样,情景关系的生成归根到底是审美主体的问题,此即宗白华所谓“意境是使客观景象作为我主观情思的注脚”[3]328。进而宗白华揭出一个“性灵”,来从审美主体角度进一步解释意境之诞生,“所谓意境的诞生,归根结底在人的性灵中”[3]329。
既然意境诞生于性灵,那么要创造艺术之意境,就必须涵养性灵。宗白华称:“这微妙的境地不是机械的学习和探试可以获得,而是在一切天机的培养,在活泼泼的天机飞跃而又凝神寂照的体验中突然涌现出来的。”[3]329性灵之微妙并非求知可得,而是一种体验的活动,所谓“天机的培养”说穿了正指向一种体验式的培养,即“凝神寂照”的体验,也正是宗白华前文所说的“充满了静气”的体验;凝神寂照即主体的一种意向性行为,这种意向性活动的对象即“天机飞跃”。需要指出的是,凝神寂照实际上正是中华心性文化传统中“主静”教义的又一个现代阐发,其先导正在梁启超从主静中提举之“主观”,也即为朱光潜等美学家所时常谈论的“静观”,与传统心性之学所不同的是这种体验方式已从道德修治之论域转向了审美体验,体验的对象正是“鸢飞鱼跃”或“天机飞跃”之盎然生意。宗白华在此文中以石涛、吴墨井、董源等人之言佐凝神寂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引米友仁之言:
宋画家米友仁自题其《云山得意图卷》云:“画之老境,于世海中一毛发事泊然无着染。每静室僧趺,忘怀万虑,与碧虚寥廓同其流。”[3]329
所谓“与世海中一毛发事泊然无着染”,即意境斩断世俗功利之羁绊,为纯然之审美境界,而所谓“静室僧趺”,指的是米友仁等画家常常采取静坐法,来获得意境体验,这种体验米友仁称为与天地万物同体之体验,亦即我们在前文中述及的心学静坐法中常见体验之一种,这种体验在宋明心性之学论域中则为道德形上学之体验,混杂了审美的因素在其中。[6]显然,即便在米友仁这儿,这种体验也已经演变为一种艺术或审美的形而上体验,这种演变自然发生,全因主静教义及静坐体验中本来就内涵审美因素于其中,而传统的道德形上学所指向的终极境界,本也是道德与审美一体圆融的境界。
这种主静体验,是获得意境体验、涵养性灵的根本方法。然而,有意思的是,宗白华在此基础上,又将另一种事实上并不相同的体验纳入主静体验之中。这种体验即酒神式的体验。他称:
元代大画家黄子久说:“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籥中坐,意态忽忽,人不测其为何。又每往泖中通海处看急流豪浪,虽风雨骤至,水怪悲诧而不顾。”[3]361
相比米友仁等,宗白华此处将黄子久式的体验称之为狄奥尼索斯式的酒神体验,尽管这种体验的类型是面对自然界巨大力量产生的迷醉体验,然而宗白华仍将之视为从静观出发所生的类型。然而,按照尼采晚期的观点,酒神与日神的体验并无二致,因为日神召梦作用事实上是由酒神之迷醉派生的,而且日神之静观本身只是迷醉的一种类型,即主要是与视觉经验和形象相关的迷醉[7]125,所谓米友仁的天人体验与黄子久的狂暴自然之体验,不过皆是酒神迷醉的不同类型而已。而且,宗白华将这两种体验视为涵养性灵的方法,也即意境创造的心理前提,并非指向一种体验内容上的混同。更值得注意的是,以酒神式的体验入静观之法,融西方理念于中国经验,这种阐释法本身将最终成就中国艺术意境论之最核心内容——“生生的节奏”与直接体会这种节奏的“舞蹈”,这也构成中国现代艺术形上学的最充分一个表征。总之,日神式的澄观一心与酒神式的腾绰万象所构成的理论张力,最终将向“生生的节奏”及其表征此节奏的艺术体验跃进。
三、“生生的节奏”与“生命舞姿”
中国现代艺术形上学的关键问题,实际上是“艺”与“道”的关系问题。“艺以载道”作为宋明心性之学乃至中国政治传统对待文艺问题的核心原则,往往割裂二者,艺术始终处在价值的低位上。从这个意义出发,中国现代艺术形上学作为为艺术树立起的超越性价值论,就必须克服这种割裂性的认识,将艺术从道德和政治功利主义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而又超然的价值地位。于是,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宗白华自然援引庖丁解牛这一典故,称:
“道”的生命和“艺”的生命,游刃于虚,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音乐的节奏是它们的本体。所以儒家哲学也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易》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这生生的节奏是中国艺术意境最后的源泉。[3]365
道的生命和艺的生命,看似两分,实则一体,此体即“音乐的节奏”;宗白华进而援引儒家礼乐思想,所谓与天地相参之“大礼”与“大乐”,来为音乐的节奏赋予价值内涵。早在《形上学》中,宗白华就已称中国形上学之道正是象本身,同时将生命与形式相结合,自然打通了时间性原则与空间性原则的通道。于是,“音乐的节奏”随即变成“生生的节奏”,也即生命的节奏。说“生生的节奏”是中国艺术意境的最后源泉,换言之,中国艺术意境的形而上根源,抑或中国艺术形上学本身,正是“生生的节奏”。至此处,中国艺术形上学的核心阐释,与中国形上学的基点相合。艺术作为形式创造的原则,与生命—道德价值的核心——“仁”的原则凝合为一。所谓“鸢飞鱼跃”“腾绰万象”,皆是生生的直接体现,也就是仁的原则的显现,所谓生生的节奏,也就是无论自然还是艺术,皆是生生之仁的直接表征,而这种表征是无法与原则相分离的。
需要指出的是,生生的节奏作为艺术形而上学、“节奏”作为艺术—形式原则与生命—体验原则的二位一体形式,可以构成一切艺术类型乃至艺术和审美之间的一般性原则。如音乐、绘画、诗歌、小说、电影等一切艺术类型,均可以此生生的节奏而求共性,也均可从生生的节奏获得形而上学的阐释。然而,在诸多艺术类型里,宗白华特别提举了舞蹈,认为这种艺术才真正能够最为充分地承载和表现“生生的节奏”。他论述道:
然而,尤其是“舞”,这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究竟状态,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艺术家在这时失落自己于造化的核心,沉冥入神,“穷元妙于意表,合神变乎天机”(唐代大批评家张彦远论画语)。“是有真宰,与之浮沉”(司空图《诗品》语),从深不可测的玄冥的体验中升化而出,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在这时只有“舞”,这最紧密的律法和最热烈的旋动,能使这深不可测的玄冥的境界具象化、肉身化。[3]366
在宗白华看来,舞蹈艺术是生命与形式结合最为紧密的艺术类型,是“生生之节奏”的直接呈现。而尼采的艺术形上学最适合的艺术表征也是舞蹈,而非其在《悲剧的诞生》中所奉上王座的音乐。在1888年的《偶像的黄昏》中,尼采称:“为了让音乐作为特殊艺术成为可能,人们停止了一批感官,尤其是肌肉的感觉功能(至少相对如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节奏都诉诸我们的肌肉)。于是,人不再立刻模仿和表现他感受到的一切。尽管如此,这其实是狄俄尼索斯的标准状态,无论如何是原初状态;以最相近之能力为代价,音乐是缓慢地形成的对同一状态的具体说明。”[7]126就尼采而言,音乐在某种意义上是叔本华的遗产,作为生命意志的直接表征;然而叔本华哲学本身对生命意志和生成本身皆持否定性的态度,于是对于自我批判之后的尼采而言,舞蹈是肯定性的生命意志,也是完全“以身体为准绳”亦即充分具身性的艺术形态。宗白华此处表现出了中西现代艺术形上学的某种一致性。
当然,本土性的要素还是被宗白华特别加以标示。“艺术家在这时失落自己于造化的核心,沉冥入神”,这意味着“澄观一心”这种本土的主静法,作为由舞蹈所表征的艺术创造—生命生成过程的一个技术前提,换言之,静观本身只是为了把握生生之节奏的通道,而非生生之节奏本身的展现。“舞”才是不可见之道以具身的形式直接展现出来,最终成为生生的节奏本身。这种联系,在尼采的艺术形上学那里并没有直接资源,而是来自中国传统艺术的融合与发展,具有典型的本土现代性特征。宗白华又引用杜甫之诗歌进行强化阐释:“诗人杜甫形容诗的最高境界说:‘精微穿溟滓,飞动摧霹雳。’(《夜听许十一诵诗爱丽有作》)前句是写沉冥中的探索,透进造化的精微的机缄,后句是指大气盘旋的创造,具象而成飞舞。深沉的静照是飞动的活力的源泉。反过来说,也只有活跃的具体的生命舞姿、音乐的韵律、艺术的形象,才能使静照中的‘道’具象化、肉身化。”[3]367在宗白华这里,静观与迷醉、沉思与表现、形式与生命之间最后形成了一种互生关系,二者相互肯定,共同奠定了本土现代艺术形上学的核心内容。不仅如此,宗白华认为,这不仅是中国艺术的核心,而且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
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3]367-368
中国艺术形上学,与中国形上学传统保持着一种异常紧密的关联,二者在对道的追求上是相通的。于是,中国现代艺术形上学,绝不只在审美和艺术的论域中被讨论,在中国哲学的现代阐释者那儿也以一种不同的话语形式言说。当哲学亦成为“生生的节奏”之时,体道之学即成艺之学;当“艺”通过“形式”而赋予“道”以“生命”之时,非道成肉身,而是肉身成道;而所谓“道”“给予”“艺”以“灵魂”,此“给予”实即冯友兰之“自同”。冯氏《新原人》曰:“儒家说:‘万物皆备于我。’大全是万物之全体,‘我’自同于大全,故‘万物皆备于我’。此等境界,我们谓之为同天。此等境界,是在功利境界中底人的事功所不能达,在道德境界中底人的尽伦尽职所不能得底。得到此等境界者,不但是与天地参,而且是与天地一。得到此等境界,是天地境界中底人的最高底造诣。亦可说,人惟得到此境界,方是真得到天地境界。知天事天乐天等,不过是得到此等境界的一种预备。”[8]冯氏道德形上学建构以“天地境界”为顶峰;而“天地境界”中的最高层级,乃“同天境界”,其所谓“同天”实为“自同”,本非道德理性之功,实为艺术形上学之能力。因此无论“自同”也好,“给予”也罢,“道”本为“艺”所造就之“灵魂”,以标示“艺”之不朽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