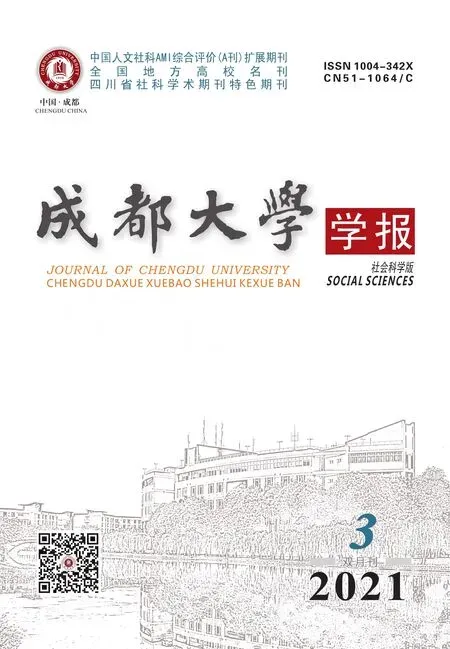旧体纪行诗和新型国际团结
——浅谈郭沫若20世纪60年代文化政治实践的一侧面
王 璞
(美国布兰代斯大学 德语、俄语和亚洲语言文学系,美国 马萨诸塞州 诸波士顿 MA02090)
一、一组问题的提出
1964年7月15日,郭沫若(1892-1978)“率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代表团”飞抵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河内,参加日内瓦协议签订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北越南访问期间,郭沫若屡屡成诗。其中,《穆穆篇》记述在主席府拜访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以“五言古”出之。在游览风景名胜区下龙湾时,“应船员索求”[1]2004,作《舟游下龙湾》,这是一首诗行整齐的押韵白话新诗。7月21日至23日,又连作八首近体七律,是为《下龙湾》组诗。7月24日结束访问回国后,访越诗篇相继发表(有些即兴之题则始终未正式发表),以上提到的几种后收入1977年出版的《沫若诗词选》。这样一批纪行诗,我们今天如何解读?在本文中,笔者想聚焦郭沫若晚年在反帝、反殖的国际交往活动和革命团结运动中所形成的纪行诗写作(尤其是其中的旧体因素),提出关于20世纪60年代文化政治实践的一组互相纠缠的问题。
首先,还是从研究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作品的难题性说起吧。笔者关于郭沫若著译的英文专著(2018年出版)曾试图贯通“新文学三十年”(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的郭沫若和晚期(包括“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郭沫若,但仍遇到些许困难[2]。本来,在中国革命及文化的进程中,这两个“三十年”的既矛盾又连环的关系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论阐发,形成了一个整体历史视野,不过在郭沫若这一贯穿性人物的个案上,新中国成立后作品的相关研究仍相对单薄。尤为关键的是,我们能否针对这一批富有争议性的文本,找到更有效的解读角度和方法?
众所周知,在上面提到的这两个“三十年”的历程中,不仅中国革命的文化态势始终处于激烈流动之中,而且郭沫若在其中的占位和身份也有多次转化。从20世纪40年代他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新文化的旗手”开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国文化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处的位置,他的实践活动的样态乃至性质,都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今天的舆论场中,却常有这样的声音,即把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的身份联想为“御用文人”,把他的大量诗词比附为“馆阁之体”,或者把他的官方角色形容为“文化屏风”。这样的说法未必能真正触及这批作品的历史性。另有学者——比如美国的文棣(Wendy Larson)教授则曾指出郭沫若在革命新政权内部所代理的“纪念性”文化功能[3]152。目前研究难点或许在于,如何从“应时”“应景”“应邀”的一面出发,进入文本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的文本构造。而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作为新中国文化界领袖的郭沫若的“纪念性”写作常以旧体诗词形式出之(一部分收入《沫若诗词选》等集,散佚作品也不在少数)。这种对旧体诗词的借重,至少可追溯到抗战时期国统区政治中的“声韵共同体”[4],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深深联系到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以及和毛泽东的诗词唱和,以至于成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的“民族形式”乃至象征性话语行动。正如拙著中所论及,郭沫若作为“开一代诗风”的白话新诗奠基人之一,后来成为旧体诗词“革命化”的高产作者,这一看似悖论的发展本身就表征了革命文化的复杂路径,更确立了一种社会主义文化人的特殊历史存在模式。所谓旧形式,反而意味着新的文化政治实践,我们还必须透过“内容的形式”探讨“形式的内容”[5]。在这里,新和旧,社会主义和诗教遗产,官方纪念功能和革命话语生产,政治身份和文人修养,高级文化交往和“喜闻乐见”的普及性,乃至于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等等,一系列问题已然彼此交织。
在拙著(及相关中文论文)中,笔者只以郭—毛唱和为线索,对郭沫若晚年旧体诗词写作略做梳理[2]271-296。此后,笔者也有意转向英文专著写作中“挂一漏万”、没有充分涉及的郭沫若作品,再做专题研究。出于对旅行书写的持续关注,笔者发表了讨论郭沫若1945年访苏日记的文章——《旅行书写与社会主义想象——以郭沫若〈苏联纪行〉为中心》[6]。一方面是革命时代的旅行文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文化政治,在这两个线索的交点上,郭沫若新中国成立后的纪行诗——尤其是旧体纪行诗——作为一个有待解读的现象就凸显出来了。本来,纪游诗在古今中外都是常见的文类,新文化中对异地、异国、异文化的文学处理也蔚为大观,但即便学界如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中的旧体诗问题进行了越来越多的讨论,晚期郭沫若的纪行诗仍是一个难以把握的对象。这不仅因为其中的新旧体并置(乃至杂糅),更是缘于它超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般意义生成和交流机制,而深度介入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交往——尤其是文化外交——乃至全球革命团结的政治建构。
自从1949年当选文联主席起,郭沫若长期以进步文化界领袖的形象出现,但如果细察,我们就会发觉,在“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坛激烈的斗争和接二连三的运动、辩论之中,这位领袖并非总是处于这一重要而敏感的场域的中心。相反,翻检《郭沫若年谱长编》便知,同一时期,郭沫若(先后)以中国科学院院长、国(政)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等身份,承担着丰富的国际交往任务,所从事的外交活动相当繁忙,这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尤其明显,简直是他工作的主要部分。他不仅参与了反帝、反殖的革命外交路线的展开和变动的全过程,而且更可以说,他所代表的文化外交形成了新中国国际交往的一大特色。反过来,脱离了这样一种新中国所力图形塑的国际革命政治,作为外交活动一部分的纪行诗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理解。
这也要求我们越出当代文学史的“国内”框架而更加重视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国际性。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文学也是深刻地参与到一种(远不同于今日全球想象的)“世界文化”的生产和构建之中。这其中不仅包括中国和苏联、东欧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多元交往,还包括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内部的泛左翼文学的译介和关注,而且突出体现于亚非拉的新兴文化政治交流,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反帝反殖运动所形成的“第三世界”的团结中,中国更扮演着极为重要但又变动乃至矛盾的角色。中国和亚非拉世界的文化外交,也产生了丰富的旅行书写,比如,艾青20世纪50年代访问拉美(为智利大诗人聂鲁达祝寿)留下的杰出新诗作品;而郭沫若的纪行诗则是其中又一例,却体现出旧体诗倾向。这些作品都需要从社会主义文化机制、革命地缘和国际团结等多重角度来解读和分析。此外,我们后面的梳理将表明,郭沫若外交实践和纪游写作见证了社会主义中国对反帝、反殖乃至于“反修”的国际政治的探寻,而且在60年代愈发转向“亚非团结”主题,标记出中国在“全球六十年代”中独特而能动的态势。所谓“全球60年代”,是近年来国际学界所常用的文化分期概念,强调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政治变革具有全球联动的特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在“断代”说中很早就点明,20世纪60年代的全球文化政治是以反帝、反殖的“第三世界”崛起为基本驱动的[7]。而越南战争就是这一全球联动的中心节点。郭沫若访越期间的诗作,在形式、内容和文化政治动向上都是一次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文化中的旧诗体、旅行书写中的新型国际团结、革命外交和“六十年代”的世界建构——这便是本文所要提出的一组问题和所要追求的视角转变。
二、外交纪行:从“国际精神”到“五洲震荡”
旅行意味着自我和远方远人的相遇,旅行书写是这一相遇的文本性“产出和记录”[8]10。1945年6月,郭沫若作为当时的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主任和中国进步文化的代表人物,受苏联科学院邀请,出访刚刚战胜纳粹德国而尚未对日宣战的苏联。他是在游苏期间,迎来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6]。回国后他发表了《苏联纪行》(1946年,再版改题为《苏联五十天》)。这可以说是郭沫若文化外交及其纪游文本实践的一段前史。新中国成立未久,毛主席经过艰难谈判,于1950年2月与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开启了外交上“一边倒”的阶段。而就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的次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告成立,郭沫若随即当选为其全国委员会主席。从那时起,他开始在中苏结盟的外交格局下全力参与维护世界和平、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国际运动(这一运动当时确定以苏联为主导)。1951年10月底,郭沫若率代表团经莫斯科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二届会议,11月2日担任会议执行主席。在维也纳时,曾作白话新诗《多谢》,而在归途中,和越南代表黎廷探博士同车,奉酬而作七律四首《西伯利亚车中》——“和平奔走幸同车,国际精神四海家”[9]62。这样的政治纪程可以说是郭沫若外交纪行诗的端倪。
同年底,郭沫若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在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所谓的“国际精神”,有两个重要维度。其一,郭沫若强调,中苏的联盟是世界和平的保障。毛泽东初次访苏并和斯大林会谈时,郭沫若颂之为“一个东方又加上一个东方”的“史无前例的大事”:
四万万七千余万同两万万,
全人类三分之一结成了联盟,
由两只最有力的慈祥的巨手,
紧握在欧亚大陆的中心。[9]12-13
到了1957年,他又这样书写中苏团结:“八亿人同甘共苦,/使和平压倒战魔”[9]182。
但如果说苏联是冷战意义上的“东方”,那么中国作为“东方”还代表着亚细亚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反抗殖民主义、追求民族解放的新兴力量。所以,和黎廷探同车穿过苏联,探讨朝鲜、越南革命形势,强调以斗争求和平,并酬唱成篇,这样的纪行场景本身就展示出一种亚洲团结的视野。这是“国际精神”所蕴含的另一维度,而且这一维度将越来越重要。郭沫若有诗作记述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于1952年在北京筹备和召开。而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在1955年的举行,又产生了以和平共处为原则的“万隆精神”(“种族反歧视,万隆又一章”[9]231)。万隆产生的亚非作家会议成为一个新平台。1958年初,郭沫若率团出席在埃及举行的亚非团结大会,同一年,茅盾率团参加了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这两个维度在50年代的交织决定了郭沫若当时的国际活动轨迹和纪行诗写作。一方面,在为中苏友好、世界和平奔走的过程中,郭沫若访问过苏联、中欧、东欧、北欧,留下了不少诗篇,如果说在政治抒情时还常用白话新诗体,那么游历即笔时,旧体诗的倾向越来越显著。1955年7月郭沫若在芬兰赫尔辛基主持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曾作五律《赫尔辛基》,记述在北欧千湖国度过了“约翰节”:“中夏逢佳节,和平发浩歌。”[10]661959年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顺访丹麦、苏联,郭沫若自称“八日三都”,在律诗《游北欧诗四首》中记述下泛舟海上与丹麦使馆人员畅谈蔡文姬的大好情致:“汽艇豪游海上驰,负暄畅话蔡文姬。”[10]57而这类旧体纪行作品中,最有名的或许还是《游里加湖》组诗。1954年5月,参加完在(东)柏林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之后,郭沫若于6月初访问莫斯科,由于6月下旬还要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会议,所以“接受苏联和平大会招待,往格鲁吉亚旅行”[1]1490。在格鲁吉亚避暑期间,郭沫若于12日游览里加湖。里加湖,通译“里察湖”,为格鲁吉亚境内高加索山脉群峰峡谷中的天然湖泊,“群峭削如壁,蓝池百米深”[10]69,为风景胜地,离黑海避暑地加格拉亦不远。里加湖“风景清奇”[1]1491,显然激发了郭沫若的游兴,给他留下了极美好印象,五绝组诗《游里加湖》先录入散文游记,共计二十首。其中第六首为:“爱山还爱海?山海皆爱之。山体森严律,海是自由诗。”[10]72从对高加索山和黑海的兼爱,论到对格律诗和自由诗的兼收,这其实和郭沫若早期“一元多体”的泛神论诗歌观一脉相承[11],也是对自己晚期新旧诗体并蓄的一种内嵌式说明,更重要的是,还流露出一种如山海般广阔的世界情怀。
另一方面,在反帝、反殖的世界新兴力量团结这一维度上,我们可以读到《游埃及杂吟十二首》中的亚非新谊:“兄弟亚非国,受灾历有年。求同情不异,反帝志弥坚。”[9]231在1957年底郭沫若参加在开罗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时,埃及纳赛尔政府刚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取得对英法老牌殖民主义大国的局部胜利,中国代表团不仅大受欢迎,还参加了塞得港的“胜利节”,夜游尼罗河,体验着“上下六千年”的古史和新变。《访问古巴》五首把外交视野从亚非引申到了拉丁美洲。在古巴革命和古巴导弹危机后访问这一加勒比海岛国,这是郭沫若一生中唯一一次西半球旅程:“景物新奇爱古巴,蔗田标穗似芦花。”[10]242新奇之中,他发现古巴松树河谷如同桂林风景——“阳朔风光照眼临”[10]242——并思考着帝国主义的历史。他见证了古巴和美国正式断交:“使馆高楼深锁定,女兵围裹抱冲锋。”[10]244又在归途飞渡大西洋,体验了“游仙”般的世界旅程:“朝别古巴含可可,夕临瑞士看《康康》。前人幻拟游仙梦,今日游仙事等常。”[10]244这是又一种世界感。
不过,也就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这两条原本合一的路线正发生剧烈的变化。中苏之间的分歧渐次浮现,1958年,郭沫若为中苏北京会谈公报欢呼,继续强调中苏友谊是世界和平的核心,但同时在纪念《莫斯科宣言》一周年时,却已经提出要警惕犹大式的“修正主义”[9]398。这是因为,中国所倡导的世界和平,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和平,是以反帝斗争为原则的和平,是以亚非拉革命为前提的和平:“亚洲人民站起来了!/非洲人民站起来了!/拉丁美洲人民站起来了!”[10]373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反帝斗争起着“连锁反应”,世界进入“五洲震荡风雷激”的60年代。60年代初的国际孤立中,毛泽东坚持中国独立自主,“天垮下来擎得起”,便是“沧海横流”时显出的“英雄本色”,而中苏论战则是“坚持原则”[10]119,“争正谊”“明真相”[12]16。郭沫若的任务随之转变,而有意思的是,在表达“反修正,斥新殖”[12]14这一对不可分割的主题时,他在60年代的诗作愈发倾向旧体。“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10]119——郭沫若的《一九六三元旦抒怀》引起毛泽东和诗,也正因为它标记出社会主义的中国走出了一个国内和国际的困难期,继续探寻革命新路。“天难挠,人难枉;帝难锁,修难谤”[12]30-31。反帝、反殖、反修合为一体,作为中国对亚非团结的新定义、新诉求,可以说是“全球六十年代”最富争议性的动向之一。在这样一个“五洲震荡”的“连锁”[10]373之上,越南显然是重要关节:第一,它是前殖民地反帝斗争的新中心,是最强大帝国主义美国倾力投入的新战场,是全世界进步力量瞩目所在,虽远却近;第二,它紧邻着新中国的南大门,战争并不遥远;第三,领导民族和人民解放事业的越南共产党和中苏都有良好关系。郭沫若外交活动和纪行写作从新中国成立到60年代初所形成的轨迹,为我们理解他60年代文化政治实践提供了富有纵深感的背景,也引导我们聚焦到1964年的访越作品上来。
三、访越作品和“全球六十年代”的革命团结
1964年,郭沫若已经72岁。这一年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不平凡的一年。新中国和西方大国法国建交,又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还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越南战争也在这一年全面升级。在肯尼迪遇刺后接任美国总统的约翰逊本已扩大美国对越战的参与,试图助南越军事独裁政府扼杀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而七八月间的东京湾事件,更是整个战争的分水岭之一,事态陡然升级,美国确定了直接介入、冒险豪赌的方针。到1965年初,美国已完成从“特种作战”到“地面作战”的转变和大部署,而在空中和海上,对北越的残暴地毯式轰炸也“滚雷”般开始,战火烧到中国边境和海疆。也是在1964年,全球范围内的反战运动和支援越南人民的行动已经兴起。越南问题构成了当时郭沫若外交活动的一个重大方面。
郭沫若率团访问越南,是在东京湾事件之前不久。《穆穆篇》这首五言古诗,记录了访问主席府、拜会胡志明的难忘经过。河内巴亭广场的主席府,是殖民地时代建筑,而富有平民精神和苦行品格的领袖胡志明,却拒绝住进这豪华的欧式宫廷,只以它作官方接待活动之用,自己安居在后花园的棚屋。《穆穆篇》虽记异国风致和外交活动,但充满了亲切感,这当然是因为胡志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和许多中国革命领袖有深交,并有很高的中国文化修养;虽然郭沫若是第一次到访河内,但和胡志明早有北京交往之谊。《穆穆篇》所写出的宾主交流,处处体现出亲切与新奇的美好融合。
首先,虽是外交场合,但“胡老信步来”[12]45,直接把郭老引入了自己所住的后花园。好奇的郭沫若先是被林间孔雀所吸引,后来和胡老相拥,一同观赏、喂食池塘中鱼,这先入庭院的一幕幕,既有越南风情,又充盈着跨国深谊,甚至还透出两国文化人所共享的“园林雅趣”。庭院之乐稍罢,胡志明才请郭沫若参观其居室:“邀我至其居,其居如珈蓝。胡老自设计,仿照旧时庵。旧庵乃竹制,革命时所潜。今虽易以木,未改村舍观。下有无壁殿,四面皆垂帘。中横长案一,宾主坐寒暄。”[12]46胡志明居室是朴素甚至有些简陋的,这段描写正从侧面成功塑造了他艰苦奋斗、贴近劳苦大众的人民领袖形象。以“珈蓝”“旧庵”为比附,在中文语境中都有寡欲、苦行的寓意,而诗人对越式室内布置的观察,也可谓认真细致。诗行展开至此,我们也可以感到诗人和领袖之间关系进一步拉近,革命情谊也被比附为这朴实无华的居室——“无文至斑斓”。诗人又“脱靴上楼轩”,走入“东寝”“西斋”。“入斋盘膝坐,坐亦无蒲团。回栏绕四周,素朴非雕镌。清风欣然来,好鸟奏笙弦。”[12]46-47如果说以“无文”为至色,已有以道家为喻的端倪,那么,这里就几乎是用一种返璞归真的清静美学来渲染革命风范。接下来,诗人和胡志明回忆两年前的交往:“胡老至北京,同观《武则天》。”众所周知,《武则天》是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重要历史剧。而胡志明仍留着当时郭沫若夫人所赠之扇,而且上面还有郭沫若手书毛泽东词《沁园春·雪》:“上题沁园春,咏雪之名篇。”[12]47两人的情谊有了更多的交织,也形成了两国团结革命的一个文化共通体。
至此,郭沫若才转向主席府的主体宫室:“正厅西式楼,遥看颇庄严。昔为殖民宫,今操专政权。”[12]47-48这样的历史鼎革、政治翻转,又立刻融入了胡志明的悠闲幽默和革命乐观精神:“胡老指顾告,意态何悠闲:在此曾判罪,枭首当悬竿。不意此头颅,至今尚安全。”[12]48胡志明带着中国友人从后花园来到正厅,是因为招待晚宴要在这从前的“殖民宫”、现在的主席府举行。全诗以畅写盛筵上的热烈气氛作结。在笔者看来,《穆穆篇》有一点远胜过我们上面提到的外访其他国家的纪行诗,那就是,它一方面远比其他作品显得亲切、不拘束、放松,革命情谊真实可感;另一方面,对异国文化风情的见闻、对异国革命精神的体察又不失新奇、细致、丰富。亲切感和新鲜感的辩证统一,也可以说是旅行书写所企及的革命团结新境界,或许也只在中越两国历史、文化、革命的特殊关系情境中才成为可能吧。
值得一提的还有据《郭沫若年谱长编》,郭沫若在访问主席府时,有白话诗《孔雀》《鱼和鸟》二首[1]2002,似为即兴、即景而作,而《穆穆篇》稍后作。相比较可知,两首从未发表的白话新诗,在诗意诗情上,可谓是后来成篇的五言古诗的原始质料。这样白话新诗先作而为后作旧体诗提供准备的“作诗法”,我们在郭沫若关于下龙湾的纪行诗中也将看到。
在河内参加完纪念日内瓦协议签订十周年的系列集会之后,郭沫若有了游览下龙湾的机会。下龙湾在越南东北部,为东京湾一部分,岛屿星罗,如“万朵花”[12]50,是越南风景胜地,今已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和在格鲁吉亚里加湖时一样,郭沫若显然为这里的奇异美景所折服并惊喜。在《下龙湾(七律八首)》中,一方面,就像他在里加湖看到了“阳朔风光”一样,诗人也发现了越南奇境和桂林的相似:“谁移桂林来海上?”[12]50通过这样的比附,越南风光得到了中国式的辨认,甚至“中国化”了,毕竟只有通过自身的语言文化才能认识异域。但另一方面,八首中又充满了“惊奇”“惊异”:“人惊北越绣天涯”“下龙湾景一奇诗”“倍觉下龙风物奇”[12]50-51。亲切和奇异的辩证法,汇入对异域美景的欣赏角度。诗人把下龙湾比作一首诗,他又联想到了“黄山云海”,而中国的“天池”也成了“砚池”[12]50,一幅中越自然风情的比较、互美的壮阔图景由此展开,更蕴含中越团结的地缘政治美学。
诗人享受着沁人肺腑的“习习熏风”,“饱吃鲜龙眼”,同时也学习考察着下龙湾的历史和现实。在这八首律诗中,诗人讲到蒙元征越的海军在下龙湾覆灭,日寇在下龙湾沉船,把越南人民抗击外敌的历史往事当作“殷鉴”,联系到越南战争的现实:“泰莱今日乌马尔,美帝当年蒙古王。”[12]52乌马尔为元军统帅,而泰莱系美国驻南越大使。在下龙湾,诗人也和越南民众一起庆祝南方战场上的新战果,而且认为下龙湾多变的天气也在和人间通感,将毛泽东词的修辞信手拈来,化用在郭沫若的自己的诗作中:“北地欢腾新生里,南中扫荡伪军营。想是下龙同感奋,湾头一出泪盆倾。”[12]52
在这种反帝、反殖、团结抗争的革命抒写中,又加入了新的内容:“反修正主义”。在越南所举办的国际活动中,当时已经事实上决裂的中苏两国不可能不同台。如前述,胡志明所领导的越南和中苏两大党都保持着友好关系,甚至对中苏论战采取调停态度。游览下龙湾的客人中,也有苏联代表。律诗之四,郭沫若写湾上诸峰——“仙女三千尽害羞,银纱罩面怕凝眸”——颇得雨雾中朦胧绰约之美,并在颔联用唐诗之典:“懒卷珠帘上玉钩”。颈联写天色放晴,日照当头,却提到所谓“两全人”。参诗人自注可知,“两全”指“全民国家和全民党”[12]53,两全人即“苏修人士”。也就是说,等到“苏修人士”扫兴离开,天立刻放晴,“仙女三千”才愿展露真容:“原来回避非无故,只见英雄不见修。”[12]51英雄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指。越南仙女认得出谁是真英雄、谁是“修正主义”——在理解越南立场的同时,郭沫若要为中越团结主题赋予时代的新指向。
《下龙湾》组诗以“骨连血肉山连水,五角星旗万古红”[12]53作结,强调的不仅是一种邻邦友好,更是新型的革命团结。同样,白话新诗体的《舟游下龙湾》作于七律组诗之前,即兴咏题,在意象、诗情、典故、修辞、政治内容上都可以看作是《下龙湾》八首的准备性“诗料”。把访越作品概括起来看,或许可以说,在20世纪60年代,旧体作为郭沫若的纪行书写的一种形式,为诗人自己所愈发倚重,也的确成就了相对更完整、更充实、更凝练的诗篇。《穆穆篇》《下龙湾》应运而生,结合时势、地缘、自然、文化、交往、人事等方方面面;而旧形式之新应用本身,在革命外交旅程中延续了“诗可以观”“诗可以兴”“诗可以群”,乃至于“诗可以党”[4]155-182的左翼民族文化抒发及交流模式,寓跨国革命情谊的亲切感(“群”)、异国特色的欣赏学习(“观”)和革命新斗争(由“兴”而“党”)于声韵律动,更应视为社会主义中国构建反帝、反殖乃至反修的新型团结的努力的特殊一部分。笔者认为,在郭沫若纪行诗中,这两部作品风格突出而内容丰富,还代表了中国文化政治在“全球六十年代”的特殊展开和表现。
四、尾声或余论:亚非作家紧急会议
郭沫若7月底离开越南回国后不久,东京湾事件爆发。为应对越南战争的空前升级,周恩来在8月6日作出指示称,援助越南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头等大事。8月7日,郭沫若发表《警告侵略者》:“你侵犯越南便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1]2005声援越南人民反帝斗争成为亚非团结事业的主轴。郭沫若在相关国际场合多次谈亚非拉的“进一步团结”,同美帝国主义斗争,更多次参加中国人民支援越南、反对美帝、庆祝胜利的大型集会。1965至1966年,周恩来代表中方多次警告美国,休想扩大战争,明确了不会坐视不管的坚决态度。而1966年春夏,“文化大革命”爆发,也就在这时,中国在北京主办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郭沫若是中方代表团团长。这次会议的“紧急”缘由,也正在于越南战争的升级,亚非进步作家必须以新的国际团结做出反应。
如前述,亚非作家会议本是万隆会议的重要成果,茅盾曾率团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1958年亚非作家会议。据考证,那次会上,中方邀请美国黑人知识分子杜波依斯(W.E.B.Du Bois)博士访华,于是才有了1959年杜波依斯和毛主席在一起的场景。但是随着中苏分裂,亚非作家会议这一交往平台也遭遇危机。在20世纪60年代初,社会主义中国不仅没有得到西方的外交承认,而且还受到各国共产党的半公开的批评,有些亚非人士甚至误解中国背叛了万隆精神。但中国不仅更加独立自主地面对世界,而且比其他任何进步力量都更强势地表态支持越南,全力援助,甚至不排除与美国直接开战的可能,并由此寻求反帝反殖反修的第三世界新团结。原本1965年要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因为中苏分歧和阿尔及利亚政变而取消。1966年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以中国为东道主,也遭到了亲苏势力的反对[13]。
1966年6月27日,郭沫若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开幕式,讲话直指援越抗美的新国际团结主题:“亚非各国人民和作家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决心,是任何力量都阻挠不了,是任何人都破坏不了的……为了支持和声援英雄的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国际统一战线,为了我们亚非各国发展反帝的民族的新文化,我们要进一步团结起来……”[1]20816月30日,会议通过了《坚决支援越南人民斗争的紧急呼吁书》。7月4日,郭沫若又作《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长篇发言。7月9日,会议闭幕。7月10日,他又主持了首都各界人民为声讨美帝轰炸河内、海防和扩大侵越战争的罪行而举行的集会。然后,他率领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各国部分代表转至武汉。在武汉,大约160名亚非作家有幸见证了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郭沫若以《看武汉第十一届横渡长江比赛·水调歌头》记此盛事:“迎接亚非战友,笔阵纵横扫敌,胜利在前程。……横渡长江毕,皎日笑容生。”[12]108-109由“皎日”可想见,彼时彼地,盛夏气氛,江上阳光灿烂,诗人当然也是“借喻毛主席”[14]675。次日,郭沫若又带着亚非战友们晋见毛泽东并合影,留下毛泽东和第三世界团结的重要影像。回到北京后郭沫若又参加声援越南的集会。8月初,他在上海欢送亚非作家代表,再次重申“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胜利道路”和“亚非反帝革命的、人民大众的、民族的新文化和新文艺的方向”[1]2084。7月12日,在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的招待会上,他又讲道:“世界人民必胜,分裂主义必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一定会不断扩大和巩固……”[1]2086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论域。但作为郭沫若访越作品和中国亚非团结工作的延续,它同样让笔者想到:如何从文化政治实践中理解中国在“全球六十年代”的特殊位置以及新型国际团结的构建?但郭沫若的外交纪行诗和“全球六十年代”的反帝团结却已经因为历史的疾速变化、反复变化而成为模糊的片段[14],需要我们钩沉、挖掘、辨认并重新展开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