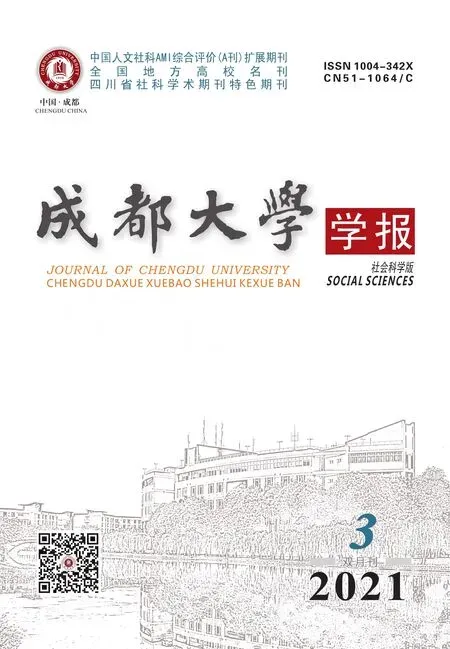乌托邦≠空想:乌托邦社会主义中“乌托邦”概念的源起、演变与理解*
陈 旺 孙 磊
(北京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9)
社会主义发展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在国内学界,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有一个颇为重要亦颇受认可的界分,即将这500年划分为6个阶段:(1)乌托邦社会主义;(2)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3)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4)苏联模式的逐渐形成;(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6)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其中,有一项大部头,即乌托邦社会主义。从时间维度上来看,乌托邦社会主义跨越了整整3个多世纪的时间,其时长约占比66.4%,占整部社会主义发展史的2/3。乌托邦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来源。由此可见乌托邦社会主义史的厚重和重要性。因此,“乌托邦”在中国,从学界到坊间,是一个为世人所熟悉的词汇。
但是,“乌托邦”却面临着一个困境,或将其称之为“‘乌托邦’困境”。准确地说,就是“乌托邦”概念在中文语境所面临的困境。本文通过考察“乌托邦”概念的原初内涵、在历史进程中的语义流变,以及其在学界的释义与运用,发现“乌托邦”概念之原初指涉已然偏移。再者,当世人提起“乌托邦”一词时,所能联想起的第一语义就是空想。也就是说,在中文语境中,“乌托邦”和“空想”几近是一对同义语。而这种普遍将“‘乌托邦’=‘空想’”的表征使用,无疑是一种对“乌托邦”概念的污名化,令笔者在学术情感上深感不满,难以接受。本文标题中的“乌托邦≠空想”,是贯穿全文的一条中心线索,亦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原初动力。总体而言,本文属于概念史的研究范畴,从题名自然可知,其想要探讨的是关于“乌托邦”的概念史。本文通过考察乌托邦社会主义中的“乌托邦”概念之源起、演变与理解,旨在为“乌托邦”概念正名,亦为展示乌托邦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叙事维度。
一、“乌托邦”概念的源起:词源和历史语境的考察
为“乌托邦”正名,对其原初指涉的考察是一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要考察“乌托邦”概念的原初指涉,首先要从“乌托邦”概念的源起出发考究。而要考证“乌托邦”概念的源起,就有必要围绕它的词源及其形成的历史语境进行考证。
(一)对词源的考察
“乌托邦”概念及其理论叙事源自于托马斯·莫尔的代表作——《乌托邦》。“乌托邦”是莫尔在写作该书时创制的一个新词。莫尔所在的时代,将拉丁文视为通往上流社会的金钥匙。作为一个并不显赫的贵族家庭出生的莫尔,自然也要修习和使用拉丁文。因此,“乌托邦”概念的词源,来自于拉丁文“Utopia”。那么,拉丁文“Utopia”缘何而来?对此,需再往前追溯。拉丁文和希腊文同属印欧语系的分支,所以二者关联十分紧密。“Utopia”,是由希腊文的两个词根组成的:一个是否定前缀的“Ου”,一个是意指“地方”的“τοπíα”。两相拼接,就形成了具有“不存在之地”的语义之新词。“Ου”这个否定前缀中的“υ”又是由意指“美好”之意的“ευ”转化而来的。因此,“Ουτοπíα”同时兼具“美好之地”的语义。此外,笔者通过查阅《剑桥词典》发现,“Utopia”在英文语境中同样具备如“理想中的完美世界”的语义。由此可看出,“乌托邦”概念在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美好之地”“不存在的地方”的双重语义。但颇值得玩味的是,在“Ουτοπíα”一词正式出场之前,在希腊文中就已经存在指称“新的、荒唐的地方或事物”的词汇——“ατοπíα”(其英文译法为“absurdity”或“absurdness”)。如若莫尔只是单纯想使用一个具有“不存在的地方”语义的词汇,完全可以直接挪用它。但莫尔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大费周章地另造新词。由此,结合词源学的理论追溯可判断得出,莫尔在创制“Utopia”一词之初,更多的是想用它来指代“美好之地”这重语义。
(二)对历史语境的考察
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出场“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1],且任何一个概念,若不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从时代背景的维度来看,“乌托邦”的诞生根植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欧洲,此时的欧洲方才从中世纪的废墟中迈出,正处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型的时期。此时的欧洲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是文艺复兴运动向欧洲诸国扩张的时代,亦是欧洲民族国家日渐兴起的时代。西欧各国热衷于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罪恶初露端倪,其中,尤以英国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农民从土地上被赶走,大片的村社房屋被拆毁,村庄变成牧场,农民沦为无产者,专制的政府却又颁布一系列血腥的法规惩治流浪者。因社会急剧转型造成的无尽苦难的现实生成力和源自文艺复兴思想冲击的历史根源力,交织缠绕共同形成了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憧憬的“乌托邦”。
面对这样的历史图景,在《乌托邦》中,莫尔选择游记文学体裁的叙事方式,描绘了他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构想。尤其在第一章中,他对私有制的评价,具有极其强烈的批判性。以莫尔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和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历史形势和主观条件的特殊结合,得莫尔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黎明阶段看到这个社会走向“残酷”的迹象的时候,不但能够用批判的态度对待社会现实,而且还能针对这些社会现实提出“社会平等”或是“全民共有”等带有“乌托邦”叙事特征的社会构想。从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历史谱系来看,“乌托邦”在此时已具有极强的“直接共产主义”色彩,是一种极具批判性、进步性的思想。
总体而言,“乌托邦”概念的原初指涉在于它的批判性和系统性。通过考察“乌托邦”概念的词源及其产生的历史图景,基本可以明晰,“乌托邦”概念在诞生之初,它的原初语义是指“美好之地”,蕴含的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崇拜人文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遭遇悲惨境遇的无产者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与期望。而通过透视《乌托邦》文本的逻辑理路,可以发现其至少具有两种基本的概念图式,即批判性与系统性:前者包含在莫尔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特别是莫尔描述了“羊吃人”现象的残酷,通过利用这种消极的素材,进而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无情;后者则包含在莫尔等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理想社会建构的乌托邦叙事维度的设计方案中。
二、内涵偏移:“乌托邦”概念的三次演变
由于“语言的意义所内蕴着的指称的意向性能否在外部世界实现的问题,意义所设定的‘观念的指称物’能否得到外部世界中确证的问题,乃是一个实践的问题”[2],因此“乌托邦”概念作为一定观念的指称物,在经历时间的挤压与空间的转移之后,其内在蕴含着的原初内涵已发生偏移。因而,要想厘清这一偏移过程,进而为“乌托邦”正名,就有必要梳理清楚“乌托邦”在时空层中的数次演变。
(一)从褒义到贬义:从“乌托邦”到乌托邦社会主义者
第一次演变,发生在从“乌托邦”到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之间。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者一般将莫尔的《乌托邦》视作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开源之作。在《乌托邦》问世之后,“乌托邦”概念的影响力也随着延续了近3个世纪之久。在这近乎3个世纪的时间里,由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生产力,推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它表现出了强于过去一切社会历史阶段总和的生命活力。而资本家与无产者的关系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中,也得到了进一步演绎。农民与手工业工人仅有的生产资料被资本家进一步剥夺,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只能被迫放弃原本的营生,进入工厂,转化成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体系的工人,即无产者。而随着无产者的不断聚集,这个共同体不断壮大,逐渐发展为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无论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过程中,在工作和生活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了和过去极为不同的特点。劳动者从过去人身依附的封建关系中走出,这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发展,无产者也愈落魄;资产阶级愈富裕,无产阶级也愈悲惨。最终,无产者也仅是从旧的显性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脱离出来之后,又进入了新的隐性的人身依附关系中——对资本的依附。
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受“乌托邦”思想的影响,在莫尔之后,出现了许多现在语境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如康帕内拉、温斯坦莱……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圣西门、傅里叶、欧文……。他们的思想或生平著作,如闵采尔的“千载太平天国”、巴贝夫的“平等共和国”、温斯坦莱的《自由发挥》、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傅立叶的“吸引原则”、欧文的“教育制度”、圣西门的“实业制度”,等等,是他们的“乌托邦”。他们在各自时代所闪烁的思想火花,虽就其思想、理论内容而言,是各不相同的,但观其内在的逻辑演绎,一脉相承的是对布尔乔亚严正控诉的批判性和对未来理想社会方案建构设计的系统性。因此,在这些实践者和理论家这里,“乌托邦”仍是一个表征美好社会追求的概念范畴。而在“乌托邦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理论流派出现在大众视野之后,基于人们对于它的不同评价,“乌托邦”概念的原初内涵也开始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偏移。例如法国经济学家日洛姆·布朗基蔑视地以“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来指代圣西门及其门徒之时,明显就是从贬义上使用了“乌托邦”这个概念。
(二)“空想”语义的赋予: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
第二次演变,发生在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科学社会主义是伴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运动中的活跃与理论创作上的灵感一同诞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他们的文本内,用了大量的笔墨来讨论乌托邦社会主义,其中不乏溢美之词。如恩格斯于1868年在《民主周报》上为马克思新作《资本论》第一卷所作的书评中,就明确肯定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在“现在和将来都是有价值的”[3]。1876年至1878年间,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时写下过这样一句话:“迄今为止是暴力——从现在起是共同社会。纯粹善良的愿望,‘正义的要求’。但是,莫尔早在350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这个要求。”[4]由此可见恩格斯对“乌托邦”之价值、意义的肯定。虽因莫尔及其后来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未能基于美好期盼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可实现的实践路径,才使得莫尔的良善愿望未能实现,但若换一个思路来思考,也正因莫尔的愿望是“纯粹善良的愿望”,所以直至350年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仍然重视“乌托邦”的价值。若“乌托邦”只有荒诞、虚无,那么马恩克、恩格斯也就无所谓再去讨论它的价值。1884年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再一次提及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历史价值,认为乌托邦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5]。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清晰地看到乌托邦社会主义在经济逻辑层面的落后,他们批判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在经济上没有预见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解、也未提出实现理想社会的可能路径,具有空想性。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建基于“实践哲学”之上,与乌托邦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科学社会主义之范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将“空想”之语义赋给了“乌托邦”。在现当代的诸多学者之语境中,“乌托邦”被等同于“空想”,其论证的依据,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乌托邦”的负面评价。但笔者想强调的是,我们要辩证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对“乌托邦”的“辩证看待”。也就是说,不仅要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乌托邦”的负面评价,亦要看到他们对其的正面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在业已肯定了“乌托邦”价值的同时,也将“空想”这一语义添加赋予给了“乌托邦”。
(三)语境的转化与语义的扭曲:从西方到东方
第三次演变,发生在从西方到东方之间。前文所述的是“乌托邦”概念在纵向——时间层的流变,第三次演变所论述的则是“乌托邦”概念在横向—空间转移过程中的流变。具体来说,“乌托邦”概念伴随着时空的转移,实现了从16世纪到20世纪、从西方到东方的迁徙。“乌托邦”概念进入中国后,其原初内涵发生了进一步的偏移。据考证,中文语境中的“乌托邦”一词,最早出现在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为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所作)中[6],他把《天演论》上卷第8章标题“Utopia”翻译为“乌托邦”[7]。这是一种音译与意译的巧妙结合:“乌”是“乌有”“没有”的意思,“托”指称“寄托”“美好”,“邦”是“国家”“地方”的意思。这个译法,和莫尔的“Utopia”的原初语义还是比较接近的,兼具“美好之地”和“乌有之地”的双重语义。随着1900年前后中国留洋潮的兴起,对国外思想著作的译介工作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刘麟生翻译的《乌托邦》首部中文全译本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译本对“Utopia”的译法仍是沿用了严复的译法。
从严复到刘麟生,在这37年的时间里,对“乌托邦”概念的译介不曾停止,但在西方语境中广泛使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伴随着中国学者对“乌托邦”的介绍,却被普遍译为“空想社会主义”。陈望道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就将“Utopia”完全地译为了“空想”。如其中的“批判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节被翻译成了“批评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8]。陈望道之后的其他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也大多沿袭了这一译法。在此后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如《反杜林传》《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包括我们今天最常使用的2012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09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凡是有“乌托邦”和“社会主义”一起出现的地方,“乌托邦”都被译为了“空想”。在中国的学术话语中,“乌托邦”渐渐被趋同于“空想”,其似乎也就成了一个“约定成俗”的译法规定。有说法认为,中国译者将“乌托邦”翻译为“空想”,是由于中国近代学界受日本影响较大的缘故。许多马克思主义中的概念范畴,都是先由日本学者译为日文的汉字,中国学者参考借鉴之,再转译为中文词汇。“乌托邦”变成了“空想”,亦是受日本学界的影响。所以,国内学界仅是沿袭了这一译法。但笔者通过考察日文语境中的译法,发现在日文中,同时有意译的“空想社会主義”和音译的“ユートピア社会主義”[9]两种译法。由此可见,是中国学者在“乌托邦”和“空想”之间,选择了后者。
三、正确指称:如何正确理解“乌托邦”概念
柏拉图认为:“命名者所作的事情,就是把一切事物还原为文字和符号……人们应该按照自然的本性来给事物命名,而不能随心所欲。”[10]如果只是简单地在“乌托邦”与“空想”之间划上等号,只会使人们望文生义。看见“乌托邦”,也就自然将其等同于“空想”,而丢掉“乌托邦”的另一内涵——美好之地——它的真正指称。从语义学的维度来看,“指称是指一个语言表达同其所指对象的关系”[11],因而“乌托邦”不仅是一个语言符号,而且还内在包含着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莫尔基于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将这张“蓝图”命名为“乌托邦”,是有着其特定历史语境的,这一语境不应被忽视。
(一)需防止在“乌托邦”和“空想”之间划上等号
从词源学、语义学的角度来看,“乌托邦”和“空想”不论是在历史维度上,还是在概念维度上,都不是同延的。在历史维度上,“乌托邦”一词最早由莫尔创造,欧洲国家在对“乌托邦”概念进行翻译时,无一例外地都是直接将拉丁文“Utopia”移植过来,如英文“utopia”、法文“utopie”、意大利文“utopia”、德文“utopie”等。要知道,在这些语言中本就有形容“空想”的词汇,但它们却仍然选择直接挪用“Utopia”。但在中文语境中,“乌托邦”一词却是一个近乎等同于“空想”语义的贬义词。笔者认为,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学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译介上对“乌托邦”概念忽视的缘故。如前文所述,虽有看法认为中文语境中的“空想”一词,最早是由日本学者在翻译“Utopia”时采取了意译的方式,因而才形成了“空想”一词,中国学者仅是选择移植了这一译法,但他们却忽视了日本译者同时保留有表征“乌托邦”原初内涵的“ユートピア”一词。
在概念维度上,“乌托邦”的内涵与外延要远广于“空想”。“乌托邦”是一个中性词,从它诞生之初起,就兼具“美好之地”“无有之地”的双重语义。而“‘空想’本身令人费解。按中文字面的意思,似乎空想就是‘凭空想象’”[12],其明显是一个贬义词。二者的内涵与外延皆不对等,用一个外延和内涵都相对小的词来完全指代另一个词,笔者认为是不恰当、不合适的。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基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乌托邦”的价值与意义,他们对其进行批判的同时,亦从正面肯定了“乌托邦”在世界历史范畴中所具备的价值意义。作为后来者,自然也同样要用辩证的视野来审视“乌托邦”,既要看见“乌托邦”的缺陷,亦要看到“乌托邦”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如只是简单粗暴地将二者划上等号,则会使“乌托邦”成了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范畴,甚至会使得人们不再关注它的具体内涵。只是简单地将“乌托邦”等同于“空想”,进而忘却“乌托邦”最重要的另一内涵,对“乌托邦”的理解产生混乱。因此,要正确理解“乌托邦”概念的指称,就要防止将“乌托邦”和“空想”划上等号。
(二)需厘清乌托邦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学术史的视域中,回溯社会主义500多年的发展历史,或可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界定为科学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前史。乌托邦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谱系上,有一个“一先一后”的位置关系。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乌托邦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材料来源。关于这点,不论是国内通行的“马工程”教材还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述,无一例外地都承认了乌托邦社会主义(虽多称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之一。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国内学者在理解其他两大来源——德国古典哲学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时,都能相对辩证地看待其二者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将它们译为“古典”,而非译为“德国空想哲学”与“英国空想政治经济学”,然而在选择“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之译词时,却选择了明显带有贬义意味的“空想”。缘何如此?本文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在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即中国学者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科学性、正统性与权威性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排斥了乌托邦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史前史的合理存在。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在使用“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在一定语境中确实带有批判的意味。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同其他社会主义(包括乌托邦社会主义)相区分,将自己的学说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但同样也要看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具有强烈针对性的,且主要是针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不明白政治活动的意义而提出的批判。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仅怀揣热情对未来理想社会进行蓝图构建是远远不够的。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种在特定语境下的批判,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误解,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态度,极具针对的批判逐渐演变为了“凡是‘乌托邦’就都要抵制”的全盘否定。这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也不利于正确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要知道“马克思的目的不是摧毁,而是实现各种远景”[13]。科学社会主义是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超越,也正是有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发展,才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如只是一味排斥“乌托邦”,继续对其带有理解上的偏见,那么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否认科学社会主义从无到有的形成规律。因而,要正确理解“乌托邦”概念的指称,就要厘清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辩证关系。
(三)需认清“乌托邦”的精神意蕴
“乌托邦”精神至今之所以还被人们时常提及,“正是人们需要拒绝理想、情感、爱情、艺术、友谊等等生命特质不断被物化的命运”[14]。虽然“乌托邦”精神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通过“形而上”的形式实现的,其形式本身缺乏实践理路,因而是空想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对美好的追求本身是没有过错的。当我们用“马学”的视野来回看乌托邦社会主义时,它们无疑是过时的和空想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乌托邦”内涵的精神意蕴,即使在今天也是有价值的。从柏拉图《理想国》中描绘的理想共和国、莫尔《乌托邦》描述的理想社会,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的终极指向——共产主义社会,再到新时代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它们所蕴含的对美好社会之追求的精神脉络是一致的,都具有“乌托邦”对理想社会美好追求的精神意蕴。从这一层意义来看,“乌托邦”在今天仍是不可或缺的精神养料。
从16世纪到19世纪,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构想与试验,或是停滞于想象,或是依托于资产阶级的“善心”,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如马克思对这些乌托邦尝试的评价那样: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主导的“理想乡”建构之所以“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不具备”[15]430,但乌托邦社会主义“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15]431。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正是基于对阶级对立以及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所存在的缺陷的判断上,才设计出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方案,如欧文的教育理念、圣西门的实业理念等。从这一意义来看,“乌托邦并非是一种每个细节都要执行的计划,它可以发挥参照的作用,帮助我们指导当前的工作”[16]。
四、余论
通过考察“乌托邦”概念的源起,可明晰的是,“乌托邦”在诞生之初,就已具有双关语义,其原初指涉更是在于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严正批判之中。“乌托邦”概念在经历时间的转移和空间的挤压之后,其原初指涉发生了偏移,考察“乌托邦”在不同的历史维度中的语义表征,亦可明晰其内涵至少发生三次演变。要准确把握“乌托邦”的正确指称,就要明白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对“乌托邦”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乌托邦”的全盘否定。如果只是简单、粗暴地在“乌托邦”和“空想”之间划上等号,只会令人望文生义。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也无益于进一步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成逻辑。
研究乌托邦社会主义,厘清“乌托邦”概念的源起、演变和阐明“乌托邦”的正确指称,就是要讲清楚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的问题。对“乌托邦”概念史进行研究和梳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过程。这对如何更好地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本质属性,以及如何更好地认识科学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性,进而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逻辑演进提供新理路。2020年正值刘麟生翻译的《乌托邦》首部中文全译本出版的第85周年,重新梳理、研究“乌托邦”概念的源起、演变与理解,对形成良好的历史反思或许有一定的帮助。最后,作为一个结论性的论断,本文认为,或应考虑取消“空想社会主义”中“空想”的译法,以“乌托邦”取代之。也就是说,今后我们在指称“Utopia”时,或许可以用“乌托邦”完全替代“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