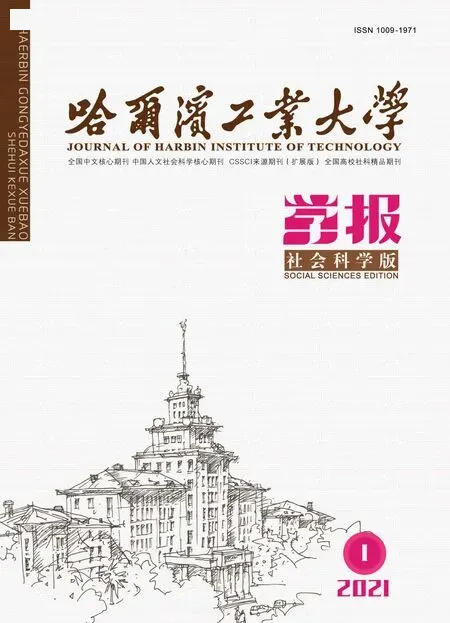BBNJ国际立法的困境与中国定位
何志鹏,王艺曌
(吉林大学 a.理论法学研究中心;b.法学院,长春130012)
为保护公海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避免“公地悲剧”发生,联合国大会在2015年6月19日通过了69/292号决议,拟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项下,针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生物多样性(简称BBNJ)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制定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BBNJ协定预委会的立法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且已于2017年7月20日向联大提交了最终建议性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建议草案》(以下简称《BBNJ建议草案》)。①Preparatory Committee Established by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92: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2020-05-04.https://www.un.org/depts/los/biodiversity/prepcom.htm.但就各方在预备会议上的分歧,以及《BBNJ建议草案》中多个核心问题未能达成一致结果来看[1]16,未来BBNJ国际立法谈判工作仍将面临诸多挑战。
分析BBNJ国际立法困境之成因,特别是明晰中国在此次海洋规则制度构建中的机遇与挑战,不仅对中国未来海洋战略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提升中国在海洋治理领域中的话语权同样具有深远影响。因此,本文将从BBNJ国际立法所面临的挑战入手,剖析导致其立法进程困境的理论原因;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BBNJ国际立法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从而就中国在BBNJ国际立法过程中应持有何种立场与定位提出一点建议。
一、BBNJ国际立法面临的挑战
BBNJ国际立法在谈判进程中,将会遭遇诸多困境与挑战。一方面,现行国际海洋法体系中的某些原则与规定,将会制约BBNJ协定中有关法律规则之形成;另一方面,BBNJ新制度的构建,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国际制度提出新的发展要求。此外,BBNJ新规则将会限制国家在公海海域的权利自由,造成海洋科技强国在公海海域的利益获得下降,进而导致一些发达国家对BBNJ国际立法工作的响应不够积极。
(一)现行海洋法原则制约BBNJ新规则体系之形成
BBNJ国际立法如何与现有海洋法律制度相协调,是BBNJ谈判进程中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尽管联大第69/292号决议肯定了BBNJ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的重要性,也表明了公海全球治理的趋势,但预委会向联大提交的《BBNJ建议草案》的B节依然指出:谈判各方就“人类共同财产和公海自由方面”“海洋遗传资源包括利益分享问题上”“环境影响评价”“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方面”“财政机制”和“争端解决”等问题,仍然存在主要矛盾[1]203。这些矛盾的根源,既来自对现有海洋法原则的冲击,也来自与现行海洋治理制度的分歧。
BBNJ国际立法在弥补海洋“公地悲剧”的同时,也对公海自由原则造成冲击。公海自由原则是国际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被格老秀斯在其著作《海洋自由论》中被论证以来,数百年间已经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然而,BBNJ国际立法将会对这项已经形成普遍共识的海洋法观念构成挑战,进而可能导致法律制定的协商过程格外漫长。例如,《海洋法公约》中规定了人类在公海领域享有捕鱼自由。根据既有的国际习惯,国家在公海捕获海洋生物资源遵循的是“谁捕获谁拥有”的原则。实际上就是把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生物属性看成是无主物,采用的是“先到先得原则”[2]。但BBNJ法律体系一旦建立,为实现对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利用之目的,公海区域的捕鱼自由必然会受到严格限制。这种限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将公海的物权属性,由原来的无主物重新界定为人类的共有物,这无疑是对现有国际海洋法体系自由原则的一种挑战。
此外,环境影响评价作为保护海洋环境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新问题。针对这项工作是应由各主权国家开展,还是应由全球化的中立机构进行,谈判各方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从现有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环境测评的实践来看,其启动的决定权、执行权和拟议活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主权国家所掌控的[3]。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违反国际法规定,导致国家间的信任度降低,反而像国际海底管理局这样机构健全、运行稳定的国际组织,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利用和管理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都作出了许多贡献[4],在国际社会中拥有更好的守法形象。因此,在BBNJ执行议定的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就提议由国际海底管理局主导开展海洋环境测评的工作,欧盟和澳新等国也主张BBNJ应建立全球化的环境测评标准,由独立的科学机构开展。但美国对此表示反对,在BBNJ谈判中明确强调了,国家在启动和开展环境测评以及相关决策方面的主导地位[5]。这种在全球化与主权化治理模式上的分歧,将会造成BBNJ国际立法进程的停滞。
(二)现有国际秩序阻碍BBNJ规则制度之构建
国际法在为国际行为体的行为提供方向性指引的同时,又被国际行为体的行为模式所影响[6]。近代国际法从其诞生之日起便伴有大国政治的烙印,而大国政治在国际法中的长期存在,是至今仍未能摆脱的客观现实[7]。在这样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BBNJ国际立法工作也依然会受到国际秩序中的政治化影响。届时如何规制BBNJ国际立法不被大国权力所左右,将是其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国际秩序中大国影响所引发的问题之一是相关规则因无法达成共识而表述不明。海洋不仅是沿海国的安全屏障与经济支柱,而且其海底蕴藏着巨大的能源与生物遗传资源,对各国都有巨大的价值,是各国利益争夺的重点领域。纵观《海洋法公约》自谈判到最终形成的过程,不难发现,在国际海洋法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各方立场原则的分歧所映射出的是其背后政治利益的冲突,而利益在短期内无法调和与平衡,往往会造成法律规则中的制度留白或有意的模糊性规定。例如,《海洋法公约》中的“航行自由”原则,实质上就是公约制定过程中,为平衡海洋强国与中小沿海国分别提出的航行自由和扩大国家管辖权的冲突主张,最终对航行自由的法律边界进行了模糊化处理[8]。
国际秩序中大国影响所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则表现为国际法体系的分散性。大国为了自身利益,可能会退出全球性质的条约,而选择构建区域性或双边的法律规范,从而造成国际法“充满了具有不同程度的法律一体化的普遍性的、区域性的,或者甚至是双边性的体系、小体系和小小体系”,而这些各种功能性制度和规范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结构上的有机联系,他们之间彼此相互冲突[9]。而国际法的分散性,将进一步导致其在治理国际事务中的适用困境,可能会产生国家必须要遵守两种相互排斥的义务的情形,从而引发国家责任与国际争端,给国际社会之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国际社会是一个高度分权的平行社会,没有统一的立法体制,各个国家在法律制定、解释和适用的过程中,会基于本国在不同领域或同一领域不同时期的利益需求,在有解释空间的问题上最大限度地朝着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方向解读,甚至不惜造成不同法律文件间的冲突或相关法律文件间的不连贯。国际秩序的这种政治化、分散性的特征,决定了在BBNJ国际立法进程中,如果忽视大国的话语和态度,可能会导致法律文本根本无法形成并生效。
二、BBNJ国际立法困境的理论解读
关于BBNJ立法困境的成因,有学者指出是有关事务主体缺失责任感造成的本体构成困境[10];也有学者认为是对公海自由原则的理解分歧,导致缔约方谈判进程之迟缓[11]。但在BBNJ谈判过程中,造成国家原则性意见与治理观念分歧的原因,除了国家在主观能动性与认知程度上存在差异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隐藏于这些现象背后的价值认同分歧,以及国际关系理论对其的影响。
(一)国家间正义观与全球正义观的治理分歧
在BBNJ国际立法谈判中,关于BBNJ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等相关事务的工作,是采用主权化的治理模式还是全球化的治理模式,实际上是国家间正义观与全球性正义观之间的纷争。换言之,是应该形成以国家间正义为价值依托的BBNJ法律理论体系,还是应该建立以全球正义为道德基础的BBNJ法律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价值基础不同,必然导致其所指引形成的法律规则与治理制度不同。
国家间正义是以国家作为正义的承受对象,强调维护国家的权利;而全球性正义则是以人类整体作为正义的承受对象,强调人类整体的利益追求。国家间正义主张自己具有平等和独立的主权道义权利,各国政府基于此种权利参与国际事务的治理与国际秩序的构建。而全球正义则认为,所有的个人(包括国家)都属于世界社会的一部分,其利益应该服从于世界社会的整体利益[12]。在当今国际法中,从由联合国及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机构来维持国际和平这一最低限度秩序的举措可知,国际法中的许多规则制度都倾向于支持国家间正义。在这种正义观的指引下,国家可以为自己追求利己的法律准则找到一个好的道义借口。例如,一国如果向另一国采取了国际法上所禁止的武力行为,其可能就会主张自己的行为是为了维护本国安全利益的预防性自卫,符合自卫权的道德基础。
全球正义观虽然理论上可以制约国家为了自身权利而对他国国民或人类整体权利造成损害的行为,但在主权原则仍是国际法中最为基石性的原则、国家仍是国际法最主要的主体这一事实不会改变的情况下[13],想要忽视国家的作用而直接构建符合人类整体利益诉求的法律制度,未免有些过于理想化。例如,谁能代表人类整体参与法律规则的制定?如果国家权利不再具有正当性,谁又能推动人人平等的国际社会之实现?又应由谁、通过何种方式来保障人类的整体安全?由此可见,只追求国家间正义指引下的国家主导的BBNJ治理模式,或者只采纳全球正义观引导下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皆非明智之选。应该选择国家与国际社会中立机构相结合的,多层级、多样式的治理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弥补两种正义理论指引下的治理模式的不足。
(二)权力政治理念导致海洋利益共同实现之艰难
权力政治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爱德华·卡尔认为,权力和政治是不可分割的,政治行为必须要建立在权力和道德的某种协调之上。经过汉斯·摩根索的发展,权力政治概念长期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4]。在摩根索看来,国际关系中的一切问题都可归结为权力问题,而国家利益是由权力所界定的。权力并不等同于武力,而是权力比重较大者对较小者的一种控制心理。因此,经济、领土、军事、文化、法律及其他形式的控制,都是权力政治呈现的方式。
权力政治理论的一个弊端在于其所谓的“囚徒困境”,即在互相猜忌与遏制中寻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而非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权力政治理论认为,追求均势是防止国家非理性行为和维持世界和平的有利保障,其核心是阻止任何一个国家占据比自己更为优势的地位。受此观念影响,权力大国就不得不一直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中,即为防止他国实力崛起对自己造成威慑,就需要不断增强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地位。而具体实现方法就包括通过左右国际规则的设置,使自己可以在这套规则体系中获得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不断凝聚自身实力,以备必要时有能力给威胁自身地位的国家以致命打击。因此,持有零和博弈思维的国家,就会在BBNJ国际立法谈判中,为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选择有利于日后本国在公海领域获取更多权力的规则体系。如果不改变这种由权力政治观所引发的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就很难在缔约各方间形成共同的利益观,也就无法设计出能真正惠及全人类的BBNJ法律制度。
(三)全人类共同利益是突破BBNJ立法困境之关键
全人类共同利益思想,萌芽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提出的世界公民概念。该派主张,建立所有人类都在理性指导下和谐共处的世界国家,人类社会不应当因为正义体系的不同而建立不同的城邦国家[15]。全人类共同利益正式成为国际法原则是在1958年的联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上,由当时的泰国代表所提出。随后马耳他驻联合国大使阿维德·帕尔多解释该原则包含四个方面:国家不得将国际海底区域据为己有,应遵循联合国的原则和目的开发国际海底区域资源,为全人类的利益使用,用于和平目的[16]。联大在1970年通过的《关于国际海底区域的原则宣言》中采纳了帕尔多的观点,该原则正式被纳入海洋法领域。
首先,在BBNJ国际立法中强调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核心地位,有利于缓解权力政治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冲突,促进各国在BBNJ治理上的合作与依赖。亚历山大·温特指出,在具有相当高的集体认同的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里,国家很少会为了感到安全而依赖相互平衡的军事力量。国家间共同观念的差异,决定了彼此关系的状态是霍布斯式的、洛克式的还是康德式的[17]。各国在BBNJ治理上,如果有了要谋求“全人类共同利益”这一共同目标,那么就可以基于各方达成的这一意愿共识,改变原有的利益争端或先占先得的观念,形成互信与合作,将自身利益融入全人类共同利益之中。如此一来,BBNJ国际协定谈判各方,不仅会考虑本国的利益,还会兼顾他国的利益;不仅会关注本代人的利益,还会基于代际正义考虑后代人在海洋领域的平等权,进而有利于BBNJ规则制定在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淡化彼此间的正义分歧。
其次,BBNJ国际立法坚持全人类共同利益原则,还有助于国家将本国的生存、发展与获利置于国际社会整体的框架下考虑,从而跳出现代的民族国家思维模式。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思想,有助于形成世界整体的共同命运概念与集体认同感,人们会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思考问题、构建法律制度,也就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不会将资源浪费在成员内部间的制衡与消耗上[18]。当世界各国都能真正地认识到,如果不进一步规范国家在公海领域的活动,将会给海洋生物资源与环境造成巨大破坏,从而给自己带来生存威胁,各国就有机会相信合作并形成集体身份。有了共同命运这一客观条件,再加之集体身份这一主观要素,各国在BBNJ国际立法谈判中,就不会只着眼于规则制度的设定是否有利于本国利益,也不会只追求一元的正义存在,而是更可能会在综合权衡本国利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上,思考人类整体利益与正义多元之共存,进而追求能实现相互利益最大化的法律制度。
三、BBNJ国际立法的中国定位与建议
中国曾经在构建国际海洋法制度中的参与度不足、话语权不够,导致中国在南海断续线内水域的历史性权利主张得不到《海洋法公约》的明确认可。BBNJ国际立法工作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可以充分参与海洋治理与观点表达的机会,这对中国是一次重要的机遇。然而,中国作为刚刚发展起来的海洋新兴国家,BBNJ规则对国家海洋活动的限制,将可能会限制中国海洋技术与研发的进一步提升。因此,中国应在充分权衡BBNJ国际立法给自己带来的利弊基础上,提出既有利于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又能满足中国发展需求的可行性方案。
(一)清晰定位BBNJ国际立法对中国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未来的根本安全和利益发展,都离不开对海洋战略利益的谋划与拓展。通过观察国际海洋实践可知,一国对海洋事务的参与程度,往往与他的综合国力相关,并影响其所追求的国际目标之实现[19]。中国若想成为国际海洋强国,维护本国公海领域之权益,就有必要积极参与BBNJ国际立法的谈判工作,推进国际海洋法体系的完善与良好发展。探析中国参与BBNJ规则制定的利与弊,对中国接下来在BBNJ国际立法谈判进程中的立场与态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BBNJ法律框架的建成,为中国引领新的国际海洋法律制度,增加中国在国际海洋法体系中的话语权,提供了机会和可能。针对BBNJ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的立法,实质就是由公海自由到公海治理的转变,是各国拓宽自身公海海域管辖权的一次活动。通过拓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域,从而缓解一国内部资源和发展空间的巨大压力,对一国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20]。从促进公海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有针对性地对公海生物多样性提供实际有效的保护措施来看,BBNJ的立法活动具备显著的意义和积极的作用。此外,BBNJ相关制度的制定过程,实际上也是对海洋遗传资源及惠益进行分配的过程,中国合时宜地推进BBNJ法律制度的设立,参与构建国际海洋法律新秩序,有助于捍卫自身的海洋权益。
另一方面,中国的深海科研能力与公海活动实践都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不仅会使中国在BBNJ国际谈判进程中处于被动地位,而且BBNJ法律制度建成,还会一定程度阻碍中国在海洋领域的技术进步。中国在深海生物资源研究上,无论是资金技术还是科研队伍,都与许多发达国家存在着差距;对海洋生物种类和资源环境的了解度与认知度,也都远不及发达国家。BBNJ国际立法谈判中,需要大量的有关海洋生态资源的数据作为支撑,而中国在公海海域的有关科学研究不仅起步时间晚,而且研究的数量、范围也较小[21]。此外,中国的海洋工程和海洋科技刚刚脱离探索阶段,正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是海洋生物医药的研发工作,还是海洋石油与天然气的开发利用,都已取得丰硕成果[22]。在这种情况下,BBNJ法律框架一旦建成,则意味着今后中国在公海海域的资源开采、科学研究等活动都将受到严格限制,进而导致中国在分享海洋资源、扩展利益空间等方面所享有的战略利益,都无法同发达国家相媲美,不利于中国长期的海洋战略发展目标。
(二)平衡中国的短期需求与长远发展
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利用,是维持海洋生态健康的重要环节,对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和维护人类的进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在BBNJ国际谈判中,应在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础上,综合权衡中国现阶段的发展需求与今后长久的海洋权益维护,结合自身海洋科研能力的现状与未来深海领域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全面斟酌、谨慎决策,确保BBNJ国际谈判设立的新规范,既能维护中国现阶段的海洋权益,又能满足中国未来之长远发展。
中国应在综合考虑自身现阶段发展需求与未来长远利益的基础上,谨慎地表达自身立场与态度。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在深海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发与数据采集活动,开始进入开发与商用阶段。如果不采取法律手段对其进行规制,那么发达国家将会独占深海水域的生物资源,甚至还可能会引发海洋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通过法律制度限制发达国家对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和资源的过度研发与利用,以使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也能平等地享有和利用这些生物资源。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应尽快促成BBNJ国际协定规则的建成。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的海洋科研能力和海底资源勘探技术都处于上升期,过度限制在公海领域的海洋科研活动,势必会阻碍其在海洋领域的发展与实践,进而造成中国与发达国家海洋科研能力的距离始终存在。如此一来,即使BBNJ新规则在立法技术上平衡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就实践而言,由于技术和经济上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在如海洋生物遗传资源惠宜分享、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也很难真正实现与发达国家的平等。因而,中国在BBNJ国际协议谈判进程中,有必要全面考量现阶段利益需求与未来长远战略之发展。
(三)协调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总体利益
BBNJ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问题,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与解决,当然由此产生的利益也应该惠及整个国际社会。但是海洋资源与环境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要依靠技术和资金来实现。在整个国际社会中,各国的科技和经济水平存在差异,导致各国在BBNJ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的能力不尽相同,只有让在海洋领域技术能力较先进的国家成为相关事项的先驱者,才能缩短人类对海洋资源认知的时间,从而实现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发展。
虽然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总体利益,长期而言方向一致,但短期内的利益方向,相互间可能存在着冲突;并且实践中,各国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利益实现程度也不尽相同。那些海洋科研技术能力领先、资金条件富裕的发达国家,已对公海领域的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形成一定程度的认知,其在资源开发与利用上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即使BBNJ法律规则建成,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也较弱。相反,对于那些科研能力不足、尚未开展公海和海底区域相关研究的发展中国家,新规则限制其在公海活动自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为明显。中国在BBNJ国际协定谈判过程中,一方面要对自身现阶段的海洋科研能力有个准确定位,清晰地判断自己与发达国家在有关区域所获取海洋利益的差距;另一方面要以发展的眼光对中国未来的海洋科研能力进行估判,多角度地确定中国在BBNJ法律规则制定问题上的战略利益较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优势。以此为基础,正确把握BBNJ国际立法活动的谈判方向,协调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总体利益的平衡,以国家的发展带动国际社会海洋领域的整体发展。
结 论
国际海洋法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予以完善。BBNJ国际立法工作可以弥补现有国际海洋法体系中,关于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的制度空白。从既有的国际立法实践来看,一项新规范的构建与完善,需要经过谈判各方不断的探讨与协商,通过不断的实践认识和理论反思,才能在国际社会上形成良好的、客观可行的国际法律制度。BBNJ国际协定谈判作为《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最重要的国际海洋法律谈判,其所产生的新规则,应能有效地引导并约束国际行为体的行为,因此需要各国间妥善权衡与制定。
一方面,应充分协调新规则对现有国际海洋法原则的挑战,使其与《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则相契合;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海洋技术与实践能力方面存在的差异,立足于国际社会与全人类整体的发展需求,均衡各方的利益与关切。中国作为正在崛起中的海洋大国,BBNJ国际立法工作无疑是中国以新兴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法律规则构建的一次机遇。法律规则的制定是为了指引和规范实践中的行为,在BBNJ国际立法谈判进程中,中国应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思考,综合权衡中国海洋领域的技术现状与发展速度,多方考虑中国现阶段的海洋需求与长久的海洋战略利益,从而明确自己的态度。中国要充分考虑国家短期需求与长远利益的平衡,协调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总体利益之发展,为BBNJ国际立法贡献对国际社会具有实践意义的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