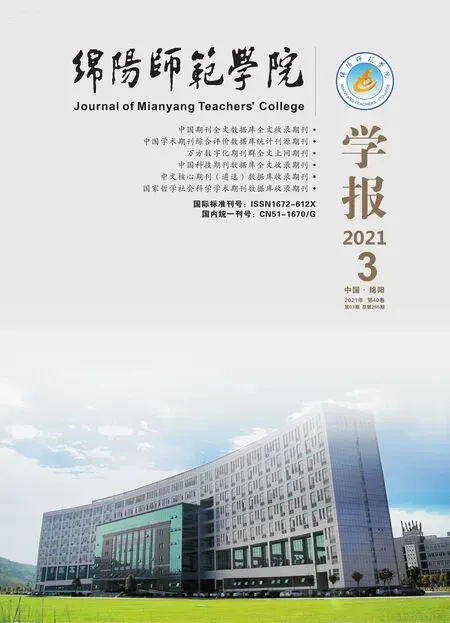神话图像建构商周政治权力
——张光直神话研究简述
田桂丞,倪峰山
(1.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安徽铜陵 244061;2.湖北大学,湖北武汉 430062)
张光直是一位出色的考古学者、人类学者,致力于中国商周的考古研究,他以世界性的眼光和人类学的方法,推动了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考古学术体系。其代表作《中国青铜时代》《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考古学》《考古专题学六讲》《青铜挥塵》成为世界了解中国考古的重要媒介。
张光直在神话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他的考古研究集中于宗族、城邑、文化和政治等方面,在探讨文明起源与政治构建的问题时,将神话作为重要研究内容,对神话的功能、分类和演变进行了极富特色的研究。其关于神话与政治权力、神话与历史等问题的解读,因具有独特的研究角度和思想维度,在一定时期引领了研究风潮。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国内学者注意到张光直对神话学研究的贡献。蒋祖棣(1987)评述了张光直的神话动物纹样与神话宇宙观的关系研究,认为其受到了世界性萨满教研究的影响[1]。叶舒宪(2013)认为张光直是神话图像学研究的先驱,促进了神话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2]。王倩(2016)认为张光直对神话学的贡献体现在对神话功能、神话宇宙观和神话历史化等问题的研究,从神话图像与权力构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商周英雄神话起源等方面解释了神话进入历史的途径及方式[3]。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质疑张光直的理论。萧兵(2006)认为张光直借助萨满教机制来分析中国文化的合理性,对“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提出质疑[4]。曲枫(2014)和吾淳(2017)也都提出了对于“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质疑。本文基于张光直先生的主要学术著作,依据神话研究的一般范式,简要评述张光直神话研究的内容,分析其商周神话的功能学说、分类学说和演变学说,并综述与此有关的研究成果。
一、商周神话的功能:神话图像建构政治权力
张光直对神话功能的探讨,集中于神话图像如何建构政治权力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国内神话学以文本神话为主要对象,形成了文本中心主义的研究惯例。这种研究范式不仅忽略了文本神话以外的口传、仪式和图像等神话形式,也极易被文本“选择、断裂、蒙蔽和遗忘”的缺陷所蒙蔽[5]。图像神话的产生早于文本,具有实在性、可视性和说服力。虽然有些学者重视开展图像神话的研究,但始终未能将图像作为要素列入神话研究的体系中[6]。叶舒宪认为张光直对神话图像功能的解读,促进了神话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是神话图像学研究的先驱[2]。
在研究内容上,张光直选择中国青铜器上的动物图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主要基于两个层面的考虑:一方面,青铜器是解读中国古代社会的关键要素。一是古代中国的神话图像主要存在于宝石、金属和陶器上,其中青铜器的数量最多,可供研究的对象充足;二是古代社会尊崇“国之大事,即祀与戎”的观念,青铜器是当时先进的工艺制品,被广泛制作成礼器与兵器,在社会语境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三是青铜礼器作为祭祀的工具,是参与仪式、记载神话的重要载体,具有十分显著的宗教与神话特性。另一方面,学者对动物图像的意义莫衷一是。动物图案是殷商与西周初期青铜器艺术的典型特征,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种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动物,如犀牛、兔、马、蝉、龟、象、鹿等,另一种是古代神话中特有的神话形象,如饕餮、肥遗、夔、龙等[7]357-358。针对这些图像,一些学者认为毫无意义,即使有也只是装饰层面的意义[8]12-13;更多学者相信其有特定寓意,有学者用“图腾”说进行解释,也有学者认为是自然或宗教力量象征,统治者用其避邪祈福[9]。而张光直认为,这些观点没有准确描述动物图像的意义,它不仅是装饰和图腾,更在古代社会和政治文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象征性和宗教性作用。
张光直认为神话动物图像具有“精灵助手”的功能。这一点明显是受到了西方萨满教研究的影响。米尔恰·伊利亚德(M. Eliade)在《萨满教:古老的昏迷术》中指出,萨满巫师在做法时,会使自己陷入迷幻的状态,这时往往需要召唤动物精灵作为助手,协助他们在昏迷中实现升向天界和降临地界的任务[10]88-89。张光直认为商周帝王在沟通天地时,不仅需要仰仗巫觋,还需要借助动物牺牲和祭祀用具。青铜礼器作为巫术仪式中的祭祀器具,担负着沟通天地的作用。青铜礼器上的动物图像,与萨满教的“精灵助手”类似,是“动物牺牲”的象征,用来协助巫觋沟通天地。据此,张光直联系古代典籍中“操蛇”“帝使凤”等内容[11]47-55,初步建立神话动物协助通天的观点。
由此,张光直提出神话的功能是参与政治权力建构。依据动物协助通天的观点,谁能占有带有动物图案的青铜礼器,谁便占有了沟通天地的手段,也就意味着垄断了上天赐予的权力。统治者通过这一手段,建立政治话语体系,获得政治权力建构的文化基础。
通过探讨动物图像的功能,张光直提出古代中国构建政治权力的基本模式。他认为,世界范围内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型,主要通过“突破性”和“连续性”两种方式:“突破性”文明依靠人与自然关系的变革,通过生产技术创新和生产力提高,突破原始社会模式,如苏美尔文明凭借金属工具、贸易和文字等手段的普及,实现了向文明社会的过渡;“连续性”文明则依靠人与人关系的演进,延续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建构政治权力体系来实现发展,古代中国和玛雅文明都是这种类型的代表[11]140-141。在后一种形态中,生产力和技术没有显著提高,资源和文明的最初集聚依赖政治手段,主要包括强制力量、道德权威、对知识及通天途径的垄断和财富:
(1)强制力量是获得统治的物质基础。一般指军队和装备,青铜武器和战车是重要要素。
(2)道德权威一般通过祖先神话来塑造,统治者将祖先塑造成英雄形象,并将其写成神话乃至历史,在道德上获得民众的拥护,实现统治的合理化。
(3)对知识及通天途径的垄断凭借垄断文字、仪式和祭祀等要素,独占与神明和祖先的沟通方式,获得祖先的知识和上天赋予的权力。青铜礼器和神话图像作为祭祀的用具和通天媒介,是垄断的主要对象。
(4)财富也在权力建构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聚集财富是文明的体现,统治者通过树立政治权威来获取财富,又通过财富来保障和支持权力的正常使用。“权力和财富相互依靠,既抚育自我,又助长对方。”[11]102-103青铜器和神话图像作为稀缺资源和技术,是统治者财富、荣耀和权力的象征,在政治建构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与此同时,张光直认为具有“连续性”文明特征的古代中国与玛雅,组成了具有明显的萨满式特征文明共同体(连续体)。这一文明连续体具有类似的宇宙观:分层宇宙、贯通天地的神山或神树以及相应的方位[12]45-48。张光直还指出,“连续性”是文明演进的一般形式,西方的“突破性”则是特例[13]。这一观点既突破了社会科学领域的西方中心论思维,又可以对中国古代思维、观念、知识、信仰等多个领域中的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揭示了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这一观点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质疑。萧兵认为张光直过分借重萨满教机制来诠释中国上古文化,指出“帝使凤”和“虎食人卣”中的凤和虎并不是萨满教中助巫通天的“动物助手”,从而质疑“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合理性[4]。曲枫则认为张光直将不同地域文化、不同历史时期所发现的人物及动物美术图像均置于单一的人类学概念(即萨满教)之下,忽视了文献形成年代与考古现象之间的差距和变迁,其构建的“萨满式文明”及“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理论框架脆弱且问题丛生[14]。吾淳肯定了张光直构建的“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但也指出其用于引证“连续与突破”理论的例子——苏美尔文明——代表性不强[13]。
这些驳论指出了张光直理论的一些瑕疵,如引证文献不尽合理、图像理解偏于主观等,但无法从本质上动摇其理论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张光直的神话图像功能论,建立在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整体理解上,认为掌握政治体系和政治话语是保障统治的核心要素。在“国之大事,即祀与戎”的社会语境中,神话、文字等元素被统治者垄断和利用,成为政治建构的工具。神话的这一功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发展中被赋予并不断强化的。这种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模式的解读,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特征和群体心理,对帮助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二、商周神话的分类:内容分类法与神话的历史化
目前我国神话学被归入文学学科,但并不代表神话是文学的分支。事实上,神话研究并不能被置于某一个独立的学科内,文学家、人类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和神话学家都可以从自己的方向对神话进行解读和研究,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对神话有兴趣[7]288-289。从不同角度进行神话研究的学者,对神话分类的方式也大相径庭。文学研究主张神话从撰写和创造的视角分类:袁珂提出可分为“神仙神话、传说、历史、民间童话、宗教故事、风俗神话”[15]2-5等九个类别;王开元则认为针对中国神话的特点,可以从语言特点、地域、民族和历史阶段四个视角进行分类[16]。人类学研究则一般认为可从内容属性进行分类:茅盾认为神话分为“开天辟地神话、自然现象神话、起源神话、神明故事、冥界神话和英雄神话”[17]18-32;林惠祥提出神话可分为“开辟神话、自然神话、神怪神话、冥界神话、动植物神话、风俗神话、历史神话和英雄传奇”[18]3。
张光直的神话分类观主要见于《商周神话之分类》一文。进行分类之前,他阐述了自己选择神话的条件:“神话要有一个及以上超自然的、普通人无法做到的故事,但却是当时社会人群信以为真的事实或观念。”[7]289-290这种选择及界定神话的标准,带有明显的人类学色彩。在人类学家看来,神话不是一种虚构的叙事,而是神话产生的时代民众信以为真的准则,是一定时期社会文化与集体心理的折射。
由此,张光直提出了商周神话分类理论,即分为“自然神话、神仙世界的神话及其与人间世界分裂的神话、天灾的神话与救世的神话、祖先英雄世系的神话”[7]299-320四类:
(1)自然神话,主要包含自然世界神话和宇宙起源神话。自然世界神话指日月风云背后都有神灵,神灵操纵自然现象影响人间。这类神话在商周文献中零星出现,与中国社会的泛灵思想有一定渊源。宇宙起源神话有分离说和化生说两种,分离说属于世界父母型神话,指世界像细胞分裂一样,由混沌一步步分裂出来,伏羲女娲和盘古开天辟地便属于此类;化生说指世界由一个古代生物的身体部分衍生而来,是神话中比较个别的现象,在东周之前的文献从未出现,流传至今的内容也很少。
(2)神仙世界的神话及其与人间世界分裂的神话在商周时期经历了重要的演变。在早期神话中,人界与祖先神仙的世界可以互通,《尧典》《穆天子传》《山海经》中均有互通神话;随着时间推移互通变得越来越难,直至东周的重黎绝通天地神话后,人神沟通便只能仰仗巫觋,神仙世界成为了人的理想乐园。
(3)天灾的神话与救世的神话产生于第二种神话之后。人与神从最开始的难以沟通,成为了后来的相互敌对状态,产生了神界降灾、英雄救世的神话。刑天舞干戚、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便是这类神话。
(4)英雄世系神话一般是氏族诞生和英雄事迹神话。与前三种神话不同的是,英雄神话在古代中国广泛出现,主要因为许多自然神话被改编成英雄世系神话。
张光直神话分类论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提出了独特的分类方式,更重要的是其勾勒出了商周神话演变的过程。商代以氏族诞生和自然神话为主,神界与人界可以自由沟通,没有出现天灾与救世神话和宇宙起源神话;西周基本延续了商代的神话体系,但开始出现神界与人界分离,相互沟通变得越来越难;到了东周尤其是春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英雄世系神话,神界与人界彻底分离,同时出现了天灾的英雄救世神话。
在讨论英雄世系神话明显多于其他类型神话的原因时,张光直认为这与中国神话的历史化有关,许多人类英雄形象来源于自然精灵形象,英雄神话是由自然神话演变而来的[7]316。神话的历史化问题早在20世纪上半叶便形成了学术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茅盾的论述:“神话的历史化,固然也保存了相当的神话,但神话的历史化太早,便容易使得神话僵死。中国北部的神话,大概在商周之交已经历史化得很完备,神话的色彩大半褪落,只剩了《生民》《玄鸟》的感生故事。”[17]188许多学者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衍生的观点。张光直重提神话的历史化问题,并不是为了从历史中“还原”神话以丰富神话体,而是将这一问题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联系起来进行讨论。他提出中国古代尊崇“英雄既是祖先”的原则,为了歌颂氏族祖先的功德,从已有的自然神话中取材塑造氏族的英雄祖先故事。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古代政治地位以氏族分支为载体,更反映了文化的政治性与功利性。神话的历史化与神话建构政治权力的观点相互支撑,并与“连续性”文明政治权力建构的观点产生呼应。
三、商周神话的演变:人与动物关系反映政治文化的变迁
从商至周,青铜器神话图像中人与动物的关系经历了较大的转变。商代及周初神话图像中,动物表现出高昂且有力的形象,人形较罕见,且展示出明显的隶属性和被动性;周代中叶的神话动物呈现出呆板固定化的趋势,反映出神力衰减的现象;东周后期的神话动物的神性几乎完全消失,人类猎杀动物的图案开始出现。
对这一变化,杨宽认为主要是由于自然知识的普及和人文主义的兴起[19]179-180,持这一观点的考古学家不在少数。也有研究认为,神话演变与商周青铜器社会功能的变化有关。早期青铜器作为神圣的礼器,具有沟通天地的媒介作用,上绘严肃的巫术与宗教图案;春秋时期以后青铜器走下神坛,负载的政治、宗教意义弱化,上绘图案也愈加生活化[20]。但这种解读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很难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青铜器的社会象征意义有明显的减弱。相反,楚王问鼎的故事恰恰证明青铜礼器在周代末期仍具有相当的政治象征意义。其次,在中国古代文明中,人与人的关系即政治权力的建构始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即使原材料和冶炼工艺逐渐普及,但青铜器作为政治话语,其表述作用始终存在。
张光直认为,神话图像中动物外观的变化取决于动物所扮演角色的变化:早期的动物多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人对动物表现出亲密和敬畏的姿态;到了周代后期,神成为了人类的敌人,动物成为了神降祸于人的爪牙,产生了人与动物的猎杀与斗争。
张光直将神话图像的演变与商周时期的社会发展进行了比对分析。他指出,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亲族关系是古代政治地位的决定性因素,表现在殷商的神话体系中,帝是最高神明,也是商代统治氏族的祖先,统治者借此获得神明的权威;周亡商后,继承了商代神话体系,但切断了神界与人界的联系,不再有氏族是帝的后代,天命由帝授予有德之人,即西周统治氏族;到了东周末期,统治氏族不再垄断文化与知识,越来越多的氏族在财富、文化乃至军事上具有一定的实力,这些氏族开始尝试将自己的祖先传说纳入神话体系,将神明塑造为敌人,而将自己的氏族祖先作为拯救世界的英雄,借此挑战宗周的神明权威[7] 327-347,获得参与统治的合理性。
对神话演变与社会演变的关系问题,李炳海认为,原生神话向次生神话演变时,受到文化变迁和社会制度发展的影响,呈现出政治化和世俗化的倾向。政治化指“社会等级制的成熟驱使原来不相统格的神灵成为君和臣,原来不曾发生过冲突的神灵变成敌对的双方”;世俗化指社会进步能激发人欲望的发展,表现在神话中即“神灵从封闭状态中走出来,与世人日益接近,脱去恐怖的性质,人神之间的关系变得轻松”[21]。李炳海从另一个侧面解读了神话演变的契机和过程,但其与张光直的共性在于承认社会演变对神话的塑造作用。神话作为原始人民生活的心理状况的产物[11]3,能够准确地反映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神话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这也是人类学和神话学共同倡导的研究方向[22]。
四、结语
张光直的神话研究集中于神话功能、神话分类以及神话演变等方面。在神话功能方面,张光直认为神话及图像充当了通天媒介,建立政治话语,参与权力建构。以此为契机提出的“连续性”和“突破性”两种文明起源模式,对代表着“连续性”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建构基本方式进行了探讨。在神话分类方面,张光直从神话内容入手,将商周神话分为自然神话、神仙世界与人间世界分裂的神话、天灾与救世神话、祖先英雄世系神话。借由不同类别神话的数量差异,提出了神话的历史化问题,与“连续性”文明的观点相呼应。在神话演变方面,张光直分析了商周神话人与动物关系的演变,认为动物神力衰减与人的能力增强是主要趋势。同时将神话演变与政治文化的变迁结合起来,提出社会对神话的影响和塑造。
一些学者指出张光直神话理论的不足,其中“连续性”文明的学说受到了不少质疑与批评。但张光直立足于中国早期文明的特征,组建了代表着东方话语的“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不仅突破了西方学界对文明起源的刻板概念[23],更提出中国式文明才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对国内外神话学研究产生的影响是广泛且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