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话语、他者叙事与集体展演
——对于脱口秀节目《听姐说》的“话术”观察
□刘永昶
【导 读】本文将湖南广电最近的脱口秀节目《听姐说》视为“她综艺”的一个典型观察样本。《听姐说》的节目核心构成元素是“说”,“她说”成了最显豁的性别表达特征。其一,《听姐说》表现的实际上是一种暧昧的混杂的、在现实与传统中游移的“女性”话语。其二,作为发言者的姐姐们并不是《听姐说》中语言的真正拥有者。无论是焦虑的“身体”讨论,还是曲折的“戏剧”设计,都能够显现出他者叙事的控制力。其三,《听姐说》的“表演”与“言说”之边界是混淆的,这是当下娱乐生产场域的注意力经济使然。
作为“她综艺”的标志性产品,湖南广电《乘风破浪的姐姐》在2020年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在2021年《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能够继续保有较高的流量话题。此外,类似于《美丽俏佳人》《妈妈是超人》《妻子的浪漫旅行》等节目也从时尚、育儿、旅游等领域切入了“她综艺”的集体生产。研究者对于“她综艺”的崛起众说纷纭,大抵聚焦于两个向度:一是人们显然看到了当下综艺节目主体受众为女性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者的产品选择倾向,进而比较乐观地欢呼女性主义话语在今天的中国娱乐场域风生水起,显露锋芒;二是人们也能够注意到消费意识形态或者商业包装元素对这些综艺节目的制约,进而讨论这些作为流量担当的综艺节目女性参与者是否依然是被操纵和束缚的。
无论如何,构成“她综艺”节目形态的决定力量一定是多元复杂的。但大多数节目都有着斑斓多彩的视听表象——或载歌载舞,或悠游山水,或庭院笑谈。这对于观众而言,固然构成了强大的影像诱惑力,但难免对研究者的深入剖析带来阻碍。在这个层面,刚刚收官的湖南广电脱口秀节目《听姐说》不啻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样本。《听姐说》的节目核心构成元素是“说”,所有的参赛选手在一轮一轮的淘汰选拔中必须不停地展开演说,以获取现场观众的青睐与投票。换言之,《听姐说》其实是综艺节目“女性”文本的一次汇聚。尽管这档节目的社会影响并不如生产者的预期,但恰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为什么“说”不如“看”的观察角度。如果进一步探讨,她们在“说”什么?她们怎样“说”?到底是谁在“说”?或许能为当下的“她”综艺提供有力的文本分析视角。
一、传统与现代:游移的“女性”话语
甫一开播,《听姐说》就亮出了非同一般的女性节目姿态,它宣称要“以女性视角切入社会热点话题,以脱口秀的喜剧形式传达女性态度,展开一场Talk大战”。它邀请了18位小有名气的女性参加节目,现场的大众评审团成员都是女性,作为嘉宾出场的“懂姐团”成员也是女性——这使得现场唯一的脱口秀男主持人王自健显得“遗世而独立”。在这个性别偏差极大的节目舞台上,人们显然有理由期待听到来自“姐姐们”内心深处的真实声音。
詹金斯说:“我们的生活相互联系,回忆、梦想、愿望也穿梭流动在各种媒体传播渠道中。”[1]《听姐说》的媒介场域不仅属于现场的参与者,也属于关注这档节目的所有受众。如果受众是女性,她们很可能会在节目中体认自己的性别经验,进而投射基于自身经历的复杂情感;如果受众是男性,那么他们也需要从节目中更好地认知自己生活中的另一半,检验自己对于“她们”的想象。于是,“她说”成了《听姐说》这档综艺节目最显豁的性别表达特征。大约可以作为参照背景的是,20世纪初发轫的女权主义话语也正是以“她说”登上历史舞台的。西蒙·波伏娃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就指出:“一个人之所以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 ‘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2]由此,经典女权主义话语一直以觉醒与反思的“她说”来与“他说”判然分离。当然,我们并不能过于高估综艺节目中的“她说”。细而观之,《听姐说》各期节目设置的所有话题,一方面能够显现出一些女权主义话语的语态特点,但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当下社会语境的习惯认知。换言之,《听姐说》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暧昧的混杂的、在现实与传统中游移的“女性”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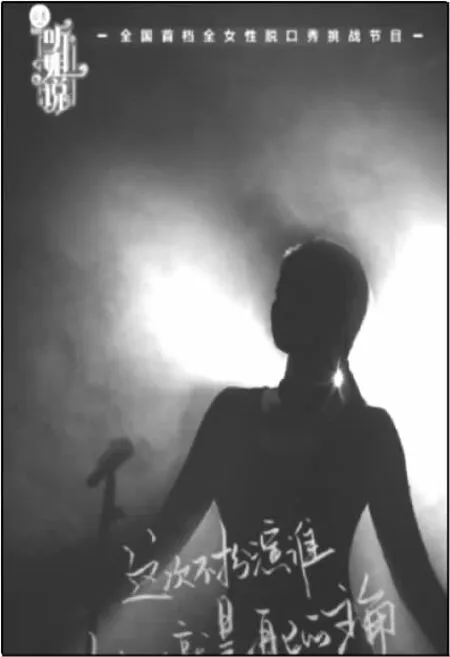
《听姐说》的脱口秀话题,大多采用命题或半命题式,这既是为了让“选手”们的表述聚焦,也是为了在同一起跑线的对比中凸显竞争。有意思的是,类似于“……这句话太可笑了”“……竟是我自己”“像我这样的女人……”“我不理解……”不少期节目的话题句式虽然都是半开放的,却有着显而易见的转折、否定或疑问语气嵌入。看起来,“转折”是在表达不同的理解,“否定”是在澄清应然的认识,“疑问”是在抛出可能的辩驳。这时,脱口秀话题设置的导向是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它们或许希望引导话语场的氛围,让脱口秀的话锋变得更加犀利,并能体现出独树一帜的女性独立思考。
相当多的节目现场表述的确是可以让现场和屏幕前的女性听众振奋的。热依扎说:“看穿一切的竟是我。”徐冬冬说:“成为一种美女,为什么是一种要求?”“就算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又怎样?”张蓝心说“像我这样的女人,永远热血沸腾”,石璐说“像我这样的女人,一直奔跑”,傅首尔说“以‘白、瘦、幼’为标准真是太可笑了”;作为特邀嘉宾的杨澜也质疑“不理解为什么叫‘女人样’”,呼喊“性别不应该限制我们任何人对于未来的想象力”。在总决赛总结陈词时,嘉宾思文直言“希望每个人有选择的自由,也有免于被他人干涉的自由”。这样的发言姿态无疑折射了当下中国社会女性地位大大跃升的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提升让她们越来越趋于独立,越来越有自己的思想,越来越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
但进一步分析人们会发现,这些话题依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或者说,话题更多呈现出的是外在的激进姿态,而具体内容则很难摆脱传统的女性定位。女权主义批评常常把这种“传统”的固化归因于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比如,盖耶·塔奇曼就指出了广告的性别偏见问题:“它们迅速将女性刻板模式化。在对女性的刻画中,广告将女性放逐为家庭主妇、母亲、操持家务者或性对象,并限制女性在社会中发挥作用。”[3]显然,女性在通常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数社会领域一展身手或者与男性并驾齐驱,是女权主义者的理想愿景。但在《听姐说》中,演讲者的具体内容涉及面基本在个人生活的私域止步不前,关于家长里短、关于儿女情长往往成了她们“脱口秀”文字里最多的关键词句。比如,在第一期节目所有演讲者的亮相演说中,应采儿就宣称“我是陈小春的老婆,小小春的妈妈,姐的代表作是家庭”;石璐讲述单亲妈妈带孩子的心酸日常,要“潇洒活出自己”;热依扎将女儿比喻为自己的作品,“为女儿傻得心甘情愿”。
当然,参加《听姐说》节目的18位“姐姐”身份是单调的,她们是歌手、演员或主持人——唯一稍有不同的是张蓝心,她当演员出道前还曾经是跆拳道冠军。这样的脱口秀阵容有着结构性缺陷,她们不能总是拿演艺圈的八卦开涮,那样节目就会变成搞笑版的艺人吐槽大会;她们的跨领域社会经验也并不多,因此长篇大论对社会议题发言又会显得华而不实。所以,最终她们的话题只能大量地向内转,转向个人化的日常生活体验。节目编导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刻意设计了命名为“懂姐团”的嘉宾阵容。除了杨澜、金星、邓亚萍这样的文体公众人物外,懂姐团的大多数成员是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如宋玺(亚丁湾护航唯一女陆战队员)、吴思容(抗疫女漫画师)、徐颖(中科院北斗导航系统女科学家)、苏锐(精密机械员)、李箐箐(长沙戒毒所民警)、张巍婷(海兴县张常丰村第一书记)、梁辰(湖南大学博士后)、李里涓子(长沙市律协女专委主任)、徐逸岑(金融投研工作者)、任晓媛(麻省理工女科学家)、尹华(全国三八红旗手)等。
“懂姐团”代表着生机勃勃的新时代女性形象,但她们未必真的懂姐。她们与文娱明星的身份反差太大,以至于很多场合只能起帮衬和呼应的作用。事实上,这些杰出女性的个人话题如果开掘起来会很有深度,但她们既然是作为平衡性的配角出现,节目组就不太可能让她们喧宾夺主。况且,她们多数人既不巧舌如簧,也不善于在镜头前展示。她们在“懂姐说”的节目舞台上,和话题设置的形式一起,构成了所谓“现代”的玻璃瓶,但瓶子里面晃动着的仍是“老酒”。
二、植入与设定:自我呈现中的“他者”叙事
《听姐说》的演说主体当然是18位轮番上场的“姐姐”,但不管是从电视节目的通常生产机制来衡量,还是从节目传播过程中透露的编剧角色来判断,参赛选手大体上会有着不断为她们量身定做文字内容的幕后帮手。福柯在讨论语义表现结构时曾精辟地发问:“谁在说话?在所有说话个体的总体中,谁有充分理由使用这种类型的语言?谁是这种语言的拥有者?谁从这个拥有者那里接受他的特殊性及其特权地位?”[4]非常明显,作为发言者的姐姐们并不是《听姐说》中语言的真正拥有者。从表述模式和文字逻辑来说,不同“姐姐”的发言其实有着语义结构上的很多相似之处,以至于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演说稿看成一个大的叙事文本。之于这个集合文本,那个极有控制力的节目叙事者以及它的类型化叙事是值得深入讨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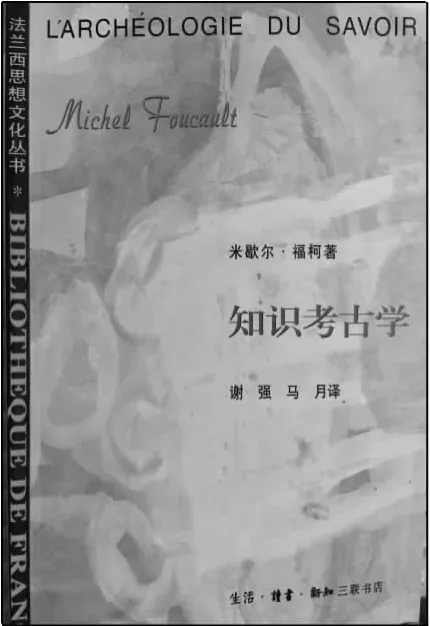
其一是具象化的“身体”叙事。“身体”是几乎贯穿所有节目场次的关键词——姐姐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身体”焦虑。张蓝心由于个子太高,在拍戏中出现许多啼笑皆非的故事;金铭可能没有长成大家希望的样子,但“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徐冬冬拍椰汁广告有身材的困惑,“穿什么都会被人讲博眼球”;倪虹洁拍摄内衣广告,一开始尴尬与害羞,之后自信大方,“敢于展示自己的形体美”;玲花告诉人们,她成为一个美女是因为坚持瘦脸和减肥健身,“成为一个美女,就是坚持的一个过程”;锤娜丽莎因为生病吃药变胖,减肥不见成效,最终接受了自己的样貌;沈梦辰谈起过度生活焦虑带来难堪的斑秃。尽管这些文本中都会有一些反对“身体化”女性的叙述,但过多地流连纠结于“身体”话题,无疑暗藏了“身体”意识形态的普适意义。比如,王子文在“给65斤王子文的一封信”的演讲中,一方面吐槽A4腰、漫画腿、马甲线、反手摸肚脐、锁骨放硬币、胯骨养金鱼等畸形身体审美标准,另一方面又不无自信地称:“我希望你们不要学我。演员需要在生活中很瘦,在镜头里看起来才刚好。”事实上,《听姐说》采纳大规模“身体”叙事的原因恰恰在于:这些姐姐们的身体形态即便不是完美的,也普遍在人们传统认知标准的上限区间。她们的身体形态和身体讨论之间构成了颇有诱惑力的互文关系。
其二是戏剧化的“挫折”叙事。布尔迪厄在讨论电视的戏剧化手段时指出:“它将某一事件搬上荧屏制造影像。同时夸大其重要性、严重性、戏剧性及悲剧性的特征。”[5]《听姐说》与其他类型综艺节目相比,要将脱口秀场景戏剧化的能力是先天不足的。于是在安排姐姐们“叙事”时,节目努力插入戏剧化的桥段,并且使之表现出明显的略带悲情的“挫折”叙事特征。演艺事业的“挫折”最为常见,这些参与节目的明星已经不是正当年的一线红人——她们来到节目现场很难说没有提升个人流量的考虑。因此,她们的舞台倾诉顺理成章地成为常态。尚雯婕谈自己的社交恐惧,玲花谈自己的“歌红人不红”,王菊自嘲不断被网友黑,阚清子说自己考试、做演员的种种失败,鄂靖文调侃自己不会交际的苦头,张蓝心分享自己找工作的失败经历,金铭苦恼自己撕不下童星的标签,沈梦辰谈“因为自己害怕失败,怕浪费每一次展现的机会”。此外,爱情的“挫折”也大量被提及,金铭吐槽自己交往过的奇葩前任,幸而能够止损;莫小奇讽刺限制自己的“渣男”,告诫大家“与其美化对方,不如修炼自己”;王菊检讨自己爱情“戏精”上身,反讽前男友对自己行为的揣测和限制;石璐讲述与前夫的故事,表示“不值得为浪子浪费时间”;徐冬冬讲述在生活中、事业上被前任的无理要求捆绑甚至被家暴,最终“离开他我照样立得住”。
无论是焦虑的“身体”讨论,还是曲折的“戏剧”设计,都能够显现出节目叙事者的用心良苦。这个叙事者搭建了一个叠沓互文的元叙事框架,将所有看似独立的个人脱口秀叙事文本编织串联起来。约翰·斯道雷指出:“元叙事故事通过包含与排斥来发挥作用,把杂乱无章的世界整顿成井然有序的王国;以普遍的原则和共同目标的名义压制和排斥其他理论和其他声音。”[6]《听姐说》的元叙事没有摆脱当下社会娱乐产业的叙事成规,它一方面通过诉诸情感的戏剧化故事博取观众的共鸣——观众们快餐式的情感宣泄与消费正是文化工业流水线的畅销产品;另一方面通过女性身体的话题讨论吸引观众的目光。有意思的是,尽管《听姐说》的主要受众是女性,但打量身体的凝视目光依然是属于男性的“他们”。正如20世纪初很多女权主义者所发现的那样,历史(History)的讲述秘密其实一直隐藏在“His”这个通常不为人所注意的词缀中。
三、言说与表演:注意力经济的舞台游戏
《听姐说》的市场反响并不如节目策划者的预期,更别说能够借《乘风破浪的姐姐》的东风再创辉煌。观众们的抱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姐姐们的脱口秀能力,她们在现场频频“忘词”“冷场”的事故反倒成为网上讨论的热点;二是关于幕后“编剧”的痕迹,他者叙事在很多情况下让姐姐们成了舞台上的提线木偶。观众们的吐槽直接点出了《听姐说》的节目定位、编排、人员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众所周知,脱口秀节目从国外舶来国内,很快成为综艺节目特立独行的一种类型,其魅力主要在于思想与言说。广受欢迎的脱口秀内容往往绵里藏针,对现实有观察、有思考也有批判,其通常表现出的幽默、讽刺风格看似轻松,但内涵深刻甚至沉重。如前所述,参加节目的姐姐们原本的身份定位都是“艺人”,她们极为擅长的是经营多年的各种“表演”,那么相对高要求的脱口秀对她们而言显然是勉为其难了。
《听姐说》的节目编导更需要的恰恰就是“表演”——在节目工作人员的名单中,“表演指导”岗位赫然在列。“戏剧表演需要把常规程序的口头内容详尽地改编为演出脚本,但是,绝大部分涉及‘流露出来的表达’的表演,经常是由贫乏的舞台指示决定的。可以预料,给人以错觉的表演者对怎样操纵他的讲话声、他的脸部和他的躯体总是已经知道得很多。”[7]戈夫曼对于“表演”操控性的论述非常适于用来解释《听姐说》的台前幕后。一方面,“演出脚本”框定了包括主持人、姐姐们、嘉宾、观众在内的所有现场人员之情景表现;另一方面,“舞台指示”又不断地指定并强化表演者的戏剧性行为,以期激发场内外的情绪反应。“表演”直接诉诸受众的感官,它与直接诉诸受众大脑的“言说”相比,传播心理机制大不相同。《听姐说》的“言说”是节目宣称的创新亮点,但节目更愿意的是请来姐姐们进行足够卖力的“表演”。节目策划者当然明白,“表演”的好看一定有助于节目的好看。这不仅是芒果娱乐最轻车熟路的技术活,也是今天注意力经济驱使下的综艺节目普遍的编导法则。
尽管通常脱口秀节目要求演讲者着正装,以衬托知识气和思想力,但在《听姐说》中,金属风、水墨风、复古风、职场风、都市风的服饰还是伴随着姐姐们的“表演”轮番上场——有好事的网友甚至据此条分缕析出美丽时尚指南。在正式的演讲之外或之中,观众们可以看到被称为“花絮”的诸多情景,比如,张凯丽戴着墨镜在脱口秀即将结束的时候唱起了rap,其他姐姐立即会意上台热场;黄小蕾可以突然横卧在舞台上,半带娇嗔半带霸气;王子文聊起曾经做女团的经历,现场大秀女团舞姿;沈梦辰自称是节目中花活最多的姐姐,大胆表演“口吞大火”,刹那间将火焰变成了一枝玫瑰花;张蓝心谈起初恋脸红害羞,但话风一转又深情朗诵起了自己给初恋男友写的情诗。当然,姐姐们的这些“表演”是插科打诨,并不是脱口秀节目的主体内容。不过,在配合节目播出的网络推广营销中,这些场景却大多被写手抽象提炼为软文和短视频的标签。因为他们知道,“表演”不仅仅是姐姐们的特长所在,也更能集聚观众们的视线。
个人表演是插曲,集体表演才是主调。《听姐说》将18位姐姐/演员纳入了一个非常曲折且“残酷”的竞争情境中,让每个人内心都充满获胜或“求生”的欲望——某种意义上,它让脱口秀变成了真人秀。且看《听姐说》令人眼花缭乱的比赛轮次及规则设计,《听姐说》短短3个月12期的节目竟然被分为7个轮次。第一轮是集体展示并由观众投票确定初步排名,选手们根据排名选择话题并互选对手。第二轮是两两对决,有9位选手胜出,另9位选手落入待定席。第三轮是晋级名额争夺赛,从待定的9位选手中晋级6位,淘汰3位。第四轮是所谓的大魔王试炼赛,晋级的15位选手自选话题组成3支队伍,每队挑战一位大魔王——懂姐团的一位嘉宾,胜者全部晋级,反之全部待定。第五轮是晋级名额淘汰赛,待定的两队进行比拼,双方轮番进行一对一对战,根据五局三胜的原则,获胜的一队将获得2个晋级名额,剩余的淘汰5人。第六轮是半决赛,采取辩论赛形式,晋级的10位选手分成5组,围绕5个话题选择正反方,胜利者直接晋级,失败者进入卡位区。最后一轮的决赛更是细分排位战、抢位赛,所有人演讲结束后守住位置的选手即为总冠军。
很显然,节目生产者已经将几乎所有娱乐节目的赛制规则混用在《听姐说》中。无论是面对面的激烈对抗,还是团队之间的合纵连横;无论是生死一线的紧张挣扎,还是未知结果的复活营救,节目始终试图营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极端戏剧情境。对于姐姐们而言,这时她们开怀的欢笑、悲伤的泪水、洒脱的身姿或黯然的背影,都会成为镜头捕捉的对象,并且往往还会通过生动的机位和刻意的剪辑被聚焦、定格、放大。对于观众们而言,他们原本聚集在脱口秀文本中的注意力,就会被转移到对姐姐们个人在节目场域命运的关心与担忧,这时他们感知的重点就不再是“听”姐说,而是“看”姐说。总想从节目内容中有所收获甚至被启发的观众们难免会失望,但习惯于综艺节目表达方式的观众们则不会太在意。《听姐说》本质上就是一个脱口秀的舞台游戏,节目生产者其实和舞台背后的广告商一样,他们的关注重心并不在于话语的启蒙,而是更在于围绕话语的流量。有论者指出,当下综艺节目“点燃大众‘嗨点’的做法,虽然有流量,却大大折损了用户好感度,也给节目长远的口碑维系增加了变数”[8]。《听姐说》的“话术”及其反响正是一面多棱镜,值得跃跃欲试的业界跟风者镜鉴与反思。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批评研究”(19ZDA269)、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移动短视频生产的形态、审美及规制研究”(20XWB00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杜永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48.
[2][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23.
[3]转引自[美]盖耶·塔奇曼.大众媒介对妇女采取的符号灭绝[A].收录于[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英]克里斯·纽博尔德.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M].汪凯,刘晓红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505.
[4][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62.
[5][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许钧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8.
[6][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8.
[7][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黄爱华,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69.
[8]杨乘虎,林沛.并置与拓展:深融视阈下的2020年中国综艺节目盘点[J].中国电视,2021(04):1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