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重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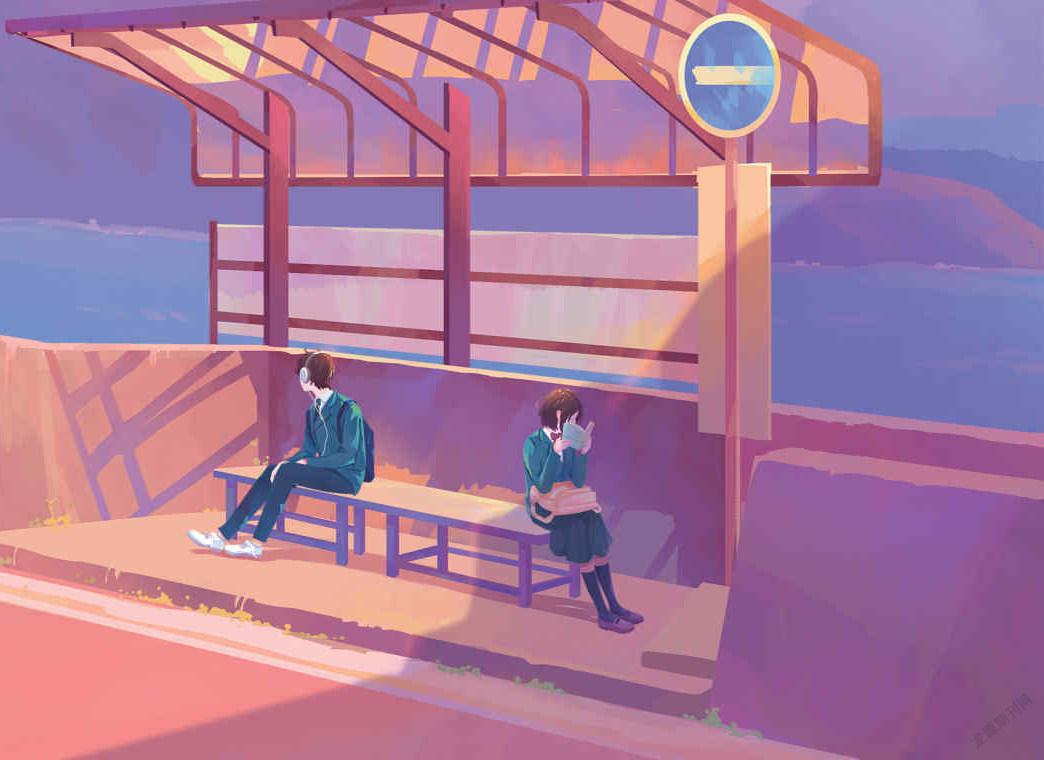
新浪微博|大黄米粒321
01
很偶然的一个时间,向晚从小助理那里得知了最近流行的“土味表白”方式。
小助理刚大学毕业,新潮另类又精力无限,白天八小时工作赚三百块,晚上夜场三小时花光,让向晚忍不住就心生感慨。果然说年轻人爱穷折腾,估计就是越折腾越穷的意思。
但人家自我感觉精神特富有,对还没过三十岁生日便老气横秋的向晚也颇为同情,为了不让她被时代抛弃,时不时就给她普及现下流行的东西。
于是她知道了若干条语句不通的土味情话,穿新衣服的时候不摘吊牌很酷,还有很多她连歌名都听不懂的流行歌。然后今天,小助理兴冲冲地给她介绍了最近很火热的告白方式。
准备一张手绘的地图,男生把约会过的地方一一在地图上标注出来,每一处都画上女孩子小小的头像,嬉笑怒骂各种表情,然后这些点连成线,汇成面,最终成了一个大大的爱心形状。
小助理说:“这代表着呀,我的爱可以陪你走到天涯海角。是不是很新潮呀……向晚姐?”
向晚愣愣地盯着面前的这份手绘地图,没动,也没说话。
“你……你怎么哭了啊?”
向晚茫然地抬起头,有什么东西掉落在A4纸上,发出清脆的“啪嗒”声,确实像极了眼泪的声音。
02
向晚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都发生在八岁之前。那时她跟随年迈的外婆住在偏远的乡下,田间、地头、春草池塘都是她的游乐园,夏日有蝉鸣,冬日有霜花,广阔天地给了她肆无忌惮的快乐和自信。外婆赶在民国的尾巴出生,小时跟着私塾先生认真地学过国学和国画,手把手教她画的那幅叫作“园柳变鸣禽”的国画,获得了小学组绘画比赛的一等奖。
奖品是一只印着美少女战士的粉色铅笔盒。记忆中,那天特别热,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却丝毫不妨碍向晚对着镜头笑出豁了两个大黑洞的大门牙。
后来那门牙长齐了,向晚却再也没那么笑过。那一年她被父母接回家,家中还有个大她三岁的姐姐。外婆给她穿了最好看的桃红色连衣裙和粉色带亮片的凉鞋,可站在狭小的客厅里,她仍是觉得手脚拘束,无所适从。
她想起临行前外婆对她的嘱托,要她一定要乖,要有礼貌,于是她咧开嘴,给了母亲一个很大的笑容。
母亲当时一愣,转头跟父亲交换了一个既无奈又嫌弃的眼神,随即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告诉她:“女孩子不要咧开大嘴笑,不好看。”
她瞬间红了脸,赶紧闭上了嘴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无论别人怎么逗她,她都只管抿着嘴巴笑。半夜起床去厕所的时候路过父母的卧室,她听见他们正在里面小声讨论:“到底不是看在身边长大的,总觉得不亲,笑容都是干干巴巴的讨人嫌。”
她愣愣地站在黑暗里,不懂自己为什么开口笑很丑,闭嘴笑也讨人嫌。她在乡下长大的这许多年,从来不知道原来笑也是件这么难的事。
她那时还太小,不懂得在这世上,不管你笑不笑,其实都不是别人喜欢或者讨厌的原因。
那天她记不清在黑暗里站了多久,只记得原本她是要去上厕所,最后却硬生生尿了床,换来母亲很长一顿时间的冷嘲热讽,言语之间埋怨外婆疏于教育,把孩子养得一无是处。
于是她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埋怨中,長成了不爱笑,不爱闹,有点儿孤僻的姑娘。尽管到高中的时候她的成绩可以稳居年级前三名,在班里人缘也算不上好。
这就导致学校组织板报比赛的时候,明明老师安排了她主画,几个同学协助,可放学铃一响,教室里就只剩下了她自己。
向晚是孤独惯了的人,倒是没觉得有什么。只是黑板有些高,颜料桶又沉,因此她不得不爬上爬下蘸颜料,累不说,还耽误时间,只画了一个整体框架之后天便有些黑了。室内昏暗,她从桌子上爬下来想去开灯,却一脚踏进了粉色的颜料桶里。
黑色的大棉鞋瞬间被浸湿,向晚用几秒钟思考了一会儿完不成板报和鞋子恢复不了原样的两种后果,最终决定两害相权选其轻,立即回家刷鞋子。
泡了水的棉鞋很沉,向晚踢踢踏踏地走在楼道里,四下很静,便把她走路的声音衬得很大,撞在墙上有了回音之后此起彼伏,黑暗里竟然走出了你追我赶的错觉。向晚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身后传来那声“哎”的时候,她猛一回头,差点儿尖叫出声。
身后的人显然被她吓了一跳,“啪”地按开了墙上的开关,霎时间整个走廊变得雪亮,向晚这才看清对面站着的穿校服,背斜肩包的少年,对方正满脸惊讶地看着她。
是周彻,跟她同班了半年却从未打过招呼的同学。
“你怎么这副表情?”他看着她,突然就略带戏谑地笑了笑,“哟,步步生莲啊。”
向晚这才看见,颜料印在鞋底,在走廊里留下了一长串粉色的印迹,因了鞋底的花纹深刻,远远看上去,倒真有些像一排盛开的绯红莲花。
她忍不住惊叹一声,又想起刚才被自己的脚步声吓到的傻样子,忍不住就抿嘴笑了笑。
灯光明亮,走廊寂静,外面无星也无月。
周彻突然间挑眉,伸出双手在半空中用拇指和食指比了个镜框的形状:“咔嚓,拍照留念。向晚,原来你笑起来挺好看的,你应该多笑一笑。”
他语气诚恳,向晚却瞬时变了脸色,冷冷地丢下一句“幼稚”,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周彻愣愣地看着她疾步离开的背影和一步步盛开在她身后的花朵。那背影瘦削单薄,却挺得笔直,在这空旷的走廊里渐行渐远,莫名走出了一种奇异的悲壮感。
03
很多年以后,向晚从记忆中翻捡出当初的那段时光,才终于能正视它,其实一切有迹可循。
班里共有四十六个人,向晚虽然因为记忆力好,能记住所有人的名字,但也仅当它们都是无意义的符号而已,有几个特别加粗的符号,周彻算是其中之一。
原因无他,向晚曾对着成绩单分析过每个人的成绩,发现周彻的成绩虽然始终排在中游,但地理学得非常好,几乎每次都是满分。
把一件事情做好可以靠努力,但每次都能达到完美的地步,她更倾向于是天赋使然。
天赋对普通人来讲,可望不可即,尤其是如周彻这般可以把校服穿成潮服的男生,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跟她这样不合群的人,更是天然隔了一道屏障。
所以隔天晚上向晚拎着颜料桶站在桌子上画板报的时候,一眼瞥见教室门口站着的人影时,差点儿把手里的桶扔出去。
“你站在那里干吗?”
周彻被她的表情逗笑:“看看你今天还会不会脚踩莲花。”
向晚觉得他简直无聊至极,毫不掩饰地翻了个白眼,手下画个不停。
周彻斜倚着门框抱臂看了半晌,突然冒出来一句:“你画的是宿锦镇?”
板报没有限定题材,向晚干脆就画了自己最擅长的,她幼时离开外婆家后,曾无数次把记忆中推开门就能看见的云山远雾、小桥流水落在纸上,白纸黑墨,似乎都能听见画里外婆走在青石板路上的脚步声。
但从无人关心她画的画,母亲对此做出过的唯一评价就是:不知道整天窝在屋里画些什么东西。
此时此刻,却有人一眼看出,这黑板上徐徐铺开的画面,是她心心念念的宿锦。
周彻走了几步上前:“你看啊,你画的这块花岗岩石头,角部受三个方向的风化,而棱与角逐渐被缩减,最终趋于球型,典型的球状风化。面前这条石板路,呈西高东西低,仔细看能发现西部背阴面长出了典型的簇状苔藓。远处这座山有一部分呈黄色,是一种呈发霉状的乔利橘色藻,都是属于宿锦的地理标志。”
向晚极力压制,也没能压住惊讶和羡慕的眼神。
或许又不全是惊讶和羡慕。
周彻一脸得意地看着她,得意完了才笑道:“关键是,你画的这是双拱桥啊,宿锦镇的标志性建筑物,我前段时间刚去拍照采风。”
向晚问道:“采风?你拍过很多照片吗?”
周彻从随身斜跨的背包里拿出一本厚厚的相册,翻了一会儿后递给她:“喏,在这里。”
那是一张雾化处理过的彩色照片,拍的是清晨时的宿锦,尚未散发出暖意的太阳斜照着双拱桥,与水面上波光粼粼的倒影交相辉映,静静地等待着日出日落,岁月更迭。
向晚的手指在上面细细摩挲,一直抚摸到照片的最边角,那里有一座静悄悄的农家小院,桐木色的双开大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其中公狮子威风凛凛的爪子上,用水彩笔画着一只小小的,可爱的猫。
向晚唰一下红了眼眶,半晌才抬头不好意思地看了周彻一眼,掩饰道:“很漂亮,你拍得很漂亮。”
对方冲她粲然一笑。
他笑得眉眼弯弯,唇红齿白,向晚突然就失了神。在她生活的世界里,父亲常年冷漠,跟她说话的次数屈指可数,周边邻居家几个大她几岁的男孩子,最常做的事便是揪她辫子,嘲笑她是乡下野孩子。
她从未见过哪一个男孩子,笑得和此刻窗外即将湮灭的霞光这般温柔。
成年后的向晚曾细细追溯十六岁时的那一段时光,当大幕拉开,光束打亮,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轮番上场,那么奏响第一声音符的,便是那张雾化了的照片和这抹如春日暖阳般的笑容。
从此音符跳动不止,她的眼睛和她的心一起,全都随之乱了节奏。
04
向晚是在很久之后才明白,很多時候我们管不住自己的心,都是从管不住自己的眼睛开始的。
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又欣赏过很多次周彻的摄影集。有逆光拍摄出的满是晶莹裂纹的冰面,有风雨欲来时茫茫原野里一棵孤独伫立的胡杨树,有在长白山山顶拍摄的漫天银紫色星辰,也有在偏远小镇随手拍摄下来的袅袅炊烟。
摄影集的扉页上写着一句话:“我们都是广阔空间里的流浪者,漫长岁月中的旅行家。”
这句话让向晚感慨且羡慕。她十六岁的人生中,只有前八年是真正恣意快乐的,在这精彩的人生旅途中感受世界的美,而这漫长的后八年,她只是在拼尽全力地奔跑,为了和外婆越来越少的团聚,母亲虚无缥缈的微笑,父亲惜字如金的夸奖,一直拼命地朝前跑着,跑向一个她自己都看不清的目的地。
所以她无比羡慕,有人可以在这岁月长河中肆意徜徉,一路朝着心中光。
周彻冲着她眨眨眼睛,随手抽过桌子上的练习册,蓝色的钢笔在纸上勾勾画画,不一会一张简版的中国地图跃然纸上。
“这里……是我已经去过的地方,接下来还要去这里……”他把每个地点都串联成线,呈现出的是类似四分之一个心形,“哇,看样子接下来我可以慢慢选择,直至走出一整颗心的形状?”
向晚失笑:“你们男生也会做这种无聊的事吗?”
对方看她一眼,慢吞吞地说道:“无聊吗?如果是和你一起去的话……我觉得还好。”
向晚讶然抬头,撞进对方明亮的眼眸里,她几乎是本能地躲避了那目光,假装全部注意力都在这张地图上:“我?我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原因不言而喻啊,向晚想。像她这样的人啊,似乎从出生起就不被期盼和喜欢,她这般努力,也不过是为了有朝一日,站在人海里可以同大家一样,面目平和,眼里既没有敏感,也没有卑怯。
这世上有人星夜赶考,有人天亮辞官,有人看山河锦绣,有人已满目疮痍,每个人都在既定的人生路上朝着终点奔跑,她从未奢想过去偷窥别人路上的风景。
但现在有人站在远山云雾里冲她伸出手来,递给了她一张色彩绚丽的邀请函。
她似在这一瞬间,终于闻见了花香。
向晚记得很清楚,那是二零一零年的春天,正是倒春寒天气,傍晚放学后的校园里空无一人,北风吹得一小股尘土在地上打着空旋,犹如跳着欢快的舞蹈。
日子过得很快,天气似乎还没来得及热起来,高考就结束了,向晚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见到了周彻。
他们选了同一座城市的不同学校,向晚选了金融贸易,周彻毫无疑问地选了地理摄影。等待着开学的漫长暑假,周彻向她发出了一起去桂林的邀请。
桂林,那里有三山二洞,两江四湖,最重要的是有个蝴蝶谷,相传是梁山伯、祝英台化蝶后曾栖身的地方,他们死后就地化成两座连绵的山日夜相望,情侣到此地虔诚许愿,此生便能“相看两不厌”。
传说美得动人心魄,但再美也美不过此刻他眼睛里的光,向晚迎着这样璀璨的目光,毫不迟疑地点了头。
她终于敢伸出手接过那张邀请函,准备和他一起启程。
可惜这旅途道阻且长。向晚在烧烤摊做了整整三十天的暑假工,每日忙到凌晨,老板共给她结了两千八百块钱工资,她把那一沓红钞票数了又数,小心地放进了天蓝色的印着小浪花图案的信封里,然后锁进了抽屉。
这些钱她准备交给周彻统一支配,虽然不多,也许不够,但是她也准备把这一路上的衣食住行,雨雪风霜,全权托付给他,如同交付了可以用衣食住行概括的往后余生。
她做了一夜的好梦,起得都比平时稍稍迟一点儿,不过是出门倒了个垃圾,再回来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桌面上干瘪的天蓝色信封。
它孤零零、惨凄凄地躺在那里。
自八岁之后,她习惯了在这个家里充当无声无语的透明人,尖利的哭腔冲出来的时候,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母亲挎了包正准备去打麻将,闻声先是诧异,接着是愤怒:“你姐姐要买电脑,家里现金不够,先拿来用用怎么了?你鬼哭狼嚎什么?”
向晚不想计较为什么姐姐可以随便买电脑,不想计较落了锁的抽屉被撬开怎么能叫作“拿”,也不想计较姐姐明知道她每天对着桂林的宣传彩页傻笑,却嗤之以鼻,她现在只有一个念头——无论用什么交换都可以,把她的钱还给她。
那是她即将开始的所有快乐和希冀。
但这唯一的念头,也在母亲的尖利叫声中戛然而止了:“什么是你的?你这些年吃的、喝的哪样不是我的?”
那天的很多事情在向晚的印象中都有些模糊了。她记不清当时是怎么站到周彻面前的,却记得那天的周彻穿白T恤、运动鞋,背着双肩包和单反相机,笑容爽朗。
她也记不清自己的心情,到底是愤怒多一些,还是悲伤占了上风。
甚至记不清火车站那扇破旧的褚红色木门上,四方的窗框里透出的天空,颜色是灰还是蓝。
但向晚清楚地记得,她当时找的理由是“桂林太远了,家里人担心安全”。周彻脸上难掩失望,却也表示理解:“你是个女孩子,家里人担心是正常的。”
向晚扯出一个很大的笑容,心底有一股飓风平地而起。很多年后再重新审视这个场景,她才终于敢承认,这飓风的名字叫作自惭形秽。
她未曾了解过周彻的成长经历和背景,却无比清晰地知道,能拍出山河日月万般颜色的人,一定是始终站在光里的。
越是胆小的人越会描述自己走过的最黑的路,越是薄情的人越会在人群中流下感同身受的泪水,每个人都有一根深藏于心的软肋,轻易不能示人,尤其是在乎的人。
于是她不由自主地在他面前编织了一件盔甲,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外出旅行都会被父母担心和制止的十八岁的普通女生。
她原来是从这一刻开始,就把彼此放在人生的天平上称量,她沉重些,他轻盈些,于是他站在稍高点儿的半空中俯视着她,而她若想和他站到同样的高度同他平视,需要脱掉很多层叫作“胆小”“逞强”“谎言”的外皮。
可若是脱掉了,她便再也没有正视他的勇气。
05
向晚收到的第十七张照片,是周彻在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湖,被世人称作“天空之境”的地方,满屏皆是流淌着的璀璨银河,浩浩汤汤,漫无边际,他在照片的左下角用羽白色的墨水写着:
“乌尤尼在波特尔暗空分类中属于1级,即天空完全黑暗,用肉眼便可见至少7000颗星星,再加上湖面倒影,便是14000颗,其中没有一颗是你,可又觉得,哪一颗都是你。”
彼时向晚已经大学毕业半年有余,向晚在一家连锁日化企业做销售,租住了一间很小的出租房,不足三十平方,靠窗的一面墙挂满了照片,最显眼处挂着的那张,是清晨薄雾笼罩着的宿锦镇。
紧靠着它的是十八岁那年的桂林,他拍了峰顶孤独伫立的一只蝴蝶。并列着的还有霞浦的滩涂、东江的漫雾、喀纳斯的冰川和巴丹吉林的沙漠,一张相片仅占180平方厘米,却慢慢地铺满了整面墙。
那面墙的正中间,挂着一幅手绘中国地图,纸张已经泛黄发脆,当年周彻在上面涂涂改改的痕迹还在,每收到一张照片,她就在上面画上点,连点成线,如今图上已經隐约有了半个心形的弧度。
可这十七张照片,十七趟旅途,向晚只参与过三次。一次是在大二的下学期,大西北下了经年未见的大雪,他们一起去了巴丹吉林沙漠的达格图湖。大自然造物不拘一格,在广袤的沙漠和戈壁中隐藏了一片粉红色的湖泊,苍茫和浪漫交织出了一种奇异的美。抵达时已是夜幕降临,向晚甚至来不及发出惊叹声,就听见身后周彻说道:“一路上还没听你报平安呢,大冷天的跟我到荒漠里来,妈妈该心疼坏了。”
跟父母的上一次通话是在两个月前,半夜十点多了,向晚看到来电显示的时候颇有些意外,还以为是外婆出了什么事情。
幸好不是。母亲不过是问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刚才打麻将听你韩姨说,她家闺女每月生活费要一千块,我怎么记得你很久没要过生活费了。”
她刚做完家教,正奋力蹬着单车往回赶,只简短地回了一句:“我有打工,不用。”
那边“哦”了一声:“家里也不是差你这点儿钱。”
是不差钱,可从来没有哪个月记得按时打过来,也从来没有哪次在电话里稍微关心一下她的近况,甚至连她足足两个月没要过生活费了,母亲还是经别人提醒才想起自己还有个上大学的女儿。
她没有将这次的出行计划告诉父母,如她所想,父母也根本没记起此时正在放寒假。家有船员就会关心风向变化,家有学生才会知道寒暑假,那些特殊的时间、节气,只对心有惦念的人才有意义。
北风凛冽,向晚捏着手机愣神,对面的周彻了然道:“有悄悄话要说?那我先去把帐篷支起来。”
她回给他一个极短促的笑,目送着他走到远处,手机屏幕亮了又暗,她到底是没拨出那通电话。
寒风把一池粉红吹皱,让向晚无端想起冷掉又干涸的草莓味奶昔,长发打在脸上隐隐作痛,向晚忍不住转头去看周彻,对方与她四目相对,笑容澄澈。
他身后的夜空,似乎一瞬间亮起了很多星星,就在这一刻,向晚心底生出了一股莫大的悲凉。
后来终于有一次,她鼓足勇气说了一句:“也许我每次都要在你的提醒下才报平安,是因为我根本不想报呢?或者说,是因为根本没人在意我的平安呢?”
周彻看着她,伸手抚摸她的长发,眼神极尽温柔:“跟家里闹别扭了吗?傻瓜,世上哪有不在意孩子的父母啊?”
彼时他们身处普陀山岛,远处是山石林木和寺塔崖刻,梵音、涛声不绝于耳,向晚能回应的,也不过是浅浅一笑。
她终于认识到,行走在人生的旅途上,遇到的每个人都是一段缘分,亲情如是,友情如是,爱情亦如是。有时缘深,一眼万年;有时缘浅,哪怕已经相处了很多年,却仍是各为人间。
她从未获得过在双亲怀里撒娇任性的资本,从未拥有过在他面前坦诚父母并不爱她的勇气。
她藏起来的,是一个真真實实,既自卑又怯懦的自己。
她多想仰起头,心无旁骛地把他澄澈的眼神和温柔的笑据为己有,可如今听着这古刹钟声,她如此不甘,又如此无力。
那是她第三次陪他旅行,似乎从那以后她便忙碌了起来,忙着打工,忙着考证,忙着毕业,忙着找工作,总之,那第三次旅行也就变成了最后一次。
发出的邀请接二连三地被拒绝后,周彻也就不再问了。大概成年人的世界中若想活得体面,都有着约定俗成的法则,其中大家不约而同遵守的一条就是,任何关系里,你若无情我便休。
只是那之后还是有照片寄过来,那些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的照片,像是一段段被封印、保存好的故事,有时向晚会沉默地盯着照片看,看得久了,似乎都能听见风穿过山涧的啸叫声和流水漫过礁石的呜咽声。
它们好像都是鲜活的,唯有她和他,始终缄默。
06
“所以说,你们从没有在一起过?”公司楼下的清吧里,小助理的脸上满是惋惜和不解,“就因为,他不够了解你的身世?你从来也没说过啊,怪不得人家。”
向晚举着杯子晃啊晃,半晌,敛起脸上的笑,极认真地说了句:“我和他一直在错过,只因为我这辈子,都在拼命追逐。”
不是追逐同甘共苦,不是追逐感同身受,唯一追逐的,只不过是能随心所欲地在风里站着,在某人面前,或快乐或忧郁,或冷静睿智或歇斯底里,哪一种姿态都可以,而对方会拂开她额前的碎发,云淡风轻。
不是心疼,也不用安慰,她来到这世上,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露出的每一个笑容,受到的每一次不公平对待,都和别人没什么不同。
可惜她这半生追逐,仍是半生孤独。
在外工作第六个年头,向晚终于回了一趟家。彼时外婆已经在她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因病去世,从此她便如同断线的风筝,与故乡最深的关联,也不过是每年阖家团圆的除夕夜,母亲会打来一个电话,没有叮嘱,没有絮叨,本该是世间最亲的两个人,却隔着一根电话线彼此沉默。最终母亲宣告这一通电话的目的——人不回来可以,但亲戚家数十个孩子的压岁钱要给,免得让人家说养大了女儿成了赔钱货。
每每此时,向晚便会生出一种荒诞感。电话那头的那个人,真的在很多年前的那十个月里,和她用一根纽带骨肉相连,同呼吸,共命运过吗?
她早已经接受了此生和父母缘分太浅这个事实,却又不得不承认,仍然会在某一个时刻,被既微妙又精准的疼痛击中。
第六个年头,公司的主流产品开始转型升级,加班到深夜,然后在公司睡着成了常事,她在某个晚上久违地做了个长长的梦。
梦里是宿锦的那座双拱桥,水雾如烟般笼罩在桥面上,外婆端着老式的青花粗碗,站在桥的最顶端,笑吟吟地冲她遥遥招手。
她带着满心的欣喜奔去,总共十六层台阶,她跑啊跑,却怎么也跑不到。
正急得满身大汗,手掌被人从后面牵住,她讶然回头,撞进一双熟悉的眸子里。
对方似乎还是年少时的模样,眼神清澈,语调温柔,他紧紧地牵着她的手,冲她粲然一笑:“快走啊向晚,粥都要凉了。”
这一次她终于踏踏实实地走完了十六层台阶,来到了外婆面前,粥香扑鼻,外婆爱怜地看着她,仿佛她还是二十多年前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
“囡囡,周彻,快趁热喝。喝上一碗腊八粥,人活百岁无忧愁。”
她忍不住笑:“外婆,你怎么知道他叫周彻?”
外婆便笑,像是很多年前的盛夏傍晚,她摇着蒲扇慢慢地给她讲过去的故事:“我当然知道,外婆啊,什么都知道。”
梦境忽然戛然而止,向晚在沙发上惊醒,窗外的天空刚露出一丝鱼肚白,桌上的液晶台历上显示着:2021年2月9日,农历腊月二十八。
于是向晚知道,这梦是来自遥远地方的惦念,又是年关将至,不要一个人孤孤单单。
天光大亮的时候,向晚登上了飞往家乡的航班。
飞机落地是下午两点,天阴沉沉的,似有风雪要来。向晚打车先去了宿锦镇,车在路口停下,向晚拖着行李箱慢慢走。小镇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唯有双拱桥上背阴处的青苔,似乎依然是旧时浓绿葱郁的模样。
越往镇中心走却越热闹起来,不远处的戏台上似乎在进行什么活动,戏台下竖着一大幅海报展板,旁边已经围满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
向晚不喜热闹,扫了几眼便往前走,不过走出几步之后,她顿住,慢慢回头。
这次她终于完全看清了海报上的字——“新派摄影师周彻国际摄影作品巡回展”,戏台上满满当当放着裱起来的照片,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的,是那幅“晨曦宿锦”。
舞台的正中间,坐着白衣黑裤的年轻男人,是熟悉的五官,眉眼间却有了淡淡的疲惫和疏离。
女主持大概率是他的粉丝,言语之间是掩饰不住的兴奋,走完流程后又多问了一个问题:“周先生,您并不是宿锦镇人,为何对宿锦情有独钟?”
周彻笑了一下,坦荡回答:“因为我爱上这小镇前,先爱上了这小镇上的一个姑娘。”
下面欢呼声四起,主持人接着问道:“哇,缪斯女神啊!怪不得您能跨越千山万水,拍摄出这么多好的作品。你们是不是经常一起旅行?”
周彻有一瞬间的愣神,随即摇头笑道:“她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从小被捧在手心里长大,我舍不得让她经受风吹雨打,但我可以把全世界缩影成相片,如数摆到她面前。”
他话音落下的时候,向晚悄悄地退出了人群。
身后喧闹声持久不散,她走得很慢,青石板路上有一种粗粝的踏实感。
她从前只觉自己倔强,有某个瞬间甚至觉得,来人间思念一场,倒不如对自己妥协,一起去看余生漫长。可如今她终于明白,阻碍他们在一起的,不仅是她的倔强和伪装,还有他的自负和疏离。
这漫长的许多年啊,他竟然从来没想过要试图了解这个,他用层层深情和在意禁锢起来的姑娘。
雪终于落下来,向晚挺直了脊背一直向前,同身后的热闹、喧嚣、人群和少年都渐行渐远。漫天风雪,她就像是终于,踏入了另一重人间。
(编辑:白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