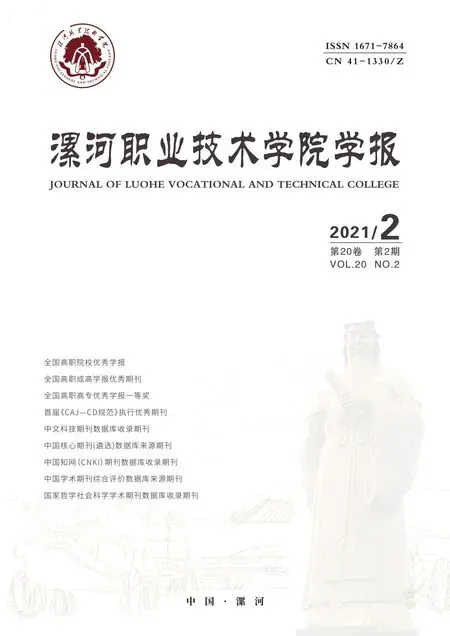苍凉的悲剧
——《雨天的棉花糖》的伦理叙事
范玉彬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雨天的棉花糖》创作于1992 年,发表于1994年的《青年文学》,主人公红豆的命运令人叹惋。在毕飞宇的众多作品中,这部小说是特殊的,作者对其所预期的情感状态是欲哭无泪的悲凉。毕飞宇意在重新审视生命个体的命运以及自我的内在灵魂,人人都想逃离束缚而追寻理想的自我,却一次次与红豆的命运重叠,在痛苦中埋葬自己的生命。红豆的命运不只是个人的,更是人类的,在社会文化的制约下,人们始终难以确证自我的伦理身份,在现实的伦理选择中无助挣扎。红豆尝试服从于权威的文化话语,却最终彻底陷入伦理困境,走上毁灭的道路。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探究性别身份模糊的主人公在强大的文化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社会中争取生存空间、进行伦理选择的艰难处境。
一、伦理身份与伦理禁忌
文学与伦理向来关系密切,对文学作品中彰显的伦理价值的关注,是近些年学界研究的热点。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文本阐释方法论,被广泛运用到当下的文学批评实践当中。诸多学科领域都重视自身与伦理间的批评关系,进而出现新的研究热潮,并在文学领域最终实现了文学批评的伦理回归。
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兴起于2004 年。华中师范大学聂珍钊教授在中国道德批评的基础上,借鉴韦恩·布斯和玛莎·努斯鲍姆等西方伦理批评学家的理论观点,提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并对其定义:“伦理批评是以文学作品为纽带,考察作者与作品、作品与社会、作品内部等的伦理内涵、道德效果、道德境界的文学研究活动。”[1]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它从伦理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阅读阐释并评价,并将文学批评与历史结合。与西方伦理批评和道德批评有所不同的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更注重文本的范例分析,并强调回到历史、伦理现场,分析人物的伦理选择及其结果。它在其理论视野中建立了诸如伦理环境、伦理秩序、伦理混乱、伦理两难、伦理禁忌、伦理结等自洽的批评话语,以此深入具体的文本细节之中,更为有效地解决具体的文学问题,从而关注文学作品中人物个体的生存本质,深刻彰显文学对人类伦理、命运的关怀。《雨天的棉花糖》中,主要的伦理线是红豆充满悲剧意味的人生经历,红豆依赖二胡活着,那声音已经成了没有故事的抽象叙述和失去情感的艰难抒怀。“我”与红豆的成长经历、隐晦暧昧的情感,红豆被迫参军、牺牲、回归,“我”的生活,“我”与弦清的婚事,红豆与曹美琴的纠葛构成了一个个伦理结。从文学伦理学角度观照作品,涉及对人物的伦理身份、伦理禁忌、伦理选择、伦理悲剧及伦理启蒙意味的解读。
文学伦理学批评一直注重分析人物的伦理身份,显见的是,伦理问题的产生同伦理身份密切关联。《雨天的棉花糖》中,人物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伦理身份,因此被赋予各异的角色和标记,面临不同的人生境遇和社会责任,一个个伦理结因人物伦理身份的转换而被串联起来。遗憾的是,红豆自始至终没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社会角色,男性生理特征和女性心理导致其伦理身份的模糊。少年的红豆女孩子一般如花似玉,曾为自己不能安稳娇羞地长成姑娘而苦闷,性别意识的错乱致使其向往和模仿女性,成为女性的渴望在扮演女性的过程中日益强烈。从气质、言行到情趣甚至欲望,红豆逐步适应女性的符号化特征,最终发展为对同性的爱,渴求像女性一样被保护。这首先是缘于红豆青春期伦理身份的扭曲,他的女性意识虽与先天因素有关,但社会、家庭环境的影响也助长了这种趋势。老师们都喜欢少年时期女孩儿一样的红豆,他的姐姐为他扮演了哥哥的形象,红豆则安心做起了妹妹,在他人的认同和帮助下,红豆彻底掩盖了男性自我身份的确证。红豆的父亲是一个极具男权意识的人,拥有绝对的男性特质,诸如暴力、酗酒、极度专制等,对红豆的性格弱点极尽蔑视。红豆对父亲恐惧、厌恶,进而畏惧男性、畏惧战争,在父亲的英雄光环下,他意识到自己伦理身份的错乱,也越发自卑恐惧,个性更加模糊黯淡,习惯于退后和寻求谅解,成为一个男权文化统治下的边缘人。
伴随红豆性别意识错位而来的是他的同性之恋。在文学作品中,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伦理混乱表现为理性的缺乏以及对禁忌的漠视或破坏[2]。“我”与红豆共同成长,总是保护和关爱红豆,尤其是在红豆背负着战俘身份归来之后。也许“我”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怜悯,却让红豆将“我”视为性幻想的对象和生活、情感上的依赖。毫无疑问,在男权思想统治下男女界限极为分明的社会,异性恋主导的文化价值取向,不容许同性爱的存在,“我”与红豆显然触犯了伦理禁忌,因此两人的感情表现得隐晦而暧昧。作者以冷峻的叙述笔调凸显了异性恋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权威,这种压迫性增加了同性爱的复杂和隐秘。红豆恭敬地喊弦清“嫂子”,压抑、控制自己的言行,而“我”则更懂得隐藏自己,以对弱者的同情、保护姿态来对待红豆。现实是残酷的,它不质疑女孩儿红豆存在的合理性,却剥夺了成年男性红豆的生存空间。文化语境中的性别差异决定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不能有任何人超越异性恋的秩序,而正是这个异性恋主导的文化世界和社会伦理环境,刺激红豆投入单一的男性关系之中。对女性地位的规定性认知使红豆向往女性的温婉柔弱,认为自己需要被男性理解和保护。这种性别伦理的界定,促使红豆尝试异性规则,试图矫正自身,融入社会之中,但同性恋的倾向始终支配着他,最终难以挣脱。
小说中,红豆的伦理身份经历了几次变化,从少年时期的假丫头片子到军人,牺牲成为英雄,背负战俘身份归来,投入与曹美琴的感情,最后走向死亡。在这漫长的过程中,红豆始终未找到自己的社会角色,尽管社会为他提供了多重不同的伦理身份,但始终未得到自我伦理身份的确证。社会的命名无法消解红豆内心的无名,这在本体论意义上造成了红豆难以逃脱的生存困境。他意欲成为女性,但又清醒地知道自己不是“妹妹”,不得不在现实之下妥协。他投入与曹美琴的情感关系中,是为了改变自身的边缘地位。在这重意义上,红豆既是一个异性恋价值取向的背离者,也是维护者,这就像一个难以挣脱的牢笼,禁锢他直至毁灭。红豆想成为理想的自己,沉醉于热爱的音乐世界,人们却硬生生把他从二胡声中拽出来,点亮他的灵魂,让他看见自己的分裂进而杀死内在自我。每一个人都渴望通过感知自我,来实现生命价值的超越,然而这世间最多的是人的荒诞处境与悲悯的现实。生活似乎总是违背我们的意志,连同生命,是你的,却也不是你的。“生命最初的意义或许只是一个极其被动的无奈,一个你无法预约,不可挽留、同时也不能回避与驱走的不期而遇。”[3]
二、伦理选择与伦理困境
人物伦理身份的转换必然使其面临不同的伦理选择,对伦理选择的分析必须回到人物当时所处的客观历史语境中,站在人物的立场上来审视其动机和目的,以此解读并阐释文学作品,而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人性因子中的伦理意识、理性意志引导着人接受社会伦理秩序的规驯。红豆在每一次伦理身份变化后都需要在伦理观念的指导下做出不同的伦理选择,人物的自我意识与伦理规约之间的冲突也得以凸显。青少年时期的红豆自主选择做一个女孩子,他热爱音乐,模仿女性,不在乎别人的嘲笑讥讽,拒绝成长,但在现实中还是摆脱不了男性的身份。性别意识的错乱让他痛苦,转而选择将理想和前途寄托于钟爱的二胡,希冀在音乐中寻找到精神的出路。他向父亲提出学二胡,是他又一次抗争,也再次发现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红豆的父亲,经历过残酷的战争,没有眼泪与胆怯、感伤与后退。不仅自己漠视生命,也无视他人的恐惧和生命的价值,他一心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接续他在战场上的荣光,红豆被迫走向战场,真实的枪声、死亡让他战栗,他始终不能适应自己伦理身份的变化。
当所有人都证实红豆牺牲了之后,他却突然归来,归来的红豆第一个来寻找的人就是“我”,他渴望被理解和庇护。在成为战俘这件事上,红豆一开始是缺乏自主性的,被动接受,后来,他自主选择并接受了战俘的身份。女性气质导致红豆畏惧死亡,他有过自杀的机会,但他选择活下来,并为自己的懦弱感到羞愧。他很清楚,对于军人来说,死亡意味着责任,接受战俘的身份意味着活命,但同时也意味着遭人唾弃,他的选择使他再次陷入伦理困境之中。果然,红豆成为大家眼中的“汉奸”“叛徒”,父母没有给予他情感上的关怀,反而认为他不是烈士,不配活着。绝望的红豆想过上正常男人的生活,在女性那里寻找宁静和安慰,获取安全感,在与曹美琴的关系之中,他寻求的更多是母爱的关怀、呵护和理解。此时虽然尝试与异性产生感情,但他更企望获得同性的理解。青春期的红豆或许经历了对曹美琴漫长的单恋,坚信在面对曹美琴的爱抚时,他怀有一种男婴的心态,女性的乳峰对他来说象征着抽象意义上的母亲。人类释放性欲的目标是结合,这种欲求绝非只是一种单纯肉体的欲望,而是在结合的过程中,生活中一切茫然、痛楚、紧张的情绪得到减缓。正如斯宾诺莎认为相爱能刺激性欲一样,在双方渴望结合的激情支配下,多种精神因素诸如征服的欲望、孤独感、焦虑感,乃至虚荣心,毁灭、破坏的愿望,都能够刺激性欲。这段关系是相对安全的、幸福的,也是畸形的,在幸福中陶醉的红豆认为找到了自己的家。处在身份认同危机中的红豆,竭力“寻找可供站立的坚实处所,在这些地方,他们或者他们的部分角色会变得真实”[4],然而曹美琴在性别伦理意义上是一个男性化的女性,她的行为方式背离了红豆对女性的认知,曹美琴的专制与控制欲让战争的阴影再次笼罩红豆,也再次走向崩溃。红豆选择服从伦理道德,服从这个异性恋规定的文化世界,逃离伦理困境,但是他的服从与抗争、逃离与挣扎,同样颓然无力。曹美琴的反目使红豆彻底绝望,将他逼向疯狂和死亡的边缘。
疯狂的红豆试图用自杀获得新生,他第一次作为男性为自己流泪,终究难以消解对生命的困惑与恐惧。被关进疯人院后,红豆拒绝吃药,这是他最后的反抗,他要杀掉那个不被社会所接纳的自我,以自毁来永远留在二胡声里。选择死亡意味着新生,放弃生命却可以坚持自己,这是红豆最后一次的伦理选择,也是他唯一能做的选择。他最终也未能与内在的自我和解,带着不甘与遗憾离开了世界。
三、伦理悲剧与伦理启蒙
红豆伦理身份认同的缺失所造成的伦理混乱,再次对其身份建构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表现为理性的缺乏以及对禁忌的漠视或破坏”[5]。红豆天生的女性气质造就了敏感的内心,他身上感性思维自然地压倒理性思维。红豆一直试图服从社会、文化的权威,去迎合公众文化心理,用理性控制自己的行动,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被社会所接纳的“男性”,但最终一切的努力失败,规则伦理的制约与个体生命伦理对自由追求之间的裂隙无法弥合,主人公陷入更深的灵魂挣扎,难以重构自身的伦理秩序。小说开篇,红豆在苍茫炎热的夏季死去,奠定了全文的悲剧基调。伦理身份的逾越、伦理禁忌的触碰使其进退维谷,非理性的历史力量干预制约其理性存在。红豆的悲剧是性格悲剧也是社会悲剧,导致其伦理悲剧的原因是三重错位:性别角色错位、社会角色错位以及公众文化心理的错位,这三重错位,根源在于其自身的性格弱点。因此,伦理悲剧源于性格悲剧,也是社会伦理环境造成的悲剧。红豆在多次伦理身份转换的对立冲突中艰难求生,从本质上讲,他是软弱的,缺乏打破规则的勇气。他依赖母性,拒绝成长,胆小而缺乏主见,并因此受制于男权社会,失去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越是向他宣扬属于男性的生理、心理特质,越能刺激他敏感的神经,使他更加厌恶、畏惧现实而龟缩于柔弱美好的女性世界中。在暴烈父亲的专制之下,红豆的个性越发模糊。红豆与其父的关系让我们联想到犹太文化中“父子冲突”的伦理关系,犹太人子辈内心世界充满困惑与无奈:“他们渴望美国式的自由,同时又身陷传统赋予的道德重荷之下,在自我质疑中摸索、探寻、彷徨、困惑。”[6]红豆也是无可救药地陷入判断缺失的自我混乱中,同性之爱就像难以挣脱的牢笼,使其难以摆脱致命的伦理禁忌,无法超越复杂的伦理困境,最终深陷悲怆的伦理悲剧之中。
更进一步说,红豆的命运悲剧是社会伦理环境造成的。公众文化心理的异化挤压个体生存空间,造成红豆的生存困境,摧残他的灵魂。显然,他是男权文化社会的边缘人,在相对严苛的社会道德环境中,人的伦理道德观念极强。红豆作为“异类”,不可能脱离异性恋主导文化的辖制,也不能不受传统文化的检验。作为家中唯一的男性后代,家国为上的思想寄予红豆过多的期望,父亲将未实现的理想移植到红豆身上,母亲姐姐则期望战争能造就一个血气方刚的红豆。红豆只能选择服从,压抑自己的理想,一步步将自己逼上绝路。当牺牲了的红豆重新归来,母亲并没有失而复得的喜悦,却因为红豆不再是烈士而心如刀割。在这里,公众文化心理发生了严重的异化,父母乃至社会大众认为一个虚空的烈士比活着的人更重要,红豆的复活让亲人焦虑和羞耻,无法忍受旁人的鄙视和嘲讽,为此诅咒红豆为什么不死。红豆成为公众的谈资,在他们眼里,被俘虏与做汉奸、叛徒是同义词,令人胆寒的梦魇般的战争,成为世俗众人刺激的享受。蒙昧大众的内心扭曲异化,脱离了战争的红豆又陷于泥淖深受戕害。
毕飞宇描摹现实中的破碎状态、剖析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写实类小说,如《男人还剩下什么》《驾纸飞机飞行》等,都带有深刻的伦理启蒙意味。作者在创作这部小说时转换叙事视角,将第三人称“他”换成“我”。“我”亲眼看见红豆从如花似玉的少年、备受羞辱的青春期,走向战场到牺牲,归来后精神防线全面崩溃直至死亡。文本的叙述呈现一个环形回归的轨迹,引发“我”对生活的质疑和对人道主义的思考。毕飞宇说到自己与这部作品的关系:“因为红豆,我看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他让我长大了,‘成人’了。通过《雨天的棉花糖》的写作,我由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蜕变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者。”[7]作者表达在社会重压之下男性的心理状态受到严重的忽视,作为男性要刚强,要抑制自己的情感,不能软弱、不可怯懦,这都是统一的意识形态之下强加给男性的文化符号。冲突和战争是和男性相关的永恒话题,它们永远存在。作者用“蛇”来形象化、拟物化地象征战争带给人的莫大恐惧,人可以坦然面对死亡却不能忍受恐怖,没有人关注军人的心理状态,许多老兵、战俘归乡后,在恐惧的阴影笼罩下了此余生,红豆的命运是具有广泛性的。读罢小说,我们不得不对传统文化中不合实际的顽固观念提出质疑,社会集体无意识制约、抹杀了个体价值和个性自由。我们无法阻止悲剧,但悲剧若让人欲哭无泪,则更为残忍。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对个体生命的独立性、个性自由的发展和生命价值予以诚挚的关怀和最大限度地包容,让生命个体在面临伦理困境时能适时找到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