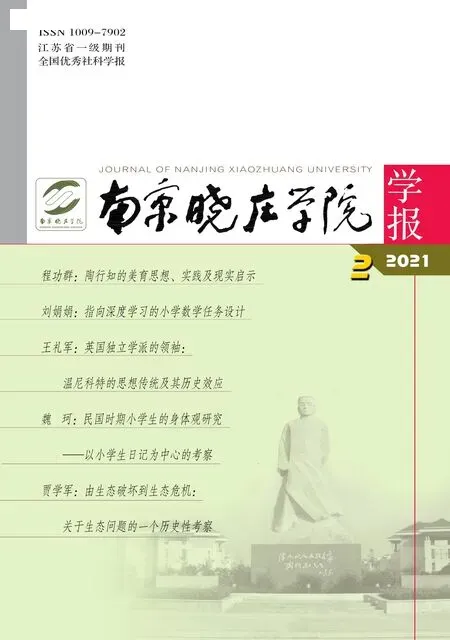由生态破坏到生态危机:关于生态问题的一个历史性考察
贾学军
(南京晓庄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尽管人与自然的冲突以及局部生态崩溃早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就已存在,但是生态问题转变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却是在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后才开始的。随着以商品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张,物种灭绝、环境恶化、工业污染等问题像涟漪一样在历史上不断回荡、扩大,以至于今天成为足以威胁人类继存的力量。因此,要想突破生态危机对人类的制约,必须从生产方式入手,改变资本主义主导的生产体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崭新的生态文明形态取代旧的工业文明体系。
一、资本主义之前生态破坏及其特点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以来,生态危机与人类续存之间的关系就成为西方社会最主要的话题之一,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将是人类长期面临的敌人。为了改善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兴起,他们把当代生态中心主义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推崇大地伦理、深层生态学,强调对环境的伦理关怀,注重大地共同体的价值与权利。由于信奉“生态整体性规律”,这一传统强调人的自然属性,认为人与自然界中其他生物一样具有同等的权利与价值,并无优先地位。这种“绿色”观念有一个基本共识,即“经常会忽视掉人类处于工业革命之前的真正历史”(1)John Bellamy 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9, p.35.,相信前工业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所有生态问题都起因于工业化带来的技术和人口膨胀。据此,他们坚决反对现代技术和工业生产,主张以“大地伦理”情怀重塑人类生存格局,寄希望于以一种“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实现“生物圈平等主义”。但是,作为一种激进的生态主义,这种广为流行的“绿色”观点强调了技术与工业化带来的直接破坏性作用,却弱化了对主导工业化与技术发展的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从而导致该理论在寻求生态危机解决路径时的自我矛盾:一方面,它把激进的后现代价值追求奉为圭臬,整体拒斥工业化与现代性,把希望寄托于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原始状态;但另一方面却又信奉改良主义,作风保守,试图以伦理的说教与行为的劝导拨转资本主义的前进之路。(2)徐艳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之所以出现这种理论上的矛盾态度,究其根本在于这种“绿色”观念主要是从伦理的视角来看待环境问题的。它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一种道德关系,为了将这种道德关系确立为对人的道德要求,必须赋予道德理由和依据,而“伊甸园”式的美好图景无疑是极具文化说服力的一种论证方案。但是,这种伦理的方法也限制了该理论的分析边界,它过于关注自然的内在价值与权利,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意义,却忽视了人与自然实际上是通过生产而紧密联系的,忽视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对生产活动的决定作用,以及它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
如果以严谨的态度去考察人类文明就会发现,社会和自然“几乎奇迹般相适应”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为了生存而艰苦地与自然抗争是人类较长时期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即使是最早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欧洲也仅是当美洲新大陆被发现,自十六世纪到整个十八世纪展开殖民地贸易后,通过从新世界引进甘薯、土豆、玉米等新型农作物并推广种植,才最终免于饥荒,并实现人口快速增长的。(3)John Bellamy 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9, p.40.事实上,在万年以前,农业从一开始发展起,社会生产就已经具有破坏环境的因素了。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人类的生活方式由农业主导,从土地与自然界中直接获取粮食与生活必需品是生产的主要形式。出于对饥饿的恐惧,以及增加人口的需要,人类不断对自然进行有计划的干预,以便获取更大量的农产品。但是这种对土地与自然的人为改变却使地区性的生态环境日趋脆弱,而每当一个地域能够容纳人口增长需求的狭窄界限被越过,生态崩溃的幽灵便会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前的前工业社会中,可以历史性的发现许多因环境破坏而导致社会制度崩溃的例子……玛雅、罗马、希腊、迦南以及苏美尔等文明的坠落……至少部分地是由于生态崩溃导致的。”(4)John Bellamy 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9, p.36.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当生产足够多粮食变得越来越困难时,大量的水利灌溉与过密的种植会破坏生产条件与土壤结构,而土壤退化使对“边际土地”的需求日益增多,从而加强了对陡峭山坡和森林的开垦与砍伐,长此以往造成了局部地区的荒漠化。而农业危机是社会危机的导火索,当食物不再能够有效供给的时候,饥荒、战乱就会象灾难一样降临,为文明的衰落埋下祸根。德国环境史学家约阿希姆·拉德卡在其著作《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中就明确指出:“新的实地研究证明了玛雅的中心地区,人口的密度曾经空前绝后,以及随之而来的突然的没有明显外在原因的人口统计的崩溃,并进一步证实了人口压力与水土流失之间的联系”(5)约阿希姆·拉德卡著,王国豫、付天海译:《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反驳了玛雅文明生态和谐的观点。
事实上,在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体系中,人与自然的对抗性关系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早就有详细的分析。马克思“主要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物质生产运动和客观规律出发,用社会历史的客观结构(生产关系)作为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尺度和理论中轴线”(6)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页。的,以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把人类历史分为四大社会经济形态,即“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页。。在晚年致查苏里奇的复信中,他又把这四个阶段与“原生的社会形态”——古代的或原始社会形态和共产主义区别开来,统称为“次生的”社会形态。(8)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2-452页。在马克思看来,与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主体与自然对象的统一不同,这四种社会经济形态是社会生产过程中四种对抗性生产关系,这种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其中,资本主义以前的三种对抗性社会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间段,但从内在逻辑上看它们却有着本质一致性,即“劳动与土地的自然的、直接的统一”(10)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这种统一与原始社会中那种人与自然的“天然同一”不同,表现的是对抗基础上人对自然的依赖。这是因为在这三个阶段中,人类的主体性存在中自然因素还占主导地位,人的生产还主要表现为“直接地从自然界中再生产自己”(11)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页。,即人的种的繁衍和向自然的索取。这样,一方面人类的续存受到自然的限制,从而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直接对抗,另一方面,人只能在自然生产中维系自身的生命从而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依赖。在这种既相依赖,又相对抗的关系中,人要想摆脱束缚,确立自主能动性,就必然要突破自然的限制,从而不可避免地破坏外在生态环境。
二、重商主义时期生态破坏向全球的扩展
尽管人与自然的对抗性关系几乎伴随着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文明史,但资本主义之前(前工业文明时期),由于社会生产以农业为主,受限于生产力与农业劳作的规模,人类需求的满足被限制在一定的水平,因而突破界限所导致的生态崩溃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还相对有限。在广度上,农耕社会的生态破坏往往以人类聚集圈为限,其范围很难达到人迹罕至的区域。从深度上来说,当时的生态问题更多表现为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森林滥伐等,破坏的基本上是与土壤相关的生态系统,对水圈、大气圈的破坏还无从谈起。但是,自资本主义出现以来,尽管只有短短几个世纪,由于它对自然的征服是非常成功的,这就导致其生产的破坏性影响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一些区域,而是开始向整个地球与生态圈扩展。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劳动资料(土地)开始分离,生产不再是从土地中直接获取生活所需的劳作,而是成为了一种创造财富的活动,围绕利润所展开的商品生产逐渐占据物质资料生产的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动轮。在这一形态的社会中,人与土地的关系开始由以种的繁衍为目的的直接关系转变为以财富的积累为目标的间接关系。这种生产越发展,人与自然就越疏离,就越会忽视自然而表现为一种自主性存在。也就是说,当资本主义出现后,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当摆脱了自然束缚的人努力创造一个物的世界来与自然相区别时,这种努力既拓展了“人的世界”范围,也同时使自然界承受了更加深重的负担。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减少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的直接依赖,但却日益把自然带入经济领域,使其成为一种经济要素,这为大规模开发与利用自然打开了便利之门。(12)John Bellamy 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9, p.40.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萌芽于16世纪,这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关键时期,也是资本原始积累和手工工场大发展的时期。而对这一时期的形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当属15、16世纪之交的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殖民统治。美洲的发现及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掀起了全球殖民统治及资源掠夺的狂潮,这种对异域的征服与掠夺不但增加了欧洲的财富积累,更重要的是它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世界市场。“美洲和环绕非洲的航路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资料和一般商品的增加,给予了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未有的刺激”(1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7页。,“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14)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9页。。在这种以血与火写就的编年史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地理的发现和科学的进步从一开始就与对地球的更深重的剥夺密切相关。”(15)John Bellamy 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9, p.40.
剥夺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早期的殖民地贸易开始,这种以自然物与农产品为主要对象的贸易对全球物种结构与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作用。首先,不断扩大规模的商业贸易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物种大屠杀,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大量毛皮动物的灭绝。为了获得毛皮耐寒动物的商业价值,整个大航海时代数以亿计的动物因商人的贸易活动而死亡,以至于整个19世纪被人们称为“灭绝时代”,在这段时间里,猎人们往往一年就杀死超过40万只臭鼬、50万只浣熊、200万只麝鼠。(16)埃里克·杰·多林著,冯璇译:《毛皮、财富和帝国——美国皮毛交易的史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44-445页。在商业利益的驱策下,贸易商人与猎人联合起来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区域性物种灭绝,这在整个16到19世纪持续发生。物种在短时间内的大规模锐减斩断了生物链,导致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出现生态环境的急剧变化。其次,为了追求经济作物所带来的高额利润,“单一作物”农业模式开始在新世界推广,在改造自然、征服人类劳动基础上创造的以经济作物生产为核心的新的世界体系开始形成,而这对全球生态系统的破坏甚至比物种大屠杀还要影响深远。
著名人类学家西敏司的研究表明,作为一种“半成瘾食品”,糖在16世纪之前还只是欧洲上层社会的奢侈品,但是到了1740年以后,食糖价格逐渐下降到了普通大众可以接受的程度,从而推动了食糖消费的平民化,而这得益于意大利、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不断在殖民地推动的大规模甘蔗种植。在西敏司看来,对蔗糖的食用,“其历史意义甚至足以和蒸汽机相提并论,因为食糖不但改变了饮食的习惯、消费的模式、工作的意义,更改变了生产、贸易和消费的关系,改变了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基础。”(17)西敏司著,王超等译:《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9页。西敏司的评价并不过分,作为重商主义阶段最主要的经济作物,甘蔗的庄园化生产以大规模和高效率著称,这种生产模式为以后的现代工厂生产提供了最早的雏形。而且,新大陆与欧洲之间的蔗糖贸易推动了大西洋两岸的洲际贸易,它与随后开展的咖啡、烟草、可可、香料、橡胶等农产品和原材料的贸易一起为欧洲工业革命的推进与工业化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物资准备。同时,这种贸易的兴盛也为全球贸易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为以后资本的全球扩张与全球输出提供了可能。
如果说重商主义与殖民地贸易共同推动的庄园化生产对资本主义而言是“建设性使命”的话,那么,这种经济活动对全球生态系统来说则完全是一种“破坏性的使命”。在殖民地推行的庄园式单一作物种植严重剥夺了土地。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量,获得尽可能多的财富,庄园主肆意破坏殖民地原有的农业生产结构,他们砍伐森林,焚烧土地里的庄稼,把土著居民驱逐到狭小的“保留地”。这样做的结果使原本“粗放”式农业生产被“集约经营”所取代,农物种的多样性被经济作物的单一性所取代。从经济效益与生产效率上来看,这种相对集约的单一化生产确实能在短期内显著提高经济作物的产量,但其对环境的破坏作用却是长期的。一方面,相较于多作物轮种而言,单一作物生产更容易破坏土壤的养分循环,使土壤中的养分在短期内被掠夺,造成了土地的迅速贫瘠;另一方面,在化学肥料还没普及之前,土壤的贫瘠催生了对土地的需求,为了拥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来扩展种植园,庄园主们“用火来为种植园清除土地上的树林”,致使一片片的原始森林被毁灭。
马克思曾经说过,“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18)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2页。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到18世纪后半段工业革命蓬勃开展的近三个世纪,通过商业贸易,欧洲殖民者从新世界掠夺了大量的人口、财富、各种原料与农作物,这推动了欧洲社会的快速发展,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但是,在宣称“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19)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2页。的殖民制度下,在“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20)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8页。的过程中,所付出的生态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亚洲、非洲、美洲的大部分殖民地由“天然地适合生产粮食的地方变为了饥饿的地方。凡是从前鸟语花香和草木繁茂的地方,都遭受到了毁灭的破坏。在所有曾经豪华一时的大庄园的身后,留下的都是贫瘠发白的岩石、被水冲蚀的土壤和腐蚀变质的土地”。(21)John Bellamy 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9, pp.45-46.
三、工业革命以来生态危机的积累与扩大
殖民地贸易快速改变了新世界的生态系统,并在全球范围内重塑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但重商主义时期还只是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虽远大于之前的世代,却仍然保留有传统农业生产的影子,其破坏生态系统的作用机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强力而粗暴的生态干预,而不是对整个生态系统进行根本改造的生态转型。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当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工业革命后,机器资本主义开始兴起,这使得财富的源泉——土地(自然)与劳动者在资本的内在逻辑驱使下转化为商品,在这种商品化的过程中,人类的生存基础进一步被破坏,社会生产与自然愈发处于敌对状态,生态问题开始转化为困扰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
工业革命催生了快速扩张的工厂体系,使生产对机器的依赖日益提高,这种“一开始就和机器,即使是最原始的机器联系在一起的劳动,很快就显出它是最有发展能力的”(2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2页。。但是这种基于技术的革新与生产方式的转变而爆发的生产能力在重塑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同时,也加速了生态恶化。扩大的生产加速了对工人的需求,直接促进了城市化,大量工人在短期内涌入城市,但是迎接他们的不但有饥饿和疾病,还有糟糕的生活环境。对此,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有过细致的描写:“到处都是死水洼,高高地堆积在这些死水洼之间的一堆堆的垃圾、废弃物和令人作呕的脏东西不断地发散出来染污四周的空气,而这里的空气由于成打的工厂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浊沉闷的了。”(23)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2页。显而易见,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不但扰乱了人的关系,而且还在更大范围内导致了环境的恶化——工人恶劣的生存状况与直接的全面的环境污染是并存的。汤因比指出:“产业革命的烟雾所带来的破坏要多于创造”(24)阿萨·勃里格斯著,陈叔平等译:《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页。。保尔·芒图则把大工业城市比喻为一个个被烟雾包裹着的丑陋而黝黑的怪物(25)保尔·芒图著,杨人楩、陈希泰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94页。。从一份19世纪中叶英国城市卫生协会的卫生状况报告我们可以管窥当时城市里恶劣的生态环境状况:“博尔顿市——实在糟;布里斯托尔市——糟极了,死亡率很高;赫尔市——有些部门坏的不堪设想,许多地区非常污秽,镇上和沿海排水系统都极坏”(26)梅雪芹:《19世纪英国城市的环境问题初探》,《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第105页。。
为什么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环境问题更加严重?究其原因,从物质层面来说,机器化大生产依赖于煤的大量使用,而化学与钢铁工业的迅猛发展则造成了各类废弃物的快速聚集。煤炭的快速消耗,导致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化学工业的萌芽——即使只是简单的生产纯碱、硫酸以及从植物中提取染料等,严重污染了河流;钢铁工业的发展则造成了森林的过分砍伐与消失,供养一座炼铁厂需要大量的木柴,这导致英国许多地方在开设炼铁厂后,很短时间内森林就稀疏了。
当然,除却物质性的直接原因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新生产方式激发了人们对利润与财富的无限渴求。工业革命的到来,改变了人们对生产的认知。与直接获取使用价值的生产不同,机器化大生产开拓了生产更广阔的前景。当机器怪兽成批吐出大量商品时,人们开始明白,大生产时代已经来临,仅仅拥有满足生活所需的物资已无法改善自身的地位,唯有获取财富,拥有大量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才会使自己“上升到社会上有影响的显著地位”。“这种生产方式始终以商品而不是以使用价值为基本形式”,遵循的是交换规律,追求的是获取利润。这个时候,商品生产开始强加于整个社会并“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27)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4页。,当所有产品都转化为商品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表现为了“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一方面,个人生产的商品成为资本家统治工人的一种异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商品本身又是资本家所追求的财富与利润的物质载体。这样,整个社会生产就表现为一种资本与利润刺激下对商品的无限追求,经济效益开始统摄一切,成为整个社会追求的目标,人与自然的真正价值被遮蔽。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进入电气时代,生产力突飞猛进,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传统的生产组织与国际经济秩序已不能满足资本家相互竞争的需要,资本主义世界开始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最先建立了机器工业的国家开始把原料产业部门转移到国外,国际经济活动中生产性经营明显增多,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分工逐渐形成。在欧美等国家的扶持与投资下,以矿产、石油为代表的资源开采业和以初级产品加工为代表的制造业继开垦种植园之后成为殖民地及边疆地区的主要产业门类。在随后的近一个世纪里,欧美国家借助私有化、自由市场、金融资本和危机操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世界的又一轮财富掠夺,将发展中国家变为了豪夺敛财的“后花园”,使它们创造的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外围流向中心,建构起了一个庞大的资本帝国主义。在这一过程中,欧美国家不但拿走了财富,留下了贫穷,还凭借资本、知识产权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利用它们在全球产业链的价值分工中占据的高位,对全球产业进行分配,将高污染、高耗能的低端产业不断移植到第三世界,实现了生态危机的外部转移,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生态问题。
当资本主义的生产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机就不可避免了。为了不断强化世界中心的地位,资本主义需要以对外围的双重剥削来巩固。一方面,在它们确立并主导的经济法律体系内,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合法”的开辟市场,收购资源,攫取利润;另一方面,为了缓解自身的环境问题,纾解生态压力,西方世界又通过产业转移与海外投资等方式把高污染企业与工业垃圾向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倾销,这无疑会提升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好形象,但却在全球范围内加重了生态危机。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资本的增殖空间开始受限,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资本不断从实体经济和生产部门中退出,转移到金融领域,形成了以金融垄断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机制,资本主义进入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这一时期,资本的总公式(m-c-m’)日益表现出m-m’的特征——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趋向于完全消失,钱开始生钱。抽象的财富创造过程破坏了实体经济,同时推动了自然物的直接资本化,这导致浪费和破坏主导着整个生产体系。借助金钱的魔力和几无障碍的资本流动,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对社会与自然空间进行重新配置,而且这一规模越来越大,完全无视生产的合理性或自然系统的可持续性。(28)贾学军:《新帝国主义是更为凶险的帝国主义——福斯特对新帝国主义的经济与生态的双重批判》,《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美国生态学者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破坏生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最终发展到了今天的“生态帝国主义”阶段,他认为生态帝国主义至少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掠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资源,并改变这些国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第二,在攫取自然资源的同时,是劳动力的掠夺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第三,前两种因素的叠加导致了外围世界的生态脆弱性,而这成为了进行帝国主义控制的有效途径;第四,向第三世界与发展中国家转移工业,倾倒垃圾;第五,资本主义最终实现了对世界的控制,但是由它所主导的生产体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却造成了全球性的“新陈代谢断裂”,并转而限制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29)John Bellamy Foster, 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 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 pp.234-235.福斯特的分析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对世界的控制从来都不是单维的,如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帝国主义一样,生态帝国主义也是资本主义控制世界的必要手段,资本主义在对世界进行“剥夺性积累”的同时,带给世界的不仅有贫富差距、南北对立、金融膨胀、市场无序,还有持续的环境恶化与全球生态危机。
四、结语:一个简短的评论
当今世界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现状,一方面是西方发达国家山清水秀、绿树成荫;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浓烟滚滚、污染严重。这种巨大的反差迷惑了很多人,让人觉得污染都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要为全球生态危机负责。但实际上,当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进行简单的梳理就可以发现,今天困扰整个世界的生态危机,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体系。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制度,这种不可持续性源自于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以及对利润无休止的追求。围绕商品所建立的生产体系会把“所有的自然物与自然规律以及一切人所独有的东西都转化成仅是它本身自我扩张的手段”,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这一体系会持续扩大它对世界的“剥夺”。事实就是如此,无论是原始积累时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还是金融资本主义时期,在其背后总是会发现人与自然真正价值的不断丧失,其中既包括人的沦丧与劳动的异化,也包括物种的灭绝与环境的恶化。因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实际上是对人与自然的双重剥削,它在引发社会危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把世界带向生态危机。
如何打破这一僵局呢?首先,寄希望于资本主义为了生态利益而放弃对利润的追求,从而自觉走上“绿色革命”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资本“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和无限制的欲望”(30)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页。,以利润增长和资本的积累为目标的生产一旦开始就不可能停下来,如果停下来,就意味着商品生产的停止,利润的丧失,危机的来临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经成为一种“踏轮磨房式的生产”,每一个人都是这种“踏轮”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中脱离。其次,对资本主义进行“绿色”改良也是行不通的。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具有后现代取向的绿色浪漫主义传统所倡导的绿色道路虽对当前的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把生态问题归因于生产力,所追求的低增长与绿色伦理具有“生态乌托邦”倾向,缺乏可行性。另一方面,绿色资本主义倡导的自然资本化、技术改良主义、开放自由市场等解决路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自我解救,仍是以资本的逻辑对待生态危机,不过是对自然掠夺更加有效的手段。
事实上,要想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必须改变资本主义主导的生产体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探索以崭新的生态文明取代旧的工业文明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位置,不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不论是从人类发展史上还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践来看,都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为人类正确看待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了典范,也为真正破解生态危机之困打开了新的历史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