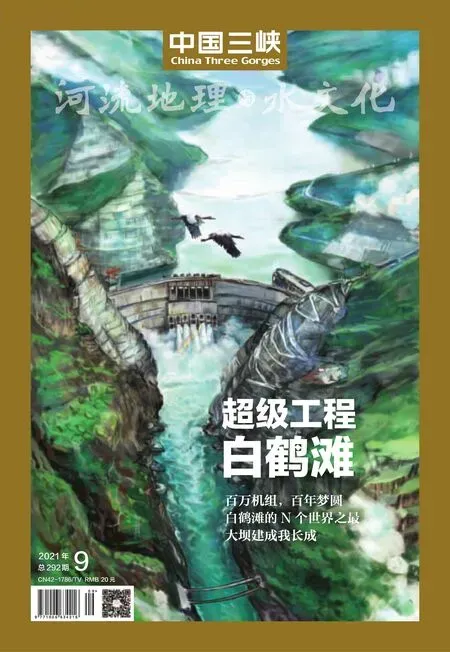金沙江: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走廊
◎ 文 | 胡正刚 编辑 | 王旭辉

蜿蜒的金沙江河谷 摄影/图虫创意
金沙江流域地形地貌复杂,涵盖了河谷、盆地、湖泊、高山等众多类型。山川割据塑造了多元复杂的地理环境,流域内的居民在改造自然环境、繁衍生息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出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
地理环境与多元民族文化
长江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源头。这一认识如今已经深入人心,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岷山导江”的观点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即岷江被视为长江源头。长江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历代典籍对其源头金沙江留下了许多记述。战国时期成书的《禹贡》称金沙江为黑水,在其他典籍中,它又有绳水、淹水的称谓,三国时期称为泸水,诸葛亮《出师表》中“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叙述的就是蜀军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的历史事件。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首次对金沙江水系作了详细描述,但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他没有阐述金沙江与长江干流的关系。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实地考证了金沙江和岷江,首次提出了“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的理论,将金沙江视为长江上游源头,纠正了自《禹贡》以来对于江源的认知。
金沙江源远流长,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四省区,全长两千多公里。其主源沱沱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沱沱河与当曲汇合后称通天河,通天河流至玉树附近与巴塘河汇合后称金沙江,至四川宜宾与岷江汇合后称长江。金沙江流域是一个广大的地理概念,北至黄河上游,东至大雪山与大渡河,南至乌蒙山与珠江,西至澜沧江。流域海拔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山岳占九成以上,是一条典型的峡谷河流。
金沙江与其支流的峡谷,既是联通西南地区的地理通道,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民族走廊”。金沙江流域面积广大,民族众多,难以概述,本文以金沙江河谷沿岸区域作为叙述中心。
在金沙江沿岸的河谷地区,世代繁衍生息着藏、彝、傣、白、纳西、傈僳、苗等少数民族,他们在长期交流中,既保持了族群文化的独特性,又共同塑造了融洽和谐的生存环境。云南省楚雄州、四川省攀枝花市之间的金沙江河谷是“民族走廊”的典型代表,这片区域山高河深,山川阻绝,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地理空间封闭,各民族生存模式相对稳定。苗族、傈僳族居住在山头,以种植耐高寒和干旱的荞、燕麦为主,早年间还保存着狩猎习俗;彝族住山腰,水稻、旱稻、荞麦并重,普遍饲养牛、羊、马等牲畜;傣族在河谷中临水而居,掌握着高超的捕鱼技术,农作物以糯稻、粳稻为主,都是水田种植。因生存环境迥异,这些族群演化出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在长期的相处交流中,也形成了互通有无、和谐稳定的立体生存格局。
中国总体地形西高东低,西南地区是多条大河的发源地,横断山脉中的怒江、金沙江、澜沧江相伴流淌,共同塑造了“三江并流”的地理奇观。“三江地区”自然环境与民族文化丰富多元,民族交流迁徙频繁,形成了民族文化厚重的“藏彝走廊”。学者李绍明先生如此描述藏彝走廊:“藏彝走廊中,迄今有着藏缅语族的各族如藏、羌、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阿昌、景颇、拉祜、哈尼和基诺等民族;其下游则有壮侗语族的傣族和孟高棉语族的佤、布郎和德昂等族以及苗瑶语族的苗、瑶等族聚居其间。这个区域自古以来就是藏缅语族诸民族南下和壮侗、孟高棉语族诸民族北上的交通走廊以及他们汇合交融之所。”
金沙江流域文化内涵丰富,除了藏彝走廊外,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也在这一区域内交融汇合。藏彝走廊、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含义清晰,各有侧重,但它们关联密切,同出一源,融自然与人文景观为一体,文化内核中流淌着金沙江的血与水。
鱼神重返村寨
金沙江流域是一座民族文化的富矿,朝着任何一个方向挖掘,都会有巨大的收获。金沙江河谷傣族是分布在中国最北边的傣族,他们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在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领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金沙江沿岸的傣族作简要概述,可以对金沙江作为民族走廊的内涵和意义有深切感知。

金沙江主源沱沱河 摄影/图虫创意
金沙江河谷傣族大多居住在金沙江沿岸地带,主要生活在金沙江上游的华坪、大姚、元谋等地。与云南南部西双版纳、德宏的傣族不同,金沙江河谷傣族不信仰小乘佛教,而是信仰带着原始宗教色彩的万物有灵论,保存着祭山神、龙神、树神、谷神的习俗,生产生活模式差异也比较大,鱼神崇拜和祭祀是最能体现他们丰富而独特的神灵信仰和祭祀仪式。
鱼神崇拜是金沙江河谷傣族的普遍信仰,这种信仰模式与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关联密切。金沙江河谷傣族居住在江边,金沙江及其支流有丰富的鱼类资源。在禁渔令施行之前,除了种植、畜牧外,捕鱼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维持生计的方式。长期与鱼相伴相生,这个民族也产生了独特的鱼神信仰。禁渔令施行后,鱼神崇拜仍旧作为文化信仰留存下来,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金沙江河谷傣族沿江而居,分布范围广,他们的鱼神崇拜核心相同,祭祀的具体细节略有差异。例如,每年农历三月初七,楚雄州大姚县湾碧乡的傣族都要举行隆重的祭鱼神仪式,当地人称之为“窝巴节”。“窝”的意思聚会,“巴”指鱼,“窝巴”即“鱼的聚会”。当地傣族群众认为,流经村庄的多底河从高处的山谷汇入山脚的金沙江,流淌的江水带走了谷魂和鱼魂。为了确保丰收,每过一段时间就需要举行祭祀仪式,把谷魂和鱼魂从金沙江中召回村寨。

窝巴节接鱼神 摄影/马淑吉
“窝巴节”前夕,村中长者会用木头雕刻两条木鱼,一条涂为青色,一条涂为红色,它们是鱼神的化身。三月初七日,村民穿戴盛装,集体来到金沙江边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祭祀仪式结束后,人们将两条木鱼放入金沙江,再沿流经村寨的支流拉木鱼逆流而上,回到村寨,把木鱼放到村里的水潭中,代表鱼神回到了村寨。祭祀鱼神后,村民会相互泼水祈福,这一环节与傣族的传统节日泼水节有密切关联。
山川异域与他者认知
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存模式,同时也塑造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文化风俗,当外来者与本土文化接触时,难免会因陌生而将初次接触的区域视为“异域”。金沙江既是地理分界线,也是气候、文化的分界线,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云南的认知。
公元1535年,谪戍云南的杨慎回四川省亲,抵达滇川界河金沙江边时,在元谋县境内的金沙江巡检司留宿,滔滔江水和皎皎月光让杨慎心潮起伏,彻夜难眠,提笔创作了一首题为《宿金沙江》的诗歌:
往年曾向嘉陵宿,驿楼东畔阑干曲。
江声彻夜搅离愁,月色中天照幽独。
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
江声月色那堪说,断肠金沙万里楼。
把《宿金沙江》放到具体的时空中阐释,对作者身处的境况会有更深的体会。写作这首诗时,杨慎已经在流放地云南度过了十年谪戍生涯,朝廷始终没有一丝宽宥他的迹象,常年远离故土和亲人,且归期未卜,前程黯淡,诗人内心的悲伤孤寂不言而喻。

杨慎题写的“不可不饮”石刻 摄影/ 杨红文 / FOTOE

《杨慎簪花图》 摄影/ 陈洪绶 / FOTOE
谪戍云南期间,杨慎曾七次往返于故乡四川新都与戍地云南之间,金沙江是云南与四川的界河,杨慎的每一次行程,都需要渡过金沙江——金沙江同杨慎的命运紧密地关联在一起,既是他旅途的中转站,也是他人生的重要分界线。江北,是念兹在兹的故乡,是深沉的离愁;江南,则是让他“断肠”的“瘴海”。就连同样的月色,也因一江南北的区别而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质。在故乡,虽然愁绪如江流一样彻夜不息,但月色“幽独”,心境也清新刚健;在云南,月光仿佛成了有形之物,沉甸甸地压在杨慎心头,让他萌生了一种“那堪说”的断肠之悲。
以时间为坐标,杨慎的人生以嘉靖初年的“议大礼”为分界线,如果以空间为坐标,那么金沙江则是横亘在他命运中的界河。谪居云南期间,杨慎为自己取了数个字号:博南山人、博南山戍、滇南戍史、金马碧鸡老兵……博南山位于云南西部,金马碧鸡指代滇池周边区域,这些自号,是杨慎对命运的接受与确认。
在金沙江畔的元谋县,杨慎除了创作《宿金沙江》描绘江畔独宿的孤苦心境外,还创作了另一首题为《元谋县歌》的诗歌,记述了元谋的险恶环境以及旅途的艰险:
遥望元谋县,塚墓何累累。
借问何人墓,官尸与吏骸。
山川多瘴疠,仕宦少生回。
三月春草青,元谋不可行。
九月草交头,元谋不可游。
嗟尔营营子,何为欻来此。
九州幸自宽,何为此游盘。

云南元谋浪巴铺土林 摄影/图虫创意
前诗称云南为“瘴乡”,后诗则认为金沙江边的元谋县“山川多瘴疠,仕宦少生回”,流露出一种荒凉险恶的氛围,这与杨慎戍滇时的心境相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旧时外界对云南的印象。
在一首题为《南枝曲》的诗歌中,杨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渡烟江来瘴国,毒草岚丛愁箐黑。”在这首作品中,杨慎强调了金沙江作为地理分界线的属性,认为渡过金沙江,即到了“瘴国”云南。值得细细体味的是,在“瘴国”“毒草”“愁箐黑”等词汇共同构建的语境中,杨慎笔下的“烟江”,显然与“烟波江上使人愁”“烟江新燕下”的语意不同,本意是“烟瘴之江”。
作为一名云南人,每次阅读古人关于云南的诗文,“瘴疠”“蛮荒”这类词语出现的频率之高,以及其字面背后蕴藏的绝望、悲哀、无助,都让我不寒而栗。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们仿佛已经成为云南的代名词。
杨慎以戍卒的身份来到云南,他在《遥夜吟》中自陈“予乃投荒人”,可以视为对自己身份与命运的自我认知。“投荒人”的自况,使杨慎在谪戍期间创作的诗文,大多带着浓郁的悲凉色彩,而他对云南认知,也常渲染着这一感情基调,如“万里炎荒万里身,销魂何事别离频”“山高瘴疠多,鸿雁少经过”“万里向炎隅,五载困羁孤”“天隅感流落,日暮吟蹉跎”“荒途不可践,为君愁我心”“大荒有晤语,空石多好音”“飘蓬落羽向南荒,憔悴荣华宁有常”“二妙风流绝代无,谈笑浑忘穷海谪”“转蓬绝域犹羁旅,细柳新营尚甲兵”“所思眇天末,吊影自荒陲”“悲来瘴海凋霜鬓,愁听山楼咽暮笳”“一辞故国三千里,独戍遐荒十六春”……
杨慎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云南度过的,他对云南有深厚的感情,创作了大量诗文赞美云南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为后人留下了富饶的文化宝库。昆明有“春城”美誉,源自杨慎的诗歌“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需要一分为二的是,在杨慎的认知里,云南是这样一个地方:万里炎荒、山高瘴疠多、炎隅、天隅、荒途、大荒、南荒、穷海、绝域、荒陲、瘴海、遐荒……这些认知,贯穿于杨慎的整个戍滇生涯,是河流地理对人们认知产生深远影响的典型例子。
从“南荒”到沃土
杨慎经金沙江边的元谋往返四川与云南间的道路,是历史悠久的“姚嶲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条道路的部分路段有所变迁,但路线总体保持一致。“姚嶲路”是川滇间的重要通道,也是有文献记载的较早进入云南的道路,历史上又被称为“建昌道”“零关道”“西川道”“清溪关道”。这条道路经邛(今四川邛崃)、雅(今四川雅安)、建昌(今四川西昌)从会川(今四川会理)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姚安、白崖(今大理弥渡),从祥云中转,往东可以去往大理,往西可以到达昆明。
三国时期的公元225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南征云南地区,“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泸”即金沙江,而蜀军具体的渡江地点,经后世学者考证,位于今楚雄州永仁县北部苴却拉鲊渡口,其行军路线大体与“姚嶲路”重合。
唐朝与南诏时期,南诏的政治中心位于滇西大理,“姚嶲路”是当时主要的入滇通道。到了宋代,这条道路的地位逐渐下降。元朝重视对云南的经营,沿“姚嶲路”设立了24个驿站。因特殊的地理气候及受瘴疠影响,这条道路通行情况不佳,《元史·地理志》记载建昌路泸州“有泸水,深广而多瘴,鲜有行者,终夏常热,其源可燖鸡豚。”明代的“姚嶲路”(当时称“建昌路”“建越路”),路线基本延续了元朝时昆明至成都的驿路。“姚嶲路”曲折陡峭,杨慎经祥云段时,作诗形容此道路:“路绕羊肠转,云从马首开。”明中期以后,随着另外两条入滇道路的修建,“建昌路”逐渐阻绝,杨慎创作《宿金沙江》的一百余年后,崇祯十一年(1638),旅行至云南元谋的徐霞客途径金沙江元谋段时,记录了这条道路的情况,“江驿向有驿丞,二十年来,道路不通,久无行人,今止金沙江巡检司带管”。

云南省金沙江大桥 摄影/视觉中国
时代向前发展,金沙江的潜力不断被开发,其蕴藏的丰富能源,让它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一座座公路和铁路大桥横跨江面,连通川滇两省,金沙江从天堑变为通途。交通状况的改善,加速了金沙江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在深刻影响着西南地区的社会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