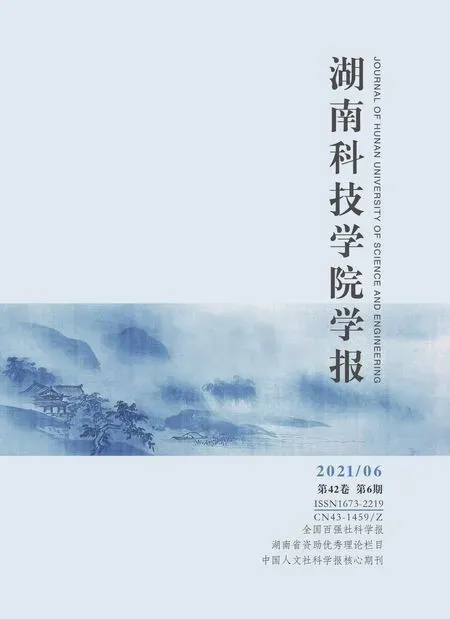再议安大简《诗经》的语气词“氏”
陈梦兮
再议安大简《诗经》的语气词“氏”
陈梦兮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毛诗中的语气词“只”,安大简《诗经》作“氏”。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三个明确的原则可以确定“只”和“氏”与其他语气词的关系。“氏”确实即传世文献中的“只”。传世文献中的“只”“也”“兮”是三个独立的语气词,分布和功能有相近之处。但“只”与“也”更加接近,这是“只”“也”历时异文产生的前提。二者可以表陈述、判断的语气,表判断语气时“只”不如“也”强烈。“氏”与“是”战国楚简同篇中也大量混用,有了代词“氏”向语气词“只”语法化的条件。近指代词、名词“姓氏”之“氏”战国使用“是”字形频度高,故语气词由字形“氏”承担。在战国楚简文献中用为代词的“氏”语法化为语气词的条件有两个,一是位于陈述句末,二是谓语动词可以带空宾语。
安大简;诗经;语气词;氏;只
安大简《诗经·柏舟》中“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一句,有了新的异文,引起学界讨论:
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传世毛本)
母可天氏,不京人氏。 (安大简本)
关于“只”“也”和“氏”字词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王志平[1]、何琳仪[2]先生认为《孔子诗论》的“氏”读为“只”,后来不少学者认为上古汉语中的语气词“只”是对“也”的讹写或误读,邬可晶先生指出“氏”读为“只”在语音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并认为语气词“只”是存在于战国、西汉文献中的语气词,字形写作“氏”[3]。黄德宽先生根据新出安大简的异文,认为对上古汉语语气词“只”“也”“氏”的关系暂时还不宜作出最终结论[4]。陈萌萌先生搜集了《诗经》中ATAT、ATBT、AT1BT2三种句式,分析AT1BT2句式的特点,认为“母也天只”即“母亲啊是我的天”[5]。近日,季旭升先生也就此撰文,肯定了陈萌萌的结论[6]。
陈文立意的根本是认为此句两个语气词不同,即AT1BT2句式在表义上有特殊性。邬可晶文中已经指出《邶风·旄丘》“叔兮伯兮”,敦煌本作“叔也伯兮”,同一句诗可以使用不同语气词。另外,陈萌萌归纳的ATAT、ATBT、AT1BT2句式性质杂糅,包含了“归哉归哉”(动词谓语+语气词)、“宽兮绰兮”(形容词谓语+语气词)、“悠哉悠哉”(形容词状语+语气词)、“日居月诸”(名词主语+语气词)等多种情况,与要讨论的“母也天只”(名词主语+语气词)不是完全同质的。
季旭升先生提出的释法,讲“母也天只/母兮天也”释为主谓句,“天”是名词谓语,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但这跟语气词的使用没有关系,“也”本身可以在名词主语之后标志话题,也可以用在句末煞句,即便该句作“母也天也”,要解释为“母亲(这里没有‘啊’因为句中的‘也’不携带语气功能,只是标记主题)是我的天啊”也无不可,至少在语法上是成立的(如《论语》“雍也弗闻也”,句中、句末都有“也”,“雍”和“弗闻”仍然是主谓短语)。季旭升的释读不存在语法障碍,但句义不从毛传而依宋儒解读,需要更多的文献证据证明语义是成立的。
研究传世毛本“母也天只”和安大简本“母兮天氏”,都不应孤立来看,至少是要从整句来看其语法位置。所以光看AT1BT2句式意义不大,以“母兮天氏,不谅人氏”为例,应该表述为:语气词“氏1”在句中位置,附在呼语后。语气词“氏2”在句末位置,用于否定句,附在动词性谓语后。然后我们再对其他出土文献中的语气词“氏”进行描写,着重从已有的出土文献材料与传世文献材料中已知的语气词,与“氏”的用法作比对。
一 三个原则看语气词“氏”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的研究应该明确基于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共时材料异文所反映的问题与历时材料所反映的问题不同,所以二者要分别分析,不混为一谈。
(1)《诗》云:淑人君子,其义一也。(郭店简《缁衣》39)
(2)《诗》云:淑人君子,其义一也。(上博简《缁衣》20)
(3)《鸤鸠》曰:其義一氏,心如結也。(上博简《孔子诗论》22)
(4)“淑人君子,其义一也。”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君子慎其独也。
(郭店简《五行》16)
(5)鸤鸠在桑,其子七氏。淑人君子,其宜一氏。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君子慎其独。 (马王堆帛书《五行》)
(6)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传世本《诗经》)
(7)《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一也。(《礼记·缁衣》)
(8)故《诗》日:“淑人君子,其仪一也;其仪一也,心如结也。”君子其结于一乎?(《淮南子·诠言》)
以上“也”“氏”的材料,(1)(2)(4)都是战国共时材料,语气词的使用存在共性,都用“也”在句末表示确定、判断的语气。(3)之所以不同,是句式与(1)(2)(4)不同,隶属于两句,并不构成真正的异文;而(4)的时代是战国时代,(5)是西汉早期,反映的问题这段时期是从“也”到“氏”的历时变化(也可能是底本不同)。(6)是传世本《诗经》,体现出来的是“兮”对“氏”的全面替换。(7)(8)是传世本《礼记》和《淮南子》,均使用“也”煞句,与(1)(2)(4)相同,辗转传抄之后用字并没有发生变化。

图1 “淑人君子,其仪一△”中语气词△的使用替换
“也”和“兮”本身也存在历时的替换关系:
(9)摽有梅,其实七也。(安大简《诗经·召南·摽有梅》)
(10)摽有梅,其实七也。(阜阳汉简《诗经·召南·摽有梅》)
(11)摽有梅,其实七兮。(传世本《诗经·召南·摽有梅》)

图2 “摽有梅,其实七△”中语气词△的使用替换
“也”和“只”也存在历时的替换:
(12)乐也君子,福礼将之。(安大简《诗经·周南·樛木》)
(13)乐只君子,福履将之。(《毛诗·周南·樛木》)

图3 “乐△君子”中语气词△的使用替换
再看本文讨论的《柏舟》中的句子:
(14)母兮天氏,不京人氏。 (安大简本)
(15)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传世毛诗)

图4 “不谅人△”中语气词△的使用替换

图5 “母△天只”中语气词△的使用替换
图1至图5体现出“只”“氏”“兮”“也”的密切关系:“也”和“兮”可以顺逆双向替换,“也”可以被“氏”替代,“氏”可以被“兮”替代,“也”“氏”都可以被替换为“只”。同时可以看出出土战国《诗》类文献使用“也”的频率是最高的,不如传世《诗经》语气词系统复杂。
二是异文现象可能是形、音、义相关,也可能是完全不同、但用法相近的语气词换用。在不同文体中,甚至用法不相近的语气词换用也是可能的。
这一点邬可晶已指出:“古书中的语气词‘只’有‘也’的异文,并不能证明‘只’本应作‘也’。”
《诗经·鄘风·柏舟》“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毛传释为“母也天也,尚不信我”,用“天也”解释“天只”。另外上博简《孔子诗论》有“既曰天也”,不少学者认为是指《鄘风·柏舟》一句。“只”“也”关系就此展开讨论。即便存在同时代“母兮天氏”(安大简《诗经·柏舟》)换为“母也天也”(《孔子诗论》)的语言事实,也并不证明这两句语气相同。因为前者是诗歌体,后者是评论体,众多文献材料显示古人“引用”并不完全照搬,所以不同语体使用不同语气词是完全可能的。
三是共现或连用的字,应该视作两个词。
同句共现或连用的语气词,宜视作两个词。如今本《诗经》“河水清且涟猗”,安大简本作“河水清且涟可”(战国楚简中的“兮”均写作“可”);《尚书·泰誓》“断断猗”,《大学》引作“断断兮”,都是“猗”“兮”异文,且古文字字形上“猗”“兮”都是从可得声的字。但《吕氏春秋》记载南音之始“候人兮猗”,语气词“兮”“猗”连用,就不能说“兮”“猗”是同一词。
上文(1)(2)(4)(5)反映了“氏”“也”的历时替换。但上博简《孔子诗论》“其義一氏,心女(如)结也”,既然“氏”“也”共现,他们就应判定为两个不同的语气词。
上文(6)可见“兮”和“氏”异文现象。但由于安大简本《诗经》“母兮天氏”,“兮”“氏”共现,即使有二者历时异文,也不能把二者作同一考虑。
所以,今本《诗经·柏舟》“母也天只”、《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诸侯归晋之德只,非归其尸盟也”,语气词“也”“只”共现,他们就不应该是同一个词。即便存在共时或历时异文,我们也宜从“用法相近”进行考虑。
综上我们可以知道:氏≠也,氏≠兮,只≠也。
然而,只有“氏”“只”作为语气词尚未共现,且有异文,语音上又相近,这个异文可能记录的是同一个语气词。邬可晶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楚辞·大招》全篇都使用语气词“只”,其中有2句与“兮”共现:“魂兮归来,恣所择只”“魂兮归来,正始昆只”;有26句与“乎”共现。除此之外该篇没有其他语气词。而“乎”在不表传疑时与“兮”是相同的,也有异文,华建光怀疑是同一语气词的不同写法[7]。这种“兮/乎”与“只”共现的强烈偏好,与安大简“母兮天氏,不谅人氏”联系起来看,“氏”的用法也是与“只”相近的。
二 传世文献中的“只”
语气词“只”不见于出土文献,在传世文献中数见。王显认为语气词“只”表示深切悲痛的感情色彩,并指出“轵”“枳”“咫”都是“只”的借字[8]。
传世文献中的语气词“只”可分为三类。
一是位于句中:
(1)乐只君子,福履将之。《毛诗·周南·樛木》
(2)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毛诗·小雅·南山有台》
(3)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毛诗·小雅·采菽》
传世文献语气词“只”仅在以上三例用于句中。“乐只君子”的“只”在安大简写作“也”。“乐只君子”是一个主谓易位句,“只”附在形容词谓语上。这种主语后置式在《诗经》中常见于“矣”:
(4)展矣君子,实劳我心。(《毛诗·邶风·雄雉》)
(5)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毛诗·小雅·车攻》)
(6)哿矣富人,哀此惸独。(《毛诗·小雅·正月》)
(7)皇矣上帝,临下有赫。(《毛诗·大雅·皇矣》)
(8)休矣皇考,以明保其身。(《毛诗·周颂·访落》)
曹银晶认为这种“矣”表“状态如此”和“感叹”[9]。而“允矣君子”上博简《缁衣》、郭店简《缁衣》和汉石经均作“允也君子”。由句中“也→矣”“也→只”的历时替换,可知今本主语后置式、附在形容词后的“只”和“矣”,出土文献都作“也”。“也”“矣”可以连言为“也已矣”,属于连用,且二者区别明显,这里不能由二者的替换关系就将二者等同。“也”“只”同样。
所以,目前可信的材料,“只”是只位于句末的。最常见“只”附在谓语后。黄易青强调,这种谓语后的“只”不等于“也”,但可以换作“兮”[10]。
(9)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毛诗·鄘风·柏舟》)
(10)仲氏任只,其心塞渊。(《毛诗·邶风·燕燕》)
(11)诸侯归晋之德只,非归其尸盟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9)中两个“只”,作用实际上是不同的。前一个“只”位于句中,附在呼语;后一个“只”位于句末,附在VP谓语上。
与“只”类似,“兮”经常附在呼语上[7]60如《论语》“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母也天只”(“母兮天氏”)的“只/氏”附在呼语上。可以附在呼语上的语气词有“也”“兮”和“乎”;在诗歌体中,附在呼语后的是“兮”,即“只/氏”与“兮”附在呼语上这一点与“兮”相近。安大简“母兮天氏”可知,“兮”与“氏”的功能可能存在不同。
(10)郑笺:“任,以恩相亲信也。”故其中的“只”附在动词谓语后,又见于《楚辞·大招》“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测只。”这里“也”和“兮”语法上都成立,只是作用不同:“也”表确定,“兮”是语气的拖拽和延长。
(11)的“只”位于叙述句句末,所附谓语是动宾短语。后一句是表判断的“非VP也”,“只”在前一句应也加强判断和确定的语气。文献中常见“VP也,非VP也”句:
(12)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
(13)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 (《孟子·告子下》)
对比“诸侯归晋之德只,非归其尸盟也”,这个“只”应该是与“也”功能相同,但所表判断和确定不如“也”强烈。
另外,“只”还与“且”连用,用于句末:
(14)其虚其邪,既亟只且。(《毛诗·邶风·北风》)
(15)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毛诗·王风·君子阳阳》)
要了解“只且”的功能,先要解释《诗经》中的“且”。
(16)不见子都,乃见狂且。(《毛诗·郑风·山有扶苏》)
(17)椒聊且,远条且。(《毛诗·唐风·椒聊》)
单独的语气词“且”,(16)附在动词谓语之后;(17)毛传:“条,长也。”两个“且”,前一个在句中,附在名词主语上,后者位于句末,附在形容词谓语上。“也且”为语气词连用,张玉金指出“只且”起加强咏叹的作用,“且”也应起加强咏叹的作用[11]。朱承平曾提出“陈述语气词>疑问语气词>反问语气词>感叹语气词(>读作‘先于’)”的连用规则[12]。杨永龙指出这种序列是因为可以在陈述句末尾增加相关句类标记转换为疑问句、反问句、感叹句[13]。如果“只”是陈述语气词,“且”有可能是表感叹的语气词,“只且”类似“也夫”“也哉”。
语气词连用中“也”“矣”二字较为活跃,其中连用序位第一字“也”是最常见的,如也哉、也矣、也夫……[7]127,不存在“兮”与其他语气词组合的例子。所以“只且”的“只”,功能与“也”近,与“兮”远。
除了“只”,文献中还有其变体“咫”和“轵”:
(18)吾不能行咫,闻则多矣。(《国语·晋语》)
(19)是知天咫,安知民则?(《国语·楚语》)
(20)许由曰:“而奚来为轵?”(《庄子·大宗师》)
(18)今本作“吾不能行也咫”,王引之《经传释词》改为“吾不能行咫”,并指出“咫犹耳也”。“咫”与“矣”共现,是典型的“咫”表静止性事实,“矣”表变动性事实。出土文献中也常见“也”与“则/而……矣”的搭配:
(21)叹,思之方也。其声变,则心从之矣。(上博简《性情论》20)
(22)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而德气塞于四海矣。(上博简《民之父母》简5-6)
这里(18)的“咫”与(21)(22)的“也”用法相同。
(19)“是……咫”,与典型的判断句“是……也”也相同。古书中也不乏类似(19)的句式,如“是贤君也,安可伐?(《战国策·中山策》)” ,“咫”的位置用“也”。
(20)《庄子》一例“轵”用于提问句,“也”也有这个功能,而“兮”只用于陈述句。上面(18)至(20)例的“咫”与“轵”都与“也”功能相近。
还有一种“枳”“咫”用在句中,杨树达认为相当于“则”的用法[14]:
(23)德枳维大人,大人枳维公,公枳维卿,卿枳维大夫,大夫枳维士,登登皇皇,君枳维国,国枳维都,都枳维邑,邑枳维家,家枳维欲无疆。(《逸周书·小开》)
这些“枳”都在句中,附在名词主语之后,并且与“维”组合。“也”“兮”都可以附在名词主语之后。
传世文献中的语气词“只/氏”出现次数不多,但经过逐一分析,可知“只”的用法一类接近“也”,一类接近“兮”。
上文提到由于共现,“只≠也”“只≠兮”,通过比对发现此结论不误。传世文献中的语气词“只”是一个独立的语气词,战国时期写作“氏”,它与也、兮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因三者有相同处,便存在历时替换的现象。“只”“也”功能上的相近,历时的替换也十分合理。总体上,传世文献中的语气词“只”与“也”功能更为接近,但所表判断和确定不如“也”强烈。
三 出土文献中“氏”

表2 清华简《系年》篇“是”“氏”的使用情况

表3 清华简《子仪》篇“是”“氏”的使用情况

表4 清华简《四告》篇“是”“氏”的使用情况

表5 上博简《彭祖》篇“是”“氏”的使用情况
《系年》《子仪》《四告》偏向于用本字,《彭祖》相反。
郭店简《缁衣》简3“好氏贞植”,上博简《缁衣》简2作“好是正植”。
另外,上博简《缁衣》同篇简9“氏”还用为代词:“集大命于氏身。”根据冯胜君的研究,上博简《缁衣》和《彭祖》为同一书手所书写[15]。《彭祖》“氏”读作“是”,“是”读作“氏”。《缁衣》“氏”用为代词,与《彭祖》是相同的。
从数据上来看,以上统计数量较少,职能分立并不明显。但在安大简《诗经》中,二字的使用有较为明显的分工:

表6 安大简《诗经》篇“是”“氏”的使用情况
在《葛覃》一篇“是刈是濩……言告师氏”,“氏”和“是”承担了不同的功能。
同篇之内使用“是”“氏”表相同的词,见于以下四篇:

表7 上博简《曹沫之陈》篇“是”“氏”的使用情况
《曹沫之陈》唯一的一例“氏”见于简64:
(1)庄公曰:“沫,吾言氏不,而毋惑诸小道欤?吾一欲闻三代之所。”
其中“氏”的读法及所处句子的断句都有争议。李零读“氏不”为“是否”,陈剑读“氏”为“寔”(是语气词,始于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九“是,犹寔也”。),单育辰将此句释为“实在不正确”[16]。陈斯鹏引《左传》“其君是恶,其民何罪”,认为“是”表强调[17]。诸家将“氏”看作表强调的词不误。

表8 清华简《管仲》篇“是”“氏”的使用情况

表9 上博简《季庚子问于孔子》篇“是”“氏”的使用情况

表10 上博简《凡物流形》甲篇“是”“氏”的使用情况

表11 上博简《凡物流形》乙篇“是”“氏”的使用情况
以上诸篇均是“是”“氏”表代词是,不用为“氏”。同样的现象也见于新蔡简;
(2)择日于是期。(新甲三·4)
(3)以其不安于氏处也。(新甲三·132)
“是”“氏”都用为指示代词,不用为“氏”。因为代词“是”本身是一个高频词,而“氏”是低频词,所以用为“是”例证更多。
数量上是使用“是”字形偏多,其原因还有待研究。
使用“是”或“氏”同一种字形,用为不同的词,见于以下三篇:

表12 上博简《子羔》篇“是”的使用情况

表13 上博简《容成氏》篇“是”的使用情况

表14 上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是”的使用情况
可以看出都是使用“是”这个字形,大部分也还是用作“是”。
《孔子诗论》仅使用“氏”,5例均用为代词“是”。其中简22“其仪一氏,心如结也。”也是比较重要的材料。《孔子诗论》和《子羔》二篇是同一书手书写的,但《孔子诗论》仅使用“氏”,《子羔》仅使用“是”,应该是底本的不同。
通过以上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如下事实:战国楚简中除了个别篇目外,“是”“氏”没有明显的职能区分。有时二者出现在同一篇中,混用;有时一篇中仅使用其中一字,根据底本不同会有偏好,但更多地使用“是”这个字形。
在这种混用前提下,用为代词的“氏”有机会语法化为语气词,由字形“氏”承担分化出来的语气词功能。
四 从代词到语气词的语法化
王引之《经传释词》“些”条指出“斯”“呰”都训为“此”,且声音相近,“二者又皆为语词”,可见一些指示代词与语气词有密切关联。王志平提指出些、斯、此、只、是声音和用法皆近,应为同源,又说“这些字又都有指代词的用法,语助词的用法应当是由代词虚化而来”。[18]汉语中的语气词绝大多数来源于实词,其中极大一部分语气词来源于代词。吕叔湘指出古代汉语语气词“焉”由指示代词演变而来,因此“焉”带有指示引人注意的语气[19]。刘利、李小军指出来源于代词的语气词有有者、焉、尔、是、诸[20]。方友国对先秦汉语语法化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涉及语气词其、斯、而的语法化过程[21]。
方友国指出处于“句末位置”是转化为语气词的原因:
一般来说,句末是“乎”“哉”“焉”“也”等语气词的特定位置……这种“为”因处于句末的位置关系,必然向语气词转化。先秦汉语中,句末位置本身也有使某些词转化为语气词的特殊作用,如常处于句末的指示代词“诸”“焉”往往具有语气词特定就是证明。
“氏(是)”和“此”作为指示代词,可以作宾语,但以作介词宾语如“以此”“以是”“于此”“于是”为常见。作动词宾语二者都可以位于句末:
(1)叔孙指楹,曰:“虽恶是,其可去乎?”(《左传·昭公元年》)
(2)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左传·宣公十八年》)
(3)晏婴闻之,曰:“君固无勇,而又闻是,弗能久矣。”(《左传·襄公十八年》)
(4)今其人在是,胜也何敢言事?(《战国策·赵策三》)
(5)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毕矣。(《战国策·赵策三》)
(6)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
(7)曰:“姑舍是。”(《孟子·公孙丑上》)
(1)~(7)的“是”位于分句句末,作为动词宾语。“是”作动词宾语,在上古汉语中,一般是前置的。赵远远指出《诗经》时期“是”作为动词宾语需要前置,但在《左传》里已经有了不前置的例子[22]。位于陈述句末,这是代词“是”语法化的条件。代词“是”语法化的另一个条件是,所在句的动词既可以带宾语,也可以带空宾语。下面两例可以体现语法化过程,(11)中的“是”是代词,作“行”的宾语;(12)的“咫”是语气词:
(11)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毕矣。(《战国策·赵策三》)
(12)吾不能行咫,闻则多矣。《国语·晋语》
(11)中位于句末的代词“是”逐渐虚化为(12)句末语气词,语法化的动因一是代词“是”作谓语动词宾语,二是代词“是”不前置,位于句末,三是动词“行”本身可以带空宾语。
(13)许由曰:“而奚来为轵?”《庄子·大宗师》
郭象注:“崔云:‘轵,辞也。’李云:‘是也。’”西晋李颐以“是”释“轵”,可作为代词“是/氏”演变为语气词“只”的佐证。
[1]王志平.《诗论》发微[M]//华学(第6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2]何琳仪.沪简《诗论》选释[M]//新出楚简文字考.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3]邬可晶.上古汉语中本来是否存在语气词“只”的问题的再检讨——以出土文献所见辞例和字形为中心[M]//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4]黄德宽.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二题[J].中原文化研究,2017(5):5-9.
[5]陈萌萌.从出土材料探究《毛诗》之三种句式[D].“国立”台湾大学,2019.
[6]季旭升.从安大简与上博简合证《孔子诗论》“既曰天也”评的应是《鄘风·君子偕老》[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71-75.
[7]华建光.战国传世文献语气词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8]王显.谈虚词“只”和“轵”、“枳”、“咫”[M]//语言研究与应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9]曹银晶.也、矣、已的功能及其演变[D].北京大学,2012.
[10]黄易青.上古诗歌语气助词“只”“些”“斯”“思”“止”的词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8(1):49-59.
[11]张玉金.出土先秦文献虚词发展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
[12]朱承平.先秦汉语句尾语气词的组合及组合层次[J].中国语文,1998(4):299-303.
[13]杨永龙.先秦汉语语气词同现的结构层次[J].古汉语研究,2000(4):23-29.
[14]杨树达.词诠[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5]冯胜君.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 2007.
[16]单育辰.《曹沫之陈》文本集释及相关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07.
[17]陈斯鹏.战国简帛文学文献考论[D].中山大学,2005.
[18]王志平.《诗论》发微[M]//华学(6).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3.
[19]吕叔湘.文言虚字[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20]刘利,李小军.主观性与语气词“焉”的语法化[M]//汉语史研究集刊(10).成都:巴蜀书社,2007.
[21]方有国.先秦汉语实词语法化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 2015.
[22]赵远远.近指指代词“是”和“此”[D].温州大学,2011.
H109.2
A
1673-2219(2021)06-0119-06
2021-06-15
2019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项目“湖南出土战国楚简研究”(项目编号XSP19YBZ 117)。
陈梦兮(1987-),女,四川自贡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
(责任编校:潘雁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