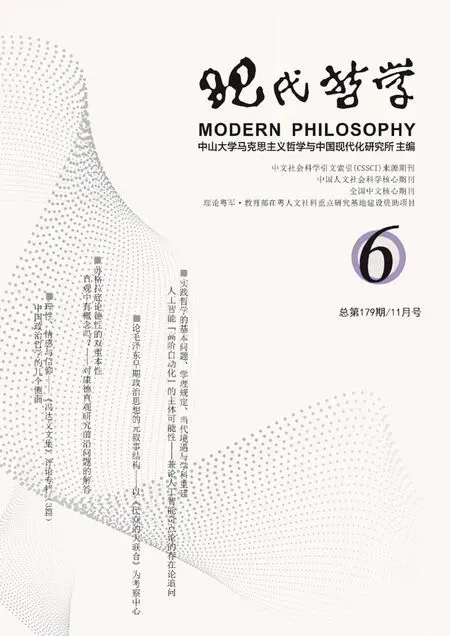苏格拉底论德性的双重本性
田书峰
一、苏格拉底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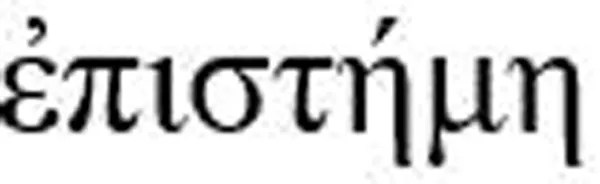
首先,苏格拉底通过诘问法(elenchus)所寻求的是关于德性的普遍定义。这显示出一种从关心外在的自然到探寻人的内在伦理特性的转向。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到人间,其伦理学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获得幸福:通向幸福的唯一正确通衢是德性,而德性就是对于善的知识。如此,苏格拉底伦理学既可以被认为是幸福论,也可以被说成是德性论、理智主义伦理学。苏格拉底的德性伦理学并没有受到后世学者们的太多质疑,但学者们对幸福伦理学则解释不一。这是因为,我们可以对苏格拉底所说的人人欲求幸福作出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解读。就像有些学者毫不避讳地主张的,我们所做的任何行动都是为了最大化地获得自己的幸福,完全为了他人的缘故而行动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的行动不能促进自己的幸福最大化,那么我们的行动就是非理性的(4)比如,厄尔闻(Irwin)就这样来解释苏格拉底的幸福论。(See T. Irwin, Plato’s Eth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3.)。但是,苏格拉底所说的人人欲求幸福是一种普罗大众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幸福主义吗?或者我们必须对苏格拉底的幸福主义伦理学作出自我中心式的解释吗?笔者认为,要解决这里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德性的概念以及德性与幸福之间的关系。
在苏格拉底对德性的讨论中,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两种核心要义。其一,德性是关于善和恶的知识,这是对德性的理智主义阐释(5)在《欧绪弗伦》(Euthyphro)中,虔敬就是一种关于如何达致一种好的神人关系的道德知识。对神和人来说,唯一的善都是德性和智慧,所以真正的虔敬就是追求德性和智慧,这是对神所做的最好的献祭和祈祷。在《凯米德斯》(Charmides)中,节制的知识本质也展露无遗,节制是一种特殊的“有关知识的知识”,有节制的人有自我意识地去行动和生活,并且能够说出这样做的理由或原因。在《拉克斯》(Laches)中,勇敢呈现为一种“关于可怕的和给人希望的东西的知识”或“关于所有的善和恶的知识”。在《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中,苏格拉底通过快乐论证揭示了知识的力量,只有智慧或知识(这里指测量技艺)让我们不受显像的力量之迷惑。(参见田书峰:《苏格拉底论德性即知识》,《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其二,德性是内在的或不可改变的善,德性是在其自身值得欲求的善,即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善,不会因人因地因时而有所变化。苏格拉底自始至终都坚持这两种论点。如果我们不从德性与幸福的关系视角来审视这两点,那么还是不能获得一个关于德性的整全图景。比如,为什么人需要有关善和恶的知识呢?苏格拉底会回答说,因为只有这样的知识才能使我们达致幸福,而无知会让我们不幸福,《欧绪德牧斯》(Euthydemus)就是主要讨论这个问题。关于第二点,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德性在其自身就值得欲求,是自在(per se)的善?苏格拉底会回答说,因为虽然德性与幸福联结在一起,但二者的联系并不是在康德的分析判断的意义上,即德性的概念自身之内就有幸福,或幸福的概念自身之内就有德性,因为德性也是一种独立的自在的善。
苏格拉底并没有清晰地告诉我们德性与幸福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甚至,他的观点有时模棱两可、并不一致。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从德性与幸福的关系视角,来重新探求或揭示德性的内在本质和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对苏格拉底的幸福主义作出自我中心式的解释。这是因为,幸福与德性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或至少是幸福的充足条件,尽管这种联系不是分析意义上的,因为德性在其自身也有一种独立的价值。首先,我对德性与幸福之间的关系的可能性逐一进行分析,虽然德性充足论和德福等同论更符合苏格拉底的观点,但这两种关系模式仍然会面对很多文本和义理上的困难。随后,我试图证明德性的双重地位或价值,即德性不仅具有一种工具性的价值,是通向幸福的唯一途径,而且是在其自身值得欲求的善、自在的善。在重要的生命时刻里,德性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活得幸福的标准,一个人是否幸福就在于他有没有在做符合德性的行动,有没有在实践德性。如此看来,苏格拉底的德性概念远比幸福还要宽广,因为德性的概念之内也包含着对他者的幸福和利益的关切。
二、德福等同论与德性充足论
学者们经常将苏格拉底伦理学称为幸福伦理学或幸福主义(eudaimonism)。有学者质疑苏格拉底是幸福主义的极力提倡者,认为苏格拉底在早期对话中所表达的很多观点与幸福主义并不一致,有关幸福主义的明显证明也是凤毛麟角(6)N. White, Individual and Conflict in Greek Ethics, Oxford, 2002; D. Morrison, “Happiness, Rationality, and Egoism in Plato’s Socrates”, Rationality and Happiness: From the Ancients to the Early Medievals, eds. by J. Yu and J. Garcia. Rochester, NY, 2003, pp. 17-34.。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苏格拉底在柏拉图早期对话中虽然没有像柏拉图在中期对话中或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那样,明显地对幸福作为人的所有行动的终极目的进行系统论证,但苏格拉底是一位幸福主义的极力拥护者,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可以大致将这些不同观点分为四种命题:(1)同一命题或德福同一论(Identity Thesis):幸福与德性是一回事,或幸福就其整体来说(intoto)是由德性构成的(7)R. Kraut, Socrates and the State, Princeton, 1984, p.211; G. Rudebusch, Socrates, Pleasure and Valu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23-128; J. Annas, “Platonist Ethics and Plato”, Le Style de la pensée: recueil de textes en hommage à Jacques Brunschwig, eds. by M. Canto-Sperber and P. Pellegrin, Paris, 2002, pp.1-24.;(2)部分与整体命题(Part/Whole Claim):幸福并非全部由德性构成,只是部分地构成,德性虽然是首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在其自身就值得欲求的善;(3)工具命题(Instrumental Claim):德性仅仅是通向幸福的一个工具或手段,换言之,德性仅仅作为通向幸福的工具而值得被欲求,人们并不因其自身而欲求德性(8)T. Irwin, Plato’s Ethics, pp. 67-68.;(4)充足命题(Sufficient Thesis):幸福与德性并不是一回事,但德性为获得幸福来说是足够的,不管是谁,只要他是有德性的,那么他就是幸福的(9)G.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p.224-231; T. Irwin, Plato’s Ethics, pp. 58-60; C. D. C.Reeve, Socrates in the Apology, Indianapolis, 1989, p.137.。
首先,命题(2)代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立场。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幸福是人的行动的终极目的,我们不可能再为了别的目的而去寻求它;至于荣誉、快乐、理智以及每种德性,我们不仅因其自身之故而寻求它们,也为幸福之故而寻求这些善(《尼各马可伦理学》1097b1-5)。这里,德性似乎并不是构成幸福的唯一要素或成分,很多其他的善对于幸福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笔者认为,虽然幸福的构成要素有多种,但德性仍然是其中最重要的要素,甚至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一样都是在其自身就值得被欲求的德性《尼各马可伦理学》1144a1-6)。柏拉图在《理想国》357b-358a中将善分为三种:为其自身而值得欲求的善(比如无害的快乐),为其自身和其后果而值得欲求的善(如思维、观看、健康和正义),只是为其后果而值得欲求的善(身体锻炼、医学训练和生意活动)。前两种都应该是幸福的构成要素,因为根据柏拉图在《会饮篇》205a2-3的表达,幸福是唯一使喋喋不休的“为什么这么做”的问题的终止者(question-stopper)。至于命题(3),笔者认为这并不是苏格拉底本人的看法,就像乌拉斯托斯(G. Vlastos)所说的,这个立场应该被苏格拉底的私密至交阿里斯提普(Aristippus)和伊壁鸠鲁及其追随者们所持有,他们将幸福等同于快乐或对痛苦的逃避。苏格拉底在《高尔吉亚篇》中严厉地抨击这种快乐主义(Gorgias494e):如果这种快乐就是幸福,那么娈童或做性奴的男童就会是最幸福的。就像很多学者们所强调的,德性在苏格拉底那里是内在的(intrinsic)、独立的(independent)善,它有其自存价值,并不依赖于他物而获得自身的价值(10)See Apo. 28b5-9, 28d6-10; Crito 48c6-d5, 49c10-d5.。德性并不仅仅因为它是通向幸福的一个途径或工具而值得欲求,德性在其自身就值得被欲求。那么,究竟是命题(1)还是命题(4)与苏格拉底本人的看法更相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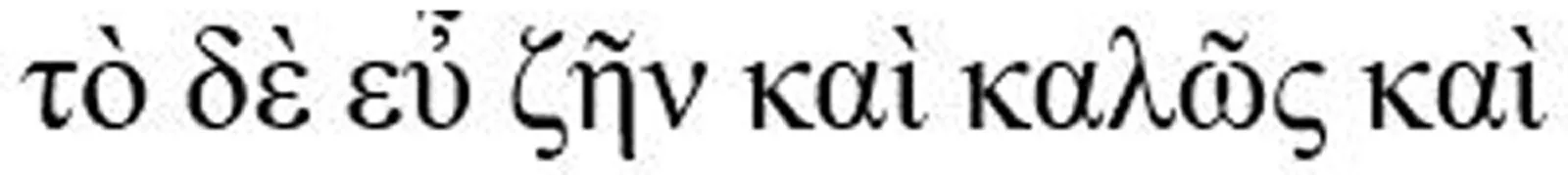
伯伯尼克(C. Bobonich)认为,总体来说,德福同一论需要面对两种困难:(1)除德性以外,还存在着其他非工具性的善(non-instrumental goods);(2)一个人的最好的生活状态中除了德性之外,还包含其他的东西(14)Cf. C. Bobonich, “Socrates and Eudaimonia”,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ocrates, ed. by Donald R. Mor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316-318.。比如,苏格拉底在《高尔吉亚篇》(Gorgias467e1-468b4)将存在着的事物分为三类:善、恶、非善非恶的东西。出人意料的是,苏格拉底将非伦理性的善(健康和财富)放入到善的事物中。如果苏格拉底主张德福等同,那么他就不会将这两种非伦理性的善放入到善中。而如果构成一个人的幸福的要素或非工具性的善对我来说只是我个人的德性,那么这将会是限制在自我之内的幸福(self-confined happiness)。但是,这仿佛与我们的日常直觉与日用不知的实践相冲突,因为我们的至亲好友的幸福也会对我们自己的幸福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比如看着自己的孩子快乐地长大、感受他们的天真烂漫和无拘无束的自然状态都会增加个人的幸福。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时不会仅仅以自我的德性状态为最后目的,而是以其他事物为我们欲求的目的,比如为了更多人的福祉或者社会的正义而作出自我牺牲。笔者认为,我们的最终目的不仅仅局限于从任何行动中获取那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东西,促成我们自己的幸福的最大化,而是可以包含着超越于个体利益之上的目的,并且可以将这种超越于自我的目的视为我们的幸福生活的一部分。
那些主张德性充足论的学者认为,《高尔吉亚篇》的470e4-11与507b8-c7这两段文本非常清楚地证明(15)“……因为我认为,高贵的和有德的男人和女人是幸福的,那些不正义的和邪恶的人是可怜的或不幸的。”“所以,卡里克勒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节制的人必然地是正义的、勇敢的、虔敬的,将会是一位十足的好人,好人不管做什么,他都会做得好、做得高贵,那些行为正直的人也将会受到祝福,是幸福的;而那邪恶的人和行为不义的人则是可怜的悲催之人。”(Grg. 470e4-11, 507b8-c7):德性与幸福有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结关系,有德性的人或正义的好人一定是幸福的,反之,邪恶的人和行为不义的人是不幸的。一个人的幸福与不幸福并不取决于他来自哪个阶层、有什么地位,而是取决于他是否有德性。《克里同篇》的49a-e同样可以证明德性充足论:苏格拉底所说的“伤害”或“损害”——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就是指不正义的行动或其他恶行,因为只有有损于一个人的德性的行动或事物才算是“损害”或“伤害”了某人。所以,一个有德性的人是无法被别人的恶行所“损害”的,这也是为什么苏格拉底在“承受不义”和“做不正义的事”之间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的原因。
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将德性与幸福的这种紧密关系理解为前者是后者的充足条件呢?为什么德性可以是幸福的充足条件呢?乌拉斯托斯提出德性的绝对的主导原则(Principle of Sovereignty of Virtue),作为德性充足论的理论根基。他举出《申辩篇》的28b5-9、28d6-10与《克里同篇》的48c6-d5这三处文本来证明这种原则:我们在最后的可能性中作出选择时所要参照的唯一决定性的标准就是,我们对正义与不义或德性与邪恶的内心感知,其他一切的考量都是多余和无用的,只有德性在我们的价值体系中是主导性的善,就连生死的危险都应被置之度外。德性充足论至少包含如下两点:(1)既然行动者的德性依赖于他本人,他的幸福就在他的掌控之下;(2)德性能够保证幸福(16)Cf. C. Bobonich, “Socrates and Eudaimonia”,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ocrates, pp.319-320.。乌拉斯托斯的德性充足论引起很多学者们的赞同,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反驳和修正。柏瑞克豪斯(C. Brickhouse)与史密斯(N. Smith) 认为,不是德性对于幸福有充足性,而是符合德性的行动(virtuous activities)才是获得幸福的充足的前提条件,否则,一个在呼呼大睡的或者是处于休克状态中的好人也可以被认为是幸福的。他们指出,德性充足论无法解决这样的难题:一个有德性的人被迫经历肉体的痛苦折磨或者眼看自己的孩子受折磨时,我们如何能说他的德性对自己的幸福是充足的?(17)T. C. Brickhouse and N. Smith, Plato’s Socra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18.潘内尔(T. Penner)给德性充足论加了一些限定或让步:一个人的德性可以保证他在可能的一定情境中获得最大量度的幸福(18)T. Penner, “Socratic Ethics, Ultra-Realism, Determinism and Ethical Truth”, Norms, Virtue, and Objectivity: Issues in Ancient and Modern Ethics, ed. by C. Gi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5, p.172; “Socratic Ethics and the Socratic Psychology of Action: A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ocrates, ed. by D. R. Morri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65.。伯伯尼克和瑞绍寇(N. Reshotko)则从不同角度对德性充足论加以反驳。
关于第一点,一个人的德性的确系于自身,如果我们将苏格拉底所说的德性理解为关于善恶的知识,那么他就可以根据这种伦理知识而行动。就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在苏格拉底看来,一个人在既定的行动处境中只要知道何者对自己是最好的,或者有关于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善的知识,那么他就不会违反这种知识而行动,因此并不存在不自制的行动,或者我们称之为“意志软弱”的现象,违背自己心里的有关何者是最好的知识来行动,这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但是,这并不表示因为他的德性系于自身,他的幸福就在他的手中受支配。关于第二点,如果我们观察世间众生的生存百态会发现,有些好人或义人并没有享受世间的幸福,比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恶(天灾人祸)、先天的劣势(贫穷出身或没有名望)、伦理上的不公平的遭遇等都会威胁到一个人的幸福。就像康德所指出的,德与福在经验世界中并没有符合比例的一致性。在康德那里,德与福的符合比例的一致性是通过上帝的存在悬设才能得到保证。情况在苏格拉底则有不同,苏格拉底一方面并没有寻求上帝的帮助来保证德与福的一致,另一方面也没有赋予德性一种足以在其自身就能保证幸福的特殊能力。一个人纵然有诸种德性,但仍然存在很多其他因素来损害或毁坏他的幸福。比如,苏格拉底在《克里同篇》47e4-6中强调正义的重要性时,将正义比喻为身体的健康状态,作为这个论证的一部分,他提出比较严重的身体疾病可以夺去一个人的幸福,以至于使他的生活不值得过(19)Cf. Grg. 505a, 512a-b.。瑞绍寇认为,根据苏格拉底在早期对话中的表述,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德性与幸福之间的法理或义理上的联系(nomological connection)是否强烈或稳固到德性对幸福是充足的地步,并且有关德性是否对幸福是充足的或必须的问题的讨论,对人来说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动机性的实践作用,因为如果幸福是我们欲求的最终目的,并且只有德性才是我们能够对我们是否获得幸福这件事产生影响的唯一希望,那么我们就会欲求德性。尽管在苏格拉底看来,对德性的寻求恰巧是欲求幸福的前提条件(precondition),即幸福只有通过对德性的寻求才能达到,因此对幸福的寻求就是对德性的寻求;但是,这种关系并不能被理解为德性对幸福是充足的和必需的,因为不管德性是否保证幸福,或者德性是否是达到幸福的唯一途径,对德性的寻求是一个人可以对他是否获得幸福产生影响或作用的唯一方式(20)N. Reshotko, Socratic Virtue: Making the Best of the Neither-Good-nor-Ba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36-142.。我们并不否认在德性与幸福之间存在着一种原因性的联系,即德性是幸福的原因,但这并不表示德性就是幸福的充足条件,正如X是Y的原因或X使Y发生,并不表示X对于Y来说是充足的。就像有学者指出的,原因对于其效果来说并不一定是必需的和充足的(21)Cf. W. Salmon, Causality and Expla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45; E. Sober, From a Biological Point of Vie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98.。
三、德性的双重地位
无论是德福等同论还是德性充足论都会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责难或问题,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那里,我们既可以找到支持前者,也可以找到支持后者的文本证明,所以我们很难将苏格拉底本人对德性与幸福的关系的原本看法还原出来。笔者赞同瑞绍寇的观点,德性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是不能从分析这两个概念的内容来获得,即与其说德性与幸福的关系是概念之间的或逻辑意义上的先天联结(a priori correlation),不如说是一种法理或义理上的(nomological)联系。苏格拉底首先关心的并不是德性与幸福作为先天概念的关系是什么,而是立足于切实的生活经验,关心如何通过对话和交谈使青年人能够转向德性,由此尽可能使他们能够活得好或幸福(22)N. Reshotko, “Socratic Eudaimonism”, 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Socrates, ed. by John Bussanich and Nicholas D. Smith,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183. 他这样总结自己的观点:“Socrates understan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etē and eudaimonia to be a nomological one... Every purposeful behaviour is an effort to achieve eudaimonia either because it is part of the process of figuring out that one wants eudaimonia, or the process of figuring out that one needs knowledge in order to get eudaimonia, or part of figuring out how to get knowledge, or part of using that knowledge to get eudaimonia or to obtain a means to eudaimonia. ”。德性与幸福之间的联系根本与概念层面上的逻辑关系无关,毋宁说,对德性的欲求隐含地被编织在人对于幸福的渴望动机中,基于人的伦理实践,德性才与幸福交融在一起。从实践法则或伦理实践的视角来审视二者的关系,确实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毫无意义的空谈,只是从二者的抽象概念入手来谈二者的关系。但是,这种做法会有一个危险,即我们很容易基于幸福作为人的所有行动的至高的最终目的而将德性工具化,陷入工具主义的窠臼中。笔者在这里想证明的是,虽然活得好或幸福是人的最终目的、是唯一的善,德性是达到或获得幸福的途径,但德性在苏格拉底伦理学中并非只是单纯的通向幸福的工具(a mere means),而是与幸福有着同样的独立价值的内在的无条件的善、绝对不会被滥用的善,尽管德性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来自幸福或对幸福的贡献,但德性仍然在其自身就是善,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人的唯一的善(the only good)。
如若德性在苏格拉底伦理学中有这么高的地位,甚至是人的唯一的善,那么这会不会与苏格拉底的幸福主义相冲突呢?按照幸福主义原则,幸福才是人的所有行动的最终目的、是最高的和唯一的善,为何苏格拉底又会认为德性也是人的唯一的善呢?虽然幸福对苏格拉底来说是人的终极目的,人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获得幸福(Euthyd. 278e3-6),但幸福在古希腊文化中仍然与神明的惠赐或眷顾分不开,也就是说,幸福并不是可以任由人来支配的东西,而是有某种超验的神性,依赖神明的眷顾。既然能否最终获得幸福并不是人能够随意支配的事情,那么,苏格拉底就更多地转向隶属于我们能力范围之下的、可以由我们来支配的德性。在柏拉图早期对话中谈论幸福(包括做得好和活得好)的次数如果与德性相比,显得非常微不足道,虽然无法确定具体的比例,但确切的是,苏格拉底谈论幸福的次数是非常有限的。至于我们最终是否获得幸福,这需要他人和神明来评判;而我们在此世有没有追求德性或实践出正义和德性,这就完全在于我们自己,彻底归责于我们自身,而且只要我们实践出正义和其他德性或过着追求德性的生活,那么我们也会认为我们是幸福的。无论如何,苏格拉底对德性的关切在其伦理学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我们越是深入了解德性在苏格拉底伦理学中的特殊地位,就越能把握苏格拉底有关德性与幸福的关系。苏格拉底在《欧绪德牧斯篇》《美诺篇》《高尔吉亚篇》中提出“依赖性命题”(Dependency Thesis)和“不善不恶说”(Neither-good-nor-bad),它们对我们理解德性的特殊地位及其与幸福的关系甚为重要。笔者认为,在苏格拉底的伦理学中,德性有双重地位:一方面,德性的价值或善来源于自身,从“依赖性命题”和“非善非恶说”中就可看出;另一方面,德性的价值也来源于幸福或对幸福的促进,德性必然地会帮助我们获得幸福,但德性并不像别的工具性的善那样只是通向幸福的工具,因为德性有其自身的价值。亚里士多德就在《尼各马可伦理学》1097b1-5中表达了这种德性的双重地位,即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在其自身就值得被欲求,也为了幸福的缘故而选择它们。

这里,苏格拉底将幸福作为最高的价值判断标准,我们通过正确地使用这些俗常的善才能获得幸福,而只有德性或智慧才能保证我们对这些善的正确使用。这些俗常的或依赖性的善并不是真正的善,因为它们的价值并不是来源于自身,而是有条件的——是否被正确地使用,进而促进了幸福。苏格拉底在这里虽然强调只有智慧或德性才是我们正确地使用这些依赖性的善的保证,但他并没有至此为止,而是指出通过正确地使用这些依赖性的善是为了获得幸福,幸福才是终极目的。换言之,德性如何保证正确地使用它们呢?德性通过使它们促进幸福来正确地使用它们,能够促进幸福就是它们能被正确地使用的保证。在苏格拉底看来,幸福是最高的或最终的价值来源,德性之所以能够使这些依赖性的善成为真正对其拥有者是有用的或有益的,原因就在于德性通过正确的使用使它们能促进幸福。苏格拉底的结论是:“让我们考虑如下推论:既然我们所有人都渴望成为幸福的,并且既然我们只有通过使用事物才能成为幸福的,且使用地正确,又既然知识是正确(使用)和好运的根源,因此,每个人就有必要不遗余力地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地成为明智的或有智慧的——或者事情不是这样的? ”(Euthyd.282a)
德性或智慧的价值来源于通过对事物的正确使用而促进幸福。因此,虽然德性并不能保证幸福,但它是促进幸福的必然途径,不是一种单纯的达到幸福的工具。瑞绍寇将幸福称为自生自成的善(self-generated good),因为幸福的价值源于自身,而不源于任何与其不同的他物;但将德性称为他生他成的善(other-generated good),必须附加上无条件的,因为德性并不是在某些情况下是善的,而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善的(23)Cf. N. Reshotko, Socratic Virtue: Making the Best of the Neither-Good-nor-Bad, pp.120-121.。这种看法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德性与幸福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是非此即彼的,而不是互相促进的关系,有时正义的行动可能会以牺牲个人的幸福为代价。苏格拉底本来有可以逃出监狱的机会,但他认为按照法律留在监狱中才是正义的、逃离是不正义的,所以他宁可留下来坚持正义的行动,也不会逃离而作出不正义的行动。苏格拉底并没有认为自己是不幸福的,他所理解的幸福并不在于身体的完好、寿命的延长、财富的积累和声望的抬高,而在于进行有德性的行动,但并不是完全的等同。

德性在苏格拉底伦理学中占据着非常独特的双重地位。一方面,它的价值来源于对幸福的促进,虽然德性并不能保证幸福,但德性是促进幸福的必要途径,因为只有德性才能保证对不善不恶的事物的正确使用。在某种意义上,德性与幸福有着符合比例的升降关系,成为有德性的,就是成为幸福的。另一方面,德性的价值也来源于自身,是无条件的善,因为幸福在古希腊文化语境中不只是人的事,也是神的事,最终人的幸福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超验的神明之眷顾,而德性纯属于人的事。所以,苏格拉底并没有对幸福的本质大写特写,而是更多地关注德性,呼吁人们转向德性;因为这是可死的凡人能够对能否获得幸福产生影响或起到作用的唯一手段或途径,德性的价值对于凡人来说有着不可取代的必然性。苏格拉底在饮鸩之后,慨然地说出如下心声:“现在,离去的时候到了。我将死去,而你们则继续活在人世。我们中谁的去路更好,除了神,无人知晓。”(Apo.42a)苏格拉底离去了,为了证明真理和实践正义而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在苏格拉底看来,正义的德性行动与个体的幸福是分不开的,他可以选择正义的行动,至于自己是否是幸福的,他只能留待神明来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