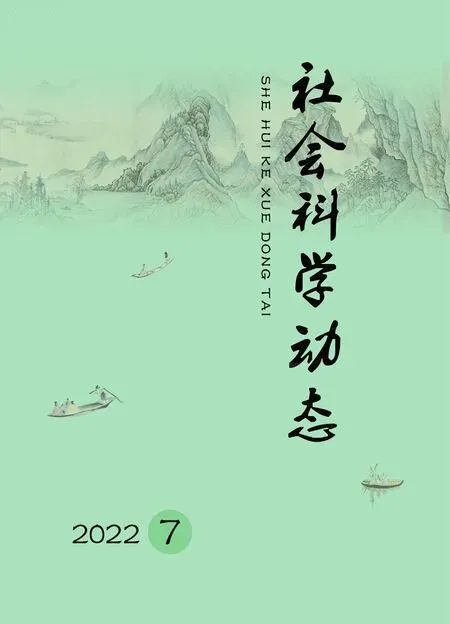征用与撕扯:战时中国的列夫·托尔斯泰纪念言说
高 强
作为19 世纪俄国的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中国的形象和地位可谓几经浮沉。大体而言,在托尔斯泰生前,他便被西方知识界当作文艺大家和思想伟人予以崇拜。而在中国,托尔斯泰的风行则是“借助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高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俄国革命胜利的东风”①。之后,中国革命文艺家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转而对托尔斯泰进行“重新估价”,将其置于被审视的位置。这一负面化的托尔斯泰形象大致延续至新时期,然后在“去政治化”和“重拾人道主义”的浪潮中,托尔斯泰又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读者的热烈崇扬。
自托尔斯泰1910 年逝世后,每逢其诞辰和忌辰,中国文人或多或少都会进行纪念,撰写纪念文章,这些纪念言说成了构建中国托尔斯泰形象的重要推手。与中国的托尔斯泰大致经历了“正—反—正”的形象嬗变轨迹相吻合,中国的托尔斯泰纪念言说语调也呈现出“热—冷—热”的发展趋势。其中,抗战时期(1931—1945) 是托尔斯泰纪念言说相对冷淡的阶段,不过称战时中国的托尔斯泰纪念言说语调冷淡,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若细加分析,便可发现语调普遍低沉的战时中国托尔斯泰纪念言说背后也有着特殊的热烈昂扬的面影,与“冷言冷语”式纪念言说并存的是一些“热言热语”式的纪念言说。最终,战时中国的托尔斯泰纪念言说便映照出一个被各方人群征用与受到各方力量“撕扯”的托尔斯泰形象。
一、“杀掉思想家的托尔斯泰,而爱护艺术家的托尔斯泰”
宣扬人道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是托尔斯泰思想的两大支柱,这与十月革命开始后苏联所奉行的阶级革命主张显然背道而驰,因此,托尔斯泰在苏联很长一段时间饱受批驳。与之相关,托尔斯泰的艺术也被判决为是“与普罗阶级有害无益”的“旧时代之遗产”,而被“加以无差别的排击”。其后,苏联开始提倡“普罗写实主义与社会主义”,当时的作家有感于自身写实主义文学手法和技术的生硬,不得不转向古典作家学习,并发明“文化的遗产之利用”的标语。在此背景下,苏联批评家们开始将托尔斯泰视作写实主义的最高峰,正面评价其艺术造诣。与此同时,对于托尔斯泰思想中有可能给革命造成消极影响的宣扬人道、反对革命,主张不抵抗、拒绝暴力等元素,又时刻加以批判和提防。最终,苏联的托尔斯泰形象便一分为二:“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是代表封建的农奴时代意识之反动的思想家,应极力地加以警戒和排击。而同时尊重艺术家的托尔斯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豪。且以他为道地写实主义之最高峰,而不能不对他的艺术加以学习”②。苏联这种将托尔斯泰的思想和艺术分别看待的作法传入中国后,与全民抗战动员的迫切现实需求相结合,进而成为战时中国托尔斯泰纪念的主潮。
署名“永成”的作者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虽然托尔斯泰在自身周围看出了恶、揭发了恶,而且“高声反抗着一切的恶”,但他却绝“不容以暴力反抗”。托尔斯泰就是怀抱这样忍从的态度,仗着这样的无抵抗主义,“以为可以叫醒作恶的人的良心”,这“实在是托尔斯泰的幻想”。他引用高尔基的话来驳斥托尔斯泰,同时提醒战时中国民众:“抗恶必以‘暴’。不诉诸暴力,而仰仗‘理性’与‘爱’,不特是对于恶的忍从,而且是对于恶的煽动”③。高洁对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予以严肃批判,他认为托尔斯泰充满着矛盾:一方面,托尔斯泰无情暴露了“俄皇专制黑暗政府的凶残,资本主义的剥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与无耻”;另一方面,托尔斯泰却“宣传世界上所有一切混蛋的一种:就是宗教的精神”。在这种矛盾思想中的托尔斯泰绝对无法了解和洞悉农奴制度下的俄国的革命性转变,即“伟大的潜势力的发生与长成”。因此,托尔斯泰离开政治、逃避政治,并“给与俄国一般民众很坏的影响,使得他们成为黑暗专制的俘虏”。高洁还将1905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失败归咎于“托尔斯泰式”的无抵抗主义的“恶影响”。他说,俄国当时虽然有小部分农民,很坚决地向他们的敌人斗争过;但大部分农民却只不过哭号过、警告过、陈述过理由,写过请愿书、派出过“请愿代表”,完全照着托尔斯泰无抵抗主义的精神行动,结果“遭到俄皇大发雷霆,屠杀了他们无数的生命”。最后,作者将目光转向中国,对战时中国那些面对外敌侵袭却不敢迎战和反抗的举动深表悲愤:“想不到二三十年后,那被俄国扬弃了的‘无抵抗主义’却又盛行于印度和中国!”④当时置身于孤岛的文人,遭受敌人的围困,随时有性命之虞,因此坚持抵抗、反对投降的精神对于他们显得尤为宝贵。相应的,那些具备民族气节的孤岛文人便会在托尔斯泰纪念文章中以斥责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来为孤岛民众的精神持守打气。万心齐正是在此意义上言说托尔斯泰,他认为托尔斯泰在思想上是一个“美善的追求者和人道的说教者”,可实际生活中却处处遭遇着“黑暗和罪恶”,自己又无法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托尔斯泰自身的矛盾使他最终变成了一个“摸不着现实的边际的空想主义者”。有鉴于此,作者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表示,托尔斯泰“造成人生悲剧的自我矛盾性格和不抵抗主义思想,足令一个青年人消失迎战黑暗的雄心”⑤。显而易见,警惕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的危害、号召人们不要丧失“迎战黑暗的雄心”,是这篇纪念文章的主题,而这分明隐含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纪念托尔斯泰,即是对孤岛民众乃至整个战时中国“迎战黑暗雄心”的鼓与呼。
在思想理念上,托尔斯泰与革命和战争虽然存在着诸多乖隔,但在艺术创作上,作为举世闻名的大作家,托尔斯泰依然可以给战时中国文人提供不少启示。因此,战时中国的托尔斯泰纪念言说在批评其无抵抗主义的软弱思想时,又对托尔斯泰的艺术创作给予了热烈表彰。钟敬文重点讴歌了托尔斯泰写作严肃诚实的特点,认为无论托尔斯泰在思想上存在怎样的缺点,但他却“缺少一般人最容易犯着的恶德——虚伪”,他不断通过作品来探求真理,最终成了一个十足的殉道的人,“他殉了人的道,他殉了艺术的道”。作者引述托尔斯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一书中的文字作为例证,以之为战时中国作家指明方向:“如果真正用精神的劳动去服务于别人,那么,他必定为着从事这种工作而挨受痛苦罢。为什么?因为精神成果的产生必须由于苦恼。蔑视自己和苦恼正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本分,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民众的幸福。人们是不幸的,他们痛苦,而且走向死亡……思想家艺术家决不像人们所想象般地坐在奥林普斯的山上。他为着发见救济和慰安,不能够不和人们共苦恼”。而在受难的中华民族艺术家们,“正迫切需要这种深刻的认识和庄严的实践”,在此意义上,“托尔斯泰是不愧充当我们的导师的,他的实践永远是求真理的一种鼓舞”⑥。与此相似,当时身处孤岛的文人周剑萧在纪念文章中写道:“托尔斯泰的写作精神更是不可几及的,他那一百万言的伟大巨著《战争与和平》经他夫人安娜手抄了七次,可见他对艺术作品是如何的一笔不苟。我不知道中国那些对自己手写的原稿看都不愿再看一遍却自以为是不朽的名著的文艺工作者,对于托尔斯泰这种毫不苟且的写作精神,究竟作何感想?”⑦
周立波在纪念文章中,将托尔斯泰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广性作为战时中国文艺的榜样:“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实在是可惊的伟大的。他是‘不仅作出了俄罗斯生活的无比的画卷,而且作出了世界文学中的最高的作品的天才的艺术家’。他的表现异样的广阔。地主贵族的豪华和淫乐,农民们的一切生活和情感,由最辽远的社会远景到最微妙的爱情衷曲,从最紧张的战争与行猎到闲散的田园,他都喧嚣的表现着。”他还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比较,进一步凸显托尔斯泰艺术创作视野的宽广性,“读托尔斯泰,像泛舟明月之下的江流,在乳白色的光芒中,你漂浮着,你看见汹涌的社会的潮流,也看见小儿女的私情的小浪。托尔斯泰的伟大是辽阔的‘平面的伟大’,他不像朵斯托益夫斯基给人以精神惨跌的难堪”⑧。事实上,抗战爆发后,人们对文艺创作者的一个重要要求,便是摆脱“高蹈”和“卖弄玄虚”的狭小天地,将笔尖对准前线,对准农村,对准大后方每一个角落,“接触更广大的天地,吸收更丰腴而健全的营养”⑨。周立波在纪念托尔斯泰时所重点张扬的“辽阔的伟大”,正是对战时中国文艺更加深入、宽广地反映现实景象的提倡。永成不仅称赞了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的“表现的广泛而且强有力”,同时对托尔斯泰写作的“单纯性”也青睐有加:“托尔斯泰以为艺术的价值应当以其接近大众的程度为衡量标准,他告诉我们,以一种一般人民不能了解的特殊的用语,创造文艺作品,使一般人民不能接近,这只是自私、恶劣、无道理。他的许多作品,因为是意识的诉向一般人民的,所以用了无比的单纯的文字。”⑩此处的“单纯性”,即是“通俗化”“大众化”的同义词,这也是战时中国文艺的重要诉求之一。可以说,纪念托尔斯泰又一次为战时中国文艺指示了方向。
正是作为作家的托尔斯泰之名声过于显赫,因此,即便托尔斯泰的某些思想观念并不符合战时中国的现实需要,但人们依然不忘从艺术写作角度来大肆纪念和宣扬托尔斯泰。1941 年托尔斯泰的逝世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桂林的《文化杂志》特意开辟“托尔斯泰逝世三十周年纪念特辑”专栏,“介绍其对文学与艺术的见解”⑪。该专辑刊发了两篇译文谈论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及其启示,以此作为纪念并期翼给战时中国文艺“导航”。其中一篇是托尔斯泰写给《艺术新闻》杂志发行者的信。信中托尔斯泰阐述了自己对于真正艺术的看法,认为只有“当它是在追求善,而且吸引人们倾向善的时候,只有这样子,我才称它为艺术”⑫。另一篇是袁水拍翻译的托尔斯泰和朋友的谈话录,其中蕴含着很多极具启示性的艺术观点。如当演员亚特梅益夫和朋友请求托尔斯泰写一则能够让他们在俄罗斯的农村里,如谷场之类的场所演出的剧本。对此,托尔斯泰回答说:“我很怀疑那些所谓为了人民所写的我们的艺术。我们不配教他们。他们必需创造他们自己的艺术。”对方继续游说:“可是他们非常喜欢,譬如说吧,你所写的民间故事形式的短篇小说。”托尔斯泰回绝道:“是的,不过这些是我从他们那里拿了来,现在重新还给他们吧。还有,我一定要告诉你们,我自己只是人民中间的一部分,假如世界上有一件事使我不耐烦的,那便是智识分子教育人民的企图。”⑬从正视艺术的价值,时刻以艺术创作来导人向善,到批评知识分子自认为高于人民的错误观念,这些都是战时中国文艺颇为重要的面向,托尔斯泰纪念言说暗中沟通和进一步强化了战时中国文艺的发展道路。
当托尔斯泰逝世时,他已经具备了世界性的声誉,他的作品连同他本人已经化作一种重要的被世界人群所熟知的象征形象。人们对托尔斯泰的认识已从一种个体思维方式演变为一种社会无意识,“具有了‘资源’所含的‘力量’的隐义”⑭。面对这一极具“力量”的象征物,苏联宣传部门不可能完全忽略。但是,托尔斯泰思想观念中又充满了不少对苏联革命进程和意识形态建构带去“威胁”的元素。于是,折衷且完备的做法便是将托尔斯泰一分为二,予以区别对待:“现代劳动者及其前卫,在这位艺术巨人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候,严肃的批判了他的意识思想的糟糕,但又懂得,用最敬爱的态度怀念这位诚实的老友的热烈的心脏,学习他的稀有的艺术。”⑮即否定托尔斯泰的思想而推崇他的艺术创作的模式。对此,在永成的纪念文章里有着极为精辟的概括——“杀掉思想家的托尔斯泰,而爱护艺术家的托尔斯泰”⑯。与苏联不愿轻易放弃对托尔斯泰的纪念,以便掌控和形塑这一巨大的象征资源类似,战时中国文人也没有忽视对托尔斯泰的纪念,也将思想家的托尔斯泰和艺术家的托尔斯泰进行区分,贬抑前者、推崇后者,然后通过对托尔斯泰思想的贬抑来强化战时中国民众抗争的决心和勇气,通过对托尔斯泰艺术的推崇来为战时中国文艺的发展指示合理的道路。不论是贬抑还是推崇,托尔斯泰实则都被征用过来服务于战时中国的实际需要。
二、“阐扬托氏的高洁理想”与“阐扬苏联的光辉形象”
如前所述,“无抵抗主义”和“反对暴力”被视作托尔斯泰的主要思想内容,这与战时中国吁求抗争的思想主潮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由此,战时中国的托尔斯泰纪念出现反复批驳托氏的思想观念。但这只是大体而言,事实上托尔斯泰的思想观念并不能被简单地框定在“无抵抗主义”和“反对暴力”层面,“人道主义”便是托尔斯泰思想世界的一个重要主张,从这个角度出发,战时中国文人的托尔斯泰纪念又识别和提取出了思想进步的托尔斯泰形象。
在托尔斯泰逝世31 周年时,汉口《自由中国》杂志推出“纪念托尔斯泰特辑”,其中刊载有一篇署名“本社”的纪念文章。该文对托尔斯泰的进步思想大加赞誉:“我们可也并非是为了‘应景’才来纪念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我们是为了他那么富于正义和爱,同时又那么勇敢,才要纪念他的。他相信‘爱会替他打开真理的大门’,为了追求‘神’底真谛,他不惜被当时握着宗教权威的神圣宗教会议,开除他底教籍,而且与之对抗。他声明,空洞的教条脱离了实行,那只是假神底名义来欺骗民众。形式上他是‘神’底叛逆者,而实际上他才真正是基督底信徒!”⑰封斗的纪念文章也一反通常的批判托尔斯泰思想的纪念语调,转而提炼出一个爱意满满的、堪为中国人民思想模范的托尔斯泰形象:“托尔斯泰以全人类的幸福为人生的目的,不像一切宗教家那样把幸福寄托于缥缈的未来,而是把它看作从现世涌现出来的现实的结果。所以他的理想,决不是避弃现实,而是面对现实的。他主张理性的生活,排斥个人的,物质的,生物的幸福,但只在这种幸福妨碍了他人幸福的时候他才排斥,他并不把它当作全然有害而不必要的东西,而且在经营理性生活的时候,还认为是不可缺乏的材料。像这样的个人幸福的排斥,是作为人的战士的自我克制的牺牲精神。而最后——爱,这是亘贯他生涯与事业的最大的精神,他把这当做完成幸福探求的途径。”他认为,托尔斯泰的艺术造诣,正是从他的“热烈的理想主义精神,热烈的邻人爱中才能够完成的”。战时中国民众无疑是置身于最大的苦难时期,这种情况下托尔斯泰的“牺牲的爱的精神的一面”,便愈是值得人们纪念了。“如果我们抽象了托尔斯泰的被自己阶级和时代所限制了的观念的、神学的形式,而摄取那纯粹的追求人类幸福、理性、爱的精神,则这样的追求,也是存在在我们今天喋血的战斗之中的,而且必然应该存在的。”⑱
其时生存于孤岛,目睹多数同胞或沉沦或附逆的周剑萧,对托尔斯泰的正面思想有着更为深切的认识和更为强烈的肯定,他称赞托尔斯泰是“全人类最伟大的良心”。在他看来,世上之所以会产生蓄意侵略别国土地,“想夷全世界的人民为他个人的奴隶”等凶残暴虐的现象,追根究底是因为敌人的“心地不良所致”。倘若人人都像托尔斯泰那样“有一颗伟大正直的良心”,那么世界的前途就充满了光明。退一步说,倘使人人都能随时反省自己,“革除自己灵魂上的污点,力求接近伟大完美的人格”,那么这世界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一团糟了”。他认为,与敌人的心地恶毒相伴随的,是中国不少青年的自甘堕落,而学习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不啻为改变这一局面的有效措施:“现在中国虽是处在一个非常时代,但沉湎于舞场睹窟中间过着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的青年,我相信也不在少数,希望他们都能向托尔斯泰学习,效法托尔斯泰批判自己转变自己的精神,把自己不合理的生活彻头彻尾的改变过来。”⑲
1940 年托尔斯泰逝世30 周年纪念之际, 《新文艺月刊》开辟“托尔斯泰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专栏。编者特撰写了《托尔斯泰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导言》一文,对纪念托尔斯泰、表彰和学习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原由展开较为详细的说明。作者首先从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平思想的形成讲起,托尔斯泰曾亲自参加过克里米亚大战,在军队中亲眼目睹战争的残酷,这种残酷的现实教训使托尔斯泰“油然地产生了高洁的人道观念”,更因此而决定了他毕生奋斗的方向——“为人道与和平而呼吁”。作者认为,托尔斯泰对“人道”与“和平”的热情是基于对“多数的民众的热诚”,这一伟大的要求是“多数的民众的要求”,因此,虽然托尔斯泰逝世30 年了,“他却活在每个有人道观念的、酷爱和平的人们的心坎里”。反观现实世界的景象,却完全不符合托尔斯泰的追求:“第一次世界大战过了,接着第二次的大战又在欧洲与亚洲进行着。人类正遭受着空前的浩劫,惨死,流亡,饥饿,寒冷,叫人类在自己造出来的战争中,度着阿鼻地狱似的惨酷生涯!”深处战火和灾害的生活中,为求人类的和平,为求人类的幸福,必须“把托氏高洁的理想,……更广泛的阐扬开来,更广泛的实践起来”⑳。
早在20 世纪初期,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便先于文学家的托尔斯泰被介绍到中国,他的“自我完善”的思想和“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都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群体尤其是革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㉑到了抗战时期,托尔斯泰这一形象又被放置在“人道主义”的名义下,被战时中国文人视作“高洁的理想”在纪念中全面“阐扬”,这是站在世界人道主义立场上对战争发出的否决之声,与前述站在国家内部宣扬民族反抗和以暴制暴的托尔斯泰纪念言说,构成了一对鲜明的参照。
战时中国文人面对的托尔斯泰是一致的,但他们的纪念言说所呈现出来的托尔斯泰形象却判然有别。在一部分人那里饱受诟病的托尔斯泰,在另一部分人那里又被当作思想上的领路人;在有的人看来不值一提,或者被有意漠视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另一部分人那里则受到重点称许。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是由于人们纪念的出发点不同,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人们发现和关注到托尔斯泰思想世界中的不同成分,最终呈现出人言言殊却又各有道理的托尔斯泰纪念声调。
在阐扬托尔斯泰的“高洁理想”之余,战时中国的托尔斯泰纪念言说还存在着另外一类重要的音调,即经由纪念和言说托尔斯泰开始,指向对苏联方面的礼赞。化用《新文艺月刊》所说的“阐扬托氏的高洁理想”,可将此类模式概括为“阐扬苏联的光辉形象”。
周立波早在1935 年托尔斯泰逝世25 周年纪念时,便著文称誉苏联对托尔斯泰的重视。他写道:“托尔斯泰死后,苏联的新兴文学的历史,证明了只有前进作家才能够继承他的伟大工作,接受他的伟大遗产,法捷耶夫、潘菲洛夫、唆洛霍夫都是托尔斯泰的真正继承者。而苏联的人民更是顶爱读托尔斯泰的作品。国家出版所印行了托尔斯泰全集六十五卷,他的散乱的著作无数次的被翻印着。他的艺术之花,在他逝世廿五周年的今日,早栽种在广大的沃土上面了。”㉒这段貌似讲述托尔斯泰被苏联人民热烈纪念和极端爱护的文字,分明暗含着对纪念和爱护托尔斯泰的苏联本身的颂赞。
苏联对托尔斯泰的评价,经历了由轻视到征用托尔斯泰来作为写实主义创作榜样的变化,苏联的托尔斯泰纪念也由此呈现出前抑后扬的演变趋势。战时中国的某些文人对托尔斯泰在苏联所受待遇的前后落差深表不满,特别是在托尔斯泰逝世25 周年时,苏联举行了大规模的托尔斯泰纪念活动,出版了托尔斯泰全集,世界各国代表作家被邀请到莫斯科,在“托尔斯泰的艺术”名下举行国际亲善盛会。有中国文人颇为感叹地说:“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艺术,是这样的被苏联所重视了……然而在我们这记忆里,托尔斯泰在苏联所受的待遇,是几历升沉的。”“由此可知,苏联对于一切事物的批判,都是因时局而转移,以对于政治的影响为标准的。”㉓这种言论,与其说是为托尔斯泰叫屈,毋宁说是对苏联政府的反感。为了维护苏联的光辉形象,署名“止戈”的作者特意撰文为苏联的托尔斯泰纪念辩解。他认为,苏联对于托尔斯泰的艺术“是始终尊重的”。在苏联内战时代及十月革命时期,因为来不及注意文化之复兴和古典文学的再认识,曾对托尔斯泰的艺术“表示冷淡过”,但也不止于对托尔斯泰,当时的苏联对于果戈里、杜斯退夫斯基、莱芒托夫等,都“因为内战的一时没有肃清,来不及研究的”。与此同时,苏联对于托尔斯泰的主义又是“始终排斥着的”,不但过去如此,即便是苏联为托尔斯泰举行盛大的纪念会时,“也没有忘记托尔斯泰主义中含有的毒素,而疏于防范的”。总之,在作者看来,苏联一直看重托尔斯泰的艺术成就而一直防范着托尔斯泰的思想弊端,对于托尔斯泰的评价和看法是前后一贯的,并没有如人们批评的那样“几历升沉”。更重要的是,作者不容辩驳地认为苏联“对于托尔斯泰的艺术,则完全尊重,对于其主义,则绝对的排斥”,这种做法“是最公正的批判”。苏联的提倡文学遗产,对于任何一个古典文学家,都曾经“批判地接受其伟大的艺术”,托尔斯泰不过是其中一员而已。时人所讽刺的苏联以“时局”和“政治”标准来评判事物的行为,在作者眼里非但不是一种缺陷,反而是非此不可的正途:“至于文学事业的建立,要和现实的社会需要,生着紧密的联系。我想,只要有人不是承认文学为空洞无用的东西,文学亦是促进社会进化的武器之一翼,该没有以这为足诟病的。”由此出发,作者强调:“文学事实的前进,也是应该配备于政治底现实的。”㉔此文虽不属于自家的托尔斯泰纪念文章,但却是对苏联一系列托尔斯泰纪念言行的拥护,通过这番拥护,苏联的光辉形象便得以确立和传布开来。
与周立波点到即止的风格不同,与止戈那种借题发挥的方式有别,戈宝权在托尔斯泰逝世33 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则明确而强有力地阐扬了“苏联的光辉形象”。他首先简单赞誉托尔斯泰“不仅只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及社会事业家”,随即把重心转向对苏联的大力阐扬。他认为,托尔斯泰在当时的苏联才获得了巨大的声誉,才被人们热烈纪念着,若与其此前的命运相比,简直判若云泥:“回想到当一九〇五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以前,当时整个反动的俄国社会是尽量来辱骂托尔斯泰的,把他视为是一位对现存制度的恶毒而有害的批评家及无神论者;但当他逝世时,整个舆论界的态度又改变了;政府的报纸对他滴了一些虚伪的眼泪,自由主义者说了一些空洞无物陈腐不堪的教授式的话语,宗教会议向人民宣称:‘托尔斯泰忏悔了’。他们当时的目的,无非是想再蒙蔽起托尔斯泰的真价值及真面目。”“只有在今天,苏联的人民才给了托尔斯泰一个正确的观点,指出托尔斯泰著作和思想中的正确的成分,而扬弃了那许多错误矛盾的地方;同时更告诉我们,应该怎样从这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多多学习!”㉕通过托尔斯泰在苏联今昔处境的对比,凸显出革命前后苏联的巨大差异,言语之间,流露出一股对苏联的浓烈爱慕、礼赞之情。
纪念托尔斯泰,却不忘谈论和表彰苏联对于托尔斯泰的重视和纪念,这同样是战时中国文人托尔斯泰纪念言说的重要维度。由此,托尔斯泰纪念本身便成为一种中介,通向的是战时中国一部分文人对于苏联自身的拥戴,“阐扬托氏的高洁理想”被进一步提升到“阐扬苏联的光辉形象”的高度。
三、“以师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自慰藉”
虽然战时中国文人的托尔斯泰纪念在针对思想家的托尔斯泰发言时,显露出正反各异、抑扬有别的分殊,但这种区别只是缘于不同文人面对着托尔斯泰思想中的不同元素:当人们注目于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思想时,一般都会语含批评;当人们谈论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时,又多半会满怀赞意。换言之,托尔斯泰的不同思想元素在战时中国文人眼中的地位其实大致相当。直到汪派文人也加入到托尔斯泰的纪念言说中,这种情况便被打破了。
汪精卫投降日本成立伪政府后,大肆鼓吹中日和平,高呼“抗战之不必继续,和平之必当恢复,……中日两国不仅当求消弭目前之战祸,且进而根本除去过去之纠纷”㉖。托尔斯泰思想中的“无抵抗主义”因子,恰好契合汪伪政府的和平主张,汪派文人很快着手“征用”托尔斯泰来为其和平主张张目,而纪念托尔斯泰则是施行此一策略的绝佳时机。1940 年托尔斯泰逝世30 周年时,汪伪政府机关刊物《新东方杂志》大张旗鼓地推出“托尔斯泰逝世纪念特辑”,明确其目的旨在“要纪念这位大文豪的人道观念及非战思想”㉗。该特辑的文章几乎都是用托尔斯泰来证明汪伪政府和平主张的正确性和必然性。
桑瞑认为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反战的”,“主持人道的”,“为真理正义、为他人而牺牲的”。托尔斯泰逝世纪念日适逢战火弥漫,对此,作者深表遗憾:“托尔斯泰是个大文豪,是个思想家,是个人道主义者。他的著作普遍全世界,他的人道的和平警号,还是惊不醒人类的‘屠魔’。在他死后第四年,欧洲大战便爆发了,他在天之灵有知,当不知如何感慨!想不到,在托尔斯泰‘三十周年祭’的今日,正是世界火药气弥漫最浓的时候。”㉘叶伟则将托尔斯泰与甘地相提并论,将甘地所倡导的“印度反战运动”当成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的继承者和支裔,认为“赞扬无抵抗主义,是托尔斯泰‘一生奉为圭臬所锲而不舍’的立场。而如今甘地则从托尔斯泰手中收到这爱与痛交织成的圣洁的光明,他把这光明放出鲜艳的火焰,照射着印度,他那万丈光芒更映照了整个的世界!现在我们已经认识托尔斯泰和甘地皆是融合着基督与佛底博爱精神而出发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全抱着慈悯的胸怀,热烈的心肠;在此风雨飘摇的世界上嘶声地疾呼着‘和平’‘反暴力’‘无抵抗’……而希冀能免除以暴易暴间的大惨剧。”他高度赞扬托尔斯泰和甘地的“和平”思想是战争年代的光明所在,是唯一可以拯救人类于战火的途径,“野蛮的骚乱,一刻不息地在演进,血迹将染红了整个的大地,所谓名都,巨邑,都随着飞机大炮底吼声化成了废墟残迹,心灵终朝沉沦在震慑状态中的人们,在这时听到甘地底精纯坚决的呼声,犹如一头云雀在长歌,这声音在更响亮更和谐的音调上,从新说出了托尔斯泰底名言,表示新秩序时代人类希望底颂曲,人们脆弱的心弦,也因之得了暂时的慰抚!”㉙
《新东方杂志》本期“托尔斯泰逝世纪念特辑”中,还刊发了一篇题为《纯化意识统一精神》的社论,该文竭力渲染战争的危害与恐惧,恣意美化和平的迫切性与正当性:“和平是人类所祈求的,一切好战之徒,仍然以标榜和平当作号召!时至今日,机群袭击,动辄千架,一弹之射,计程万里;数十间巨厦,毁于顷刻,千万人性命亡在瞬间,惊心动魄,惨绝人寰,愈显出战争之罪恶,和平之可贵……中日事变,日本当局说奠定东亚永久和平,决不妨碍中国独立与生存!所以在今日我们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与自由,倡导和平,是一个革命运动,而不是卖国勾当;我们不避艰险,不计毁誉,为和平而努力。并不是罪恶,而是一种正义感!”㉚汪伪政府的托尔斯泰纪念显然是在这种“战争危害”与“和平正义”的精神统摄下所制造出来的产物,它反过来被汪伪政府用于支撑、粉饰自身“叫嚣和平”的政治意图。他们以托尔斯泰的钦仰者和忠实信徒自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这次欧战和中日战争,世界人民饱嗜了战争的滋味,无量数的妇孺和青年,在战争的炮火下牺牲了,无量数的财产和文化精华,在铁鸟的淫威下毁灭了。正是惊心的动魄,惨绝人寰。我们在浩劫中留得了残生,瞻念着欧洲人民正在枪林弹雨中过生活;中日全面和平,尚未实现,抗战的操纵者仍在引着人民向死路上走。有人类残杀最厉害一环的今日,我们对于托翁的和平思想,是特别表示钦仰的。”纪念托尔斯泰,讴歌托尔斯泰的和平思想,最终不过是为汪伪政府开展“和平运动”及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大唱赞歌:“托翁的和平种子,毕竟在静默中渐渐长成,开花而结果了,印度独立运动的愈来愈烈,法国贝当元帅的毅然放弃战争,倡导和平,在中国,更有着划时代的伟大革命运动——和平运动——在不久的将来,世界是会更灿烂,更光明的。”㉛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内一部分人的不抵抗行径,有人想起托尔斯泰曾写信给辜鸿铭并对中国人丧失忍耐性的情况表示“愤慨”的史实,转而提醒中国人应该坚决批判托尔斯泰的不合理的“愤慨”,拥抱对敌人的强硬的“愤慨”。㉛更有人撰文对中国民众学步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以为师托尔斯泰与甘地无抵抗主义自慰藉,以为他们是做托尔斯泰与甘地无抵抗主义底信徒相解颐”㉝的行为大加贬斥。某种意义上,汪派文人的托尔斯泰纪念正是一种“以托尔的无抵抗主义自慰藉”的表征。托尔斯泰被汪派文人“借用”过来予以反复纪念,将其雕琢成“和平主义”的“先行者”和“领路人”,进而使得托尔斯泰成为汪伪政府的政治号角。
结语
综上所述,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托尔斯泰是战时中国的托尔斯泰纪念主要观照和言说的内容。对于前者,人们普遍给予了热烈的赞扬,并以之作为战时中国文艺的榜样参照;对于后者,人们的纪念言说则呈现出一种矛盾和抵牾,“在消极的痛恨上他是积极的,而在积极的反抗的斗争上,他却显示着不可理解的消极!”㉞进而当人们试图通过纪念托尔斯泰来达成不同的现实目的时,便会挑选和彰显托尔斯泰思想中的不同元素,其言说的口吻自然会相当对立。但不论是面对艺术家的托尔斯泰,还是面对思想家的托尔斯泰,也不论人们的态度是正是反、语气是冷是热,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纪念托尔斯泰,之所以如此这般言说托尔斯泰,都是为了满足各自不同的现实意图。概而言之,托尔斯泰成为一种被战时中国所“征用”的异域资源。另一方面,托尔斯泰事实上已成为一种公共记忆,不同派别群体在“征用”这一公共记忆时,会诉诸截然不同的策略,或利用、或弘扬、或纂改、或抹杀、或压抑,旨在借助托尔斯泰纪念并且通过对这一资源的有效把控,创造出符合各自价值取向的公共记忆。其结果是,战时中国文人的托尔斯泰纪念,不仅在言说托尔斯泰的不同维度时音调各异,即便在谈论托尔斯泰的相同元素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在这个维度上,亦可以称战时中国的托尔斯泰纪念是政治派别“撕扯”的“战场”。
注释:
①李今:《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309 页。
②毛尹若:《托尔斯泰在苏联》,《逸经》1937 年第25 期。
③⑩⑯永成:《思想家及艺术家的托尔斯泰》,《苏俄评论》1935 年第9 卷第6 期。
④高洁:《托尔斯泰小传》,《世界晨报》1935 年11 月9 日。
⑤万心齐: 《谈托尔斯泰》, 《人世间月刊》 1940年第2 卷第1 期。
⑥静闻:《纪念托尔斯泰——回英室随笔》,《青年文艺》1943 年第1 卷第5 期。
⑦⑳苗垺(周剑萧):《向托尔斯泰学习》,《新文艺月刊》1940 年第1 卷第2 期。
⑧一柯(周立波):《纪念托尔斯泰》,《生活知识》1935 年第1 卷第4 期。
⑨郭沫若:《中国战时的文学与艺术——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在中美文化协会演讲词》,《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第19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191页。
⑪参见《编后》, 《文化杂志》 1941 年第1 卷第4号。
⑫L·托尔斯泰著、荘寿慈译:《论艺术——给〈艺术新闻〉的发行者N·A·阿历山德罗夫的信》,《文化杂志》1941 年第1 卷第4 号。
⑬袁水拍译:《托尔斯泰对于文艺的见解》,《文化杂志》1941 年第1 卷第4 号。
⑭王海洲:《暗箭:政治象征的三重争夺》,《江海学刊》2010 年第5 期。
⑮M.Brovin 作、高植译:《托尔斯太百一〇年诞生纪念》,《抗战文艺》1938 年第2 卷第11、12 期合刊。
⑰本社:《纪念托尔斯泰》,《自由中国》1941 年第1 卷第2 期。
⑱⑲封斗: 《纪念托尔斯泰》, 《奔流文艺丛刊》1941 年第1 辑。
㉑编者:《托尔斯泰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导言》,《新文艺月刊》1940 年第1 卷第2 期。
㉒王志耕:《列夫·托尔斯泰与中国革命》,《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1 期。
立波:《莱夫·托尔斯泰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世界知识》1935 年第3 卷第7 期。
㉓㉔止戈: 《对于托尔斯泰的评价》, 《礼拜六》1935 年第620 期。
㉕葆荃(戈宝权):《关于托尔斯泰》,《学习生活》1943 年第4 卷第2 期。
㉖汪兆铭:《和平宣言》,《大民》1940 年第3 卷第3 期。
㉗参见《编辑后记》, 《新东方杂志》 1940 年第2卷第3 期。
㉘桑瞑:《托尔斯泰的生平及思想》, 《新东方杂志》1940 年第2 卷第3 期。
㉙叶伟:《在甘地倡导的“印度反战运动”中想到托尔斯泰》,《新东方杂志》1940 第2 卷第3 期。
㉚参见《社论:纯化意识统一精神》, 《新东方杂志》1940 年第2 卷第3 期。
㉛祝平:《向托尔斯泰致敬》,《青复半月刊》1941年第3 卷第2 期。
㉛淡云:《托尔斯泰的愤慨和我们的愤慨》,《新闻报》1936 年2 月11 日。
㉝丘斌存:《岂是托尔斯泰底无抵抗主义》,《新时代》1931 年第19 期。
㉞林若:《论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纪念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十四年》,《时代中国》1942 年第6 卷第5、6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