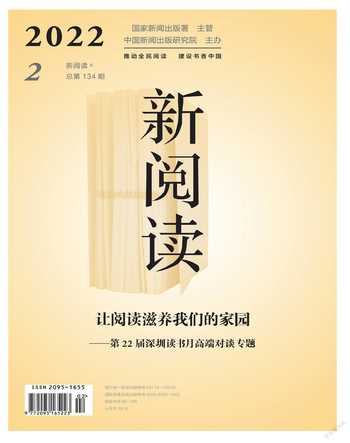以生命审美诠释科幻文学的“宇宙之问”
王红旗
吴言的刘慈欣评论集《从流浪地球到三体:刘慈欣星系》,在中译出版社出版问世。这是一部全方位系统研究科幻作家刘慈欣创作思想与艺术成就的评论专著。
吴言以理性与情感体悟认知的生命审美,以纵横开掘而勘测源头的“灵魂考古”,检视人类“未来往事”集体记忆的神思智慧,阐释刘慈欣作品科幻宇宙的星际宏构,超越单一性的文本批评,试图抵达对作家与文本探察的“双重”深度。不仅揭示刘慈欣的个体生命成长与精神发育历史,而且以其历时性、共时性的宇宙大裂变、大灾难,展现一个科幻作家“与宇宙精神沟通的无限想象力”,以在兼容中锐化差异的重构,所创造的科幻“最离奇的意境”,彰显人类“种植文明”历经的腥风血雨,渴望世界和平、多元共生的精神诉求。
不禁想到,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里写到:在新环境下,一个“真正的作家的诞生应是像一个人类的诞生——而不是像一个人的诞生——那样独一无二而有合情合理”。作家“已不是勤奋或广纳博采,而是把自己开放给整个宇宙……”[1]吴言正是从刘慈欣的人类意识,破开天极地心众妙之门的宇宙思维,想象力能量超凡或超验的“独一无二”,发现了其怀揣理想,把自己开放给整个宇宙的星际创构与精神飞翔。因为,只有精神的创造才能赋文本予生命,有精神性与想象力的作品才会飞出文本字面,深入心灵海天与社会时空,产生共鸣意义。此时,吴言的评论文字如同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仿佛也生出了飞向宇宙的翅膀,化解了科幻文学与纯文学之间所谓的“森严壁垒”。
“文以载道”是文学的天生使命,是所有文学样式心脉灵魂之本宗。刘勰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在?”强调“文源于道”的本原性,“道”即自然之道,可谓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规律性。吴言从本原性意义立论梳理,把这部评论集分为,星云初现、星系之恒星、星系之行星、星系漫游四辑。新颖独特的宇宙星际延展结构,是吴言与刘慈欣作品中的科幻星群意象无数次的精神相遇、碰撞而生成,呈现人类“个体”与“宇宙”生命审美的哲学逻辑,构成寻找“人类共同精神”的、形而上的“宇宙之问”。
第一辑“星云初现”,以标举“刘慈欣与中国电影科幻元年”的电影《流浪地球》横空出世,荣获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开篇,把刘慈欣的科幻小说电影放置于世界科幻历史,在与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卡梅隆导演的《阿凡达》、诺兰导演的《星际超越》电影比较中,从其对西方科幻作家的仰慕、学习、质疑,到“自我”走向科幻创作的心路历程,表现刘慈欣创造中国科幻世界的实践与雄心,走向国际舞台的影响力,进而推向世界科幻界的前沿。并且,把刘慈欣丰富的中短篇小说,以末日系列三部曲、大艺术系列作品与战争题材科幻演绎等等,划分为十个部分,如不同经纬星罗棋布的十个星座,勾画出刘慈欣科幻宇宙星系的轮廓样貌。以2000年《流浪地球》问世为界,把新千年之始,定义为刘慈欣科幻小说创作的“转折之年”,开启“人与自然”“现实+科幻”宏大叙事的“流浪地球时代”,把人与自然命运面临的“多重困境”抛入他的科幻宇宙创构之中。
第二辑“星系之恒星”,是对刘慈欣最重要的长篇代表作,“三体三部曲”即《三体》《三体Ⅱ:黑暗森林》《三体Ⅲ:死神永生》的文本评析。吴言运用汇通古今中西的转换与拼接,明察秋毫的文本细读与讲述,探索刘慈欣“三体系列”隐喻世界演绎的“察今”之意。详尽分析其严酷的自然环境、极端的霸权专制,以及“三体人”情感冷酷麻木的“金属质地”。在《三体Ⅱ:黑暗森林》里,飞向“近未来和近太空”,看到弱肉强食的黑暗丛林法则;在《三体Ⅲ:死神永生》里,飞向“遥远的未来和更遥远的宇宙”,象征人类携带着“原根”的飞翔梦从现实延伸到永远,“初次触摸到宇宙的边缘”,领略到“悲壮之美”的更高境界——“空灵之美”。在人类难以企及、“见之未见”的宇宙边缘,发现了不朽时空的黑夜里,永恒的光明“元境”——宇宙之爱,在于“母性”。
第三辑“星系之行星”,虽然是对刘慈欣“三体系列”之外的其他科幻长篇评析,却与其有着必然联系。吴言变换更自由的叙事方式,首先从被誉为“三体前传”的《球状闪电》开始,讲述刘慈欣“球状闪电”的创作灵感,来自与一种大自然现象的启示,是亲眼目睹雷雨天的球状闪电记忆,深藏于心孕育二十多年的科幻形象。接着详细解读《超新星纪元》的诞生,这部小说与《流浪地球》有着相似的恒星“氦闪”创意,以“宏人”与“微人”的空战,“太空史诗与人类歷史糅杂”、儿童游戏虚拟的世界大战等,似是而非地“童心”视角,以“地球童年的全息寓言”隐喻现实“不稳定”的国际关系局势,可谓惊心动魄。进而分析《魔鬼积木》中表现的基因技术伦理困惑,引出刘慈欣与戴锦华的对话,提出“人”的定义有谁来确定的问题,直指现代尖端科技突破人伦底线,尤其制造的战争武器可以瞬间毁灭人类,科技可以为实现人类梦想服务,也可以为“梦魅”助纣为虐。那么,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发明者,人的定义当然由人自己的人性来定义。因为“一个人的本性是由他的行为决定的,他所面对的现实是他自己的产物。”[2]这是一种对“拟真”科幻的“神经质社会”的体验、质疑、反思与追问。
第四辑“星际漫游”,是刘慈欣星系全景综论与两场对话。如果说第一、二、三辑,吴言以层层递进、极详尽的叙事与诠释,描绘出刘慈欣科幻宇宙的星系图景,那么“星际漫游”则是以高度概括,整合其科幻世界独创性的“创世纪式”价值,“黑暗森林法则”“宇宙文明公理”“宏细节”等最具特色的“硬科幻”风格,科幻意象的丰富奇异、塑造地外文明形象、以及更高级智慧文明“他者”的文化意义。尤其对“三体系列”救世主人物形象威慑度、技术与道德指数分析,以科幻宇宙“零道德”、星际战争的末日体验,喻指人类社会文明进化“路上”的冷酷铁血,论证人性善恶、爱憎与终极悖论。警示人类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自己才是自己困境的制造者,揭示刘慈欣的科幻宇宙与人类社会结构病体之间内在联系的真谛,向当代文坛树起一位科幻宇宙星系雕塑者与星际沉思者作家形象。
刘慈欣科幻创作的诸多人物,虽为人名但并非人形,或者只是地外文明类形象的符号代码,但是,当与人类社会事件发生遭遇性嵌入或连接,科幻宇宙的漫长黑夜,“三体文明”失败,地球的毁灭与拯救,太阳的陨落与再升,诗云的壮美,空灵的场景,呈现的便是以科幻为筋骨、翅翼,人文为灵魂的“人化自然”,其超验的形象与精神性力量,不仅隐喻家国民族文化结构内部发生的巨变,世界社会秩序动荡浮沉导致人类生存命运之艰难困境。而且对厘清现代性文明的致命“痼疾”,即世界霸权、战争拓殖、暴力掠夺等,野蛮的文化“拔根”造成越来越多的“文明黑洞”,提供了一种具有攻心力的认识途径。再者,其科幻文本的主题表达,拯救、牺牲、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内在灵魂,更蕴含一位当代科幻作家对人类历史、现世与未来的沉思关怀,大野之恋,济世之梦。
吴言对刘慈欣创作的“流浪地球时代”,《流浪地球》《微纪元》《吞食者》《乡村教师》《中国太阳》《诗云》《梦之海》《欢乐颂》等科幻文本,“多元性”“互文性”的分析阐释,不仅以“未来往事”“星系云图”表现刘慈欣精神星系演化史,而且文本细读传递出刘慈欣的自我生命成长亲历经验,在黄土高坡山水之间,日常生活的人生小道,思考人类生命价值大义,领悟宇宙星空万物奥秘,是其创作科幻小说的最初灵感来源。尤其亲眼目睹社会现实,假托科技之名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产生对人与自然命运的深切忧虑。这种忧虑同百年前爱因斯坦的忧虑有惊人相似:“原子的分裂改变了一切,就是没有改变人们的思想方式。于是,人类正朝着一场无与伦比的浩劫漂流过去……”[3]
因为“21世纪是科技的世纪”,不仅科技成为世界强国之间的竞争焦点,而且越来越成为未来世纪的权力主宰。新千年伊始,人类文明的新生性力量、破坏性力量与强生性力量,展开了殊死博弈。人类未来命运是迈向“多元一体”的合作共赢,美美与共之大同,还是硝烟弥漫的分裂与战争?刘慈欣作为一个人类危机意识的觉醒者,以科幻“拟真”社会的宇宙宏大叙事应运而生。刘慈欣的科幻笔下,尽现人类亿万年进化的“文明病态”与沧桑之悟:人类的理想信仰是不灭的精神之火、希望之光,其生成的文化力量之强大,可以决胜乾坤;人类“智慧生命的精华和本质,是技术所无法触及的”。
吴言在解析刘慈欣《三体》游戏建构的隐喻世界时,最先出现了中国古圣先哲,周文王与墨子、殷纣王与伏羲、神农氏与轩辕氏、孔子与孟子,等等,还出现了西方科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形象,哥白尼、教皇格里高利、亚里士多德、伽利略、布鲁诺,接着更出现了牛顿、爱因斯坦、冯·诺依曼、秦始皇、居里夫人与吴健雄等。她把一個个不同时代的古今中外哲学家、科学家与思想家,一件件科学历史事件演变的科幻壮举,从其科幻小说影视里如数家珍地捡拾出来,进行重组,构连成一条中西智慧跨时空地整体“合一”、纵贯人类文明的文化、哲学与科技发展数千年流变历史,论证其科幻场景与社会历史真实之间的本质联系,仿佛把人们带回了被“长期遗忘”的人类童年记忆。
尤其,对作品中既遥远又亲近、既陌生又熟悉的“宏细节”捕捉,更表现出其阐释力的独特性。如秦始皇率领统一六国的三千万雄师,在冯·诺依曼指挥下,竟然演化成宇宙绝无仅有的、庞大的“人列计算机”,即便是“中西合璧”的最尖端科技,具有雷霆万钧的威慑力,却仍然未能挽救“三体文明”的毁灭;再有在《三体Ⅱ:黑暗森林》里,人类两艘仅存的太空舰队“青铜时代”号、“蓝色空间”号,演绎着只有脱离“地球母星”,才是人类文明延续的希望,《三体Ⅲ:死神永生》中,云天明身患绝症安乐死之前得到一笔巨款,为自己暗恋的大学女同学程心买了一颗星星。一个个充满悖论的多重隐喻,自然会联想到人类智慧第一次大觉醒的“轴心时代”至今,东西方两种文明形态的社会历史真实。
吴言评论到,在“疯狂的技术主义”驱使下,“黑暗森林法则在互联网界已被誉为从业圣经……成为他们合理化自身的所谓市场行为的理论依据。而若用技术指数和道德指数衡量互联网这一行业,那么它的技术指数在递增,而道德指数在递减”。[4]因为全媒体科技时代的“疯狂的技术主义”,更会衍生出肮脏、色情与暴力甚至邪恶,恶的传播速度与繁殖能力远比善更快更强。因此刘慈欣在《三体Ⅲ:死神永生》里,把“三体世界”在地球的代表最终显化为一位女性——程心。程心选择了对人、地球与宇宙的爱和责任,却陷入一个接一个的道德困境,而失去拯救地球的机会。吴言解开这位具有全人类共同精神与“正确普世价值”形象的很快被人类遗忘,与女魔法师之死、与精神危机和女性象征的文化联系,意在强调如果世界上没有如圣母般人性“完整的人”的程心,人类可能早就灭亡了。人类对她的误解甚至“遗忘”才是人类自毁。
总之,这部评论专著,是吴言对刘慈欣的创作理念、历史“心途”与科幻文本的整体考察、跨文化研究,对中外报刊网站有关作家作品的报道评论文章,以及作品中涉及的古今人类社会政经、科技与文化历史人物与“元事件”,广泛搜集与综合提炼的融会贯通而生成。吴言的计算机工程师专业、从事金融信息工作的科技思维经验,与科幻文学有着“血脉”近亲的优势,更有其对文学具有天赋性灵的情有独钟,因而能够穿越其浩瀚文字与在场感极强的科幻星际表象,洞察其精神内核即人类学、未来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等多重隐喻,进而深度理解与精准把握其本质深意。不仅摆脱了“学术教条”的呆板套路,而且以科学与文学语言的结合转换,理性与情感之间无处不在的人类关怀意识,对宇宙生命的审美探索,建构起一座令人举目的、多维度的刘慈欣科幻“宇宙精神星系”。
这部系统的“刘慈欣星系”,发现了其创作的科幻宇宙,以独有的精神震撼,改变观念、涤荡灵魂的醒世力量,为疗救人类社会病的综合症候,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家与国、国与国之间,爱与关怀的平等伦理,发起了数十年如一日的人类文化“寻根”行动,引领人们找到“回家”的路。其“现实主义在科幻中产生了核裂变般的力量”,“科幻的魔法棒一经同现实结合,就焕发出神奇的、前所未有的生命力。”[4]希望吴言将来能够超越“自我”与“他者”既定的技术、哲学与文化局限的束缚,为科幻文学批评探照进文学“道义”精神的暖阳,开拓出新的宇宙审美苍穹。
参考文献
[1] 伊塔洛·卡尔维诺. 新千年文学备忘录[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9: 10.
[2] 乔治·弗兰克尔. 心灵考古[M. 北京: 国际出版文化公司, 2006: 8.
[3] 余谋昌. 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2.
[4] 吴言, 从流浪地球到三体:刘慈欣星系[M].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20: 288-28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