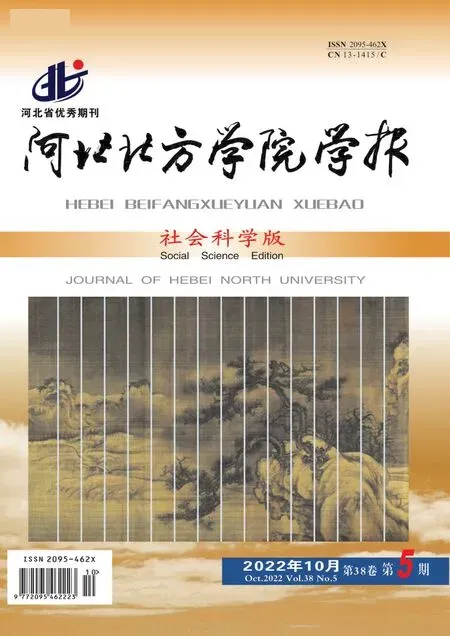“闲情渐遣借途穷”:论叶燮的闲适诗
汪 超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叶燮是清代最著名的诗论家之一,其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也不容忽视。王士禛称赞道:“《已畦大集》诗笔皆凿凿有特见,熔铸古昔而自成一家之言。每见近日稗贩他人语言,以墉赁作活计者,譬水母以螺为目,鹰不能行,得距驶负之乃行。夫人而无足无目则已矣,而必藉他人之目为目,假他人之足为足。安用此碌碌者为惟先生卓尔孤立,不随时势为转移,然后可语此。”[1]现存二弃草堂本《已畦诗集》共11卷,除残卷里叶燮的一些早年诗作外,前10卷明确时间最早的是1681年的《予自癸丑春过明圣湖辛酉冬重至湖上访昔年同学故人大半为异物孤山六桥一带亦苍凉非昔日毛稚黄王仲昭访予客舍为谈往事慨然赋长歌贻二子》,此时叶燮已50多岁,早已被罢官回乡。该诗集的体例大致是以时间先后为序,所以其中的绝大部分作品均为叶燮归隐之后所作。既为归隐之作,必然少不了徜徉山林间的闲适之情。因此,闲适诗成为叶燮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山中隐士:闲适诗中的诗人形象
许慎《说文解字》:“闲,隙也,从门从月。”清代段玉裁注:“闲者,门开则中为际,凡罅缝曰闲。”《庄子》载曰:“夫圣人,鹑居而殷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2]421闲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源远流长的概念,且陶渊明和王维等人的诗歌早就具有闲适意味,但闲适诗的正式命名则要追溯到白居易将自己的诗作分为“讽喻”“感伤”“闲适”及“杂律”4类。“又或退公独处,或卧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3]2794由此,闲适诗成为诗人颇为青睐的一种诗歌题材。闲适的本意指时间或空间上的空暇,但在诗人的创作中往往更进一层,上升到对心境的描述。徐增言:“夫作诗必须心闲,顾心闲惟近乎道者有力。”[4]433白居易言:“身闲无所为,心闲无所思。”[3]1492由此可见,“身闲”与“心闲”息息相关。对叶燮而言,罢黜后的山林生活让他“身闲”,也由此远离了朝堂的纷争,因而又获得了“心闲”,身心俱闲,自然会创作出带有闲适意味的诗篇。
身为遗民之子,叶燮选择出仕想必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康熙十五年(1676),因与当地士绅发生冲突,叶燮遭到罢黜。据《清史稿·文苑传》记载:
康熙九年进士,选授宝应令。值三藩乱,又岁饥,民不堪苦。累以亢直失上官意,坐累落职。时嘉定知县陆陇其亦被劾,燮以与陇其同罢为幸[5]。
仕途遭阻,又无经济田产,叶燮只能回归山林,正如《次韵答魏里蒋声中》中描述:“丈夫不封侯,所需田二顷。二俱无是公,决策逃箕颖。吾常以此心,质之形与影。”[6]357在归隐山林后创作的闲适诗中,叶燮常流露出自己的隐逸之心,并表现出一种安贫乐道的心境。如:
我本山中人,只说山中事。勋业镜不看,远道书绝致。三株两株梅,半池半屋地。饥来谴无方,客到谈自恣。幸无汲汲肠,奚事勉勉志。所求石与甔,一乐在饱醉。远檐花满枝,便是吾生遂。(《山居杂诗其二十九》)
仕途已断,亦无汲汲之心,只能与梅花相伴。他隐居于自己的二弃草堂,自称是“尽忘门外事”[6]334,还呼唤朋友一起隐居。如《赠海盐曹飞雝》“早携妻子鹿门去,天空海阔迟君来”;《叠韵答学山其三》“拂拭汾干留片石,我将樵隐尔为渔”。这些诗都透露出一种悠然自得的快意,也可以看出叶燮对自己的隐居生活十分满意。
众所周知,叶燮视杜甫、韩愈和苏轼为最优秀的诗人,曾言“杜甫之诗,独冠古今。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惟韩愈、苏轼,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立为三”[7]。此外,他对隐逸诗人的代表性人物陶渊明亦颇为推崇,还在《已畦集·密游集序》中将陶渊明与杜甫、韩愈及苏轼并列在一起:“志士之诗,虽代不乏人。然推其至,如晋之陶潜、唐之杜甫韩愈、宋之苏轼,为能造极乎!”同时,陶渊明对叶燮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叶燮会直接在诗中提及陶渊明,将其作为隐逸的象征,表达自己要步武其后的心愿。如《大林寺心壁上人以山居诗相示次韵以赠其四》“东林犹是当年寺,可拉渊明共住山”、《上巳后三日遇胡存仁方伯于虎阜精舍示赠邹郎和之其二》“只有闲情销不去,还拈五柳一株香”以及《同韩蘧庐羽南闻山游弁山夜宿资福寺禅寺其三》“携得陶公酒,来寻谢客山”等诗句,都表明自己希望能与陶渊明一样做一个山中隐士。另一方面,叶燮在诗中化用陶诗,如《京口何雍南为余言向年游西湖适蒋大参秉节会城总角笔研友也此行本为两峰而来若佝偻宪使之门当为西湖所笑竟不见蒋而返余高其意作歌增之》“兴尽长歌归去来,一肩挥手越王台”、《口号赠真际开士其一》“结庐不必去人寰,车马喧中自性闲”和《陈殿升过草堂有赠次韵答之》“坐待月明升绝嶂,哪知晋魏莫论秦”。这些诗句分别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和《桃花源记》,都带有脱离俗世与回归自然的潇洒快意,表明叶燮渴望拥有如同陶渊明一般的悠然心境,渴望成为与陶渊明一样的闲居隐士。此外,在叶燮的归隐生活中,美丽的山水风光自然成为诗人欣赏和吟咏的对象。如:
故宫遗迹乱山中,俯挹清泉注不穷。獭随螺痕人面杳,轻钩淡抹水心空。遥青借月双双见,曼睩横波曲曲工。识得眼前非相在,不须空有问庞公。(《酌画眉泉同王禹庆周汉绍》)
与三两好友一起寻访古迹,欣赏山水,在“人面杳”和“水心空”这种静观中获得一种超然的感受,并由此想到隐士庞德公,这首诗可视作叶燮山林生活的一个缩影。与朋友一起游山玩水是他归隐后的主要娱乐之一,他的许多诗作中都著有副标题,标注出与哪些友人同游。如《红梅同顾侠君李含英》《赋得柳色黄金嫩同陈起雷郑贾生汝鸿书》和《小天平山同顾迂客雷阮徒》等诗,与《酌画眉泉》一样都透露出相似的闲情逸致。值得注意的是,叶燮的草堂还是他悠闲度日和谈天话旧的场所,在谈及草堂时他不无自得:
语我园林好,荷花一里开。岂真营晚计,不负叹奇才。濠上缨堪濯,城隅迳绝媒。借君鱼鸟话,佐我草堂杯。(《乔石林侍读来过草堂即事八首之七》)
欣赏着“园林”与“荷花”,与友人闲话“鱼鸟”,在草堂饮酒作乐,这应该就是叶燮山居生活的真实写照了!总之,叶燮在闲适诗中表现出的闲情逸致与悠然洒脱,以及他对陶渊明诗歌的化用,共同塑造了一个在山居生活中悠然自在的隐士形象。
二、佛道之间:闲适诗的思想渊源
闲适诗从创作之初就总是浸透着宗教的意味,即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里,儒家思想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佛道思想作为补充。其中,儒家思想意味入世与世俗,佛道思想则代表出世与超脱。读书人仕途一旦受阻,入世的理想就会幻灭,而佛道的出世思想便会占据上风。这或许就是闲适诗总带有佛道色彩的原因。
叶燮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清初思想界正对晚明空疏的学风进行反思,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王学末流的批判,即认为道德感沦丧的王学末流大行其道,是国家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于是,大儒们纷纷强调恢复古礼,重建儒家的道德伦理。例如,许多人通过每日撰写善行与恶行这种方式来督促和警醒自己,时常带有沉重的罪恶感。发展至后来,甚至梦境中的不安也被视作自己的内心不诚,其道德警示可谓无孔不入了[8]。简言之,儒家思想容易给人在心理上造成强大的道德压力,因此难以使人产生闲适的心态。胡应麟曰:“曰仙、曰禅,皆诗中本色。唯儒生气象,一毫不得着诗;儒者语言,一字不可入诗。”[9]这话或许苛刻,但也表明至少闲适诗与佛道两家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叶燮的家学渊源也与佛教有相当紧密的联系。正如他所言:“家风述德有传经。”其祖母冯氏笃信佛教,“燮父绍袁,明进士,官工部主事,国亡后为僧”[4]12,还曾应西方庵主德安所请撰写《西方庵碑记》[10]。此外,叶家曾与为僧的金圣叹有过一段交往。这样的家庭氛围使叶燮自小就浸润于内典之中,弟子沈德潜在为其作传时写道:“稍长,通《楞严》《楞伽》,老尊宿莫能难。”[11]佛教思想是叶燮用以排解忧愤的工具,或者讲是一种逃脱俗世的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讲:“轩然酒罢论时事,不如归正三摩心。”[6]305再如:
忆昔十五六,庄诵首楞严。妙奢三摩他,错向文字诠。浮沉四十载,七处纷纠缠。侈口析真妄,杀活竿头粘。近知黜耳目,八识根现前。不婴世网剧,安从解牢衔。世尊问圆通,灰心第一圆。(《山居杂诗其二十五》)
“不婴世网剧,安从解牢衔”,这与陶诗“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表述颇为相似,都是将世俗生活看作牢笼。叶燮归隐后开始回忆自己年少时阅读佛经的经历,借佛教思想以求解脱与超然。除此之外,佛教在更具体的层面亦对叶燮的诗歌产生了一定影响,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与通俗化。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向普罗大众传教是光大教义的必由之路。因此,佛教从诞生那一刻起,僧侣就运用多种方法来推广和宣传教义。讲经和超度等言说方式不能过于深奥,而应通俗晓畅,于是便出现了偈颂。偈颂一般是偶数句,有时押韵,有时不押,在形式上与诗歌有相似之处。叶燮的一些诗作就很像偈颂,语言口语化和通俗化,还流露出明显的理趣。例如,《一偈赠行脚》“草鞋不费赵州钱,拖却随风去住缘。尘世真穷师独富,家门地阔与天圆”;《和济苍上人原韵》“立处何须问别峰,别峰只在此峰中。自从吸尽西江后,哪得湖流一滴东”。
从叶燮诗中也可看出其与道家思想的渊源。叶燮对庄学甚为推崇,屡屡在诗中借用《庄子》的典故,如《奉和秋岳先生惠示次韵》“临濠鱼乐谁知我,出岫云多似有心”,《叠韵重答孟举》“自笑宫商瓮里音,筌蹄翻傍兔鱼寻”,《留云堂歌为白田乔云渐赋》“白衣历乱幻苍狗,伎俩尽态终何有”。还有从《庄子·逍遥游》中得到启发的《鹏息篇》:
漆园语逍遥,鹏搏九万里。六月始一息,息后尔何以。斥鷃笑奚为,鹏亦悔其指。却敛垂天云,饮啄篱落里。伊昔六合弥,藏固在一黍。回首谢南溟,吾将鸠鸾侣。
诗人在诗中常通过庄学万物齐一与宠辱不惊的精神使自己豁达释然。如《叠韵投乔云渐四首其四》“种柳成围叹汉南,树犹如此孰能堪。周旋只我宁容两,不朽凭他莫管三。有酒自浇驹过隙,何心去问俗交諵。纵饶大地无风雪,只向袁安卧里贪”和《被黜后叠前韵六首其六》“空华奚事参同契,齐物何须问永龄。敢拟前贤缘底事,也知磨蝎坐身星”。再进一步,是诗人的心态转向了隐逸之乐,如《叠韵又得三首》“不是濠梁地,翻令鱼鸟亲。道旁谁塞马,石畔几情人。借尔孤生竹,赢他十丈尘。绳床贪稳卧,忘却漆园身”。以上这几首诗都蕴含了一种旷达潇洒的意味。《庄子》中夸张奇诡的意象也为叶燮所喜,由此更呈现出粗豪壮丽的风格。例如,《留云堂歌为白田乔云渐赋》“君不见,垂天如翼起南溟,待族须臾滓太清。又不见,白衣历乱幻苍狗,伎俩尽态终何有”;《由栖贤涧北上岭见五老峰下瀑布》“闻根色界倏然惊,鹍水鹏云总不成。匹练银河非隽物,峰顶瀑布莫安名”。《庄子》中许多篇目本身就带有寓言的性质,叶燮在诗中化用其中的诗篇,这无疑为诗作增添了一种梦幻的气氛,恰似离开了现实世界,这多少也与叶燮远离尘世的愿望相契合。
佛道色彩在闲适诗中的多次出现反映出其对叶燮诗歌创作的深远影响。联系诗人的身世遭遇,可知佛道思想是叶燮闲适诗的思想源头,他借此逃避失望的世事,从中寻求宠辱偕忘的境界与乐趣。
三、内心冲突:闲适背后的激愤与感伤
叶燮在闲适诗中时常提及陶渊明,并以佛道思想追求超然世外的解脱,看上去潇洒自然,俨然一副隐士模样。然而,在看似平和的诗作背后却隐藏着些许不和谐的因素。
叶燮的闲适诗中常残留着徘徊不去的激愤与感伤,如《集吴天章传清堂感旧限红字》“行路真难摈病废,闲情渐遣借途穷”、《梅花开到九分》“祝汝一分留作伴,可怜处士已无家”以及《叠韵答元礼侄其一》“抱璞无须泣卞和,阿咸此日胜人多”。这些诗虽有“闲情”,但不过是因为诗人“途穷”而已。本在赏花,却又借梅花哀叹身世;祝愿侄子之余,却以命运坎坷的卞和自比。先扬后抑,先积极后消极,这些诗句都产生了某种情绪上的冲突,也为诗作蒙上了一层阴郁。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仍与叶燮自身的思想斗争有关。因为叶燮成为隐士也是他仕途受阻后的无奈之举,虽受佛道思想影响,但他仍是坚定的儒家信徒。他曾在《罗汉寺隐峰演禅师语录序》中称赞一位高僧的同时又自称“吾儒”,以儒家的标准来衡量一位禅师的行为,“其为人诚实恳到,固吾儒所称笃实而有光辉者也”,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在其心中孰轻孰重可谓昭然若揭。在其文集赠序文中,放置在最前面的《家礼纂要序》和《闻礼述略序》两篇序文都是写给儒家礼学著作的。在《闻礼述略序》中他对儒家的凶礼作出解释:“于是阴阳之理,明人鬼之道,合幽明生死之故,盖不出日用之恒而得之。此凶礼之丧、之葬、之祭,圣人酌为万古之经,不易则至深远也”,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对儒家经典的熟稔与推崇。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自然还是将出仕做官当做人生的第一选择。此外,也有学者指出叶燮撰写《汪文摘谬》的主要原因就是汪琬常以士大夫自许[12],《汪文摘谬·送魏光禄归蔚州序》:“‘传于世’,尽矣,复添‘士大夫家皆有’句,岂士大夫又在世外者乎?甚矣,汪君之沾沾于士大夫也!宜其与昆山归元恭书,诎区区之布衣,而以士大夫自炫……殊不知当世之嗜仕不止者,即此士大夫也。”汪琬屡屡以士大夫身份自得,使叶燮大为不满,这多少也透露出他对自己仕途不顺的愤恨不平。换言之,叶燮的归隐并非心甘情愿,而是无奈的选择。因此,其诗中也常透露出激愤与不甘。如:
住山今日偶离山,为爱春塘碧涨潺。好友乍逢常惜老,名花错过尚留殷。风旛惯听空王句,樱筍能肥高士颜。怪底冲泥双曳屐,也知无计且消闲。(《集友人斋次壁间王勤中韵》)
这看上去是一首标准的闲适诗,与朋友在春天来临之际游山玩水,“空王”是对佛的尊称,由此可看出该诗的佛教色彩,整首诗的基调应是平静缓和的。但最后一句“也知无计且消闲”却急转直下,充满一种无奈的感伤,似乎是在诉说自己无事可做才来“消闲”。又如《溪边残雪》:
一夜寒溪冻色匀,忽闻滴沥已通津。乍惊玉质随萍梗,犹抱冰心问水滨。断粉临流难写照,遗钿委地属何人。桥边早有骑驴客,浅印霜蹄去觅春。
该诗题目下还写着“同金亦陶赵书年”,表明这是一首同朋友游山玩水的诗。但除了最后一句稍见一丝快意之外,诗中“萍梗”“冰心”“断粉”以及“遗钿委地”意象都充满了一种感伤。即便是在借庄学以图忘记烦恼之时,这种情绪也挥之不去,因此他频频使用“嗒焉”一词。如《翌日雨中再过采山亭复各赋四十韵仍限东字》中“嗒焉真丧我,无是子虚公”,《同南海梁药亭过平湖郭皋旭吴趋寓斋适海宁查韬荒至三叠韵》中“嗒焉吾丧我,灰木将焉欲”,《夜泊钱塘江》中“万象竞各有,嗒焉冥混濛”。“嗒焉”出自《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2]43“荅焉”即“嗒焉”,指一种怅然若失的状态,这大概也是叶燮的夫子之道。正如王阳明批评苏轼:“人言鼻吸五斗醋,方可作宰相。东坡平生自谓放达,然一滴入口,便尔闭目攒眉,宜其不见容于时也。”[13]这是儒士对文人的一种贬低,认为他们过分耽溺于行藏遭遇,不能像儒士那样长保志气和勇猛精进。评论是否苛刻暂且不论,但此言未必没有一定道理。按其思路来讲,苏轼并非真放达,同理,叶燮也非真闲适。叶燮在诗中透露出的种种消极情绪,说明其终究未能达到如陶渊明纵浪大化或者庄学中宠辱偕忘的境界。
闲适诗是叶燮归隐后创作最多的诗歌题材之一,表现了他的山林生活及其精神状态。从小熟稔的佛道思想成为其闲适诗的隐形源泉,但身为儒家信徒的他终究不能达到真正的闲适与忘怀。这不仅是叶燮个人的内心挣扎,也是所有心怀天下的隐士共同的心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