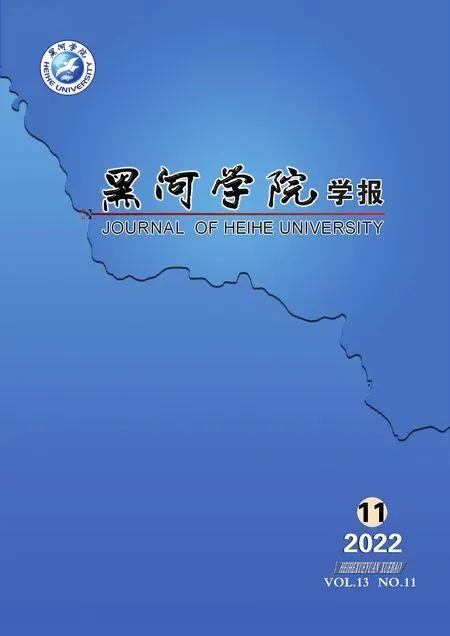论吉卜林戏剧独白诗中展现的英国性
李 姝
(大连财经学院 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近年来,随着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北美和欧洲的兴起,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1936)重新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值得注意的是,与吉卜林广受关注与肯定的小说作品相比,学界围绕吉卜林诗歌展开的研究不多,对其作为诗人所取得的成就褒贬不一。英国两位现代文学家叶芝和艾略特对吉卜林的诗歌作品就有着截然相反的评价。艾略特对吉卜林的诗歌作品不乏溢美之词,称其“有杰出的文字天赋”“诗歌作品不可轻视”;叶芝则认为吉卜林的诗歌甚至没有讨论价值[1]。实际上,吉卜林一生出版了8部诗集,其诗歌创作生涯跨越半个世纪之久。尤其是其戏剧独白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高度的鉴赏价值,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领域举足轻重。
戏剧独白诗脱胎于英美传统文学中的抒情诗,融合了抒情诗、叙事诗、诗剧的特点,既能抒情,又能叙事,还兼具诗剧的表现力,是一种独特的诗歌形式。丁尼生与勃朗宁所创作的戏剧独白诗作品对该诗体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吉卜林也从二位文学巨匠的作品中受到不少启发。其中勃朗宁的作品对吉卜林的浸染作用更大,吉卜林曾在自传中坦言自己对勃朗宁作品有所借鉴,并自比勃朗宁戏剧独白诗中的角色利波·利比。吉卜林的戏剧独白诗既有丁尼生式的主观抒情,又有勃朗宁式的人物塑造,是二者的有机融合。研究吉卜林的戏剧独白诗有助于了解该诗体由抒情向叙事转变的完整过程,并更进一步地把握诗歌文学与维多利亚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
一、英国性的建构:主流价值观与唯美主义的交锋
《玛丽·格罗斯特号》是吉卜林创作生涯中最负盛名的戏剧独白诗,此诗和其姊妹篇《麦克安德鲁的赞美诗》一同收录在《七海诗集》中。吉卜林在写给亨利·詹姆斯的信中不吝对该诗的赞美与推荐之辞,果不其然,诗歌发表后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肯定。《玛丽·格罗斯特号》的主角兼叙述者安东尼·格罗斯特爵士是一位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白手起家的船主,他在临终之时向儿子迪克交付嘱托,着重批评了迪克热衷文艺、缺少勇气的品行与心性,并用金钱诱导迪克将自己的尸体安放在玛丽·格罗斯特号(以迪克的母亲命名的货船)上,送至其母死亡的地点海葬。
文学界普遍认为,《玛丽·格罗斯特号》在结构与内涵上与勃朗宁《我已故的公爵夫人》有相似之处,两者都在诗歌中塑造了对立的形象与观念。在《玛丽·格罗斯特号》中,老船主格罗斯特坚毅、果敢、勤奋,是一位“敢于冒险的男子汉”,与之对立的是他那喜好文艺、性格软弱、不务正业的儿子迪克。诗中迪克的形象是由他父亲在斥责中侧面描绘的,而随着故事的深入,格罗斯特的独白演变为两种声音、两种性格,甚至两类迥异的价值观念之间的激烈交锋。可以说,诗中父子二人的冲突喻示了英国维多利亚晚期(尤以19世纪末为盛)的两种价值观念的碰撞:秉持勤俭、勤奋、谦卑的主流价值观与反对严肃保守、提倡特立独行的唯美主义思潮。其中,老船主格罗斯特是英国主流民族性格的写照,而儿子迪克则是唯美主义艺术家在诗中的映射。
从阿兰·欣菲尔德的观点看,戏剧独白诗中的叙述者往往会成为表达诗人观点的传声筒[2]。诗中叙述者与诗人思想观念的联系无论是明显还是隐晦,都能创造出不同的戏剧效果,使诗人个人观念的表达更有力量。在丁尼生《尤利西斯》中,叙述人尤利西斯与作者本人在思想上高度重合,尤利西斯的声音就是丁尼生的声音,因此,作品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在勃朗宁《我已故的公爵夫人》中,叙述人站在客观的视角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声音,但在叙述者客观、克制、冷静的背后却能隐隐察觉到作者对民主的推崇与对封建专制的鄙夷。《玛丽·格罗斯特号》同样描绘了两种不同的形象,代表着两种对立的观念,但相对《我已故的公爵夫人》,吉卜林的情感倾向更为明显,读者更容易察觉父子形象哪个是受到赞扬、哪个是遭到贬低的。吉卜林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清教徒,严肃、保守的教派作风对他的成长历程影响甚大,这使得他一生都对英国主流社会所尊崇的勤劳、简朴、诚实、坚毅等具有“英国性”品质的信条奉行不悖,同时对那些精致、新奇的艺术抱有抵触态度[3]。
结合上述背景,不难看出《玛丽·格罗斯特号》里老格罗斯特以独白的形式总结自己勤劳、成功的一生,就是作者吉卜林在表达自己对“英国性”品质的赞许、对唯美主义思潮的排斥。诗中的叙述者格罗斯特认为付钱满足儿子对精致艺术的追求是“荒唐的幻想”,但面对自己的海葬计划他又自豪地宣称“我能够付的起钱满足自己的幻想”。这一极富戏剧张力的对比明确地表达出了作者的价值倾向。斯克拉格认为,吉卜林曾借诗中叙述者安东尼爵士来表达他对颓废派运动的贬斥态度。此外,吉卜林类似的态度在其他戏剧独白诗中也有呈现。比如,《机器的秘密》一诗歌颂了机械造物的强大,而这些机械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发明家创造的,吉卜林借此盛赞那个时代人们的勤奋态度与蓬勃生命力,批评唯美主义者的颓废、懦弱与不务正业——他们就像《玛丽·格罗斯特号》里的迪克一样是社会的累赘,充满“荒唐的幻想”却没有行动力和毅力,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自理。总的来说,吉卜林在维多利亚晚期两种价值观念激烈交锋中借用戏剧独白诗的形式对英国民族性问题展开深入思考,他在许多诗作中都塑造了敢于展示自身性格与思想的叙述者,这些叙述者有效地传达了吉卜林的价值观念。
二、英国性的内涵:英格兰性与不列颠性
斯蒂芬·希桑认为,19世界末的英国为协调来自社会、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矛盾,开始使用“英国性”话语为主流意识形态塑性,从而达到重构大不列颠核心民族身份的目的[4]。但需要注意,这种重构仍然是“英格兰本位”的,英国主流社会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具有的“英格兰性”品质,即坚强、勇敢、真诚、率直、追求自由等是英国民族特性的基石。而大英帝国的其他民族,如爱尔兰人、苏格兰人等在这些品质方面都比不过盎格鲁—撒克逊人。因此“英国性”话语的建构必须以“英格兰性”为基础。吉卜林的戏剧独白诗自然可以归入这股英国性话语构建的潮流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民族叙事的基础上,英国性话语体系是同时超越了阶级叙事与性别叙事的。
其中,“超越阶级叙事”这一点不能用今天的眼光看。当时英国并未打破阶级壁垒,各阶层之间并没有建立起自由、平等的对话渠道。虽然贵族阶层已经没落,但工人阶层却还没有积蓄足够的政治力量。随着英国改革法案的出台,中产阶级掌握了议会选举权,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与价值引领者。因此,所谓的“超越阶级叙事”指的是用中产阶级价值观引领社会主流价值,各阶层都向中产阶级学习与靠拢。当时的英国女王亚历山德丽娜·维多利亚身为上层阶级却自觉信奉勤勉、顾家、行事稳重、忠于配偶等中产阶级价值观,并因此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尊敬。她的婚姻、爱情与家庭观念也成了英国民众争相学习的典范。安·帕里认为,吉卜林在《七海诗集》中,经常会借助勤奋努力的叙述者之口表达自己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赞同[5]。如《玛丽·格罗斯特号》中的老船主格罗斯特,他虽为出身底层的英格兰人,却靠着勤俭持家的作风、敢于冒险的精神与灵活的头脑成为富甲一方的船商并获封爵位。格罗斯特的成功离不开其妻子玛丽的支持,正是因为玛丽在精神上鼓励他、在事务上帮助他,才使他成长为一个坚毅、负责的男子汉。可以说,在格罗斯特的成功之路上几乎看不到阶级矛盾与性别对立,有的只是超越阶级与性别的勤俭、勇敢、坚毅、热爱冒险等“英国性”品质,也正是这些优秀的品质成就了格罗斯特。
吉卜林在戏剧独白诗《诺曼人与撒克逊人》中描写了诺曼贵族在临终时嘱咐后代一定要尊重撒克逊人、学习萨克逊人的文化,并指出撒克逊人看重公平与正义,是可靠的战士与忠诚的臣民。诺曼贵族在描述撒克逊的民族性时用的都是正面、赞美的语言,诗人借助诺曼贵族之口表达了自己心中所认同的英国性。根据这首诗中诺曼贵族教育后代要向撒克逊人学习的桥段,可以看出吉卜林笔下的英国性相比建立在“英格兰性”上的传统英国性更具独到之处:强调民族的融合与和解。吉卜林生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印度,在英国读完中学后又回到印度做记者,工作期间频繁与各民族、阶层打交道,正是因为这些经历使其可以从更宏大的视野阐释“英国性”。吉卜林的另一首以诺曼征服为背景的戏剧独白诗《铁毡》也表达了各民族和平共处的思想。此诗最大特点是没有明确叙述者的身份,读者无法从文中得出叙述者是诺曼人还是撒克逊人。叙述者将诺曼国王比喻为铁匠,将诺曼征服英国的过程比喻为“在铁毡上锻造英国”。吉卜林认为正是得益于诺曼国王这位“伟大铁匠”的锤炼,原本分散、弱小的英国才终于被打造成统一、强大的新国家。民族征服中的血腥杀戮、攻城略地都被描绘成为了打造更为宏大、完美的“英国性”所采取的必要手段。根据叙述者的描述,不难看出诗人对民族融合的褒贬倾向。综上所述,同英国主流社会一样,吉卜林笔下的英国性以“英格兰性”为基石,并在此基础上打破阶级壁垒与性别沟壑、支持民族的融合,与其说这种拥有宏大格局的民族性话语是“英国性”,不如说是“不列颠性”。
三、英国性的坚守:帝国的式微与诗人的守望
吉卜林在戏剧独白诗中关于临终场景的描写也具有丰富的品鉴价值。《玛丽·格罗斯特号》和《诺曼人与撒克逊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即诗中所描写的情境都是叙述者在临终时向后代交付嘱托。霍华德认为,人在临终时更容易展现真实的自我,因此,描写临终状态有利于角色的性格塑造。实际上,文学作品中临终场景的使用很常见,并非吉卜林独创,比如,勃朗宁就经常在作品中描写人物临死前的话语。吉卜林作品中临终场景的使用不仅仅是为了塑造角色,更是为了烘托出作品的气质、主题与调性。比如,《玛丽·格罗斯特号》中老船主的死亡与作品整体阴郁、衰落、腐朽的调性非常一致。格罗斯特爵士正是吉卜林所坚守的英国性品质在诗中的化身。他的儿子迪克软弱、散漫、喜爱唯美主义艺术,完全没有继承格罗斯特的品行。更重要的是迪克没有后代,因此,格罗斯特所代表的坚毅、勤奋、勇敢等英国性品质无法得到继承,他的死亡仿佛昭示着大英帝国的衰落。此外,从《诺曼人与撒克逊人》中的那位愿意学习撒克逊人、希望各民族和谐共处的诺曼贵族的临终嘱托,也可以看出吉卜林对英国民族融合问题持有悲观态度。
乔治·奥威尔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英帝国开始走下坡路,社会主流价值逐渐淡化,年轻人变得贪图享乐、玩世不恭,英国社会这些衰败的迹象令吉卜林长期处于一种焦虑、不忿的情绪中。其实,乔治·奥威尔的评价完全可以代入19世纪末的吉卜林身上,因为当时的英国已经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英国内部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机械化、城市化进程的冲击,逐渐走向瓦解,进化论的普及也极大打击了教派思想所涵盖的美德。而英国外部随着美、德、法、俄的崛起,“日不落帝国”的权威地位遭到威胁。大英帝国的崛起过分依赖殖民地,这也成为帝国衰败的诱因。运作如此庞杂的殖民领地需要消耗巨大国力,再加上殖民地发展起来后,当地人民的民族意识与独立意识会更强,并因此产生对抗情绪。面对上述忧患,吉卜林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从1849年起就连续为《泰晤士报》提供免费创作,通过发表《白人的负担》《退场赞美诗》等诗歌作品指出当时英国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应对策略:通过重构“英国性”话语,形塑民族核心品格,将各民族、阶层凝聚成一股力量,以此延续大英帝国昔日的辉煌。科尔斯认为,民族性的重塑往往发生在一个民族较为脆弱的时期,而当时的英国面对内忧外患,不可谓不脆弱,吉卜林的《七海诗集》也恰恰在这一时期出版。在《玛丽·格罗斯特号》中,务实、勤俭、敢于冒险的精神让老格罗斯特打拼出一个成功的商业帝国,而这个商业帝国实际上隐喻了富强的英国。从隐喻中不难看出吉卜林针对帝国的衰落给出的应对策略就是坚守务实、勤俭、敢于冒险等“英国性”品格。
四、结语
戏剧独白诗于维多利亚时代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学形式并非偶然,这一时期充满了民族与民族、科学与神学、贵族与中产、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在矛盾与交锋中乐观与悲观态度、积极与颓废思想交织在一起,谱写了一曲多声部交汇的音乐篇章。吉卜林正是这支交响乐中独特又不可或缺的声部,他从自己的经历出发,通过戏剧独白诗参与并反映了“英国性”话语体系的建构。吉卜林作为诺奖得主,小说成就颇丰,但其诗歌作品却并未受到文学界广泛关注,他在戏剧独白诗中既展示了自己的优秀品质,又为大英帝国的衰落给出应对策略。只有从多方面进行解读并挖掘出吉卜林戏剧独白诗的内涵,才能更准确地定位吉卜林的诗人身份与文学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