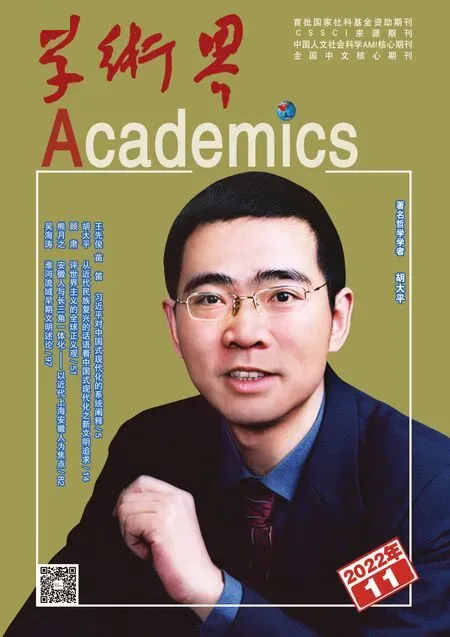乐府诗学“事”义命题的生成与内涵变迁〔*〕
王志清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6)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汉武帝时代乐府所采歌谣的说明。〔1〕因汉乐府的经典性,这一诗学命题也获得了经典性,更被后人视为乐府诗的本质特征。明清以来的诗学著述多以“叙事”论乐府,与“缘事而发”之说有直接关系。明人徐祯卿《谈艺录》曰:“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2〕清人郎廷槐《师友诗传录》述张实居语曰:“乐府之异于诗者,往往叙事”,〔3〕冯班《钝吟杂录·古今乐府论》曰:“盖汉人歌谣,后乐工采以入乐府,其词多歌当时事,如《上留田》《霍家奴》《罗敷行》之类是也”,〔4〕沈德潜《古诗源》曰:“措词叙事,乐府为长”,〔5〕“叙事”几成论乐府者的共识。“即事名篇”是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对杜甫新题乐府的赞誉,白居易《新乐府序》又提出“为物、为事”而作的宗旨。明清以来多以“叙时事”“传时事”“指论时事”“风刺时事”评价杜甫、元白的新题乐府和新乐府。缘事、即事、叙事、时事等,说明了乐府“诗”与“事”之间的特定关系,本文将之称为乐府诗学中的“事”义命题。“事”义诗学命题的重要价值,显然是由于在古典诗歌的抒情主流中,于古典诗学“言志”“缘情”说之外,又开出“缘事”一途,促使人们全面审视诗歌和诗学遗产。
当代学人对“诗缘事”的研究,关注乐府诗所缘之“事”的特点,其依据则是汉乐府文本。〔6〕这里面存在的问题是,“缘事而发”固然是对汉乐府的描述,但它首先是一个诗学命题,作为诗学命题的“缘事”与作品实际表现出来的“缘事”是否一回事?能否以今所见乐府诗之“事”完全对应诗学意义上的“缘事”?同时,目前研究中对“缘事而发”的生成问题关注较少。笔者所见,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对此稍有提及,认为其可能出自刘向的乐论、诗论,〔7〕但并未展开讨论。韩经太先生认为“缘事而发”是汉代的政治诗学,其发生机制可能来自“图议国事”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方式。〔8〕上述成果给本文以有益的启发和参考,但就这一经典性诗学命题生成的丰富的观念和话语资源,以及“缘事”与唐代“即事”命题的关系,后者相对于前者的内涵变迁等,还存在研究空间。对乐府诗学“事”义命题的深入考察,无论是对“乐府学”、古典诗学还是古典诗歌的认识,都颇为重要。笔者尝试论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生成的观念与话语资源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提出,建立在先秦两汉儒家乐论与诗学基础上,其中亦有刘向父子、班固的诗学贡献。〔9〕这一诗学表述中,“感于哀乐”与《尚书》“诗言志”说、《乐记》“诗者,人心之动”实质近似,认为人心之感与情志抒发的需要是诗、乐的创作动因。比较而言,“缘事而发”的诗学创建意义更为突出。当代学界往往将其单独出来作为古典诗学与“言志”“缘情”并列的“缘事”说。
(一)两个接近的诗学命题
“缘事而发”之前,与之较为接近的诗学表述有《韩诗序》“劳者歌事”一说,以及纬书《春秋纬·说题辞》中的“在事为诗”之说。唐代李善注《文选·闲居赋》云:“《韩诗序》曰:‘劳者歌其事’。”〔10〕《太平御览》卷五七三“乐部”一一引《韩诗》曰:“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其义甚明,认为“歌”与人的实际生活处境关系密切,有感于处境不足,遂发而为歌。饥者、劳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其歌谣直接表现真实生活与心境。在汉代以政治讽谕为《诗》学主流的背景下,此说关注到《诗》与下层民众生活的关系,尤为可贵。但也不宜将其意义提升过高,以为《韩诗》具有人民倾向,这样说的理由是,即便在对最能代表“劳者歌事”的《魏风·伐檀》一诗的解说中,实际上也未曾发现《韩诗》从“劳者”角度进行的解释。清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于《伐檀》篇引《毛序》《鲁说》《齐说》,皆认为诗旨为“刺在位尸禄”者,《韩诗》诗旨不异于此。“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引《韩诗》说曰:“素者质也,人但有质朴而无治民之材,名曰素餐。”〔11〕汉四家诗在对《伐檀》诗旨的解释上,都将主题归于刺在位者的政治讽谕意义下,而并非真正关注“劳者”所做之事,或对他们表示同情。“饥者歌食,劳者歌事”虽然注意到了《诗》对下层民众真实处境的描写,但还谈不上是对《诗》与现实生活密切关系的认识,不能视为对《诗》创作动因的理论形态说明。〔12〕
《春秋纬·说题辞》曰:“诗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故诗之为言志也。”〔13〕西汉末出现的纬书,以天人感应说为理论依据,其中《诗纬》《乐纬》以及《说题辞》中对于诗、乐本原性的认识异于传统儒家乐论。《诗·含神雾》曰:“诗者,天地之心”,《乐·动声仪》认为“乐”为“承天心,理礼乐,通上下四时之气,和合人之情,以慎天地者也”,皆将诗、乐置于宇宙天地的框架中,作为天人之际的沟通。《说题辞》“诗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的说法同样是将诗、乐提升到体现天地意志、居于天地核心地位的高度,这是《纬书》诗、乐论的特殊之处。除去对诗本源的哲学性认识外,其实《说题辞》还是可归入传统诗学“言志”一派的。“恬淡为心”描述心的未发状态,“思虑为志”是心动之后打破恬淡的感发状态,其实就是“感于哀乐”。恬淡之心升起哀乐之情,进入思虑、不平衡、不平和之状态,其情、其志乃不得不发。“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是说诗因事起,事在诗中,未发于诗中时为“谋”。《说文》云“虑难为谋”,故“谋”“虑”相通,“未发为谋”与“思虑为志”实则都是指人心被触动故而情志处于酝酿中的那个阶段,也就是诗情腾涌而未发的准备时刻。对“在事为诗”的理解,应考虑到《纬书》谶纬之学的性质。汉代有所谓谣谶之说,谣谶被视为神秘的预警和昭示,体现所谓上天意志。《汉书·五行志》中记录的“诗妖”,皆出以童谣的面目,被视为朝政、祸福的征兆和暗示。这类歌谣在解说者看来,实有两层“事象”,一是歌谣表面所写之事,二是歌谣隐射之事。作为纬书的《说题辞》,“在事为诗”中的“事”可能更指向谶纬中的灾异之事、政治与宫廷中的祸败、难言之事。诗谶、谣谶所述之“事”的政治性、隐秘性,决定了“在事为诗”的“诗”实为一种政治和社会寓言。如果我们注意到“在事为诗”出现于纬书的特定语境,注意到纬书对诗作为天人感应中介的推崇,那么,对其诗学意义就不宜放大,不能将之与更具社会性的“缘事而发”同等看待。“在事为诗”尽管主要指向政治生活中的隐秘难言之事,出以诗谶、谣谶,借助“天人感应”的理论力量获得隐射时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其说有特定的谶纬之学意义,但毕竟这一说法以“事”称诗,在经典化的“诗言志”之外,开出以事说诗的方向。
(二)“感于哀乐”与刘向论心之“感动”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本为论汉乐府所采歌谣特点的,“感于哀乐”意为人心升起哀乐之情,这是歌谣创作的心理动因。强调“心”的易感状态,在刘向的著述中也很明显。因为《艺文志》与《别录》《七略》的渊源关系,故其中的诗学表述也可能与刘向的诗学及其他论述相关。刘向确实对人心之“感”的问题较为重视。首先,刘向的《说苑》多次征引《乐记》,其中包括“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这一为人熟知的观点,说明刘向认同这一音乐发生动因。其次,在其著述中,多次论及“感动”问题。《说苑·贵德》曰:“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满,满然后发,发由其道而致其位焉。”〔14〕诗之“发”是由于“思”的积与满这样一个渐进过程使然,“诗”发于人心之“思”,“哀乐”也在人心种种之思的范围,诗起于人心之思与“感于哀乐”对创作心理动因的认识是一致的。所不同者,刘向此论强调了感情的蓄积对诗之“发”的推动,所谓“满而后发”即意味着已至不得不发的状态,诗的产生是由于内在之思不断聚集而达至充实并最终引发的结果,人心之思必然要得到发挥和抒泄。《说苑·尊贤》借孔子之口曰:“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发其情者也……”,〔15〕人之胸怀、怀抱以及情感情绪会借助“言”这一渠道表述出来。无论“思”“情”还是怀抱,都在人心之内,都属主体情志。
除了对人心之思、人心之情必得以抒发的表述外,刘向还论及更具根本性的“气”之“感动”。《说苑·辨物》曰:“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气感动,触情纵欲,故反施乱化。”〔16〕批评无教养者刚刚具备了精气化育的质性而感动了生息之气,便触发了内心潜藏的情欲以至做出纵欲之事。“生气”可理解为人的生命体气,其气易于“感动”并引发人心之“情”,故“生气”较之“情”更具本体性。“生气感动”的必然发生,源于人的生命能量不得不释放的特质,这是属人的规定性。“生气感动”与“触情”,既是人的自然之性,就不能堵塞,应控制的是“欲”。《谏营昌陵疏》为刘向上书汉成帝要求停止营造劳民伤财的昌陵的奏章,其中述及民之怨气,曰:“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固流离以十万数……”〔17〕死者、生者因不堪其扰、不堪其苦生发之怨气,必使阴阳失序而有所警示。这固然是所谓天人感应之说,但强调了怨气的巨大感发力量。《列女传·卫姑定姜》认为,“燕燕于飞,差迟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是定姜“恩爱哀思,悲心感动”之作。〔18〕“怨气”“悲心”,是人之“生气”和人心中强烈浓重之力量,这些力量的感动感发,或以阴阳的感应,或诉之于歌咏。“生气感动”“怨气感动”“悲心感动”,实则都是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开启和引动。较之《乐记》“乐者,心之动”、〔19〕“由人心生也”的表述,刘向似更强调人心、人的“生气”不得不发的状态,以及更具力度的怨气、悲心的感动,明显突出了人心“感动”所具有的力量。从“心之动”到“感于哀乐”,正是以具有力度的哀、乐之情作为心之动的代表性力量,这其中,刘向所论思、情、“生气”等的“感动”,更靠近“感于哀乐”之说。
(三)“缘事而发”与《乐记》的“感物说”
“缘事而发”与《乐记》“感物说”存在一定的互通关系。《乐记》认为音乐为人心之动的结果,而人心之动则是“物使之然”,即“感于物而动”。《乐记》开篇反复言“音”“乐”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且分论哀心、乐心、喜心、怒心、敬心、爱心感者所形成的“声”之差异,指出“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20〕认为哀心、乐心等情感并非人心固有恒定之内容,实由感物而生,遵循物→心→声的发生机制,故“物”为诗、乐发生最基本的动因。我们在《汉书·艺文志》中也可发现“感物”之说,《艺文志》曰: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而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21〕
唐代颜师古注曰:“因物动志,则造辞义之端绪。”〔22〕“感物造端”将外境所感视为诗赋创作之发端。同为“感物”,《乐记》“感物而动”是指人心感于物,所论为诗乐发生的心理机制,停留在人心“动”的初始阶段。“感物造端”进一步论及具体的“造辞义”,这就进展至创作阶段了。
“缘事”与“感物”的关系,可从先秦两汉文献中“物”“事”义同的语言现象见出。《礼记·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23〕“物”“事”并举相通。《礼记·哀公问》:“敢问何谓成,孔子对曰:不过于物。”郑玄注曰:“物,犹事也。”孔颖达《疏》曰:“言成身之道,不过误其事。但万事得中,不有过误。”〔24〕《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郑玄注曰:“物,犹事也”。〔25〕《诗·大雅·烝民》“有物有则”,郑玄注曰:“物,事。”〔26〕“物”“事”既相通,“感物”“缘事”亦在一定程度上互通。
物、事虽义同,但“缘事”并不完全同于“感物”。这里引进孔颖达对《乐记》中“感物”的阐释。孔氏释《乐记》所言“物”为“外境”,“乐初所起在于人心之感外境也”。孔《疏》曰:“性本静寂,无此六事。六事之生,由应感外物而动,故云非性也。所以知非性者,今设取一人,以此六事触之,言此人必随触而动,故知非本性也。”〔27〕孔氏将六种心的状态、六种情感状态,也称为六“事”,实以“情”“事”为一体。这里所言的“事”,并非纯粹客观的外境,而是与人发生关联之外境外物。杨柳依依、雨雪霏霏,本为自然时序特征,但在征夫眼中,它们化而为可哀之事,遂生出哀心之情,故杨柳、雨雪等外境,就已进入人心,成为人心映照下之外物了。孔氏所谓“六事”,已附着了人的情志,而“物”“外境”则是更具客观性的存在。从“物”到“事”即以己心迎对外物,将之变为有情之物、有情之事的过程,实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审美体验,“六事”就是审美事件。孔颖达的“六事”之说,以“情”“事”为一体的阐释,对于理解“缘事而发”与“感物说”之间的差异或有助益。如以孔氏“六事”之说观照“缘事”之“事”,此“事”正是社会生活中人心映照过的“人事”。
(四)“缘事而发”与《毛诗》以“事”论风、雅
“缘事而发”的提出是以《诗》为典范的,观风俗、知得失,既是《诗》的社会政治功能,也是《艺文志》所认为的乐府歌谣的价值所在。从汉代《诗》学角度继续寻绎“缘事而发”的生成资源,首先应关注《毛诗大序》。《大序》论风、雅之别,曰:“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28〕一国之事是各诸侯国所在的地方性歌谣,反映一地风俗与政事,此为“风”;天下之事是周王朝统治下的四方之事,反映王朝的政治状况,是为“雅”。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周王室为天下共主,同时诸侯国又享有相当的自治权利,因此就有了天下之事与一国之事。风诗反映各诸侯国、各区域的人情风俗,从《秦风·无衣》中,可以见出秦人尚武、重义的慷慨之气,郑、卫之风则多见其民性民俗中重情、浪漫的一面。但《小雅·采薇》《小雅·出车》等表现的则是“王事”,为周王室征战即天下之事。《小雅·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诸篇,揭示出周王室乱亡征兆,显为天下之事。
“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意为《诗》从表层情节和叙述者来看,皆为一人之事一人之口,叙说的是个体命运和感怀。孔颖达《疏》曰:
“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29〕
作诗者虽只言“一人之心”,实则也是“一国之心”。因这一人之事,实可反映一国之事。比如《卫风·氓》,诗人所言固然为一人被弃之事,并非整个卫国妇女皆被弃,但此一人之事实际上是有代表性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卫地女性的命运,据此可以观察其地风俗,因此也就成为了一国之事。这正是艺术表现中的个别性与一般性的关系。艺术都是“个别”的,而优秀的艺术作品所体现出的社会生活和人类情感的“一般性”也就在这“个别”之中。《诗》以一人之心合于一国之事、天下之心,以一人之事揭示一国之事、天下之事,只有这样才可实现观风察俗、以正得失的政治目的。如孔颖达所言:“必是言当举世之心,动合一国之意,然后得为风、雅,载在乐章。不然,则国史不录其文也。”〔30〕周王朝曾实行王官采诗,各诸侯国也可能有采诗之举,采诗的目的是为观风。什么样的歌谣可能被采集,具有采录价值?孔颖达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能合于一国之意、举世之心的歌谣,具有较为普遍的社会认识价值,这样的歌谣才可能传唱开来。有无一人之心、一人之事不合举世之心的情况?自然有。孔氏例举了这样的史事,周武王推翻暴政,建立周朝,但伯夷、叔齐耻事周武,则不合海内之心;董卓乱汉世而身灭,蔡邕却为之可惜,同样也有悖天下之心。可见一人之心未必能合于天下之心。《风》《雅》则能以一人之心合于天下之心,以一人之事反映天下之事,故可据之观风俗。汉乐府如要实现观风目的,其所缘之“事”固然也是一人之事,但同时也必得合于天下之事、一国之心,“事”之内涵正在此。
当代学人对此亦有认识,王怀义先生认为:
“缘事而发”是指汉诗不是作者本人的凭空创作,而是作者在某些事件的触发之下创作而成。“事”既可是个人之事,也可是集体家国之事。就流传情况看,能被作歌传唱的“事”一般是在某一特定的社会团体中影响较大的事,并引起了民众的共鸣。诗中情感应有代表性和普遍性,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和同情,因而有传唱的必要和可能,也才能流传开来,产生重大的影响,进而被官方采录到。〔31〕
能够表现天下人共情之事的诗,才可能传扬开来,产生社会影响。以“事”论风、雅,以及前面提到的《韩诗序》“劳者歌事”,汉代《诗》学确实体现了“事”在《诗》中的意义。
(五)“缘事”与班固的求实观念
“缘事”这一语词同时出现在班固的《典引·自叙》中,自叙曰:“臣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动有规矩,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32〕“缘事断谊”是指汉明帝根据司马迁作《史记》的具体行事及表现出的观念评判其“非谊士”。在班固看来,“缘事断谊”就是根据事实作出论断。
“缘事”体现出据事实而论的求实观念。《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33〕桓谭《新论·正经》评《春秋三传》云:“《左氏传》遭战国寝废。后百余年,鲁人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34〕这是经学阐释中的“本事”论,要求据事释经。《汉书·河间献王德传》评价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35〕指出刘德为人重视从实际之事中进行正确的判断。《汉书·艺文志》对历史上的杂占现象提出批评,所谓“惑者不稽诸躬,而忌訞之见……”。〔36〕“不稽诸躬”,是说对一些怪现象人们不亲自查验以揭开事实。班固对司马迁及《太史公书》多有批评,但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称赞其书“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7〕故在经学、史学领域,都可见出班固重事求实的观念。
班固的诗、赋批评也体现出这种求实倾向。《离骚序》曰:“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38〕“虚无之语”是指出自传说和幻想的不实之辞。《汉书·地理志》批评楚辞“失巧而少信”,〔39〕“少信”即未能得到事实的充分检验。《汉书·叙传下》评论司马相如赋“文艳用寡,子虚乌有”,〔40〕《典引》“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无实”。〔41〕《东都赋》中虚设的西都宾盛赞东都主人所授之五篇诗曰:“美哉乎斯诗,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42〕提出了典正且合于实事的诗赋理想。班固之后,王符《潜夫论》批评赋颂“竞陈诬罔无然之事”,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论体有六义,其一曰“事信而不诞”,白居易《新乐府序》要求新乐府“其事核”,都是诗赋之学中的重“事”与征实倾向。
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与汉乐府文本“题”“事”关系
上文对“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诗学命题的生成资源从多方面进行探查,讨论了与之接近的诗学表述,对其与刘向诗学、《乐记》、《毛诗大序》等汉代诗学的融通处给予了分析,也注意到了班固其人的求实观念与“缘事”说可能存在的关系。对这一命题的深层意涵可获得如下认识:“感于哀乐”较之“人心之动”,在创作心理机制中更强调人心情感集聚和抒泄的力度;“缘事而发”之“事”具有情、事一体的趋向,更关注人事而非客观外境。较之“感物”说以客观外境作为创作动因,更符合创作实际和审美体验的规律。
“缘事而发”既然是对乐府歌谣的说明,下面就以乐府诗对此命题进行检验。问题集中在:“缘事而发”之“事”是否出现于作品中?对此,袁行霈先生的观点较有影响,他认为:
“缘事而发”常被解释为叙事性,这并不确切。“缘事而发”是指有感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情发为吟咏,是为情造文。“事”触发诗情的契机,诗里可以把这事叙述出来,也可以不把这事叙述出来。“缘事”和“叙事”并不是一回事。〔43〕
按袁先生之说,“事”是触发诗情的契机,诗情才是直接的动因,缘事而发也就是为情造文。这样一来,“事”其实隐在“情”之后,“事”可以不出场,在前台的依然是“情”,这就将“缘事”归并到“言志”的诗学方向上了。为此,必须明了“缘事”并非“叙事”。叙事是要出场的,而缘事只是契机。“缘事”既然是触发诗情的契机,它就依然属于创作的心理动因,而“发”也就还是停留在人心层面。也就是说,“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同属创作动因,二者形成平行并列关系,既因哀乐之情发而为诗,又因触事感怀发而为诗。本文的看法与上述有不同。首先,就叙述逻辑而言,递进型较之并列型更为合理。如果确是针对已有歌谣的特点而论,论者就可能兼顾创作动因与创作形式两方面。其次,《艺文志》另一表述“感物发端”具有“造辞义”的所指,正是对文本实际创作的重视。“缘事而发”近于“感物发端”,这个“发”落实在创作阶段更合适。再次,“缘事而发”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功效中首先提及的是“观风俗”,加之班固本人的求实、征实观念,我们认为,将“缘事”的内涵理解为凭藉事实最为合适。
据此,“感于哀乐”揭示诗情的生发与触动之因,突出人心和情感的强度;“缘事而发”解释诗情落实、据事而作的特点,要求诗、事的实质性合一,以发挥“观风俗,知薄厚”的功能。只有凭藉事实,歌谣歌诗的认识与讽谕功能才能更好地实现。“缘事而发”包含了“触事而作”与“凭事而作”两个意思,可能更倾向于“事”的出场。明清人既然以“叙事”论汉乐府,当然不会无视《艺文志》“缘事而发”的经典表述,所以,他们理解中的“缘事”可能就是“叙事”。当然明清人所言“叙事”不能以今天的叙事观去看待,葛晓音先生将汉乐府的叙事称为“叙事体”,“严格地说,汉乐府没有纯客观的叙事诗,而只有内容客观、语调抒情的叙事体”,“这些诗歌实质上是叙事体的抒情诗,其艺术表现本身就蕴含着转化为抒情体的内在因素,尤其是叙事只截取某一情景或场面集中描绘的方式,直接提供了转化的有力条件。”〔44〕汉乐府的“叙事”确为场景截取,场景中既然有人的行动有时也包括对话,这也就构成了“事”和叙事。
汉乐府有“曲题名”或曰“题名”,题名往往是乐府所缘之事所叙之事浓缩了的信息。从汉乐府曲题名与所缘本事的关系,可对“缘事而发”在实际文本中的丰富表现获得认识。有同一性质的本事发而为若干曲者,所谓“一事多题”。“一事多题”就是“一事多发”,这说明“事”的较大影响和社会传播的广泛性。清人冯班《钝吟杂录·古今乐府论》论“汉人歌谣多歌当时事”,所举作品包括《上留田》《霍家奴》《罗敷行》等,“多歌当时事”既是说触事感怀,也是指作品内容对“事”的直接呈现。《上留田》一曲,据崔豹《古今注》、吴競《乐府古题要解》,是因见有父母死兄不抚养其孤弟的现象,邻人怜之而作,以地名为曲题。此曲今不见全貌,《乐府广题》存数句“里中有啼儿,似类亲父子。回车问啼儿,慷慨不可止”。〔45〕从所存数句推断,歌中必然有孤儿回答身世的内容,而这个内容在汉乐府名篇《孤儿行》中出现了,其中孤儿自述父母死后所受兄嫂驱遣与虐待种种之事。孤儿受盘剥、陷困境之事,在当时的社会必不止一桩,这类事引起时人较大关注故作歌传扬。受虐之事固然是个体的命运,但由于它反映了汉代社会因逐利而亲情丧失的不良风俗和凉薄世态,故其引起的情感能合天下之心。因一类事而发为数题,充分说明了所缘之事的社会影响。《霍家奴》《陌上桑》两题,均为豪强、居高位者对女子行为不端而反遭斥责之事。豪强凌弱必是当时社会的真实之事,至于聪明、贞烈女性的严加斥责,巧加斥责,则可能是作歌作诗者书写出的理想之事。二题也属一类事的多发,所发之事有实有虚。
汉乐府中还存在“数事一题”的现象,即所缘之事为多件,但都集中发于一曲一题中。《鸡鸣》一曲,《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曰:“古词云:‘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中。’初言‘天下方太平,荡子何所之。’次言‘黄金为门,白玉为堂,置酒作倡乐为乐。’终言桃伤而李仆,喻兄弟当相为表里。”〔46〕题解中的初言、次言、终言,已说明内容之间存在断续。“天下方太平”数句有教训荡子勿做不端事,正因有荡子不端之事,才有教训之意,其后明显有更为具体的“事”,但“事”只是一个痕迹,隐于诗后,并未展开。主体内容是描述一门兄弟俱显贵之事,“事”则以奢华的场景描写和围观者的艳羡目光进行呈现。明显存在一个叙事者,他正是那围观者中的一员。最后数句曰:“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以桃李相依现象反衬兄弟相忘。不难推测,这是另一个关于家族中兄弟富贵后相忘的事,这样的事情也引起他人的慨叹。一门显贵事和富贵相忘事是两件不同的事,既然一门俱显,就不存在相忘的情况,故为二事。作歌者目睹一门显贵之事,又联想起听闻的兄弟富贵后相忘之事,这一正一反之事,令其歆羡之时又生慨叹之感。至于“荡子何所之”其后所隐之事则无法纳入到一个合理的叙述框架中。多“事”汇聚于一曲中,造成乐府歌诗的乱章现象,这一现象多是乐工入乐时拼凑导致的。也可能诗中所言三事,各有歌谣传唱,乐工入乐时将其拼合在一起,由于主体部分的富贵之事和其后的兄弟相忘事有一定关联,一从正面一从负面关涉的均为家庭和睦、亲情伦理之事,故此二事即便出自乐工拼凑,也非随意为之。总之,《鸡鸣》一曲述及数事,实为缘数事而发。还要指出,《鸡鸣》的主体情节又出现在《相逢狭路间行》一曲中,形成一事数题。汉代社会中的显贵之事引起时人的艳羡和关注,故以不同曲题传扬之,反映出当时崇尚富贵的社会风气。
“缘事而发”之“事”还有可能“变形”。“变形”最明显的是寓言诗,如《乌生》《枯鱼过河泣》。无疑,两首寓言诗都寄寓着深刻苦痛的人生感触和人生经验。歌诗虽因人世间苦痛事而发,但这些事全部隐在了自然界鱼鸟之事后。实事未出场,代之以角色不同、内核相同的自然之事,从人生事象到自然事象,形成了台前幕后平行的两种事象。而就歌诗感发的力量,鱼鸟之事更令人惊心,形成一种奇崛的悲剧感染力。此外,事之“变形”在汉乐府歌诗中还体现为一定的戏剧化场景。这些场景中的事,固然也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创造了更多戏剧化的不平常情景,如《陌上桑》《妇病行》《上山采蘼芜》等。在这些作品中,“缘事而发”之“本事”和最终呈现在作品中的事并不完全一致。
从汉乐府歌诗文本中,我们看到“缘事而发”在实际作品中的复杂性,也发现了作品与诗学意义上的“缘事而发”的距离。汉乐府之“事”并非全部能够求实,而更可能在实事的基础上作出艺术处理,比如强化事件情节,增加观、听的感染力。汉乐府“事”的种种强化和变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乐府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态它所意欲获得的艺术效果使然,这就使其对“事”之本身进行了种种艺术上的改动。而班固以经典化了的《诗》为标准提出的“缘事而发”,主要目的是为“观风俗,知得失”,以作治理参考,对于乐府付诸表演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可能并不在“缘事而发”这一命题的关切范围内。
三、唐代新乐府“即事”义的变动
汉乐府之后,始于魏晋时代的文人拟乐府出现了新的现象,即摹写题面之意,这种现象至南朝文人乐府诗登峰造极。当运用汉魏乐府旧题创作时,在南朝文人那里,题名成为唯一的依据,“缘事而发”之“事”甚至被彻底抛弃了。这就不是为事而作、为情造文,而是为文而造文了。至此,“事”“情”的创作动因在部分文人拟乐府那里完全被放弃了,由此引起了唐代乐府研究者和创作者的不满。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就是有感于拟作者因对古题、本事不了解或无视,而仅就题面之意生发的现象而作的。但明了古题、本事之后,乐府古题的拟作就应该做到“回归本事”,如此一来,就可能出现陈陈相因的模拟现象。由此,唐人的乐府创作开出了两条新路:一是如大诗人李白那样由于其通“古乐府之学”,故能在古题、本事中翻转腾挪,牵连、融入现实感怀;二则是放弃古题,摆脱古题的束缚,自立新题,写新事、时事,这就是由杜甫开启,而成于元、白的新乐府创作实践。元稹《乐府古题序》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等歌行之作“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即据事立题,出以当下之事和诗人之心,不受古题限制。杜甫的做法在元稹看来是上承了一个优秀的诗歌传统,“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47〕讽兴当时之事,是出于诗歌深度参与现实、讽谕时政的目的。元稹所例举的杜诗,“事”皆为当时军事、政治之大事要事。《悲陈陶》《兵车行》自不必说,即便《丽人行》也通过美丽的游春场景隐射了杨氏一门受宠和跋扈之态,在杜甫看来,这是关乎唐王朝命运的要事,讽兴的意味很清楚。
白居易《新乐府序》对新乐府所述之“事”提出标准,“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白氏作新乐府是预备朝廷采集的,这组诗如同奏章,触及了王朝政治、社会、民风方方面面的问题。既然准备被朝廷采用,所写之事须真实、核实,否则或要陷欺君之罪。事“核”的标准,是以诗代谏章的政治实用目的必然要求。从元、白关于新乐府的阐述来看,二人看待“事”的出发角度其实不全同。元稹从诗歌传统出发,白居易则从功用目的考虑,但其都肯定“事”的真实性和重要性,突出“事”关乎国家社稷、政教治理的讽谕目的。
明清以来诗论家一致以“时事”指论杜诗、元白之新题乐府,形成共识。王世贞认为李白拟古乐府不及杜甫“以时事创新题”;〔48〕胡应麟指出元稹和李绅《新乐府》诸题中的《华原磬》《西凉伎》等篇皆为讽刺时事之作;〔49〕许学夷论杜甫“自立新题,自创己格,自叙时事”;〔50〕王夫之评杜甫《出塞》“三别”“以今事为乐府,以乐府传时事”;〔51〕李畯《诗筏汇说·说诗体》认为“新乐府,皆自制题,大都言时事而中含美刺”。〔52〕“时事”一语更切中事件的当下性、影响性与较为突出的政治色彩,今日所谓“时事政治”一语,正可说明“时事”在人们心目中之性质。
“即事立题”不仅是对杜甫新题乐府的表彰,其意义还在于倡导恢复《诗》、乐府“讽兴当时之事”的传统,为唐代乐府指出方向。这一方向就是反映时政要事,发挥诗之讽谕功能。“即事立题”的提出,固然存在乐府自身演进规律、现实环境激发、元白的从政活动政治理想等多方面原因背景,若从诗学资源的角度考虑,除了“缘事而发”,尤其要注意初唐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多次提出的《诗》“缘政而作”的观点。“缘政而作”将王政得失视为诗人情感生发的重要源头,善政则生颂赞之心,恶政则有怨刺之心,遂将王政善恶与《诗》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缘事而发”与“缘政而作”,所论皆为诗的创作动因,但从“事”到“政”,有收缩之态,诗的指向性更明确。
从汉乐府的“缘事”到唐代新题乐府、新乐府的“即事”,“事”的范围发生一定程度的收缩,从广泛的社会生活与风俗之事聚焦为政治时事。究其原因,还在于班固、元白赋予歌谣歌诗不同功能使然。“缘事而发”可“观风俗,知得失”,故诗中之事为宽广的百姓生活风俗之事。“缘事而发”的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经过乐府的采集、乐人的加工后,固然可能改变了民间歌谣之原初面目,但从《孤儿行》《妇病行》等经典篇目来看,若非亲身经历或目睹,不能想象如此真切的细节之事。民间歌谣更关注实际的生活层面,故“缘事而发”具备真实真切的生活基础,歌谣本身可提供更丰富的生活与风俗场景。唐代新题乐府的创作主体则是从政参政的士大夫文人。杜甫一生实际参政时间很短,但其参政意识一直很强烈,所谓“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而白居易创作新乐府时,对个人的身份意识念念不忘。他们的即事之作,更关注军国、社稷、政教之事,是其所属阶层决定的。白氏《新乐府》五十首不尽是时事之作,也有历史题材,如《李夫人》,诗序言“鉴嬖惑也”,即便咏史,也必卒章显志,将史事的意义引向当代政治和治理,故其诗中之事无论时事还是史事,政治意味均较为浓厚。
“即事立题”本是对杜甫时事歌行的说明,既然“即事立题”,“事”在诗中出场的可能性较大,否则读者就不知缘何立题,由此也就在文本中加强了诗与事的显性关系。白氏《新乐府》不全为“即事立题”之作,有些属“为物”而作,比如《秦吉了》。诗表面描述一种能言之鸟,诗序曰“哀冤民也”,诗末言“岂不见鸡燕之冤苦,吾闻凤凰百鸟主,尔竟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闲言语”,以此将诗所谕之事几近明白地揭示出来,其讽谕指向那些不为民伸张、不将民之冤痛达于天听的官僚自保行为。“物”承托了真正要言说的“事”,“事”虽未正式出场,但其面貌是清晰的。对比前面讨论过的汉乐府寓言诗,如《乌生》一篇,生活中真正的无常之事隐没到了一个表层化的禽鸟之事背后。汉乐府本有不少教训与训诫诗,比如《长歌行》,基本是说理,没有事的痕迹。但《乌生》因有一个事的架构,情感和感慨也就有了附着和依托,由此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情之动人。而且这种生命感慨始终含蕴禽鸟之事中,并未如白诗那样,最终出以论事说理口吻使所谕之事现身。如袁行霈先生所言,汉诗是“为情造文”。“缘事而发”之前首先是“感于哀乐”,故汉诗虽朴质却情韵悠长。白氏《新乐府》实则“为理造文”,要将国家诸事之理阐明,故无论所谕之“事”在诗中正式出现与否,其实“事”与理都是显豁的。“事”服务于“理”,“事”本身的丰富与多义得到强制性规制,因“事”的含蕴空间的缩小,其动人的艺术力量也被削弱。这就是白氏《秦中吟》《新乐府》在当时的流传和影响不及《琵琶行》《长恨歌》的原因吧。由此可见,“缘事而发”而非“缘理而作”,让“事”居于诗之主体地位,这是诗歌情感力量的源泉。
汉诗、杜诗、白诗中“事”的真切可感程度不同,这是作诗者与“事”的不同关系形成的。汉诗作者更像是当事人,处身“事”间,《韩诗序》所谓“饿者歌食,劳者歌事”,人与事的这种切肤关系,赋予事更多的情感特质。杜甫亲历乱离,身遭困境,他既记述个人乱离之事,也观察民众之事,但他做到了如《毛诗大序》所说的“以一人之事系天下之事”,故其诗中之事也可感发读者之心。白居易《新乐府》叙事的目的在于言理,所述之事是一个意欲为大唐提供疗救药方的朝廷参政者眼中之事,政治观察者的身份使其对“事”本身的感知度受到影响。因此,《新乐府》对“事”的叙述是一种他者再叙述,即以特定政治眼光过滤后的事件,“事”的真切度、在场感受度削减。《新乐府》几乎不再有汉乐府歌诗的对话场景,显然,对话场景更具生活原态和事件原初发生的真切感。如何看待事件,决定了事件本身同时也就是诗的真切可感程度。总体来看,事与人的密切关系,事在诗中自主和充分的呈现,这是实现叙事力量的保障。
本文对乐府诗学中的两个“事”义命题的生成和内涵变迁进行了探查和分析。总体来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吸纳了先秦两汉丰富的诗乐观念与话语资源,命题的重要贡献是彰显了“事”与诗之关系,“缘事而发”突出了实际创作阶段和文本层面“事”的地位和意义。这一经典表述在唐代新乐府诗学“即事立题”“为物为事”而作的诗学主张那里得到发扬,但从“缘事”到“即事”,内涵意义有所变化,简言之,从较宽广的现实社会风俗之事聚焦于时政之事,“事”的内涵有所收缩。无论“缘事”还是“即事”,都指向了诗与事之关系,对于古典诗歌中的叙事因素而言,具有诗学上的引领意义。唐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大型咏史乐府数量激增,乐府创作转向历史维度,与乐府诗学上的“缘事”“即事”传统发生偏离。至近代以来,乐府全面参与了近代重大时事和社会现象的记录和书写,乐府“缘事”“即事”的特点在新的意义上得到深化。近代乐府诗在纪实性、写实性和细节性方面,使诗、事关系得到前所未有之提升。清代、近代诗歌的叙事性特征,与乐府的“缘事”“即事”存在一定关系。乐府诗学中的“事”义命题,是对古典诗学和诗歌实践的重要贡献。
注释:
〔1〕《汉书·艺文志》是班固在刘向父子《别录》《七略》的基础上完成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提出与刘向也有一定关系,但班固在这个诗学命题中的贡献应该是主要的,学界一般也将之系于班固名下。
〔2〕〔明〕徐祯卿:《谈艺录》,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69页。
〔3〕转引自张寅彭、黄刚编撰:《唐诗论评类编》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12页。
〔4〕〔清〕冯班:《钝吟杂录》,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0页。
〔5〕〔清〕沈德潜:《古诗源》卷首“例言”,《新世纪万有文库》本,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6〕袁行霈先生指出“缘事”并非“叙事”。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16页。葛晓音先生认为汉乐府的“叙事”实际上是“叙事体”的抒情诗,而非纯客观的叙事诗。参见葛晓音:《论汉乐府叙事诗的发展原因和表现艺术》,《社会科学》1984年第12期。王怀义先生认为能被作歌传唱的“事”一般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性,并能获得共鸣。参见王怀义:《汉诗“缘事而发”的诠释界域与中国诗学传统——对“中国抒情传统观”的一个检讨》,《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7〕参见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08页。
〔8〕参见韩经太:《“在事为诗”申论——对中国早期政治诗学现象的思想文化分析》,《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秋之卷,第96页。
〔9〕有学者指出,刘向、刘歆父子所著《别录》《七略》的基本内容保存在《艺文志》中,“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理论有可能直接来源于刘向。参见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08页。
〔10〕〔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25页。
〔11〕〔清末民初〕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卷七,《十三经清人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09页。
〔12〕有学者认为,《韩诗序》“劳者歌其事”可说明西汉韩婴最早发现古诗的言事传统,本文认为将其提升至这一诗学位置的理由尚不充分。参见殷学明:《诗缘事辨》,《北方论丛》2013年第5期。
〔13〕〔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56页。
〔14〕〔西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5页。按:这一说法与西汉末出现的纬书《乐纬·动声仪》几乎全同,“诗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积,积而后满,满而后作”,二者明显有渊源关系。
〔15〕《说苑校证》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86页。
〔16〕《说苑校证》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3页。
〔17〕《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56页。
〔18〕〔西汉〕刘向:《古列女传》,卷一,张元济等编:《四部丛刊初编》史部0265册,民国十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本,第11页。
〔19〕《说苑校证》卷一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06页。
〔20〕〔27〕《礼记正义》卷三十七,《乐记》第十九,〔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11、3311页。
〔21〕〔22〕〔33〕〔36〕《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第1755、1756、1715、1773页。
〔23〕《礼记正义》卷六十,《大学》第四十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631页。
〔24〕《礼记正义》卷五十,《哀公问》第二十七,〔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499页。
〔25〕《周礼注疏》卷十《大司徒》,〔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523页。
〔26〕《毛诗正义》卷十八,〔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24页。
〔28〕〔29〕〔30〕《毛诗正义》卷一,〔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68、568、568页。
〔31〕王怀义:《汉诗“缘事而发”的诠释界域与中国诗学传统——对“中国抒情传统观”的一个检讨》,《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32〕〔41〕《全后汉文》卷二十六,〔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614、614页。
〔34〕桓谭:《新论》,卷中,《正经》第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6-37页。
〔35〕《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河间献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10页。
〔37〕《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第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38〕《全后汉文》卷二十五,〔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611页。
〔39〕《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8页。
〔40〕《汉书》卷一百,《叙传》第七十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55页。
〔42〕《全后汉文》卷二十四,〔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605页。
〔43〕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16页。
〔44〕葛晓音:《论汉乐府叙事诗的发展原因和表现艺术》,《社会科学》1984年第12期。
〔45〕〔宋〕郭茂倩编撰,聂世美、仓阳卿校:《乐府诗集》卷三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05页。
〔46〕《乐府诗集》卷二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77页。
〔47〕〔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5页。
〔48〕〔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7页。
〔49〕〔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53页。
〔50〕〔明〕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卷十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09页。
〔51〕〔明〕王夫之著、陈叔良校点:《唐诗评选》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6页。
〔52〕转引自张寅彭、黄刚编撰:《唐诗论评类编》上册《各体论·乐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