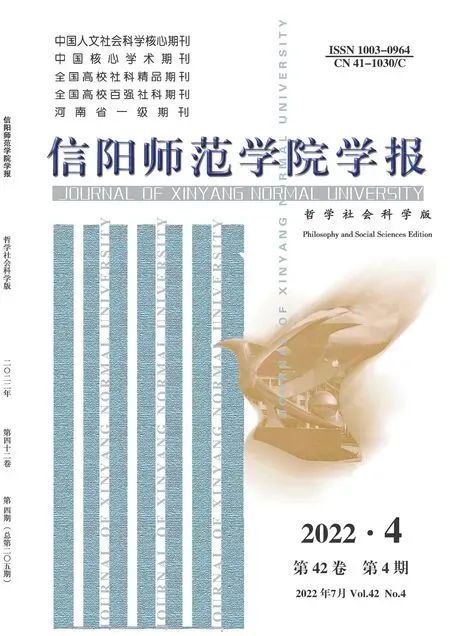明清易代时期的时代焦虑与文学表达
——以《清夜钟》《照世杯》《云仙笑》为中心
王委艳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一、明清易代与话本小说的演变
明清话本小说创作成熟、发展和衰落贯穿整个17世纪,同时又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也就是说,明清话本小说的发展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明清易代之际,对于普通文人来说是一种痛苦选择,这种痛苦并非来自易代本身,因为易代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并不新鲜,或者说国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但明清易代不同,正如梁启超所言:“本来一姓兴亡,在历史上算不得什么一回大事,但这回却和从前有点不同。新朝是‘非我族类’的满洲,而且来得太过突兀,太过侥幸。北京、南京一年之中,唾手而得,抵抗力几等于零。这种刺激,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而自觉的率先表现实在是学者社会。”[1]14作为底层读书人的话本小说作者群体也受到冲击。对于明末乱局和明清易代,话本小说作者采取了不同的行为姿态,这种姿态随着时局危机的加重逐渐靠近时事。明代后期的冯梦龙、凌濛初选择积极作为来维护一个岌岌可危的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跨朝代的李渔早年科考蹭蹬,易代之后对新朝廷采取不合作的玩世态度,游戏人生。处于易代变局中的艾衲居士则以“豆棚”为书场,营造了“官话”之外的“闲话”空间,并对明亡的历史教训进行了全面的反思。而处于明末清初的一些小说如《清夜钟》《云仙笑》《醉醒石》《照世杯》等从不同方面写出了易代之际的时局乱象及世道人心。
明清易代之际,话本小说创作表现出了集体的时代焦虑,其程度随着时局动荡的升级而逐步加深,又随着清廷对时局的掌控,由动荡逐步转变为平静而逐渐变成一种较为低调的表达,由直接的对时局的描写逐步过渡到影射、隐喻为主,从格调方面逐步走向一种无奈甚至逐步接受新朝廷的创作趋势。同时,这些易代之际的话本小说在表现时代焦虑的时候,采用各种方式。有的是以道德倡导为主,如《型世言》;有的揭露易代之际仕宦、士人等的各种丑行,如《豆棚闲话》;有的则直接表达时局之危,如《清夜钟》;有对世象丑恶的烛照,如《照世杯》;还有对下层百姓的悲悯,如《云仙笑》;等等。当然这些作品并非聚焦一端,而是有多方面表现,如《豆棚闲话》既有隐喻,又有对时局的直接描写,同时还揭露了易代之时一些人的种种丑态。而李渔的作品则醉心于隐逸为乐,同时又梦想做人师,为乡野高人。如此种种,无论何种面貌,均呈现了易代之际,作家通过文学的方式传达出的焦虑情绪。这种情绪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从而在各个方面表达了对时局的影射。换句话说,这些易代之际的话本小说,呈现出了不同于此前的面貌,这种新变是易代之际的种种现象在作家作品中的一种投射。这些作品就像各种镜子,无论是平镜、哈哈镜、放大镜、屈光镜还是其他,其映照的是同一个现实,但其效果不同。也就是说,话本小说的发展与时局演变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前期话本小说除了对历史文本的整理改编外,还包括一些紧贴时代的作品,对社会虽有批判但并没有显示出末世焦虑,到《型世言》则表现出强烈的说教,从侧面表现了时代的混乱。到了李渔的作品及《豆棚闲话》《清夜钟》《照世杯》和《云仙笑》等,时代色彩越来越强烈,从而表现了话本小说作者及读者对世事的关心。同时,话本小说的分期也以时代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即明代最后几十年,以历史材料的整理和表达世情为主,代表作品是“三言二拍”等;中期即朝代转换过程中,以李渔《十二楼》和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等为代表,表达易代之际的文人的微妙心态;后期即清初,以《清夜钟》《照世杯》和《云仙笑》为代表,表达了时局的危急和焦虑。因此,可以说话本小说的发展与易代的时局演变具有某种同步色彩,这种同步既是话本小说的价值所在,又为其消亡埋下了伏笔。
下面即以《清夜钟》《照世杯》和《云仙笑》三部小说集为例,来阐述话本小说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关系,并借此讨论话本小说的价值。
二、影射时局:《清夜钟》《照世杯》和《云仙笑》的易代表达
明清易代之际,话本小说不同程度地表达了时代的焦虑情绪,这种情绪或隐或显或明或暗地显示出时代剧变在文学领域的反映。《清夜钟》《照世杯》和《云仙笑》对明清易代之际不同阶层的描写,反映了作家对时局的关切,并以此为观照发现存在于作品中的士人的微妙心理。这种易代心理不是一种个案,而是易代之际身处跨代的士人真实的人生处境。三部作品正是从文学的角度反映了易代之际士人的复杂心态。
1.《清夜钟》的时代焦虑
《清夜钟》是明末清初话本小说,其作者经多位学者考证,似可确定为陆云龙。笔者无意对《清夜钟》的作者问题置喙,更愿意聚焦于小说所表现的时代焦虑上面,并认为《清夜钟》与明清易代之际的其他小说一样,表达了一种易代之际的焦虑情绪,是易代心态的代表性作品。小说取材明末时事,并屡次提及崇祯十七年(1644年)事,当为作者亲历明清鼎革之痛而对之进行的切近时代的描写。
《清夜钟》表达了一种时局艰危、迫在眉睫的焦虑情绪。显然,作品产生的时候正值明朝灭亡的前夜。《清夜钟》的易代心态主要表现在对时代的贴近式描写和文人们的焦虑情绪方面。在序言中,作者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写作目的:“明忠孝之铎,唤醒奸回;振贤哲之铃,惊回顽薄。名之曰《清夜钟》。”并强调:“著觉人意也,大众洗耳,莫只当春风之过,负却一片推敲苦心!”[2]154
首先,贴近时代的描写。贴近时代本身说明时代的特殊性,在明清易代之际,刊刻于这一时间节点的话本小说或多或少有对于时代的贴近式描摹。如《豆棚闲话》第十一则中对明末乱象的描写。明末小说有这种描写时代的传统,如魏忠贤倒台不久就出现《梼杌闲评》这样揭露魏忠贤丑行的小说,其中很多描写的是史实。《清夜钟》多个回目提及明末动乱。第一回“贞臣慷慨杀身 烈妇从容就义”中直接描写了明末的动乱,小说开头即赞扬崇祯皇帝:
若在明朝毅宗烈皇帝,他自信王为天子,不半年,首除崔呈秀,渐去魏忠贤,五彪五虎。这时身边何曾有一个亲信的近臣、才识的大臣去相帮他?真乃天生智、勇、胆、力、识都全,不落柔懦,亦非残忍。后来身衣布素,尽停织造,何等俭;时时平台召对,夜半批发本章,何等勤;京畿蝗旱,素衣布祷,何等敬天恤民;对阁下称先生,元旦下御座相揖,何等尊贤礼下。[2]155
但是,就这么一位好皇帝,却得到吊死煤山的下场,而死的时候“煤山下从死的止一内官”,对于崇祯皇帝,小说寄予了莫大的同情,并对明朝的文臣武将贪赃枉法、贪生怕死、误国误民的种种劣迹进行了揭露,“闯贼还坐在长安,这厢已是如麻似乱”。然后,小说写了编修汪伟为官“公明廉洁”、为人“忠孝节义”。小说揭露了明末官场考选行贿的种种丑行,而汪伟因“宦囊清薄”自然落选。后崇祯亲自考选,汪伟被选为内翰林简讨。后甲申之变,李自成入京,崇祯吊死,汪伟看到迎贼的官民,非常痛心,对夫人道:“夫人,我这哭,不是与你舍不得死,怕死贪生。我是哭谋国无人,把一个三百年相传宗社,十七年宵旰的人君都送在贼手里,这等哭。若论今日,我臣死君,你妻死夫,是人间的正事,人间的快事!什么哭?被人闻知耻笑。”于是,和夫人一起双双悬梁殉国。
小说虽然对李自成农民起义颇多批判,但我们看到这明清易代之际,写下这样的文字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在清初时局艰危、文人生存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刊刻这种明显倾向于明朝的作品,尤其难得。这第一回小说对明末乱象的揭露入木三分,饱含了对于明亡的痛惜与思考。
《清夜钟》第二回“村犊浪占双桥 洁流竟沉二璧”中,首先写任丘、济南、临清等地失守后女性的悲惨命运,正话写了两个童养媳的故事,写她们的孝道,临死时还不让逼迫她们的婆婆出丑,然后作者对她们的品行进行赞扬:
这两人不生仕宦之家,也不晓得读书识字,看他处事,何其婉转;临死,何其勇决!可见天地正气,原自常存,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今天下这些喜淫失节妇人,奈何有好样不肯学?[2]176
《清夜钟》对忠、孝、节、义的宣扬有其直接的现实原因,并将之上升为国家层面,在明清易代的大背景下显然有所指涉。其中多篇有切近时事的议论文字,第一回宣扬忠君,第二回宣扬孝道,第三回写恶奴欺少主的故事,并得到恶报下场。这篇看似写一个家庭的故事,但在小说开头,作者同样将故事上升为国家伦理道德层面:
国家重良贱之条,名分严主仆之辩,盖平日既甘服役,受其衣食,便有休戚与共之义,若富时相事,贫贱弃之,生则相依,殁遂易主,向来抚养之谓何?[3]289
显然,在明清易代,尤其是崇祯殉国之后,对于明臣易主而事的现实,作者是有颇多愤懑之词,借小说进行旁敲侧击。《清夜钟》第四回“少卿痴肠惹祸 相国借题害人”中,则直接写南明弘光朝的乱象,写假太子案,写各色人等为保命,认假为真,为权位弄虚作假等丑态。《清夜钟》第五回“小孝廉再登第 大砚生终报恩”写科场舞弊,李代桃僵,小孝廉被人欺骗失去功名,大砚生利用小孝廉的试卷获得功名,并最终报小孝廉之恩。小说显然对于大砚生的所谓报恩并不买账,而是聚焦于大砚生的所作所为,指出:“我道这大砚台还不足取,我图功名,人也要功名,怎教那人撇自己功名成我功名?况窃一一鹤声句得官,犹是个窃,这是个劫,劫可施之士林乎?”对于窃取功名之人进行揭露和批判。这是有所指的,难怪这回末评中写道:“借事写世情,尽多题外之意。”这无不引人对明末官场乱象的联想。这也是对明朝官场的一种反思,如果联系第一回对变节之臣的批评,就会明白作者的这种反思意味着什么:明朝灭亡其实是自内部开始的。这种思考方式还表现在第六回“侦人片言获伎 圉夫一语得官”对武将误国的描写中。这回故事写王威宁用计破敌,其人虽有缺点,但能够用人从谏、信赏必罚,所以能够破敌立功直至封伯。写这样一个人物显然有所指涉:
但如今为大将的,贪财好色,愎谏蔽贤,还要掠人妻女,怎肯舍自己的美姬与人?圣旨部劄,视如等闲,那个肯听人说话?所以如今用哨探,不过听难民口说,不破的城说破,已失城说不失,说鬼说梦,再没个舍命人,入敌营探个真消息的人。随你大将小将,远远离敌三四百里驻扎。只晓得掘人家埋藏,怕敌兵来,每夜还在人屋上睡,那个敢劝道杀贼?总之上边没这如王威宁样一个大臣,自不能得人的力,成朝廷的功。[2]186
联想到明清易代之际,明朝武将的各种行径,不难体会作者的这种愤懑之情。《清夜钟》第七回写“孝”、第八回写兄弟相残、亲情泯灭,第十三回写阴骘积善、本心不可失,第十四回写贪图功名终致祸端。尤其是第十四回末,作者写道,“官高必险,反不如持瓢荷杖之飘然”,俨然是醒悟之言。对于那些由明入清的明朝旧臣,依附新朝,汲汲功名的人来说,实为劝退之言。
纵观《清夜钟》各篇题旨,忠孝节义、亲情、功名等无不和易代之际的时局相关,而且多个回目直接提及明末时事,如崇祯殉国,甲申之变,任丘、济南等地失守,南明弘光朝乱象等。这是一种贴近时代的写作,显示出作者的易代反思,和对于易代之际种种世相的批判。小说持封建正统立场,反对农民起义,在小说中把农民起义说成是“贼”。“作者能立即将最高统治者的政事写成小说,寓兴亡之恨,并在当时印刷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刻印问世,实在难能可贵,这无疑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4]112。小说有意回避了清朝与明朝之间的战争,这一方面说明作者身处清初有所顾虑,另一方面也说明作者的反思主要从明朝自身寻找灭亡原因。
其次,从小说文体特色方面来说,《清夜钟》的叙述方式已经突破话本小说的文体规范,那种“拟书场叙述格局”已经被大量切近时事的议论打破,大量存在于“三言二拍”的说话人套语,如“且说、话说、看官听说”等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作者的直接议论。这种叙述方式其实已经改变了话本小说“超叙述者—说话人—故事”的双层叙述格局,取而代之的是“叙述者—故事”的叙事格局,这种叙述方式的优点在于作者可以毫无顾忌地直接发表议论,而无须借助说话人之口。
同时,语言文人化,书面化,且并不流畅,貌似急就章。大量议论影响了故事主题的自然呈现。很明显,作者并不想让读者自己去领悟小说的内涵,而是直接站出来表达看法。如果从艺术性角度来说,《清夜钟》并没有多少可取之处,无论从语言、文本形式还是故事内容等方面,均表现得很粗糙。但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特殊时期的小说文本,它给我们留下了特定历史时期文人对时局看法的宝贵资料。如果与《豆棚闲话》进行对比,可以很明显地表现出二者之间的精神联系,再比照李渔《十二楼》《连城璧》等作品,可知,处于朝代鼎革之际的文人的不同表达方式。但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均表现出某种“易代心态”。正统价值观、劝讽、揭露以及无处不在的悲观情绪构成17世纪易代小说的时代风格,正如韩南所说:“17世纪40年代的短篇小说集所具有的这种共同价值观,也就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它在一定程度上渗透于整个传统小说创作中。”[5]311
小说中的大量议论极易招致研究者批评,欧阳代发认为:“作者痛惜明代灭亡,大力褒忠奖孝,呼唤重振纲常,以救末世,因而文中有长篇忠孝说教和痛心疾首的哀叹。但说教多,令人生厌。而且其说教既枯燥又陈腐……”[6]331就文体特色来说,议论是话本小说文体的特征之一,从“三言”始,小说中掺杂议论,头回即点明小说主题,故事展开中的议论穿插、结尾处再议论等都是话本小说文体的一部分,但话本小说发展前期的“三言二拍”,并没有将议论作为小说的主要部分,或者其议论文字甚至和小说故事自然呈现的内涵相背离。而处于17世纪40年代的易代小说则将议论上升为小说的主要部分,甚至可以与故事分庭抗礼,这无疑是这个时代小说所表现出的独有特征。议论虽然延续了话本小说的文体规范,但刻意地强调和突出实际上打破了这种规范。这有话本小说的文体惯性,但更多是来自时代对人心理的投射。从议论本身来看,既有宣扬忠孝节义等儒家思想,又有针对时局而发的一些看法,甚至是对当权者的某种劝诫或建议。这些议论在时代危机之下,是作家焦灼心理在创作中的一种投射,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情景中的一种心理表达。正如《毛诗序》所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7]13因此,17世纪40年代小说家没有话本小说前期作家的淡定和从容。
2.《照世杯》:烛照世相
《照世杯》作者酌元亭主人,为明末清初人,小说的刊刻时间,欧阳代发认为是康熙朝,且在康熙九年(1670年)之前[6]407。“照世杯”之名,根据195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照世杯》“出版说明”:“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一云‘撒马尔罕在西边,其国有照世杯,光明洞达,照之可知世事。’为本书书名所本。”[8]1由此可见,此书写作目的:烛照世相。在小说的“序”中,以对话的形式表明写作初衷:
客有语酌元主人者曰:“古人立德立言慎矣哉,胡为而不著藏名山,待后世之书,乃为此游戏神通也。”今曰:“唯唯,否否。东方朔善恢谐,庄子所言皆怪诞,夫亦托物见志也。与尝见先生长者,正襟敛容而谈,往往有目之为学究,病其迂腐,相率而去者矣。即或受教,亦不终日听之。且听之而欲卧,所谓正言不足悦耳,喻言之可也。今冬,过西子湖头,与紫阳道人、睡乡祭酒纵谈今古,各出其著述,无非忧悯世道,借三寸管为大千世界说法。昔有人听妇姑夜语,遂归而悟奕,岂通言儆俗,不足当午夜之钟,高僧之棒,屋漏之电光耶!且小说者,史之余也。采闾巷之故事,绘一时之人情,妍媸不爽其报,善恶直剖其隐,使天下败行越检之子,惴惴然侧目而视,曰:“海内尚有若辈,存好恶之公,操是非之笔,盍其改志变虑,以无贻身后辱。是则酌元主人之素心也哉!抑即紫阳道人、睡乡祭酒之素心焉耳!”[8]105
“托物见志”“借三寸管为大千世界说法”“善恶直剖其隐”等无不说明《照世杯》的写作目的。其书名“照世杯”也有烛照世事之意。“透过全书,我们不仅可以烛照话本小说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的历史轮廓,而且还能窥探到小说所展现的那幅封建末世社会世俗生活的画卷”[9]1159。《照世杯》并没有像《清夜钟》那样聚焦于影响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而是聚焦于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揭露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各色人等的丑陋行径,以烛照世道人心。
在《照世杯》第一篇“七松园弄假成真”中,叙述了才子阮江兰追求扬州名妓畹娘,其中多有曲折,受到友人张少伯帮助,并最终发奋读书考取功名,同时又抱得美人归的故事。故事之中塑造了一位胸无点墨、还假装斯文的假才子乐多闻形象作为衬托。该小说属才子佳人类型,没有脱离中举团圆窠臼。小说不时对一些世事进行冷嘲热讽,如看到佳人配白丁,写道:“天公不肯以全福予人,隔世若投人身,该投在富贵之家,平平常常,学那享痴福的白丁,再不可做今世失时落魄的才子了。”这个故事本身并无独特之处,但其叙述曲折婉转,人物性格鲜明,阮江兰的痴情多才、乐多闻的小人行为、张少伯的智慧与对朋友的热心肠跃然纸上。但最令人称道的是小说中阮江兰中举之后,其家人在其与名妓畹娘的婚姻问题上所持的态度,这让人想起杜十娘。杜十娘的悲剧源于李甲的软弱,但最终原因则是李甲父亲对其婚姻的态度:不会接受他把一个风尘女子娶回家。而阮江兰的父母则是另一种态度,即要求孩子遵守诺言:
父母道:“孩儿你倒忘记了?当初在扬州时候,曾与一个畹娘订终身之约么?”阮江兰变色道:“这话提他则甚!”父母道:“孩儿,你这件事负不得心,张少伯特特送他来与你成亲,岂可以一旦富贵遂改前言?”[8]23
很明显,这里没有什么门当户对和封建的贞洁观念,有的是劝孩子遵守诺言的诚信之心。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价值倾向。抛开门户之见和长久以来的贞洁枷锁,让我们看到一对开明父母对诺言的信奉和坚守。这是不是可以看作作者对封建正统思想所坚守的儒家道德伦理产生了厌恶,并转而相信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信诺并进行坚守。
在《照世杯》第二篇“百和坊将无作有”中塑造了一个童生欧滁山,冒充才子招摇撞骗而得到700两银子,又由于其贪财好色而被另一拨骗子以美色诱之并最终人财两空,最后病死。小说显然对现实中的沽名钓誉之徒进行无情嘲讽。正如小说开头议论:
丈夫生在世上,伟然七尺,该在骨头上磨炼出人品,心肝上呕吐出文章,胼胝上挣扎出财帛。若人品不在骨头上磨炼,便是庸流;文章不在心肝上呕吐,便是浮论;帛不在胼胝上挣扎,便是虚花。且莫提起人品、文章,只说那财帛一件,今人立地就想祖基父业,成人就想子禄妻财。我道这妄想心肠,虽有如来转世,说得天花乱坠,也不能斩绝世界上这一点病根。[8]27
显然,作者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例如,对打秋风这种风气及其所带来的种种丑陋世相的揭露。小说中欧滁山到出贡朋友姜天淳那里打秋风,将自己童生的身份掩盖,冒充秀才招摇撞骗,靠走“衙门线索”获利。作者对打秋风丑行进行无情抨击:
世上尊其名曰:“游客”。我道游者流也,客者民也,虽内中贤愚不等,但抽丰一途,最好纳污藏垢,假秀才、假名士、假乡绅、假公子、假书贴,光棍作为,无所不至。今日流在这里,明日流在那里,扰害地方,侵渔官府,见面时称功颂德,背地里捏禁拿讹。游道至今大坏,半坏于此辈流民,倒把真正豪杰、韵士、山人、词客的车辙,一例都行不通了。歉的带坏好的,怪不得当事们见了游客一张拜帖,攒着眉,跌着脚,如生人遇着勾死鬼一般害怕。
明代官场的这种不正之风显然败坏了社会风气,小说中的议论揭示了这种风气带来的危害,使那些真正的“豪杰、韵士、山人、词客”无法生存。打秋风不但败坏了官场风气、士林风气,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它使得一些不学无术之辈靠招摇撞骗获取名利。
《照世杯》第三篇“走安南玉马换猩绒”塑造了一个类似《水浒传》中高衙内的人物形象——胡衙内。胡衙内贪色成性,以汗巾裹玉马掷杜景山妻子以调戏,不料反而自己倒霉。胡衙内之父胡安抚为了儿子公报私仇,强迫杜景山交三十丈猩猩绒,但猩猩绒是官府禁品,加之生产于安南国,并不易得。杜景山被迫去安南国采购猩猩绒。经过一番离奇经历,终于用玉马换取40丈猩猩绒,同时又附带做香料生意而成富家。而那胡衙内贼心不死,又在家中调戏丫鬟被误打,丫鬟被吊打致死,衙内整日梦见丫鬟索命,遂致病,而呜呼哀哉!小说虽然以杜景山发家致富收场,但描写了胡安抚、胡衙内等为非作歹、欺压良善、公报私仇的邪恶嘴脸,揭露了官场的黑暗。同时,也描写了普通商人的诚信、相互救助等故事。古代以“士农工商”来划分社会等级,小说将官僚的丑恶和商人的诚信帮扶进行对比描写,尤其是胡安抚下面的各级官吏对胡安抚及胡衙内唯唯诺诺,趋炎附势,从而构成了一个地方官僚体系的基本生态。所谓世道险恶,其实是乱自上作。
《照世杯》第四篇“掘新坑悭鬼成财主”是一篇难得的讽刺佳作。小说写了一位吝啬、守财奴式的乡下人物穆太公,有生意头脑,见乡间没有坑厕,便掘三个大坑,然后装饰一番,请镇上训蒙先生写一匾额,名曰“齿爵堂”,还请训蒙先生写广告,结果“生意”兴隆。穆太公靠卖粪便发家致富。其子穆文光受其赌徒娘舅引诱学习赌博,后几个赌徒算计穆太公500两银子,而穆文光由于学习赌技,深得其法,赢回银子,并持刀为父报仇,但又被现任知县“爱才”免罪,录为门徒,后读书进学成书香之家。本篇语言幽默、讽刺犀利,对穆太公吝啬守财而不乏商人的精明、赌徒势利、知县随意断案等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活画出世相百态。
纵观《照世杯》4篇小说,其实写了两方面内容:士林和商人。前者不乏真正的才子,但更多是沽名钓誉、坑蒙拐骗之徒;后者有精明的商人如杜景山,也有精明而守财的穆太公。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反面人物形象,如沽名钓誉的乐多闻、假冒名士秀才坑蒙拐骗的欧滁山、贪色恶少胡衙内、开“马吊学馆”专门教人赌博的吊师等。当然,《照世杯》还塑造了一系列正面角色,比如,有真才实学的才子阮江兰;有古道热肠,为朋友解危济困的义士张少伯;有热心助人的朱春辉等。“《照世杯》揭露官场,描绘世相,虽能洞照幽微,却不能深入,较为浅露。不仅罗列现象,挖掘不深,而且作者似乎还是故意回避冲淡”[6]409。但这种有意地“冲淡”矛盾冲突,难说不是作者用以“自保”的一种方式,“《照世杯》确实像一只光明洞达、烛见幽微地揭示社会人情百态的镜子。可是,也要看到小说对社会弊端的剖析、官场黑暗的鞭笞、世相人生的透视虽很独到,却不能尽兴尽致。不过它使人感到并非出自作者见识和才能的限制,而是作者的有意为之,点到为止。这或许是作者运用的一种回避麻烦的护身术吧?”[10]23虽然如此,但《照世杯》通过曲折的故事和精巧的构思,“采闾巷之故事,绘一时之人情”,以短篇小说塑造较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的确难得。因此,有论者给予较高评价:“《照世杯》文笔流畅,反映时风世态颇为真切。如对老童生欧阳醉、土财主穆太公心理的刻画,文辞峭拔冷峻,夸张而不失其真,谐谑但未坠入恶趣,如此描摹世情,在清初拟话本中还不多见。这对后来的讽刺小说乃至谴责小说,都有影响”[11]76。
值得注意的是《照世杯》4篇小说,只有一篇明确提及朝代,即第二篇“百和坊将无作有”,提及“且说明朝叔季年间……”这与《清夜钟》明确的时代标记以及话本小说对时间的精确记述有明显不同。但这唯一明确提到的时间标记说明故事大致发生的年代背景,所谓“叔季年间”,即末世。而其他篇目则采取暗示方式,如第一篇开始没有交代具体朝代,但在文中,则有暗示,即阮江兰进京应试,“带领焦绿上京应试。刚刚到得应天府,次日便进头场”。说明京城是应天府,应该也是明代。其他篇目只有通过官员称谓或者其他方式获得信息。在文网渐密的清朝初年,这种有意回避具体朝代的做法,的确情有可原。这种做法本身也是在表明一种立场。
除了上述烛照世相的描写之外,《照世杯》另一个重要的成就在于其语言。小说语言流畅且极富张力,与《清夜钟》形成明显对比,《清夜钟》语言佶屈聱牙,难以卒读,而《照世杯》的语言非常具有活力,如第一篇“七松园弄假成真”中对阮江兰天分的描写:
原来有意思的才人,再不肯留心举业。那知天公赋他的才分宁有多少,若将一分才用在诗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精神;若将一分才用在画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火候;若将一分才用在宾朋应酬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工夫。[8]21
连用“若将……”排比句来写才人,并同时有弦外之音。
第二篇“百和坊将无作有”对老童生欧滁山的描写:
但年近三十,在场外夸得口,在场内藏不得拙,那摘不尽的髭髯,渐渐连腮搭鬓,缩不小的身体,渐渐伟质魁形。[8]25
这段描写活画出一个老童生的形象,语言幽默,讽刺辛辣。
《照世杯》语言流畅,文笔犀利,最为人称道处是语言蕴含的讽刺意味,这与小说描摹世相构成极佳的契合,加之小说叙事曲折,引人入胜,这在易代之际的话本小说中,是不可多得的优秀之作。
3.《云仙啸》:下层人的悲辛
《云仙笑》又题《云仙啸》,清初天花主人编次,共“5册”,为5篇小说。小说集编著时间,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云“清初刊本”[12]639。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云仙笑》“校后记”对于编著时间考证较为详细:
这部小说集的编著时间,可能在清顺治三年以后,康熙十二年以前,二十八年间。因为第三册描述到都仁、都义参与清兵征福建,叙功擢用。唐王在福建被杀是在顺治三年,所以这部小说集不会早于顺治三年问世。第三册又称吴三桂为吴平西。吴三桂反清后,被视为逆藩,称作吴逆,编著者绝不敢再使用平西王官称,所以这部小说集的撰写和刊行,不会在吴三桂开始造反的康熙十二年之后。[13]97
《云仙啸》第一册“拙书生礼斗登高第”是一篇主题超出作者预期的颇耐玩味的叙事文本。小说写一个天分不高的书生吕文栋如何通过一系列机缘巧合获得功名的故事。吕文栋论才学,不及同窗学友曾修、曾杰同胞兄弟。小说中这样描述吕文栋才学:“独有资性,却是愚钝不过。莫说作文不能够成篇,若念起书来,也有许多期期艾艾的光景。”因此,是一个“拙书生”。吕文栋的每次应试成功均是机缘巧合:第一次县试,进场之前买了糕果,而那包裹糕点的纸上抄写的一篇文章,恰恰是考试的第一道题目,而他本人恰恰把这篇文章“暗暗记在心上”;考试的第二题“又是平日读过几篇文字的”,因此这次考试竟然取得第5名。吕文栋善于“藏拙”:不参与文社、不拜门生、不应小试,从而成功避开平时的应酬,使得外人很难知道其底细。吕文栋自知才拙,竟不敢参加科举考试,后在其准丈人卜升资助打点下才参加遗才考试,而其考题恰恰是曾杰想要戏耍他的题目,阴差阳错又一次高中第一名解元。吕文栋上京会试,恰好与一个名叫纪钟的书生住在同一个寓所,而纪钟得到了会场房师的考题恰好被吕文栋看见,结果吕文栋中了进士,又殿试二甲。而才分高的曾杰、曾修兄弟却屡试不中,后曾杰病死,曾修虽中解元,但会试不第,选无锡知县,又得罪上司被罢官。小说写了明代士林的种种丑行,如靠夤缘进学、靠贿赂获取考题、文社徒有虚名、拜门生只为找个护身符而与学问无关等。作者将吕文栋的成功归结于命相八字、归结于“善心”。小说看似对吕文栋的成功进行肯定,对真正才子曾杰、曾修兄弟进行批评,但小说自身的主题却走向了另一面,即小说对明代科举考试中各级考试中种种丑行的暴露,对明代科举打压真才实学的客观揭露。小说自身所呈现的主题与作者所宣扬的命相八字、善心形成了背离。“作者把这一切归之于命中注定,‘天公’对‘守拙’‘诚实’人的照顾。作者把吕文栋礼拜斗母的迷信行为,视为应有的虔诚;把一个愚昧无知,言行不ー,凭借夤缘,行为鬼祟而仕途如意的人,作为正面人物加以歌颂,实际是提倡迷信、钻营、希图侥幸,这明显地反映了作者思想的混乱”[13]101。
《云仙啸》第二册“裴节女完节全夫妇”是一篇揭露明代税赋沉重的小说,在头回部分,写了官府催逼官粮,致使农家卖儿还债的故事。正话则写了一个秀才之子李季侯因官府催逼官粮,不得已听从开果子店的陶三建议,卖妻渡难关。小说塑造了李季侯懦弱无能又极力维护陈腐伦理观念的形象。作为对比,李季侯之妻裴氏却是一个有情有义、有智慧、有操守的女性。她为了不使丈夫李季侯在卖掉她之后伤心,假装高兴,使李季侯认为她水性杨花,为了达到自己的不便明言的目的,裴氏让丈夫答应三件事:一是须卖与50余岁的人;二是要有儿女;三是要一两卖自己的银子。此为裴氏为日后谋划:前两件为守节,后一件为赎身。等到裴氏用那一两银子做本钱绩麻卖钱,3年得十三四两银子,然后找现任丈夫赎身。裴氏在谋划整个过程中,有勇有谋,与李季侯的懦弱无能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当知道李季侯已经续娶,然后毅然出家。小说揭露官府税负猛于虎的社会现实,即使有5亩薄田的秀才之家也不得不卖妻偿债。同时也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有勇有谋的女性形象。
《云仙啸》第三册“都家郎女妆奸淫妇”叙述崇祯年间,开绸铺的平子芳,其母亡故,其父平云峰续娶丁氏,平云峰好色伤身,不上一年亡故。而丁氏年轻,与富家子弟都士美勾搭成奸,后被平子芳发现。丁氏与都士美雇都仁、都义谋害平子芳未遂。后丁氏与都士美躲避起义军被发现后,被起义军杀掉。平子芳历经磨难,后终于夫妻团聚。小说写明末乱象,写了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写了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明遗臣南京立弘光帝。小说写了明朝在起义军面前不堪一击的状况,“只因太平日久,不惟兵卒一时纠集不来,就是枪刀器械,大半换糖吃了。总有一两件,已是坏而不堪的。所以一遇战斗,没一个不胆寒起来。那些官府,收拾逃命的,就算个忠臣了。还有献城纳降,做到了□寇的向导,里应外合,以图一时富贵,却也不少”[13]45。揭露了明朝政府不堪一击的败象。
《云仙啸》第四册“一碗饭报德胜千金”正面描写了元顺帝时期,皇帝无道,天下饥荒,水旱蝗疫,民不聊生。穷秀才曾珙自幼父母双亡,又无妻室,与一老仆相依度日。不料老仆得瘟疫病死,曾珙无钱葬送。只得典当衣服、单被,后遇到卖水的刘黑三帮助。后来曾珙因饥饿倒在雪地,又被刘黑三救起,并将讨来的饭让他吃,得以保命。曾珙后来被起义领袖刘福通请去做了参谋,曾珙带兵救了被官府抓起来的刘黑三,报了一饭之德。小说正面描写了元代刘福通起义,写了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这种状况与明末有相似之处,无不引起读者的联想。
《云仙啸》第五册“张昌伯厚德免奇冤”,写了开布店的富翁张昌伯夜遇入室盗贼,不但不予责罚,还与他酒食。此人名叫朱恩,因无钱赡养老母,不得已做下偷盗勾当,得到张昌伯厚待之后,遂决心不再做偷盗之事了。后来,有个光棍刁星专事诈人钱财。张昌伯家一个70余岁饭婆子病故,刁星撺掇卖鸡的虞信之假装饭婆子的侄子,欲讹张昌伯钱财,后被识破,遂又让虞信之到张昌伯门首假装上吊,不料弄假成真。虞信之吊死恰巧让朱恩看见,为报答张昌伯之恩,朱恩将虞信之尸体移走丢弃到河中。后来朱恩发现死者竟然是自家表兄。刁星了解情况,要朱恩将张昌伯告到官府,朱恩念及张昌伯恩情,将事实告诉张昌伯,后又得到公济的帮助,将刁星罪行告之官府使其得到惩罚。张昌伯因自己的厚德而避免被冤枉。小说写了救人危困的张昌伯、知恩图报的朱恩、贪财丢命的虞信之和诈人钱财最终被法办的刁星。值得关注的是,虞信之虽然贪财,但也情有可原,即官府追比钱粮,其五六亩田尚不够纳粮,他不得已卖鸡凑纳。揭露了官府催逼、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云仙啸》通过5篇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下层人的形象,他们的悲惨命运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比如,虽然有才但屡试不第的曾修、曾杰兄弟,被官粮催逼卖妻的李季侯,经历农民起义、清兵入关、明清鼎革的、命运多舛的平子芳,加入起义军的曾珙,济人危困的张昌伯,以及知恩图报的朱恩等。小说除第四册故事发生在元代,其余均发生在明代。这在本书刊刻的清初很容易引起联想。清初的政治环境自然不允许作者有太明显的对明代反思表达,但通过阅读整部小说,不难理解作品从士林乱象、官府税赋、农民起义等多方面对明代灭亡进行反思。尤其是提到官兵在起义军面前不堪一击的情形,以及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等,无不使人对明代灭亡的原因进行思考。《云仙啸》写了下层人的悲辛,以及造成他们悲惨命运的原因。这无疑对于明清易代时局的一种影射。
三、《清夜钟》《照世杯》和《云仙笑》等明清易代话本小说的价值
在西方, “17世纪”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这一世纪由于遍布全球的气候异常直接影响世界各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西方学术界直接以“17世纪危机”进行概括,并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进行研究。“17世纪危机”主要“表现为经济衰退、人口减少、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等等”[14]1。这些表现也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作为话本小说末期重要的作品,《清夜钟》《照世杯》和《云仙笑》更加集中反映了17世纪中国的各种矛盾,使其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史价值。
首先是时代价值。话本小说作为贯穿整个17世纪的重要小说类型,从其产生开始就与时代紧密联系,在内容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性。 《清夜钟》《照世杯》和《云仙笑》从不同侧面描绘了明清易代之际的时代焦虑,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不同的角色在末世的背景下,显示出躁动不安的时代情绪。这些作品正是鼎革之际时代情绪在文学上的表现。如《清夜钟》多个回目写了明代统治阶层在面临国家危局的时刻表现出的自私、冷漠、混乱等时代乱象,这种乱象不但表现在每个人的言行方面,而且从整个统治集团的价值基础——忠孝节义等儒家价值规范方面描绘了其崩塌情形。这就从国家价值观根基方面反思了明亡的历史教训。《照世杯》则从士林、官匪、商业等方面表现了处于社会中的各色人等的普通生活。士林阶层的沽名钓誉、官员的横征暴敛和公报私仇、衙内的贪财好色、社会中各色人等的趋炎附势等,社会生活充满各种污垢杂碎。很难想象,这样的社会还会有什么希望?《云仙笑》则写下层社会,书生、农民、起义者、小商贩、地痞、流浪汉等,并正面写了农民起义和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将上述作品联系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其共同组成了整个明代社会的末世乱象。共同作为一种易代之际的文学表达而对明末世相进行影射。是明清易代心态的重要表现。同时,这些作品虽写到易代之际的动乱,但一般只写农民起义,而对清军入关、杀戮等三缄其口。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作者的遗民身份和对清廷的顾虑,这本身也表明了易代之际的焦虑心态。
其次是思想价值。话本小说的思想并非统一,而是一个多元的思想文本。这反映了明末清初中国主流思想的崩塌和多元思想的崛起。从阳明心学开始,明代的哲学思想就开始裂变,到顾炎武、王夫之,中国哲学思想开始回归人本体,个人价值、个人欲望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表现在小说领域,我们发现话本小说的思想充满矛盾,主要表现在对儒家伦理思想的怀疑,就是说虽然很多篇小说表现出对儒家伦理的遵从,但是还有一些篇目则表现了另一种声音。有时候,在一篇之中,竟有两种不同声音。随着话本小说的发展和时局的恶性变化,这种异质声音越来越成为小说的主流声音。在话本小说发展的末期,以《清夜钟》《照世杯》和《云仙笑》等文本为代表,对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伦理观念的怀疑更甚。无论《清夜钟》里对忠孝节义的种种议论及乱局之中人的各种表现,无不表达一种怀疑与期望重建的心理;《照世杯》中对贞洁观念的理解与思考、对明末社会乱象的批判、对官场祸国殃民的揭露及对经商的肯定等,无不在思想层面突破了封建思想束缚;《云仙笑》则从下层人角度揭露易代之际普通民众遭受的种种磨难,显示出难能可贵的民本思想。
再次,文学史价值。按照事物产生、发展、成熟、衰落的基本规律,话本小说也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就短篇话本小说来说,宋代的《醉翁谈录》记载了大量的小说名目,同时有一部分故事情节完整的话本小说,这类小说故事描写较为简单,有“说话”套语,但并不固定为一种模式。这些小说文本形制并不统一,语言文白掺杂,篇幅长短不一,而且一些篇目类似笔记小说。到《清平山堂话本》,在故事情节、描写以及文本套路方面更加完备,如有入话诗词、头回,篇中夹杂说话人套语和诗词,篇末有结尾诗词等。也就是说,到《清平山堂话本》,短篇话本小说的基本文本形式已经非常完备了。明代冯梦龙编创“三言”,严格规范了短篇话本小说的写作套路,使话本小说的“说话体”文体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并影响了17世纪话本小说的创作。也就是说,17世纪是短篇话本小说发展成熟时期。17世纪末话本小说的衰落,其原因多方面,但主要原因还是来自清廷的查禁。换句话说,话本小说的衰落原因并非来自话本小说自身,而是外力使然。以《清夜钟》《照世杯》和《云仙笑》为代表的末期话本小说由于其在贴近时代、表达焦虑,思想激进、表现出对儒家道德秩序的怀疑等内容恰恰为清廷封禁提供了借口:封禁这些统治者所惧怕的文学作品恰恰是这些文学文本的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清夜钟》《照世杯》和《云仙笑》等明清易代之际的话本小说的价值绝非上述三点所能概括完全,但至少说明这些产生于明末清初的易代小说作品,无论从文本的仓促成篇还是从其表达内容等方面都应当引起学界重视,其价值也应深入挖掘。
四、结语
话本小说在古代白话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在于,确定了古代短篇白话小说的写作方式,丰富了“说话体”小说的表现力。一种小说类型的成熟不但要靠长篇小说的成熟,同时还要靠短篇、中篇小说的成熟。也就是说,正因为话本小说确立了古代中短篇白话“说话体”小说的文体规范,才使得古代白话小说成为一个具备长、中、短三种形式的成熟的小说类型。17世纪话本小说的发展史与纷乱时局的演变具有某种同步关系,其取材、思想内容、价值取向等所传达的时代情绪无不显示其存在的价值所在。《清夜钟》《照世杯》和《云仙笑》等集中表达了话本小说发展末期的时代性和思想性,从而使其成为无可取代的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小说作品。对于这一点,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