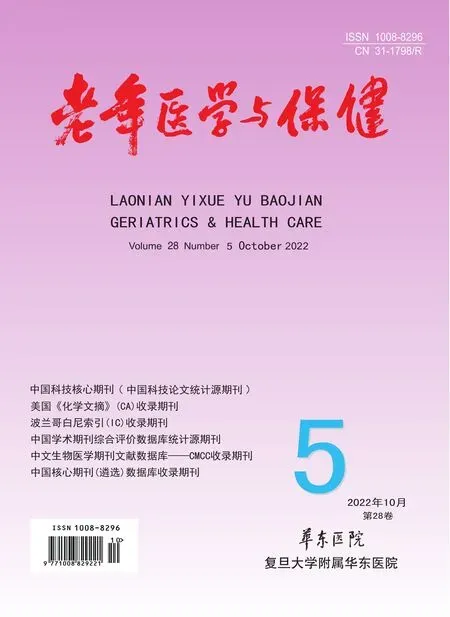关注社区老年人群抑郁障碍问题
黄延焱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全科医学科,上海 200040
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又称抑郁障碍,是多因素相互作用引起的疾病,是一种以多种行为和情绪症状为特征的情绪障碍,如情绪低落、兴趣降低、精神亢奋或嗜睡、悲观、失眠、食欲减退、思维迟缓,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和行为等。
中华医学会对“老年人”的定义是:60 岁及以上人群。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老年精神医学组2017年发表在《中华精神科杂志》上的《老年期抑郁障碍诊疗专家共识》[1]上确认对老年期抑郁障碍(late life depression,LLD)的概念为:年龄60 岁及以上人群中出现的抑郁障碍。
LLD 是老年人群中一种较常见的精神障碍,而全球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使老年人将从现在的12%上升至2050年的22%,意味着老年人面临着身体和精神卫生两方面的特定挑战。世界卫生组织(WHO)2017年的报告显示超过20%的老年人患有精神或者神经障碍(不包括头痛疾病),老年人出现的所有残疾(残疾调整生命年)中,有6.6%归咎于神经和精神障碍。这些老年性健康障碍导致了17.4%的伤残损失健康生命年[2]。这一年龄组最常见的神经精神障碍是认知障碍和MDD。MDD 可对患者本人造成很大痛苦,并会影响到其本人及家属的日常活动。目前国内外的社区初级保健场景中,MDD 既存在诊断不足,又存在治疗不充分的情况。LLD 易被忽视,因为这些症状与老年人所患的其他慢性疾病或者健康问题并存,所以常得不到有效的诊治。2009年费立鹏教授等[3]对中国四省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时发现我国LLD 的患病率为10.56%。一项调查显示,2017年我国MDD 总患病率从1990年的3.23%上升到3.99%,患病率在5~54 岁的人群中是不高的,但在55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中却出现上升趋势[4]。2017年刘宏军等学者对北京地区LLD 筛查检出率为7.7%[5];2019年下半年黄延焱等在上海闵行区四个街道启动的针对2 500 余位老年居民的问卷及入室筛查发现LLD 的发生率为13.38%。上述研究均为新冠疫情前筛查的结果,Covid-19 带来的居家隔离、就诊手续的增加、子女探望受限等多种因素对LLD 的发生率及情绪的长期改变会带来何种影响还有待后期的研究。随着老年人群心理问题及精神疾病发生率的增加,LLD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对于LLD 有效干预的前提是及早及有效的筛查与识别抑郁症状,但目前我国基层卫生机构中对MDD 的识别率低,有效治疗和管理水平仍欠缺和不足,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患者无法得到及时诊断和有效干预。
LLD 的病因和影响因素很多。目前国内外绝大多数学者及文献报道认为其发生发展与老年人的社会环境因素、躯体健康状况、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等方面相关[6,7]。欧洲的一项大型研究调查了来自欧洲6个不同国家的38 434 名男性与40 024 名女性,在调整了工作薪酬和躯体不适等影响因素后,发现女性的抑郁症状表现及程度均高于男性[8]。老年期常见的负性生活事件包括离退休、丧偶、家庭矛盾、自身患病等;这些不仅可以促进抑郁情绪的发生,还能影响MDD 的预后[12]。目前有学者认为丧偶或者亲人离世等应激事件产生的短时期内(症状持续不足2 个月)的悲伤和情绪低落状态(居丧反应)并不属于情感性障碍,应当归于适应障碍,但DSM-5 已将时间低于2个月这一排除标准移除,希望是确保符合抑郁症状诊断标准的居丧患者不要被耽误诊治[9]。Brown 等[10]学者发现,有超过90%的老年人在MDD 出现之前经历了负性生活事件,且提出了“应激-易感模式”,认为易感因素和负性生活事件相互影响可导致抑郁的发生。经济收入是代表社会经济地位的最好指标,低经济收入会让老年人承受较大压力,产生慢性应激状态而导致抑郁的发生。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可忽视。社会支持是个人与社会其他个体或社团组织之间的物质或精神上的联系,包括婚姻状况、居住情况、社会参与程度等。Djernes[11]在一篇系统综述中发现缺乏或失去社会交往是LLD 的主要预测指标之一,同时躯体健康状况尤其是慢性疾病与MDD 存在着相关性。在对上海闵行区老年人群的研究中同样发现罹患糖尿病、高血压、特别是认知障碍者的MDD 的发生率比较高。不良生活方式,如缺乏运动和久坐也有多项研究认为是MDD 发生的危险因素。一项包括来自11 个国家的300 多万成年人的荟萃分析发现有规律的中等强度到剧烈的体力活动水平与成人的MDD 的发生呈负相关[12]。
临床上如何评估一位老年人是否伴有LLD? 问诊有助于寻找迹象,如:面容愁苦,缺少目光接触,语速缓慢或者语调低沉,没有感情的表述,行动缓慢或者坐立不安等。就诊时可以按照症状清单进行询问,至少有下述中一种症状影响到患者的日常活动,持续至少2 周:(1)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2)疲惫不堪或精力不足;(3)感到悲伤或者烦躁。其他经常出现的、需要询问的症状有:睡眠紊乱,疲倦,食欲不振,注意力不集中,感到无价值或内疚,无望或者自杀念头,全身酸痛。
需要重视老年人的自杀或者自伤的行为。老年人自杀率并不低,但自杀念头常常很隐蔽而容易被人所忽略,因此老年人自杀成功的风险更高。在诊治时要注意: (1)不可忽视任何一次自杀尝试;(2)自杀与自伤行为常常和抑郁障碍有关;(3)询问自杀的想法并不会导致自杀,相反,大部分患者在与他人或者医务工作者交流和倾诉自己的自杀想法后会感到放松;(4)对于有婚姻问题和经济财务问题(投资失败、被骗等)者要特别关注自杀倾向并及早干预。此外,对于LLD 的诊断要除外内科疾病如甲状腺功能减退,或者药物如β 受体阻滞剂、降压药物、抗反录病毒药物等的影响[13]。
LLD 的主要治疗措施为抗抑郁药物,药物起到减轻抑郁症状,缓解抑郁发作的作用。对于老年专科医师及全科医师,可以使用的主要的抗抑郁药为[13]:(1)三环类抗抑郁药物:阿米替林、多塞平、丙咪嗪、去甲替林等;(2)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ator,SSRI):氟西汀、西酞普兰、艾斯西酞普兰、氟伏沙明、帕罗西汀和舍曲林;(3)其他抗抑郁药:阿戈美拉汀、度洛西汀、米氮平、曲唑酮、文拉法辛、伏硫西汀、安非他酮等。老年人药物耐受性较差,建议个体化调整初始用药剂量,一般从半量开始。在选择抗抑郁药物时,应结合老年患者自身伴发的慢性疾病来选择相对适合的抗抑郁药物。合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可以酌情选择安全性较高、药物相互作用较少的治疗药物,如舍曲林等。伴有明显焦虑、疼痛等躯体症状的患者可以选择有相应治疗作用的抗抑郁药,如文拉法辛、度洛西汀等,也可考虑短期小剂量合并使用苯二氮卓类药以及其他抗焦虑药。伴有明显睡眠障碍的患者选择具有镇静和睡眠改善作用的抗抑郁药,如米氮平、曲唑酮等。罹患认知障碍的患者在选择抗抑郁焦虑药物时尽量避免有可能加重认知障碍的药物,可根据临床表现选择使用舍曲林、西酞普兰、艾司西酞普兰及米氮平。对于难治性抑郁和单纯抗抑郁药疗效不佳的患者可以考虑抗抑郁药之外的其他药物增效治疗,如第2 代抗精神病药喹硫平、阿立哌唑等[1]。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伴有其他内科疾病,如缺血性心脏病、前列腺增生、癫痫、甲状腺功能亢进及青光眼的老年患者是不建议使用三环类抗抑郁药物的。老年患者服用的大多数抗抑郁药物需要2~4 周开始起效,对服药的老年人需要观察6~12 周。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增加,LLD 对老年人躯体疾病的治疗和康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保持精神卫生和社会保健的良好状态对于促进老年人躯体健康及精神健康、预防疾病并处理慢性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生活环境的社会问题及生活方式与精神健康(抑郁、焦虑等)密切相关,社区健康工作者参与社区卫生改善行动,加强居民社会关系网络联系,提供就业信息及路径,对社区精神问题高危人群有针对性地开展精神问题预防等措施可有效改善社区精神健康。无论从国家对国民健康关注的层面,还是WHO 健康照护要求层面,均强调基层/社区卫生中心医务工作者应提高和掌握常见精神健康问题的诊治能力,应对从事老龄问题和疾病工作的所有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开展精神卫生和保健知识培训,在社区层面为老年人提供长期及有效的精神卫生保健服务。WHO 将“加强并促进老年人精神卫生”作为“积极健康老龄化”的工作目标,将认知障碍与MDD 纳入到了世卫组织精神卫生差距行动规划(mhGAP)之中,以增进和提高基层/社区对精神、神经和物质使用障碍的诊治能力[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