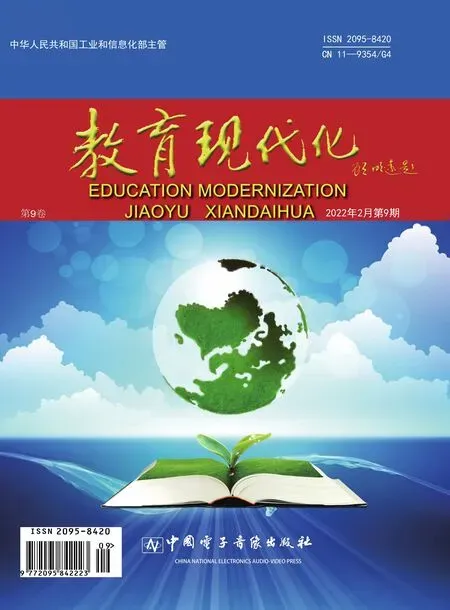中国传统筝曲的声腔特征及教学思考
尹璐,雷思雨
(武汉音乐学院 中乐系,湖北 武汉)
一 引言
古筝作为有两千多年发展历史、当代学习人数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民族乐器,传统筝曲的学习是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文化自信、保护乐种多样性的重要载体,也是深入掌握古筝音韵特征的重要途径,是筝乐创新的重要基础,因此无论是诸如“中国音乐金钟奖”这样高规格的专业音乐赛事,还是音乐普及教育中社会考级的要求,习筝者对传统筝曲的掌握情况都是考察的重点内容。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一方面我国传统音乐的土壤已发生较大变化,传统筝曲所依托的母体乐种逐渐远离我们的生活,当代的古筝学习者对于传统筝曲的文化背景、母体乐种的音乐特征等相关知识缺乏了解及感性认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音乐强调音与音之间腔调变化的音乐特色难以在乐谱上准确记录,尽管在千百年来的历代传承中,中国音乐从记谱法到教学法形成了自身的传承体系,然而当今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下,传统筝曲的学习并非遵循中国音乐自身的传承规律。其结果往往造成习筝者演奏传统筝曲风格的缺失,乃至音乐审美、艺术精神的偏离。
当代筝乐教学主要包括创作筝曲和传统筝曲两个部分的内容。“创作筝曲”指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作曲家、筝乐演奏家在学习西方音乐文化的基础上,将西方作曲技法与我国音乐文化精神、传统音乐素材、古筝演奏技法相结合所创作的乐曲;“传统筝曲”是指清末民国年间在我国说唱、戏曲、民间器乐艺术基础上形成的,未经西方音乐文化影响的,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中国古筝音乐。
在多年的演奏实践、田野采风及教学积累中,笔者意识到当代学生难以准确把握传统筝曲的音韵特征,一方面与对传统筝曲及其所依托的母体乐种的音韵特征不熟悉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下的教学方式相关。下文将分别从传统筝曲声腔特征和对传统筝曲的教学思考两方面予以论述。
二 传统筝乐的声腔特征
民歌、戏曲、说唱、民族器乐作为我国传统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艺术门类间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戏曲、说唱的音乐唱段往往来源于民歌,而器乐作为戏曲、说唱音乐的伴奏,又与其音乐特征紧密相连。综观我国各传统筝艺流派的曲目,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当地说唱、戏曲的器乐伴奏、间奏,一是民间器乐合奏。来源于说唱、戏曲部分的传统筝曲因受剧情、唱段的需要,篇幅长短各异,而来源于民间器乐合奏的传统筝曲,多为68板,结构工整。
古筝作为中国传统器乐的代表乐器之一,尽管从史料来看,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由于战乱、历史变迁等原因,目前筝乐教学中所演奏的传统筝曲,主要源自清末民国时期。这段时间既是说唱、戏曲音乐发展高度繁盛的历史阶段,也是古筝各传统流派形成的时期。在一些地域的说唱、戏曲音乐中古筝常作为重要的伴奏乐器出现,乐器伴奏为配合演唱者表达好唱词内容,烘托唱腔,渲染感情,通常会通过以下几种主要方式进行伴奏。其一为随腔伴奏,即伴奏与唱腔基本一致,伴奏与唱腔的线条同步进行,从乐谱来看,伴奏声部和演唱声部的旋律基本一致,伴奏者要注意演员在演唱中的变化和气口,要与之呼应。一种腔调在表达不同内容时会发生一些小的变化,要求伴奏者随之变化而变化。其二是与唱腔的对比变化,如唱腔长时伴奏密集进行,类似紧打慢唱,以及简化唱腔,弱化旋律只衬托节奏型。表现演唱中的某些特定情绪和环境,使演唱的内容从音乐角度讲更形象化一些[1]。此外,即便是间奏或前奏的纯器乐部分也要为演唱做好铺垫和过渡。总而言之,器乐伴奏为唱腔服务,必须对演唱非常熟悉,必须把所弹奏的曲调熟记于心,并根据内容及演员情绪的变化来演奏。
从传统筝曲的来源看,以北方的山东、河南筝派为例,山东筝曲分大板筝曲和小板筝曲,大板筝曲来源于山东民间器乐合奏,小板筝曲部分则来源于说唱音乐山东琴书的唱腔伴奏及间奏部分。山东琴书是是山东省最富代表的说唱曲种之一,也是山东筝艺流派曲目的主要来源。雍正年间于鲁西南地区产生的汇集南北俗曲及当地时尚小调连缀演唱的“小曲子”,是山东琴书的前身。当时,城市中的一些风雅之士在宅内修建琴台阁楼,弹奏琴、筝自唱自娱,由于琴台临水,使乐音清雅动听,故也被称为“琴筝清曲”。山东筝曲主要流传于鲁西南一带,与山东琴书兴起地重合。一段时期内古筝是山东琴书的主要伴奏乐器。山东筝家高自成先生1986年编撰的《山东筝曲集》中,包含83首小板筝曲。其中19受来自山东琴书曲牌,64首为山东琴书唱牌[2]。河南筝艺流派则是在河南南阳大调曲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河南大调曲子是曲牌体的说唱曲种,伴奏以三弦、琵琶、筝为主。古筝依附于大调曲子作为伴奏乐器存在,是它从大调曲子板头曲向河南筝曲进一步发展蜕变的前提条件与土壤根基[3]。河南筝派传统曲目主要包括唱腔牌子曲和板头曲,其中唱腔牌子曲源于大调曲子中古筝为唱腔的伴奏部分,而板头曲则来自于唱腔之前的器乐合奏。由此可见说唱音乐山东琴书、大调曲子对山东河南筝曲的直接影响。
再从代表人物的艺术经历来看。代表人物对于一个流派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其演奏、传谱、艺术观点都深刻影响该流派的确立与传承[4]。传统筝艺流派的代表人物除了在筝演奏方面造诣深厚,往往也有很好的说唱、戏曲功底。山东筝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如清末时期的黎邦荣就擅长演唱山东琴书。民国时期高自成、张应易、赵玉斋等山东筝派代表人物也都有学唱山东琴书的经历[5]。河南筝派的代表人物王省吾出身曲子世家,从小学习弹唱,成年后常参加曲子演唱活动。曹东扶先生的父亲曹怀清就以唱大调曲子为生,曹先生自幼随父学唱曲子,以唱奏俱佳闻名[6]。曹先生曾经说到:“我一生将百分之七十的精力用于大调曲子的演唱,百分之三十的精力用于古筝演奏,却在古筝演奏上结了果。”从山东河南筝派代表人物艺术经历的共性,可知扎实的唱腔功底是他们的筝演奏被肯定推崇、成为流派代表人物的基础,由他们传谱的筝独奏也必然沿袭了唱腔的特征。在南方,广东潮州、客家筝曲,与北方河南山东一样,来自于民间器乐合奏的多为68板结构,而来源于潮剧、汉剧的唱腔伴奏音乐则结构灵活多样,代表人物也多有在剧团工作的经历,这里不再赘述。
从上文列举的山东、河南筝艺流派传统筝曲与母体乐种的紧密联系,以及代表人物因谙熟山东琴书、大调曲子的唱腔,才能得其精髓,精准把握,将其特点风格以筝独奏的形式得以继续发展,从而为独具特色的地方筝艺流派形成奠定基础。反映出母体乐种的风格特征及声腔特点对独奏筝曲的重要影响。南方潮州、客家筝艺流派也有着同样的艺术规律[7],在此不再赘述。
杨荫浏先生曾总结:“从历史上看,声乐的发展,曾既是器乐发展的先导,又是器乐发展的基础,历史上有无数器乐作品是从先有声乐作品上加工改编而来;有不少器乐种类曾通过为声乐服务的漫长过程而后逐渐脱离了声乐,形成其独立的器乐体系。”古筝作为中国民族乐器的重要代表,其传统曲目更是典型体现了黄先生所总结的中国音乐共性规律。
三 对传统筝曲教学的思考
(一) 传统筝曲教学现实困境
首先,中国传统音乐由于其无定谱、即兴强、重个人风格等特点,历来以师徒之间“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早期传统曲艺的伴奏学习也是如此,以传统筝派的代表人物的经历来看,多是世代相传,或在乐团通过大量观看师傅的演出、溜活,从中自己学习、自己体悟。长期的熏、泡过程中,他们对某一音乐风格能非常地道准确的掌握,由于演奏者长期直接与演唱者合作,或者自己就能较好的演唱,因此在对风格特点谙熟于心的基础上对音乐所表达的内容情感也有了清晰了解和深刻体会,并能很好的与演唱和乐队配合。当他们将器乐伴奏发展独立成古筝独奏时,个性、审美便在地方音乐特色的共性基础上形成自身独特鲜明的艺术个性。每一位民间艺人都可以被称之为一座“小型博物馆”,他们往往是创造者,同时又是表演者和传播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生于清末民初的各地杰出民间艺人也就是各传统筝派的代表人,他们受邀分别在全国不同的音乐专业院校任教,他们亲授的学生由于能直接向代表人物学习,虽然没有在说唱音乐背景下耳濡目染的经历,尚能通过老师口传心授的方式来了解、熟悉、把握某一风格流派的乐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代传承人也相继故去,科技进步、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曾经的传统音乐文化环境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当代的习筝人对于传统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已比较陌生,对于传统筝曲的背景、音乐特征也觉得难以把握。
第二,自五四运动以来,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中国社会推翻了千年封建帝制禁锢的同时也将一系列本国特有的教育体制教育方式淡化,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应关注到中国传统的教学方式,就音乐学院的音乐教学来看,当下全国各大音乐院校的教学方法、教材体系以西方德奥体系为主,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在音乐教育的普及性、规范性等方面确实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用这套体系学习中国传统音乐却实难适应。沈洽老师在《音腔论》中提到,“欧洲(诸民族)传统音乐音体系”并不能帮助我们正确的表述“汉民族传统音乐音体系”,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还常常歪曲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形象,并由此在理论和实践中引出一系列的矛盾和混乱[8]。
的确,不同文化体系的传承都有自己的方式,特别是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在文化上未曾断流的国度,我们的文化传承有着自身规律。中国音乐以旋律为主,传统的记谱法无论是工尺谱还是减字谱、二四谱都给演奏者的个性发挥留下巨大空间,传统的筝乐演奏右手施音左手作韵,很多老一辈筝乐演奏家都认为表现古筝韵味的左手才是筝的灵魂。然而确切的音容易记谱,微妙的韵味变化则主要通过对唱腔的模仿上来体现,从记谱上难以准确表达。声乐作为器乐的先导,人声作为一件万能的乐器,无论在音高、音色还是力度等方面都比器乐拥有更加灵活多变的控制,所以旋律因素尤其重要,口传心授的教学方式成为最主要最重要的传承方式。但是随着当代筝乐艺术的普及,老一辈代表人物的故去,面对面的口传心授方式已难以实现。
此外,传统中国器乐作为民间音乐在民间自发传承,演奏者往往只需要学习一个地域的乐种唱奏,在数十年的熏陶中,在大的地域特征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个人艺术风采。但是当代习筝者在需要掌握多个传统流派的音乐风格、技术特征、艺术审美,传统教学数十年成形的“熏泡法”在当代显然是行不通的。
基于以上原因,当今的古筝学习者常常对传统筝曲的演奏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但是在这些客观存在的制约下,对于如何将中国传统筝曲在当代更好地继承并发扬下去,在长期的教学中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予以解决。
(二) 传统筝曲教学改善举措
首先,应加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学习。当前,大部分古筝演奏者不愿意或害怕演奏传统筝曲,主要是因为对传统风格不熟悉、不了解,面对记谱“简单”的乐谱,无法演奏出丰富的音韵特色,这与对传统筝曲母体音乐的了解不足,用现有的音乐基础理论切入演奏传统音乐的方式有关。例如传统筝曲记谱通常使用工尺谱,潮州地区也用二四谱,强调对调骨的念唱。各民族、各地域、各乐种的工尺谱为适应音乐特征的需要均有不同的变化,随着主奏乐器的不同也会附上各乐器互有区别的演奏手法记号,这种记谱方式的独特魅力是简谱或线谱所缺失的。如果能加强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学习,相信演奏者会对传统音乐的传承能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有助于广大音乐学子对传统音乐的学习把握,提高学习效率,从而更好的传承传统音乐精髓。
其次,强调对代表人物及母体乐种录音录像的模仿。中国传统艺术强调临摹积累,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都是在大量模仿的过程中,谙熟艺术规律,建立良好的审美,从而再根据自己的个性进行融会贯通的创造,厚积薄发,在艺术共性中形成自身的个性。中国传统音乐在漫长的历史传承中,“口传心授”的教学方式实际上也是对师傅的模仿。工尺字记下骨干音“框格”,旋律之色泽润饰、神情气韵则主要在师徒的口口相授之中,由传承者进行体察、领悟、创造、发挥。正是在这一系列过程的不断反复中,历代艺人、乐工、音乐爱好者为传统音乐的传承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尽管口传心授的方式在当前条件下难以继续,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我国对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视,目前很多早期代表人物的演奏录音以及母体乐种的视频得以整理问世,这些资料为学习者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所以学习传统筝曲仍然可以建立在对代表人物录音模仿的基础上。通过尽可能的贴近代表人物的唱奏,积累丰富的感性经验,将某一流派的风格特点吸收把握,再在其基础上融入自身的理解。
再次,多唱谱。鉴于传统筝曲演奏与声腔的紧密的联系,而中国音乐中的诸多细节特点与方言、地域、个性相关,又难以用谱面记录,因而对于这种音乐的学习需要多哼唱乐谱,以准确把握谱面音符背后的韵味。笔者在多次采风的过程中,很多前辈都曾介绍他们的学习经历:首先唱好,之后再上琴演奏。前辈们强调唱的共性经验反应了传统音乐教学的规律。从多年的教学中不难发现,当代专业音乐学院的学生的技术水平、视奏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然而面对记谱简单的传统乐曲,乐谱常常只能提供一个大致框架和轮廓,仅按谱面演奏就如隔靴搔痒,难以反映出其特征。因此传统筝曲的学习要强调多唱谱,强调对声腔的模仿体会,通过大量的哼唱将音与音之间的韵味特点,将谱面无法记录的声腔特征、风格特点把握准确,从而将作品地道的诠释出来。回顾各位代表人物的经历,实际上也是从唱到弹,从模仿到创造的过程。
最后,深入到民间艺术的土壤。作为专业院校的老师、学生,职业古筝演奏者、传播者,除了依靠录音等音响资料学习外,还应到进行田野采风,深入了解音乐背后的地理、人文特点,并向当地的传承人交流学习。音乐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传统筝乐与当地的民间音乐、风土人情、语言文化等多方面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尽管时过境迁,当代的文化土壤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深入到田野仍然可以感受到不同地域、不同气候、不同的风土人情,从而了解音乐所产生的环境,以及当地对某一乐种的传承,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学习、研究传统筝乐作品,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展。
四 结语
中国传统音乐作为我们重要的音乐文化素材,在当代音乐创作中仍然在延续,例如陕西风格的筝曲创作常运用当地秦腔、碗碗腔,王中山教授创作的《梅花调》来自梅花大鼓的器乐伴奏和唱腔,在此不一一列举。学习中国传统筝曲以及以中国传统音乐艺术为基础的创作筝曲,都应尊重中国音乐自身的规律学习多听、多唱、多对母体音乐进行了解模仿,再进行发展创造,得其门而入方能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