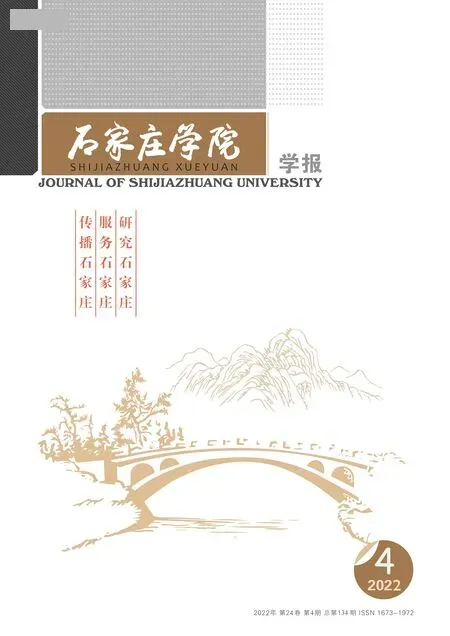《玄怪录》的诗化特征
张启惠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玄怪录》是唐人文言传奇集的代表作,也是牛僧孺文学史地位奠基之作。牛僧孺作为儒家传统士人,积极入世,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不收贿赂;并且在风雅精神影响下,形成了关注现实、反映民生的人文情怀。《玄怪录》寄托了牛僧孺的理想与志趣,不仅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同时具有唐人文言小说的典型特征,即大量的想象与虚构,浓郁的抒情色彩,叙事婉曲,施以藻饰,“始有意为之”。在此基础上,《玄怪录》形成了独特的诗化特征,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
那么,何谓诗化特征?简而言之,就是《玄怪录》虽为小说,却具备了诗歌的美学特征。无论是最表层的外在形式诗之笔法,还是更深层次的小说关节筋骨中流淌的诗意,抑或是诗化意境的营造、诗意气氛的渲染,《玄怪录》都做到了诗意盎然。
一、诗笔
赵彦卫在其《云麓漫钞》中曾论述:“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1]135,由此提出了“诗笔”一说。后来学者在研究诗笔时大多从此出发,以陈寅恪与程国富为代表。陈寅恪认为诗笔即诗之笔法,指韵文而言;程国富认为诗笔指作品的抒情性及其想象、虚构、夸张等文学手法。综合观之,何为诗笔?其外在表现大概就是诗的笔法,即具有诗的外在形式美,音韵和谐,铺采摛 文,节奏鲜明;又或者具有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想象、虚构、夸张等。
《玄怪录》中,诗笔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韵散结合,词采清丽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提到:“小说亦如诗,至唐代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2]65在以往六朝的志怪小说中往往都不会摛 词造句,而是简奥质朴;然而到了唐代,这个气象玲珑的时代,在诗歌的浸润之下,文学发展的自觉性使传奇小说具有了诗的特征,即“诗赋欲丽”,增加修饰藻绘,追求辞章之美。
牛僧孺又是进士出身,从小勤奋好学,善文属诗,一生都与著名文学家白居易、柳宗、韩愈等交往甚密,交相唱和,是一位典型的文人代表。他的诗心灵性必然揉进了其传奇集中,从而使《玄怪录》文本韵散有致,诗文并举,辞藻清丽,具有诗的外在形式美。
1.韵散结合
《玄怪录·卷一·杜子春》中:“一二年间,稍稍而尽。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徒,疏忽如初”[3]3, “ 婚嫁甥侄,迁 祔旅亲,恩者煦之,仇者复之”[3]4以及“雨泪庭中,且咒且骂”[3]5等四字一句,略为工整;再如《玄怪录·卷一·裴谌》中:“吾所以去国忘家,耳绝丝竹,口厌肥豢,目弃其色,去华屋而乐茅斋,贱欢愉而贵寂寞者”[3]12等,韵散结合,朗朗上口;再如《玄怪录·卷九·齐饶州》中的一段对话:“夫妻之情,事均一体,鹣鹣翼坠,比目半无,单然此身,更将何往?苟有歧路,汤火能入。但生死异路,幽晦难知,如可竭诚,愿闻其计”[3]86,在押韵的同时,也用诗歌来代替对话,表情达意,细致动人。
2.词采清丽
《玄怪录》继承了“诗歌缘情绮靡”“诗赋欲丽”的特征,但却不繁缛,而是清词丽句穿插于行文之间,寄予作者的微情妙思,玲珑有致。在《玄怪录·卷一·裴谌》中描写神邸“裴宅”,文云:“烟翠葱茏,景色妍媚,不可形状。香风飒来,神情气爽,飘飘然有凌云之意”[3]13,玉树、香风、氤氲缥缈的白云,用简约曼妙的文笔再现了裴宅的神秘与朦胧。
在《玄怪录·卷四·柳归舜》中:“周匝六七亩,其外尽生翠竹,圆大如盎,叶曳白云,森罗映天,清风徐吹,戛为丝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树,高百尺,条干偃阴,为五色,翠叶如盘,花径尺余,色深碧,蘂深红,异香成烟。”[3]32柳归舜被风偶吹至君山,君山在牛僧孺的笔下,色彩缤纷,飘渺朦胧,生机盎然,君山的景致似乎历历在目。牛僧孺笔下的山水清音如水月镜花般不可凑泊,这正是《玄怪录》诗笔的完美展现。
(二)叙述婉曲,细致生动
由于唐人在文言小说创作上向诗赋学习,体物而浏亮,内容上抒情达意,重视细致的描绘语言,重视虚构,这使唐人文言小说即唐传奇,脱离了六朝志怪与史传文学的叙述性语言,从简洁平淡走向婉曲细腻,从现实走向浪漫。《玄怪录》作为唐传奇集的优秀代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无法脱离史传文学的叙述手段,但是许多篇章“有意而为之”,描写得细致生动,值得一品。如在《玄怪录·卷八·古元之》中:
“其国大山,石际生青彩萝条,异花珍果,软草香媚,好禽嘲哳。……其人长短妍媸皆等,无有嗜欲爱憎之志。人生二男二女,为邻则世世婚姻,笄年而嫁,二十而娶,人寿百二十……每日午时一食,中间惟食酒浆果实耳……野菜皆足人食……其国千官皆足,而仕宦不知其身之在仕,亲于下人,以无职事操断斩也……。”[3]79-80
牛僧孺用洋洋洒洒的百字,细致地再现了如桃花源般的“和神国”的山碧石青、异花珍果、香草软诺、好鸟相鸣。除了对于仙境神邸一类的描写,他还用大量的笔墨描绘了淳朴民风、风调雨顺、自给自足、无欲无私、无怒无愤和美好和谐,有一种大同社会的意味。这种巨细无遗的描写在《玄怪录》中大量出现,不仅体现在《古元之》这篇,在牛僧孺打造其他神邸仙境时皆有体现。作者耗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心之所向,使得作品情意盎然,充满了诗情画意。
(三)玄虚怪异,亦真亦幻
先秦时期,屈原的《楚辞》通过想象创造了一系列浪漫图景,上天入地,自由驰骋;唐代诗人李白想象奇特,发想无端,飞跃古今,达到继屈原之后又一个浪漫主义的高峰;诗鬼李贺的想象更是诡谲怪异,变化莫测,幽艳冷峭。《玄怪录》是诗歌盛行时代的产物,必然受到诗歌浪漫主义的影响。六朝志怪小说与唐传奇整体风气中都有着浪漫的抒情主义传统,想象奇幻,情感奔放,如海天风雨般爆发,直泄而下。《玄怪录》是一部传奇与志怪杂糅的集子,其中大部分故事都是玄虚怪异,其中《齐饶州》及另一篇《齐推女》是写中唐真实人物饶州刺史齐推的故事,这类假托古人故事演绎情节,情意缠绵,寓真于幻,以幻笔写真情。
二、诗情
汪辟疆在《唐人小说》中论述:“刘宋贡公常言:‘小说至唐,鸟花猿子,纷纷荡漾’,洪景庐亦言:‘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4]1,纷纷荡漾到凄婉欲绝,无论是人物还是情节,都是以情致贯穿,荡气回肠。诗歌以及词赋最大的功能或者是特征是言情抒志,《玄怪录》大部分篇章都是“幻设为文”[2]65,牛僧孺是“有意而为之”。因此可以说,《玄怪录》是牛僧孺的情感释放,或者说是其理想寄托,他将诗心用灵性的诗笔化成诗情,写成一个个亦真亦幻的诗篇。《玄怪录》中的诗情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抒情化的人物形象
《玄怪录》中塑造了大量充满诗意寄托的人物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功业无成,光阴已逝之寄
《玄怪录·卷一·杜子春》中,在黑暗社会的腐朽现实面前,杜子春借酒消愁,虽最后得老翁资助愿帮之炼丹,但终因爱而失声呐喊,前功尽弃,将其所有毁之一炬。杜子春的功业无成可能包含作者本人心里的情感暗示。牛僧孺虽曾官至宰相,但他在早年求仕的经历和后来的官场升沉遭际中也非一帆风顺,对年轻士人在现实中遭受挫折、个人理想难以实现的落拓失路之感,应当有过亲身的体验。《玄怪录·卷一·裴谌》中的王敬伯曾与裴谌一起进山修道,却中途放弃,下山从政。但在其下山之后,最终看到的却是:“乃荒凉之地,烟草极目,惆怅而返。”[3]14仅仅几句话,足以表达出王敬伯的失意之情。《玄怪录·卷七·萧至忠》中的“使者”更是一番苦闷在心头,有诗云:“昔为仙子今为虎 ,流落阴崖足风雨。更将斑毛披余身,千载空山万般苦。”[3]67仅四句诗就把“使者”昔日辉煌今落魄的巨大人生落差、心中无奈和辛酸的感慨表达得淋漓尽致,引来无数文人志士的叹息。
《玄怪录》中还有许多类似篇章,如《刘讽》中“明月清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愉不终”[3]54、《许元长》中的失落人士陆俊之、《来君绰》中如泥中蚯蚓的威污蠖以及来君绰等人、《马仆射总》中“人生之世,白驹过隙,谁能不死。而又福不在遇,良时易失,苟非深分,岂荐自代”[3]111等,牛僧孺用诗笔寄之予深情,使浓郁的传统文人情结萦绕在作品的字里行间。
2.客游他乡,人生漂泊之寄
牛僧孺因朋党之争多次调任,虽曾官至宰相,但这浮浮沉沉的漂泊生活让他有了十分细致的体验与感悟,便产生了飘絮浮萍的感伤。《玄怪录·卷九·许元长》中有文云:
“俄而妻亡,俊之伤悼,情又过之,美至春风动之,秋月明时,众乐声悲,征鸿韵咽,或辗转忘寐,思苦畏叹,或伫立无憀 ,心伤永日。如此者,逾年已。全失壮容,骤或雪鬓。”[3]103
客居异地他乡的陆俊之,在听闻家乡传来爱妻突然身亡的消息,忧思重重,辗转反侧,致两鬓成霜,面容枯槁憔悴。从文中得知,陆俊之是一位典型的宦游仕人,有着沉重漂泊之感,其政治理想上的壮志难酬、现实生活的无迹可求,加上妻子的突然死亡,精神和现实的双重打击让他心中人生如梦如电的感伤飘然而起,难以压制。长期宦游在外,家和妻子便是他的归属与慰藉,失去这一切,让他感到自己像一只振翅孤飞的大雁,悲伤凄凉。
《玄怪录·补遗·魏朋》中的建州刺史魏朋,任期满,客居南昌,卧病久居床榻,睡梦中竟作诗一首,其诗曰:
“孤坟临清江,每睹白日晚。松影摇长风,蟾光落岩甸。故乡千里余,亲戚罕相见。望望空云山,哀哀泪如霰。恨为泉台客,复此异乡县。愿言敦畴昔,勿以弃疵见。”[3]125
魏朋因做官不得已远离家乡,因思念其亡妻,独望青松白日,泪如流霰,漂泊如絮的孤独感催生了其无尽的思乡之情和人生无依的悲戚之感。另外,《玄怪录·卷四·来君绰》《玄怪录·卷五·元无有》等都是写文人志士流落漂泊在外,入异境,遇奇事。当然,牛僧孺是以幻笔书真情,寓哲与理于玄虚怪异、亦真亦幻的志怪故事中。人生漂泊无依、幻灭之感不仅是牛僧孺一人之感,而是晚唐大多数文人的亲身感悟,牛僧孺只是寄之于笔端,用诗笔道出了一代文人的心理图景。
3.山水真情,理想抱负之寄
牛僧孺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传统文人,《玄怪录》短篇中的主人公往往寄予了其理想与抱负。最为典型的是《玄怪录·卷八·古元之》中的古元之,借古元之之口描述出和神国的纯美之境,塑造了古元之最后看破世尘、素心若雪的形象。或者说,古元之(张老、裴谌、柳归舜等)这类形象正是牛僧孺理想的寄托、理想的意象化,他在现实世界无法实现的理想,凭借传奇,用诗笔打造出一个个玲珑剔透的纯美之境,创造了一个个亦真亦幻的人物,并赋予他们自己的情感,以完成自己未完成的遗憾。不只在《古元之》中有这种体会,《玄怪录·卷二·郭代公》中落第士子郭震公偶入荒凉宅院,却遇落难少女,打抱不平,仗义救人,这或许就是作者侠义情感的寄托。
牛僧孺在《玄怪录》中塑造了众多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或抒发飘零流落之感,或感叹人生无成的失意,或寄托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找寻。诗歌中诗人用意象来寄托自己的情思,而小说中则用人物作为一种意象来寄托自己的感情。这正是牛僧孺《玄怪录》的特殊之处,处处有情,以情贯穿整部小说集,使整部小说充满了诗情,韵味无穷。
(二)抒情性的情节推进
首先,用诗歌直接作为线索,推动情节的发展。如《柳归舜》一文,作者用韵文描写君山景致,用大量的诗歌对话作为线索推动情节发展,具有浓厚的诗意色彩。柳归舜偶然被风吹至君山,从而见到如水月镜花般不可言的君山,看到众多声音清越、通人言的鹦鹉谈论诗词歌赋。作者用丰富的诗歌代替对话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为全文增添了浓厚的诗意。
其次,用诗意作为内在驱动力为情节发展埋下伏笔,暗示小说结局。《玄怪录·卷六·袁洪儿誇 郎》则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不仅用诗歌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而且诗意线索的暗示作为内在驱动力,使整个篇章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故事的开始便是由诗句引起,“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3]59,封郎的翠翠鸟闻其诗,便引袁生与封郎相见,二人相识。封郎又下诗书邀请袁生来其宅做客,诗曰:“佳辰气茂,思得良会,驻足吃台,企俟光仪,惟足下但东驰耳”[3]59,袁生二人相谈甚欢,并在其介绍下娶到贤淑妍丽的王家千金,文中诗赞曰:“圆扇画方新,金花照锦茵,那言灯下见,更值月中人”[3]60,其色倾国,二人相敬如宾、琴瑟和谐,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但最后因丈人升迁,夫妻二人呜咽流涕,凄凄惨别,使整个故事充满浓郁的悲情。诗意的暗示则在于故事的开头那一联句“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早就奠定了整个故事的悲情基础,而且既渲染了清冷寂寥的气氛,又暗示了袁生与王家千金呜咽泣别的结局。用诗歌作为抒情线索,推动了情节发展,使故事更加婉转动人、含蓄蕴藉,充满了诗思情韵。
(三)抒情化的主题呈现
唐人诗歌最重要的是以情动人。无论何种情感,不管是人生漂泊孤独之情、人生失意之情,还是理想抱负寄托之情,情在诗歌中的地位都是极其重要的,它是诗歌的核心与灵魂。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毛诗序中也说诗言志,都曾强调了情感的重要性。唐人在诗歌的浸润下,在创作传奇小说时往往也带有强烈的情感特征,常常是“为情造文”,从而幻设为文。而唐人小说中最浓墨重彩的情感则是男女爱恋真情,《玄怪录》同样用了细腻的笔墨来创造了许多动人的爱情诗篇。爱情主题的呈现与强烈的抒情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浓郁的诗情。
首先,悲剧的仙遇之情。神女与凡人书生相遇一直是古代文人乐此不疲的写作素材,从先秦时期屈原的《离骚》,求女的情节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以及其凄美飘渺的《山鬼》,是著名的人神之恋的诗篇,其伤情令人泣泪感叹;再到著名诗赋《高唐赋》《神女赋》,以及之后曹植的《洛神赋》,这种母题本身就具有诗情画意、凄美动人的效果。
《玄怪录》中神女与书生的爱情故事,也是被作者写得凄清飘渺、婉转动人。《玄怪录·卷四·崔书生》中崔书生与神女的爱情,因遭到封建家长的怀疑,疑神女为狐媚之人,导致神女不得不远去,与书生分离,有情人泣泪相别,数年之久,书生叹恨而终。尤其是故事一开始对浓郁春色的描写,二人相识时的胜景描写充满了诗情画意,文曰:“春暮之时,英蕊芬郁,远闻百步”[3]35;再到后来二人分别时,对山林间景色的优美描写,“山间有川,川中有异香珍果,不可胜纪”[3]36,以乐景写哀情,更衬托了小说凄美朦胧之感。《玄怪录·卷六·袁洪誇 儿郎》中的袁洪儿与其在异境之妻,因丈人迁升,其妻不得不饰装随行,文中描述其妻云:“忽觉妻皆惨然”“其妻鸣咽流涕”,别后回顾却不见一物,恍惚如梦,悲戚之情难以抑制。
论诗中曾有用“味”来评价赞美诗文,《文心雕龙》中曾出现过“余味”“滋味”“可味”等,钟嵘也有“滋味说”,而到了唐代又有了“韵味”一说。《玄怪录》这本传奇集在诗歌以及诗歌理论和审美的滋养下,不仅注意词彩清丽、情兼雅怨,也注意诗歌创造出的韵味无穷的审美空间。悲情的结尾正是对“余味”或“韵味”的最好的回应,往往营造出可遇却不可达的心境。记忆、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苦涩的。这两个篇章通过书生与异境神女或者异域之妙龄女子神遇的故事,传达出的是人的恍惚如梦和美好事物倏忽间的流逝。神遇美好情感以及别离后怅恨的凄凄伤情一直萦绕在整个故事中,再加上中间些许诗句的穿插,诗情余味无穷。
其次,动人的人间真情。《玄怪录·卷九·齐饶州》中:“夫妻之情,事均一体,鹣鹣翼坠,比目半无,单然此身,更将何往?”[3]86齐饶州对妻子更是一往情深,为了求得高人相助救回妻子,被唾弃打骂都不言怨愤,最终用真诚打动了“先生”,有语云:“官人真有心丈夫也,为妻之冤,甘心屈辱,感君诚恳,试为检寻”[3]87,齐饶州更是被赞为“有心丈夫”。在《玄怪录·补遗·魏朋》中魏朋因思念其妻而感慨作诗,数日后便卒。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漂泊在外的游子的孤独情思,也感受到他对妻子的真情,虽然二人肉体泯灭,但至真热烈的爱情却难以磨灭。这一部分牛僧孺用动人的挚情、婉转细腻的诗笔,热烈地赞颂真挚爱情,也表达出了作者本人在奇异之笔下的人情人性,道出了他心中夫妻间的真情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深情真情的找寻。
三、诗境
王昌龄在《诗格》中曾说道“诗有三境”:“一曰物镜: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像,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5]172《玄怪录》产生于诗歌繁荣的唐代,必然会受诗歌创作的影响,其中意境的营造则是少不了的。因此,我们也可以从王昌龄对唐代诗歌诗境的分类,对《玄怪录》小说中的诗境进行分类探讨。
(一)物境
按照王昌龄《诗格》中的分类,物境是如山水诗般纯美景色之境。在《玄怪录》中有许多关于山水风光的细致描写,个个都让人耳目清新、赏心悦目。如在《柳归舜》一文中,其文曰:“紫云数片,自西南飞来。去地丈余,云气渐散,遂见珠楼翠幕……一青衣自户出……颜甚姝美。”[3]33对桂家十三娘子住所的描绘,更是曼妙朦胧;不只在《柳归舜》一篇中有这种描绘,在环境描写极为少的篇目中也会有,如在《元无有》中,作者用八个字“须臾霁止,斜月自出”[3]46描写雨后初晴,也是极为空灵。
当然这种对环境的细致描绘在《玄怪录》中极为常见,尤其是对仙境神邸的描绘,更是美妙绝伦、亦真亦幻。虽然说《玄怪录》中的仙境神邸之美,写得太过于虚幻飘渺,但这其实是对盛唐风象的再现,是牛僧孺心中美好的再现,对往事的一种追忆。
(二)情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论境界时云:“能写真景物真情感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6]9《玄怪录》中的许多篇章虽然都是幻设为文,有些更是精怪出没,但寄予的都是作者的真情感,亲情、友情、爱情、侠义之情甚至愤世嫉俗之情都囊括其中,让读者体会到人间真实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玄怪录·卷七·萧至忠》篇中,风雪之神居然因人间献祭的美女、酒肉才降风降雪;同样在卷七中,《董慎》则讲述的是仙界的元太夫人的三等亲属犯事却未被正确处理,从而招致120 个犯人的积怨,因此请来人间性情正直的董慎来断案,才得到较好的处理;《玄怪录·卷三·崔环》篇中,崔环因误入矿人院,骨肉尽被摧碎,却因为他是判官阳间之子,众人惊惧,立刻要帮其恢复骨肉;《玄怪录·卷九·吴全素》篇中,吴全素被阴间官吏误带入阴司,阴司查看其阳寿未尽,便派阴司官吏送其返阳,在返阳的路上,他居然被两个小吏各敲诈了五十万钱财,可以说是荒唐至极。从仙界到人间再到阴界,吏治黑暗,官员受贿、贪得无厌,百姓因此生活在暗黑之中,惊恐受怕,充满了无奈。
牛僧孺用阴间或者仙界的吏治暗示着人间的吏治,将仙界以及阴司吏治人间化,真实地再现了中晚唐社会的混乱与黑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玄怪录》不仅让我们感受到牛僧孺作为一个文人的愤世嫉俗之情,也感受到他对百姓的怜悯之心;他抒发的不仅是个人的情感与理想,而是在揭露社会的黑暗、为民发声。牛僧孺设身处地地为民着想,体会百姓的哀乐愁苦,以情入境,再现了那个时代的悲哀与无奈,可谓情之“真境界”。
(三)意境
诗歌除了有强烈的抒情性,另外一个重要而显著的特点则是诗歌的意境。何为意境,即抒情性作品中呈现出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7]217,韵味无穷。刘熙载在《艺概》中曾对意境进行过分类:“花鸟缠绵,云雷奋发,弦泉幽咽,雪月空明,诗不出此四境”[8]84,这四种诗境都是情景交融,诗意盎然。
牛僧孺的文人情怀、诗心灵性,使《玄怪录》许多篇章都是借景抒情,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情景交融,诗情荡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仙境神府的细致描写,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具有诗情画意的、美妙理想化的异域之境,代表作有《裴谌》《张老》《柳归舜》《古元之》等。其中柳归舜所遇的君山,山水清音、清新明丽,身体和心灵在此处仿佛都得到了安置;古元之所遇的和神国更是一片美好,不仅在环境上塑造了水中月镜中花不可凑泊的纯美之境,也寄托了牛僧孺的政治理想,那就是百姓安居乐业,君臣治理清明,没有动乱、没有病痛,和谐安宁,风调雨顺,所以才有了这个如《桃花源记》般的王国,空明静好。安静、祥和、纯美的“和神国”到处洋溢着作者对黑暗现实的厌恶、对美好安宁世界的向往,或者说作者是在寻求一种躲避,在寻找安放心灵的家园。
四、诗化特征产生的原因
(一)牛僧孺的个人原因
1.出色的文笔诗才
人们对牛僧孺一直以来的定位都是政治家,却忽略了他也是一个传统文人,而且是一个从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典型文人。唐代的科举制度科目分两种——进士科与明经科,而唐代进士又是以诗赋取士,所以在科举制度下产生了一批充满诗才诗情的文人才子。牛僧孺在贞元二十一年,荣登进士第,这显然为其文采煊赫奠定了基础。牛僧孺的才情藻思,自然而然地运用到了《玄怪录》的创造中,使小说有着诗歌的外在形体之美,韵散结合、词采华艳,叙述婉转细腻、亦真亦幻,充满诗情画意。
2.自觉的抒情意识
徐传玉、张仲谋在《论古典诗文对小说发展的影响》中说道:“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名篇佳句的熏陶积淀,既使得小说家们或多或少地染上了几分诗人气质”[9]136,即感时伤世、伤春悼秋的情怀。牛僧孺的《玄怪录》也不例外,充满了诗人气质,我们可以称之为“诗人小说”。《玄怪录》无论是对现实的针砭或是黑暗的讽刺,还是对人生漂泊孤独无依情感的抒发,或者是对失意人生的感慨、对美好事物以及理想的寄托与追求,又或者是对真挚爱情的热烈歌颂,都是牛僧孺以情感作为审美对象的抒发与寄托。这种抒情意识的自觉,或者说成是传统文人的情结,无论是强烈地抨击现实,还是感叹兴衰、朝代更替,或是敏感地感时伤世,都是文人独特的一种情愫。当然,这种强烈情感的抒发必然与诗歌的盛行密切相关。首先,唐人自幼在诗歌的浸润下成长,诗骚传统浓郁,耳濡目染之下,培养起他们浓厚的诗人气质,“重词赋而不尚经学,重才华而不尚礼法”[9]9。牛僧孺也不例外,诗人气质使他具有敏感的情感体验;其次,唐代诗歌的玲珑气象虽在中晚唐逐渐变淡,但气韵犹在。牛僧孺自然也受唐代诗歌气象的影响,创作《玄怪录》时不拘一格,强烈而自觉地抒发感情,大量的想象与虚构玄虚怪异,却又情思荡漾、绰约有致,写情真挚感人,写事婉转曲折,以清丽典雅之笔传要妙之情;再者,中晚唐时期经历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遭到极大的破坏,物质上也不像盛唐时期那样繁荣富裕,精神上的气象玲珑也一去不复返。最先感受到这种凋敝的就是这些文人,他们用敏感的内心记录着最为真实的情况以及内心独特的体验与感悟。牛僧孺生活在中晚唐时期自然有着独特的感受要抒发,因此赋予了《玄怪录》浓厚的诗情。
3.浓厚的文人雅趣
古代文人饱读诗书,腹有诗书气自华,在闲暇之时,必然有自己的消遣娱乐方式。这种娱乐方式带有极为浓厚的文人特色,可以看成是文人的雅趣。牛僧孺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文人,自然也少不了文化娱乐。具体来说,牛僧孺的文人雅趣是什么呢?即作文之趣与文人文化娱乐之趣。
首先是文学趣味,即个人的文风好尚与审美追求。
庄谐相济,谐中见警。《玄怪录》中有许多篇章都是借精怪之口,用诗歌词赋甚至酒令吟咏生平之事,或者清谈评论历史名人,或者慨叹历史,以幽默诙谐的笔墨讥讽现实或历史,寓庄于谐,寓真于幻,使故事既具有诙谐色彩,让人读之一笑,又能从荒诞诙谐中看到牛僧孺的机警。文中的诗句含蓄凝练、清丽可人,增加了故事的诗意色彩。
有意为文。《玄怪录》中的许多篇章都是牛僧孺有意为小说,作者用虚幻怪诞之语以寄情思,表达自己独特文人的审美趣味。无论是神仙还是鬼怪精魂,作者都赋予他们文人的才思,让他们弹琴、作诗、赋词、品评诗文,使整个故事洋溢着文人的气息,诗味极为浓厚。
逞才炫学。李宗为在《唐人传奇》中提到,“传奇小说的创作意图,则主要是为了显露作者的才华文采,一方面遣兴娱乐、抒情叙志,另一方面也带有扩大名声、提高声誉的目的”[10]12-13。《玄怪录》中之所以有明显的诗化特征,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炫才之作。炫才,或者说是逞才,在唐初传奇中就已经露出端倪,如从《游仙窟》中的众多诗作就可看出,虽为露才而作,却使整个故事显得繁缛枯燥。《玄怪录》中自然也少不了炫才之作,但是其中的炫才往往使故事文采翩翩、诗意盎然、回味无穷,如《柳归舜》一文,诗词歌赋的吟唱、诗意环境的描写、朦胧飘渺氛围的创造,是文人自我才思、清雅别致的情趣与品格的炫耀。
其次是生活情趣,主要是文人之间的雅宴集会。宴饮集会是古代文人最为常见的娱乐休闲方式,抒情遣怀,聊以慰藉。而且雅宴集会是自古就有的传统,文人雅士在此联句,吟诗作文,饮酒畅谈,聊古探今,驰骋遨游,欢愉畅快。牛僧孺曾多次将现实中宴饮聚会的场面搬入《玄怪录》的篇章中,写得空灵婉转,无处不萦绕着诗情。最为典型的是《刘讽》,文章叙写的是刘讽夜投夷陵空馆,遇众女,“因此间好风月,足得游乐,弹琴咏诗,大好事”[3]53,如此良辰美景,玉盘珍馐陈列于眼前,何不吟诗饮酒。再者则是《柳归舜》一文,柳归舜被风吹至君山,于意外中进入君山这个人间仙境,见到了一群相互吟诵诗词歌赋的鹦鹉仙子,这群鹦鹉仙子似乎就是文人墨客的化身,口口生莲,吟诵完还能品评诗作文人,这完全是牛僧孺现实生活中雅宴的再现,也是其独特的文人雅趣的再现。
(二)唐代文学发展水平的影响
1.文备众体——小说文体自身发展的结果
小说的发展从先秦的神话就有了渊源,之后又有了传记等一系列叙事文体,从《春秋》《左传》到《史记》《汉书》等,为小说的文体奠定了基础。到了魏晋南北朝,《世说新语》《搜神记》等文言小说逐渐走向成熟,有了小说的基本模型。到了唐代,传奇小说的出现更是将文言小说推向了一个高峰。
“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对唐人小说比较中肯的评价。那么,文备众体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按如下理解:史才则是史的叙事才能,诗笔则是诗的抒情之类具有诗歌的特点,议论则是说理,三者皆备,则是文备众体。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判断《玄怪录》中的每一篇文章,符合该标准的却少之又少[11],但符合其中两个标准的倒是很多,即史才和诗笔或是诗笔和议论或是史才和议论,从这个方面来看,《玄怪录》在逐渐往这几方面靠近。可能牛僧孺并没有意识到,但其写作小说的史传传统以及他的文人才性,使其小说向文备众体靠近,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诗歌融入小说,是小说发展的需要。
在《玄怪录》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诗歌,还可以看到其他文体,如赋、酒令、谜语等一些文学形式,这也是小说文本的需要。丰富的文学形式使得《玄怪录》极具特色,诗化特征只是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特点而已。
2.诗歌繁荣的时代背景的影响
诗歌从先秦以来就有悠久的创作传统和基础,从洋溢着现实主义光辉的《诗经》,浪漫飘逸、摇曳多姿的《楚辞》,质朴的乐府诗集,充满文人情怀的《古诗十九首》,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曹、建安风骨、竹林七贤、陶渊明等,诗歌发展逐渐繁荣。等到了唐代,诗歌彻底地繁荣起来,宫商与气骨兼备,兴象玲珑,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完全是神来、情来、气来,形成了唐诗不可替代、不可超越的气象。
唐代是诗的国度,是诗的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诗歌的印记,从生活琐事到伦理道德、人生思考、婚姻爱恋,从平民到上层文人、僧人甚至歌妓等,到处都融入了诗美,到处都体现着诗意。唐人用诗歌创造出一种无法超越的玲珑气象,在这种气象中又创造出一代充满诗情的小说。在浓厚的诗歌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唐人小说像《玄怪录》不可能不受到诗歌的影响,自然会去吸收诗歌中富有韵律节奏般的语言以及极为抒情达意的创作方法,并且不仅仅是使诗穿插于小说的行文之间,而且使小说从本质上、从内部就洋溢出诗情诗意,从内到外都闪耀着诗的光芒。《玄怪录》这本传奇集像诗歌一样,广泛地描绘了中晚唐社会的各个方面,展示了唐人的精神风貌,反映出中晚唐时期像牛僧孺般的文人士子普遍的理想追求以及心理图景,寄寓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独特感受以及思考体悟,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价值以及审美价值。
五、诗化特征的意义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这样评价《玄怪录》:“造传奇之文,会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2]85其中“煊赫”一词就是对《玄怪录》艺术和内容上的最为中肯的评价。显然,《玄怪录》在小说发展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影响了之后唐人小说集的创作。
《玄怪录》问世后,像《河东记》《续玄怪录》《宣室志》等一系列志怪传奇集的出现,都是在《玄怪录》影响下创作的,这些作品诗化的痕迹极为明显,如小说中大量出现诗歌等,无论是抒情达意还是烘托营造气氛、推动小说情节发展,都使小说诗思盎然。虽然许多作品与《玄怪录》风格极为相似,但只有《玄怪录》的诗化创作是最为成功的。这是因为《玄怪录》能在众多唐人传奇集中出类拔萃,其“煊赫”特色是当时仿书或者是续书无法企及的。煊赫的诗笔、烂漫纯真的诗情使《玄怪录》整本书的每个关节都流淌着诗意,《玄怪录》也因此在文学史上能够留下浓墨重彩一笔,也为牛僧孺在文学史上争得了不容忽略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