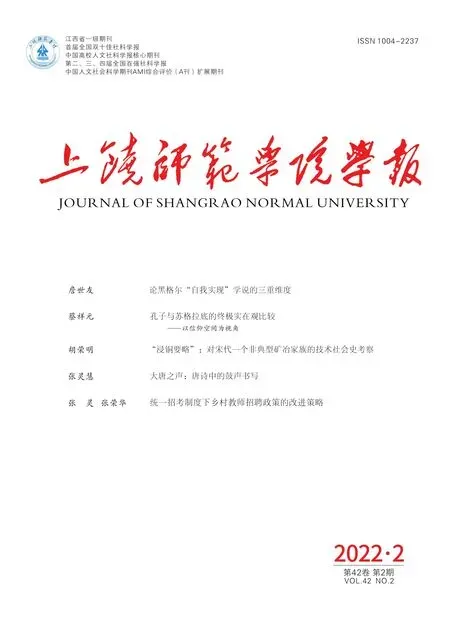论汉代人的疠疫观念与抗疫措施
陈克标
(上饶师范学院 历史地理与旅游学院,江西 上饶334001)
“疫”,也就是俗称的传染病,现代医学对它的定义是:“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类疾病。”[1]166《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对这里的病原体解释为:“大部分是微生物,小部分为寄生虫。”[1]166传染病是人类生存的一大威胁,其中的恶性传染病对人类更是一种灾难。目前,汉代人对传染病的认识与救灾措施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出现了一些重要成果(1)如:张剑光、国慰《略论两汉的疫情特点和救灾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杨振红《汉代自然灾害初探》,《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王文涛《汉代人眼中的疫病》,《河北学刊》2007年第4期;王文涛《汉代的抗疫救灾措施与疫病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6期;王福昌《汉代南方疫灾、疫战与空间叙事》,《深圳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但由于角度不同,此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目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厘清汉代人对传染病的认识与抗疫措施,对当前的疫情防控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汉代疠疫的含义
在汉代文献中,“疫”也称为“疾疫”“疫气”“疠疫”等。在汉代,人们对微生物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汉代人对“疫”的理解与今人并不完全相同。那么,在汉代,“疫”指的是什么呢?东汉许慎将“疫”解释为“民皆疾也”[2]352,即不管男女老少,很多人得病,因此,“疫”似乎并不一定是传染病,但显然包括传染病。东汉刘熙在《释名·释天》中将“疫”解释为:“役也,言有鬼行役也。”[3]9与许慎不同的是,刘熙从他所认为的“疫”的来源进行解释。范行准在《中国病史新义》中说:“起于军队中发生传染病,则士兵服役而得,故称‘役病’。”[4]显然,范行准认为刘熙所谓的“役”就是“疫病”。杨树达也把此处的“役”解释为传染病[5]。笔者认同该解释。
学术界对“疠”的含义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者将“疠”解释为麻风病[6]246,此观点在学术界达成了共识,如李牧《云梦秦简麻风律考》[7]以及吕亚虎《秦汉时期对传染性疾病的认知发微——以出土简文所载疠病为例的探讨》[8]都这样解释秦简中的“疠”。然而考之史籍可知,汉代的“疠”绝不仅仅是麻风病。李曌华认为,“疠”本指皮肤恶疮,到东汉中后期,则有多人同时患病的含义[9]。笔者以为,西汉中期,“疠”就有与“疫”相似的含义。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平闽越之乱时,淮南王刘安曾上书曰:“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10]2781,其中所说的“疠”是在南方湿热的环境下因“蝮蛇蠚生”感染而致,且造成百分之二三十的人死亡,这显然并不是麻风病,但符合许慎对“疫”的解释。
东汉时“疠”的含义与西汉中后期基本相同。许慎对“疠”的解释是:“恶疾也”[2]350。刘熙对“厉”的解释是:“疾气,中人如磨厉伤物也。”[3]9这里的“厉”,指的就是“疠”。许慎和刘熙都是从严重程度描述疠病的,认为这是一种很严重、让人很痛苦的病。许慎和刘熙的解释并没有概括出时人对“疠”的全部认知。如《礼记·檀引(下)》记载:“吴侵陈,斩祀杀厉”,郑玄注曰:“厉,疫病”[11]77,将“疠”与“疫”同等看待。作为东汉的大经师,他对“疠”的理解在东汉应该很有代表性。史籍中多有将“疠”与“疫”并称的记载,如:“风雨不时,疫疠流行”[12]3370,“疠疫为灾”[12]252。王充在《论衡》中也有“温气疫疠,千户灭门”之语[13]45。
在汉代人眼中,“疠”或“疫”是否有传染性呢?《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有个叫作丙的人被怀疑有“毒言”,原因是其“外大母同里丁坐有宁毒言”,“丙家节(即)有祠,召甲等,甲等不肯来,亦未尝召丙饮。里节(即)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桮(杯)器。甲等及里人弟兄及它人智(知)丙者,皆难与丙饮食”。整理者对“毒言”的注解是:“一种传染病,经过饮食或唾液等途径,可以传染他人”[6]316-317。丙似乎并没有染疫的症状,只是他的外祖母(外大母)同里之人中有人染疫。这种情况下,丙依然被怀疑有“毒言”。众人皆尽量避免与丙接触,至少不能与丙同饮食。显然,秦人已清楚地知道,疫是能传染的,也知道染疫之人不一定会有症状,似乎已经知道染疫之人中有我们今日所说的“无症状感染者”。秦人已经对疫有这样的认识,以常理来说,汉代人也应当有这样的认识。王充在《论衡》中记载:“太阳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为毒”,又说“促急捷疾,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脤胎
(胀),肿而为创”[13]949-959。以现代医学来看,王充对毒言来源的解释并不准确,但他知道这种病可通过唾液传染。当人们看到一个人得疫之后其身边人也陆续得相同的疫,很容易得出疫是可以传染的结论。汉代人确实清楚疠疫是可以传染的。
二、疠疫爆发的原因
有研究者指出,汉代人认为疾疫爆发有“君王‘不明’”“恶鬼造成”以及“‘天地之道’和自然规律”[14]105等原因。笔者认同“恶鬼造成”以及“‘天地之道’和自然规律”这两种说法,但“君王‘不明’”说似有不足之处。汉代人不仅认为君王要对灾异负责,三公也应对灾异负责。此外,汉代已有人意识到饮食不当有可能染疫。笔者以为,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四种。
(一)君王与丞相或司徒行为不当
西汉前期,人们就已经把君王的行为和灾疫联系在一起。晁错在给汉文帝的对策中说,五帝的行为符合天、地、人之道,所以“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膏露降,五谷孰,祅孽灭,贼气息,民不疾疫”[10]2293。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之后,人们基本上承认了灾异与政治有关。董仲舒认为,“王者不明,善者不赏,恶者不绌,不肖在位,贤者伏匿,则寒暑失序,而民疾疫”[15]385。东汉人也基本上延续了这个看法。《论衡》记载:“行尧、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灾消灭,虽不逐疫,疫鬼不往。”[13]1043王充认为,如果君王都能像尧、舜一样品德高尚,天下就不会有灾疫。反过来,如果君王举止不当,就会招来灾疫。灾疫是上天对君王犯错的谴责。同时,时人还以为,灾疫也有可能是中央高层官员行为不当造成的。汉元帝初即位时,曾因“关东流民饥寒疾疫”责问丞相于定国“欲何施以塞此咎”[10]3043-3044。延光四年(125),张衡曾上书说:“臣窃见京师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上并猥)死有灭户”“厉气未息,恐其殆此二(年)[事]”[12]3350。张衡认为这次疫灾是中央高层官员在“祀”方面行为不当造成的,并列举了两件事加以说明。在他看来,这次疫灾无疑正是上天对大臣过错的警示。汉桓帝永兴二年(154),“人民疾疫”,时人以为这是“梁翼专政”造成的[12]3311。可见,汉代人普遍认为疫灾是上天对君王以及中央高层官员行为不当而降下的谴责。
(二)恶鬼
恶性传染病会造成人口成比例死亡,汉代人难以理解其中的真正原因,认为这似乎非人力所能为。时人多认为,这是由某种超自然的恶鬼造成的。如前文所提,《释名》在解释何为“疠”时,说的正是其来源于鬼。《汉旧仪》云:“昔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亾去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罔两蜮鬼,一居人宫室区隅沤瘐,善惊人小儿。”[16]104在汉代人眼中,世间不仅有疫鬼,而且至少还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疫鬼。曹植在《说疫气》中曰:“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17]3294-3295。虽然曹植以为这是愚民可笑之言,但确实反映了人们普遍认为疫灾由鬼神造成的这一观念现象。
(三)自然环境
汉代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特殊的自然环境容易引发疫情。南方气候湿热,原始丛林多,时人以为其中有“瘴气”,人若处于其中,就有可能染疫。左鹏在《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中说:“至晚在东汉初年,人们已对交阯(约今越南北部)之瘴气有了认识,比之更早的时代有无此说则不得而知。”[18]258王子今《汉晋时代的“瘴气之害”》从病理学和生态学的角度论证了汉代人对“瘴气”致疫的了解[19]。西汉初年,人们已经体会到“瘴气”的危害。《史记》记载:吕后时期,发兵攻击南越,“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20]2969。建元六年(前135),汉武帝欲派兵攻闽越时,刘安劝阻曰:南方“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10]2779。刘安是淮南王,生活于南方,对南方湿热的丛林显然有一定的了解。建武二十五年(49)马援征武陵时,“会暑甚”,很多士兵因疫而死,马援自己也得病,为此,“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12]843。顺帝永和二年(137),象林叛乱,顺帝准备调军镇压,李固说:“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12]2838。永建四年(129),杨厚曾说:“今夏必盛寒,当有疾疫蝗虫之害”[12]1049。他根据以往的经验以及当时天气的变化断言将有灾疫发生,后来果然发生了蝗灾与疫灾。也就是说,在杨厚看来,气候的某些变化可能会引发疫灾。曹植也曾说:“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17]3294-3295现代医学认为,在湿热的环境下,昆虫与微生物非常活跃,人如果在其中活动,很容易感染这些昆虫所携带的病原体。例如疟疾就是通过蚊虫传播的,而蚊虫在湿热的环境下非常活跃。刘安、李固、杨厚和曹植等人的看法是比较符合我们今日的科学常识的。
(四)饮食不当
《内经》中记载:“乱于肠胃,则为霍乱。”[21]汉代人所谓的“霍乱”与现代医学所讲的霍乱是不同的。从撰者把霍乱归于肠胃类可以看出,似乎时人认为此病与饮食有关。对此,范行准先生指出,“夏日或热带地区,食物易腐”,容易引发汉代人所谓的“霍乱”,即“急性肠胃炎或食物中毒”[22]。张仲景对这类疫病有较为明确的看法,他在《金匮要略》中明确指出,“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23],并在《伤寒杂病论》记载了以“饮食不节,寒热不调,清浊相干,阴阳乖隔”而导致的“霍乱”,其症状为“呕吐而利”[24]。可见,时人已经意识到,饮食不当有可能致疫。
三、汉代的抗疫措施
对于汉代的抗疫措施,学术界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张剑光、邹国慰在《略论两汉的疫情特点和救灾措施》中说:“两汉统治者采取了帝王自责,给医药,施钱财,开仓赈济,安葬死者,隔离病人等措施。”[25]王文涛在《汉代的抗疫救灾措施与疫病的影响》中指出,汉代采取了“发放药物,医治疫病,强制隔离病人,安葬死者,控制疾疫传播”以及“减免田租赋税,施放财物,开仓赈济,安辑流民,节用抗灾”等措施[26]。王福昌《汉代南方疫灾、疫战与空间叙事》从“直接救治、研究认识、灾前预防和舆论引导”四个方面对汉代南方的疫战措施进行研究[27]。这些论述有不足之处。张剑光文中并未论及罢免丞相或司徒,“开仓赈济”也不准确,而应该是赈济老弱,且疫灾赈济似乎不对所有人。王文涛文中亦未区分“开仓赈济”与赈济老弱,“发放药物”与“医治疫病”笔者以为可归为一类。王福昌文中所论的“研究认识”与“灾前预防”应视为汉代的日常行为,并非疾疫发生后的应对措施。考之史籍,笔者以为汉代有明显针对性的抗疫措施主要有:君王自责与罢免丞相或司徒、驱鬼、减免赋税与赈济老弱、医疗救助以及隔离病人等。
(一)君王自责与罢免丞相或司徒
汉代人认为,君王犯错会引发上天降下灾异以示谴责,那么君王自责就成为必要的抗疫措施了。汉文帝在后元年(前163)曾因“水旱疾疫之灾”下诏检讨自己是否有过,曰:“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10]128。初元五年(前44),汉元帝因有灾疫下诏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众僚久旷,未得其人”[10]285。鸿嘉二年(前19),汉成帝因“水旱疾疫之灾”下诏罪己[10]317。东汉桓帝也曾下诏曰:“比岁不登,民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盗贼征发,南州尤甚。灾异日食,谴告累至。政乱在予,仍获咎征。”[12]317
时人眼中的天谴不仅针对君王的过失,也可能针对三公。西汉前期鲜有三公因灾异而被问责。西汉后期因灾异问责或罢免三公时,疫灾被视为灾异的一种,并不区别对待,而被免的三公多为丞相。如:汉元帝时,丞相于定国因疫灾“上书谢罪”,后因“春霜夏寒,日青亡光”而“上书自劾”[10]3043-3045;永始二年(前15),丞相薛宣被免,其原因除了“疾疫死者以万数”之外,还有“变异数见,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以及“人至相食,盗贼并兴,群职旷废”等[10]3393;绥和二年(前7),丞相翟方自杀,其原因除了疫灾之外,还有其他数种灾异[10]3422-3424。东汉时,废丞相,置司徒。王小明在《东汉三公因灾异被免现象考论》中指出:东汉时期,“因灾异免三公已经成为一项正式的政治制度”“太尉多因天文灾异被免”“司空则多因水土灾异被免”,因疫被免的三公多为司徒[28]。笔者认同这样的看法,如:延熹四年(161),司徒盛允在疫灾发生后不久被罢免[12]308;建宁四年(171),司徒许训因“大疫”被罢官[12]332;光和二年(179),司徒袁滂也在“大疫”后不久被免[12]342;光和五年(182),司徒陈耽也因为“大疫”而被罢免[12]346。《汉书》中有:“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10]722疫灾伤害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而司徒的职责对象是人,东汉疫灾后罢免司徒当与此有关。
(二)驱鬼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汉代人多以为疫是鬼造成的,那么驱鬼也就成为解决疫灾的重要办法。时人多以一种被称为“大傩”的仪式驱疫鬼,主要方式有:击鼓、用扫帚除不祥、用“桃弧棘矢”射鬼以及用其他各种武器斩杀各类恶鬼等。郑玄对《礼记》中大傩有注曰:“此月之中,日历虚、危,虚、危有坟墓四司之气,为厉鬼,将随强阴出以害人也。”[11]735因为有厉鬼出来害人,所以要举行“大傩”驱鬼。高诱对时人如何举行“大傩”有简要的介绍,他在对《吕氏春秋》中所载的“大傩”(2)《吕氏春秋》中记载一年中有三次不同形式的“大傩”,分别是:季春时,“国人傩”;仲秋时,“天子乃傩”;季冬时,“命有司大傩”(参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第122页、422页、615页)。作注说:“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驱除是也”[29]。《后汉书》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当时举行“大傩”的情形:“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皁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乘舆御前殿”,众人说一段驱疫言辞后,“因作方相与十二兽儛。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洛水中”[12]3127-3128。从中可见汉代的“大傩”参与人员多、规范宏大、仪式复杂,费用想必也很高。张衡在《东京赋》中也描述了“大傩”场景,其中主要活动有用工具扫除不祥、用“桃弧棘矢”射鬼以及其他各种方法斩杀各类恶鬼[30]。与先秦时期相比,虽然东汉的“大傩”由每年三次减少为每年一次,但是东汉官府非常重视,即使在“阴阳不和,军旅数兴”的财政困难之时,也如期举行,只是规模减小,即“减逐疫侲子之半,悉罢象橐驼之属”[12]424。据此可知,驱鬼是汉政府定期举行的重要抗疫活动。
(三)减免赋税与赈济老弱
严重的疫灾导致平民家破人亡,此时,灾民根本无力承担赋税,减免赋税也就有了积极的意义。当疫灾来临时,汉政府能够积极采取措施,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如: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有诏曰:“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10]256;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关东饥疫,“上乃下诏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税”[10]3171;顺帝永建元年(126),“疫疠水潦,令人半输今年田租;伤害什四以上,勿收责;不满者,以实除之”[12]253;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荆州发生疫情,“尽除荆州民租税”[31]1121。面对灾民,仅仅是减免赋税是不够的,要想恢复生产与生活,还需要其他措施。如:安帝元初六年(119),对灾民“赐棺木”[12]230;顺帝永建元年(126),面对受疫灾民,下诏曰“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贞妇帛,人三匹”[12]252;建安十四年(209),曹操下令,因为疫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31]32;建安二十三年(218),对面疫情,曹操下令,“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廩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31]51。据此可知,疫灾发生时,政府有可能采取减免赋税的措施,而赈济灾民时,受惠之人往往是无“基业”或几乎没有劳动力的老弱之人,没有惠及普通百姓。究其原因,应该是疫灾只对人造成伤害,并不会直接破坏庄稼,当百姓的庄稼或财产没有受损时,政府一般不会对有劳动能力的百姓提供生活补助。这从发生水、旱、蝗等破坏庄稼的灾害时,政府开仓赈济所有灾民也能窥知。
(四)医疗救助
疫情暴发时,医疗救助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应对措施。汉代政府也积极采取医疗救助的方式来对抗疫情。如:安帝元初六年(119),会稽发生疫情,“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12]230;桓帝元嘉元年(151),“京师疫疾,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12]296;灵帝建宁四年(171),“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12]332;灵帝熹平二年(173),“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12]334;灵帝光和二年(179),“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12]342。史籍中记载的很多汉代的疫灾并未说明政府是否采取医疗救助措施,然而,没有记载并不意味着没有,而可能是被史家所略。疫灾如果不及时处理,往往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汉代通讯与交通不发达,如果疫灾都要靠中央来处理,那是难以想象的,能对疫灾之民提供最重要帮助的是汉代各级地方官府。当时的地方官员也确实能主动采取医疗救助措施,如:建武十四年(38)会稽发生疫情时,钟离意“独身自隐亲,经给医药,所部多蒙全济”[12]1406;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军士大疫”,司马朗亲自“巡视,致医药”,自己却染疫而死[31]468。建武十四年(38)之疫见载于《光武帝纪》中,建安二十二年(217)之疫《献帝纪》中亦有记载,只是两帝王纪之中并未说明有医疗救助情况,而事实上,这两次疫情地方上均采取了积极的医疗救助措施。史籍中有传的地方官毕竟是极少数,所以,汉代地方政府积极为灾民医治疫病的行动多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不为世人所知。
(五)隔离
隔离病人是防控疫情的有效措施。在对微生物缺乏足够了解以及治疗手段较落后的秦汉时代,隔离显得尤为重要。秦人就已经把隔离病人纳入法律之中,《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关于隔离病人的记载:
“疠者有辠(罪),定杀。”“定杀”可(何)如?生定杀水中之谓殹(也)。或曰生貍(埋),生貍(埋)之异事殹(也)。(简121)[6]246
整理者认为此处的“疠”指的是麻风病。由简121可知,犯罪的麻风病患者应该投入水中淹死,当时有人认为应该活埋,然而活埋不符合法律规定。简122说明,犯罪之后,如果患了麻风病,应该被隔离,有人甚至认为应该将其杀死于隔离所。简123则说明,被判为修城或鬼薪(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引应劭曰:“取薪给宗庙为鬼薪也。”参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第227页。的麻风病患者应当被迁往疠所隔离。据此可知,在秦代,犯有传染病的罪犯依律应该被隔离于专门设置的“疠所”或被杀。是隔离还是杀死,应该取决于罪犯所犯之罪的轻重以及所患疾病的传染性大小。罪犯染疫会被隔离,普通人染疫想必也会被隔离。秦朝官府为了防止疫情扩散,采取的措施是非常果决而严厉的。
秦人将隔离写入法律之中,汉代人也了解隔离是有效的抗疫措施。汉平帝元始二年(2)疫灾暴发,有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10]353。政府专门腾空一些房舍用来安置病人,显然是为了隔离“疾疫者”。汉桓帝延熹五年(162),皇甫规讨陇右时“军中大疫”,“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12]2133。从“亲入庵庐”这样的描述可知,“庵庐”应该是专门用来隔离患者的地方。传染病的治疗手段主要有药物治疗和隔离,在医疗水平较为落后的汉代,隔离病人更显重要。
四、结语
疫情暴发后,汉代人因相信“天人感应”神学而错误地归因于统治阶层行为不当,因此君王自责,丞相或司徒被罢免,这不仅不能让灾民摆脱疫病之苦,反而会造成政局不稳,王莽甚至利用之以篡汉。恶鬼造成说使汉政府坚持每年举行规模宏大、参与人员众多、仪式复杂、费用庞大的驱鬼活动,这是对疫情没有积极作用的劳民伤财之举。所以,通过敬神与驱鬼抗疫是极为不妥并且非常危险的。
同时,汉朝政府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方法应对疫情。首先,向灾民发放医药、医治疫病,这是最直接有效的抗疫措施。如钟离意亲往抗疫,其所部有很多患者因此而愈。其次,汉代人意识到,隔离是防控疫情的有效手段,这是长期与疫情对抗摸索出来的正确办法。再次,疠疫发生后,汉政府采取减免赋税以及赈济老弱的措施,在减轻灾民生活压力的同时,既能够精准帮助最需要帮助之人,又能够避免因大规模开仓赈济而使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最后,时人已经意识到良好的卫生环境与饮食习惯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如曹植曾说,疫病对“被褐茹藿”“荆室蓬户”的穷苦之家威胁很大,而“殿处鼎食”“重貂累蓐”的人受疫病伤害较小[17]3294-3295。汉代这些行之有效的抗疫措施在后世得到很好的传承。历史证明,这是符合科学规律的积极抗疫措施。
古往今来,传染病不时地在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出现在世人面前,新冠疫情也是如此。充分汲取古代人抗疫的经验教训,科学抗疫,秉承我国自古以来积极抗疫的优良传统,对我们彻底战胜疫情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