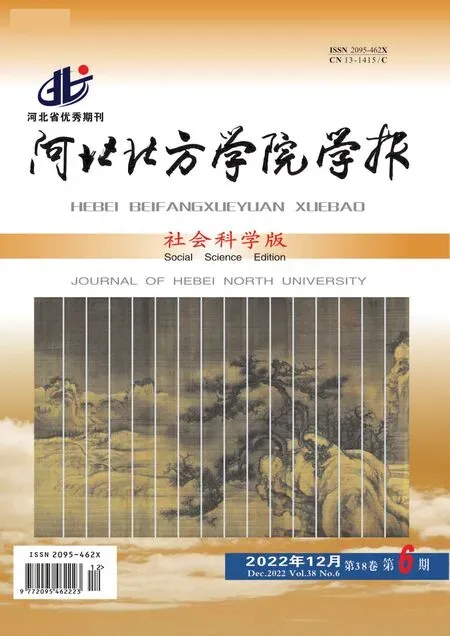论《词觏》和《词觏续编》的词律观
陶 风 风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傅燮詷(1643—1706),字去异,号浣岚,直隶灵寿(今河北灵寿)人,历任鲁山县知县、四川邛州牧、奉天治中和福建汀州府知府等职,著述颇丰。《词觏》始编于丙申春(1656),成书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共22卷,其中收录清初词人457家,词作2 000多首。该书现存6卷残本,词人64人,词作585首。《词觏续编》成书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现有22卷稿本,收词人474家,词作2 235首。从所收词人及词作的数量看,两书都可与《倚声初集》和《瑶华集》相媲美。顺康时期,“托体尊”与“审律严”使得清词中兴。傅燮詷在此期间编选《词觏》和《词觏续编》两部大型词选,并通过强调词律在词体中的重要作用来提高词体的地位。《词觏续编》的编纂理念与《词觏》一脉相承,但发现较晚,保存更为完整。下文结合《词觏》与《词觏续编》来完整探讨清初词坛背景下这两部词选的词律观。
一、破体、辨体与推尊词体
随着清词中兴时代的到来,词人逐渐打破“词为小道”与“诗之余”的禁锢,通过探讨词体的本质特征来提高词体的独立性。叶恭绰曾高度评价傅燮詷对词体的认识:“诚为通识至论,似较之后来论词作词者,反为中肯。如论调名音律等,尽高于万红友诸人。”[1]傅燮詷编纂《词觏》和《词觏续编》的重要目的是存史立名而非消遣娱乐:
其为是编也,特不忍以三十年罗猎之苦心,弃之败簏,徒饱鼠肠蠹腹,且亦可以少志当代名公先生悲歌慷慨、浅斟低唱之盛,以备他年采辑者之一脔耳。若幸而得传,则予三十载之苦心,亦庶可窃附于名公先生之绪余,而并籍以不朽云①。
傅燮詷肯定了词的传世功能,认为无论是因词存人还是因人存词,都是存史的一种手段,但更没有忽视词的抒情功能与感染能力:
虽然词亦难言矣,自湖上开山,花间萃锦,尊前兰畹,斗艳争奇,及有宋之时,词流代作,雾霨云蒸,周柳诸公,演增慢引,换羽移宫,体制日繁,新声竞起。南渡之后,姜、史以艷丽称奇,辛、刘以雄浑造极。较之汴京,殊不似诗家有初晚之分。故《花庵》《绝妙词选》又继《花间》而开《草堂》焉。夫艳思绮语,触绪纷来,士人若不能自己者。诚以具区之菁,五侯之鲭,并列盘餐,不妨与太羹玄酒杂进,而与诗文同脍炙人口也。况考古三百篇,皆可备之弦歌,是里巷歌谣、明堂、清庙,即古人之词。秦人一炬,风雅道亡。汉始创兴乐府,而乐府即汉人之词也。渐及于唐,而乐府又失其声,别为乐歌,如《清平》《阳关》《柳枝》《竹枝》《西河》《水调》《小秦王》《阿鹊盐》之类,大都绝句为多,是亦即唐人之词也。至于末造,乐部散佚,而词调渐出。词一出,而唐之乐歌又不传矣。宋末元兴,始有南北曲,则曲之声日繁,而词之声日失①。
傅燮詷在此论述了词的发展史,还从音乐方面探讨词的起源。他从破体的角度打破了诗词之间的界限,认为诗词同源,并将词的地位提升到诗的高度,甚至将《诗经》、乐府诗和唐诗当作词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同时,为保证词体的独立性,他又从辨体的角度挖掘词的本质特征。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傅燮詷看来,一代有一代的词。唐代末年兴起的词区别于之前文学形式的最本质特征便是出现了词调,“词调的形成标志着词体的成立,它不仅是曲调的确定、词格的建立,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创作规范和文本样式的确立,一种新文体的独立和自觉”[2]。填词应择腔选调,内容应与词调相配合,正如傅燮詷所言:“夫词寄兴耳,兴至则然,必曰此调因何事而摛。”[3]他明确表明腔拍的重要性,选词时也是以词调腔拍为首要标准,“惟作者代有其人,而选者亦世不一姓,然皆沿腔缀曲,按拍征辞。夫腔拍短长,每一成不变;情辞感触,率万绪而无穷”②。傅燮詷在抓住词本质特征的基础上进行辨体,并进一步指出诗词曲的区别在于用韵的不同。“唐人诗韵甚严,而词则出入。元人以入声分隶三声,而词必不可遵。”①词的用韵较诗宽泛,与曲相比不用遵循入派三声的规则。只有严格遵守词的特性,才能保证推尊词体的合理性。傅燮詷重视词律是为了推尊词体。“词律是词体的核心要素,直接关系到词体的破与立。”[4]但面对“词为小道”的现实,许多词人往往涉笔成趣,这使得词作往往不符词律。因此,傅燮詷认真谨慎地对待僻调。如他在《词觏》和《词觏续编》提及的自度曲以及犯调合调:
凡自度及合犯等,谱《初编》业已详言之。近日诸公更尚此种,佳篇佳句,割爱置之者甚多。盖缘宫调既已失传,宁慎无滥,矜新闻异徒,遗讥大稚,吾所不解。……总之,作词既失其声,则填者必不可失前人矩矱。若率意为长短句,而强名之曰词,则麞可代璋,鹿可为马矣,又奚其可。③
古来词体约略千种,即古人未有全填者,去古既远,本调亦不胜填,况其他乎?且合调如《江月晃重山》《月城春》,犯调如《花犯》《念奴》《玲珑四犯》之类,古人合之犯之之由,腔拍既已失传,正不必强作解事。好奇之家,如范仲闇自度之《花富贵》《风流社》,毛稚黄自度之《拨香灰》《双鸾怨》等合调,如顾梁汾之《踏莎美人》,李笠鸿之《携琴独上凤凰台》之类,果有当于古人之宫调否?果无乖于词中之腔拍否?吾未敢深信。即有佳思妙句,亦未敢采入①。
词作为一种音乐文学,产生之初便配乐演唱。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篇》中便谈到声律和谐的重要性,“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徵。夫宫商响高,徵羽声下;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廉肉相准,皎然可分”[5]384。“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则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5]385-386傅燮詷以宫调和腔拍作为选词的标准,“歌词所要表达的喜怒哀乐、起伏变化的不同情感中,也得与每一曲调的声情相谐会,这样才能取得音乐与语言、内容与形式的紧密结合”[6],忽略了宫调则无法准确反映出词体的原貌。
实现清词中兴的重要手段就是推尊词体。傅燮詷肯定了词能够“立言”的传世功能和感人心绪的抒情功能,从破体的角度肯定诗词同源,将词的地位提升到诗的高度,还从辨体的角度肯定词的独特性与独立性,进一步促进了词体的独立。
二、《词觏》和《词觏续编》的订谱功能
词在唐宋时期是配乐演唱的乐曲歌辞,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词的创作逐渐脱离了音乐,乐谱也因而失传。因此,按格律谱填词成为创作的规范。据江合友考证,“明代中后期始有编者制作以字声格律为主要内容的词谱,为词设立规范,为初学者指示门径”[7],这对清代词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清代,在词选编纂成风的同时,词人的格律意识进一步加强。《词觏》和《词觏续编》成书于康熙时期,这时的词坛呈现出“创作呈现繁盛之势、词学呈现中兴之象”[8]113-114的特征,词选具有“兼收并蓄的选心、多种多样的选型、徘徊于订谱与选词之间的体例”[8]146-153的特点,谱体型词选增多。《词觏》和《词觏续编》具备谱体型词选的特点,还具有订谱的功能,且两者不仅以选代谱,还能够通过谱体的特点以选正音。
(一)以选代谱
由于选词目的和编纂体例具有差异,因此词选有不同的类型。肖鹏根据词选的功能将词选划分为应歌、存史和立论3种。《词觏》和《词觏续编》兼具存史与应歌两种功能。在词乐失传的情况下,按谱填词是最好的选择。作为两部应歌型词选,《词觏》和《词觏续编》不仅具有词谱的性质,还有重要的订谱功能:
今所谓词者,不过存其格调之梗概而已。至于引商刻羽,求之宫调绝响之余,不啻扣盘揣签也。予固伤历代之宫商湮没废坠,不得复闻朱弦越瑟、一唱三叹之美,犹幸留此一线,以存宫商之遗音,政如靖节之琴,不必有弦而自得琴中意也。故兹集所载,既不能以声律求合古人,必以今词之句法字法求合于古词之句法字法。至其宫调律吕,愿以俟之知音①。
面对历代乐谱乐律亡佚的现实,傅燮詷提出了填词与选词的可行之道,即以“今词之句法字法求合于古词之句法字法”①来探寻宫商律吕的遗响。傅燮詷尤为喜爱词谱,“迨十四岁春,病疮伏枕,因捡得词谱,以遣闷郁,于是遂好之”②。对词谱的喜爱也体现在他所编选的两部词选中。因此,他以词谱为准则选词:
词之腔拍,失传已久,然以调俪名,以名定体,求其遗意于句读平仄间,思过半矣。稍有出入,便属支离。至于数体同名者,盖初无定格,各家度曲立名,偶尔相同,又或字句之内,参差不一,不过笔意偶然,非阙另是一体。今《啸余谱》《选声集》《词学全书》诸种,凡本是一调,多一字,少一字,即注为第几体。以予言之,良亦不必。今依沈天羽《四集诗余》例,必一人之作,小令长调名同而句法迥别者,始注为又一体,余悉不注。①
词既有定格,则平仄尚不可紊,况句读乎?近来坊刻词谱,率多任意更改,如《选报集》之《木兰花》,谓逐字可易平仄,而《连理枝》之“水晶帘外”“竹枝寒守”“羊车未至”,且于“外”字、“守”字上分句矣。《啸余谱》之《惜余春幔》亦属妄注,举一可例其余。而毛氏所刻《词学全书》,更是门外汉强作解事。唯万红友之《词律》最为精详,但云上入可代平。吾不敢尽信,学者慎之③。
傅燮詷把词谱作为判断词体的标准,他较为认可沈天羽《四集诗余》和万红友《词律》中对词体词律的划分标准,批评了《啸余谱》《选声集》及《词学全书》中轻易平仄与句读失误的问题。错误的平仄与句读会破坏作品原有的气脉,导致其读之不畅且观之不美。《文心雕龙·声律篇》中也有“迕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5]385的论述。傅燮詷认为,同一词牌不仅要追求平仄的和谐,还要符合句法的一致。面对同调中字数的差异,他并不以字数多少作为判断正体变体的标准,而是严格按照句法进行判断。只有同作者的词作句法迥别时,变体才可注为“另一体”。如朱彝尊《临江仙·枯荷》一词为效晏同叔体,与正体有别,故《词觏续编》标注“又一体”。傅燮詷在《词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审视词体词律的特点,他以句法来区分正体别体的作法比万树单纯以字数多少为准先进,但其否定“上入代平”的理论还需进一步商榷。
傅燮詷对《词觏》和《词觏续编》中不符合词谱的词作多加删削,即便有佳词丽句也一并不录。“及再为详阅,则有《鹧鸪天》用仄韵,而《酹江月》用平声者。或句法读法不依古谱者,既有佳词,实乖法则。兹所删者,大率类此。”①《词觏续编》便因此删去了491首词。如秦松龄《锁窗寒》一词:
料峭西风,个人独自,下帘庭院。镜里眉山,约略寒深寒浅。问凄凉、心情可宜,近来担阁闲针线。爱长宵久坐,绣窗微透,一丝烟篆。莫怨。韶华变。只一片霜华,清光堪剪。卖珠人去,剩有笔床诗卷。还猜他、翠袖熏笼,温黁宿火心字展。待相逢、月转阑干,秋水芙蓉面③。
在《钦定词谱》中,此调以周邦彦《琐窗寒·暗柳啼鸦》和张炎《琐窗寒·乱雨敲春》为正体。《词觏续编》中选录秦松龄的这首词应是周体,以周词衡量,则秦词中“个”“镜里眉山”“莫”“清”“卖”“还”以及“秋”诸处平仄不符合《琐窗寒》的平仄规范,故傅燮詷以“删”字标识。傅燮詷谨慎地以词律为标准选词,使《词觏》和《词觏续编》两部词选具有了标识平仄、词调、词韵以及字声的功能。
(二)以选正音
出于对词律的严格要求,傅燮詷在《词觏》和《词觏续编》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词韵及字声的要求,以期能够作出统一的规范。《文心雕龙·声律篇》中以《诗经》和《楚辞》为例说明方言和用韵的问题,“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取足不易,可谓衔灵均之余声,失黄钟之正响也。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5]387-388。傅燮詷十分重视词韵,强调正音的重要性,并认为填词“若一字不稳,必致棘喉”③,故必须严格按照词律,不能使用方音,用韵也不应过杂,并以此理念来选词。在他看来,只有使用标准的正音才能使词切合音律:
词原欲付之檀口,若一字不稳,必致棘喉。予昔在蜀,孝廉王子林云:“先有老伶,犹是蜀府子弟,能于洞箫中吹诗余数十调。若字稍差讹,则吹不成曲。”朱检讨竹垞亦云:“吴下有老山人,犹能长调数曲之腔。”惜二人皆死,予未及见。然天下大矣,岂无如二人者耶?安得逐调使歌之吹之,以律天下之音③。
傅燮詷征引王子林和朱彝尊之言,强调字声平仄对词的重要性,用字稍有差错则吹不成曲。他进而探讨词的用韵标准,虽然认为诗词同源,并将词的地位提升到诗的高度,但同时也指出诗词的区别是在于用韵的不同。为规范词韵,他编纂了《词韵印证》一书,可惜现已亡佚,无法深入考证。但通过只言片语便可以看出傅燮詷具有深厚的音韵学修养,特别是他还注意到各韵发音方法及发音部位的不同之处:
何以作一图辩开合甚严,而江韵甫数音,即开合相混。如是之类,不能强解。……奈中多北音,如东庚俱并括,则又非天下之通引矣。②
词生于诗而流为曲,则字句思致近乎诗固不必,似乎曲更不可,自有一段词之风味,介夫诗曲之间,其用韵亦犹是也。唐人诗韵甚严,而词则出入。元人以入声分隶三声,而词必不可遵。即宋诸名公,止当以汴京周秦为法。近日词人多不分开合,如真文与庚青及侵寻同用,元寒删先与覃盐咸同用是也。竟用乡音,如吴人读清为侵,燕人读弘为红,楚人读路为漏,晋人读风为分是也。称名手者,率多犯之,余可知矣。予昔纂《词韵印证》一书,颇极苦心。后见沈去矜《词韵》,与予大同小异,其辨开合,若合符节,则方音之不可用也明矣。兹用韵过杂者,遂多所删①。
由于方言并非通用语言,因此读者会有理解上的困难。而且每种方言的发音不同,也会产生讹韵谐声等问题。此外,韵的开合问题也会影响字声。“古代音韵学家根据韵头的不同,把韵母分为‘开口’和‘合口’两大类(古代只分开、合)。其区别是‘凡韵头是[u]或者是以[u]为主要元音的,就叫做合口呼;反之,凡韵头不是[u]或者不以[u]为主要元音的,就叫做开口呼’。”[9]元音不同,发音时舌位的前后和高低便不同,[u]属于后、高圆唇元音。当舌位发生变化,发出的音则会不同,韵部的归属便会发生变化,这会造成不押韵的现象。所以,用韵时要考虑到开合及方音等问题,避免因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不一致造成字声差异。
“审律严”是清词中兴的重要原因,对词律的严谨要求也成为选词人选词的重要标准。傅燮詷对词韵的谨慎态度正如徐釚的评论,“灵寿浣岚傅先生自幼喜倚声为长短句,审音于南北清浊之间,用心专一。有一字未安者,辄翻古人体制,叶其声之高下,必尽善乃已。故于填词一道,独能得其精奥”①,由此也可见其对词的用韵要求十分严格。
三、由重音律而树立周柳典范
因重视音律,傅燮詷在《词觏》和《词觏续编》中十分推举周邦彦和柳永两位词人。据统计,“两宋词人中居于前10名的十大词人依次是:辛弃疾、苏轼、周邦彦、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李清照和晏几道”[10]。其中,周邦彦和柳永二人工于填词,精通音律,创制新调,促进了长调慢词的发展。《词觏》和《词觏续编》中选录的词人与词作在透露出傅燮詷审美倾向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读者对词作风格和词律的接受与学习。傅燮詷在两部词选中表现出对周邦彦与柳永的认可,无形中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取法标准。《词觏》和《词觏续编》中不乏和韵之作。根据现存词作,可知两部词选中和韵前十的宋代词人(表1)。

表1 《词觏》《词觏续编》宋代词人和韵前十统计
虽然周邦彦与柳永在两部词选中的和韵数量不是很多,但傅燮詷多次合称周邦彦与柳永二人,并强调他们在创制新调与精通音律方面的重要成就:
周柳诸公,演增慢引,换羽移宫,体制日繁,新声竞起。①
周侍制增演慢引,换羽移宫;柳屯田广拓篇章,比声切律。此诗余之所由备也②。
周邦彦和柳永在宋词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11]。
小令之声律多有近于诗者,而慢词长调由于篇幅较大,其音律之转折变化自然较小令要繁复许多,音乐修养稍弱之人不敢轻易一试。而柳永兼具诗人与乐人的双重素质,在其与乐工歌妓的合作下终使慢词长调得以恢张。柳永所做慢词,不仅声律谐美,如上举《八声甘州》中那些由“对”“渐”“望”和“叹”等去声字所引领的词句,读来便有音节顿挫而又摇曳美听之感;而且笔法工整,总在铺叙之中显得层次分明,开合之间讲求首尾圆融。所以从宋至清,柳词虽以俗情俚语招致诟病,但其长调之工致、音律之精审却始终为人所肯定。至周邦彦,慢词长调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周氏妙解音律,曾提举大晟府,故其所创《六丑》《大酺》诸长调,平仄声律极为严格,并在柳永讲求去声的基础上又严分上、去,极尽四声之变化。同时,周邦彦对于长调中的勾勒跌宕、谋篇布局煞为讲究,将词之写作由自然感发状态推进到了精思结撰的境地[12]142。
《文心雕龙·声律篇》载曰:“练才洞鉴,剖字钻响,疏识阔略,随音所遇,若长风之过籁,南郭之吹竽耳。”[5]388刘勰在此讨论了文采与识音律的关系,并强调识音律的重要性。傅燮詷也认识到这一点,突出音律对填词的重要性,正如他评价柳永词“耆卿之残月晓风,韵生歌管”②。
词固小道,但文情易为格调所缚,辞义每为声律所拘,即倚马之才,谱不熟谙,填之正未易易也。况诗文家多以填词为降格,而经生家又视之为不急之务,是以涉笔成趣者多,耑工是道者少。兹集诸家,或多者至连篇累牍,或少者仅一二短章,端由于是。然王元泽之《倦寻芳》,未始不与《片玉》《乐章》同垂千古也①。
清词的发展离不开对宋词的学习,“词至清初,逐步走向中兴。而清词的中兴需要以对宋词遗产的总结和吸收为基础,宋词学便在这股清理、研究前代词学遗产的热潮中得以建立”[12]26。周邦彦和柳永在填词音律方面具有典型性,只有“入门须正,取法乎上”,才能在潜移默化中使读者加深对词律的了解与认可。
傅燮詷在《词觏》和《词觏续编》中从词调出发,强调词的本质特征。他严格按谱选词,对音律和词韵等方面的要求切合《文心雕龙·声律篇》中关于声调和韵律的理论。同时,他还推举周邦彦和柳永作为填词的效法对象。因此,《词觏》和《词觏续编》中关于词律观的主张有其合理性的存在,在清词中兴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影响也不应被忽视。
注 释:
① 选自敬睦祠藏家刻本《词觏》。
② 选自敬睦祠藏家刻本《绳庵杂著》。
③ 选自《词觏续编》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稿本。
——以乾隆时期《清绮轩词选》《晴雪雅词》《自怡轩词选》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