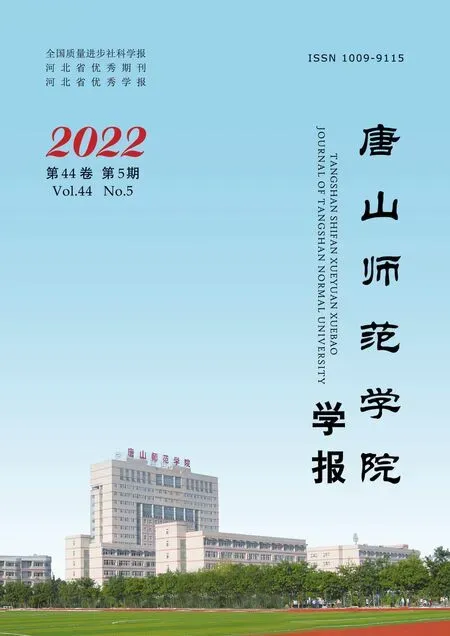《清平山堂话本》“得”字研究
王 怡
语言学研究
《清平山堂话本》“得”字研究
王 怡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明代洪楩编印的《清平山堂话本》口语性强,基本能够反映宋元时期的语言面貌,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在本书中,完备地保留了“得”字的各种用法,除出现在人名外中,包括作谓语动词、作助动词、作动态助词、作补语或结构助词构成述补结构以及以语素身份参与构词五种主要用法。根据677条有效语料,对《清平山堂话本》中“得”字的动态助词用法和构成述补结构用法进行详细描写,梳理“得”字的语法化过程,并归纳得出影响其语法化的多种因素。
《清平山堂话本》;“得”字;语法功能;语法化
《清平山堂话本》原名《六家小说》,由明代洪楩编印,是现存刊印最早的话本小说集。原书分为《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醒梦》6集,每集各10篇又分为上下两册,现仅完整保存27篇,又有2篇残叶。据前人考证,《清平山堂话本》虽刊印于明嘉靖年间,但其收录的话本小说多属宋元时期,可能只有3篇作于明代。
现存的29篇中,只有3篇使用文言,其余各篇均为通俗白话小说,语言质朴,口语性强,基本能够反映宋元时期的语言面貌。通过观察这29篇小说,可以发现《清平山堂话本》所收内容芜杂,除语言既有文言亦有白话以外,篇幅长短不一,题材多样,文字较为粗糙,存在不少夺文、脱文之处,可见编印者并未进行统一的修改润色,较多地保留了宋元时期的语言特点,能够作为研究宋元时期语言实际使用状况的重要语料。
“得”字作为学界探讨研究的重要对象,其来源、词性、语法化过程等一直是重要研究内容,并且仍然存在着不少争论。但正如沈家煊先生所说,“在历时线索还不明朗的情况下,可以先把精力集中于考察一个词在某一共时平面的各种具体用法,通过共时分析来‘构拟’历时演变过程,然后用历史材料来验证和修正”[1]。在历时性研究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作为其基础的共时性研究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清平山堂话本》中“得”字使用频率较高,使用状况情况复杂,形式亦多种多样,而现有的语言学研究有关“得”字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动态助词及结构助词,对“得”字的其他用法功能有所忽略。本文通过归纳整理“得”字在书中不同的语法分布及功能,对“得”字进行共时层面上的系统研究,从而证明“得”的历时变化在共时层面上的语言变异。
根据统计,《清平山堂话本》中“得”字共有677条有效语料,除用于人名外,主要有五种用法,分别是作谓语动词、助动词、动态助词、构成述补结构以及参与构词。由于《清平山堂话本》中“得”作动态助词用法较为特殊,构成述补结构用法全面且具有代表性,现主要针对这两种用法展开论述。
一、“得”作动态助词
近代汉语中使用的动态助词有“了”“着”“过”“将”“取”“得”等,其中“得”字用作动态助词,表示动作的完成或动作、状态的持续。王力[2]、曹广顺等[3]认为动态助词“得”产生于唐代。自先秦起,“得”用于取义动词后,表示借助某种动作得到某物或某一结果。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字前不限于取义动词,形成结果补语结构。唐代开始这一结构使用频率提高,“得”字逐渐虚化成为表完成或持续的动态助词。
在《清平山堂话本》中,动态助词“得”出现67次,多位于动词之后,尤以动词“听”后为常,构成“V得”格式,句法位置灵活,其后有无其他成分均可。只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与实现,而并不表持续。如在以下例句中,“得”字相当于“了”,出现于已然语境中,其后可接名词性成分“书”、数量短语“一声”和“五里地”,亦可单独出现于动词之后起修饰作用。
(1)山前行,道:“殿直,如今台意要如何?”(《简帖和尚》)
(2)宇文绶展开看,读了词,看罢诗,道:“你前回做诗,教我从今归后夜间来,我今试过了,却要我回。”(《简帖和尚》)
(3)小娘子则,掩着面,哭将入去。(《简帖和尚》)
(4)是冬日,时,纷纷雪下。(《曹伯明错勘赃记》)
全书只有一例动态助词“得”位于形容词之后,即例句(5),表示性质的实现,意为多了一贯钱。
(5)这里,与你这媒人婆买个烧饼,到家哄你呆老汉。(《快嘴李翠莲记》)
动态助词“得”构成的“V得”格式易与述补结构“V得”混淆,“得”字不再具有实在意义,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与实现,其前动词不限于取义动词,与前后成分语义联系较弱,且语音形式弱化,可与动态助词“了”替换时,“得”字为动态助词,而非作述补结构中的补语或结构助词。
二、“得”字述补结构
正如蒋绍愚所说,在汉语语法史上,述补结构的产生是一件极具意义的大事,它使得汉语的表达更为精密。唐代出现了真正的述补结构,唐以后迅速发展,得到普遍使用。“得”字述补结构中,“得”字既可作补语,亦可作结构助词,这两种不同用法的“得”字有不同的来源,但目前仍存争议。王力、蒋绍愚等人认为作补语的“得”字源于连动式“V得(O)”[4],而祝敏彻等人则认为作结果补语的“得”源于表获得的“得”,可能补语的“得”源于表可能的“得”[5]。关于结构助词“得”的来源,学界一般认为是由表获得义或完成义虚化而来。《清平山堂话本》中“得”字述补结构中的“得”作补语或结构助词这两种用法均有,下面对其进行详细讨论。
(一)“得”字作补语的述补结构
根据语义类型,根据结构中“得”字意义及功能,把“得”字作补语的述补结构划分为结果补语和可能补语。主要表现形式为“V得(O)”“V(O)不得”和“V不得(O)”。
1.“得”作补语的结果补语结构
唐宋时期,“V得(O)”格式能产性较强,到现代汉语中基本已经消失。结果补语结构中,当前一动词为取义动词时,“得”字具有较强的实义,表示动作行为的结果,而当前一动词非取义动词时,“得”字意义较虚,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或实现。《清平山堂话本》中,该结构共89例,多用于已然语境中,语义指向其前动词本身。“得”前动词多为单音节及物动词,如“听、讨、寻、支、吃、借、夺”等。
结果补语结构不带宾语,构成“V得”格式,如“讨得”;带宾语宾语构成“V得O”格式,宾语形式多样,可以是单个名词,如例(7),可以是定中短语,如例(8),也可以是数量短语,如例(9)。
(6)时,千万送来。(《简帖和尚》)
(7)相公明镜,小人在五里头,并不知贼情。(《曹伯明错勘赃记》)
(8)宣赞再抱了卯奴,耳边。(《西湖三塔记》)
(9)忽一日,,在昭庆寺弯,选个吉日良时,搬去居住。(《西湖三塔记》)
结果补语结构“V得(O)”的否定形式有三种,即“V(O)不得”“V不得(O)”和“不V得”,与肯定形式不完全对称。多用于否定已经实现或完成的动作行为与结果,也可用于假设句中否定尚未发生的动作行为与结果。例句(10)“借不得”与肯定式“借得”对举使用,表示说话人的假设语气。
(10)你去,与,便回,免交我记念。(《董永遇仙传》)
(11),忽然跌倒。(《死生交范张鸡黍》)
(12)纵然,修得个小佛儿也罢。(《快嘴李翠莲记》)
2.“得”作补语的可能补语结构
关于其中“得”作补语的能性述补结构中的“得”字的性质,朱德熙先生认为:“‘说得’是能说的意思,‘说不得’是不能说的意思,这种类型的‘得’和‘看得见’里的‘得’性质不同。‘看得见’里的‘得’是中置的助词,‘说得、说不得’里的‘得’是动词。‘说得’实际上应该分析为:说得得,前一个‘得’是助词,后一个‘得’是充任补语的动词,只是因为两个‘得’语音形式相同,所以把助词‘得’省去了。”[6]因此,“得”作补语的能性述补结构中的“得”确切地说应是受副词“不”修饰的助动词。
“得”作补语的可能补语结构共67例,多用于疑问、假设等语境中,述语由单音节及物动词、双音节动词、动词性短语和形容词等充当,如“留、去、劈、打、吃、怨、奈何、开船”等。
(13)倘若大限到来,身归泉世,命染黄沙,如何?(《张子房慕道记》)
(14)他如何?(《杨温拦路虎传》)
可能补语结构带宾语时,宾语包括名词、代词、定中短语、数量短语等,形式多样。
(15),。(《简帖和尚》)
(16)若是恼咱性儿起,揪住耳朵采头发,扯破了衣裳抓碎了脸,漏风的巴掌顺脸括,扯碎了网巾你休要怪,擒了你四鬓。(《快嘴李翠莲记》)
(17)你若,他养你家一世,不用忧柴忧米了。(《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18)你见静山大王,。(《简帖和尚》)
“得”作补语的否定式能性述补结构与其肯定式基本对称,主要形式有“V不得(O)”和“V(O)不得”,但否定式的使用频率远高于肯定式。
(19)我年纪高大,。(《合同文字记》)
(20)如,你便离了我这里去休!(《杨温拦路虎传》)
(21)罢,罢,我两口也老了,,只怕有些一差二误,被人耻笑,可怜!可怜!(《快嘴李翠莲记》)
(22)一住三日,风胜大,。(《错认尸》)
“得”作补语的能性述补结构表示的可能义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主观是否具有进行某种动作行为的能力,二是客观条件及情理上的是否许可。例句(16)是说话人认为听话人若惹怒自己后而遭受打骂,情理上不可以怨恨自己,例句(19)是指说话人自己因年纪大,主观上不具备远走投奔别人的能力,而例句(22)则是因大风这一客观原因导致不能开船。
3.“V得(O)”凝固形式
《清平山堂话本》由“得”作补语的述补结构中,不少“V得(O)”形成了凝固程度不等的词或固定结构,按照所表示的语义内容,将其分为四类:表认知与感觉、表情形、表须要、表主观性。
表认知与感觉的凝固形式有“认得”“晓得”“觉得”“记得”等,都与其在现代汉语用法功能基本相同,如:
(23)我官人,在我左近住。(《西湖三塔记》)
(24)我儿,我了。(同上)
(25)娘娘醉了便上床去睡着。(《洛阳三怪记》)
(26)将及二更,忽闻梢人嘲歌声隐约,后两句曰:有朝一日花容退,双手招郎郎不来。(《刎颈鸳鸯会》)
表情形的凝固形式有“见得”“了得”“免得/免不得”“少不得”等,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是“见得”,经常和疑问代词“怎”组合构成“怎见得”,表达反问语气,如例(27);“了得”用来表示某种情况不平常以及某人能力很突出的同时,流露出说话人的赞赏、钦佩之情,如例(28);“免得/免不得”“少不得”与现代汉语用法相同。
(27):百禽啼后人皆喜,惟有鸦鸣事若何?见者都嫌闻者唾,只为从前口嘴多。(《西湖三塔记》)
(28)杨玉道:“且告爹爹,这汉会使棒,!”(《杨温拦路虎传》)
(29)只除害了这蛮子,方才人知。(《错认尸》)
(30)如此数次相推,张客见林上舍再三再四不受,去写一张领状来,与林上舍。(《阴骘积善》)
(31)饥餐渴饮,夜住晓行。(《杨温拦路虎传》)
表须要的凝固形式只有“消得”一例,具体表示须要进行某一动作行为,可作句子谓语,也可作副词修饰谓语成分,但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再使用。
(32)你是胡说,便做供养,也不多,必有缘故。(《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33)大娘只顾倚着自身正大,全不想周氏与他通奸,故此要将女儿招他,若还思量此事,只打发了小二出门,后来不见得自身同女打死在狱,灭门之事。(《错认尸》)
表主观性的凝固形式有“不见得”“巴不得”“恨不得”“使不得”。本书中“不见得”带名词性宾语,做句子谓语成分,不同于现代汉语中作副词,修饰谓语动词,如例(34);“恨不得”与“巴不得”意义基本相同,相当于“等不及”;“使不得”表示说话人委婉的建议或劝阻。
(34)王酒酒被骂,大怒,便投一个去处,有分叫乔家一门四口性命——能杀的妇人,道底无志气,胡乱与他些钱钞,也此事。(《错认尸》)
(35)每日早起赶程,身生两翼。(《死生交范张鸡黍》)
(36)打发我出门,你们两口得零利。(《快嘴李翠莲记》)
(37)!既嫁了我家,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二)“得”字作结构助词的述补结构
结构助词“得”无实在意义,可将之视为述补结构的语法标记,关于其来源问题,众说纷纭,但一般都是从表获得义或完成义的“得”字虚化而成这个角度来进行解释的,其所构成的述补结构主要表现形式为“V得(O)C”和其否定式“V不得(O)C”。本文采取杨平所作的分类[7],把带结构助词“得”字的补语分为结果补语、状态补语、趋向补语、程度补语和可能补语五类。
1.“得”作结构助词的结果补语结构
结构助词“得”构成的结果补语结构全书共出现8例,表示某一动作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述语主要是单音节动词,补语类型有指示代词、主谓短语、动宾短语、状中短语。
(38)你不要瞒我,这病思量老婆了,气血不和,以致。(《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39)这官人不幸父母早亡,只单身独自,自小好学,。(《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40)且说李小官人想这莲女,。(《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41),命仆取笔,作一只词,词寄《虞美人》,乃写于楼中白粉壁上。(《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
(42)住了两年,财本。(《错认尸》)
以上五个例句中,结果补语结构的格式为“V得C”,“如此”“着了床”“大醉”“文武双全”“一空”都是前行动词“害”“吃”“学”“使”所造成的结果。
(43)时,无甚相谢你,待你百年之后寿终,我夫妻二人与你带孝,如母亲一般断送。(《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44)稍公,你与我问巡检夫人,若肯将此妾与人,我情愿与也多些才礼,讨此人为妾,了,我把五两银子谢你。(《错认尸》)
例句(43)和(44)中的述补结构的格式为“V得OC”,吴福祥提出判定此类结构,用介词“把”将宾语提至动词前,可以看出补语与宾语不存在直接的语法关系,而是动作行为的结果。如“教得我会”中,“会”并非“我”发出的动作,而是动词“教”所造成的结果;“说得此事成”中“成”并非“此事”发出的动作,而是动词“说”的结果。
2.“得”作结构助词的状态补语结构
“得”作结构助词的状态补语结构共有140例,侧重于描摹动作呈现出怎样的情态或状况,主要表现形式为“V得(O)C”,按照述语的词性、音节数量、补语类型及是否带宾语,将其分为以下几种:
(1)V+得+形容词
在这种格式中,述语主要由单音节动词充当,如“生、下、脱、剃、说”等,只有2例双音节动词作述语。
(45)且张二官是个行商,多在外,少在内,不曾,就下盒盘羊酒,涓吉成亲。(《刎颈鸳鸯会》)
(46)匈奴,诸军催战,广怒气上马,与虏交锋。(《汉李广世号飞将军》)
状态补语为形容词,包括单音节形容词、双音节形容词、形容词重叠式,如:
(47)上头之后,越觉。(《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48)且是。(《五戒禅师私红莲记》)
(49)头儿,那个不叫一声小师姑。(《快嘴李翠莲记》)
(2)V+得+短语
这一格式中,述语多为单音节动词,形容词性质述语较少,充任状态补语的短语根据性质可分为名词性短语和动词性短语。
A.补语为名词性短语
名词性短语性质的状态补语用例较少,全书只有4例。
(50)年去月来,看看长成十六岁,,有十分颜色。(《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51)那杨温却离他庄,更,思量道:“我妻却在这里,我若还去告官,几时取得?不如且捉手中一条棒,去夺将来!”(《杨温拦路虎传》)
B.补语为动词性短语
由动词性短语充当的状态补语中,有动宾短语作补语的、状中短语作补语的、述补短语作补语的、联合短语作补语的:
(52)女儿不是夸伶俐,从小。(《快嘴李翠莲记》)
(53)枷梢在上道士头向下,拿起把荆子来,。(《简帖和尚》)
(54)本妇,只说:“不!不!不!”(《刎颈鸳鸯会》)
(55)方二十五岁,,人材出众。(《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
(3)V得OC
带宾语的状态补语结构中,根据动词、宾语与补语三者之间的语义关系,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述语为形容词或不及物动词,宾语既是动词施事,又是补语成分的施事。
(56)只为一个冤家,。(《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57),不敢回对。(《戒指儿记》)
由于宾语在语义上是述语动词的施事,两者之间存在陈述关系,因而可以变换语序为“OV得C”,如“急得夫人眼泪汪汪”变为“夫人急得眼泪汪汪”。
第二类是述语为及物动词,宾语既是动词受事,又是补语成分的施事。如例句(59)施事主语为皇甫殿直,匈奴是动词“掿”的受事宾语,又是其后补语成分的施事主语。
(58)当时。(《曹伯明错勘赃记》)
(59)皇甫殿直,去顶门上屑那厮一扌暴,道:“好好的把出来教我看!”(《简帖和尚》)
第三类是述语为及物动词,宾语是动词受事,与补语成分无语义联系,补语修饰动词。如例(60)“五更”为动词“打”宾语,补语成分“紧”修饰动词,描摹动词“打”的状态,与宾语没有直接语义联系。
(60)收拾停当慢慢等,看看。(《快嘴李翠莲记》)
3.“得”作结构助词的趋向补语结构
这种结构的趋向补语只有1例,补语为趋向动词“去”,表示的是位移的事物和说话人立足点间的位置关系。本句的立足点并非施事主语“待诏”和“染坊博士”所处的位置,而是说书艺人立足于西湖这一位置,“去”表示宾语“水”背离立足点向取水之人所在位置移动。
(61)那装銮的待诏,堆青叠绿,令别是一般鲜明;那染坊博士,阴紫阳红,令别是一般娇艳。(《西湖三塔记》)
4.“得”作结构助词的程度补语结构
学界通常根据述语性质与结构语义功能的不同区分状态补语和程度补语结构,认为状态补语结构侧重于对动词的状态进行描摹,程度补语着眼于对述语动词或形容词所达到的程度进行补充说明。但正如赵长才所说,程度补语所表示的动作行为达到的程度,“广义上讲,这种程度(幅度)也是一种结果状态”,两种结构有相通之处[8]。因此他提出了界定程度补语的狭义标准,即存在起修饰作用的表示程度高的程度副词的补语是程度补语。《清平山堂话本》中,受“好”“越”“甚”等程度副词修饰的形容词性成分必然是程度补语,只有3例。
(62)宣赞,你!(《西湖三塔记》)
(63)当日雪,周氏在房中向火,忽听得有人敲门,起身开门看时,见一人,头带破头巾,身穿旧衣服,便问周氏道:“嫂子,乔俊在家么?”(《错认尸》)
(64):脸衬桃花,比桃花不红不白;眉分柳叶,如柳叶犹细犹弯。(《刎颈鸳鸯会》)
5.“得”作结构助词的可能补语结构
“V得C”能性述补结构可以视为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的可能式,表示实现某一动作行为、结果或位移的可能性。因此,不表示可能性的“V得C”结果补语结构和趋向补语结构又被称为实现式述补结构。朴元基认为能性述补结构是“从实现式的语境变体逐渐语法化而独立的形式”[9],也就是说,可能式述补结构与实现式述补结构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大多用于假设、疑问等未然语境,而后者用于已然语境。
《清平山堂话本》中,“V得C”能性述补结构只有11例,出现在述语位置上的多为单音节动词,如“吃、说、赶、忍、寻、禁”等,基本由形容词和动词作补语。
补语性质为形容词的只有1例,“吃得多少”带有反诘语气,实际上意为吃不了多少,即吃得不多。
(65)量你一个老人家,。(《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作补语的动词除一般行为动词外,还有不少为趋向动词,如“上、下、去、住、出来”等,表示实现某种位移或结果的可能性。
(66)去也不多时,若是小员外行得快,便也。(《洛阳三怪记》)
(67)山前行山定看着小娘子生得怎地瘦弱,怎,怎地讯问他?(《简帖和尚》)
(68)那船主人排些酒饭与乔俊吃,那里。(《错认尸》)
例句(66)为假设语气,是说潘松如果走得快就能够赶上翁三郎。“禁得打勘”和“吃得下”出现于疑问语境中,其前有疑问代词“怎”和“那里”,表示反诘语气,表达了说话人对“禁得打勘”和“吃得下”所具备的可能性的否定态度。
“V得C”能性述补结构的否定式为“V不C”,只有1例,与肯定式对举使用,表现陈辛对寻见妻子这件事的不确定态度。
(69)只说陈辛去寻妻,未知。(《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这种结构还有一种“V得OC”格式。判定“割舍得他去”与趋向补语结构中“取得这水去”两例的性质,只能依据句子语境的已然性与未然性来进行。
(70)这妇人怎生?(《刎颈鸳鸯会》)
(71)那草寇怎,斗无十合,一矛刺镇山虎于马下,枭其首级,杀散小喽罗,前来迎敌。(《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例句(70)“割舍得他去”,“他”为动词“割舍”的受事宾语,同时又是补语成分“去”的施事主语,而在例句(71)中,草寇为动词“敌”施事主语,陈巡检作动词受事宾语,补语“过”修饰动词,两者联系紧密,因此“敌得陈巡检过”可改为“敌得过陈巡检”。
6. 述补结构“V得C”凝固形式
“V得C”格式的述补结构语义、结构较为凝固的只有“休得C”一种,共出现5次。“休得”意为不要、别,表示禁止或劝阻,命令色彩较强,语气强烈。
(72)姆姆要惹祸,这样为人做不过。(《快嘴李翠莲记》)
(73)二位大人慢慢吃,坏了你们牙!(《快嘴李翠莲记》)
三、“得”字语法化过程及原因
《清平山堂话本》中“得”字的用法十分完备,通过上文对几种用法的描写与分析,可以看到“得”字语法化的大致过程及影响其语法化的因素。
“得”最初为实义动词,本义为获得、取得,可单独作句子谓语。受到汉代为动补结构的产生提供基础的“V1+V2”连动式的影响,动词“得”的句法位置得以改变,具有了置于另一动词后的可能性。由于“得”自身词汇意义的影响,最初通常被置于取义动词后,构成“V得(O)”格式,但仍表示获得义。随着前一动词不再局限于取义动词,可以出现非取义动词,“得”的意义虚化,由获得义演变为达到或实现义,语义不再指向宾语而是前指动词,“V得(O)”格式由连动式演变为述补结构,“得”成为补语成分。
曹秀玲认为,“得”字达成义的出现为“V得(O)”分流成为状态补语(即本文所说的结果补语)和可能补语提供了前提,因为“‘达成’可以指现实中的‘达成’,也可以指意念中的‘达成’(即可能)”[10]。又因为所出现语境的不同,结果述补结构与可能述补结构得以真正分流。出现在疑问、假设等未然语境中,“V得(O)”的是可能述补结构,而出现在已然语境中的则是结果述补结构。
(74)只今吃饭成火,吃水成火,如何。(《敦煌变文集》)
(75)蒙世尊慈悲,。(《敦煌变文集》)
同为“救得阿娘火难之苦”,例句(74)前有疑问代词“如何”,从而表示“救”这一动作尚未发生,是可能述补结构,而例句(75)则是说这一动作已经发生,当为结果述补结构。
在长期的使用中,“得”由达成义进一步发展为可能义,这种发展使得“V得(O)”可能述补结构能够脱离语境来表示可能。
(76),,经商买卖诸般会。(《快嘴李翠莲记》)
“V得(O)”结果述补结构中“得”语法意义进一步虚化,演变为表示动作完成或动作、状态的持续。在《清平山堂话本》中,动态助词“得”表示动作完成,基本等同于完成体助词“了”。由于典型的完成体助词“了”最早见于宋代[11],因而其他动态助词如“得、却、将、取”等得以长时间频繁使用。现代汉语中“得”作为动态助词的功能已经消失,一方面是因为“得”所承担的功能过多,容易造成混淆,另一方面则是动态助词“了”已经十分稳定,可以完全取代“得”字表完成的动态助词功能。
组合成分的变化同样对“得”的语法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V得(O)”述补结构中宾语成分性质从体词性到谓词性的转变,促使“V得C”述补结构的产生,“得”字意义进一步虚化,发展为不具有实际意义而只有语法意义的结构助词。
在整个语法化过程中,“得”呈现出一种“边缘化”趋势,即不再作为结构焦点,承担中心功能。动词“得”作句子谓语时,处于结构的中心位置。位于动词前作助动词时,“得”成为句子谓语动词的修饰成分。在句法位置转移至谓语动词后,形成“V得(O)”格式,随着意义虚化的同时,“得”字与前一动词的关系愈发紧密,两者由最初具有同等的语法地位转变为“得”地位虚化,逐渐依附前一动词。而在“V得(O)C”述补结构中,“得”完全演变为语法标记,不再具有实在意义。
四、结语
《清平山堂话本》基本保存了“得”于宋元时期的所有用法。除出现在人名中,本书中“得”主要有五种用法,即作谓语动词,作助动词,作动态助词,作补语或结构助词构成述补结构以及以语素身份参与构词。动词“得”表示获得义、致使义与经过(一段时间)义;助动词“得”位于谓语动词前,表示客观条件或者情理上的许可或因主客观条件导致某一动作发生的可能;动态助词“得”由“V得(O)”结果述补结构进一步虚化而来,表示动作的实现或完成。“得”作补语构成的述补结构,主要表现形式为“V得(O)”“V(O)不得”和“V不得(O)”,可分为结果补语结构和可能补语结构;结构助词“得”构成的述补结构,补语可分为结果补语、状态补语、趋向补语、程度补语和可能补语五类,以状态补语为多;两种述补结构中都存在一些凝固程度不等的词或短语,如“认得”“晓得”等。语素“得”的构词能力较强,所构成的词有动词“得知”“得罪”“得志”、形容词“得意”“不得已”和副词“只得”。
动词“得”的语法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V1+V2”连动式的大量应用使得动词“得”句法位置改变,孕育了语法化的可能。前一动词范围由取义动词扩展至非取义动词以及“得”与前一动词之间语法地位的改变,加之自身词汇意义的影响,致使“得”由最初表获得义,虚化为表达成义,再发展为表可能义。在“V得(O)”结果补语结构中,“得”进一步虚化为表示动作完成或实现的动态助词,但由于自身功能繁多以及与动态助词“了”的适用范围相同而在现代汉语中消失。受到组合成分性质从体词性到谓词性演变的影响,“得”字最终演变为没有实际意义只有语法意义的结构助词。
[1] 沈家煊.实词虚化的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J].当代语言学,1998,37(3):41-46.
[2] 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15:429.
[3] 曹广顺,梁银峰,龙国富.《祖堂集》语法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72-80.
[4]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196-199.
[5] 祝敏彻.“得”字用法演变考[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60,19(S1):49-61.
[6] 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35.
[7] 杨平.带“得”的述补结构的产生和发展[J].古汉语研究, 1990,3(1):56-63.
[8] 赵长才.汉语述补结构的历时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99.
[9] 朴元基.《水浒传》述补结构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7: 242.
[10] 曹秀玲.“得”字的语法化和“得”字补语[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8(3):82-85.
[11] 吴福祥.重谈“动+了+宾”格式的来源和完成体助词“了”的产生[J].中国语文,1998,47(6):452-462.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 "De" in
WANG Yi
(College of Art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9, China)
compiled by Hong Pian in the Ming Dynasty ha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spoken language. It can basically reflect the language features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has important linguistic value. In this book, the various usages of the word “de” are completely reserved, including five main usages of predicate verb, auxiliary verb, dynamic auxiliary word, complement or structural auxiliary word to form predicate complement structure and morpheme in word formation. Based on 677 valid data,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parts of speech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the word “de” is given into sort out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word “de”. Various factors influencing its grammaticalization are also summarized.
; the character “de”; grammatical function; grammaticalization
H109.3
A
1009-9115(2022)05-0026-08
10.3969/j.issn.1009-9115.2022.05.005
2021-10-18
2022-07-04
王怡(1998-),女,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词汇学。
(责任编辑、校对:郭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