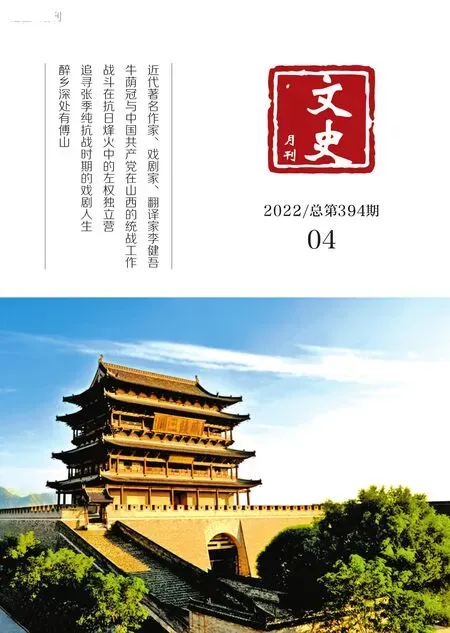梨花落尽成秋色
武海燕
山西省太原市钟楼街一带,曾经有多少晋剧名家登台献艺。一颦一笑,衣冠魅影;举手投足,倾国倾城。
“永远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台湾诗人席慕容的一首《戏子》,写尽了戏剧演员的妆后人生。世人只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的华彩,却很少知道他们的身世遭遇。旧社会艺人社会地位低下,生不能受尊敬,死不能进祠堂。学艺的除梨园世家子弟,其余大多是极其贫苦、身世可怜的孩子。现在的孩子们,生长在“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21世纪,学艺的多是家境优越的孩子,与旧社会简直天壤之别。由于篇幅所限,本文艺海撷英,仅以几位戏曲名家的故事与读者共同品读他们的飘零身世,瞻仰人物风流,感受时代变迁,歌颂盛世华章。
“抽的顺风烟,看的丁果仙。”少年听《空城计》,以为丁果仙是位老先生。再听《捉放曹》《太白醉酒》,仙风道骨,大气豪迈,仿佛诸葛再现,李白复生。后来才知道创造了晋剧须生“丁派”唱腔的艺术家丁果仙,原来是女儿身。
丁果仙(1909—1972),原名丁步云,艺名果子红。据考证,丁果仙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王口镇翰林庄村的钱流风家,从小生活艰难,三岁丧父,到处沿街乞讨,四岁时被卖到邻村丁凤鸣家。后来当地遭遇饥荒,丁凤鸣只好举家到太原投亲。六岁时,养母也去世了,养父就把她送给兄弟丁凤章的儿子做童养媳,不久“丈夫”也去世了,她就做了丁凤章的养女。丁凤章后来又捡回来一个孩子,取名丁巧云,成为丁果仙的姐姐,两个女孩和隔壁妓院的小红一起玩耍,有一天,小红被妓院的人活活打死了。丁凤章告诉俩姐妹,家里生活艰难,要不学戏,要不去隔壁做妓女。丁果仙跟养父说:“我要好好学戏,挣大钱,好好孝敬爹,养活爹。”丁凤章就把这个有主意的孩子送到了晋府店双胜和女科班(山西第一个女科班)学戏。没过多久,山西很多地方发生瘟疫,政府下令不让聚集唱戏,她只好回老家跟上孙竹林老师学戏,改学须生。晋剧中把“胡子生”这个行当称做“红”,“果子红”就成了丁果仙的艺名。丁果仙身世悲苦,却很有志气,特别要强,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她每天披星戴月地练功。为了演好须生,她认真观察男士的声情举止,经常女扮男装,头戴礼帽招摇过市,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尽管挨打受骂,她仍然咬紧牙关苦练基本功,终于在小演员中崭露头角。学了五六个月,居然能到泰山庙票儿班里唱票。当时会唱戏并不稀罕,但即便是名角儿,如果不被请到泰山庙,就不算红。客串了一年半,丁果仙又去了荣梨园戏班子“科班”学戏。但她在泰山庙太受欢迎了,在班子里唱了三个月,就被泰山庙的班主千呼万唤地请了回去,又唱了一年半的票。1921年,丁果仙去了庆梨园戏班(后改名为众梨园、聚梨园)。1922年,丁果仙进入祁县城赵村的众梨园戏班。她的表演俊逸脱俗,嗓音高而不挑,亮而不破,气息流畅,清晰纯正,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丁派”唱腔艺术。十五六岁时,丁果仙已经红遍山西,誉满张垣(张家口),名驰京津。京沪名流听说了丁果仙,都争着一睹她的风采。上海、北京的百代公司相继邀请她录制唱片。她多次赴京津演出,与京剧大家马连良、谭富英等人广泛学习交流,开拓艺术视野,丰富表演手段。“果子红”驰名京津,红极一时。



尽管如此,旧社会艺人地位低下,经常遭受欺辱。每每丁果仙刚唱完戏,当地地痞就不让她走了,人身安全成了头等大事。1925年冬,丁果仙嫁给了经常保护她的商人冀午斋(祖籍平遥小胡村)作妾。1927年冬天,冀午斋为丁果仙成立了錦艺园班社,自任班主,名震三晋。阎锡山特别爱看丁果仙的戏,每个月都会把戏班请去唱戏,冀午斋也因此积累下一点人脉。然而造化弄人,情深义重的冀午斋于1934年为了搭救朋友而入狱去世。冀午斋去世后,丁果仙成为班主,后来嫁给了冀的朋友任秀峰。1936年,丁果仙在天津北洋戏院演出一个月,合同期满,老板却以各种理由不让离开,并雇用流氓打手拦路闹事,要求赔偿两千银元“损失”。惹不起地头蛇,丁果仙师徒只好花钱买平安,白白辛苦了一个月的演出。1937年七七事变后,丁果仙不愿为日本侵略者唱戏,于是洗黛从农,在忻县归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果仙参加了太原新新晋剧团并担任团长,她与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新凤霞、张君秋、周信芳、常香玉等全国著名艺术家一起参加了赴朝鲜和福建前线的慰问演出,展现出了一名艺术家的爱国情怀。1952年,丁果仙的《打金枝》《蝴蝶杯》等剧目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荣获政务院颁发的表演一等奖。毛主席、周总理看了《打金枝》,都夸她把唐代宗演活了。毛主席说:“《打金枝》是很有意义的戏。你演的唐代宗很有气度,有风采。唐代宗这个人虽然治国无能,却懂得干部政策,他处理家庭矛盾是有办法的。”伟大领袖的鼓励,使丁果仙更加努力精进,无论唱腔还是表演,都有了更高更新的突破。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丁果仙主演的《打金枝》搬上了银幕。1956年,她再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当场为毛主席清唱了晋剧移植剧目《屈原》里的“橘颂”。1959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帮助国家渡过难关,她先后两次交纳了各一万元的党费,两次主动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爱国忧民之心,天地日月可鉴。为了培养更多的艺术人才,丁果仙于1962年捐资创建了山西戏曲学校并兼任校长。在创办戏校的同时,她收徒传艺,扎实培养了一批新的晋剧名家。丁果仙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常委,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于1972年正月初二去世。作为晋剧丁派艺术的奠基人,丁果仙的功绩将永载我国戏曲史册。
牛桂英(1925—2013),生于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小张义村,原名月英,乳名英子。小时候家里一穷二白,等英子长到六岁,家里就养活不了她了,无奈之下就给人做了童养媳。九岁时,“婆家”也困难得过不下去了,好在英子有一副好嗓音,就拜了李庭柱师傅(艺名二牛旦)学艺,后来又进入祁县娃娃班,先学须生,后改青衣。她苦练基本功,风雨无阻,在台上唱得字正腔圆、走得端庄大方、演得细腻优雅,深得名家喜爱,十三岁便与著名艺术家盖天红、十四红、毛毛旦(以上都是艺名)等同台,当小配角。十四岁初登舞台时,扮演《拣柴》中的姜秋莲和《游花园》中的梁凤英,主攻小旦和青衣。由于练得太刻苦,牛桂英不慎练坏了嗓子。但她并未就此服输,积极向前辈讨教,总结出一套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即嗓音含而不破,声情并茂,低回婉转的“云遮月”牛派唱腔,受到广大戏迷的狂热追捧。1940年起,牛桂英随戏班在北京、张家口、包头、绥远一带演戏。1944年,牛桂英与丁果仙在张家口首次合演了《清风亭》《四进士》《芦花》等戏,享誉晋冀蒙。两位艺术家珠联璧合,联袂演出的《打金枝》《坐楼杀惜》《走山》《八件衣》《九件衣》《蝴蝶杯》等,脍炙人口。她们合作演出二十余年,成为一对晋剧舞台上的“情侣”。

牛桂英是国家一级演员,擅长青衣、小旦两个行当,有“晋剧皇后”之称,作品有《断桥》《教子》《祭江》《狐狸缘》《赠剑》等120多部。1950年,牛桂英与丁果仙第二次合作,在大中剧院献演了《坐楼杀惜》《走山》《桑园会》《四郎探母》《女中孝》《蝴蝶杯》等戏。1952年,牛桂英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得演员二等奖。1954年,牛桂英应长春电影制片厂之邀,拍摄了戏曲舞台艺术片《打金枝》。1961年至1962年,牛桂英与丁果仙合演的《走山》赴北京展演,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她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省晋剧院副院长、名誉院长,山西省戏曲学校校长等,并带出不少弟子,可谓桃李芬芳,名满天下。1986年,牛桂英作为名誉院长随省晋剧院青年团赴香港参加中国地方戏曲展演。1988年退休后仍经常参加舞台演出,2013年6月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宁可误了吃饭,也不能误了程玉英的《情探》”“宁愿跑掉老贝(婆)的鞋(hai),也不能误了程玉英的咳咳咳”“宁可跑得蹶(jue,意思是累)死(se),也不能误了程玉英的哭恻”。这三句晋中人民耳熟能详的话,生动反映了晋剧名家程玉英当年的“火爆”程度。程玉英生于平遥县梁赵村,祖父程遵濂系晋商巨贾,并因兴学助教有功,清廷诰授学政衔。不幸的是,父亲程福荣染上毒瘾,变卖家产,还把大女儿卖给别人当了童养媳。幼小的程玉英眼见也难以生活下去,又不愿受委屈当童养媳,就去了戏班子学艺。她十岁时拜晋剧艺人“说书红”(高文翰)为徒,初学须生。十三岁时,程玉英随师进京演出,为应急救场,在《二进宫》中饰李艳妃,一炮打响,遂改攻青衣。不料备尝艰辛、学徒十年,却在十四岁时坏了嗓子,唱不了高音,这可急坏了热爱唱戏的程玉英。但师父“说书红”并不甘心,他结合程玉英的嗓音特点进行点拨,聪明的程玉英又借鉴了“洋冰糖”(艺名)的说唱方法,巧妙加入民间说唱,苦练八年,终于以时而欢快活泼、时而缠绵悱恻的“咳咳”腔,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俗话说,名师出高徒。程玉英不但有名师“说书红”的教导,还经常得到师姐丁果仙的指点。她最初表演《走山》时扮演清廉高官曹正邦的女儿曹玉莲,只见她在舞台上步履轻盈,形象温柔美丽,落落大方,自以为演得不错,谢幕以后却受到了丁果仙的批评:此时此刻,曹玉莲不是享清福的千金小姐;此情此景,她是一路逃过追杀,仆人冻死,爬过雪山去找未过门夫君的苦命人,其状态应当是悲愤交加、忐忑不安、苦不堪言,怎么能轻松而过,举重若轻?一语点醒梦中人,从此程玉英更加注意揣摩剧中人物不同时期的心情和状态。20世纪30年代初,程玉英随师在太谷锦梨园与盖天红、三儿生、毛毛旦、秋富生、丁果仙等同台演戏,以《武家坡》《火焰驹》《双官诰》《女中孝》《清风亭》等风靡剧坛,后来又与丁果仙等人进京联袂演出,受到马连良大师的指点,功力大进。她和丁果仙被北平观众誉为“山西两个女戏王”。

日军占领太原后,有的日本军官看了程玉英的戏,就让她去陪“打牌”。程玉英不去,师父的中华大戏园就遭到打砸抢。无奈之下,她嫁给翻译赵雪岩作妾,自己暂别舞台,同时也能保护戏园不受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平遥县委、县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深情挽留下,程玉英担任了平遥群众剧团的团长,后来又去了榆次专署晋剧团。1953年4月,她去太谷康复医院慰问朝鮮战场上回来的伤员,和伤病员深情拥抱。她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程玉英。鉴于她的突出表现,组织批准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0年,程玉英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她表演的《算粮》《秦香莲》《情探》《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劈山救母》等,感情真挚,朴实深沉,深深感染了广大观众。程玉英情商高、人品好,“文化大革命”中受的冲击小,改革开放后,又培养了一大批梨园子弟,2011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2015年5月去世,享年九十六岁。
张美琴本姓王。那怎么就更名换姓了呢?说来话长,1919年,张美琴出身于河北一户铁匠家庭,后因兵荒马乱,又遭了灾荒,只好流落山西。父母正要把她卖了当“童养媳”,幸得名演员筱金梅引荐,她才开始了戏曲生涯。为了不辱“王氏门风”,张美琴随母改姓张,到了太谷“富庆社”向师傅刘玉富(艺名“玉石娃娃”)学戏,艺名为“富艳亭”,约定“五年学艺,一年谢师”。不到一年工夫,在师傅的悉心传授下,张美琴便学会了《赐环》《杀府》《斩子》《走山》等戏。第二年,刘师傅应丁果仙之邀带领全社人马到“锦梨园”戏班演出。张美琴眉目秀丽,品貌端正,能勤学苦练,还有一副好嗓子,没过多久就唱红了。“锦梨园”名家荟萃,张美琴认真向盖天红、丁果仙等名家学习,跟随师傅刘玉富和子都生、彦章黑、筱金枝、筱金梅及“富”字辈门徒,征服了晋冀两省观众;在北平“吉祥剧院”连演数月,场场爆满,盛况空前;又在天津劝业场“天华景”演出一年,广受欢迎。张美琴在演出中不断钻研磨砺,吸收融合各派精髓,十七岁时就已能在戏班挂“头牌”须生。她扮相美、嗓子冲、做派细腻、气度不凡,深受观众喜爱。晋中一带的观众给她起了个“赛果子”的外号,意思是赛过“果子红”丁果仙。张美琴出师后,住太原“荣梨园”戏班。她同程玉英、周瑜生等合演的《打金枝》《走山》《桑园会》等,倾倒无数戏迷,曾有一天之内连演四场《走山》的记录。正当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兄长和父母相继辞世,张美琴悲伤过甚便唱不出来了。后来,她在丈夫张宝魁的指导下,刻苦学习武戏,并融合京剧、河北梆子的艺术特色,艺术表现更加丰富。抗战时期,张宝魁夫妇在太原“鸣盛楼”和老十四红、盖天红、筱桂桃等名家同台演出,直到太原解放。张美琴文武兼备,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筱派艺术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美琴担任了太原市三个晋剧团的总工会主席。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时,张美琴和牛桂英、郭凤英、冀美莲、王明甫演出《打金枝》,荣获个人表演二等奖,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总理亲自给她们颁发奖状奖章并合影留念。1956年,张美琴参加了赴朝慰问团,受到志愿军的热烈欢迎。
张美琴和张宝魁一生琴瑟在御,相互鼓励、相互切磋,她冲破了女须生只能文不能武、只重唱不重表演的“禁区”,主演的《法门寺》《周公桃花女》《封神榜》《薛仁贵征东》《昭君出塞》《芦花河》《十五贯》《四进士》《二堂舍子》《走山》《定军山》《金沙滩》《窃符救赵》《蝴蝶杯》等剧目,一度成为经典,并在《张羽煮海》《春香传》《孔雀东南飞》等剧中反串小生,轰动一时,形成了唱做俱精、文武兼擅的“张派”须生艺术风格,使古老的晋剧表演艺术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将自己在《凤台关》《芦花河》等戏中的绝招传授给武忠、李月仙、王秋玲、高翠萍等晚辈。张美琴于2009年6月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位享誉三晋的刀马花旦,名叫程玲仙。这样又美又仙又飒的角儿,身世却异常可怜。程玲仙于1935年生于山西省和顺县,因父亲染上毒瘾,她被卖给了别人,后来又被转卖了三次,做了童养媳。当了童养媳还吃不饱,又在10岁时投靠程全虎为养父。老程虽在戏班,但唱功一般,收入微薄,程玲仙只好白天唱戏,晚上靠练几招学来的武戏沿街乞讨。程全虎看女儿如此刻苦用功,又善解人意,想让她出人头地,于是带她投奔了榆次的新生剧团,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来吊嗓子。玲仙不识字,养父每日要教唱词到晚上一点多。养父急于求成,达不到要求的水准,就拿鞭子、棍子打她,累得程玲仙几次吐血,一气之下就跳了井。幸亏是枯井,小玲仙又有武功基础,养父赶紧找人把她救上来,倒也没落下什么毛病。养父含着泪对她说:“不受苦中苦,难能学成艺,名艺人都是从这条路走出来的。”在养父和师父们的严格教导下,玲仙首次演出《凤台关》《双锁山》就获得好评。遇到牛桂英等名角在榆次演出,爱学习的程玲仙就跟着场场去看。这一看不要紧,她看出门道来了!除了学牛桂英,她又向程玉英等名家学习,在声线上扬长避短,在表演上体味剧中角色,成为多才多艺、角色丰富的一代名伶。尤其是《小女婿》,尾音拖腔挽花,曲调优美动人,在榆次连演四十多场,场场爆满。她以《游西湖》中李慧娘的“就地十八滚”“桌子上下腰”等特技,手舞“阴阳扇”,翻滚大喷火,接连表演六十余次高难特技,受到程砚秋、田汉等名家的好评,在山西省第二届戏曲观摩汇演中力拔头筹,荣获演员一等奖。1984年6月,程玲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5年10月,程玲仙主演的《游西湖》参加了全国中老年戏曲汇演,荣获全国梨园“宝中宝”杯牡丹奖(一等奖)。
程玲仙是国家一级演员,曾在中南海汇报演出,在中央戏剧学院讲学,受到过中央首长的接见,但她一直都很谦虚低调。可能是因为儿时遭遇了太多苦难,新社会的每一天,程玲仙都感到无比幸福;别人对她的点滴帮助和建议,她都要拿东西或从言语上感谢人家。她说,是党的关怀和培养给了她力量。程玲仙于1999年11月去世,终年64岁。这个刀马花旦,以其与众不同的义气、勇敢和勤奋,树立了一座艺术和人生的丰碑。
有一天,太原市猪头巷太平戏(科)班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榆次小孩,他再三恳求戏班收留自己,不要工钱,有饭吃就行。戏班师傅们见这个小孩虽然又脏又臭,但眼神明亮,反应机灵,就收留了他。这个孩子就是高文翰,他生于光绪七年(1881年),父亲早亡,随母改嫁后,倍受继父打骂,十一岁时,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就跑到太原投靠了太平戏班。小文翰不畏严寒酷暑,刻苦练功记词,十四岁就以《斩黄袍》《走边》《三疑记》唱红太原。1894年,一个张家口戏班班主来太原,偶然看了高文翰的演出,感到这个小孩能给他带来不菲的收入,就买通土匪把他劫持到张家口,强迫卖艺。两年后,高文翰因变声无法再唱,班主见无利可图就把他抛弃了。回到家后,继父成天挖苦,高文翰立志出人头地,更加发奋图强,努力认字读书,自创了说唱流派,人称“说书红”。他曾与丁果仙、狮子黑、盖天红、老三儿生等名家,在锦梨园、堃梨园、荣梨园、自成园等班社演出。他精通武戏,兼通文戏,能演各类男角,既能在《空城计》《天水关》中扮演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也能在《高平关》《卖华山》中表演马上帝王赵匡胤。他表演《教子》《黄鹤楼》《清风亭》时,观众人山人海,场面欢声雷动。他对艺术精益求精,曾与马连良、袁世海等切磋技艺。
高文翰是传统戏曲改革的代表人物,一生共创作、整理、演出戏剧百余部,并结合演出效果改进剧情,塑造出了各类人物形象,如《空城计》中的诸葛亮,《观阵》中的秦琼,《高平关》中的赵匡胤,《杀院》中的宋江,《斩黄袍》中的高怀德,《法门寺》中的赵廉等等,所演作品脍炙人口,誉满京津冀。旧时艺人讲究门派,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说法,因此传艺不多,但高文翰却乐于培养人才,先后收了刘桂英、程玉英等“九英”,还接收了丁果仙、乔玉仙“二仙”,可谓名师高徒,桃李芬芳。1947年,高文翰因病在石家庄辞世。
乔国瑞(约1883—1957)出身贫苦,十一岁入梨园,立志“学艺不成,决不回家面父”。他刻苦学艺,先后在寿阳福庆园、介休禄梨园学花脸。由于扮相威武,声如洪钟,逐渐在《草坡》《捉放曹》《玉虎坠》等戏曲中成名,人称“狮子黑”(太谷一带方言,黑与吼同音)。后来又到锦梨园、自诚园、锦艺园等班社学艺,走到哪里,周边观众就跟到哪里。“狮子黑”台风端正,不管晴天雨天、城市农村、人多人少,表演都很认真卖力。他塑造的鲁智深、曹操、董卓等角色,深受廣大戏迷热爱。
乔国瑞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和平等思想的艺术家。七七事变后,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多次资助民兵购置武器,为根据地购买布匹、食盐、火柴、纸张等奇缺物资。他支持独生子乔荣华参加革命,冒死为太行二分区购买食盐、布料及其他物资;在戏班安插地下党员,还让女儿传送情报。1947年,儿子乔荣华(时任民主政府太谷六区副区长)光荣牺牲;女儿乔喜云为解放区传送情报被阎军活活打死。一双儿女为国捐躯,乔国瑞本人也被捕入狱。他拒不交待“秘密”,敌人一直关押不放,幸得朋友多方保释才出狱。悲愤交加的乔国瑞将自己收入的1/3捐献给了革命事业。看过电影《霸王别姬》的人,对旧社会小戏子的苦难都略有了解。1948年前后,一些太原艺人生活无着,他毅然变卖家产,组织“有饭同吃、有难同担”的众梨园,与大家共渡难关。太原解放后,乔国瑞马上率团为解放军义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当选为山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2年随团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乔国瑞为人慷慨,不计得失,在戏曲界德高望重,曾担任新华剧团副团长。第一届山西省政协委员。1957年,乔国瑞因病逝世,华北戏剧界隆重悼念。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逢国庆,总能听到电视机前传来那熟悉又动人的旋律。这首穿越时空的《我的祖国》,已经红了七十多年,它的主唱郭兰英,一位来自山西平遥的老艺术家,饱受过解放前生活的辛酸,才对新中国那样地充满热爱、充满自豪,那样地饱含深情。
别人的童年是童话,郭兰英的童年是噩梦。1930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香乐村,那是一个戏剧之乡。她家特别贫困,兄弟姐妹十二个,有的被卖了,有的饿死病死了,最后剩下仨姐弟。穷得实在活不下去,父母就把郭兰英丢在村外的野树林里。幸运的是,郭兰英的姑姑刚夭折了一个孩子,听说兰英子被扔了,就赶紧跑到野树林里,把奄奄一息的孩子带回了家。郭兰英童年时,同村郭羊成教他家的童养媳唱戏,旁边的兰英子一听就会了,郭师傅觉得兰英子是块唱戏的料,就经常教她学戏。“小时候练功,晚上枕着脚睡,把脚翻起来翻到后边睡觉。前半夜左腿,后半夜师父用棍子敲着头喊‘换腿换腿’,天亮后整条腿拿下来的时候,都没有知觉了。”稍有走神或不到位,小兰英就要挨打。但她都咬牙坚持着,因为她知道:要想人前显贵,就要人后受罪。后来,她几经辗转到了榆次,十三岁时就能挂头牌登台。宽广的音域,大气的唱腔,一唱便是万人空巷。她在《明公断》中扮演的秦香莲,在《坐楼杀惜》中扮演的阎婆惜,在《金水桥》中扮演的银屏公主,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1946年,郭兰英投奔我部队文工团。1956年,电影《上甘岭》拍摄完成,乔羽作词、刘炽作曲的主题曲《我的祖国》,通过郭兰英的深情演绎,唱遍了祖国大地。1986年,郭兰英告别舞台,卖掉家产,在广州番禺区创办了“郭兰英艺术学校”。2020年春晚,九十岁高龄的郭兰英不惧疫情肆虐,再次唱响《我的祖国》,亿万海内外中华儿女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要看花艳君的《孔雀东南飞》,先得准备下手巾巾擦眼泪”。花艳君的身世,比《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还苦。她从小就成了孤儿,没有人知道她从哪里来,只知道她大约是1928年生,六岁时被卖到晋剧艺术家邱凤英门下当养女,并随养父姓王,叫王玉贞,小名丑妮。然而好景不长,疼爱她的养父王凤鸣在演出时遭到垂涎邱凤英美貌的恶霸突袭,命丧黄泉。无奈之下,邱凤英只好嫁给商人作妾,不料在大老婆的欺辱下含恨九泉。丑妮决心出人头地,再也不受欺负。在姥姥的严格要求下,聪颖过人的丑妮学会了很多东西。她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每天天不亮就去练功,练得不对就要挨打。她初学刀马旦,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一学就会,有板有眼,七岁便能和丁果仙同台献技。十二岁时,因为腿上受了伤,她开始转型唱青衣。十四岁时,王玉贞在鸣盛楼演出平生第一部青衣戏《三娘教子》,一票唱红。邱家所在的榆次郝村老秀才春生大爷为她起名花艳君,从此成为她的艺名。花艳君博采名家之长,先后跟随过筱桂桃、牛桂英、丁果仙、乔国瑞、高文翰等老艺术家学艺。花艳君成名之后依然注重向省内外名家学习。1956年,花艳君参加全国戏曲演员讲习会,如饥似渴地向梅兰芳、程砚秋等大家学习,并向郭兰英、常香玉等新一代艺术家学习唱腔,还学习了音韵学文化知识,戏路更加宽广,她在《急子回国》《二堂舍子》中塑造的形象拿捏准确,演绎到位,成为晋剧经典。她结合旧社会女性的悲惨遭遇,把女性的痛苦表演得入木三分。1984年,我省举办“振兴晋剧”四省调演,由“三英一君”(牛桂英、郭凤英、程玉英、花艳君)进行示范交流演出。花艷君扮演《三上轿》中的“崔秀英”,三哭三别,唱尽了杀夫之恨别子之痛,唱出了洞房复仇的勇敢和悲壮。
邱家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与地下党多有往来,花艳君的两位舅舅曾因掩护地下党活动被捕,她早就对中国共产党充满向往。1956年公私合营,她将价值两万元的戏箱上交国家,并于195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我省首批入党的戏曲艺术家。花艳君体恤孤儿,经常为儿童福利基金会集资捐款。为了给剧团大楼筹集资金,她白天组织大家在工地干活,晚上组织大家在舞台演出,还亲自表演节目,时间长了就把嗓子累坏了。“钉鞋靠掌子,唱戏凭嗓子”,无奈之下,她只好去实验晋剧团辅导排练,在她的带领下,《汾水长流》《送肥记》《新媳妇》《琼花》等现代戏相继演出,誉满三晋。“文化大革命”时期,她和丈夫受到不公正对待,但她始终对党一片赤诚。她在晚年常画松梅,并以此自喻。山西古籍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了《花艳君评传》,封面为著名画家王木兰老师创作的仕女图,华茂春松,荣曜秋菊,仿佛年轻的花艳君,她永远活在艺术的花间。
明清时期的平遥曾是“海内最富”,但后经历战乱,商号凋敝,光靠种地根本吃不饱。1937年,邱金兰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沿村堡,没多久父亲就去世了,薄田不够种,粮食不够吃,母亲只好带着她沿街乞讨。终于熬到了解放,她家分到了地。村里有唱秧歌的一个小团体,她就经常去跟着唱。十五岁时,邱金兰拜交城秧歌艺人“文明丑”为师,刻苦学习文化艺术,在舞台上崭露头角。从小因自卑而口吃的邱金兰,到了舞台上却字正腔圆,尤其是《偷南瓜》,人见人爱,场场爆满。平遥人喜欢得不得了,给她起名“盖平遥”,意思是整个平遥县没有人能唱过邱金兰。由于是半路出家,她的功底没有自小科班出身的戏曲名家们深厚。但她扬长避短,认真学习了程玉英的“咳咳腔”,使晋剧和秧歌完美结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特色。1955年,邱金兰加入榆次秧歌剧团,成为剧团中唯一的女演员。在1956年和1959年的全省戏曲调演中,她两次荣获一等奖。1958年,在全省文艺调演中,她主演的《偷南瓜》荣获特等奖。由其主演的传统秧歌剧《卖高底》《小姑贤》《不见面》《苦伶仃》及现代秧歌剧《李双双》《李二嫂改嫁》《焦裕禄》等,受到广大群众喜爱。
邱金兰热爱戏剧,非常珍惜舞台生涯,经常不顾身体忘我工作,二十八岁就做了卵巢切除手术,术后又投入到艺术的舞台上。1970年,榆次秧歌剧团撤销,邱金兰被迫去商店当了服务员。1979年,在领导的支持下,邱金兰和大家共同努力,恢复了榆次秧歌剧团,邱金兰被任命为团长。她重新感受到了党的光辉和温暖,更加悉心传艺,忘我工作。1982年,因劳累过度,邱金兰在排练场上与世长辞,时年四十五岁。
刘仙玲,生卒年不详。自小被家人遗弃。一位名叫刘永聚的老清道夫收养了她。吃遍了生活的苦,小仙玲决心出人头地。她从小喜欢唱戏,8岁就拜“北田旦”王增山为师。刘仙玲嗓音晶莹剔透,被观众起名“梨儿脆”。加之聪颖过人,一学就会,生旦净末丑,演谁像谁,表现出极高的艺术天赋。《坐楼杀惜》中的阎惜姣,《算粮》中的王银钏、《穆桂英挂帅》中的穆桂英、《打金枝》中的金枝等等,都是她的经典之作。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刘仙玲扮演的金枝获得演员三等奖。刘仙玲两进北京、九进怀仁堂,清亮明丽的风格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评。她在《日月图》《火焰驹》《茶评计》《金水桥》等剧中的表演也皆是上乘。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刘仙玲善于观察生活,把握人物特点,唱腔情真意切,表演恰到好处,得到丁果仙等名家的称赞。刘仙玲老师与世无争,从容淡定,在业界口碑极佳,德艺双馨。她后来任职于山西戏曲学校,兢兢业业,培养了大批新秀。
时光倏忽,往事如烟。除了高文翰、乔国瑞两位苦出身的男儿,丁果仙、牛桂英、程玉英、张美琴、程玲仙,都是童养媳出身,郭兰英、花艳君、邱金兰、刘仙玲曾是弃儿、乞儿,他们历尽坎坷悲欢,励志戏曲艺术,终成一代名家。艺术,是艺术家的艺术,更是时代的艺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在舞台上和生活中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崇和荣誉。当今时代,日新月异,节奏飞快,人们难得停下脚步,过一过慢生活,品一品剧中人。现如今,在继续将戏曲文化发扬光大的同时,传承戏曲唱腔的民族唱法大放异彩,那一曲《我的祖国》,永远回荡在中华大地,回荡在中华儿女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