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队”的艺术

冯晨辰
今天我们对“站队”一词已经完全不陌生,“站队”的本质是信息加上逻辑性选择形成的群体意识,首先是部分个体对相对“确定性”的主张,接着由不同“确定性”之间的争论所构成,而这些争论的發展和衰落周期,在当前这个时代比以往更加迅速。与其称之为“站队”,毋宁说是保持“队形”——一种占据主导性地位的结构。这种结构伴随着站队者的数量,队形稳固,其中一部分“对现实批判性的回应”,将余下的事实部分虚化催眠。
在这一过程中,“站队者”所表达的个人志趣、理论倾向、哲学诉求,实际上影射出“站队者”的社会背景、身份阶层、所受教育、生活经验和自我认知等。由此,“站队”作为行为本身很可能在看似不断向外向上的攀缘前坠入谷底。而他们的理论中不乏来自历史的“干预”和未来的“期待”,两者以“犬牙交错”的面貌被自我欢迎和重复肯定,不停歇地沉浸在“狂欢化”中,甚至强烈到这种肯定似乎意味着他们“拥有”的未来。然而,尚且未知的是,这种被重新组织和结构的既定内容,将由怎样的力量、怎样的场所去拆解。
这是因为,即便没有认同,其他没有“站队”的群体作为它的他者存在,要么需要它的反证,要么需要它来澄清自己。这就如同我们去看待现当代某些被称为“艺术”的内容。在尼采著作《我们的艺术的终极感激》中,假设没有艺术,尼采认为“生活将变得完全无法忍受,诚实会毫无例外地令人作呕,导致自杀”。不同的是,核实“艺术”的意图和被解读都是必要的行动,“艺术”把未来带入当下,而“站队”则是为了在确保重复自身的过程中进入未来。
“信息+逻辑的选择”这一公式来自一位修行者的提炼。如今是信息传播极其发达的时代,伴随着以非物质劳动果实为基础的知识产权新经济的出现,信息符码成为这个时代真正的资本,而“站队”的本质正是信息加上逻辑的选择。

2022年4月1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支持者互动。
如今,人们获取信息的来源大多是公开共享的,信息抵达的时间也基本一致。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人们便开始迅速列队,因为发声是迫不及待的。即使通过同样的渠道,获得相同的信息,人们依然会产生分歧甚至是绝对割裂的对立,这一点则是上文所说的个体的社会背景、身份阶层、所受教育、生活经验和自我认知——个体“逻辑体系”,所决定的。不同个体的逻辑产生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人们争论哪种方式是“对”的,哪种方式是“错”的,或者简单粗暴地用“好”“坏”来划分,这些界定都是由不同的个体观点建立而来,从而每支队伍都代表趋同者自我的“群体正确性”,是隶属于社会存在的虚无概念。
这些通过“信息+逻辑”的选择产生的局限性言论,被人们急于结构为新的信息符码发出,并在重复性传播中不断获得自我认可。但这好比一部影片,当中某个个体的纯粹自恋或某一片段的影像反复回放,也就消解了真正的主体表达。信息和事件本身与人类重建的信息队列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行为主体,取代人类的体验和实践,最终成为一场“信息的表演”。
我们没有生于犬儒主义、大乌托邦、追逐机器的时代,这是一个合适的时代,合适“站队者”将自身置于集体的凝视中,试图将一部分理解、感知(分析)、结合实践(想象力),最终建构成为“悲壮的诗歌”,全然不知地被自我局限性围困。在人类历史的研究中,人类自身是一种有诸多局限性的社会性物种,人类的信息也受限于个体认知范畴内的视觉、语言或文字,一部分“群体正确性”引领着产生共识的群体发展,但这种“群体正确性”无法避免犯错,人们很难在群体中完全拥有客观认知,并因此打破团结,团结包含疏离和约定、容纳多样性,但反对任何一种基于单一集体共识的社群。
我们再通过趋同性看“站队者”的相似之处,他们对彼此很可能一无所知,他们之间的对话基于对某些事件的共识,而大多数时候更多是一致性的否认。对于事件的批判性包含自我的理解、想象,同时调动、投射和部署。然而,就像你在某一片花圃里种满同一种花,一旦遇上这种花的天敌虫害,就会出现不可挽回的集体灾难性灭绝。
一些选择“站队”的开端来自当代世界的边缘,关于战争、流行病、灾难、突发事件的发生和信息传播,在“边缘”处产生转折分化。关于这里讲的“边缘”,我们引用《动力沉思》一书中的阐释:“表示特定种类或程度的关注度的人物。在这一意义上,这一人物可能位于我们正在讨论的现实的核心,但仍然处于边缘,因为它没有跨越某种低可见度和低关注度的门槛,或者因为它被看作是现实基本过程里的残渣。边缘具有自己的图像—场域,并转向这个图像—场域来挖掘和激发一些可用来实践的资源。”
在中世纪装饰手稿中有一部分绘画内容属于“旁注”,“旁注者”题写关于构成与主题文本反差的世俗智慧、人物、寓言等,这些边缘注脚中大多出现普通人的形象,以构建同国王、贵族、英雄等人物的对位。前者和后者都可能是实践者,也都可能成为世俗偶像,但前者的一部分很可能以自诩的方式对后者发话,甚至不惜学习一种新口音、新手势,以圈出安全范围和危险边界。
这其中真正的实践者想要恢复主体意识,需要花一些力气学习和扩大思想共同体,以避免被过度修辞和抵抗。 那么,由此回到“站队”这一初始话题,是否能断定站队者同“抵抗”的真实关系呢?又或者是出于生存和自身利益的某种集体行为——行动者复调式的主张。若仅仅是召集了一致的声音大声诵读,终究不过是“理论的遗体”,在伸张的道路上也必然遭受缺失思考的阻力。
“站队”的必要性之一是满足人类的被认同感。在原始社会,有“站队”意识的个体更容易生存。人类社会中,相互间的认同感也使人类达成更多的协作,尽管这种协作在当下时常体现为内耗。另一方面,人类对独特性的追求也能通过“站队”来满足。人类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可能模糊,但对于身份排他却相对清晰。也就是说,相对于自己是谁,更清楚自己不是谁。 在“站队”的过程中,人们对自我和他人的身份进行了主观建构。比如:美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到现在依然坚持地球是平面的,他们很认真,付出成本、行动去证明这件事,并就这一领域的新发现召集学术会议进行讨论。这些人以相对偏锋的方式,成功地找到一种刷存在感的机会,并且能够找到有共识的朋友以及敌人,再通过对抗表现了自己的勇气、智慧。他们仅仅需要强烈地表达或渗透一个观点,就收获了存在感、正义感,甚至是一部分的话语权、否定权,不乏是一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然而,这种方式对漫长的社会进程而言不具有绝对意义。一些人在“站队”的同时讲出更隆重的故事,使得问题变慢、停滞,甚至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倘若能在“站队”的行为中实施倒置的处理,增添几分辩证法的价值,体现出思想的运动,在当下窥视历史和未来,赋予更多理性和知识,无疑会产生对这部分主体的敬畏。

2022年4月,韩国公众聚集场所的营业限时、私人聚会、活动和集会限员等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全面解除。餐厅、咖啡馆、娱乐设施、练歌房、洗浴中心、健身房均可营业至凌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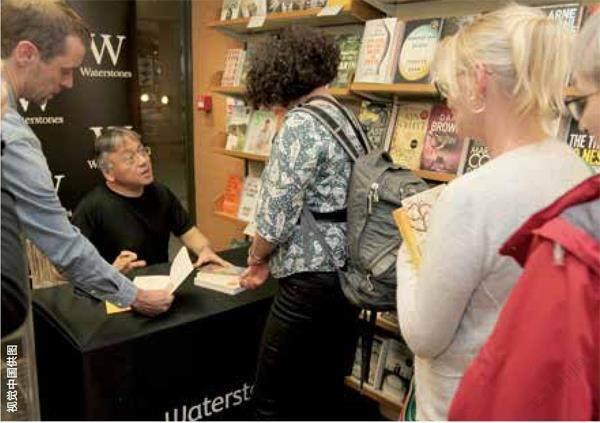
在我们的时代,发生了一些事情,把一切都改变了。一部分人对于事实本身毫无兴趣,他们站在道德高地上,成为语言、文字信息的俘虏,选择简单粗暴的逻辑方式传播见解,急于“站队”,表达个人主张,这好比将道德准则赋予奔流的洪水,看似强烈地发声,实则充满风险。
在新旧意识形态的交替中,对于一些“罪责”的赦免未尝不是一件必要性的事,在一些我们所有人都参与的悲剧中,特赦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悲剧永无止境,总要拆解,总要写上一个结尾,总要开始审视反抗的积累,开始重建受损的信任。当我们反复使用一面镜子去照射美杜莎的首级,它也会成为我们自己的面具,我们努力驱逐的影像也会影响我们的视野。
长此以往,“站队”最终如同“灾难”的想法,也会成为一种标识,用来辨认那些抛弃自身产生力量的人们,辨认将一切不完整认知与不确定性视为行动与思想条件的人们。“站队”与当下事件同样只是形象化的表現,而所有被调整的对立关系、批判思维和“否定作用”会被工具化,在“站队”的过程中,曾经作为历史和人类行动之动因的否定性正在消失。当否定性的力量彻底消失,恶会腹语。
(责编:常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