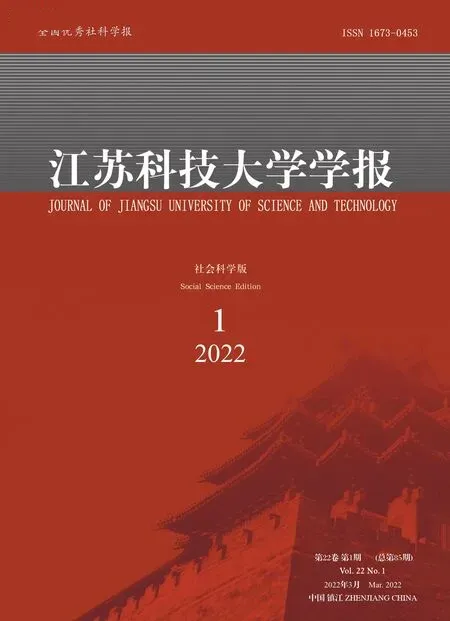状元丁士美诗文探佚及风貌探究
白金杰
(海南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海南 海口571158)
明代状元及第后,大多身居清要之职、文冠翰苑之所,其别集的典型性价值与意义不容忽视。明代嘉靖己未科(1559)状元丁士美(1521—1577)身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历任《永乐大典》编修官、帝王日讲官、国子监祭酒、教养庶吉士、礼部侍郎、吏部侍郎、乡会考官等清要之职,生荣死哀,是明代状元中仕途颇为顺遂的代表。遗憾的是,丁士美没有别集行世,亦不见有文献著录,这一缺失影响到对彼时文坛风貌的整体关照。郭皓政《明代状元与文学》(齐鲁书社 2010年版)一书提出丁士美别集无考,有待来日挖掘、整理与研究。笔者搜残补阙,共辑得丁士美佚诗六首、佚文十数篇,试从其生平史料、地方文献与存佚诗文出发,探究其别集无考的原因与佚诗文著录的情况,管窥其诗文的创作风貌与文学价值,籍以补充明代状元与文学的相关研究。
一、 修其实行:佚失的原因考述

肃皇赐对大廷,擢为天下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一时馆阁诸英,皆负夙望,公居其间,如楚之在薪,盖翘然者矣。壬戌、乙丑,礼部贡士,公举为同考试官,丁卯、庚午,顺天再乡试,皆命公主试事,又充武举考试官。凡五司文衡,所荐文武之士,称为得人。以重录《永乐大典》书成,升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加俸一级,又升侍读学士掌翰林院事。隆庆五年,升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未几,奉旨充东宫侍班官,又充日讲官,视篆翰林院兼教习庶吉士。今上万历元年,升礼部左侍郎,又改吏部右侍郎,升左侍郎兼官日讲如旧。(1)参见丁承炎、丁承建编修《御书堂·丁氏族谱》,下引简称《丁士美墓志铭》,不另出注。
丁士美自殿试抡元后,所任皆清要之职,其卒后亦被赐封赠礼部尚书,加谥文恪,敕赐祭葬,立石坊碑铭,安置华表翁仲,可谓极尽哀荣。就年寿而言,丁士美生于正德辛巳(1521)三月初七日,卒于万历丁丑(1577)八月十一日,享年五十有七,又因丁忧守孝,逝于淮安老家,也算寿终正寝。此外,丁士美有三子:有虞、有殷、有周。有虞生前得荫,但不幸早夭,次子有殷、三子有周均得以补荫。前者官至户部郎中,升姚安府知府;后者曾任莱州府通判、盐运使通判[2]。丁士美过世时二子尚幼,但其子成人后均跻身仕林,不存在后继无人、无人刊刻文集的问题。
丁士美虽未见文集行世,但有两点可以推断:
一是丁士美生前应当写有大量文章。登科后,丁士美有会试程文、殿试策与及第谢恩表传世[3]。清乾隆年间,阮葵生还曾在淮安人邱谨家中见过丁士美的殿试策[4]45。此后,丁士美入翰林、为帝师、兼教习、典文衡,身居翰林院十数年,所写翰林馆课、经筵讲章、奏议诏令、书牍赠序、题跋碑志、杂记诗赋等应不在少数。因此,丁士美佚文虽不多,但大体分属如上文类。
二是丁士美有较高的行文(包括时文)与衡文的水平。丁士美虽自述不以文辞为念,但能够身居翰苑,其文字能力毋庸赘言。丁士美的乡试程文《是集义所生者》有“当详处不放过一字,当略处不牵扰一词”“题中字义,无一不切”“谓集义兼念虑应感尤确,复伴笔势超佚”等评价[5]。他的殿试策不仅得到了嘉靖帝的赏识,也因切中时弊而为仕林广泛认可,“是时,帝方专任严嵩,海内耗竭,士美对颇切至,士论称之”[6]。于慎行在《会祭少宰丁文恪公文》中赞称:
周流学殖,驰骋词源,披褐入说,其牍万言,卿云在廷,胪句以传,公于其时,洛阳广川。演纶秘阁,汇笔棂轩,玉堂领篆,石室开编,清标凤翥,雄藻霞宣,公于其时,为唐许燕。穆考之世,公在法筵,皇开经幄,公入实先,论思两朝,日侍蜎涓,公于其时,韦贤史丹。升华春省,晋贰衡铨,回翔卿座,践武台躔,望邻爰立,地迩具瞻,公于其时,夔龙比肩。[7]148
许国在《丁士美墓志铭》中高度评价了丁士美的文学才能及出任考官时的衡文能力,称他“资禀端凝,文词优赡,巍科擢隽,艺苑蜚英,史局书,克效编摩之绩,经筵进讲,尤殚启沃之诚,遂掌篆于翰林,荐升华于卿寺……凡五司文衡,所荐文武之士,称为得人”。此当属盖棺论定。如隆庆四年(1570),丁士美将房师定为第二的李廷机点为解元;万历十一年(1583),李廷机由会元而成榜眼,由此可见丁士美确有慧眼。
丁士美的别集之所以难考(或未结集),可能与以下两个主观因素相关。
一是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8],表现出君子惜名轻利的操守。尤为仕林称道的是,丁士美殿试抡元后,曾冒着仕途蹭蹬的风险拒婚权贵:
榜下脔婿,古已有之。至元时,贵戚家遂以成俗。故有《琵琶记》牛丞相招婿事,亦讥当时风尚也。至国朝则少见,如程篁墩学士之婿于李文达,则未第时事,而识者犹议之。嘉靖中,翰林编修赵祖鹏者,号太冲,浙之东阳人,居京师,有女嫁缇帅陆武惠炳为继室,倚陆声势张甚,富贵擅一时,然为士林所不齿。赵幼女甫笄,才而艳,值己未春榜后,状元丁文恪士美丧偶,赵欲以女字之,丁坚拒不从。赵大不堪,适会元蔡茂春室人亦亡,慕赵光焰,托媒为道地,赵喜甚,蔡遂委禽为赘婿,一时清议沸然,咸重丁而薄蔡。[9]
与丁士美坚拒不从形成对照的是,该科会元蔡茂春主动入赘,两相对比,高下判然。同僚于慎行评价丁士美“性和而介,志洁而坚,内绝嗜好,外断尘缘,遇事侃侃,抵掌而谈,义所不可,推之莫前,清标劲节,如水如弦”[7]148。此可谓是对他品行的概括。丁士美行事缜密,也体现在他不轻易接受别人的请托。因此,目前所见的佚文,或为表彰儒家的忠孝之道;或为孝妇刘奇臣之妻田氏撰写墓志铭(2)未见原文,所题条目见李鸿章修、黄彭年纂《畿辅通志》,出自《康熙志新安旧志》,第20函第247卷,1934版第315页。;或为地方官造福一方的事功记传[10]857-859;或因不得以而为之,如为交好的同僚送行“不敢以不文辞也”(《送少司空双江方公赴任留都序》)等。
二是丁士美不以雕藻为尚、不以文辞为念,即重德行胜过炫文辞。许国在《丁士美墓志铭》中称他“性好聚书而尤慎于取,与为文,极根于理,典雅浑融,不以雕藻为尚,在仕籍殆二十年,存心未赏一日不在天下”。在作国子监祭酒期间,丁士美也不喜浮华,主张修实行,不以文艺为尚。主持科举考试时,丁士美有意抑制浮华、险怪之风。隆庆四年(1570),丁士美与申时行主持顺天乡试,录取李廷机、郭子章等为举人,以李廷机为解元。原本房师王一岳将郭子章评为第一,将李廷机评为第二,但丁士美和申时行却调换了二人的顺序,因为李卷平正、郭卷偏奇。丁士美对郭子章解释称:“顺天首善地,毋令天下议我好奇。”[11]由此可见,丁士美有意抑制求奇逐险之风,这与他持重谨慎的个性直接相关。
综上,丁士美没有别集存世,并非生前著述不足以结集或无人刊刻流传的缘故,大抵与他本人重实行、轻文辞有关。尽管如此,丁士美仍有少量诗文存世。
二、 邑里难徵:佚诗文的著录情况
丁士美的诗文存世较少。著录丁士美佚诗的选集仅有两部:一为清吴玉搢所辑《山阳耆旧诗》第二册,一为清丁晏所辑《山阳诗徵》上册卷七。后者虽系对前者“踵事辑补”[12]而成,但于“丁士美”条并无增订。二人都是丁士美的同乡,同系饱学之士,出入经史,熟谙方志,但未有新见。由此足见至少于乾隆年间,丁士美诗已难徵考。
较早收录丁士美佚诗的《山阳耆旧诗》,是一部专门收录淮安诗人诗作的作品集,编纂者是淮安著名金石学家吴玉搢。乾隆十一年(1746),吴玉搢因多识闾史里故而志在乡土,因而被推荐参与《山阳县志》的编纂。该书编纂前后历时三年,为吴玉搢日后编纂《山阳志遗》《山阳耆旧诗》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之所以强调吴玉搢金石学家的身份与编修地方文献的经历,是为了阐述一个事实:至少在吴玉搢生活的乾隆年间,丁士美的诗文在其家乡就很难搜求了。邑人阮葵生在《茶馀客话》中引述了吴玉搢《山阳耆旧诗》小序的原文,提到吴玉搢为了搜求文献所下的苦功,“求之数十年,于宋、元得三家,于明得数十家,或刻集,或写本,或从他本刺取,或从书画题跋录出,几数千首,虽未尽卓然可传,而精光亦断不可磨没。乃手自抄写,积为五大册,仿元氏《中州集》意,人各详其姓字官阀,时代先后,间论次其逸事,名曰《山阳耆旧诗》”[4]531。据阮葵生所记,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山阳耆旧诗》原为五大册,至壬寅岁(乾隆四十七年,1782),仅剩二大册,因此同乡人丁晏再作《山阳诗徵》,以增补订讹前传。
《山阳诗徵》是《山阳耆旧诗》的续集,编纂者丁晏也是当地名士,道光元年(1821)举人,清代著名经学家,曾长期主持乡里观海书院、丽正书院、文津书院,至道咸年间,“丁氏著籍山阳三百年于兹矣”[13]。丁晏对山阳风土、典故、人物颇为留心,除《山阳诗徵》外,另编著有《淮安艺文志》《淮阴脞录》等。《山阳诗徵》是丁晏早年编成,历时十八年之久。乡人李宗昉(嘉庆七年榜眼)、潘德舆(道光八年南闱解元)为之作序。李宗昉曾在书肆中购得“法时帆祭酒钞本”(《山阳耆旧诗》),但因“缺误殊甚,为之怅怏”[14]235,意指丁晏《山阳诗徵》可补缺憾。潘德舆称该书“上溯汉魏,下讫近时,已物故者访其全集,详其出处,录其行谊,缀其轶事,凡撮拾十余年始成编”[15]。丁晏在自序中道出编写原委:
乾隆中,吴山夫征君选《山阳耆旧诗》,仿元氏《中州集》,系以小传,罔罗采获,其用力亦綦勤矣。顾此书为征君未成之本,抄录未竟,以出游置之。征君自言为胸中一未了事,且世无刻本,间有传写者,重沓错迕;或为俗子所改窜,增损互异,甚且厌其繁而删之。余因征君之选广为捃摭,其诗其人增多以倍,诗话事实又加详焉。[14]240
以上材料提到了丁晏为了增补《山阳耆旧诗》的缺漏所下的苦功。然而,尽管前有吴玉搢求之数十年广为稽考,后有丁晏历时十八年再为裒辑,又有王锡祺(1855-1913)《山阳诗徵续编》补后者之缺漏,但对比现存的《山阳耆旧诗》《山阳诗徵》与《山阳诗徵续编》诸版本(3)现存《山阳耆旧诗》为四册,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台湾图书馆藏有钞本。2018年,谭平国发现国家图书馆馆藏钞本所录,丁惠增据该本所录撰有《先祖丁士美佚诗六首发现及今译》一文。淮安图书馆藏有《山阳诗徵》光绪二十四年铅印本,南京图书馆藏有光绪二十四年“清河印本”及2009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周桂峰点校本,笔者所引版本为台湾图书馆所藏咸丰年间钞本(第110-111页)。,笔者遗憾地发现,《山阳耆旧诗》仅收录丁士美佚诗六首,《山阳诗徵》并无增补,仅全文抄录,个别字句略有出入,而《山阳诗徵续编》无一语涉及,不再赘及。由此可推知,至迟在乾隆初年,虽有乡里耆儒广征博引,丁士美的诗作在其乡里就难以搜求。
经多方探佚,丁士美文除了乡试文、殿试策、谢恩表等随史志传世外,只有几篇散见于方志和家谱中。目前可见有《高加堰记》(明天启《淮安府志》卷二十一·艺文志一)、《臬副纪文泉传》(清康熙四十二年刻本《文安县志》卷九·艺文志十一)、《送少司空双江方公赴任留都序》(《东安方氏宗谱》卷四)、《赠冒桂亭荣任南都序》(《如皋冒氏宗谱》卷六,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经书音释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50册)、句容《义台张氏家乘》序、孝妇刘奇臣妻田氏墓志铭,另有《经筵四书直解》(鲁通甫编纂《咸丰清河县志》卷之二十三《艺文》),已佚(4)以上佚文除笔者探佚得到外,《丁士美墓志铭》《臬副纪文泉传》《赠冒桂亭荣任南都序》《句容义台张氏家乘序》由丁士美状元后人丁祖宏提供,《经书音释序》可参见张一民《丁士美经书音释序浅识》,出自《纪念丁士美诞辰五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1年4月17日。。
三、 学胜于文:佚作的审美风格
丁士美的佚诗文存世数量不多,这与丁士美本人并不留心文辞有关。虽然身为状元,但丁士美主要着力于编修大典、撰写讲章、制诰公文等,并不把文学视作毕生追求。这是状元群体的普遍做法[16],也合乎明人对状元的期待,即首推德行与学问,次论辞章文采。尽管如此,从丁士美的佚文仍可窥见其文学风格与价值。
丁士美佚诗六首,见于吴玉搢《山阳耆旧诗》,现将该书相关条目抄录如下(5)参见台湾图书馆古籍与特藏文献资源收藏的吴玉搢《续山阳耆旧诗》咸丰间钞本 (台湾图书馆索书号:403.314463)。丁惠增据国家图书馆所录文字与本版略有不同,可参见《先祖丁士美佚诗六首发现及今译》,淮安文史资料网,http://www.hawszl.gov.cn/lgxd/2019-12-20/6217.html。:
孝恪皇太后挽歌(十首存四)
虎旅陈新隧,仙舆改故山。
白云封处合,青鸟倦时还。
风雨三春暮,松楸百里闲。
舜心原至孝,哀慕泪潸潸。
明德当年重,追称此日尊。
龙章宣节惠,凤诏播遗芬。
永巷风今熄,长秋迹已陈。
泉台留谥册,千载勒徽音。
麟迹培仁远,螽斯咏德芳。
昔年追凤逝,兹日并龙藏。
永夜啼乌鸟,悲风动白杨。
嵬嵬阳翠岭,埋玉亦摧伤。
三日西陵道,春风尚惨寒。
凤车千羽列,龙阜万山环。
玉掩崇冈润,衣藏大寝安。
都人争眄望,仙驭竟谁攀。
送同年之任留都
少日看花醉玉京,
喜随仙侣共登瀛。
送君忽忆十年事,
把酒相期万里程。
南浦晴云生去马,
上林春树啭迁莺。
风流江左人争羡,
好赋三都答圣明。
春日游宝光寺有感
野寺寻春花较迟,
晓来风雨更相欺。
肯缘抱病违芳侣,
不惜春寒赴远期。
莲社自携新漉酒,
杏园曾忆旧题诗。
浮云已逝韶华暮,
赢得东风两鬓丝。
公初第日,有柄臣欲以内之妹子归之,力辞得免。迴翔近禁凡数十年,充日讲官时必以正言格论,反复开导,上悉嘉纳,御书“责难陈善”字以宠之。五司文衡,得人称盛。虽不以诗名,而所存数诗极隽永可诵。其殿试原卷,今尚存吾乡邱翼堂先生家。
丁晏《山阳诗徵》所录文字与此大体一致。诗虽六首,却分属三大类型:《孝恪皇太后挽歌》是应制之作,《送同年之任留都》是酬唱之作,《春日游宝光寺有感》是抒怀之作。
应制之作,难出佳构。阁臣张四维也有同题诗,其诗辞采华茂,与丁士美的诗风迥异。丁士美此诗应作于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登基后,穆宗尊生母为“孝恪渊纯慈懿恭顺赞天开圣皇太后”,以皇后礼仪改葬永陵,嘱词臣作挽歌。丁士美的挽歌用平实的语言写出了死者的哀荣,也写到了生者的追缅,这两种感情都表达得收敛、克制。如,用“白云封处合,青鸟倦时还”来代指死亡,用“永夜啼乌鸟,悲风动白杨”写出哀挽,用“玉掩崇冈润,衣藏大寝安”表示落葬,与张四维“御辇初辞宠,金波遽堕空”“讴歌归圣子,贻庆本涂山”等风格不同[17]。今人虽不见丁士美诗文全貌,但大体可知其诗风。即便是应制诗,丁士美也没有驰骋文辞、堆砌华藻,仍然保持了简淡的风格。
丁士美《送同年之任留都》一诗,所赠之人已不可考,但科举时代的同年之谊有特别之处,值得一考。丁士美在首联回忆了二人“共登瀛”的过往,颔联将往日情、今日景以“忽忆十年事”与“相期万里程”一笔带出,颈联与尾联则是对同年仕途的美好祝愿。总体来看,该诗文风得体恰切,不作空语。《春日游宝光寺有感》一诗曾入选王鸿鹏选注《中国历代状元诗》(明朝卷),但该书注宝光寺“在四川新都,是全国唯一未遭破坏的名刹,为四川省保护单位”[18],当为讹注。据载,北京通州区次渠村也有宝光寺,“元大德元年(1297)始建,是北京东南著名禅宗名刹,明正统五年(1440)重修,易名宝光禅寺,俗称宝光寺”[19]。丁士美长期身居内翰,除了典试江南,不闻有赴四川之举,因此此诗所指当是通州宝光寺。这首诗用语极为简淡,除“莲社”代指宝光寺外,通篇未用典故,只将野寺、风雨、春寒、花迟与人的韶华暮、两鬓丝铺叙写出,不粘滞于眼前之景,也不拘泥于伤春之情,姿态敦厚自持,但抒情自然真切,既不同于馆阁之臣的优裕闲咏,也与失意寒士的穷愁自怜迥异,当得起“极隽永可诵”的评语。
丁士美的文虽不多,但文如其人。他为人谦厚,文章亦有儒者之风。如《高加堰记》将治水的郡守与范仲淹、苏轼等名宦并举:
民之难与虑始也,自昔然矣,其堰之谓与!余尝观宋天圣中,海潮漫为咸卤,范文正公时监泰州西溪仓,议筑捍海堰于通、泰、海三州之境,长数百里以卫田。逾年堰成,民享其利,三州之民生祠之。又元有祐中,杭之西湖多葑田,六井几废。苏文忠公时守杭,遂浚茅山、盐桥二河,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杭人名苏公堤,家有画像,饮食必祷于公。今兹堰之举,视文正、文忠又奚异也?淮民之尸祝二公也无疑矣。世尝谓古今人不相及,非然哉,非然哉。[10]
丁士美以古代贤臣为榜样,嘉勉当时的地方官,体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政理念。《赠冒桂亭荣任南都序》是为鼓励科场蹭蹬的冒桂亭,不必纠结于功名,要发挥才学去报答君父。《臬副纪文泉传》阐释了忠与孝的关系,自古忠孝难两全,但丁士美认为,纪文泉的父亲推崇“忠”,纪文泉服从父命去尽忠,等于是在尽孝,从这点来看,纪文泉实现了忠孝两全,诗人高度认可了父子二人在传统伦理上达成的共识。丁士美诗文的风格质朴无华,这是当时馆阁文风的普遍特色,即“文辞主典实不主浮华,体格贵雅驯不贵矫杰,议论贵切事情不必以己意为穿凿,歌咏意在寓规讽,不得以溢美为卑谀”[20]等,体现了文以载道的创作观念。
丁士美本人虽不以诗名,但对后学诗赋颇为推举。刘克正是隆庆五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克正质敏才茂,词赋为丁士美、诸大绶辈所推。尝作《越裳白雉赋》,世竞传之”[21]。对冒桂亭这一科举考试的失利者,丁士美也能赞许他的才学,勉励他“君虽厄于一第,然就是选而能其官,益饬其履,谇其业”(6)参见冒文焕《冒氏宗谱》,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以实现忠君孝亲之举。用《儒林外史》中评价虞博士的话来评价丁士美:他身上没有所谓的进士气与学究气,即不以功名自傲,也不以道学自居,颇为难得。此外,黄霖辑录《文心雕龙》历代评点,收录了丁后溪(即丁士美)的评点。黄霖称其具有“评点眼光,也注意到《文心雕龙》本身的文采”[23]。可见丁士美对诗文创作理论也颇为留心,并能够关注论述本身的文学性。
概言之,明人对状元首推道德,次为文章,而状元亦往往自矜身份,砥砺德行,以道义自持。丁士美的立德立功已载于史册,因此虽诗文不多,但呈现出丰富的面貌,既有馆阁文学的共性,也有简淡自然的个性,涵咏有大家气象。由此可见,丁士美并非不善为文者,而是意不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