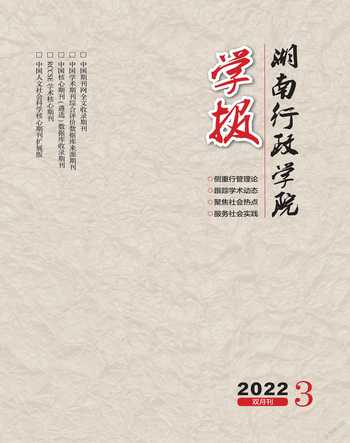猥亵儿童罪中“聚众当众”型加重情节的认定
陈丽
摘要:近年来,我国“聚众猥亵”和“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犯罪案件增长迅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更好地保护儿童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猥亵儿童罪的加重情节作出较大修改。由于“聚众当众”型加重情节颁布实施时间不长,司法实践可参考的案例不多,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导致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况普遍存在,认定猥亵儿童罪中适用“聚众当众”型加重情节存在诸多难点与困惑。从现有法律法规及司法实践来看,在现实空间认定“聚众猥亵”时,聚众人数必须是3人及3人以上,并且行为人共同参与实施犯罪;在网络空间认定“聚众猥亵”要综合分析案件发生的场所、行为人数、共同犯意和与之相当的社会危害性等因素;除我国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公共场所以外,在性质、功能、使用对象、开放性等与其相同的场所,都可以认定为“公共場所”;“当众”要考虑其客观存在的现实性和能够感知的可能性;“情节恶劣”要结合具体案件的法益侵害严重程度、社会影响恶劣程度、社会公共秩序破坏程度和涉案人数等综合判断、科学认定。
关键词:猥亵儿童罪;聚众猥亵;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司法认定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22)03-0085-07
一、猥亵儿童罪中“聚众当众”型加重情节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难点
近年来,我国“聚众猥亵”和“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犯罪案件增长迅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更好地保护儿童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猥亵儿童罪的加重情节作出较大修改,其中,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第二项明确规定:“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当下由于“聚众当众”型加重情节颁布实施时间不长,司法实践可参考的案例不多,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导致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况普遍存在。下面我们重点探讨猥亵儿童罪中适用“聚众当众”型加重情节存在的难点与困惑。
(一)“聚众猥亵”认定标准不明确
一般来说,刑法意义上的“聚众猥亵”是指3人及3人以上对被害人共同实施犯罪[1]。那么,在现实空间,聚众猥亵与普通共同猥亵犯罪的界限如何确定?比如王某静、王某福、王某武强制猥亵案。2017年9月10日晚,被告人王某静、王某福、王某武在盲人按摩店拔罐时对被害人赵某实施猥亵。法院认为,由于三个被告人没有事前的商量预谋,而是临时起意,不应认定聚众猥亵加重情节(即五年以上刑罚),而属于普通共同猥亵犯罪,判决五年以下刑罚。这就说明,司法实践有必要把聚众猥亵和普通共同强制猥亵进行区分。同时,随着网络社交平台的普及化、网络用户的低龄化和网络通信的匿名化,一些犯罪分子更是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在网络空间伪装身份、年龄等基本信息,联合其他人,要求被害儿童做猥亵动作、拍摄裸照或视频等来满足其性刺激。这种发生在网络空间的聚众猥亵如何认定,必须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判断。
(二)“公共场所当众”的认定标准尚未统一
除《性侵意见》规定的校园、游泳馆、儿童游乐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第42号“齐某猥亵案”中明确的学校教室、集体宿舍、公共厕所、集体洗澡间等以外,生活中还有很多公共场所,如民办培训班教室、小区电梯或广场、公园僻静处等等。这些是否属于公共场所,尚未在实务界达成共识。例如,孙某猥亵儿童案。2021年7月,被告人孙某在去女儿新装修的房屋某县某小区时,为追求性刺激,在小区电梯内对着7周岁的马某“手淫”并射精,法院判决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可见,法院并不认为小区电梯内猥亵儿童属于“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还有,“当众”的人数是2人还是3人仍有分歧,例如,徐某猥亵儿童案。2017年7月,被告人徐某在某培训中心书法教室内为被害人张某(女,案发时10岁)等3名学生上课,另一位刘老师坐在教室里休息,顺便看看学生的上课纪律,期间进出过教室几次。被告人在上课期间以抚摸隐私部位等方式猥亵被害人。检察机关指控徐某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已构成当众猥亵儿童罪,应依法从严惩处。法院认定:当徐某实施猥亵儿童犯罪时只有两名学生在场,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证明刘老师也在场,没有达到“当众”中3人的要求,故不能适用“公共场所当众”的加重情节,应判处徐某有期徒刑三年。另外,司法机关对“当众”人数是否包括行为人和被害人等问题认识也不一致。
(三)“情节恶劣”的认定存在分歧
“情节恶劣”的具体含义不够明确,司法机关自由裁量随意性较大,对行为人量刑差异明显。可以从以下两个案例中窥见。一是唐某猥亵儿童案。2020年12月27日17时许,绵竹市某书店正在营业中,店内有多名顾客在选购书籍,被告人唐某在书店内看书时,遇到独自在书店学习资料区看书的被害人马某(女,案发时10岁),便上前对其实施袭胸等猥亵行为。法院认定被告人唐某的行为属于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且情节恶劣,构成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二是孙某猥亵儿童案。2018年6月,被告人孙某采取抓、摸胸部的方式在新华书店、学校、花店门口等公共场所猥亵儿童4次,一审法院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两年。尽管检察院提出抗诉,二审法院仍然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理由是被告人采取袭胸方式猥亵,时间短,被他人感知的可能性小,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恶劣程度相对较轻,属普通猥亵行为,不宜认定为“情节恶劣”的猥亵行为。我们对比两个案例,明显有失公允。孙某不仅在新华书店、学校作案,还在花店门口当众猥亵儿童,而且有4次之多,主观恶意和社会危害性都比唐某更大,却判刑更轻,足见司法机关对“情节恶劣”的理解不同所导致量刑差异明显。
二、“聚众当众”型加重情节中“聚众猥亵”的认定
(一)厘清现实空间“聚众猥亵”的认定原则
一般来说,现实空间的“聚众猥亵”司法实例并不多见。有学者选取100例猥亵儿童罪判决书分析发现,其中只有1例属于聚众猥亵儿童。这跟聚众猥亵的特性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猥亵儿童违背社会正常伦理和公众的基本道德感,行为人作案时一般会选择避开旁人进行;再者,猥亵时大多是行为人临时起意,没机会去预谋和商量;最后,猥亵儿童行为人中有80%是熟人作案,很难找到共犯。要想构成聚众猥亵,必须满足三个要件:一是聚众的人数,二是共同的犯意,三是与之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应该说,现实空间的“聚众猥亵”比较容易判断,但也有两个争议点值得讨论:第一个争议点是聚众的人数问题。一般来说,聚众的“众”必须是3人及3人以上,但部分司法机关也存在把“众”理解为2人的情况。笔者认为,尽管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儿童利益,但不宜无限制扩张适用法律,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第二个争议点是共同犯意的衡量标准问题,集中体现在搞清楚聚众猥亵和普通共同强制猥亵的区别。关于聚众猥亵,学界有两个观点:一是聚众犯罪是共同犯罪的一种形式[1];二是聚众猥亵是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以聚众的行为方式实施猥亵的犯罪[2]。可见,聚众猥亵和共同猥亵犯罪是有交叉关系的,但又与共同猥亵的定罪量刑有所区别。在王某静等人猥亵案中,法院认为三个被告人没有纠集,就没有聚众猥亵的首要分子,因此不能适用加重情节。其实不然。笔者认为,只要是客观上有3人或3人以上以聚众的方式共同实施了猥亵行为,不管是否有犯罪集团的核心人物,都构成猥亵的共同犯罪,说明被告人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共同犯罪的间接故意,从而可以认定为“聚众猥亵”。
(二)厘清网络空间“聚众猥亵”的认定原则
在网络空间猥亵儿童的案件,如何认定“聚众”还没有明确标准。结合前文所述的网络空间“聚众猥亵”具体情形和主要特点来看,笔者认为,要满足网络“聚众猥亵”必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众”的人数。即行为人必须达到3个或者3个以上。二是共同的犯罪故意。在判断网络猥亵案件是否符合“聚众”这一标准时,应当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为猥亵被害儿童而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出邀请和行动计划的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如在群聊时,故意散播相关消息,有意向的人就会采取行动加入其中。当然,在网络中“聚众”可能存在被迫“猥亵”他人的可能[3],比如误入群聊或直播间等。这要结合具体案情具体分析。三是具有与加重情节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后果。比如猥亵时间长,导致对被害儿童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造成严重的伤害;传播速度快,导致社会影响恶劣,甚至严重影响到儿童今后正常的学习、生活,等等。
三、“聚众当众”型加重情节中“公共场所当众猥亵”的认定
(一)明晰“公共场所”的认定标准
1.从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公共场所”来看:我国很多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了列举式表述。比如,《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二条、《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和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寻衅滋事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中都对公共场所作了列举,主要有车站、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等。公共场所具有公共性,对公众开放,是供不特定多数人随时出入、停留、使用的场所,其主要功能在于满足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从事工作学习、社交娱乐、体育锻炼、旅游参观等主客观需要,具备公共性和实用性等特征。司法机关可以依据这些特征作出科学认定。
2.从猥亵儿童案件中的“公共场所”来看: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罪及猥亵儿童罪中都有把“公共场所”列入加重情节,但只有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公共场所”的内涵外延被解释得更宽广,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性侵意见》)。《性侵意见》第二十三条规定,“在校园、游泳馆、儿童游乐场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场,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均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猥亵儿童。”这不仅在保护未成年人人身权利上通过扩张解释严厉打击相关犯罪行为,而且在刑法解释论上进行了良好的路径探索,体现了“面向司法者的刑法学立场”,赢得了学者们的赞誉[4]。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除《性侵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列举的场所之外,只要在性质、功能、使用对象、开放性等与上述规定相同或相似,都可以认定为“公共场所”[5],如小区电梯、民办培训班教室、广场或公园僻静处等等。
3.从网络猥亵儿童案件中的“公共场所”来看:自从“两高”把编造虚假信息在网络上散布导致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公共场所”的范围也从现实空间扩大到网络空间。这一解释突破了对“公共场所”的传统认知,甚至于部分学者极力反对,他们认为网络空间虽然属于公共空间,但是公共空间不等于公共场所,空间是场所的上位概念,公共场所只能是公众身体可以进入的场所[6]。笔者认为,网络空间能否解释为“公共场所”,需要结合具体罪名中的犯罪行为特征进行分析。例如奸淫幼女罪,因性交行为以性器官的接触为要件,即使将网络空间解释为“公共场所”,也不可能隔空满足这一犯罪的现实条件。而就猥亵儿童犯罪来说,猥亵行为可以通过不接触身体的方式实现。特别是在当下,网络高清视频技术发达,使观看者如在现场般感同身受,而且网络传播速度更快,对儿童的身心伤害更大,社会影响也更恶劣,更有严惩的必要。
(二)明确“当众”的认定标准
1.要综合考虑“当众”的含义。一般来说,“当众”是指当着众人的面实施犯罪行为[7]。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众”猥亵是指公然对儿童实施猥亵犯罪,从行为能够看出其内心存在故意放任可能被众人发现或感知的结果发生。显然第一种含义的行为人主观恶性更大,但发生的概率并不大,反之第二种含义的行为人犯罪案件较多。秉持着“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一步减少猥亵儿童刑事案件的发生,采纳第二种解释更为适宜。
2.要综合考虑“当众”的现实性。猥亵儿童案件中“当众”是指行为人在公共场所实施猥亵行为时,必须有其他多人现实的、客观的在场,而不是抽象的、主觀的在场。关于“众”的对象和数量,前文已经有所谈及,此处可以作一致理解,即行为人在实施猥亵犯罪时,除被害人以外,还应有3人及以上的其他人,符合《刑法》严厉打击强奸、猥亵这一类性犯罪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的立法本意。另外,关于“当众”的“众”是否要求同时在场的问题。其实,《性侵意见》第二十三条早就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即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场,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均认定为“公共场所当众”。此处的在场是存在随时在场的可能,并未要求同时在场。如果要求同时在场,势必增加加重情节适用难度,客观上并不利于保护受害儿童利益。
3.要综合考虑“当众”的可能性。从学界和实务界的观点来看,“当众”的理解分为行为人的立场、被害人的立场和常人的立场,并且不同的立场产生不同的理解。虽然分析颇有道理,但从刑法是打击犯罪、维护正义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站在常人的立场思考问题,惩治犯罪,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从大众的理解来说,只要在场的多人对猥亵行为有随时可能发现或者感知的可能即可认定为“当众”,不管他人是否实际感知到。上述解释方式虽一定程度上对“当众”的词义范围进行扩张,但就目的论而言,契合保护儿童、严惩犯罪的出发点,真正发挥了司法应有的功能,应予支持。另外,如果行为人在网络直播间要求儿童实施猥亵行为,满足不特定多数人可能发现的客观性,情节恶劣的,也可考虑为公共场所“当众”猥亵。
四、“聚众当众”型加重情节中“情节恶劣”的认定
“聚众当众”型加重情节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其行为社会危害性理应满足应受刑法处罚的程度。但实践中部分猥亵儿童犯罪案件虽属于聚众当众等情形,却情节轻微或显著轻微,适用加重情节有过当之嫌。立法者考虑到这一点,明确增加一条“情节恶劣”进行约束。司法实务界在适用法律时必须对猥亵行为的法益侵害严重程度、社会影响的广泛性、恶劣性和社会公共秩序的危害性以及涉案人数的多寡等进行综合考量,最大限度满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一)根据法益侵害的严重程度进行综合判断
法益概念的最重要作用是,在对刑法的处罚范围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将其限制在对侵犯或者威胁了法益行为的处罚上,法益具有限制刑法适用的功能[8]。也就是说,《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第二项规定只能对“情节恶劣”的猥亵犯罪行为处以加重刑罚,对那些情节较轻的一般猥亵犯罪,即使是符合“聚众当众”的条件,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司法实践中,在学校、广场等公共场所发生猥亵儿童案件,往往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公共场所当众”的问题。如前面提到的唐某猥亵儿童案,被告人唐某在很多人都在选购书籍的书店内,冒着随时被发现的巨大风险,当着众人的面,对10岁女孩进行猥亵,导致被害人心理受到巨大伤害,法院对其处以五年六个月有期徒刑,不违背一般人的法感情。但如果将地铁或公交车上实施猥亵行为的“咸猪手”行为都适用加重情节,也不够合理。因此,“聚众当众”型加重情节的认定要综合考虑猥亵时间、地点、手段、持续时长、社会危害性、法益侵害程度等各方面因素,合理适用加重情节。
(二)根据具体案件中对社会公众影响的广泛性、恶劣性和对社会公共秩序的危害性进行综合判断
猥亵儿童案件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严重损害了儿童的身心健康。猥亵儿童侵害的是性的自我决定权[9],或者是性的羞耻心[10]。一般来说,被害儿童受到猥亵侵害,起初受伤的是身体。然而猥亵行为最根本的危害在于儿童的内心,会让被害人心理上造成巨大创伤,造成心理应激障碍,甚至造成精神分裂症等疾病。二是违背人性合理范围的主观恶性评价。猥亵犯罪一般选择隐蔽实施,像这种“聚众当众”的案例极为罕见,说明行为人主观恶性大。行为人选择“聚众当众”实施猥亵,就表明其毫不忌惮周围人的想法,显现一种超出一般公众接受范围的人身危险性,必须动用加重情节予以严惩。三是严重侵害社会正常公共秩序等其他法益。犯罪的当众性体现出行为人蓄意挑战公共道德和治安底线,藐视公序良俗,嚴重侵害了他人对公共安全的合理信赖[11]。所以,“聚众当众”型猥亵儿童犯罪,不仅伤害了儿童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而且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公序良俗,迫切需要通过法定加重情节给予刑罚打击,维护社会正常的公共秩序。
(三)根据具体案件中涉案人数进行综合判断
在人数较多的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公共场所,比如公园、游乐场、微信群聊和直播间等,涉案人数多寡尤其是儿童人数的多少是衡量“情节恶劣”的重要因素。猥亵儿童案发地的人数越多,被他人发现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大,儿童回归正常学习生活的难度也就越高[12]。在这些公共场所实施猥亵儿童犯罪,对被害人而言极其容易产生心理阴影,严重影响其回到今后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于情于法都应认定为“情节恶劣”的情形。而且,在这些场所实施犯罪,在场其他儿童也会觉察到犯罪行为,从而对这些儿童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五、结语
社会治理必然依赖于法律,法律是保障社会治理目标实现的基本方式[13]。一方面,在立法层面,“聚众当众”猥亵儿童的认定需要通过立法解释予以明确。另一方面,“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规范只有在实践层面被遵守、执行、适用,才能具有法治实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需要多出台一些猥亵儿童犯罪相关问题的指导性案例,为“聚众当众”型加重情节的认定作出示范。猥亵儿童案件要站在保护儿童的立场,适当地对“公共场所”的定义进行扩大解释,只要是性质、功能与其类似或相同的场所都可以认定为“公共场所”。“当众”不一定要当着众人的面,只要众人存在感知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就应认定为“当众”。对“公共场所当众猥亵”的认定,司法机关在具体适用时,“公共场所”“当众”必须同时满足,缺一不可。另外,“聚众当众”型猥亵儿童犯罪并不一定必然适用加重情节,还要把猥亵案件的社会危害性、法益受侵害严重程度和猥亵时间、地点、持续时长、猥亵手段等要素加进来综合考虑。
参考文献:
[1]张正新,金泽刚.论我国刑法中的聚众犯罪[J].法商研究,1997(5):5.
[2]马克昌.犯罪通论[M].3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3]宋美奇.猥亵儿童罪的认定研究[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20:23.
[4]于志刚.刑法学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3.
[5]钟芬,金昀.猥亵儿童案件中“公共场所当众”的认定及适用[J].青少年犯罪问题,2020(1):117-120.
[6]陈家林.《刑法修正案(九)》修正后的强制猥亵、侮辱罪解析[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8.
[7]赵俊甫.猥亵犯罪审判实践中若干争议问题探究——兼论《刑法修正案(九)》对猥亵犯罪的修改[J].法律适用,2016(7):9.
[8]刘艳红.“法益性的欠缺”与法定犯的出罪——以行政要素的双重限缩解释为路径[J].比较法研究,2019(1):18.
[9]日高义博.违法性的基础理论[M].张光云,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143.
[10]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M].7版.桥爪隆,补订.王昭武,刘明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103.
[11]王丽枫.性犯罪行为地系公共场所的认定标准[J].人民司法,2015(16):32-33.
[12]李琳.《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猥亵儿童罪加重情节的理解与适用[J].现代法学,2021(4):202-208.
[13]钱大军,赵力.地方治理视野中的地方立法[J].湖湘论坛,2020(6):42-53.
责任编辑:詹花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