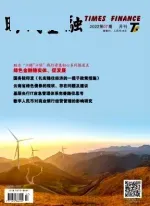中共革命时期创立红色金融的实践与历史经验
杨昌儒 王俊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金融探索中发现,建立根据地与发行货币是皮与毛的关系。国共日三方军政力量的博弈也决定着法币、边币和伪币排他性力量的对比,即军政实力保障货币供给;不同于法币、伪币的剥削性质,真正内生于国民经济的边币最终在货币需求端赢得市场信用,从而巩固了新生政权,所以金融体系的建立既离不开国家军政主权的保护,也离不开社会经济基本面的支撑。而无论是贵金属本位还是汇兑本位,国家都无法独立自主地实现货币主权,并且金融改革必须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以上经验对新时代金融改革依然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前言
在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完全独立的财政货币体系,而是依靠外援来维持基本的财政运转,但是随着国民党与日伪对边区的军事经济封锁,边区财政陷入困境,彼时边区新发行的货币既面对可在全国范围流通的法币排挤,也面对背后有军事强权支撑的伪币的掠夺。在这样的绝境之下,中共政权发行的货币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化险为夷,逐渐占领全国货币流通市场。
本文正是主要围绕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金融活动,按照中共1941年发行边币和1944年边币彻底脱钩法币这两个标志划分为三个阶段,以革命时期的边区货币史为鉴,来总结中共创立红色金融的经验。
二、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红色金融的实践
(一)红色金融酝酿期(1921-1941)
1.国民政府的统一推进法币统制。民国时期,尽管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在金融方面仍然存在货币发行权分散、制度混乱等情况,并且連年征战也使国民政府在财政严重赤字的情况下不得不大量举借内外债,因此其财政金融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1933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结束了银两与银元并行市场的局面,彼时的中国仍然是实行银本位的国家。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使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尤其是当1934年美国出台《白银收购法案》后,国际银价暴涨,中外银价差距拉大,国内白银因之疯狂走私外流导致国内发生严重的通货紧缩。
首当其冲的是广大农村地区,白银外流导致农村资金荒,农民得不到贷款就无法正常开展农业生产,农村市场萎缩,白银更加从乡村外流,形成恶性循环。而农村垮塌连带以棉花为原料的城市工业也陷入困难,城市私人资本从实体经济析出流向投机市场,从而使得利率大幅上升,大量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市场悲观情绪蔓延,银行挤兑时有发生。为了防止白银大量外流动摇国家银本位的基础,国民政府推动币制改革:1935年末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制”,改而推出实行“汇兑本位制”的法币,其本质是国民政府以放弃货币发行主权为代价,换取美元英镑的信用援助来缓解此次通缩危机。此外,国民党官僚垄断资本通过横征暴敛和高利贷对基层民众进行多重剥削,导致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农民革命运动因而兴起。
2.日军霸权的威胁强制伪币收兑。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但其为积累原始资本而进行海外殖民扩张。1931年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傀儡政权,1933年伪满洲傀儡政权确立了全面集中控制的货币金融制度,并为日军的殖民掠夺服务。于是,伪满傀儡政权强行吞并当地银行的发行准备,并将各类银行业务悉数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发行银本位的伪币强制折价收兑沦陷区通货。
1934年国际银价暴涨使伪币也受到冲击。1935年伪满政权开始实行货币换锚,将伪币逐步与实行金汇兑本位的日元挂钩,日本垄断资本从而建立“日满一体化”的货币制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为转嫁急剧增加的财政压力,强制没收沦陷区银行,包括外资银行,同时将之前收兑的法币倾泻至国民党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用以攫取物资,并发行大量伪币、军票排挤法币。
3.中共政权的稳定保证边币发行。1927年中共将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偏远农村山区,组织当地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并在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随着各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以及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建立,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直接隶属于财政人民委员部”①,发行银本位的苏票,以税收维持其信用。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国家银行工作人员也跟随红军进行战略转移。
长征结束后,中央红军在陕甘宁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和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在当时银价飙升的金融市场环境下,西北分行发行苏维埃纸币收兑银币。1937年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共中央将西北办事处正式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②,兼具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职能。随后,八路军先后建立了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③。这些解放区大都分散在农村和山区,为了解决根据地各级政权的财政困难,中共中央提出“有计划的与敌人发行伪币与破坏法币的政策做斗争,允许被割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④,于是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相继成立了边区银行并独立发行货币,一般称为边币或抗币。
由于红色政权缺少贵金属作为货币发行准备,按国共两党协议﹐边区银行收回苏票并宣布法币是边区流通货币,一切交易计价和内部核算均以法币为计算单位,国民政府每月向边区政府提供经费。出于找零需要,1938年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⑤作为法币的辅币。1940年8月,边区的外援骤然中断,导致边区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原来发行的小面额光华券已不能满足各方面的资金需求,于是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边币作为唯一的边区通货单位,并以边币逐渐换回光华代价券。
(二)红色金融探索期(1941-1944)
1.军事封锁导致财政危机。为了应对国民党和日伪的军事经济封锁,同时打击货币投机、熨平汇率波动,边区政府于1941年12月“授权各地贸易局联合当地商民组织货币交换所”⑥。通过交换所的挂牌交易,边区银行得以对边法币的黑市交易进行引导和控制。然而由于边币与法币挂钩,所以法币的泛滥导致边区政府面临“保物价”还是“保汇价”的两难抉择:如果维持以边币计价的物价稳定,则可能承担法币“以邻为壑”政策的代价转移;如果维持边币与法币的比价稳定,则边币将会被迫进行对冲增发,从而使得边区物价上涨。
以上情况由边区政府内部的两次争论可见一斑:第一次在1941年,一方认为边区银行为政府财政所累,过多增发边币导致物价上涨,所以银行应该与财政分离并且边币应该限制发行;另一方认为物价上涨使财政严重赤字,财政只能依托银行发行边币增加财政筹码⑦。第二次在1942年,一方认为边币的发行应当稳定在边法币汇价上,通过增发边币来对冲泛滥的法币,但可能会导致边区内物价上涨;另一方则认为边币的发行应当以稳定物价为主⑧。对此,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⑨,从而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在总方针的指导下,边区政府和边区银行都加大对生产和贸易的扶持力度。
2.发展生产实现自给自足。在生产方面,得益于大生产运动,各边区根据地的粮、棉、布、盐等重要战略物资的紧缺情况得到缓解。在分配方面,边区政府由之前向军队供应部门划拨军费到市场上购买,改为由公营商店统筹物资再分配给供应部门。这是由于军队作为边区最大的消费群体,之前经常在短时间内大批量采购物资,很容易加剧市场波动。这种供给制通过指令计划来调配物资,避免了发行大量货币参与流通,边区政府因而逐渐走出“财政赤字—增发货币—物价上涨—财政赤字加重”的恶性循环。
为了支持大生产运动,边区银行不仅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放款力度,而且对农业贷款采取实物贷款的方法⑩,农民生产积极性因此得以大大提高。此外,针对工业和商业放款也是采取加工订货,将来以货还本的办法。这种完全隔离通胀的折实制度使農、工、商形成了对物资生产经贸的稳定预期,不仅促进了生产发展,而且也使银行能够保本增值。大生产运动为夺取抗战的胜利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红色金融成熟期(1944-1949)
1.汇兑本位换锚物资本位。1943年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边区政治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5月份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致使边区政府不得不大批量蓄备物资备战,使得边区出现明显的贸易入超。窘迫的财政使边区只能通过发行边钞来弥补巨额开支,而这些陡然增发的边币却缺乏足够的法币作为发行准备,这必然造成通货膨胀。
为了巩固边币币值,防止其贬值过快,1944年5月,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以盐、农产品等物资作为发行准备,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流通券发行后,因市场信誉良好而逐渐取代边币成为边区通货。这种一不用新发行边币,二不用提高边币牌价,三还可以驱逐法币的货币实践,本质上是实现了边币的货币换锚,使货币最终回归到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属性。
2.政权更迭完成货币统一。日本战败后,其伪币体系也随之崩塌。1944年西方主导国家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客观上无法为国民党提供大额外汇援助,而彼时国民政府因为没有完整货币主权,也难以进行货币换锚,直至1948年的金圆券改革失败,标志着国民党财政金融体系全面崩溃。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分散的各解放区迅速连成一片,为适应全国解放形势的发展,亟需一种统一的货币替代原来各解放区的货币。1948年末,西北农民银行、华北银行和北海银行发起组建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人民币作为新中国的本位币,同时收兑各解放区货币。1949年6月,为统筹各解放区财经工作,中央军事委员会设立并领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各地军委会下设地方财委会,于是军队和国家资本紧密结合,保证了所有物资的统一调运,从而形成高度集中的财政制度结构。
3.举国之力解决恶性通胀。新政权相继解放各大城市后,由城市粮棉投机诱发的以人民币衡量的高通胀并没有得到根治,再次引发了中央高层对人民币发行问题的争论:一方认为物价上涨压力大,增发货币只会更加恶化通货膨胀,应该收缩货币发行;而另一方尽管承认货币增发是造成通胀的主因,但指出如果货币增发得当,可以促进生产恢复,吸收当前增发的货币,况且控制通胀的物资也需要增发人民币购买。最终,中央决定采纳后者的观点。
在经济基础方面,新政权直接担任市场主体,统筹使用财政、金融手段“定向做多”,避免资金再次进入投机领域。在上层建筑方面,新政权通过“三折实”建立物资本位制:折实储蓄对应银行体系;折实工资对应工资体系;折实公债对应财政体系,从而使人民形成了对储蓄、劳动和投资的稳定预期。
于是农民通过向公营商店出售物资来积攒储存人民币,从而降低了新增货币在市场上的流通速度,缓解了通胀压力。而公营商店雄厚的物资运销能力与财经委员会严密的组织体系相结合,使新政权能够统一调运全国资源、集中抛售物资,严厉打击了市场的投机倒把。此外,政府在百废待兴的经济环境下,利用集中收购的粮食物资通过以工代赈等方式在农民中进行再分配。由此人民币真正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新政权最终为人民币赋予实物信用。
三、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红色金融的历史经验
(一)军政实力保障货币的排他性
货币的价值尺度即是人们对于商品价值的量化标准,而这种量化标准是主观的、想象的,但是承载这一职能的货币材料是客观的、现实的,这也使得货币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分离成为可能。为了统一这种价值量化标准,就需要强制性力量来促成社会认同。纸币的出现就很好的印证了这种属性,纸币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差额就形成主权国家的铸币税收益。
当中共被迫长征时,原先发行的苏票在湘赣边区随之销声匿迹,之后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其先后发行的苏票、光华券、边币都可以在该地区正常流通。而抗战前期日伪在华势力的持续扩大和国民党阵地的不断失守也使伪币和法币的流通范围形成此起彼落的关系。这种军事政权与纸币发行之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反映出军政主权力量对纸币发行的排他性乃至独占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货币外生影响主权的独立性
在国民政府推出法币改革前,中国是银本位制度,这种外生于国内经济的金属本位制度具备三种属性:一是作为国际贸易中的清偿货币;二是作为国内流通的通货;三是作为金融体系的准备金。三种属性相互交织影响,于是1934年国际银价暴涨使国内白银纷纷流出,影响了国内的金融稳定和经济运行,所以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制实行汇兑本位制。
对于汇兑本位制,特里芬悖论揭示了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政策两难。同样地,对于以国际储备为基础发行货币的国家,也必然会陷入货币发行的二律背反:当该国长期处于入超地位无法持续获取外汇作为本币发行的准备时,必然会导致本币缺乏“坚实”的信用基础;而当一国长期处于出超地位得以持续获取外汇时,则意味着向储备货币发行国“进贡”大量实际物资。
(三)物资本位体现人民的主体性
人类最初的贸易是换货贸易,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使商品流通更加顺畅,一般等价物应运而生,商品流通表现为一般等价物的运动。而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典型代表,其流通速度也只是商品转手速度的结果,而非反过来。因此,货币的流通应服务于商品经济的流通。
中共推行的土地政策完成了几乎全体农民的政治动员,并在农村地区构建起严密的组织体系,从而以革命的名义从农村征购物资,为党建、征兵、发展生产等工作提供坚强后盾。边区银行在没有贵金属、外汇等发行准备的条件下,根据物资储备来进行相应的货币投放,本质上恰恰是回归了“货币运动适应商品流通”的货币属性。这种由我国劳动人民产出所内生性决定的货币发行制度,根本区别于贵金属本位和汇兑本位制,使人民币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的货币”。
四、启示
现如今我国城市大量金融资本过剩形成资本溢出的动力,与之相对比的是我国传统乡村地区却仍然面临着流动性短缺危机,如同改革开放前西方主导国家与中国之间形成的经济势能一样,城乡之间尽管出现了金融资本的结构性不平衡,但也积累了较高的要素落差。只有打破城乡要素流通阻碍,挖掘乡村经济增长潜力,缩小城乡之间贫富差距,提高广大基层劳动人民的收入,振兴乡村扩大内需,才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注释:
①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49.
②梁洁.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J].中国钱币:2005(4):58-61.
③范军.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版活动研究综述[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8.
④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15.
⑤郭本意.全面抗战时期山东地区国共铸币权之争[J].抗日战争研究:2018(4):50.
⑥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陕甘宁边区金融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101.
⑦“就边币发行方面,谢觉哉等认为银行要限制性发行,而部分人坚持有政府的支持,边币可继续增发”耿磊.朱理治与1941—1942年陕甘宁边区银行[J].史学月刊:2015(6):87-97.
⑧据曹菊如回忆,“对边币究竟是稳定在边、法币比价上还是稳定在物价上,又成为财经工作者的议论中心意见纷纭,其说不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曹菊如文稿[M].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59.
⑨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陕甘宁边区金融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101.
⑩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党委宣传部.红色金融的不懈开拓者——陕甘宁边区银行第二任行长朱理治[J].金融博览,2019(20):93.
?高翠.陕甘宁边区货币政策研究[J].中国钱币,2013(5):
59-71.
参考文献:
[1]王同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建设[J].中共党史研究:1990(3):53-62.
[2] 耿磊.朱理治与1941—1942年陕甘宁边区银行[J].史学月刊:2015(6):87-97.
[3] 黄正林.边钞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事业—边钞问题研究之一[J].代史研究:1999(2):192-206.
[4] 谢月华.革命时期红色货币比价管理实践与启示[J].华北金融,2020(3):86-94.
[5] 张燚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中共晋察冀边币的应对与处理[J].抗日战争研究:2014(2):58-79.
[6] 汪澄清.货币之战:论抗日根据地的金融稳定政策[J].中共党史研究:2005(6):42-47.
[7] 陈新余.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述评[J].中国钱币:2002(4):7-11.
[8] 吴景平.蒋介石与1935年法币政策的决策与实施[J].江海学刊:2011(2):148-157.
[9] 郭秀清,杨晓冬.对1935年国民党币制改革的反思[J].学海:2002(2):130-134.
[10] 汪澄清.论抗日根据地的金融稳定政策[J].中共党史研究:2005(6):40-45.
[1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39.
[12]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49.
[13] 冷泠.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J].党史文苑:2020(8):64.
[14] 王卫斌.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J].理财:2010(3):38.
[15] 梁洁.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J].中国钱币:2005(4):58-61.
[16] 范军.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版活动研究综述[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8.
[17]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15.
[18] 万立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及成因[J].江苏社会科学:2015(5):215.
[19] 郭本意.全面抗战时期山东地区国共铸币权之争[J].抗日战争研究:2018(4):50.
[20]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曹菊如文稿[M].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59.
[21] 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陕甘宁边区金融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101.
[22] 陈俊岐.延安时期中直机关财会工作的回顾[J].会计研究,1983(12):7.
[23]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党委宣传部.红色金融的不懈开拓者——陕甘宁边区银行第二任行长朱理治[J].金融博览,2019(20):93.
[24]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1):166-172.
[25] 高翠.陕甘宁边区货币政策研究[J].中国钱币,2013(5):59-71.
[26] 李建國.试论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与反通货膨胀措施[J].抗日战争研究,2007(2):157-174.
[27] 朱绍文.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对我国东北的经济掠夺(1931—1945年)(续)[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4):92.
[28] 马克思.资本论:卷一[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87.
[29] 温铁军.土地改革与新中国主权货币的建立[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4):16-42.
[30] 马克思.资本论:卷三[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610.
作者单位:杨昌儒,湖南科技大学,金融硕士在读;王俊,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博士,副教授。